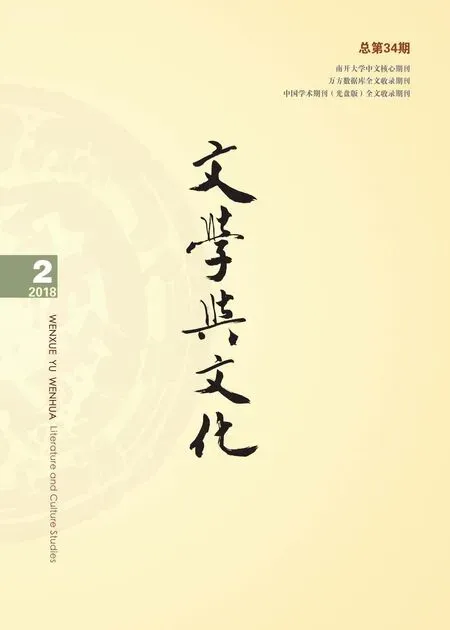戒律与计时
——以唐代一行法师为中心*
2018-11-13湛如
湛 如
内容提要:唐代人才辈出,一行以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为佛教与科技的关系提供一个样本,本文以此为基点,进行一些探讨。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考察一行之前,佛教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积累;其次是从一行的师承探究其学历法的动机;最后是从僧人修持角度看待计时方法的意义,同时考察一行制历的目的,以期能对“释门制历”这一事件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引 言
自白马东来,佛教为中国带来众多改变,众多科技经过发展后硕果累累,有撰写《寒食散对疗》等医疗书籍的个人努力,也有为传播经典发展印刷术的团体贡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古代佛教与科技的良性关系值得深究与借鉴,因此本文选择一行作为研究对象。一行在佛教方面贡献颇多,曾经参与过翻译佛典,还撰写过众多经文注疏。本文拟讨论的重点是其参与国家历法制定之事。“释门制历”是当时的政治需求,还是佛教科技的体现。已有的研究中,1963年日本长部和雄的著作《一行禅师之研究》,以密宗为中心,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1984年,严敦杰以一行的天文工作为侧重,清晰地展现一行的一生,写成《一行禅师年谱》一文;2009年,吴慧在《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中,以一行的经历及其在天文和佛教上的工作,结合盛唐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使得本文能进一步研究一行参与制定历法的原因。
一 沙门与天文历法
古人认为,帝王“受命于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天子的德行息息相关,因此历法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制定历法是国家最高天文机构的常规工作之一。开元十三年(725),一行未获得与天文相关的职位,以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编制《开元大衍历》,甚至连太史监南宫说也为其制历服务。对“释门制历”现象,吴慧在其《僧一行研究——盛唐的天文、佛教与政治》一文中明确提出,“释门制历”起决定作用的,是开元初年玄宗的政治主张和文化选择。该结论可以解释一行为何被选择为制历之人,却无法厘清一行如何在众多的历法家中脱颖而出。开元六年,瞿昙悉达已经参与到历法的制定中,以此而言,天竺僧人瞿昙家族比一行更有资格入选,即使一行的算法高明,也只能做为参与者出现。此外《宋高僧传》说其“深达毗尼”,《佛遗教经》中明确说明“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皆所不应”。一个严守戒律的人,为何会违背佛教的戒律精神去学习阴阳谶纬之学,因此“释门制历”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究。
一行参与历法的制定并非偶然,在一行之前,佛教已有大量关于天文历算方面的积累,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包含大量天文学知识经典的译出,其中《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摩登伽经》、《时非时经》、《大方等大集经》等经典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如《摩登伽经》中就有大量星象学和时间计算内容。另一方面,来华的高僧带来大量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安息人安世高不仅是译经第一人,并且精通天文,“七耀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他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印度的医术星相带入中国,此后西域来华僧人层出不穷,大多都具有深厚的天文知识,以《梁高僧传》为例,其中记载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识运变,莫不该综”,康僧会不仅“明解三藏”,而且“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鸠摩罗什“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求那跋陀罗“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呪术,靡不该博”。这些高僧掌握各种天文知识,通过译经、教学等方式,在僧人当中代代相传,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
此外,《隋书·经籍志三》中还著录有一些关于印度天文知识的典籍: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经》一卷
印度天文学著作,大多由佛教僧人翻译,如《婆罗门天文经》就是由达摩流支翻译。各种典籍的完善,以及佛门内部的传承,为一行参与制定历法提供了深厚的背景。
二 戒律与历法推算
一行对政治并不热衷,对教派之争也不加留意,玄宗会选择他,与其算法高明关系密切。据长部和雄的研究,一行曾向学于道士尹崇、具体姓名无可考辨的天台山国清寺布算僧人,禅宗的普寂禅师、律宗的弘景禅师、玉泉天台系的惠真禅师、玉泉天台系的道一禅师、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等八名高学。这八人中,与算学有关的是国清寺无名僧人。《旧唐书·方伎传》中载一行求学无名僧人的动机是“求访师资,以穷大衍”,《宋高僧传》则说是喜欢“阴阳谶纬之学”,大衍、阴阳谶纬之学都包含有历法,一行向无名僧人求学的是历法无疑。
在此之前,一行在当阳山学律,从学的律师是当阳惠真,学完历法之后,一行又回到当阳山学律。一行学律中途转学历法原因何在?《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中记有惠真生平,中有一事耐人寻味,惠真从义净三藏手中获得律本,仔细学习后,提出“始以五月十六日结夏安居”,众僧惊诧莫名,至善无畏三藏到达,指出“迦利底迦星合时”才是正确的安居时间。惠真自学戒律,推算出结夏安居的时间并非固定,而是要根据星辰变化决定,获得善无畏首肯,这样的做法在戒律中并非错误。除结夏之外,还有众多有时间要求的戒律,如诵戒、蓄物等都涉及计时问题。这些时间的细则,惠真作为一代高僧,自然不会无视。他从义净三藏手中获得律本,义净三藏重视计时的态度自然也会影响惠真,才出现惠真计算结夏安居时间的事件。
计算历法在唐代是研究戒律必备之学,另外一个例证是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认为祇园精舍有一座“天下阴阳院”,可见其认为历法是必备技能之一。在其撰写《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之时已经注意到印度历法与中国历法的差别。宋人元照在为道宣的疏文做注时,更详细阐释了两者的差别,明确指出:
如佛法春分,以腊月十六日为始者,须准阴阳历家。大寒是十二月中气,如是类例,十六日便为立春,克定步数,可知时分,故僧祇中令作脚影,此即是也,多论昼夜各分九时,僧祇日夕三十须臾,唐国晷漏箭为百刻。
但因他本人对历法不够精通,只能是无奈地说“须准阴阳历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指出印度人须学五明,其中工巧明包含“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义净文中盛赞:“故西国相传云,观水观时是曰律师矣。”可见计算历法对于当时的印度高僧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许多来自印度的高僧也证明这一点,如一行曾参学过的善无畏应也是精通历法之人,在《开元释教录》中赞他“艺术技能无所不谙”,并且曾经对惠真所推算的结夏时间做出过评判,一行的另一位恩师金刚智,其父精通五明,家学渊源之下,精通历法也是理所当然。此外,同时代的菩提流支也是“阴阳历数”了如指掌。
善无畏于开元四年到达长安,路过当阳的日期应在在此前。一行开元二年前往国清寺求学历法,他的历法最初应是跟惠真学习,觉得有所不足才出外参学。惠真所学历法内容不清,碑记中记载其称呼火星为“迦利底迦星”,据此而言,其所学应是印度历法。一行在《大日经义记》卷三中提及“西方历法”并解释印度历中的大月小月和定朔法的设定,介绍昼夜六十时、二十七宿、九曜的含义,可见其对印度历法有过深入学习。开元二十一年,南宫说、瞿昙譔等人联名上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新唐书》认为起因是瞿昙譔“怨不得预改历事”,测算结果是《大衍历》优于《九执历》。以此反推,一行最初从惠真学习印度历法,或与惠真推算结夏日期有关,觉得有所不足,因此又前往国清寺从无名僧人求学。惠真是天台玉泉系,与天台发源地天台山关系密切,一行的这次参学,应是目的明确的一次出行。因此他对天文历法态度,绝非《高僧传》所说喜好阴阳谶纬之学,在《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四中,一行自述对历法的态度是为了“顺彼情机”,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一行最终学贯中印,测算出《大衍历》。《大衍历》的一大创新是打破传统历法关于晷长、漏刻和日食等的推算仅限于某一地点有效的局面,大胆尝试使历法适用全国各地,这与文中分析其学历法目的,计算出与佛教戒律相符的历法一致。
综上所述,一行学习历法,有两重目的,一是深研戒律,二是认为这是顺应众生需求的一种方便法门,能让众生知道佛的智慧无量无边,世间出世间都具足。
三 持戒与刻漏记时
持戒过程中,涉及很多具体细节的操作,尤其是关于时间的问题,“非时”而作,便是犯戒。最著名的是“非时食”戒,《摩诃僧祇律》中说“非时者,若时过如发瞬、若草叶,过是名非时”,在明朝弘赞的《四分律名义标释》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并且明确指出,每年春秋分要重新量定时间,并且因为地理差异,每个地方采用当地时间计算。除日影法测算时间之外,还有前文提及的刻漏法。义净三藏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若能奏请置之,深是僧家要事”,认为把握刻漏记时是出家人的一件大事。所以除测算年月的计时外,佛教还追求更细致的计时方式。在这种需求下,一行经改进制作出“浑天铜仪”。
浑天仪始创于西汉,东汉张衡改为漏水推动,此后历朝历代屡次改进,至唐代,一行与梁令瓒等人再次进行改进。《旧唐书·天文志》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浑天铜仪具有自动报时功能,该功能并非一行首创,在典籍记载中早有此事。宋人的《乐邦文稿》中提及,慧远弟子曾经制作过十二叶木莲花,中间藏有机关,一个时辰折一叶,被人称为莲花漏。唐人神清赞其“晷景无差”,并在夹注部分指出慧要擅长机关,曾做木鸟能飞数百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印度的计时方法是漏水,铜碗底部开小孔放置在铜盆内,水漏满之后下沉,一碗即一鼓,四碗成一时,昼夜共八时。中国将一木分为百份,竖放于铜盆中,滴水渐满,借助浮力将木头浮出,上刻十二兽作为十二时辰标志。来自印度的计时方法给中国的计时带来了冲击,佛教僧人为了使自己的修行能够更精准,结合印度计漏刻对中国漏刻进行改良,莲花漏已经具有每个时辰自动报时的功效。
此莲花漏在唐代开始传入民间,《唐语林校正》中载: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沈。每昼夜十二沈,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
灵澈也是著名的律僧,著有《律宗源引》二十卷,他得到莲花漏之事,在一行圆寂后大约半个世纪,因此莲花漏应从东晋开始一直在寺院之中使用。在稍晚的九世纪,唐诗中出现了许多与莲花漏有关的诗句,最具代表性的是皮日休的《奉和鲁望同游北禅院》,诗载:“吟多几转莲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这首诗说明当时的禅院坐禅之时,用莲花漏计时,并且根据其计时功能进行焚香等宗教祭祀。一行的师承中,普寂、弘景皆是当时著名禅师,因此对禅院中的莲花漏有过密切接触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关于莲花漏的造型,现在已经不得而考,宋人燕肃对莲花漏进行改造,做出了更精密的莲华漏,在《青箱杂记》中说,它将原来百刻浮木分为四份,每份二十五刻,有六十四面,百刻分为千分。以此反窥,可见当时佛门的莲花漏优于普通的漏刻。到明代崇祯十一年,皇宫中为了供佛制作出更精妙的漏刻,供佛的佛龛藏在漏壶中,时间到自动浮出水面,并且能自动击钟鼓报时,与一行建造的浑天铜仪大同小异。
唐之前,佛教传来的大量典籍为“释门制历”一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僧人为了持戒修行,从东晋开始就不断将印度与中国的计时方法整合改进,进行巧妙构思,制造出更精美准确的计时器,为一行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基础,改良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
后论
一行以民间沙门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历法的制定,与佛教从传入中国后,将印度与中国的历法融合关系密切。许多传自印度的历法到中国后不适用,引发种种错误,僧团需要统一的时间以方便行持戒律,急需有人修正历法,此时,义净三藏将印度取回的书籍赠送给惠真,一行承学于惠真得到印度历法的传承,又远赴天台山学习中国历法,集二者于一身,为后来的《大衍历》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计时仪器上,自东晋慧远开始,佛门莲花漏盛行于世,一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作出具有自动报时功能的浑天铜仪,为佛门的持戒修行提供了具体的计时方法。以此而言,佛教不管从教义,或者从修持上,都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