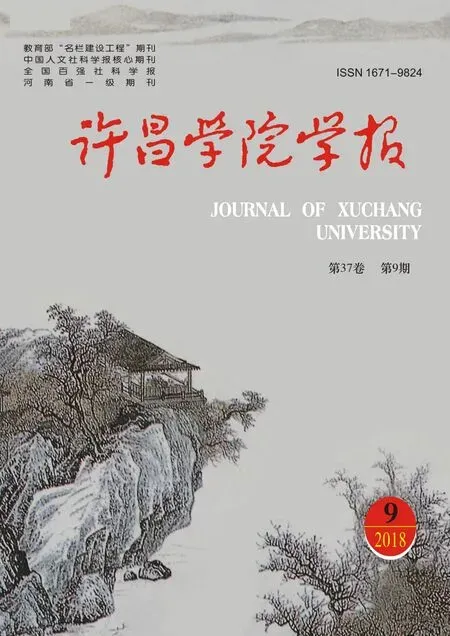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贡品问题探究
2018-10-12刘春香
刘 春 香
(许昌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贡品”指古代臣民或属国贡献给帝王的物品。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其多为全国各地或品质优秀、或稀缺珍罕、或享有盛誉、或寓意吉祥的极品和精华。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贡品文化,包括制度、礼仪、生产技艺、传承方式、民间传说故事等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贡品,自然会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贡品文化。本文主要从该时期的进贡与受贡者、所贡之物、进贡目的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贡品问题进行探讨。
一、进贡及受贡者
(一)地方政府及官吏贡献
在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中,凡一方之土特产,尤其是其中最新最好的,即一地“所生异物”向朝廷交纳,供皇族使用,称之为贡赋。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臣民进贡之事多见于史册。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司马懿献白鹿:“四年,获白鹿,献之。”[1]9司马懿获得灵瑞之物白鹿,不敢自己占有,向曹氏进献以表示效忠。北魏太宗永兴四年(412)九月,“建兴郡献白鹿”[2]2927-2928。北魏明元帝泰常元年(416)“定州献白兔”[2]2927。北魏高祖太和二年(478)十一月,“徐州献黑狐。周成王时,治致太平而黑狐见”[2]2928。统治者治国有方、天下太平才会有黑狐出现,是祥瑞之兆。太和三年(479)九月,“齐州献嘉禾”。太和五年(481)八月,“常山献嘉禾”[2]2938-2940。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四月,“兗州献白狐”,北魏肃宗正光三年(522)五月,“东郡献三足乌。颍川郡许昌献三足乌。肆州献三足乌”[2]2934。世祖延和三年(434)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高宗和平三年(462)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僚咸曰:‘神明所授,非人为也。’诏天下大酺三日”。高祖承明元年(476)八月,“上谷郡民献玉印,上有蛟龙文”。太和元年(477)三月,“武川镇献玉印,青质素文,其文曰‘太昌’”[2]2956-2957。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宁州献虎魄枕:“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3]63宋武帝生活节俭,得知地方所献的虎魄枕具有药用价值,即分给出征的将领用以治疗创伤。
(二)百姓贡献

地方政府、官吏及百姓所献主要是一些龟、白鹿、白虎、白獐、白雀、甘露、嘉禾、玉印等灵征祥瑞及珍稀之物。古代人们认为,当国家兴盛、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之时,上天会降祥瑞以示褒奖,如北魏世祖始光四年(427)六月,“甘露降于太学。王者德至,天和气盛则降。又王者敬老,则柏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2]2938-2939。太祖天兴三年(400)四月,“有木连理,生于代郡天门关之路左。王者德泽纯洽,八方为一则生”[2]2958。北魏世宗正始二年(505)九月,“后军将军尔朱新兴献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2]2931。因此,祥瑞之物的出现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每逢此时,国家会有大举措,例如,借助祥瑞之物出现进行大赦、改元、迁都。北魏肃宗神龟元年(518)二月,“获龟于九龙殿灵芝池,大赦改元”。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兗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年”。“魏氏世居幽朔,至献帝世,有神人言应南迁,于是传位于子圣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绝,仍欲止焉。复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积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2]2927-2928。正是由于形似马声类牛的神兽引导,拓跋氏才 历经“九难八阻”[2]2南迁蒙古高原,进而据有匈奴故地而逐渐强大起来。
(三)周边国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与周边国的关系基本上因朝贡和册封作为媒介而缔结,周边国立足于本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向中国皇帝朝贡,朝贡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为阻止对方入侵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而进行的先行性朝贡,有的是利用中国皇帝的政治权威或接受中国方面的先进文化而展开的朝贡。如魏文帝黄初七年(226),昆明国贡漱金鸟:“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5]魏明帝青龙四年(236),肃慎氏献楛矢:“五月……丁巳,肃慎氏献楛矢。”[4]107魏齐王正始元年(240),倭国贡大句珠:“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4]858魏齐王正始四年(243),倭王献丹木:“其四年,倭王……上献丹木。”同年,倭王献短弓矢:“其四年,倭王复遣使上献短弓矢。”[4]857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夏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1]37。”魏元帝景元三年(262),肃慎贡弓箭、铠、貂皮:“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4]149吴国地处沿海,与南洋诸国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互通使臣和进行贸易往来,如吴大帝赤乌六年(243),扶南王献乐人:“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4]1145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扶南、林邑来献:“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1]58晋武帝太康年间,大秦贡献:“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1]2544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琏(高句骊王高琏)每岁遣使。……世祖孝建二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哀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三年,又献肃慎氏楛矢石砮”[3]2393。
对于周边国的朝贡,中原王朝统治者作为答谢礼为派遣国的首领封王号或官爵,以此来赋予其政治权力,周边国的朝贡次数、密度受双方实力、亲疏关系及外部环境影响。如南北朝时期,东南亚各国对南朝的进贡有时是一年一贡,有时是一年多贡,有时是数国同贡。如盘盘国于“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稽首问讯。今奉薄献,愿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534)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6]793。”齐武帝永明二年(484),扶南王(今柬埔寨)朅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问讯奉贡:“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琉璃苏鉝二口,瑇瑁槟榔柈一枚。”[7]1016还有其他土特产。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扶南国)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并修书给梁武帝要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瑞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6]547-548。”另有狮子国(地在斯里兰卡)、婆利国(地在加里曼丹)、盘盘国(地在泰国)、丹丹国(地在马来亚)等国进贡大佛珠、佛像、浮图。东南亚诸国不厌其烦地向南朝政权奉表称臣进贡,主要原因是立足于本国政治上的利害关系,通过对南朝政权的政治认同寻求自身利益。
二、所贡之物
此时的贡品主要是一些稀缺之物、祥瑞之物、地方特产等,有日常用物、赏玩之物、装饰之物等。
(一)马匹、大象、骆驼等动物类
魏明帝太和五年(231),鲜卑贡名马:“夏四月,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兒禅诣幽州贡名马。”[4]98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康居国献善马:“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1]2544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大宛献汗血马:“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1]60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大宛贡汗血马:“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1]2544晋穆帝升平元年(357),扶南国献训象:“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6]789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高句骊献赭白马:“东夷高句骊国,今治汉之辽东郡。高句骊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3]2392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六月癸亥,林邑献驯象、白鹦鹉”[1]266。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林邑乞降,输生口、大象、金银、古贝等”[3]2264。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高句骊献马:“琏(高句骊王高琏)每岁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3]2393梁武帝天监五年(506),邓至国献黄耆、马匹:“(天监)五年,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马四匹。”[6]816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381),“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1]2904。北魏太武帝延和三年(434),蠕蠕(柔然)献马:“延和三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献马二千匹,世祖大悦,班赐甚厚。”[2]2294北魏太武帝正平元年(451),“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8]3221。在所献的动物类贡品中,马匹数量明显多于它物,大宛所献多是名贵的汗血马,可见,马在当时之重要程度。值得一提的是,高句丽在立国期间,朝贡是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程尼娜先生考证,从公元一世纪到五世纪,高句丽向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积极朝贡,朝贡的王朝和政权达十多个[9]663。仅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的朝贡次数就达154次[10]664,从高句丽贡马情况,也可知其养马业发展之迅速。
(二)祥瑞之物
进贡者所献的祥瑞之物主要有龟、白狐、九尾狐、五色狗、白鹿、一角兽、三足乌、白獐、嘉禾等。
白狐,在古代被认为是祥瑞之物,认为“王者仁智则至”,以《魏书·灵征志下》为例,关于地方贡献白狐的记载共有18次,“分别是抚冥1次,司州3次,河州1次,汲郡1次,兖州1次,相州1次,汾州2次,南青州2次,魏郡1次,瀛洲3次,幽州1次,西兖州1次”[11]154。可以推断出北魏时期白狐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等地。
嘉禾,是生长奇异的禾,异苗同穗或一颈多穗之禾,古代被认为是祥瑞之物,“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穗;于夏德,异本同秀”[11]154。《魏书·灵征志》记载了大量嘉禾出现的例子,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方水稻的种植技术在南北朝时期比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珍希之物
北魏太武帝延和三年(434),乐安王献玉玺:“世祖延和三年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2]2956晋孝武帝太元中,临邑贡金盘椀及金钲:“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金盘椀及金钲等物。”[1]2547晋安帝义熙初,狮子国献玉像:“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6]789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师子国送牙台像:“师子国,元嘉五年,……国王刹利摩诃……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又“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3]2384-2385。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呵罗单国治阇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钚、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3]2381。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芮芮(柔然)贡貂皮:“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师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7]1023齐武帝永明九年(491),林邑国献金簟:“永明九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7]1013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干陁利国“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6]795。所献金芙蓉即金质的莲花,佛家称佛祖乘莲花而坐,可见,金芙蓉为吉祥物。梁武帝天监初,大秦贡献:“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6]799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十二月,南康郡献瑞钟:“甲子,南康郡献瑞钟。”[12]89上述贡品在当时来说,均可称得上稀世之宝。
(四)锦、帛、布之类
在进贡的物品中,锦、帛、布之类亦占一定的比例,史籍中多有记载,兹举数例。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倭女王献班布:“景初二年六月,……献班布二匹二丈。”[4]857魏齐王正始四年(243),倭王献缣、锦、绵、帛:“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4]857魏齐王正始八年(247),倭国贡锦:“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4]858由此看来,三国时的魏与倭国来往频繁。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王公妃主献金帛:“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3]2349由于战事频起,自上而下纷纷捐款捐物以助国用。
三、进贡之目的
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进贡很难成为常态化,只是断断续续的贡和献,而且进贡之目的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联络人与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关系的手段,或者通过进贡形成一种归附关系,或者通过进贡形成一种政治认同。
(一)通过进贡联络人与人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关系
汉献帝延康元年(220)七月,“孙权遣使奉献”[4]60。孙权贡献目的在于拉近与曹魏之关系。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时,袁绍地广、兵多、粮足,手下战将谋士甚多,而曹操地狭、兵少、粮缺,从整体上看袁强曹弱,但具有政治眼光的钟繇却力挺曹操,对曹操给予大力支持,在紧要关头送马与曹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这对曹操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当时曹操就作书道谢:“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4]393钟繇的贡马之举,奠定了曹操与钟繇之间君臣相遇之关系,而后曹操视钟繇为肱股,究其起始,在于贡马。吴大帝嘉禾元年(232),辽东太守献貂马:“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籓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4]1136公孙渊献貂马与孙权,孙权加赠爵位给公孙渊,通过进献与赠爵,推进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刘渊献玉玺:“晋光熙元年,渊进据河东,克平阳、蒲坂,遂都平阳。晋永嘉二年,渊称帝,年号永凤。后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之玺也。得者因增‘渊海光’三字而献之,渊以为己瑞,号年为河瑞。”[2]2045
(二)通过进贡形成一种归附关系
汉献帝延康元年,比能献马:“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4]838轲比能是汉末三国时期鲜卑民族的杰出首领,他统率下的部众,战守有法,战斗力强大。自曹操北征后向曹氏进贡表示效忠,到魏文帝时比能受封附义王。汉献帝延康元年,素利等献马:“素利、弥加、厥机皆为大人,……延康初,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4]840魏文帝黄初三年(222)“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应劭汉书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4]79之后西域遂通,曹魏置戊己校尉进行管辖。魏文帝黄初四年(223),鲜卑献马:“文帝践阼,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4]836
(三)通过进贡形成臣属关系和政治认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并未隔断中原内地王朝与周边政权的联系。如当时的西域诸国一直与内地保持着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交往。曹魏、西晋与河西诸凉政权仍然在政治上实施着对西域局部地区的有效管辖和控制,西域诸国则以时断时续的朝贡等形式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
三国时期,由于曹魏政权占据中原并在名义上禅承汉祚,从而成为西域诸国朝贡的对象。“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4]840。元帝咸熙二年(265)“闰(九)月庚辰,康居、大宛献名马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4]154。曹魏对西域的经营规模虽不能与汉代相比,但这一时期的西域和中原的经济交往还是比较频繁的。
西晋建立后,积极经营西域,有效管理西域东部地区。但是随着西部鲜卑的崛起,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交通线一度被阻断,西域诸国与西晋王朝的联系亦因之时断时续,然而,一旦丝路交通畅通,西域诸国便纷纷向西晋遣使朝贡甚至“遣子入侍”,西晋则册封西域诸国王,借以宣示自己的宗主地位。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1]60。太康六年(285),“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1]2544。咸和五年(330)十二月,“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1]2747。
北魏立国之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拓跋氏始定中原,有司奏请通西域,目的是“振威德、致奇货”,因国力不逮而未能控制河西及西域,“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同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2]2259-2260。可见,中原王朝势力强大时,对周边国具有威慑作用,周边国自愿“称臣致贡”,双方之间的关系基本因册封和朝贡而缔结。
(四)通过进贡增进民族间的沟通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之间有数不清的纠葛,但在民族纠葛中也有交往,甚至也有友好的沟通。这一点,在贡品上也是有反映的。战乱中,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仍然以贡品为媒介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交往,甚至有时两个民族之间在交战的同时仍然有互贡关系。如后赵石勒五年前后,“秦州送白兽、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1]2747。秦州隶属石勒所建的后赵政权统治,当地的汉族父老向石勒贡献白兽、白鹿等物,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瑞物,以此上贡,表现了汉族父老对石勒所代表的匈奴族的友好情谊。
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虽然政治军事上处于对峙状态,但人员的往来与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却未曾中断,既有官方使臣的交聘,也有民间的往来,同时也有出于军事目的的各种有意识接触,而贡品常常作为双方交往的媒介。公元422年,南燕王慕容超,向南朝的宋武帝“献马千疋(匹)”[3]16。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实力远远强过偏安江南一隅的刘宋王朝,可拓跋氏曾多次向宋朝进贡猎白鹿、马、毡药等物,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贡猎白鹿马,“……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3]2348。可谓是情意殷殷。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拓跋焘贡骆驼名马:“焘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氈(毡)屋。……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3]2352
综上所述,通过贡品这一历史多棱镜,透射出了民族交融过程中的缤纷色彩,与各种看得见的实物贡品一同彼此通达的是看不见的精神涓流,思想、语言、文字等在看不见的相互的精神流动中,产生的效应不亚于物质对彼此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