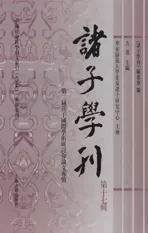從老子的“道法自然”到莊子的“法天貴真”
——審美“自然”論哲學依據的再認識
2018-09-06涂光社
涂光社
内容提要 老莊哲學在華夏民族思想文化的歷史演進中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老子》以“道法自然”表述了道家學説的核心理念,《莊子》中對此多層面的闡發可用“法天貴真”説概括。本文梳理《老》《莊》的“自然”論相關叙述,證之以歷代文藝評論祖述其説的言論及其範疇概念,宣示審美自然論對歷代追求“真”美的藝術創造所具有的爲其他思想流派難以企及的推動作用。文學藝術是體現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老莊自然論的積極影響可以作爲諸子之學成就輝煌傳統文化的一個例證。
[關鍵詞] 道法自然 法天貴真 素樸恬淡 虚静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老莊自然論原屬廣義的社會哲學,後來卻在審美和藝術領域得到最充分的闡揚和運用。西方美學也推崇真美,但對真美本質規律的探究遠不如老莊自然論深刻、充分。這與古人思考和理論建構的文化特徵相關聯。
老莊倡言“自然”。其後《管子》《韓非子》,及《淮南子》《論衡》中也用到這一概念,但義涵的側重點不盡一致,顯示出理解和運用方面的差異。漢魏六朝“自然”範疇現身於審美領域和文藝評論,在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的論説中都有重要地位。古代文學藝術所以成就輝煌,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常能獲得崇尚“自然”的理念和美學追求的有力推動。
《老子》中的“無爲”、“素樸”、“恬淡”、“無味”與其“自然”的意旨密切聯繫,《莊子》更以“法天貴真”的系列概念對“自然”範疇義的若干層面進行闡發和拓展,爲審美“自然”論提供充分、堅實的理論依據。
以文學評論爲例,若説唐人多直接運用“自然”、“天真”範疇概念的話,宋以後不僅擴大“自然”的運用範圍,又從“平淡”和“無味”、“無迹”、“巧拙”等方面進行拓展;宋話本和元曲、雜劇以及明清小説等“俗文學”樣式登上文壇,促進了對通俗文學“真”、“樸”、“凡俗”美學特徵的認識,明、清是驗證、辨識、匯總古代文藝實踐和理論成果的時期,在“貴真”、“童心”、“性靈”、“本色”、“化境”、“化工”諸説中對此前的“自然”論作了有價值的補正和闡揚、提升。
學界歷來不乏對老莊“自然”論的闡釋探討。本文概言元典“自然”要義,並對以往易被忽略的部分(包括解讀與“自然”論密切關聯的概念和“萬物並作,吾以觀復”等論),以及《莊子》對《老子》“自然”論多側面的闡發等方面進行補充。
一、 從老子的“道法自然”説起
“自然”中的“自”字原爲鼻的象形,是本我自指之義;“然”是如此、就這樣的意思。合成一個概念,其義爲本然和自然而然: 本然即原本如此的本真,自然而然指合乎客觀規律的運動演化。“自然”指自在、本然、自然而然,不矯飾、不造作、非人爲,也即不受人們主觀意識左右的客觀存在;既指自在之物(無論被人們感知與否的自然萬物),又指一切事物(包括人)生成消亡、發展變化、運動和表現的客觀規律。老子的“道法自然”表述了“自然”與“道”吻合,在藝術中“自然”是表現對象的本質、精神和真美之所在,也指表現上的自然而然,其核心是真樸與和諧化一。
“道非常道”即其義涵不可由言説作最終的邏輯規定,永遠在萬物之“自然”中不斷顯現。“自然”渾融模糊,其演化不會終結,對“道”的體驗也就不可窮盡。古代文人對萬事萬物之自然不求甚解,以“道”代指、無所不在的“自然”既是真實的,又神妙難測;既導引和制約一切,又是超越一切的。簡言之,是本原,是實質、真諦,也是規律。
“自然”的概念首見於《老子》(《道德經》),萬物之本然和自然而然是其基本意涵。“自然”包括本然(原本如此、客觀存在)以及運作和生成演化的自然而然(合乎自身規律)兩方面的意思。也可以説是存在與屬性的本然,以及運作演化規律的本然。《老子》有云: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
希言自然。(二十三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
就“自然”的範疇義而言,表述最爲全面貼切的是二十五章的一段。其中明謂此“物”“先天地生”可爲“天下母”,由於義涵“混成”(模糊渾融),無法確切表述,不知如何稱“名”,以“道”爲别名稱之,勉强以“大”名之。隨後的“法”是取法、效法之法。“域中四大”儘管皆“大”(都了不起),但其涵容有遞進的層級,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最高層級的“道法自然”表明“自然”就是地位至上、“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的“混成”之“物”。
説“字之曰道”,是因爲“道”畢竟是一種比況,而非對其學説核心理念嚴謹的邏輯規定。“道”原義爲路徑,能通達目標;出自“道”所比況的範疇義包含萬物運作殊途同歸的必由之徑,以及由此通達的至境。“自然”生成天地萬物,在永無止境的演化中不斷呈現。因此“道法自然”也是一個永不休止的過程,這也是《老子》一章稱“道可道,非常道”(“道”所況喻的意涵若能用語言作終結性的邏輯規定,那就不是恒常不變的“道”)的緣由。
“道”況喻由兩字組合成詞的“自然”,儘管未必盡善盡美,也較爲理想。表述上尚簡約的古代學者普遍認同“道”所取法、所喻指的“自然”學説的核心理念,則稱老莊爲道家就不足爲奇。
“道法自然”畢竟非“自然”範疇義的邏輯規定。老莊所謂“自然”常爲其某一側面義藴或功用的描述。
“自然”範疇在《老子》中並非特立獨行,其自然和自然而然的基本義涵更多時候是以與其通同的概念和理論話語(如“無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和“赤子德厚”、“虚無恬淡”以及“萬物並作,吾以觀復”之類)在不同層面進行闡釋和拓展的。《莊子》這方面所用的概念和話語更豐富多彩。
以下略述一些首見於《老子》,又在《莊子》得到闡揚的“自然”論言説:
《老子》四十五章云“大巧如拙”;十九章有“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三十七章的“不欲以静,天下將自正”;五十七章“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不僅“無爲”、“静”、“素樸”與“自然”有通同處,幾段話中的“自”皆自然而然之義)。《莊子·天地》則有:“明白入素,無爲復樸。”《刻意》有:“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於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應帝王》有:“雕琢復樸。”《山木》稱:“既雕既琢,復歸於樸。”
《老子》四十九章稱“聖人皆孩之”,五十五章有“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莊子·庚桑楚》亦云:“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倪,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是衛生之經已。”
《老子》明言“恬淡”、“淡乎其無味”的道方爲至境。三十一章反對戰争殺戮,稱:“恬淡爲上,勝而不美。”恬淡,清心寡欲之謂也。《老子》十二章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以聲、色、味這類人感官的感覺體驗比況社會政治生態,指出超過生命需求的享受會導致對生命的傷害,須理性地減棄。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王弼注云:“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悦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悦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娱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儘管不否認交織的五色、五音、五味能帶給人美的感受,卻不能如同“無味”和“淡味”那樣適“中”和“不可窮極”。《莊子·天道》稱:“夫虚静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胠篋》有:“釋夫恬淡無爲。”
《老子》六十三章稱:“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前一個“味”動用,是品味、體味的意思,其後的“無味”即指道的清虚恬淡。“味無味”也可以説是體味事物之本真——自然純素的質性,一種道家修養的恬淡無爲的境界。
老子對“道”的性狀多用渾沌模糊的詞語形容,其義涵的相關表述中常用“無”字,除上面已經叙及的以外,還有如下一些: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二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十一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十四章)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一章)
“法自然”的“道”作爲宇宙本體是渾成的,有“象”而無“形”(相對於具體的“物”而言,“道”是模糊的、涵容無限的“大象”),其義藴生生不息無法窮盡,不可能用邏輯的語言作終結性規定。這也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緣故。
此所謂“無”,並非一無所有(正如“無爲”不是無作爲,“無事”不是無所事事。“無爲”是没有背離自然法則的作爲,“無事”是不違“常道”的事務)。“無味”是謂弘深精妙的“道”(至道)全無那些尋常訴諸人感官的具體屬性,故以“淡”和“無味”稱之;“味無味”表明“道”的義涵可由人琢磨體味、逐步拓展深化。“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表明,“道”不可能得之於任何有違自然的人爲,不在人的感覺中呈現,只能尋味於體悟之中。
文學作品也能見到這類概念。李白詩:“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淡無味”就是對“道”的體味。南朝齊梁間丘遲《思賢賦》:“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南宋魏了翁《題跋》:“無味之味至味也。”凡此皆明確表述這一命題的意旨。
尤須補充説明的是: 道家學説的特點就是高度重視對事物本質和運作演化客觀規律的探循,在《老子》十六章一段未直接運用“自然”範疇的論證中,明確宣示了“道法自然”宗旨的一個重要側面:
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其意爲: 務必營造最佳的“虚静”精神狀態,從而能够考察萬物的本質和運動變化的規律;“觀其復”的“復”既指回復到“萬物”之根本,又指“萬物並作(運作)”重複回還出現的規律性。“命”指本性;“常”即常規、客觀規律。“知”(認知、瞭解)事物運作的常規,才能“明”取捨;明取捨、有包容才能公允無偏,才合乎指向與“自然”通同的“天”、“道”,“没身”(一輩子、永遠)不遭災害。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就是對萬物本質和客觀規律的考察,實爲“道法自然”認知上的一條重要途徑。
老子説:“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天道》對如何體認天地萬物作了進一步的解釋:“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静也。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静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虚静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本也,而道德之至也。……虚則静,静則動,動則得矣。”其後兼綜諸子的《荀子·解蔽》亦云:
心何以知?曰: 虚壹而静。心未嘗不臧(藏)也,然而有所謂虚;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虚壹而静,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虚,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静,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虚壹而静,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此爲“體道”必由“虚静”而致之説最透闢的解讀。莊子所謂“通於萬物”、爲“大匠取法”、其所“得”都指向本然和自然而然的“道”。
哲學中的“自然”範疇有深厚的美學涵藴。萬事萬物之本然(原本如此)和生成演化的自然而然,皆有鮮明的客觀性。本然的美即天成的本真之美;自然而然指合乎事物運作演化(包括藝術表現)的客觀規律,也是自如的、不受其他非本質因素干擾的運作和表現。兩方面的義涵都指向真。
二、 “法天貴真”: 莊子對“自然”範疇義的演繹
《老子》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漁父》的寓言中的“客”(漁父)則向孔子表述一通“法天貴真”的宏論,其所謂“法天”即與“法自然”通同;《天道》篇中也倡言“以虚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
《莊子》中除用一些寓言對“自然”範疇義作形象性的表述外,更以“法天貴真”的系列概念入論作了全面的闡發。
老莊“自然”論在審美領域的核心義涵是尚本真和合規律的藝術表現。不僅體現在“自然”、“天真”、“天成”、“樸拙”、“恬淡”、“天籟”、“本色”、“化工”、“童心”等範疇概念運用和相關言説中,其他範疇概念系列中也常能見其浸潤,如“無味”、“天趣”之類。
“自然”指萬有(一切事物)的本然和自然而然,包括人類社會以及與其相對應的、常以大自然代指的外部世界。與人類的思想行爲相比,大自然涵蓋面寬泛無際,運作演化客觀,能够給人以種種啓示、導向乃至生命精神的歸宿感。
《説文》云:“天,巔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古人意識中,天至高無上,有最大的涵容,籠蓋一切: 日月星辰、山嶽湖海、四時更替、風霜雨雪、動植衆生皆在其中,萬物的生存演化也聽命於天。以農立國的華夏民族,人們常以大自然代指的客觀世界爲“天”,“天人合一”是傳統“自然”觀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自然”初始義並不能與今所謂“自然界”和“大自然”完全畫等號,是天地萬物無干擾的(也即原生、自在、本然的也是合乎客觀規律的)生存狀態和運動演化方式。以此爲基礎,後來才指向大自然和自然界。山水描繪的自然和當代所謂“自然”多指大自然,而易被忽略的是範疇義的另一側面——順適客觀規律的自然而然。儘管兩者有内在聯繫。
老子説“道可道,非常道”,“道”永遠在自然萬物演進的不斷顯示中被體認。“道法自然”,自然的顯現無限豐富,其演化不會終結,道也就不可窮盡。古代學者認爲“自然”是不可能求得“甚解”的。自然萬物所藴含的無所不在的道,既是真實的,又是幽深莫測的;既是指導和制約一切的,又是超越一切的。簡言之,是本原,是實質,也是不可窮盡的規律和真諦。
(一) 通同“自然”的“天”與“真”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命題對自然論可謂居功至偉。“法”是效法,以爲法則。“道”是道家的最高範疇,“道法自然”除凸顯客觀規律制約一切的内涵以外,還由於“自然”是萬物之原創和演變的自然而然,表明“道”是一個没有止境的顯示過程,因此對於人而言“道”的體悟是一個在“自然”的啓示下不斷進展、不斷完善又不可窮盡的過程。老莊之所以被稱之道家,可以説是其“道法自然”的理念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
《莊子》沿用了“自然”的概念,如《德充符》中莊子對惠子説:“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天運》中黄帝稱:“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繕性》説:“古之人,在混芒之中……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田子方》中老聃曰:“無爲而才(才性)自然矣。”除《秋水》中的“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的“自然”是各因其自己所然而爲然(即自以爲是)的意思以外,都是强調無爲和自然而然。
《老子》説“道法自然”。莊子倡導“法天貴真”,其“法天”就是法“自然”。“法”就是效法,就是以爲規範!老子的“道法自然”與莊子的“法天貴真”指向的就是對萬事萬物之本然和自然而然的探尋和遵依。
“道法自然”表明道與“自然”的吻合。在藝術中“自然”是表現對象的本質精神、客觀屬性和美的所在;也指表現上的自然而然。“法天貴真”即以自然爲法則,表現上恪守事物的淳良天性,其核心是真樸與順適自然。
作爲核心理念,“自然”與老莊學説中許多範疇概念密切關聯,由“天”、“大”、“素”、“樸”、“適”、“迹”、“待”、“遊”等參與組合的話語,常常就是對“自然”範疇義某一側面的闡發,有的甚至本身就與“自然”通同,其論即“自然”論的一種延伸。莊子的“法天貴真”論可謂老子“自然”論的充分拓展。
《秋水》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所謂“天”,就是本然(自然天成)的意思;所謂“人”,即有違本然的人爲。此外,《刻意》有“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虚無恬淡,乃合天德”,“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無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故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等論。《達生》説梓慶削木爲鐻達到“以天合天”的至境。《天運》云:“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齊物論》則將“天籟”自鳴稱爲音樂之至境。諸説皆爲“自然”論的闡發。
自然環境中青天清虚、博大、弘深、幽遠,超然於世界大地之上,是日月星辰運行的無垠空間,有莫測的風雲變幻,不可窮盡也不知究裏,當然也不受人的意志制約;它提供芸芸衆生的生存條件,又能造成無法抗禦的災難,甚至毁滅一切,似乎主宰着萬物的命運。在人們心目中,天是至上的、威力無窮的、永恒神秘的,在各個民族歷史發展的早期幾乎都受到崇拜。有“天人合一”傳統觀念的中國更是如此,《尚書·泰誓》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論語》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屈原説“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且不説帝王認爲天是至高無上的神明,自稱天子代表上天對萬民進行統治;民衆也接受對天的崇拜信仰,家中供奉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指天爲證,祈禱天地者,史不絶書。《詩經》中記録有少女述情呼天明志之語,漢樂府的《上邪》亦然。在人們心中“天”既是至上的,也是最親近和最可仰賴、最可鑒證的。人們對天滿懷敬畏和親近,投入許許多多想象和情感。
“自然”較“天”抽象,“天”雖高遠無可窮盡,畢竟是切近、可感的存在,其引申義更易接受和理解。何況“天”頂戴於上,本有高高在上的心理優勢。
周代更多地以對天(儘管代指着主宰一切的神明、上帝)的崇拜取代殷商時代對鬼神的崇拜,在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仍然有重大意義。莊子之“天”雖與“自然”相通,畢竟凸顯了其天性授予者至高無上的地位。莊子更多地超越了政治,從生命意義的探求、人個體天性的維護、虚静心境的修養、精神桎梏(世俗的道義觀念、禮法成規)的破除,到對事物自然屬性和客觀規律的尊重,都進一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豐富了崇尚自然審美意識。於是,對後來文學藝術中主體意識的覺醒、對真(包括素樸和超越)美追求的强化,對藝術規律的探索和推崇都有重大意義。
與老子的“天法道,道法自然”相比,莊子的“天”就是“自然”,兩者同一而無間隔層次,也體現着道。
《莊子》中除篇名人名外用了644個“天”字,有天地、天下、青天、天子之類指稱,更多的是以“自然”之義組詞者,如天池、天籟、天鈞、天府、天理、天德、天樂、天行、天門、天災、天性、天壤、天機、天放、天年、天刑、天鬻、天光、天民、天成、天布、天和、天難、天倪……即使是天地、天子,也未必與“自然”無關聯,《刻意》的“恬淡寂寞虚無無爲,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質也”和《庚桑楚》所謂“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就是例子。
天和天地常與受人景仰的品格聯繫起來。《德充符》中仲尼説:“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天在地之上,似乎更側重道德智慧和精神的創造力和統馭力;而松柏雖有“冬夏青青”的堅貞品格,畢竟不是“萬物之首”而只是其中的一員。天地常代指自然萬物,在分開的時候往往又各有强調。頭頂上的天爲人們熟悉,對天的直接觀感就是至高無上、籠蓋一切的。
儘管老子有“道法自然”的論斷,以“天”代指“自然”或者將“天”與“道”、“自然”等同帶來了自然至上、規律至上、超越至上的理念。莊子常將“天”指代和等同“自然”,而且所用的“天”和由天參與組合的詞語基本與神明無涉,既是對老子“道法自然”學説的拓展,也是對西周以來“天”的理念的進一步更新和非宗教化。
文明的進程中會出現人性的異化,走入誤區。學術思想演進的動力來自批判。先秦出現諸子百家的學術争鳴,其思辨精神高揚、論辯水準躍升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對固有觀念、結論、規範、法則的質疑和批判、否定,反向思維取得的突破是普遍的。莊子的“天”論也有一系列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的高論:“天籟”是和的最高境界;天倪是以大自然爲模式的包容一切(是與非,彼與此,然與不然,可與不可)的和;素樸是修飾之極至(“既雕既琢,復歸於樸”);辯不若默;黄帝遺失“玄珠”,“知”(智識)、“離朱”(明察)、“喫詬”(巧辯)都找不到,而“罔象”(超經驗、超感覺、非邏輯的模糊把握)得之。《莊子》是那個時代批判哲學的代表,其“天”論可謂集反向思維之大成的自然論。
(二) 天 人 之 辨
老莊“自然”論的要義集於其天人之辨。
莊子的主導傾向誠然是出世的,但並非與政治不相干,不妨説是因由對政治的失望。《莊子》也有與老子“無爲而無不爲”一脈相承的東西,以“天德”論無爲就是很好的例子。《天地》説: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静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
其他篇中,《刻意》曰:“虚無恬惔,乃合天德。”《天道》説:“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土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虚無恬惔”的“天德”有無爲而治的意味。
《齊物論》有個不無諷喻之義的寓言:“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狙公給予芧的總量没有差異,只是分配手法略有變化,本來這種改變對狙毫無益處,衆狙前後卻有“怒”和“悦”的不同。以此比喻政治,受治於人的民衆或“怒”或“悦”没有意義,甚至是上當。聖人的治理其實不能改變自然賜予的多少,道其“是非”充其量是其調和矛盾的手段,一切只會在“天鈞”——自然的平衡和諧中協調統一起來。
老子的自然與無爲相通,與人爲相對立。這在《莊子》中得到闡揚,是其論“天”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常將無爲引申到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萬物的生成變化上,如《養生主》説: 老聃死,他的朋友秦失去弔喪,只號哭三聲就出來了。其弟子問這樣可以嗎?秦失回答,若像老人哭兒子,少年人哭母親,就是“遁天倍(背)情”;忘懷所稟受自然生命的長短(“忘其所受”)古人稱爲“遁天之刑”。秦失所謂“遁天倍情”指背離自然,違背真情;“遁天之刑”也指有悖自然而遭受的刑罰。同篇還有另一段對話:“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右師只有一隻腳(“介”),公文軒不知這是天生的還是人爲造成的,故驚問之。所謂“天”就是與“人”(即人爲)相對的天生、天成。又如:“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生。……故曰天地無爲也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至樂》)是把“天”(或“天地”)和“無爲”直接聯繫起來。《大宗師》指出,能够區别“天之所爲”和“人之所爲”是認識的至境,由此才能智慧地享受自然賦予的整個生命:“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德充符》云: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斫,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聖人的精神境界無須“知”、“約”(約束)、“德”、“工”(工藝)。不用謀劃何須智?“不斫”(無傷於自然)何須人爲約束?無所失於天性何須德?不做買賣何須商?有這四者就是受自然的“天養”,而不用人爲,就没有一般人的情和是非。屬於人爲的東西是渺小的,唯獨與天同體的聖人是偉大的。隨即又有惠子與莊子討論人究竟有無“情”的對話: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情”不是來自“天”,即非天性;是世俗之好惡影響下産生的可能“内傷其身”的繼生之情。“益生”是增益、人爲養成,意即並非自然天成。
《秋水》中説:“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這是區分“人”和“天”最直白的論斷。隨即説:“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這是强調對自然本性的維護和回歸。
然而莊子看來,人與天不僅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山木》篇借受困於陳蔡間的孔子之口説:“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無受天損易”是謂作爲人,本來就是整個自然運行參與者,生存、遭際和言行與自然合拍,不受其損傷容易。“無受人益難”謂世俗追求的爵禄之類,雖是自己本性以外的東西,欲辭卻難。郭象釋“無始而非卒也”云:“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對於“人與天一也”,孔子自己的解釋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是説産生“人爲”本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但人們不能保全自然是受性分所限,只有聖人的一生能够安然地體現出天人的合一。
《大宗師》指出:“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人間世》也説與“與人爲徒”不同的“與天爲徒”,是與自然作伴、交往的意思,爲超越世俗的活動。莊子以爲,天人原是合一的,不會因人們的主觀好惡而改變,在真人那裏天與人是不矛盾的。
莊子的天人之辨是自然無爲與人爲的論證,包藴着對客觀與主觀、永恒與短暫、博大與狹隘、超脱與拘滯等的思辨。
(三) 審美和思維創造領域的天論
《莊子》天論的意義並不高懸於哲學本體論的層面。精神的解脱和對政治的超越,個體生命、天性的維護,對客觀事物屬性和規律的尊重,都會深刻地影響審美的追求和創造。其論向若干層面拓展,有的與思維和藝術創造直接發生了聯繫。
1. 以天合天—天籟—天和—天倪
《達生》有“以天合天”之説: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削木爲鐻是一種工藝製作,雖然是寓言,卻直接描述了造藝上“疑神”(疑爲神工)的最高境界——“以天合天”,即以創作主體之“天”契合表現對象之“天”。這是創作主體對道本體的體認前提下的“合”,是自然生命的原創力得到完全維護基礎上的“合”,是擺脱世俗名利機巧干擾之“合”,是“忘我”——擺脱主觀感受、意識狹隘偏執之“合”。
古人最初多以調味和音樂的例子來比況和説明“和”的境界。《尚書》有“律和聲,八音克諧”之論,《國語》的“和”“同”之辯説“聲一無聽”、“味一無果”。大凡美味總是多種味道調和而成,而非單指五味之一;悦耳的音樂也由五音錯綜排比而非皆同一音響。善於“近取諸身”的古代論者於是就由此開始討論“和而不同”。可以説音樂是早期最爲重視“和”美的藝術門類。《齊物論》云: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籟”是孔竅及其發出的音響,人籟是人爲的,地籟相對於天籟是有限和具體的,只有天籟是自然生發和無人爲形迹的。莊子以“天籟”强調天然音響是音樂的至境,從此古代文學藝術批評有了“天籟自鳴”的語彙。《天道》有“人和”、“人樂”以及“天和”、“天樂”之論:

“和”分出了“人和”、“天和”的層次,而且“與天和者”是“大本大宗”,是與仁義、壽夭和機巧無涉的“天樂”。把“知天樂”與對自然生命的理解和通於天地萬物的天道聯繫起來,可以認爲莊子是反過來以音樂之和的層次來況喻人們對天道體認的層次。《天運》中黄帝説道自己製樂時亦云:“……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
天倪與天和、天鈞、天樂等概念組合,都體現出以大自然本身的和諧、均衡爲楷範的意藴。《齊物論》在前即云:“何謂和之以天倪?曰: 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寓言》介紹全書表述方式時對“天倪”有所論: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言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天倪”是自然本身的和諧。天地萬物總體上是平衡和諧的,由於在不停地運動變化,新的變數隨時出現,也隨時在協調整合,不斷由不平衡到實現新的平衡和諧。學術語言表述和形象描繪也應如此。《知北遊》曾直言“天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説,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一汝視”可致“天和”,説明調整、端正主體(即“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的忘我)的立場,以全面的無所偏執(也即“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恃”)的視角去考察、理解和表現,“天和”的境界就能够到達。
2. 天府—天倫—天機—天門—天守—天放
莊子以爲言辯是一種人爲。《天運》有“無言而心説(悦)”。《列禦寇》有段耐人尋味的話:“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至人,天而不人。”此似與禪宗的“不立文字”的“拈花微笑,以心傳心”相近。《齊物論》亦有可相印證發明處:“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能解“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的奥秘,也就擁有了無盡藏、取用不竭的“天府”。
《刻意》指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神”是内在的、本質的,與純粹素樸之道相通的是渾全的生命精神,故稱“合於天倫”,“天倫”者自然之理也。老子最早提出“見素抱樸”的主張,贊許過“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古樸社會。莊子説“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應帝王》),描述了“其民愚而樸”的建德之國(《山木》),以爲“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天道》)。
《天地》有子貢見抱甕丈人不用機械提水灌園而與之討論的故事。丈人説:“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機心”是與内在精神的“純白”背離,全德之人其心必“忘”功利機巧。
人爲的機巧有違自然,故不可取。《大宗師》中的許由和《天道》中的莊子,都曾讚歎其師“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天道》還有老子對士成綺的批評:“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所謂“機”與“知巧”都不是出於本性之真。
“天”論還涉及心理和思維層面。
從弓弩擊發裝置機栝引申出來的“機”是機巧之機,由於此類“機”是人爲,莊子論中的“機械”、“機事”、“機心”皆不可取。但“機”也常有機會、機緣方面的意思,指在瞬間或特定時空諸多因素湊集、巧合。當“機”與“天”連成一體的時候,其靈動就可寶貴了。《大宗師》説:“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是謂“真人”身心不受“嗜欲”干犯,葆有深固的天然慧根;世俗之人則不然。《天運》言及製樂時有曰:“……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説。”其“自然之命”近乎客觀規律。是謂以人爲的媒介和技巧製樂總是有局限的,“天樂”只能是無形迹的自然之和。《秋水》的寓言中百足之蟲蚿和無足之蛇的前進都爲“天機所動”,指無須主觀努力和意志左右的靈動自如。“機”有時指生命活力的勃發,慧根嶄露,要素的湊集、巧合,乃至鬼使神差出人意表的神機突現,如此則創意超凡,對道的體認和妙悟忽然而至。故後來有所謂玄機、禪機。
“天門”亦首見於《天運》。老子有云:“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謂自正者才能糾正他人,不能如此心靈就不能自由通達地活動,天門得開就可進入虚無逍遥的境界。《庚桑楚》也説到“天門”,仍與精神活動相關:“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能够出入天門,則可作精神無掛礙的遊履。
“忘”的境界能入於“天”。《庚桑楚》云:“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静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受到他人言語的侵害而不報復,“忘人”指不知世俗慣常情緒、態度和處理方式,故得稱“天人”。《天地》中老聃説:“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忘物”、“忘己”可謂精神境界上對外部世界和對自我的超越。
《達生》中説,至人之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栗”,“是純氣之守也”,“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純氣之守”和“天守”皆指天賦生命精神的自我營衛。隨後又説“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是“神全”所至,而“得全於天”的聖人也因“藏於天(渾全無損的天然),故莫之能傷也”。
對“天”的推崇並不忽略精神視野和思維的主觀控馭。《馬蹄》中“一而不黨,命曰天放”的“一”與《知北遊》被衣告誡齧缺的“一汝視”的“一”相同,是强調渾全、整體性。“不黨”是無偏;“天放”則是自然曠放。是一種對自我精神活動取向自然的把握。而《在宥》的“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表明,“神動而天隨”不只是“精神活動都合於自然”,依上下句的句法,“神動”與“天隨”是相對的,是謂有神妙的運作卻出於自然。
(四) 貴 真
《老子》感慨世俗“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十七章),以爲“智慧出,有大僞”(十八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體現出强烈的尚真意向。
《老子》的“真”與“道”和“德”有聯繫。當然這“道”與“德”不是儒家的倫理規範,是老莊的“道”本體及其體現。二十一章説:“道之爲物,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指出在“道”難明的幽深中有可信的“真(諦)”。四十一章説:“質真若渝。”是謂質達於純真卻好像污濁。五十四章的“修之於身,其德乃真”,是説以“善建”、“善抱”之理修身,“德”可達於“真”。
《老子》也有未直接用到“真”、“信”、“僞”而實爲尚“真”的議論,如讚美赤子嬰兒的渾樸、全神和天真,以爲“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五十五章)。儘管屢有所及,嚴格説在《老子》中“真”還只是“道”的一種屬性,是達“道”的表徵之一。莊子在其自然論中給予“真”更重要的地位,多層面地拓展了“真”的内涵,使其具有了更多的哲學和美學的意義。《齊物論》説:“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宰”與“真君”,本真的身心情感之主宰,以真心釋之也無不可。
老莊之“真”是天成之真,人爲矯飾則與之背離;其所指在内在本質,常有内外不一或隱而難辨的情況。
“真”出於天然。《馬蹄》中説:“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秋水》對於“天”與“人”的解釋中指出:“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 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反同返,“反其真”即回到“天”(自然、本然)的狀況,足見“真”、“天”有同一性。莊子以爲文明進程中的人爲使人出現異化,尤其是世俗汲汲於名利權勢的“日以心鬥”會背離“真”性。《山木》中有螳螂捕蟬、異鵲在後的寓言,道出“見利而忘其真”的危害。此處“真”就是本真之自我(包括自我的天性和真實處境)。其後莊周强調了異鵲“遊於栗林而忘真”對自己精神的震撼。《漁父》“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的警示出於同樣的理由,所以告誡人們“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天道》亦有“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真”是本質的,也是自然的。本然與“真”相通,故有“本真”一詞。《達生》中的一段話很有意義:“不厭其天,不忽其人,民幾乎以其真。”永不滿足在順適自然上的求索,不忽略作爲人的天性本能,就幾乎達於“真”的境界。看來“天”與“人”並非絶然對立,畢竟“人”也可以説是“天”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這裏的“人”不是有違自然的人爲,而是葆有自然本能和天性的人。此所謂“真”可以理解爲在合乎自然的前提下共性與個性的統一。
在古代中國,與“真”協調的是“誠”、“信”和“實”,與“真”相背離、對立的是“僞”、“詭”、“欺”、“詐”,乃至於“虚”、“誕”、“機”、“巧”。《周易·乾卦·文言》曰:“修辭立其誠。”《禮記·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荀子·樂記》要求“著誠去僞”。儒家也强調誠信,與老莊相比,他們的誠信更側重於善;老莊之誠信也自有其善的内涵,但更側重真。《人間世》云:“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人爲易僞,法天則真。《應帝王》中蒲衣子説王倪:“其知情信,其德甚真。”
“真”有時與“故”對立。《秋水》的“反其真”與“無以故滅命(命,指自然天性)”相聯繫。《知北遊》説:“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天下》又有“以重言爲真”,是謂“重言”令人信服。莊子聲明其“重言”不取於“陳人”。可見其“真”與“故”的不兼容似乎包含着這樣的意味: 批判和否定未能與時俱進、與“道”的不斷展示相適應的陳舊思維模式、故步自封的陳腐觀念。
《秋水》作了“無以人滅天”、“反其真”的呼吁,《漁父》更有一段名言: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禄禄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法天貴真”標舉“精誠之至”,倡導對自然天性的維護和回歸,説聖人“不拘於俗”和對“禄禄而受變於俗”的批評,矛頭所向是扭曲天性的禮義成法和一切造作、矯飾,更不用説欺詐、虚僞。與“誠”密切聯繫,是與人類主體、與主觀情感的聯繫。莊子這種“真”又是擺脱世俗關係、去我執、忘己(去“成心”、不“師心”)的“真”,是天成的、本質的、精神情感層面的“真”,所以可以説是超乎感官感知範圍、無關乎外在形態(哪怕無形或形殘)、不涉某些具體屬性的“真”。以“精誠之至”來釋其“真”,强調精誠才能動人,真情可以形成一種無形而强勁的感召力和震撼力。此論對於審美和藝術創造的積極影響不言而喻,幾乎是像對造藝者説的一樣。莊子所舉的例子全在感情方面,表明其“真”所追求的核心不在忠實於事物的客觀屬性,而在於主觀情感的率真至誠。
“真人”的稱謂首見於《莊子》,後來它被奉爲道教經典,所謂“真人”於是指修煉成功的得道者,莊周也列其中,以“南華真人”名號入了仙班。莊子的“真人”指的什麽人?爲何言其“真”?在討論“貴真”的時候是有必要探究的。
莊子推崇“天人”、“神人”、“聖人”、“至人”和“真人”。天、神、聖、至的意義不難理解,不離天生、神聖、高明至極一類意義,都是對超人所達境界的膜拜之詞,唯獨“真”明顯兼具美學的指向。
對“真人”介紹最集中的一段出自《大宗師》,其中有云: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知”唯(不受嗜欲干擾,“天機”深的)“真人”所能體認,故《刻意》有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真人”不輕視些微,不違忤少數,没有成功的驕矜,也不用謀慮,無所謂得失;他們在感覺、心理和情感欲求上都超越了常人,環境因素不會對他們構成傷害和威脅;他們没有違背“自然”“素樸”的嗜欲,没有世俗關係的干擾,充分地營衛和享受着智慧生命;他們順隨“自然”大化,不忘自己來自“自然”,不求以一己的意志改變生化的進程和結局。他們是“天人合一”的,知道“天”不需“人助”,“助”則適得其反。
結 語
“自然”範疇首見於《老子》,此後才在多家子書中出現。老子的“自然”範疇與萬物及其廣義的道、德相聯繫,意義側重“無爲”。主旨是順應事物的天性,使之不受人爲(人們主觀意志和行爲)干擾自然而然地運動演化,告誡執政者做到理想的治理——“無爲而無不爲”。
全面闡揚“自然”之要義使之成爲系統學説的是《莊子》。莊子多以“天”代指“自然”,全面拓展了尚自然的理論,並使之精緻化。
在各個民族歷史發展的早期,天幾乎都受到崇拜。有“天人合一”傳統觀念的中國更是如此。古人心中“天”既是至上的,也是最親近和最可仰賴、最可鑒證的。不過,天畢竟是自然的存在。周代更多地以對天(儘管代指着主宰一切的神明、上帝)的崇拜取代殷商時代對鬼神的崇拜,在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仍然有重大意義。莊子之“天”雖與“自然”相通,畢竟凸顯了其天性授予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其説更多地超越了政治,從生命意義的探求、人個體天性的維護、虚静心境的修養、精神桎梏(世俗的道義觀念、禮法成規)的破除,到對事物自然屬性和客觀規律的尊重,都進一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豐富了崇尚自然審美意識。於是,對後來文學藝術中主體意識的覺醒、對真美追求的强化,對藝術規律的探索和推崇都有重大意義。
與老子的“天法道,道法自然”相比,莊子的天就是自然,同一而無間隔層次,也體現着道。莊子常將“天”指代和等同“自然”,由天參與組合的詞語基本與神明無涉,既是對老子“道法自然”學説的拓展,也是對西周以來“天”的理念的進一步更新和非宗教化。“法天貴真”大抵可以看作是對老莊自然論宗旨的簡要概括。
老子的自然與無爲相通,與人爲相對立。這一點在《莊子》中得到充分闡揚,是其論“天”的核心和依據。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常將無爲引申到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萬物的生成變化上,天人之辨不僅是自然無爲與人爲的考論,也包藴着對客觀與主觀、永恒與短暫、博大與狹隘、超脱與拘滯等的思辨。
《莊子》主要是人生哲學,莊周認爲勘破人生是超越世俗觀念、獲得精神解脱的要務。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生死問題,就不可能享受智慧生命的快樂,解除對生老病死的憂懼。而這正是世俗庸人最大的誤區。美好的生命是完整的,應該“終其天年”,無塵俗干擾、無所憂懼,即智慧健康、天性無損、從容自在地暢遊生命。他主張不忘自己從自然而來,也不追求非自然的結局,情感也像四時節候的變化一樣自然。莊子重生有兩方面的追求: 時間上完全享受自然賦予的年壽,精神上自在逍遥擺脱世俗的桎梏和痛苦。
“天”之自然是本然和自然而然,體現着客觀屬性、規律,事物演化的趨勢和法則,也體現着“真”,人們理當順應之、維繫之。
《莊子》天論的意義並不限於哲學本體論的層面。精神桎梏的解脱和對政治的超越,對個體生命、天性的維護,對客觀事物屬性和規律的尊重,都與自然和諧、真美的追求以及藝術思維論有直接聯繫,也體現着一種精神和情感的取向。
人類在文明進程中會出現人性的異化,走入誤區。學術思想演進的動力來自批判。先秦出現諸子百家的學術争鳴,其思辨精神高揚、論辯水準躍升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對固有觀念、結論、規範、法則的質疑和批判、否定,反向思維取得的突破是普遍的。《老子》有“無爲而無不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類論斷。莊子也有一系列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的高論:“天籟”是和的最高境界;天倪是以大自然爲模式的包容一切(是與非,彼與此,然與不然,可與不可)的和;素樸是修飾之極至(“既雕既琢,復歸於樸”);辯不若默;黄帝遺失的玄珠“知”(智識)、“離朱”(明察)、“喫詬”(巧辯)都找不到,而“罔象”(超經驗、超感覺、非邏輯的模糊把握)得之。《莊子》可謂當時批判性最强的著作,其“天”論可謂集反向思維之大成。
老莊對於自然和“天”的推崇近乎極端,無爲、素樸之論似乎完全否定了人爲的修飾和形式美,卻是對正統、世俗美學的批判和補充。質疑了審美創造中陳舊、平庸的觀念、方式和標准,從反向開拓了思維空間,肯定了自由審美意識,從而啓示人們從膚淺走向深入,從表象走向本質,從因襲走向變異,導致更高層次美學規律的探求和揭示。
“天”和“真”作爲莊學的理論範疇完全“自然”化了,其論深入到哲學的本體論等若干領域和層面,卻没有真正的宗教和神學色彩。它倆不僅可以各自入論,而且可參與概念組合。“法天貴真”論的優勢正在於成系列的概念組合上。“法天貴真”(《漁父》)簡明地道出了道家自然論的宗旨。“法天”就是效法自然,以自然爲最高准繩;“貴真”就是追求真實、本色和至誠。“素”、“樸”、“純”、“白”與“天”、“真”相通,是道家崇尚自然天成和純樸本質的一些要素。
“天”在古代中國人意識中地位至高無上。瞭解這種心理的普遍性就不難認識莊子用“天”替代“自然”進行理論表述的用意。而以精誠、信、實去理解“真”,則能凸顯老莊自然論的另一要義,國人尚真的美學追求中倚重真情實感的特點。
在漢語中,單個的“天”或“真”比兩字的“自然”另組新詞更方便靈活,合乎漢語的詞以雙音節爲宜、爲美的規律,更有利於拓展、深化或凸顯某一層面的特殊意義,衍生出龐大的概念族群。《莊子》中就有天籟、天理、天年、天性、天和、天成、天倪等數十種;“真”也有“真性”、“真宰”、“真君”、“真人”等。“法天貴真”的論説比原來老子“自然”論展示的意藴更爲豐富、精緻,得其概念組合上的助益,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可見莊子以“天”與“真”參與的概念組合,建構了道家自然論和概念系列和理論框架。
人來自自然,也應當和必然回歸自然。自然是極至的精神歸宿;“天成”是造藝的化境,精誠之“真情”是動人所本。
“自然”論意指萬物之本然和人的天性,肯定合規律的演化和新變(包括在特定時空向對立方面轉化)的必然性;法“自然”永無終止,有無限的發展空間。《老子》哲學中“自然”不僅與“道”、“德”、“天”、“大”、“真”、“素樸”、“恬淡”等有所通同,也是藝術論許多範疇義和理論話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綜覽自唐以後的文學藝術理論批評不難發現,“自然”論系列的概念大都可以從《莊子》“法天貴真”之論中找到源頭和依據,如“天然”、“天真”、“純素”、“樸拙”、“平淡”、“天籟”、“無味”、“天成”、“本色”、“化工”等即然;其他,包括與佛學有所融通和默契的“羚羊掛角,無迹可尋”和“童心”説之類,也有莊子論“迹”與“真”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