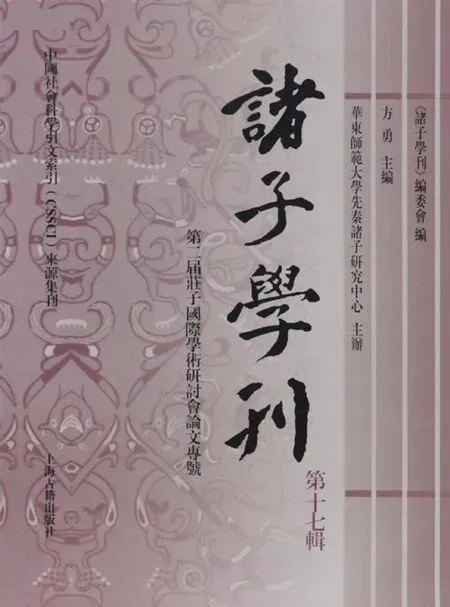散文化的詩與詩化的散文
——簡論《老子》與《莊子》的文學特質
2018-01-23湯漳平
湯漳平
内容提要 道家文化在我國兩千多年來所産生的巨大影響,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對道家著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有着許多争論。建國以後的數十年間,《中國文學史》的編著者極少談起老子。對莊子,在思想上既視其爲“没落的奴隸主階級的哲學家”,而其作品所表現出的浪漫的創作方法則被斥爲消極浪漫主義而大加撻伐。然而在文學藝術領域内,先秦諸子百家中唯有道家對文學所産生的影響最大、最深刻。道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從文學創作實踐、文學形式、文學内容、藝術風格等方面,可説是全方位地影響於中國文學。正是道家的深刻影響,使中國文學形成自己獨特的傳統和藝術品位,從而在世界文學史上顯示出特有的光彩。《老子》和《莊子》,這兩部道家創始人的經典之作,由於它們自身最具文學性,因而分别被後世稱之爲“散文化的詩”和“詩化的散文”。
[關鍵詞] 道家文化 《老子》 《莊子》 文學特質
由道家創始人老子和直接繼承者莊周所創立的道家文化,在我國兩千多年所産生的巨大影響,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對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有着許多争論。建國以後的數十年間,《中國文學史》的編著者極少談起老子。而對莊子,在思想上既視其爲“没落的奴隸主階級的哲學家”,而其作品所表現出的浪漫的創作方法,也被斥爲消極浪漫主義而大加撻伐。這種狀況直至上世紀末方才有所變化。這些其實是很不公平的。儘管爲統治者所提倡的儒學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然而在文學藝術領域内,先秦諸子百家中唯有道家對文學所産生的影響最大、最深刻。這一點,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早已指出,他説,諸子中“文采之美富者,實唯道家”。道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從文學創作實踐、文學形式、文學内容、藝術風格等,可説是全方位地影響於中國文學。正是道家的深刻影響,使中國文學形成自己獨特的傳統和藝術品位,從而在世界文學史上顯示其特有的光彩。《老子》和《莊子》,這兩部道家創始人的經典之作,由於它們自身最具文學性,因而分别被後世稱之爲“散文化的詩”和“詩化的散文”。
一、 《老子》——散文化的詩(一) 先秦詩歌中的鴻篇巨制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1)劉勰《文心雕龍·情采》。劉勰的這句話雖是談到文學作品的情采時説的,其實也可以概括中國古代的學術風貌。特别是在先秦時期,不論是文學、史學、哲學、教育等各方面的著作,同時也是很好的“文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學價值。
而《老子》,首先從它的表現形式而言,則是誰也難以否認的一部哲理詩,因而較之諸子的其他著作,更具有文學的特性。作者采用詩的形式,以簡潔的文字,流暢而富於音樂感的語言,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雖然大家對這一體系的完整性有不同的認識,但對它的文學特性的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儘管有的不把它稱爲“詩”,而説成是“簡括而有韻的理論文”。這也只是换一個説法而已。
從時代地位上看,《老子》可説是繼《詩經》之後,《楚辭》之前的一部重要詩作。我國學者一般都認爲,《詩經》反映的是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間的生活,最後成書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從這個時候起到屈原的作品問世,其間約經三百多年。這期間所保留下來的詩篇,確屬微乎其微。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僅散見於史書和諸子文章中引用的一些民謡、民歌,如《越人歌》《滄浪歌》《接輿歌》《飯牛歌》等。近年來,隨着大批先秦及漢代簡帛的出土,我們才看到數量不多的一些佚詩。正因爲如此,《老子》這部哲理詩就更加顯得可貴了,它真實地反映春秋戰國這一歷史時期知識分子的動向。在西周前期,周王室鼎盛,王朝的卿士們争做“頌”詩,以“美盛德之形容”。到了東周,王室開始衰微,階級鬥争日趨激烈,統治階級的文士們意識到這種狀況,因而“頌”詩消失了,代之以擔憂國家命運和對當權者不滿的諷諫之作,提出“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蕩》),用以警告當政者。《小雅》的大多數詩篇都是反映這種感情的。到了春秋末年,周王室已成朽木,大廈將傾,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這時士人爲瞭解決現實問題,諸子百家紛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2)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他們便利用各種語言形式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老子》哲理詩的出現,正是合乎規律的現象,我們不能認爲只有抒情詩才是詩,而把哲理詩排除出詩歌領域。其實,不僅是《老子》,戰國時期諸子的一些文章,有的很可以當作散文詩看,如莊子的《逍遥遊》、荀子的《天論》中的一些段落。至於荀子的《成相》篇,從内容到形式都可以看出直接受“老子”的影響。
《老子》的重要地位還表現在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鴻篇巨製。許多人在談到《老子》時,都説它篇幅不長,只有五千餘字。這實際上是把它當成哲學論文來對待了,而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不僅在先秦,就是在我國整部詩歌史上,也都可稱爲鴻篇巨製。在《詩經》裏最長的詩篇《閟宫》,全文共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字數不足五百。章數最多的是《桑柔》,也只有十六章一百一十二句,字數四百五十左右。屈原的《離騷》是大家公認的長篇詩歌,全文三百七十餘句,二千四百餘字。而《老子》卻長達八十一章五千餘字,這確實是相當可觀的了。這部哲理詩,同世界上其他民族同時期産生的哲理詩相比,無論從作品形式的美感,語言的表達,内容的豐富等方面,都可説是卓然獨步的。
作爲文學的形式,《老子》的出現,對我國文體學的發展也是大有貢獻的,因爲它豐富了詩的形式和内容,開創了用歌謡形式宣傳道理這種新文體。這種文體一直爲後代所沿用,《老子》在這方面的首創之功是不能抹殺的。當然,用韻文的形式來宣傳哲理,並非自《老子》始,早在我國古代哲學典籍《易》中,已經有了一些簡短的韻文,作爲卦、爻象解釋的繇辭,但還難以稱之爲真正的詩。而《老子》則確實是具有完整哲學體系的哲理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子》在我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還在於,它是春秋戰國時代我國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結合的産物。不少人認爲老子是楚國苦縣人,便認爲《老子》純屬楚文化,如“老子生活在遠離中原文化中心的楚國。據記載,楚國從他的遠祖開始,就有和中原文化不同的文化,《老子》書中没有引用西周以來官方的典籍訓誥,卻吸收了不少民間謡諺。”(3)任繼愈《老子新譯·緒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頁。但我認爲,從《老子》的語言特色來看,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作爲《老子》是“楚文化”的證據,卻似乎有些牽强。因爲從老子的出生地或老子的經歷來看,不能得出《老子》這部書和中原文化關係不大的結論。楚國苦縣,就在現在河南省鹿邑縣東,原屬陳國,春秋末年才爲楚所吞併。這個地區長期以來一直屬中原文化地區,南蔡(國)北宋(國),因而談不上“遠離中原文化”。再説老子也不像屈原那樣是楚王族世家的地地道道楚人。從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便知,老子還當過東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爲周王室掌管過多年的文書。毫無疑義,他受過相當深厚的中原文化的陶冶。由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使老子有可能把我國古代這兩種文化融會起來。事實上在《老子》書中,也確實明顯地表現了這種特色,同時兼具有這兩種文化的成分。比如《老子》一書,從思想内容到藝術形式,都可以明顯的看出對《周易》《詩經》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在語言的表達方面,不少地方用的是“楚語”,即楚國人的習慣用語,如“夫唯”也是《楚辭》中常用的發語詞,有的用的是楚方言,如四十五章“躁勝寒”,據《詩·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五十五章:“終日號而不嗄。”據《莊子·庚桑楚》司馬彪注:“楚人謂唬極無聲曰嗄。”四十二章“吾將以爲教父”,《方言六》:“凡尊老,楚謂之父。”在詩韻方面就更明顯了,既可以找到和《詩經》同韻的章節,又可以找到和《楚辭》合韻的地方。
《老子》中的一些章節,如果將它獨立出來,則簡直就是楚辭作品。如二十章的自我心態的描寫,十五章的“古之善爲士者”的刻畫,就是其代表。
從上可以看出,《老子》這部著作,無論在我國古代文化史或文學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老子》的藝術特色
哲理詩是不容易寫好的。高爾基曾經説過:“所謂哲學的詩,雖然有少數例外,但大體我是不感興趣的,在我看來,哲學正和數學一樣枯燥乏味。”(《給布拉洛夫斯基》)而今人讀古代的哲理詩,自然更不易理解。五經文字,到漢代已經很多人看不懂,朝廷需要設五經博士進行傳授。到唐代,連著名的學者韓愈都要摇頭感歎,“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其實,五經文字裏面,往往還保留着古代人大量的口語。
我們今天讀《老子》,許多人都感到困難,但是在産生《老子》的那個時代,人們應該是覺得很好懂的,這是因爲這部著作采用詩的形式,爲方便誦讀傳記的。爲此,這部著作便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下面試分别説明之。
1. 生動而形象的比喻。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是《老子》這部作品十分明顯的特色。形象生動、運用貼切的例子,在《老子》中俯拾皆是。
“有無”關係,這本來是抽象的概念,老子這樣寫道: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11章)
通過三個比喻,我們看到了有與無的統一關係,所以他得出“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結論時,就感到很具體。
他提出要把壞事消滅在萌芽狀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時這樣寫道: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64章)
他指出聖人必須“虚懷若谷”時,説“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從而得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66章)。
他對天道這樣描述: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77章)
他主張柔道,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争”(8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43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78章),用水把柔的形象充分顯示出來。
正是這些形象生動的比喻,深入淺出地説明了他的哲理,這與許多枯燥純理論演繹的哲學論文是何等不同!而且,由於這些比喻,多取自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常識,特别通俗易懂。
2. 以簡樸的語言,白描的手法,勾畫出一副副鮮明的圖畫。如他對理想社會的描寫: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80章)
前後僅用了75個字。
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描述,則僅用26個字: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虚,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53章)
這兩副圖畫,色彩對比何等鮮明!
又如他描寫“古之善爲士者”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時,這樣寫道: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15章)
正是通過這樣多種形態的描寫,加强了對“深不可識”的理解。
3. 結構的完整性。
對於《老子》一書的結構,歷來有一種看法,認爲它作爲一個體系並不完整,内容龐雜。這種看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全書的宗旨。也有的學者説,它的“體制和《論語》的語録式相類似”,所不同的,僅僅是“《論語》主於紀言,此則主於説理”,“《老子》的文章全是説理的短篇”(4)詹安泰、容庚等合著《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105頁。。這實際上也是否認它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其實,《老子》這本書是一個關於中國古代理想社會的藍圖,這是貫穿於全書的總綱。在這個綱領下,全書81章,有的章節間好像銜接性不强,然而這並不影響全書的完整性。因爲,老子正是從各個不同方面來談他的理想國的設計,各章之間往往有相對的獨立性。如第一章,集中談他的宇宙觀,提出道的概念和性質;第二章則提出宇宙萬物矛盾對立統一的規律,並由此提出治政的總則;第三章則是他的政治論,提出治政的一系列方針等等,内容豐富而不斷,佈局分明而自成一體。(從這些年出土的《老子》簡帛本看,有些章在傳抄過程中顯然出現前後錯置的情形,可作進一步研究。)
4. 語音節奏和諧,合韻悦耳,讀起來朗朗上口。
先秦的詩大多是配樂歌唱的。《老子》雖未必配樂(没有調查過,道士們誦讀時想必是要配樂的),但卻重視押韻以便流傳。雖然由於時代的變遷,古代和現代語音有很大變化,但《老子》中許多章節,全部或部分仍然符合於今天的韻律,讀起來很富於音樂感。
全部合韻的,如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部分合韻的,如二章“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關於《老子》的詩韻,從宋代吴棫起,一些學者就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此後,顧炎武、江慎修、鄧廷楨等都有專書考證。他們把《老子》同《易》《詩經》《楚辭》的音韻詳作比較,認爲《老子》的韻,有的和《詩經》的韻腳完全相同,如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歌支通韻)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支部)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侯部)
又如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歌支通韻)
他們認爲像這樣的章節,“以聲論聲,即置之三百篇中,亦不知有何區别”(5)朱謙之《老子校釋·老子韻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25頁。。
而有的篇章則和《楚辭》作品合韻,如第五章“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在《楚辭·雲中君》裏有“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這是屬於《楚辭》比《詩經》多出的冬部。
從以上這些用例中也可以看出,《老子》正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結合體,而它的文體也兼具《詩》《騷》的特點。
至於《老子》文中有的地方押韻,有的地方不押韻,句式上的錯落不齊,是否和歌詠需要有關,仍可進一步研究。因爲孔廣森就認爲,古代詩是爲歌唱用的,就必須合於音樂的節奏,而“歌有疾徐之節,清濁之和。或長言之,詠歎之,絫數句而無以韻爲;或繁音促節,至於句有韻,字有韻,而莫厭其多”(6)轉引自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13頁。。朱謙之在他的《老子校釋》一書中,專門列了《老子韻例》作爲專題研究,綜述歷代對《老子》詩韻的研究成果,可資有興趣者比較和研究。
5. 語言簡潔,富於哲理性,且多吸收民間諺謡。
吸收民間諺謡,目的是爲了通俗易懂。在《老子》書中有許多這一類的話。如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又如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四十二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這些話,讀起來很順,理解起來也比較容易。
老子的許多話成爲後代經常引用的格言或成語,就因爲它語言清新,富於哲理性。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58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74章)。再如,“物壯則老”(55章);“大器晚成”(41章);“慎終如始”(64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33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44章);“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63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73章)等等。所以,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老子》也是有很大貢獻的,它豐富了祖國的語言。這些成語和格言雖經幾千年時間的考驗,仍然有着極强的生命力。
二、 《莊子》——詩化的散文
戰國時代的諸子散文數量不少。然而,從其文學價值而言,没有能與《莊子》比肩的。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説: 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無事實,而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汪洋辟闔,儀態萬方”八個字確實道出了《莊子》作品的創作特色來。事實上,從文學作品的角度看莊子,是很難用一句話來給他下個判斷,因爲莊子本身便是具有文學家或者説是詩人氣質的哲學家。《莊子》一書從作品的風格、内容、藝術特色等方面看,其内涵的豐富性更是讓人盡够説的。正如聞一多所説: 這書中“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説,種種的原料,盡够你欣賞的,采擷的”(《古典新義·莊子》)。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對此問題略作説明。
(一) 詩人的氣質與詩化的散文
如果説,研究者迄今爲止對《老子》是不是“詩”的問題還有不同看法的話,而對《莊子》卻幾乎衆口一詞認爲是“詩化的散文”。20世紀初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便説,《莊子》具有“詩歌的原質”,認爲“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聞一多在《古典新義·莊子》中進一步指出,莊子不僅是位哲學家,而且是“真實的詩人”,“他那嬰兒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悵,聖睿的憧憬,無邊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豔羨,便他成爲最真實的詩人”,“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絶妙的詩”。爲什麽明明是詩歌形式的老子《道德經》不被人們看成詩,而分明是散文作品的《莊子》卻被衆人異口同聲認爲是“詩”?這其中應涉及作者與作品兩方面的問題。
從作者的角度看,雖然老子和莊周同爲道家哲學的代表人物,但從他們的氣質上和作品的風格上講,兩人卻有着極大的不同。從總體而言,《老子》整部作品是以闡釋哲理爲主的,儘管用的是詩歌的形式,但其内容上是理勝於情的,這不符合中國傳統詩論的要求,因爲中國的傳統詩論從開始起便是總結抒情詩的特點——“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顯然,按照這樣的詩論,《老子》這樣冷静地思考宇宙哲理,感情含而不露的著作,自然不能視之爲詩。
和老子比起來,莊子卻是一位感情頗爲豐富的,具有詩人氣質的哲學巨匠。他的著作,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繹或枯燥無味的邏輯推理,而是通過衆多具體鮮明生動的意象,從不同側面加以啓示,讓人從中悟出作者所要闡釋的“理”來。我們不妨從《莊子》的首篇《逍遥遊》説起,映入眼中的先不是一連串的道理,卻是有關“鯤鵬展翅”的壯麗景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這些描繪如詩如畫,引人入勝。《莊子》中有着大量諸如此類的描寫,他引領着讀者進入藝術美的境界之中,讓他們去欣賞,去吟詠,去回味,雖不是詩,卻勝似詩。
同樣,《莊子》第二篇《齊物論》,一開頭先寫的是“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然後進行關於天籟、地籟、人籟的描繪: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虚。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同樣,《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即使是那些純屬説理的文字,莊子也盡量采用簡潔而整齊的句式,並使之具有歌詩的旋律,如《齊物論》中的一段話: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養生主》一開頭的一段: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上述所列,大體已可以看出《莊子》的語言特色,它確實有詩的意境,詩的感情,詩的形式,詩的旋律,詩的韻味,從而給人以美的藝術享受。
形成《莊子》作品的這種語言特色,和莊子本人的氣質有極大的關係。莊子熱切期望能够憑藉自己的理論和智慧爲民衆在亂世中尋找一塊心靈的浄土。我們切不可被他那些同物我、等是非的理論所迷惑,以爲他是個無好惡、無是非的避世者。實際上史籍的記載,以及《莊子》一書中莊子自我形象的描繪,都給我們留下十分鮮明的印象。這位體道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道家奠基人,在現實生活中卻是另一種形象: 他終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他鄙視功名,傲視權貴,痛恨虚僞,嫉惡如仇,正是看透現實的黑暗,因而采取了和統治者絶不合作的態度;他追求自我品格的完善,安貧樂道,是非分明,感情真摯,是一位敢笑敢罵,介然獨立,人格清高的士人。《莊子》一書中記載了許多這方面的事例: 當宋王的寵倖曹商向莊子誇耀自己如何受寵並得到十車時,莊子將其譏諷爲“舔痔”者(《列禦寇》);惠子因害怕流言所傳的莊子將代他爲相,在國中大搜三天三夜,莊子之後前去見惠施,並將魏相之職,比之爲“腐鼠”(《秋水》);他在魏王面前直斥當今統治者都是一些“昏上亂相”(《山水》);他抨擊當時的社會是“竊钩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胠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載: 楚王派人前去聘他爲相,莊子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絶,並對使者説:“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以紀實的手法,寫下民衆所遭受的苦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他以深厚的感情,寫下對故國的懷念:“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陽》)而他的朋友惠施去世之後,莊子懷着深深的思念,在他的墓前發出深深的感歎。凡是種種,充分表明,哲學家的莊子,同時又是具有熾熱感情和詩人氣質的人,這種感情在《莊子》散文中時時鮮明地流露出來,震撼着讀者的心弦,從而也使《莊子》散文洋溢着濃濃的詩意。
(二) 我國古代浪漫文學的奠基作
在詩歌領域裏,《詩經》一向是被稱爲寫實的奠基作,《楚辭》被稱爲浪漫文學的奠基作。《莊子》散文的出現,早於《楚辭》,作品中所表現的强烈的浪漫氣氛,對我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學創作産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郭沫若曾説過,大半個中國文學史,都受到《莊子》的影響,這是符合實際的。《莊子》影響所及,不僅是散文,而且也影響到詩歌、寓言、神話、小説等等衆多文學創作的領域。在以往幾十年研究中,許多人往往用簡單化的比較方法,動輒將《莊子》散文同屈原詩歌作比較,認爲莊文屬於消極浪漫文學,而屈作代表積極浪漫文學。其實這種説法是不正確的。《莊子》中表現出對人類命運和現實苦難的深深關愛之情,這應該説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積極的人文情懷,不能因爲莊子思想上的消極避世,而全盤否定其積極救世的一面。
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以“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來概括《莊子》散文的特點,是很准確的。莊文的這種特點,是與其哲學上的觀念有直接聯繫的。莊子所追求的道,與天、地、自然相一致,他的視野十分開闊,思維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因而想象的空間,也就無邊無際。這樣開闊的視野加上作者異常豐富的想象力,自然就産生了“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的創作特點了。莊文的浪漫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文章風格上的超凡脱俗。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莊子追求一種詩化的人生,希望能擺脱塵世的束縛,通過體道的方法而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理想境界。所以,《莊子》中描寫了許多人物,就不是現實中的。如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又如黄帝、廣成子、許由等等衆多的得道者的出現以及他們的對話,都使人有一種超凡脱俗的感覺。
其次是作品中大量運用神話、寓言、傳説故事,這些故事本身,便充滿各種奇特的内容,再加上莊子誇張的叙述和描寫,自然使作品的浪漫氣氛分外强烈。
再次是莊子的誇張和神奇想象而産生衆多的奇景、奇事、奇人、奇物,從而使莊子文章形成一種奇麗峻峭的藝術風格。我們前面提到的鯤鵬展翅時,“其翼若垂天之雲”,而且會産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這樣壯麗的景觀(《逍遥遊》),《外物》篇寫任公子在會稽山垂釣於東海時,爲大钩巨緇,以五十條牛爲鉺,當大魚上钩時,“牽巨钩,陷没而下,騖揚而奮髻,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上述景象,可謂奇麗至極了。
奇人與奇事則往往是聯繫在一起寫的,如庖丁解牛,列子御風而行,匠石運斤成風,梓慶削鐻,吕梁丈夫蹈水,等等。莊子書中寫到的人物衆多,其中有各種異人,有得道的仙人,有帝王,有達官貴族,有學者,有隱士,有盜賊,有美女,有醜婦,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他還特别描寫了一群相貌醜陋,甚至肢體殘缺不全的奇人,如《人間世》中的支離疏,《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形象奇醜的哀駘它、闉跂支離無賑、甕盎大癭等,他們都“以醜駭天下”,然而卻有着過人的智慧和奇特高尚的德行,從而贏得世人、甚至國君的敬意。至於書中所寫到的奇物,則如其廣數千里的鯤鵬,以五百年爲春、五百年爲秋的冥靈和八千年爲春、八千年爲秋的大椿樹,以及大瓠、樗樹、齊地“徑寬百圍”的櫟社樹,等等。這些景、物、人、事,更使莊子作品帶上濃濃的神奇色彩。
(三) 包容衆體影響深遠
《莊子》雖爲哲學著作,但同時又是極有特色的文學著作,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作説明。更爲重要的是,《莊子》和諸子散文不同,其中包容衆多文學體裁,因而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十分深廣。具體地説,《莊子》對詩歌、散文、小説、寓言、神話的貢獻和影響都是其他先秦諸子難以企及的。
莊子的散文具有詩的抒情特點、詩的意境和韻律,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代表着這一時代的最高成就,這兩方面我們在前面均已談到了,下面集中談談對小説、寓言、神話方面的影響。
《莊子》中有近200則寓言,在先秦諸子作品中,其數量略少於晚出的《韓非子》和《吕氏春秋》(它們分别有300篇左右),但《莊子》寓言同樣代表着中國古代寓言的最高成就。
雖然在莊子之前,中國古代寓言已歷經上千年的准備和成長過程,但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作品也只是分散地出現於《詩經》《國語》《左傳》《墨子》等典籍中。而莊子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寓言創作的理論並自覺地進行創作,從而影響和帶動了諸子寓言創作的熱情。《莊子·天下》中説,莊子“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這便是人們常説的莊子“三言”創作論。在《寓言》篇中,他還提出“寓言十九,藉外言之”。有的學者認爲,這一寓言創作理論的提出,與孔子提出的“詩言志”理論一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莊子寓言和諸子寓言相比,具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是過去的人雖在言談中也應用寓言和民間傳説等來説理,但這些寓言與民間傳説多是現成的,在民間口耳相傳的。而莊子是有意識地編造寓言,其中的大量寓言或神話,或由莊子根據説理的需要,進行藝術想象再創造出來,並無原型與傳説的根據。如雲將東遊遇到鴻蒙之事,南海之帝儵與北海之帝忽爲中央之帝渾沌開竅之事,鵷雛譏笑鴟得腐鼠,莊子夢髑髏、化蝶之類,顯然都是莊子自己編出來的。二是對以前的故事原型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莊子説理的需要。莊子書中有許多歷史人物,如老聃、孔子及其弟子顔回、子貢,各諸侯國國君等,他們的故事和言論大量被寫在《莊子》中,其中便有真實與虚構兩種成分。作爲歷史人物,他們是真實存在過的,但他們在《莊子》中的言語,卻大量是莊子自己根據人物的性格邏輯發展的必然性,進行構思出來的。老聃和孔子及其弟子們在《莊子》文中多次出現並有許多對話,但這些言行未必是真實發生的事,而是莊子在對他們充分認識理解的基礎上,做了合乎各自性格和思想邏輯的編創。三是與其他諸子相比,莊子寓言視野最爲開闊,所寫的對象從天帝到人間,從遠古到現在,從帝王將相到各類凡人,甚至肢體殘缺的人物,還有動物、植物等,作者不受空間時間的制約,以宇宙萬物爲直接描寫對象,加上其奇特而誇張的想象,構成《莊子》寓言的浪漫特色。如海鱉和井蛙的對話,鵷鶵與鴟的對話,莊周與涸轍之鮒、與髑髏的對話等,均幽默詼諧而藴含哲理,令人回味不已。四是莊子寓言中特有的“物化”境界。道家思想認爲,人是自然的一個部分,因此人與萬物是相通的,人“與物爲春”(《德充符》),“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因此物我之間能够統一並達到物化的狀態。《莊子·齊物論》中有“莊周化蝶”的寓言:“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必有分也。此之謂物化。”莊子認爲自己達到這種“若化爲物”(《大宗師》)的境界,所以他與惠施在濠梁觀魚時就能够知“魚之樂”,能够在去楚途中與髑髏對話。這種超現實的幻覺,溝通了人與物、生與死、過去與現在、神與人之間的聯繫,從而使莊子的寓言具有夢幻般的神奇色彩。由於莊子在寓言創作理論與創作實踐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莊子》可以稱爲是中國古代寓言的開山祖。
再談《莊子》中的神話。《莊子》中的神話與寓言往往是交匯在一起的,許多看似神話故事,實則又是經莊子重新創造的寓言。在《莊子》文中,我們看到許多人物形象,顯然是從上古神話中來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北冥的鯤鵬,中央之帝渾沌,黄帝昆侖遺玄珠,河伯與海若,還有西王母、顓頊、禺强、彭祖等,許多都是神話中的人物。這些神話中的人物和故事,有不少我們可以從《山海經》之類的古籍查到他們的原型。從衆多神話中可以看到,莊子引述的神話,既有流傳於北方的(如《齊諧》),也有流傳於南方的(如《山海經》),擷取的範圍相當廣。但是《莊子》中所引用的神話,目的是爲了形象地宣揚他有關“道”的主張。因此,這些神話不是照搬其原意,而是對之進行了再創造,使之具有哲學的意義,而原有的含義卻在改造中失落。經過莊子改寫的神話,已經成爲宣揚道家哲學主張的工具,這樣的神話當然與原始神話有了較大的差距。然而,神話在其流傳、發展中,也是經歷代口耳相傳的,在這相傳的過程中,不斷有人進行加工並增添神話的各種内容,使之不斷豐富。如有關西王母的神話,從《山海經》中的那位豹尾虎齒、披髮戴勝而善嘯的怪物,到《穆天子傳》中熱情好客,接待周穆王,並與之歡宴賦詩的君主,再到《漢武内傳》中年輕而容貌絶世,賜蟠桃給武帝的女神,一代代神話不也都在改造創新之中嗎?《莊子》中也寫到了西王母,雖然着墨不多,但她是位得道高人,和得道而成爲天帝的黄帝、顓頊等在一起。所以,莊子對神話的改造,也是對神話的創作和發展。大量神話的運用,增添了莊子文章的神奇浪漫氣氛。對於《莊子》神話的内涵,近年來有學者集中進行研究,提出新的見解,並對其意向做出文化闡釋。
最後,我們再談一談《莊子》與小説。
有人將莊子稱爲“中國小説之父”,有人稱之爲“中國小説之祖”,這都是從《莊子》研究中所得出的認定,是有其根據的。《莊子》一書中,首次出現“小説”一詞,《外物》篇中有“飾小説以干縣令”之語,雖然這“小説”一詞之含義與後來有所差别,但也存在某種聯繫。因爲“飾小説”即修飾淺陋的言辭。此文之前有“後世輇才諷説之徒”,“諷説”,林希逸注爲道聼塗説;劉鳳苞釋爲誦説往事,這個意義正與“小説”的含義相近。《漢書·藝文志》曰:“小説家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聼塗説者之所造也。”並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莊子·外物》中也是認爲小説“其於大達亦遠矣”,“大達”即“大道”,可知孔、莊都認爲“小説”是一種“小道”。
當然莊子的最大貢獻不在於提出“小説”的概念,而是作品中的創作實踐對後代小説創作的影響。
《莊子》中的神話、寓言數量衆多,從小説史的發展過程而言,中外小説均起源於神話。而寓言是晚於神話而産生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從神話到小説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作爲叙事文學,中國和西方經歷了不同的過程。西方的叙事文學最早的是英雄史詩,而中國的叙事文學則是從神話到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東周時期的編年體史作《左傳》中對歷史事件的叙述,已寫得十分出色,其中的場面描寫、情節安排、人物性格刻畫、結構均體現出作者高超的叙事藝術。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穿插其中數量衆多的寓言故事。前面我們已經談到《莊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准。書中的篇章,有的從頭到尾均由一個接一個的故事連綴而成,僅在各個故事的結尾處,有簡略的議論和説理成分。如《外物》篇,開頭有一段關於“外物不可必”的點題議論,接着便寫莊子向監河侯借糧、任公子之釣、儒以《詩》《禮》發塚、老萊子遇仲尼、宋元君夢神龜的五個寓言故事,最後才是莊子與惠施關於“無用之用”的辯論,五個故事均寫得娓娓動人,人物語言和形象刻畫皆可謂繪聲繪色,後之評論者以“奇事奇聞”、“錯綜變化,筆妙入神”(劉鳳苞《南華雪心編·外物》)贊其叙事之妙。《莊子》雜篇中還有幾篇尤其值得注意,如《盜跖》《説劍》《漁夫》這幾篇作品和其他篇章不一樣,全文自始至終寫的是一個故事。這些故事具備了小説創作的各種要素,作品中情節發展的設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場面氣氛的渲染,人物對話的叙寫,均有其獨到之處。這些作品創作的成功,爲此後我國小説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如《盜跖》篇,作者把不同時代的人物盜跖與孔子(相距100多年)放在一起,讓他們面對面辯論是非,而且被斥爲“盜”的跖反而把被稱爲“聖人”的孔丘罵得張口結舌,難以置詞,確實是很富戲劇性的。無論是《盜跖》還是《説劍》,都寫得情節跌宕起伏,曲折生動,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宋人黄震便已説過:“莊子以不羈之才,肆跌宕之説,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蹤,固千萬世詼諧小説之祖也。”(《黄氏日鈔》)清人林雲銘也認爲像《盜跖》篇,“徑似小説家閒話”(《莊子因》)。胡文英更直接説:“此種形容,便開唐人小説派矣。”(《莊子獨見》)
莊子作品“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來構思和叙寫,采用“卮言”、“重言”、“寓言”作爲作品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三言”均是有意識進行創作,將抽象的哲理化爲人們易知易懂的形象,極大增强了文章的説服力與影響力。他對歷史人物形象的重新改塑,使動植物擬人化,將無生命的事物化爲有生命能思維的形象。他將人與物、人與天相互溝通,顯示其思維的活躍和創造力的深厚,這些都對我國幾千年的文學史産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和老子一樣,莊子也是位元語言大師。和《老子》比起來,讀《莊子》更是一種藝術享受: 這裏有詩的語言,畫的意境,音樂的旋律,飄動的舞姿。莊子的文筆流暢,有如行雲流水,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當其描寫物的“動態”時,氣勢磅礴,有如大江東去,浩浩蕩蕩,不可遏止;而當他描寫物之“静態”時,則如枯木,如死灰,寂静無聲,杳焉無息。至於其高超的形象刻畫藝術,浪漫的藝術氣氛的營造以及如詩之美的語言,前文中已詳論及,這裏就不多説了。
《莊子》中,運用了多種多樣的修辭手段,以加强其文章的説服力,如前所談到的“三言”的運用,在《莊子》中便是一種極其重要的修辭手段。此外,《莊子》中還大量使用比喻、誇張、對比、對偶、襯托、鋪排等修辭手法,在行文中交錯使用,不拘一格,使文章顯得變化莫測,多姿多彩。就以比喻的運用而言,就有明喻、暗喻、排喻,等等。
雖然兩千多年過去了,莊子的語言仍然在今人文章中時時出現,如“莊生夢蝶”、“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望洋興嘆”、“運斤成風”、“井底之蛙”、“庖丁解牛”等,充分顯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説,莊子對中國文學語言的貢獻是巨大的、罕與倫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