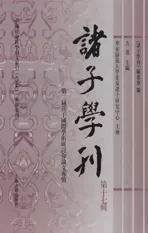莊子與海德格爾: 無用之用、以明、物化
2018-09-06臺灣賴賢宗
(臺灣) 賴賢宗
内容提要 首先,筆者探討了海德格爾對於《莊子》的“無用之用”以及老子的無的討論。《莊子》的“無用之用”涉及“以明”的課題,筆者進而研究《莊子》的“以明”的三個面向,對比於海德格爾所説的“解蔽”的真理觀與“澄明”(Lichtung)。莊子闡明“以明”的第一個面向是理論理性的知性分析的面向,以及由概念的相對性而相反相成地更爲全面地掌握物論。第二個面向的“以明”是無的智慧的面向,是莊子所説的“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在這裏“以明”與“無用之用”的論題具有重大的相關性。第三個面向的“以明”則是葆光、天倪的面向,呼應於《齊物論》一開始所説的“天籟”,而關聯於筆者所闡明的“物化”。海德格爾在他對於技術的批判之中,以及他的存有思想的藝術觀(藝通於道)之中,提到了《莊子》的“無用之用”,《莊子》的“以明”對於海德格爾來説是如何面對人類的理性的光芒,以及如何進入到“澄明”的林中空地(存有的界域)的問題。
[關鍵詞] 莊子 老子 海德格爾 以明 物化 無用之用
導論: 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
討論海德格爾與老子的思想的親緣性的文章很多,是學界一個熱點。例如張祥龍説:“海德格爾的轉折與他對老莊的關注之間有着内在的聯繫。”(1)張祥龍《海德格爾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頁。英語世界當中的相關研究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帕克斯(G. Parkes)於1987年編輯出版的《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HeideggerandAsianThought)(2)帕克斯(Graham. Parkes)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但是,此書有一個根本缺失,帕克斯認爲只有到了海德格爾的晚期著作才引用了《老子》,但是張祥龍和筆者的著作對於1930年海德格爾已經引用《老子》的事實,已經加以詳細闡明。對於海德格爾與老子的思想的交涉在海德格爾存有思想的形成史之中形成與演變過程,梅耶(Reinhard May)著有《來自東方的光: 東亞影響之下的海德格爾作品》(Exorientelux:HeideggersWerkunterostasiatischemEinfluβ)(3)梅耶(Reinhard May)《東亞影響之下的海德格爾著作》(Ex oriente lux: Heideggers Werkunterostasiatischem Einfluβ),Stuttgart,1989。,有比較更爲清晰與具有突破性的見解。此書的德文本於1989年出版,G.Parkes將此書英譯,英譯後之書名爲Heidegger’shiddenSources:EastAsianInfluencesonhisWork(海德格爾的隱藏的根源: 東亞思想對他的影響),此書從海德格爾所受的東亞哲學(尤其是道家)的影響來重新闡釋海德格爾思想的核心概念(4)G. Parkes英譯,英譯後之書名爲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海德格爾思想的隱藏根源: 東亞對他的思想的影響》)(New York, 1996)。。梅耶的研究指出,早從1920年代開始,海德格爾就已經進行思想之根源的探索,强調必須回到思想根源的“空無的滿盈”,因此而呼應道家的思想之路(5)梅耶(Reinhard May),G. Parkes英譯,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海德格爾思想的隱藏根源: 東亞對他的思想的影響》)(New York, 1996),第47頁。。
學界一般强調海德格爾和蕭師毅於1946年夏天合作翻譯《道德經》八章,然而此一故事的遠因可以追溯到1928年海德格爾所進行而九鬼周造參與的謝林講座之中,討論了謝林對於老子的無的詮釋以及謝林所闡明的nicht-wollen(無意欲)的思想,乃是人類自由的本質之關鍵,以nicht-wollen(無意欲)之説來和尼采講座之中的意志學做一個對比。如此,才能恰當地解釋1929年、1930年之後海德格爾重視“無”,以及由此而有的所謂的海德格爾的思想轉向(Kehre),道與本成(Tao,Erignis)和無的思想成爲海德格爾晚期思想的主題。顯然,1946年夏天海德格爾翻譯《道德經》八章並非憑空出現的一時靈感,1929年、1930年海德格爾轉而重視“無”也在著作之中引用了老子,這些都是早在1946年《道德經》德譯之前。
在九鬼周造死後,在Auseim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從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來)一文之中(6)Auseim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從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來)一文收入海德格爾《走通往語言之途中》(Unterwegszur Sprach)一書(Stuttgart,Neskel出版社1997第十一版)。海德格爾《走通往語言之途中》編爲《海德格爾全集》第十二卷。,海德格爾與手塚富雄於1954年談到九鬼之墓並表達對其人的追憶。以對於九鬼的追思爲開端,海德格爾與手塚富雄兩人討論東亞的藝術觀和語言之有别於西方的特殊性,認爲東亞的藝術與語言是更爲近於藝術作品的存有真理之根源以及存有的語言。海德格爾在這裏以他的晚期思想所進行的存有思想來面對日本美學、語言與色空的禪思想,與手塚富雄進行了精采的對話。海德格爾此一對談所運用的其晚期存有思想依其對話進行的先後,有下列幾項都是涉及到道家與禪宗思想,以老子的思想來對比: 回到開端(In das Anfangendezurück)是老子所説的“歸根復命”,雙重性與共同隸屬(Zusammengehören)是老子所説的“玄同”,道言(die Sage)是老子所説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其自在(Gelassenheit)是老子所説的“讓”,本成(Ereignis)是老子所説的“道法自然”,一如(das Selbe)是老子所説的“一”(“得一”、“抱一以爲天下式”)。此處要注意的是海德格爾與手塚富雄兩人談到美學觀的時候討論到“いき”(粹)、“色空”,海德格爾對於九鬼周造與手塚富雄的見解是抱持着批判的態度。海德格爾對於九鬼周造的見解可以正確無誤地復述,他發揮自己的晚期存有思想,批評手塚富雄的且是還落入於二元對立與表象形象學之中的見解。所以,我們對於京都學派的學者與海德格爾的對話不應給予過度的評價,而是要體認到海德格爾更多地是從他與老子莊子的思想對話得到啓發,而發揮成爲他的晚期存有思想。因此必須存筆者所謂的本體詮釋的觀點來重新把握此一海德格爾與禪宗道家的跨文化的哲學對話的深刻意涵,而不可以局限在日本京都學派對於此一論題的説法之中。梅耶《來自東方的光: 東亞影響之下的海德格爾作品》較能深入地掌握到海德格爾與老子的對話對於晚期海德格爾思想的發展的重大意義,但是此書的問題是對於海德格爾思想的整體發展過程的掌握不够清晰,也對於老子莊子思想的本體詮釋以及它和海德格爾思想的對比性,没有真正加以把握。
相對於以上帕克斯與梅耶兩個人只是從思想的形成史過程來掌握問題,施瓦德勒(W. Schweidler)的研究方法是就哲學問題的親緣性來加以探討。如果説前述是一種外部研究,或至多是思想史的研究,則施瓦德勒的研究方法是内部研究與哲學性的研究。
施瓦德勒著有專文討論海德格爾的老子接受過程(7)施瓦德勒《海德格爾對老子的接受》,收於《中國哲學史》1995年3、4期的《西安國際老子研討會專輯》。德文稿Heideggers Laozi-Rezeption發表於Peter Koslowski,Richard Schenk編,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der Forschungsinstituts für Philosophie Hannover,Band 8,1997,第266—289頁。,他由“常道”、“無”與“道的雙重性”等三點來發揮老子哲學詮釋與海德格爾思想的可能銜接點。施瓦德勒嘗試從海德格爾與老子的思想内部來做比較研究,具有獨到的見解,這和一般的研究只是收集文獻,隨文解義地做一些海德格爾和老子的外部比較,是不一樣的。筆者很贊同他的研究進路。筆者進而由海德格爾的思想形成過程來探索存有思想的整體性,並從哲學思想的親緣性來從事二者的内部性的比較研究,寫作《本成(Ereignis)與有無玄同: 論海德格爾思想的“轉折”(Kehre)與老子的有無玄同》等文(8)賴賢宗《道家詮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哲學與詮釋學叢書”)。又,賴賢宗《海德格爾與道家禪宗的跨文化溝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筆者此文則以同樣的方法論來探討莊子哲學與海德格爾的對話。
相對於老子與海德格爾的思想的比較研究具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對於莊子與海德格爾的比較研究的學界既有成果則相對少很多。此中,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是一部莊子與海德格爾的比較研究的專書,次第展開許多兩位哲學家的對話的課題,但是文義錯亂之處比較多。此外,比較傑出的有近年留德歸來的鍾振宇在“中研院”發表的《莊子與當代批判——工作、技藝、壓力、遊戲》《莊子的死亡存有論——與海德格爾死亡哲學之對話》等論文(9)鍾振宇《道家與海德格爾》,(臺灣)文津出版社2010年版。鍾振宇以研究無爲與Gerlassenheit的博士論文於2005年取得德國Wuppertal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中國大陸,筆者特别注意到了王凱的《道家詩性精神: 兼與海德格爾比較》一書,算是質量俱優的一部專書(10)王凱《道家詩性精神: 兼與海德格爾比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筆者强調不能只從外部關係以及觀念的外觀上的類似性來討論,而必須從思想的内在本性的親緣性來探探,尤其是要從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歷經前後期的思想轉折的形成過程之中探討其存有思想的整體性,並與老子莊子哲學的本體詮釋所對應的相關課題,如此從事跨文化對話的研究。前述的王凱主張老子莊子的物論和海德格爾的物論在本質上不同,筆者無法苟同。假如可以適當把握莊子對於老子哲學的發展之創造詮釋,以及闡明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歷經前後期的思想轉折的整體性,那麽就可以見出老子莊子和海德格爾三者互相呼應與貫通之處。
這闡明了所謂的海德格爾思想的前後期的轉折,首先是一種存有的轉折(本成發生在存有力動之中的轉折),這是貫穿於海德格爾一生的洞見,而不是方向的轉折、思考的方向的轉折。並不是説從《存有與時間》的此有的時間性出發而轉折到晚期的從存有自身出發,而應該説是: 存有的力動就包含了轉折。海德格爾常常以物物化(Das Ding dingt)、世界世界化來表達存有的力動,包含了此有的時間性在其中,也包含了存有學差異在其中。這個情況和迦達默爾在《海德格爾之路》(HeideggersWege)對於早期海德格爾教學的回憶,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説: 海德格爾的《存有與時間》(1927年)出版之前的1920年、1921年,海德格爾已經討論了Esweltet(如是世界化)的思想,已經開始了所謂的十年之後的思想轉折(11)迦達默爾《海德格爾之路》(Heideggers Wege), Tübingen, Mohr, 1983,第141頁。。奇斯爾(Theodore Kisiel)的研究指出,海德格爾更早在1919年,就已經有了eser-eignetsich(如是事物發生)等等的思想,已經是一種所謂的轉折之後的海德格爾Ereignis(本成發生)的思想的萌芽(12)參見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 Time(海德格爾《存有與時間》的形成),California,1993,第16、23、494—495頁的相關討論。。
筆者此文探討莊子比較於老子的具有特色之處,在於三點: 用(庸、無用之用)、心(靈台心)、化(物化)。因此而呈現出莊子哲學具有絶對唯心以及藝術化的傾向,莊子哲學是一種即現象即本體的絶對唯心的現象論。
就此而言,傅偉勳在他的《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指出“莊子超形上學的突破是激活老子哲學的思想創獲”,“莊子爲老子未曾完成的超形上學課題所踐行的,即是通過超形上學的突破,將我們的心靈從人爲思辯與名言徹底解放出來,而在我們的主體性以毫無羈絆的無心體認老子所首倡的自然、無爲、無事、無言的道家形上學”(13)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灣)東大圖書1990年版,第40—42頁。。此中的“超形上學”(Trans-Metaphysics)就是對於海德格爾的Metontologie(超存有學)的翻譯,後者首次出現於他的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Metaphysische Anfangsgriinde der Logik)(1928)一書。
老子與莊子都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開創者,都是道家哲學與功夫修練的大成者與思想的創造者,但是二者有一些差别。如果説老子的性格更多的是沉思的哲學家,而莊子則是一位藝術家。老子第一章有無玄同,觀有觀無重玄道觀;莊子則是直接以逍遥遊的生命境界呈現哲理於藝術性的直觀之中。又,老子在修練上循循善誘,專氣至柔,致虚守静,有其次第性——法地法天法道與法自然,而逐步展開其圓滿境界於天地人道的四方之中;莊子則當下即是,大道物化只如蝶夢,天機流衍,和盤托出,當下現成。
1960年7月18日,海德格爾在《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UeberlieferteSpracheundTechnischeSprache)的演講中討論了莊子關於“無用之用”的三處文本(14)海德格爾《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Überlieferte Sprache und TechnischeSprache),Hermann Heidegger編,1989年,編5—8。此小册子的内容出自海德格爾於1960年7月18日在國家教師進修科學院爲職業學校的理科教師舉辦的培訓班上發表的演説手稿。,涉及到對於技藝的省思,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絶對真心的妙用,此一真心的妙用表現爲三面向的“以明”,而終極呈現爲“葆光”。筆者本文由此切入,對比於海德格爾的相關思想,討論了莊子的用(庸)的思想;也藉由海德格爾關於技藝與藝術(Techne)的省思,討論了莊子的相關思想,筆者探討“莊子的無用之用與海德格爾對於技藝的省思”的課題。又,莊子的“物化”是道化、大道玄化,相通於海德格爾的“物物化”(Das Ding dingt)、“世界世界化”(Die Welt weltet),筆者就此加以探討。
《莊子》譯成西文而在西方世界流傳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對於中西文學、宗教與哲學的交流具有重大貢獻。方勇先生的《莊子學史》六卷本洋洋灑灑,於莊子學的詮釋史用力甚深,具有莊學研究史的多方面的劃時代的貢獻。但是《莊子學史》未及於《莊子》在西方世界的流傳史與詮釋史,可以説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尤其是方勇先生所説的新子學之所謂的“新”無疑地是以當代詮釋與中西文化對話爲其重要内涵,因此就不能完全忽略《莊子》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史與詮釋史,料想此一缺失在未來的增訂版之中一定可以得到修正。
德國的《莊子》譯介首先是著名的漢學家與哲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所做的翻譯和經典詮釋。於1912年,他用德文編譯《莊子: 南華真經》(DschuangDsi[ChuangTzu]DaswahreBuchvomsüdlichenBlütenland)一書在德國出版。此外,德國著名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英國漢學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英國,1845—1935)的《莊子》英譯本的基礎上(15)1889年1月,翟理思出版《莊子: 神秘主義者、倫理學家、社會改革家》(Chuang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該書翻譯工作歷時整整兩年時間。相對于老子而言,西方學者對於莊子的研究並不多。翟理思的《莊子》譯本分爲三大部分: 導論、莊子哲學札記、譯文。,於1910年出版了德文的《莊子語録與寓言》(RedenundGleichnissedesTschuang-Tse)一書。布伯所説的“我與你”的互爲主體的關係,强調同情共感,此説就有《莊子》的魚樂之辯的影子。1930年10月9日,海德格爾在《真理的本性》的演講中就曾引用《莊子·秋水》(布伯譯書)中的此一莊子與惠施討論魚樂的寓言來闡明藝術體驗乃是發源於存有(本體)體驗的共通感(16)參見Thought on the Way: Being and Time via Lao-Chuang一文,收入帕克斯(Graham. Parkes)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第 105頁。。
1930年10月9日海德格爾在演講之中對於《莊子》的觀點信手拈來,他要求與會者提供莊子文本而立刻將之用來詮釋自己的存有思想之藝術觀,可以説這個時候的海德格爾已經熟讀《莊子》的德文譯本,而且已經在心中將《莊子》和他自己的存有思想融爲一體,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60年7月18日海德格爾在《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的演講稿中討論了莊子關於“無用之用”的見地。海德格爾與莊子的思想對話貫穿海德格爾存有思想成熟之後的全部過程。
一、 莊子的無用之用與海德格爾對於技藝的省思
筆者此文探討莊子比較於老子的具有特色之處,在於: (1) 用(庸、無用之用);(2) 心(靈台心);(3) 化(物化)。莊子哲學因此具有絶對唯心以及藝術化的傾向。此節探討的是第一點用(庸),並討論海德格爾引用了莊子所説的“無用之用”而對於“技藝”的課題將以省思。莊子哲學强調本體的功能妙用,此一妙用是要透過無、無用方能顯化,所以稱之爲“無用之用”。“無用之用”並不是某一個存在者没有作用,而是本體(存有,Sein)透過虚無所顯化的妙用。因爲某一存在者没有作用還是落在表象性思想與機械因果的作用之中,並不是真正的、超越的自由的“無用之用”。就好像老子莊子所講的“無”、“虚”並不是“没有”、“存在活動的闕如”,因爲所謂的“没有”還落入於“有”和“没有”的相對性之中,“存在活動的闕如”還是以在表象性思想與機械因果的作用之中來把握,並没有達到真正的自由。毋寧説:“無”、“虚”是一種超越的能力,是一種海德格爾呼應老子而説的澄明聚集的敞開,是謝林詮釋老子學所説的純粹的可能性。
海德格爾《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討論了莊子《逍遥遊》的末段關於無用之樹的寓言,並批判了技藝的語言,批判了片面性的工具性之用的科技語言,海德格爾説:“在《南華真經》(即《莊子》)本文的另處,還有兩段類似的、文字上有所變化的話。這些段落説出了這樣一個見地【無用之用】: 人無需擔憂無用者。無用性的力量使他具有不受侵犯和長存的能力。因此,以有用性的標準來衡量無用者是錯誤的。”
在此,海德格爾用的是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莊子》德文譯本。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晚期海德格爾闡發了“用”(Brauch)的思想,這是一種“大用”,一種“無用”的“大用”,這裏的思想是來自於莊子,海德格爾强調的乃是“存有”對人的使用。
海德格爾於1960年在《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中也討論了《莊子》的無用之樹的寓言,並批判了技藝的語言(17)海德格爾《流傳的語言和技藝的語言》(Überlieferte Sprache und Technische Sprache), Erker: Herausgegeben von Hermann Heidegger, 1989,第5—8頁。此小册子出自海德格爾於1960年7月18日在國家教師進修科學院爲職業學校的理科教師舉辦的培訓班上發表的演説手稿。。海德格爾此處還提到了《莊子》另外兩處文本討論到無用之用。《莊子》的《逍遥遊》一篇記録莊子與惠施的對話,莊子説: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在此,莊子是以寓言故事來叙説《老子》十一章所説的“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的哲理。老子是從條件利益與空無妙用的觀點來討論有與無的關係。這是説: 從有的觀點來發揮萬事萬物的相對條件與利益,從無的觀點來妙用萬物的存在。其實莊子這裏的實踐論已經隱含了《老子》第一章的有無玄同的道論形上學,《老子》第一章已經講了“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所以討論有無之利益與妙用,不能脱離有無玄同的道論的思想架構。
海德格爾所注目的關於“無用之用”另處的兩段莊子文本,他自己並没有明指出來,可能是指下列文本:
《莊子·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莊子·山木》:“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山木》:“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此中,《莊子·人間世》説桂可以食用,故被砍伐而夭折。漆樹可以提供漆,所以被割裂。科技的語言是割裂生命而使得生命存在異化而夭折的語言,有用之具體物都落入一定的條件限制之中,落入機械性因果之中,而失去自由。所以,“無用”才能恢復存在場所的靈妙,此乃無用之大用。但是,“無用”並不是“没有作用”,没有作用還是停留在機械性因果的作用之中,只是呈現爲一種“機械性因果的闕如”。
故《山木》篇就此論題有着進一步的討論。主人之雁以不材而被主人所殺死,但是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材與不材並不能保證生命的生存,那麽要遊處於二者之間嗎?揣摩外界權力者的心態而隨之表現爲或材或不材,但是這樣的心態,其實在深入之處而言,已經喪失了心靈的自由,而且也無法終極避禍,因爲外界權力者的掌控與謀略機心終究不能被我所符應。所以,莊子又指點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真正要實踐的是對於“材與不材”的超越,從“無”來加以超越。
從道家的本體詮釋學來説,材與不材,即是不只知道采用正面,也知道運用反面,這樣的“相反相成”的辯證性還停留在“常有以觀其徼”的局限性之中(18)《道德經》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帛書《老子》甲本中此句爲:“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噭。”。此中,還要進一步到達“常無欲以觀其妙”,以無來觀生命存在的根源是虚無的深淵,返虚入渾,向上超越,進而與道合真,如此才能恢復生命存在的場所的靈妙。材與不材,用與無用,都落入片面性,修道者以“相反相成”的智慧來掌握,此乃“常有欲以觀其徼”,但是有時候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仍未能全善,此乃“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進而要“材與不材”全部超越,要有觀無的智慧,“常無欲以觀其妙”,nicht-wollon(無意欲)、Gelassenheit(泰然讓之)(19)nicht-wollon(無意欲)淵源於海德格爾關於謝林哲學的討論,筆者此前翻譯爲“無意欲”,彭富春翻譯爲“不意願”。Gelassenheit則是筆者跟從彭富春的翻譯,翻譯爲“泰然讓之”,此前翻譯爲“泰然自在”。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71頁。。這裏的無並不是有没有的相對的無,而是絶對的無,將情義我的各種粗細的執著整個“無”掉,“常有欲以觀其徼”,甚至於“無自無”,乃能向上超越。與道合真之後,修道者以有觀無,以無觀有,重玄道觀,重重無盡,以上經歷了“觀有”“觀無”“重玄道觀”的三個面向,經歷了莊子所説的“用: 材與不材之間”、“無用”、“無用之用(本體大用)”的三個面向,乃是來自老子所説的“爲”、“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是莊子運用老子的無爲思想而在實用論上的創造性詮釋,而其思想模型都來自於“觀有”、“觀無”、“重玄道觀”的有無玄同的本體詮釋。
老子哲學的本體論闡明在實踐功夫上的“觀有”、“觀無”、“重玄道觀”,而莊子其物逍遥的玄觀境界則發揮爲“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寓言故事: 堯治天下民,平定海内政,往見四神人於藐姑射之山,忘天下。莊子圓教以秋水之寓言來玄觀大道則爲“以無觀”、“以功觀”、“以趣觀”。至人以無觀,萬物無貴賤。神人以功觀,萬物功分定。聖人以趣觀,萬物莫非自然(20)《莊子·逍遥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秋水》:“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柏格勒(Otto Pōggeler)指出: 海德格爾1960年的Bremen(布來梅)演講《意象與世界》引用了莊子《達生》篇所説的“梓慶爲鐻”的故事,運用了莊子的美學思想(21)參見柏格勒(Otto Pōggeler)《東西對話: 海德格爾與老子》一文,收入帕克斯(Graham. Parkes)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此處的討論參見《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第55頁。。他在這個演講之中,將莊子的思想以及Heraclitus(赫拉克利圖斯)的思想當作是本源性的思想,可以帶領吾人走向一個新的思想起點。
帕克斯也指出在1930年10月9日,海德格爾關於《真理的本性》的演講,提到了《莊子·秋水》之中的莊子與惠施關於魚樂的討論(22)參見Thought on the Way: Being and Time via Lao-Chuang一文,收入帕克斯 (Graham. Parkes)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第 105頁。。一直到1943年,他才出版《真理的本性》此一文本,而1946年他才開始與蕭師毅翻譯《老子》爲德文。
但是,海德格爾高度評價謝林對老子哲學的詮釋,從形上學的根本問題來詮釋老子的無,並和九鬼周造討論東西美學,則起於20世紀的20年代。實際上海德格爾關於老子的興趣起源於20年代,而不是如帕克斯説的只有晚年的海德格爾才提到老子的道而加以詮釋以作爲另一個思想的開端。
這兩條海德格爾討論莊子的文本,對於我們海德格爾在其存有思想之中運用莊子的無用之用一説,雖然没有直接的相關性,也可以當作背景理解之參考。
圖 老子的有無玄同與三觀(“觀有”、“觀無”、“重玄道觀”)

圖 莊子的無用之用與三觀: 以功觀、以無觀、以趣觀

技藝(Techne)來自希臘字 τ僉χνη, 一般在英文中翻譯爲“craftsmanship”、“craft”或是“art”,海德格爾認爲技藝(Techne)原本是把存有帶入存有者的一種展現,具有解蔽(解除遮蔽)的意思;作爲技藝的解蔽相當於希臘人所説的Aletheia。但是,羅馬人以Veritas來翻譯之,如此就將真理變成爲一種對於正確性(Richtigkeit)的追求,乃是表象式的語言之符合於外顯的事實,如此使得存有的真理觀從解蔽(解除遮蔽)的真理觀淪喪成爲一種符應的真理觀。海德格爾認爲Aletheia應該是A-letheia,而其真義是解除遮蔽。解蔽(解除遮蔽)的真理觀除了别於符應的真理觀,它和開顯的真理觀也是不一樣的。海德格爾的真理觀由《存有與時間》(1927)的開顯的真理觀,發展到了後來的解蔽的真理觀,解蔽的真理觀是A-letheia解蔽(解除遮蔽),是一種即開顯即遮蔽,以及對於不斷自我退隱的遮蔽性的自覺。因此同時掌握到開顯與遮蔽,同時也體會到這個不斷自我退隱的遮蔽性是一種無,一種無自無的超越,因此它乃是存有的真理。
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討論了海德格爾關於技藝的本性的思想回溯到解蔽的思想(23)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第145頁。。海德格爾説“那種帶出來基於解蔽”(24)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Verlage Guenther Neske,第七版,1994),第16頁。,技藝的本性“它是解蔽亦即真理的領域”(25)同上。。海德格爾回到古希臘的技藝觀來省思此中的問題,技藝(art)是手工活動和能力,同時也是美的藝術的名字。海德格爾:“技藝從屬於那帶出來,從屬於詩作,它是某種詩意的。”(26)同上。這裏所説的詩是指“poesis”,是一種生産、詩境的創生,是一種帶有詩性美感的境界創生。
Poetry(詩)的字源來自於希臘文的Poiesis,本來也是創造或生産的意思,希臘人將創造、生産和詩歌當作是一回事,此中的深意值得吾人深思(27)高宣揚《生命的自我創造》,廣東醫學院演講稿,2015年5月。Autopoiesis(自我創造、自我生成),馬度瑞那(Humberto Maturana)所創,是指自我生成是在機體原有的組織結構中不斷繁衍分化,使得機體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能處理週遭環境的變化。自我生成是魯曼(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指有機體和社會系統内在透過其本身組成分子的交互作用,因此會有持續生長發展的傾向。此字的德文字Selbstschöpfung是兩字組合而成,前者指自我,後者指創造或生成。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和Autopoiesis的關係參見Being-in-the-world, Temporality and Autopoiesis-Parrhesia(journal)。。海德格爾引用《柏拉圖對話録·饗宴篇》205b而重新將poesis加以詮釋,他説:“帶動它,讓它自尚未出現中超出,再往前成爲出現。這種帶動就是生poiesis,也是帶往前來(Hervorbringen)。”(28)QT10,TK11。陳榮華《海德格爾哲學》,(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頁。海德格爾這裏所詮釋的poiesis是一種帶動再往前成爲出現,此處要注意的是“讓它自尚未出現中超出”,必須從“解蔽”(Unverbongenheit)來理解,它越過了遮蔽而到達解除遮蔽的情況。海德格爾説:“詩作爲對安居之度本真的測度,是建築的本源形式。詩首先讓人的安居進入它的本性。詩是本源的讓居(Wohnenlassen)。”(29)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想》,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頁。
海德格爾也用老莊的“道”來加以闡明。作爲區域,未隱蔽狀態是本源的運動,是道路本身(道,如老子所説)。海德格爾把存有的真理瞭解爲同時展現和隱蔽,瞭解爲未隱蔽狀態的本成發生(Ereignis)。在世界中支配着的東西是未隱蔽狀態的進行展現的自身的遮蔽,是一種本成發生。這裏所説的“同時展現和隱蔽”、“未隱蔽狀態的進行展現的自身的遮蔽”(30)柏格勒《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臺灣)仰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3頁。筆者對於某些文本根據德文重新翻譯。可以以更爲中文傳統式的方次而表達爲“即開顯即遮蔽”。
Poesis與對於現代的科學技藝的批判: 現代的技藝變成了一種現代的科學技藝,被一種“强索”(Herausfordern)所控制,失去了poesis“詩性創生”的特質。海德格爾以萊茵河上的電廠爲例,傳統的橋是架設在河流之中,屬於河流自然景物的一部分,而電廠則是吞噬了萊茵河,據爲己用,只是爲了滿足人類膚淺的物質慾望。海德格爾稱爲Gestell(架構)(31)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07頁。。
回到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的發展過程來思考“無用之用”的課題。藝術作品的根源是存有的真理將自己設置於作品之中,因此,存有的真理將自己設置的動作乃是“即開顯即遮蔽”,此乃是“技藝”(techne)的古意,這樣的“技藝”(techne)乃是一種“無用之用”。但是當“技藝”變成一種“科學技藝”(科技),則變成一種外加於自然的强索的控制方法,使得人和自然都異化了。《山木》篇所説的“材與不材”都是一種開顯,開顯爲某一種限定性或是此種限定性的闕如,比如會叫的鵝或是不會叫的鵝,如此都落入於一種遮蔽之中。透過此有的時間性來開顯存在的意義,回到本真,也還是落入於某種限定性的自我理解,因此也還不能真正回到根源性的思想,因爲没有能體會“即開顯即遮蔽”。只有通過“無的無化”,才能真正超越存有的遺忘,真正把握到存有學的差異。
柏格勒追索海德格爾此中的思想的發展過程説:“在《存有與時間》的發表的部分所達到的最高點上,此在地實際存在證明自己爲空虚的基礎。……論文《論根據的本質》和演説《甚麽是形上學》接受了在《存有與時間》中已經被提出的任務。《甚麽是形上學》問到了虚無,《論根據的本質》問到了存有學的差别。”(32)柏格勒《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第97頁。筆者對於某些文本根據德文重新翻譯。《論根據的本質》在於在存有學的差異之界域中,追問存有者作爲存有者,追問其理型形式、實體、本質。只有在《甚麽是形上學》才到達了真正的突破點。
以上關於“無用之用”的討論,也涉及老子所説的“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海德格爾意識到此一課題,在1949年12月的不來梅演講《物》(DasDing)(33)海德格爾《物》(Das Ding),1950年6月,講於慕尼克的巴伐利亞藝術學院,收於《演講與論文》(Verlage Guenther Neske,第七版,1994),第157—180頁。,海德格爾舉“壺”(Krug)當例子來解釋“無”的重要性——“做爲容納的器皿的壺的物性決不在於它由以構成的材料,而是在於具有容納作用的虚空”(34)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Verlage Guenther Neske,第七版,1994),第161頁。。柏格勒認爲這裏的思想正和《道德經》十一章的“埏埴以爲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一致的(35)相關討論見柏格勒《海德格爾新的道路》(NeueWegemit Heidegger),第406頁。。“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其實,海德格爾這裏關於老子的“無之以爲用”的討論必須放在他對於《莊子》“無用之用”的討論之中,才可以釐清,這裏所涉及的是莊子的“以明”的第二個面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綜合以上所説,莊子所講的“無用之用”,是由老子所説的“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再加以發展而有的,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也討論了這兩個課題。莊子的突破之處,在於以“心”來闡明“無用之用”,以絶對真心的心靈境界來闡明之。《莊子》的《逍遥遊》一篇所説的“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是“無用之用”的心靈境界,是逍遥遊的心靈境界。
二、 莊子的“以明”與海德格爾論存有的真理
(一) “無意欲”(nicht-wollen): 謝林與海德格爾的道家哲學詮釋
莊子哲學對於老子思想的發展的第二個特色在於朝向絶對的真心説而發展。“心”在莊子書上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如“師心”、“機心”、“不肖之心”、“賊心”……一切的巧智機械都是由這些後天的妄心而發生出來的。這一種意義的心爲種種外欲所吸引牽絆,從而人爲之所奴役。另一種心是真心,即“常心”、“静心”,莊子又用“靈府”、“靈台”來形容這種真心。二者之間的則是“成心”。唐君毅曾以“靈台心”來總説莊子的哲學。
《莊子·天地》叙述了丈人抱甕出灌及與子貢對話的故事,對於“機心”加以批評。文曰:“子貢南游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天地》這裏對於“機心”的批評,比較偏重在否定性的、消極性的一面,還没有涉及到絶對真心的積極内涵,所以還不是圓教意義下的道家心性論。莊子要修道者通過心齋坐忘,來去除機心、賊心,恢復“靈台心”。“靈台心”具有“明”的功能,下文探討莊子所説的三個面向的“以明”,並比對於海德格爾之所説。
對於機心的問題,海德格爾認爲不可能廢除、打倒或毁滅技藝,而是要善用技藝,要從存有的思想來重新善用技藝,他説:“如果説存有的變化——現在是框架的本質的到場——將發生,那麽,這可絶對不是説,本質在於框架的技藝將被廢除。技藝不會被打倒,也肯定不會被毁滅。”(36)海德格爾《關於技藝的問題》,第37頁。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第117頁。
如前文所述,筆者在此探討莊子比較於老子所具有特色之處,在於下列三點: (1) 用(庸、無用之用);(2) 心(靈台心);(3) 化(物化)。莊子哲學因此具有絶對唯心以及藝術化的傾向。現在,此節探討的是第二點心(靈台心),此處所要展開的是《齊物論》所説的“以明”的三個面向。
謝林是西方道家思想詮釋史之中第一個從形上學根本問題的角度來掌握老子哲學的哲學家。謝林《神話哲學》從形上學基本問題的高度來詮釋老子的哲學智慧,他説:
道的學説不是一種發揮了的體系,體系力求提供關於事物産生的詳細解説。道的學説毋寧説更多是討論一種原理,不過卻是以多樣的形式,並討論基於這一原理建立起來的實踐學説。(37)謝林《神話哲學》第2卷,第564頁。F.W.J. Schelling, Ausgewählte Schriften(《謝林選集》),Band 6(第六卷),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出版社,第576(564)頁。
謝林這裏關於“自然”、“意願”的見解,其實在作於1809年的《論人類自由的本質》一書之中已經有其雛型。謝林於此認爲“被説出來的真實的道言(Wort)是光明與黑暗的合一”,此中,一方面是知性的光明的原理,一方面是求索於自然之中的遮蔽的黑暗的原理,這兩個原理必須活生生地同一在人類的靈魂之中。這裏所説的光明與黑暗的合一,來自老子所説的“知黑守白”、“混沌”、“恍惚”,我們想到莊子所説的“以明”、“葆光”。一般人只具有知性的光明的原理,而不具備自然之中的遮蔽的黑暗的原理。“靈魂就是這兩個原理的活生生的統一性,這樣的靈魂就是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存在於神之中。”(38)Reclam版謝林的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第77頁的相關討論。
海德格爾自覺地繼承謝林的《老子》詮釋,從而抉擇了謝林所説的“無意欲”(nicht-wollen)的哲學,捨棄了尼采的超人、權力意志等學説的意志哲學。海德格爾從“無”的超存有學來重新把握根源性的存有思想,他在《泰然自在》(Gelassenheit)一文説“在傳統方式下所瞭解的思想,它是作爲表象的,則它就是一種意志(das Wollen)”,相對於此,根源性的思想則是“無意欲”。但是這裏的“無意欲”並不是對準意志而加以否定。這裏的是完全超越於任何一種意志,它並不存在於意志的領域,它存在於意志所無法理解的另一個領域。從意志的領域解放到“無意”的領域,並不是棄絶意志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而唤起(erwachen)泰然自在,而是要保持覺醒(Wachbleiben)(39)陳榮華《海德格爾哲學》,第164頁。陳榮華將Gelassenheit翻譯爲“静觀”。。謝林在討論人類自由的本性的時候所提到的“無意欲”(nicht-wollen),並不是對於意志的否定,不是對於生存的意欲、願望的否定,而是一種超然,不受其影響而能自由地投現,在投現的時候又保持自身的空明。這樣的“無意欲”存在於另一個領域,存在於真實的本體之中,也就是存在於本成(Ereignis)與道(Tao)的領域。這樣的空明自由的本體生起妙用,物物化,無無化,世界世界化。
《莊子·齊物論》的三個面向的“以明”闡明了謝林這裏所説的由知性分析的原理,到達求索於自然之中的部段自我隱蔽的無的原理,以及神性精神的靈魂之中的光明與黑暗的兩個原理的活生生的統一性原理。
(二) 《莊子·齊物論》的本體詮釋三個面向的“以明”
基於《莊子·齊物論》文本的分析與詮釋,莊子這裏所説的“以明”包含了三個面向: 知性分析的“以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以明”,本體妙用的“以明”。筆者本文就此加以闡明,並且給予本體詮釋學的闡明。
《莊子·齊物論》第一個面向的“以明”是在知性的分析以及機械性的因果法則之中來做邏輯推演的論辯,具有第一面向的“以明”的人明確地知道這種知性分别,而更瞭解正面與反面是相反相成的道理。《莊子·齊物論》: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對於敵方論點所反對者加以贊成,對於敵方論點所贊成者加以反對,例如儒墨之是非,例如墨家主張薄葬非樂以攻擊儒家的厚葬隆樂。
又,第二個面向的“以明”是以無應有,“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子·齊物論》:“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不同的是非陳説各有其所堅持的理由,得道的聖人並不因於如此的是非,而是“因是(Suchness)”,任其自在(lets it be),再由無來超越、提升,“照之於天”、“得其環中”。此處所謂的“環中”是指“無”的超越智慧,來自老子所説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照之於天”就是“照之於無”,也就是老子所説的“常無欲以觀其妙”。掌握了這個虚無的超越智慧的環中圓心就可以“以應無窮”,因爲在無的以明觀照之中,圓周的每一點也都可以是圓心,都在當下成就以其自己來成就自身的圓滿,是非兩端之中的“是”是無限(無窮),“非”也是無限,因此在第一個面向的以明之中的“是非”得到解放了,“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莊子·齊物論》第三個面向的“以明”是文中出現兩次的“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爲“無用之用”的積極内涵,而其狀態是“滑疑之耀”的葆光體驗。
《莊子·齊物論》的“以明”的第三個面向:
第一條:“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第二條:“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40)“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平常的事物”乃是大道玄化之顯化。《齊物論》最後叙述了一個莊周夢蝶的物化的寓言故事,“物化”乃是道化。從無的超越智慧來觀照,從覺者(醒過來的莊周)來看,夢蝶雖然虚幻不實,但是在覺夢必有分矣而有的存有學的區分之中,夢蝶此一事物界大道的玄化,稱之爲“物化”。
兩次出現的“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都用“用”來解説“庸”,此處“庸”就此字義相通於《中庸》所説的“庸”,“庸”是指平常的事物、日常生活中的本體作用。此外,《中庸》也很重視“明”,講求“自誠明”、“自明誠”。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中的“達者”是指達道者,知道整體的自然大化的人。“爲是不用”就是不用“爲是”,“爲是”的“是”就是前面所説的“彼是”的“是”,落入於彼此是非的無窮的争論之中。
在三種“以明”的解説之後,《莊子·齊物論》最後提出了“葆光”:“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的“葆”具有遮蔽的意思,“不知其所由來”是一個不斷遮蔽它自身的根源性的道;即使這個根源性的道解蔽而開顯,也仍然是一種即開顯即遮蔽,在場與不在場的相反相成,如此方能“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圖: 莊子的“以明”的三個面向

“以明”的三個面向以及其本體詮釋: 《莊子·齊物論》所説的“以明”包含了三個面向: 第一,知性分析的“以明”;第二,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以明”;第三,“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本體妙用的“以明”。筆者就此給予本體詮釋學的闡明,也就是運用“體-相-用”的體用論的思考方式加以詮解。知性分析的“以明”屬於“有”的面向。其次,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以明”屬於“無”的面向。以上兩個面向屬於“作用”的層次。知性分析的“以明”屬於“有”的面向,正如老子所説的“常有以觀其徼”,在這裏是要能够觀照現象作用的相反相成。其次,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以明”屬於“無”的面向,莊子説“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最後,莊子説“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又解説這裏的庸是常(常道)的意思,此一本體妙用的“以明”屬於“體性”的層次,生命體驗的存在根基全然轉换之後,得以“重玄觀道”,在超越性的道的體性由上往下來無限無窮地觀照有無重玄,在道的化境之中,以有觀無,以無觀有,交涉互攝,重重無盡,如此本體妙用,道化本成,最後達到此一道化境界自然而然,道法自然。
圖: 老子的有無道與體相用的本體詮釋

莊子的“無用之用”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本體詮釋乃是淵源於《道德經》,例如《道德經》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中所説的“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此不盈之用淵源自“道沖”,而且以“淵兮似萬物之宗”來形容此一“道沖”與“道沖的不盈之用”,則其本體詮釋的意味甚明顯。顯然莊子的“無用之用”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不只是主體的主觀境界,如牟宗三、勞思光之所言。牟、勞二氏强調以主體性哲學來詮釋老子莊子的道不符合老子原意,也不是老子莊子的詮釋史之中的事實。又,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谷神、玄牝、天地根來解釋“用之不勤”,此一“不勤之用”也是本體詮釋的意味甚明顯。老子雖然没有用到莊子的“無用之用”這四個字,但是他討論到了“玄牝”、“天地根”的“不勤”之用與“道沖”的“不盈”之用,莊子的“無用之用”出於老子乃是明顯的事實,而且“無用之用”是具有本體詮釋的意義。海德格爾關於莊子的“無用之用”的詮釋的基本立場是本體詮釋學,乃是符合老子與莊子相關討論的原始含意的。
復次,《莊子·齊物論》《莊子·逍遥遊》的“無用之用”也出於、也涉及《道德經》十一章所説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海德格爾在1949年12月的不來梅演講《物》(DasDing)(41)海德格爾《物》(Das Ding),1950年6月,講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藝術學院,收於《演講與論文》(Verlage Guenther Neske,第七版,1994),第157—180頁。,就以“壺”(Krug)當例子來解釋“無用之用”,正是出於《道德經》十一章。而海德格爾此處討論所涉及的“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就是莊子説的“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淵源。“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以明”的第二個面向,也是“無用之用”的本體詮釋的第二個面向。海德格爾所説的Ereignis(本成發生)是“以明”的第三個面向,思想者與存有的共同隸屬之中一如,此一共同隸屬顯示的是差異化活動的不斷生成發生。
海德格爾以“林中空地”來闡明“澄明”(Lichtung)的三個層次,天光照入“林中空地”之中,林中空地明明滅滅。此中,首先“澄明”(Lichtung)不是“理性的光明”,而是在遮蔽之中呈現的解蔽,遮蔽比開顯更爲原初,因爲有遮蔽才有所謂的開顯,開顯因此而成爲一種敞開。“理性的光明”就像刺眼的陽光,並無法讓我們看清楚林中空地,並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讓我們看清楚林中空地的是“澄明”(Lichtung),是即開顯即遮蔽的澄明。而更重要的是自我隱藏着的遮蔽性本身,這個遮蔽性是一個奥秘,暗示了林中空地最爲深刻真正的本性。如此,林中空地的開顯是“澄明”的最末端的層次,即開顯即遮蔽的“澄明”則是“澄明”的中間層次,而自我隱藏着的遮蔽性本身則是“澄明”的最根源的層次(42)參照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第45—50頁,“2.1.2爲了自身遮蔽的林中 空地”。。這裏所説的海德格爾闡明的“林中空地”之“澄明”的三個層次就如同《莊子》所説的“以明”的三個面向。至於刺眼的陽光一般的“理性的光明”,只是《莊子》所批判的“機心”,並没有辦法讓我們體會到真正的“林中空地”,無法讓吾人體驗到生命的存在之真實界域。
海德格爾在他的演講中討論《莊子》的“無用之用”,從而涉及到了“以明”的課題。“以明”表達了《莊子·齊物論》的知識論,而“無用之用”在《逍遥遊》一篇則表達了逍遥的生命境界論。在此一脈絡之中,“無用之用”的三個面向的本體詮釋的圖解如下。
圖: 莊子的“無用之用”

莊子的“以明”在老子思想中的淵源:
《道德經》多次講到“明”。“知常曰明”(十六章),“是謂微明”(三十六章),“明道若昧”(四十一章),“見小曰明”(五十二章)。此中,二十七章所説的“襲明”有二解: 一是遮蔽,一是繼承。就遮蔽來説,聖人順化自然,絶聖棄智(帛書《老子》作“絶聲去智”),遮蔽自己外顯的光明,謙下柔弱。《道德經》十五章也説“蔽不新成”。“蔽不新成”(43)通行本:“孰能濁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或作“敝不新成”,河上公本、王弼本、范應元本作“蔽不新成”,傅奕本、帛書《老子》乙本作“敝而不成”(44)帛書《老子》乙本作“敝而不成”,敝字爲敝與衣的合體字。韓禄伯(Robert G. Henricks)《簡帛老子研究》,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頁。。近代學者易順鼎、馬叙倫依據二十二章的“敝則新”改爲“蔽而新成”。“敝則新”説的是相對的概念的問題,而此處則涉及到功夫論,所以將“敝則新”改爲“蔽而新成”並不洽當。又,“敝”是破蔽的意思,而“蔽”則是“遮蔽”的意思,此處是在描述修道者“微妙玄通”之狀態,所以當以“蔽”字而爲“遮蔽”的意思較佳,修道者微妙玄通而遮蔽其外顯的光華,如此也相通於莊子的“以明”,最後歸結於“葆光”。
復次,《道德經》的“襲明”的“襲”也可以解作繼承,繼承道的常明,所謂的“知常曰明”。吴怡認爲“襲明”的襲是繼承自然的常道,在《莊子·齊物論》中,强調是非不用而寓諸庸,一連詮釋了三種“以明”,就是莊子所説的“照之以明”,順承天道之明(45)吴怡《老子解義》,(臺灣)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95頁。。
(三) 海德格爾從“開顯”(Erschlossenheit,disclosedness)到“解蔽”(Unverbongenheit,unconcealment)的真理觀
1927年的《存有與時間》所説的真理觀是要開顯存有的意義,這是“開顯”(Erschlossenheit)的真理觀,是以詮釋學現象學來對此有(Dasein)從事存在分析,是“在世存有”,進而闡明“在世存有”的“在”、“世界”、“存在”的時間性的未來、過去、現在的三個實存方式,也就是以境遇感(Befindlichkeit)、理解(Verstehen)、言説(Rede)的時間性實存方式來作爲超越界域而能够開顯存有的意義,生命的實存是背負過去、面對未來而在現在去言談並且通過抉擇(Entschlossenheit)而詮釋出生存的意義。
但是,隨後海德格爾反省到存有的意義的開顯這個説法已經預設了既已開顯,所以已經不是本源性的思想。“存有的意義的開顯”已經遮蔽了自身,因爲它忽略了既已開顯就已經有所遮蔽,也遺忘了開顯的存有活動是在“即開顯即遮蔽”才有其靈妙的動能。
復次,遮蔽是存有的真理之核心。柏格勒説:“如果遮蔽被思考爲真理的心臟核心,那麽,存有的真理不再能作爲先驗的視域而被把握。當然,它也不再能作爲存有的意義而被把握。”(46)柏格勒《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第189頁。筆者對於某些文本根據德文重新翻譯。“開顯”的真理觀的問題在於所開顯的意義追索其本真性(Eigentlichkeit,Authenticity),然而所謂開顯的本真到底是不是真實的本真,其實開顯已經預設了遮蔽,開顯了某一面必然已經有所遮蔽,遮蔽性其實比開顯的活動更爲原初,更爲本源。
復次,這裏所説的比開顯的活動更爲原初的遮蔽性,它就是“無”、“虚無”,是實存的深淵(Urgrund),是無基礎(Ungrund)。柏格勒引用《哲學獻集》説:“存有在其真理之中是基礎,即它的基礎是遺漏的,基礎作爲深淵。作爲深淵的基礎同時是無基礎。它掩蓋和掩埋了它自己的建立,並且只做爲深淵和無基礎,它才是原始基礎。”(47)同上,第193頁。筆者對於某些文本根據德文重新翻譯。追尋基礎的思考方式是表象性思考,還落入在存有神學構成之中,開顯已經預設了有所遮蔽,遮蔽是比開顯更爲根源的。遮蔽和解蔽則是同等原初的。事物的開顯已經有遮蔽,對於這個狀況的自覺已經是一種解蔽。此處的解蔽不是對於開顯意義上的解蔽,而是對於開顯已經預設了有所遮蔽的自覺,而透過無、無自無來回返於這個遮蔽的根源本身。解蔽是對於相反相成的解蔽仍在遮蔽的根源本身這一回事的自覺。此後是要深入於遮蔽的根源而反虚入渾,通過虚而回返於存在的深淵,體會到Ereiginis(本成發生),Ereiginis(本成發生)是“即開顯即遮蔽”的。而海德格爾現在闡明的“解蔽”的真理觀,是回到“遮蔽”這個存有的真理的根源,“遮蔽”是虚無的深淵,它不斷地無化它自己(無自無),所以這樣的深淵本身又是無基礎的、無住的。
復次,對於“即開顯即遮蔽”這樣的存有,並不能够通過此有的主動的“投現”(Entworfenheit,projection)而掌握,而是要被動地加以“領受”(Vernehmung)(48)陳榮華《海德格爾哲學》,第83頁。。現在,“投現”的並不是人的此有,而是存有本身。人的此有唯有通過“無”、“無意”才能够真正傾聽此一存有本身投射給人的澄明(Lichtung)。
在此,海德格爾從“開顯”(Erschlossenheit,disclosedness)的此有的真理觀,進展到“解蔽”(Unverbongenheit,unconcealment)的存有的真理觀。海德格爾在晚期思想之中,以Ereiginis(本成發生)的“即開顯即遮蔽”來進一步闡明存有的真理。
(四) 海德格爾與老子莊子的道言觀: 海德格爾的道言觀的發展過程以及與莊子老子的對比
晚期的海德格爾從存有思想來把握語言,“語言是存有的屋宇”。“言自言”(Die Sprachspricht)、“道言(Sage,Logos)”,語言將它自己説出來,而不是人去説出語言。人所説出的語言是“道無常名”,難易相成,高下相傾,人所説出來的難易高下等等語言的使用都是在相對性、無常流轉之中。比較起海德格爾所在文化傳統,不管是希臘或是希伯來都是重視Logos(言),老子比較强調“常道無名”、“道常無名”,重點在於“無名”。“常道無名”是就道體的不可思議、不可言説而言。而“道常無名”則就無相、虚實合成妙象而説,以“無”、“無名”、“虚”、“一”等超越屬性來指點關於“道”的體驗。以“無”等超越屬性來指點“道”並不可以加以辯解論説,而是爲修道者指點出超越性的向上一機。莊子哲學走向即現象即本體的絶對唯心的現象論,其思想更有藝術的化境,和老子的道論又有所不同,但是也是從老子思想發展而來,並不能孤立來研究。又,晚期的海德格爾雖然强調“言自言”(Die Sprachspricht)、“道言”(Sage,Logos),但是也通達“無意欲”(nicht-wollen)、“泰然讓之”(Gelassenheit)、“寂静”(Stille)、“無”、“空”,和東亞的禪宗與道家思想有很多對話,架起了東西方當代哲學溝通的橋樑,也爲了現代之後的人類生存問題提供和東亞哲學攜手合作的方案。
將上述討論,以下列圖來表示:
圖一: 早期的海德格爾思想之路: 《存有與時間》的基本存有學(Fundamentalontologie)

圖二:轉折(Kehre)剛開始的海德格爾思想之路: 《什么是形上學》

圖三:晚期的海德格爾思想之路: 本成的轉折是存有自身和思想在即顯即隱之中的共同隸屬: 《哲學獻集》《同一與差異》《時間與存有》

圖四: 老子的有無玄同(比較於前圖,顯示老子和海德格爾思想的親緣性)

圖五: 老子的有無玄同(比較於圖三,顯示老子和海德格爾思想的親緣性)

圖六: 老子的語言觀:“常道無名”、“道常無名”、“道無常名”

哲學的道可分爲“不可道的常道”和“可道之道”兩個層面,此涉及“道的二重性”的課題。老子哲學的語言觀(道言觀)包含了“常道無名”(《道德經》一章)、“道常無名”(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一章)(49)通行本《道德經》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以及“道無常名”(二章)(50)通行本《道德經》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論者以爲這是莊子對於老子所説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詮釋。
圖七: 莊子的語言觀:“一”、“言”、“道無常名”

海德格爾説:“人如果想尋找他再度進入存有的近旁的道路,那麽他首先必須學會在無名之中生存。”(51)海德格爾《基本著作選》,第199頁。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第45頁。不管是林中之道的隱喻,或是此處所説的存有的近旁的道路,首先是要以“無名”才得以進入而生存於其中。
海德格爾説:“由於思想把它從存有而來的道言放到語言中去,以之作爲生存的寓所,思想便關注着存有的澄明。”(52)海德格爾《路標》,第361頁。語言是存有的寓所(安宅),而言自言的道説(道説出它自己)才使得思想者得以進入此一寓所,此一寓所安居在林中空地之明明滅滅的澄明之中,而隱入自身遮蔽的本源性之中,與大地的終極祕密在寂静中一同澄明(53)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第50—54頁,“2.1.3自身遮蔽的本源性”。。
三、 莊子的“物化”與海德格爾的“物物化”(Das Ding dingt)
如前所説,筆者在此探討莊子比較於老子所具有特色之處,在於下列三點: (1) 用(庸、無用之用);(2) 心(靈台心);(3) 化(物化)。莊子哲學因此具有絶對唯心以及藝術化的傾向。此節探討的是第三點: 化(物化)。
王節慶的論文《道之爲物: 海德格爾的四方域物論與老子的自然物論》比較研究海德格爾的四方説的物論與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物論,很具有洞見與突破性。王文就《老子》通行本統計老子對於道、物、有、無的出現次數。“物”字出現共24章,達32次之多,“無”字出現共38章,“有”字出現23章,可見得“物”在老子哲學的重要性(54)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第82頁。。
在《道德經》之中,“物”有時候就是“道”的意思。比如“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二十五章)、“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其中有物,其精甚真”(二十一章)。
在莊子一書中,“道”字出現308次,“大道”、“天道”各出現6次,“物”字出現221次,“萬物”出現101次(55)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第102頁。。可以見出“物”在莊子哲學的重要性。其實,莊子以爲現象就是絶對,莊子其書又着重以“寓言”來進行,故鯤鵬山木等現象、物都是“道”的顯化,因此,“物”的道化思想在《莊子》一書之中觸目即是。其實,講“物”是“道”的顯化在莊子哲學中有其語病,因爲這種説法落入將“道”實體化,是一種本源——回返的思想方式,而此乃老子的思想特色,恰好是莊子要加以超越的。就此,莊子《齊物論》提出“物化”。
相對於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强調的是本源、根源,所以偏重於道論。而莊子哲學則從本源性的道論更加走向現象論,由道的實體説走向萬物的現象論,莊子是要吾人“吾喪我”體會絶對真心,如其所如觀照萬物,從而萬物現象都是活生生的道的顯化,大道玄化就是《齊物論》説的“物化”(56)《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這裏所説老子與莊子的物論,是一種道化的物論,本來現成的物就是道化。海德格爾也常説“物物化”、“世界世界化”。
王凱認爲海德格爾與莊子的物論是不同的,他説:“對物的道的態度是莊子所肯定的,對物的詩意的態度是海德格爾所提倡的。”(57)王凱《道家詩性精神: 兼與海德格爾比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筆者認爲這種説法太過於執著文字的表面,没有看到二者思想在深處的匯通,其實所謂的“對物的詩意的態度”所涉及的詩性是poiesis,是一種帶動再往前成爲出現,此處要注意的是,Poeisis(詩性創生)是“讓它自尚未出現中超出”,也就是透過虚無來聚集而有物之發生。遮蔽是比存有的意義的開顯更爲根源的。存有的道言以存有(Sein)上面畫××來表現,思如詩,在虚無深淵中敞開而成爲天地人神的四方。遮蔽與解蔽是同等源初的,都同屬於根源性的道言,有如“原野之路”(Feldsweg)。此路不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被有計劃地製造來連接城市。“原野之路”則屬於原野,屬於大自然,不是一個對象,而是開端性的生成。原野道路是一條這樣的道路,它運動於“林中空地”之中。“林中空地”,天光穿越林間,明明滅滅,即開顯即遮蔽,遮蔽與解蔽或者説光與暗是同等源初,都在道路的向前運動的左右上下的不同界域中明明滅滅,生命存在於這樣的“林中空地”得以真正的自由,天地神人四方在此遊戲和諧,得以逍遥遊。
黄漢青在書中闡明了老子莊子與海德格爾的物論之不同,這是筆者所不贊成的。他認爲:“海德格爾物物化和世界世界化的觀念不能與莊子的物化混爲一談。”(58)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第82頁。海德格爾的物化之説,是指物透過虚無而敞開,讓四方聚集並且互相趨近;而他認爲“莊子以人對物起作用爲起點,把物論歸結在以虚静之心應物,把道之無拉回到人之主體。”(59)黄漢青《莊子思想的現代詮釋》,第104頁。
筆者以爲: 莊子是以人爲起點,强調絶對真心,現象即事而真。而老子的物論或説是道論,强調的是其作爲本源的本體意義,而和莊子的現象即是本體有所不同。但是,莊子哲學是老子哲學的發展,所以應該説老子的物論的最高峰就是莊子的物是大道玄德的現象即本體之物論。海德格爾的物論分爲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的物論以中空的壺和屋宅爲例子,闡明通過虚無而敞開和聚集成爲物,這明顯是相通於老子的物論。而海德格爾的物論的第二個面向闡明四方的映射——遊戲(Spiegel-Spiel),則是和莊子的莊周夢蝶的物化説默識心通。海德格爾的物論包含了不同面向的逐步深化的過程,而符合於老子物論進展到莊子的物化之説的先秦道家思想的發展脈動。
老子所説的“無”、“四大”和海德格爾討論的無是在四方的思想架構,亦有其異曲同工之妙。下面對此加以解説。
在1949年12月的不來梅演講《物》(Das Ding)(60)海德格爾《物》(Das Ding),1950年6月,講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藝術學院,收於《演講與論文》(Verlage Guenther Neske,第七版,1994),第157—180頁。,海德格爾舉“壺”(Krug)爲例來解釋“無”的重要性,闡明“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海德格爾説:“做爲容納的器皿的壺的物決不在於它由以構成的材料,而是在於具有容納作用的虚空。”(61)同上,第161頁。
海德格爾運用“壺”(Krug)爲例來闡明“無”,柏格勒認爲這個説法正和《道德經》十一章的“埏埴以爲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一致的(62)相關討論見柏格勒《海德格爾新的道路》(NeueWegemit Heidegger),第406頁。《道德經》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其實,更多的例證存在於海德格爾《建築、居住、思想》一書對於“居住”(Bauen)、“屋宅”(Haus)、“安居”(Wohnen)的闡明與《道德經》十一章所説的“鑿户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的思想的相通性。“屋宅”因爲中空虚無才能有其居住的用途,人才能在其間有自由澄明的生活。
“物”的存在是因爲虚無敞開了存在的界域、聚集了諸條件才能有物的存在。關於物、有、無的關係,《道德經》四十章稱“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在《物》此一文本,海德格爾在討論了“壺”、“無”之後,隨即討論了“天、地、神、有死者”(Erde,Himmel,Göttlichen und die Sterblichen)的“四方”(Geviert)的思想,十分類似於老子所説的“四大”。
海德格爾説:“物物化,物化之際,物居留大地與天空,諸神與中有一死者: 居留之際,物使在它們遠中的四方互相趨近,這一趨近即是近化,近化爲切近的本質。”(63)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海德格爾選集》,第1178頁。
海德格爾説:“地、天、神和有死者,從其自身而有的互相隸屬,從統一的四方的純真之中而有共同隸屬……這種失去小我的轉讓(dieses enteignendeVereignen)就是四方的映射——遊戲(Spiegel-Spiel),由之而來,四方的純真才得到信賴。天地神人的純真的生成的映射——遊戲,我們稱之爲世界。世界在世界化中存在。”(64)海德格爾《物》(Das Ding),此處的討論參見《演講與論文》第172頁,後半的德文原文:“Erde und Himmel, die Göttlichen und die Sterblichengehören, von sich her zueinandereinig,aus der Einfalt des einigen Geviertszusammen ... Wir nennen das ereignende Spiegel-Spiel der Einfalt von Erde und Himmel, Göttlichen und Sterblichen die Welt. Welt west, indem sie weltet.”
海德格爾説:“我們把這四方的統一性稱爲四重整體,終有一死的人通過安居而在四重體中存在。”(65)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海德格爾選集》,第1185頁。
《物》這裏的思想被認爲和老子二十五章所説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的思想相通,都彰顯了物的渾成、周行不殆,道法自然,物物映照,相互和諧。此處所説的“世界世界化”(Die Welt weltet),這樣的“世界”是及手的(zuhanden)域中四大渾成的世界,而不是科技態度所面對的手前的(vorhanden)世界,甚至海德格爾《存有與時間》的存有意義的實存性,也并不足够到達此一“物物化”、“世界世界化”,此一世界世界化是《物》一開始所説的存在於遠方的近處(die Nähe)。在映射——遊戲(Spiegel-Spiel)之中,四方的四者遊戲着,且互相映射傳遞着遊戲,爲了互相的交互生成,四方互相隸屬,海德格爾以此“萬物輝映”的思想來對抗科技的“框架”(Das Gestell)對於自然的壓迫,海德格爾此一“萬物輝映”不僅近似於老子的四大渾成的思想,也更接近莊子《齊物論》所説的“天籟”、“天鈞”、“天倪”。
《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何謂和之以天倪?”
老子的生命境界經歷“地”、“天”、“道”的境界而最後到達的是“道法自然”。老子重視的是指點“道”之“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本體義,並强調“混沌”、“恍惚”、“杳冥”,此是對於修道者在修道之因上的層層指點。莊子則是鑽破“混沌”,超越“恍惚”“杳冥”的層層虚空,最後到達“寥天一”,是站在修道者證道之後,由果觀因,因果圓融,所以即現象即本體,爲絶對唯心的現象論。諦聽天籟,與“天鈞”、“天倪”同一造化,莊子鼓舞吾人在道家圓教之中“逍遥遊”,成就“天與人不相勝”的大宗師,回返人間世,德充符而應帝王。
《莊子·齊物論》:“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類似於莊子以天籟來闡明其物逍遥的境界,海德格爾常用聲音(吟唱、道言)的生命體驗來詮釋天地人神的四方的映射——遊戲(Spiegel-Spiel)與“萬物輝映”的“物物化”的存有思想,這是起源於他童年時候諦聽父親在教堂敲鐘而有的生命體驗。
海德格爾説:“吟唱和思想是詩作的相鄰樹幹。”(66)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全集》,第85頁。關於存有的吟唱和思想乃是詩性創造與安居的相鄰樹幹。海德格爾説:“在吟唱時,歌聲開始作爲歌聲去存在。歌聲之詩人是歌者。詩篇乃歌聲。”(67)海德格爾《通往語言的途中》,第189頁。彭富春《無之無化: 論海德格爾思想道路的核心問題》,第177頁。
在吟唱時,歌聲的臨在使得存有作爲敞開的場所而存在。里爾克(Rikle)《致奥爾弗斯十四行詩》説:“歌唱即此有(GesangistDasein)。”海德格爾解釋里爾克此詩説:“何時我們如此這般存在,以致於我們的存在就是歌唱。”(68)引自海德格爾《詩人何爲》,收入海德格爾《林中路》,第293頁。
海德格爾説:“歌唱之道言道言着世界實存的美妙整體,此世界實存在心靈的世界内在空間中無形地爲自己設置空間。……歌唱本身乃是‘風’。……冒險更甚者是詩人,而詩人的歌唱把我們的無保護性轉變入敞開者之中。因爲他們顛倒了反敞開者的告白,並且把它的不妙的東西回憶入美妙整體之中,所以,他們在不妙之中吟唱着美妙。”(69)同上,第294頁。
海德格爾晚期存有思想所達到的圓熟的境界只有在莊子的相應説法之中能得其解人。所以説,海德格爾與道家思想的對話起始於他於1920年代之初識老子而心動,而終極於他的晚期存有思想與莊子的默識心通。
結 論
莊子哲學對於老子思想的發展的三個主軸,首先在於莊子闡明“無用之用”是一種逍遥遊的心靈境界所顯化的本體大用,這是莊子在實用論、價值論上的突破。第二點則是莊子朝向絶對的真心説而發展,這是莊子在心性論上的突破,由於這是在《齊物論》一篇所提出的,所以也是在道家知識論上的突破。莊子哲學第三個主軸可以説是由老子的道論到莊子的物論的發展,這是莊子在本體論的突破,莊子闡明物化的每一個現象就是本體,完成了他的即現象即本體的絶對唯心的現象論。
本文以莊子爲老子思想的接續者與發展者,在上述三個項目,筆者也探討了莊子文本如何由老子思想發展而來。
在上述的三個項目之中,本文的重點在於海德格爾與莊子二者的對話,首先,筆者探討了海德格爾對於莊子的無用之用以及老子的無的討論。又,筆者研究莊子的“以明”的三個面向,對比於海德格爾所説的“解蔽”與“澄明”(Lichtung)。莊子闡明“以明”的第一個面向是理論理性的知性分析的面向,在此面向,事物的用都落入某種限定性之中,甚至於由概念的相對性而相反相成地更爲全面地掌握物論也是如此,就其後更爲辯證性的開展而言,先在的發展中的事物盡管可以相反相成來把握,但是仍然落入限定性之中。
第二個面向的“以明”是無的智慧的面向,在這裏,“無用之用”是牟宗三所説的通過無、讓開一步來達到“作用的保存”,這裏的“無用之用”是主體性所呈現的主觀境界,而其呈現是無,因此乃是牟宗三所説的消極型態的境界形上學。這裏的“無用之用”是通過無(讓開一步)而達到“作用的保存”的“無用之用”。
第三個面向的“以明”則是葆光、天倪的面向,呼應於《齊物論》一開始所説的“天籟”,則和下一節所説的“物化”相關。在這裏,“無用之用”是本體妙用,是天鈞大化之中的“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無用之用”是如此的“不用寓庸”。
因此,對於老莊的“無”與“無用之用”不能局限在勞思光所説的主體性哲學的角度,貶低爲只是屬於情意我的層次,還達不到德行我、主體性的價值自覺;也不能像牟宗三將之只是理解爲消極型態的境界形上學。而是要對老莊的“無”與“無用之用”進行本體詮釋,正如傳統的老莊詮釋學史的諸位大家之所爲,同時也是海德格爾之所理解。本文的結論是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之中的關於“無用之用”的詮釋,涉及到《莊子·齊物論》“以明”的三個面向的本體詮釋。通過對於海德格爾的存有思想的整體發展之考察來討論他對於《莊子》“無用之用”的解釋,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爾對於《莊子》哲學的討論架起了中西方的《莊子》詮釋學史的對話交流的橋樑。海德格爾此説所涉及的科技批判藝術技藝的省思,不僅是他晚期存有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爲他援引了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來作爲他的最重要的東亞同道之同行人,而使得老子莊子的哲學詮釋進入當代,從而在生命哲學與生態思想上具有當代批判與當代詮釋的重大意義。
筆者本文雖然主要環繞於海德格爾論莊子的“無用之用”以及《齊物論》“以明”的三個面向的本體詮釋來加以討論,但是筆者所開展的面向比較多,涉及莊子對於老子的繼承以及三點自己的特點突破,也討論了海德格爾存有思想的發展過程,並涉及到海德格爾與莊子的道言説,所涉及的海德格爾“物物化”與莊子的“物化”的討論還過於簡短。若要真正深入課題的深處來作探討,以上這些面向的討論都是海德格爾論莊子的“無用之用”所必然涉及的。因此,此文看來比較龐雜,筆者希望未來能够寫作多篇專文來對於此文所涉及的幾個面向一一詳細探討,釐清其中的複雜問題。
《莊子》譯成西文以俄文、英文、德文爲最早,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對於中西文學、宗教與哲學的交流具有重大影響。《莊子》譯本所引發的中西哲學對話以在德文世界之中最具有意義,而其中又以海德格爾與老子莊子的對話最具有深度,爲世界哲學界公認。
海德格爾與道家思想的對話開端於海德格爾於1920年代之初識老子而心動,而終極於他的晚期存有思想與莊子的默識心通。海德格爾與莊子思想的默識心通所涉及的精神内涵,開端於他童年時候諦聽父親在鄉村教堂敲鐘而有的生命體驗,1930年10月9日,海德格爾在《真理的本性》的演講中就曾引用《莊子·秋水》,其後此一關注貫穿於他對於荷爾德林、里爾克的詩作吟唱的詮釋,晚年達到“物物化”的本來現成(Ereignis)的如詩之思之中,尤其是他對於《莊子》“無用之用”與“藝即是道”的討論。海德格爾與老子莊子道家思想的對話是真正的兩鏡相照,此一心心相映的兩鏡相照是晚期海德格爾所説的映射——遊戲(Spiegel-Spiel),乃是莊周夢蝶的“物化”境界。在這樣的海德格爾與莊子的兩鏡相照之中,莊周夢蝶的“道化”的藝術夢土與心靈净土也顯化在海德格爾的南德黑森林的田野之道上,天地人神的四方的映射——遊戲(Spiegel-Spiel)與“萬物輝映”就在這樣的鐘聲、詩歌吟唱、如詩之思、田野之道之上漫遊,一同逍遥遊,在21世紀的未來,海德格爾的思想通過和莊子的默識心通的對話,在夢蝶一般的道化物化之中,空谷傳音,“震乎無盡,寓乎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