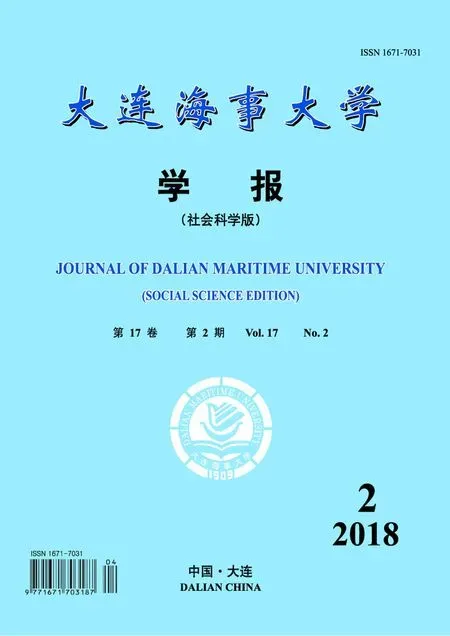从多重世界透镜解读纳博科夫艺术创作中的边界主题
2018-04-24崔永光张艺玲
崔永光,张艺玲
(大连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美国女作家安扎尔朵(Gloria Anzaldúa)所著的自传式理论著作《边界》(Borderlands/LaFrontera:TheNewMestiza, 1987)开启了美国文学“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大卫·约翰逊和斯科特·迈克尔森合著的《边界理论:文化政治的界限》一书前言(Border Secrets: An Introduction)中将“边界”划分为“物理边界”和“软边界”。他们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包括心理的、地理的空间,将之扩展成一个融汇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和种族问题的复杂概念。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由设置“边界”而引发的文化边界的分析。的研究。她在该著作第一版前言中指出:“边界是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交界地。在那里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人们占据着同一空间,他们之间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空间在不断缩小。”[1]“边界”的概念已经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概念,延伸到心理学、性别和精神上的边界,涵盖着“美国-加拿大边界、美国地方主义和美国移民的流散经历”[2]等众多主题。
享誉世界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仅是一位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小说家,还是一位集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诗人、鳞翅目分类专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多面手。他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移民社区与其蝴蝶世界和文本世界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交织作用,构成了其艺术世界中的“多层次、多色彩”的特征。*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本土研究学者A. A. 多里宁、列捷尼奥夫等都对纳博科夫艺术世界中的多层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作家的世界观和诗学中的重要特征。因此,纳博科夫的创作主题涵盖着流亡、爱情、追逐人生、死亡、彼岸世界、时间与回忆等多元主题。
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同样具有“边界”主题特征。他早年同家人多次颠沛流离、远离故国,至死也未返回俄国。对流亡作家而言,流散经历(diasporic experience)首先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越界”行为。越界表示对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对人类寻求幸福、自由的权利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3]离开俄国和童年天堂让纳博科夫感受到了种种不适,作家“突然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4]289。他的多部小说如《玛丽》、自传体回忆录《说吧,记忆》等都明显地带有对俄国丰盈的怀旧情结。流亡的岁月,作家心中怀藏的对过去的思念是对失去的童年的一种极度复杂的感情。[4]69再者,流亡意味着创作语言上的转向。纳博科夫不得不放弃“美妙的、极为丰富和无比温馨的俄语,转向二流的英语”[5]14。尽管作家创作出了最为出色的英语小说,然而从俄语到英语写作的彻底转向是极为痛苦的,“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了七八根手指,要重新学习拿东西一样”[556]。面临着越界的痛楚和语言的分离,纳博科夫是幸运的,其创作生涯中的俄文和英语作品同样出色,是真正的世界文学杰作。
尽管流亡越界的生活和创作语言的转向使得纳博科夫的作品具备“边界”主题因素,但是其笔下的“边界”主题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理边界”,更多地关注文本作品中的“内部边界”或是“软边界”,诸如美学、科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中文化和精神的隐喻意义。流亡者的“越界”行为一方面要面临孤独、异化和疏离;另一方面,他们感到一种自由与解放,“打乱了传统的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分界线”[3],在异域寻找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为作家带来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通过纳博科夫多重世界的透镜去解读其艺术创作中的边界主题,读者可以深入地认识作家对现实与幻想、科学与艺术、美学与伦理、诗性与哲性等微妙关系的细微刻画,了解其小说创作中复杂难解的“中国式套盒”的叙述结构,理解纳博科夫丰富的艺术观和世界观,进而揭示其艺术创作中潜藏的世界遗产和独特价值。
一、纳博科夫的文本世界:现实的虚幻与虚幻的现实
纳博科夫创造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主题多元,无法用寻常的主题来界定。其丰富的文本世界涵盖着翻译、诗歌、小说、文论、传记、信函等多重文本体裁,塑造了具有“众多主体形象的艺术世界”,同时也为纳博科夫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玛丽》中俄罗斯侨民流亡生活的柏林、《洛丽塔》中的汽车旅馆、《普宁》中的美国校园、《微暗的火》中虚构的赞巴拉,以及《阿达》中的反地界等多重文本世界揭示出纳博科夫艺术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各种文本作品之间既完全独立,又“互相作用着,互为澄清,互相丰富,赋予作家的全部创作一种超结构的特性”[6]374,并暴露出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特征。这些创作文本反映出纳博科夫对认知世界的多种方法的尝试,折射出“人类意识的复杂规律性问题,对人类生活事件进行主观解释的多样性问题,人类认知的可能性和边界的问题”[6]374。
纳博科夫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是他创造的文本世界让濒于枯竭边缘的小说样式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枯竭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是美国作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他提出这一文学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类型的作家几乎不可能写出原创性,或者是任何原创性的文学作品。一些作家将文学已经枯竭的痛苦假设用作新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主题。除了代表作《洛丽塔》之外,《微暗的火》《劳拉的原型》《阿达》等作品形式独特,在当时文学枯竭论与小说危机表征下发出了最强音。纳博科夫的真正意图是消除成见,打破僵化思维,“开拓小说领域的‘反地球’(《阿达》中的场景)与生机盎然的‘未知领域’,从而恢复与培育小说艺术的无限生机与自身的内在活力”[7]。可以说,正是因为乔伊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纳博科夫、福克纳等20世纪现代实验派作家的存在,“小说的可能性的地平线在20世纪一下子延伸得很远,至今可能还没有人能完全看到它的边际,这就给小说家和读者都留下了异常广阔的空间和令人激动的前景”[8]。可以说,纳博科夫对20世纪小说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做出了创造性拓展,小说的边界延伸到诗歌、评论、传记、回忆录等“杂糅性”(hybridity)的多元创作体裁。
纳博科夫首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文体学家,其复杂的叙事结构、众多的文学典故、多样的制谜游戏等高超的艺术手法让这个声誉名副其实。同博尔赫斯一样,纳博科夫的小说文本同样使用“中国式套盒”(Chinese boxes)的技法,以期消除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想象领域的差别。在《透明》中,虚构世界和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之间的边界不断变化。在《洛丽塔》和《阿达》中,纳博科夫通过声称虚构的编辑凌驾于剧本之上,努力去描绘一幅幅画中画。[9]细读《洛丽塔》可以看出,该小说带有戏拟文本体裁的特点。它是一部传记、侦探故事、浪漫小说、道路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非正派小说,是一部由一系列文学典故和许多具有嘲讽意义的名字组成的元小说”[10]。小说不仅具有独到的技巧构思,还刻画了主人公在世界中的心理挣扎,折射出作家艺术创作中的道德力量和伦理内涵。
《洛丽塔》中充满忏悔之意的亨伯特找到已经结婚怀孕的洛丽塔时,依然会充满柔情地对她痴迷眷恋。洛丽塔拒绝了亨伯特的请求,亨伯特悲伤离去,杀死了奎尔蒂。去世前不久,他在狱中写下了最后的几句话:“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11]同主人公洛丽塔一样,小说《洛丽塔》终究成为艺术与道德完美结合的文本典范,不仅具有特异的创作风格和叙事技巧,其艺术价值的背后还闪烁着道德的光芒。
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微暗的火》是运用“中国式套盒”手法最为巧妙的一部长篇英文小说。小说一经出版,立刻驳斥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小说形式危机的论调。奇特的文本结构、曲折的故事情节、复杂的迷宫叙事成就了“20世纪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的口碑。然而,阅读这样一部带有后现代文学特征的实验主义小说,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反复读者。他曾大声疾呼道:“给我具有创造性的读者,这个故事是给他们写的。”*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专门有一篇题为“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的文章,列举出“优秀读者十大条件”,同时提出,“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因此,对于纳博科夫的小说,要求读者反复地阅读和揣摩,才能理解其深层次的文本结构和审美狂喜。梅绍武先生在《微暗的火》一书译后记中谈到纳博科夫对自己心目中的读者要求甚高:他们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学修养,精通多种语文,又得是个头等诗人和福尔摩斯,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特强的记忆力。纳博科夫的意图是邀请读者与其一起踏上发现之旅,感受细读文本的奖赏与狂喜。纳博科夫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乔伊斯的互文性、戏仿等创作手法,还糅纳了碎片拼贴、元叙述、解构和接受美学等诸多实验主义技法。
后现代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是开放性的。首先,《微暗的火》的文本结构呈现多层次性的套盒结构特征。最外一层是作家纳博科夫,其创作灵感明显地来源于翻译普希金的诗作《叶普盖尼·奥涅金》。接着是小说《微暗的火》包含着真实与想象的分界线。第三层是波特金(Botkin),故事中隐藏的叙述者。而波特金使用的化名金波特(Kinbot)是文本第四层。接着是评注和索引,讲述了赞巴拉(Zembla)和其国王的故事。而金波特模糊了下一层结构,约翰·谢德(John Shade)的诗歌“微暗的火”。文本最后一层是谢德,他属于诗歌的内部世界,因为他撰写了一部揭示其生活的自传体作品。[9]叙事结构的多层次性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内部文本中是金波特对谢德的诗篇“微暗的火”的第一层次的解读,而呈现给读者的外部文本是经过金波特阐释的文本。那么,读者提出的疑问是:谁是文本中可靠的叙事者(reliable narrator)?该诗篇的主题究竟是关于谢德的传记,还是依据金波特的生活创作而成,引发了读者的多元化阐释。在诗歌的评注中,金波特暴露其真实的身份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北方国度的流亡国王查尔斯二世。《微暗的火》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虚构性文本,暴露这一点的正是隐藏在模仿话语中的金波特的不可靠叙述。*在《越界的叙事者》一文中,黄艺聪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微暗的火》的故事世界进行了划分,探讨了嵌套模型和越界问题,展现了纳博科夫与叙事者之间的层级关系,同时建构了读者进入各个可能世界的桥梁。详见文献[12]。
复杂的迷宫式的叙事结构,作品中主人公之间的交织关系和多重阐释深刻地暴露出纳博科夫的现实观,以及他对现实与虚幻关系的独到理解。纳博科夫在其复杂的、带有自我意识的小说中经常探究现实的虚幻本质以及艺术家与其手法的关系。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其幻想性的欺骗性和复杂性。通过将艺术的文体特性置于道德或社会意义观念之上,纳博科夫倡导想象力的至上性。通过想象力,他认为可以获得更有意义的现实。[13]为此,许多评论者批判纳博科夫一味地使用文字游戏、拼字手法和多重双关语等伎俩来创造复杂的迷宫叙事结构,批判他拒绝处理社会、政治问题和伦理主题。事实上,在其复杂的文字游戏、语言戏拟和文体互文性等美学策略的背后,隐藏着纳博科夫对捍卫自由与个性、追求彼岸世界、反思时间哲学等形而上主题的深刻拷问。
纳博科夫坚决反对将真实生活与艺术创作等同起来。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具有误导性。“真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你离真实越来越近,但你不可能完全达到真实,因为真实是不同阶段、认识水平和底层的无限延续,因而不断深入、永无止境。”[5]10-11纳博科夫创作的艺术世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具有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艺术的起源便是人运用记忆和想象来调整、组建混乱的外部印象。真正的作家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是自己对现实的美妙幻觉。因此,艺术现实永远是一种幻觉;艺术不可能不是虚拟的,但虚拟性绝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艺术的力量之所在。”[6]373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同自然界一样都是骗局,而大作家就是魔法师,运用高超的手法和艺术的想象,讽喻和嘲弄一般意义上的现实存在。
总之,纳博科夫多元的文本样式、迷宫式的文本叙事、多层次的文本结构等特点赋予了其“小说文本本身具有文学批评的功能”的后现代元小说特征。这一写作范式和文体策略并非去揭示现实生活,而是试图揭示由话语构成的叙述文体的虚构性质。作者直接表达了对文本的艺术思考和质疑,玩弄小说的艺术本质和创作过程,使得叙述策略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纳博科夫采用的元叙述在构筑小说幻象的同时又揭露这种幻象,使读者意识到它远不是现实生活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编纂的故事。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文本揭示了元叙述的革命性和实验性,指出小说虚假性的本质,因此保持了小说作为虚构想象艺术的魅力,构成了显示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巨大张力。
二、纳博科夫的蝴蝶世界:科学与艺术的交融
在世界文学史上,纳博科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大师,他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纳博科夫对蝴蝶分类学的满腔热情与成就,让读者看到了他在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中的建树与造诣。他创作的部分作品扉页上都有一只蝴蝶和印有To Véra(献给薇拉)的字样,似乎说明他的创作灵感都来自蝴蝶和薇拉。早年的很多诗歌如《发现》、回忆录《说吧,记忆》、短篇小说《蝶蛾研究家》,以及长篇小说《天赋》《洛丽塔》《爱达》等都涉及蝴蝶的要旨和对鳞翅目昆虫学的敬意。“纳博科夫的文学不仅巧妙且毫不做作,作为天才科学家的纳博科夫在鳞翅目昆虫学上体现了对自然界更深的理解。他在科学上的敏锐对见多识广的读者解读其文学的方式产生了影响。”[14]406
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热爱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西方学者就将眼光投向纳博科夫的蝴蝶分类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约翰逊(Kurt Johnson)和科茨(Steve Coates)共同撰写的《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为读者揭示了纳博科夫在蝴蝶分类研究领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2009年,布莱克威尔(Stephen H. Blackwell)撰写并出版了专著《笔尖与手术刀:纳博科夫的艺术和科学世界》(The Quill and the Scalpel: Nabokov’s Art and the Worlds of Science)。通过探究其艺术思想中的物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多重维度,布莱克威尔阐释了纳博科夫的美学敏感度如何帮助其科学工作,以及其科学热情又如何塑造、影响和渗透于其小说创作。2016年,由布莱克威尔和约翰逊共同编写的《优雅的线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科学艺术》(Fine Lines: Vladimir Nabokov’s Scientific Art)以精装形式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第一部分首次全面地对纳博科夫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了跨学科的描述,列出了148幅珍贵的纳博科夫研究蝴蝶的图片和构造。第二部分呈现了前沿科学家和纳博科夫研究专家撰写的10篇研究论文,阐释了纳博科夫对进化生物学的预言性贡献,同时为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克威尔尝试理清纳博科夫艺术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纳博科夫的科学活动和博物之旅对其小说美学思想具有发生学意义,[15]或是认为纳博科夫的蝴蝶情结,使作品闪烁着超现实的激情,达到了写实性与诗意性的双重效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16]甚至认为作者笔下的洛丽塔是作者塑造的一只变态的蝴蝶,是文学中的一个昆虫学试验。[17]尽管将纳博科夫的蝴蝶情结强加于其文学创作影响的做法值得商榷,但是纳博科夫的蝴蝶世界是让读者深刻全面地了解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他对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捕蝶的科学发现中对自然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这种自然观对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观或文学观具有重要的启示,也让读者领略到纳博科夫的科学世界与艺术世界重叠交织的别样风景。
首先,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是创作。小说是虚构。[18]5小说创作的本质是虚构性。自然的骗术比大作家技法更为高超。“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播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无穷的神机妙算。”[18]4-5因此,对于作家而言,如同大魔法师般,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段和技巧,一方面去叙述故事,设计棋题与制造迷宫,一方面要暴露虚构,体现互文性的元叙事策略。换言之,纳博科夫作为世界公认的艺术大师,首先要归功于其创作中高超的艺术手法、文字游戏和后现代叙事技巧等。
再者,1962年,纳博科夫在接受BBC电台采访时重申:他对蝴蝶的兴趣纯属科学性质的。而这种观点与其创作紧密相关。在他看来,一件艺术品存在着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某种融合,即诗的精确与纯科学的欣喜。[5]10纳博科夫从7岁开始捕捉蝴蝶,12岁投稿《昆虫学家》杂志,1941年发现第一个蝴蝶新种,并且创新分类方法。可以说,纳博科夫将文学与博物学的深度结合做到了极致。有学者认为纳博科夫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艺术上、在科学上有所成就,是需要一点贵族气质的。[14]11纳博科夫的贵族气质在于无论生存境况如何,始终如一地坚持文学创作,迷恋蝴蝶与博物发现。这种坚守科学的韧性与文学创作的诗性让他对优秀读者提出了独特的标准: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18]4-5因此,对于阅读纳博科夫作品的优秀读者而言,一定是一个“反复读者”,需要在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不断探险、发现惊奇、领悟真谛,一如纳博科夫经历多年发现蝴蝶新品种时的狂喜与快感。他说过,“我不能把发现蝴蝶的美学愉悦与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科学乐趣彼此分离”[19]。
最后,纳博科夫将博物情怀与文学创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强调科学观与艺术观的和谐交融,两者都注重对细节的关注。一方面,在纳博科夫的教学生涯中,他总是设法让学生去关注艺术作品的细节。“关于细节,关于细节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的火花的,没有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5]162另一方面,从事博物学研究同样要求精益求精、考究细节,对复杂的蝴蝶品种的鉴别与分类,离不开细节的精确。纳博科夫最大的创造性在于他在科学探索和艺术创作中体验乐趣和愉悦,发现了一种深层次的审美快感。在博伊德看来,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他是在探索更为有力的方式,以便将他在昆虫学中发现的快乐传给他的小说,那是特殊性的愉悦,是发现的惊喜,是神秘的直觉,是愉快的骗术。[20]102
总之,纳博科夫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得其艺术创作具有科学和艺术的重叠特性。这来自纳博科夫想要了解世界的科学观。“这种想要不断了解世界的激情部分是科学性的,部分是美学的。最终艺术与科学的不可剥离成为纳博科夫创造视域的核心。”[21]可以说,纳博科夫竖立起一座高耸的山脊,一面是科学的激情,另一面是艺术的想象。纳博科夫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他总是巧妙地回答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纳博科夫通过自己全面的博物学及鳞翅目昆虫学知识,把他虚构的创作牢固地根植于真实的鳞翅目昆虫学世界里。[14]409他在其文本世界中多次使用蝴蝶意象和鳞翅目典故或修辞,一方面是要引导优秀读者去思考其作品中的艺术策略,另一方面展示了其看待世界的习惯方式。一言以蔽之,纳博科夫不仅为科学世界和艺术世界竖立起一座山脊,更为两者搭起一座桥梁,让科学和艺术交织生辉。
三、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诗性与哲性的形而上主题
可以说,国内外学界对纳博科夫艺术作品阐释最多,也是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彼岸世界”(the otherworld)主题。亚历山大罗夫、博伊德都多次著书立说对“彼岸世界”主题进行解读,尽管两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这也引发了读者和评论家对这一主题的多元化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对“彼岸世界”的解释不能基于自我推测,而是要根据作品自身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主题。在亚历山大罗夫看来,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展示的是形而上学、伦理学与美学思想的不可分割性。[22]接着他对三者分别进行了界定与区分,认为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协调统一。在这一点,他同博伊德一起为纳博科夫正名,驳斥了纳博科夫仅仅是一位杰出的,但却没有深刻内容的文体家的观点。其实,他作品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伦理与哲学内涵,是诗性与哲性的形而上主题的内在统一。读者要真正理解“彼岸世界”主题,首先要走进纳博科夫的诗歌、小说、文学讲稿,甚至是他的翻译作品,反复研读文本,领悟“此岸”与“彼岸”的内涵与联系,从而理解纳博科夫的诗性与哲学信仰。
一方面,纳博科夫的真正奥秘是他创作的抒情性或是诗性。在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地将其诗人的气质融入其小说创作中。从《微暗的火》中那首由约翰·谢德所作的四个诗章、共999行的优秀诗篇,到作者自认为最为出色的俄语小说《天赋》中那首作者最喜欢的俄语诗,*在《独抒己见》中,纳博科夫对这首诗解释道:诗中有两个人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一座桥上,河水映出落日,燕子飞掠而过,男孩转身对女孩说:“告诉我,你会永远记得那只燕子吗?——不是任何一种燕子,也不是那些燕子,而是刚飞过的那只燕子?”她回答:“当然,我会记得!”说完,他俩都热泪盈眶。“有如这位年轻的诗人使用其他诗人的形容词和感叹词来描绘他的世界和感情一样,他试图通过走向邻近的天堂使人联想到有比这个世界更广阔的空间”[20]。纳博科夫在多次接受采访中称《斩首之邀》是他“最富梦幻性且最有诗性的小说”[5]76。《阿达》是“最为世界性的诗性小说”[5]179。在纳博科夫看来,诗性是带有想象的魔力,是带有和谐的精致。“活跃的想象或诗性,是纳博科夫全部生命活动的核心,是纳博科夫艺术世界的关键词。”[23]总之,纳博科夫笔下无论是对主人公细腻的心理刻画,还是对俄罗斯本土及异域风光的描绘,对童年时光的深刻记忆与诗性想象,都揭示了纳博科夫创作语言上的抒情性和诗性情怀。
另一方面,纳博科夫的哲性世界在于其艺术创作中的存在主义主题。“纳博科夫的小说使人在无意义的世俗生活中,感受到某种真正的、崇高的东西。”[6]3891999年,由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加兰版纳博科夫读本》(TheGarlandCompaniontoVladimirNabokov)中收集了42位纳博科夫国际研究学者的74篇评论。该书从多元化视角全面评述了纳博科夫的诗歌、小说、译作、风格及其与其他世界作家的内在关联。其中,不乏评论者探究了纳博科夫与柏格森、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普鲁斯特、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作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关系。*国内学者刘佳林在《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对两者的文学风貌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两位作家在文学观念及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认识方面有着一致的立场,同时都具有世界性或西欧性的艺术品貌。对双重人格形象的描写,对个性自由的关注,使得这两位作家在心灵方面更加契合。详见文献[24]。这些研究为探究纳博科夫小说创作中的哲学命题提供了学术基础和研究视角。在《尼古拉·果戈理》一书中,纳博科夫认为:“在艺术超尘绝俗的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注意的是人类灵魂那隐秘的深处,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名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25]
对此,国内学者戴卓萌等将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置于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内,梳理和解读了蒲宁、纳博科夫等作家和白银时代诗人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特点。可以说,国内学者的独到眼光和哲学意识为纳博科夫在新时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颇具挑战却值得尝试的路径。戴卓萌等给予纳博科夫较高的评价,“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在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达到了顶峰。纳博科夫的创作玄妙难解,他因此成为俄罗斯存在主义文学中最深刻、细腻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26]。纳博科夫不仅在其早期俄语小说《眼睛》《绝望》《防守》中隐藏着存在主义思想,其后期英语创作的成熟小说《洛丽塔》《微暗的火》《阿达》等同样具备形而上的哲学思想。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亨伯特、普宁、金波特等人物都具有孤独的个性,都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这种孤僻与其周遭的世界形成了对立和冲突。他们又渴望一种方式,或是亨伯特心中洛丽塔的不朽的艺术形象,或是普宁心中对往昔生活浓重的怀旧情结,或是金波特对谢德诗篇“微暗的火”中的自传想象,来阐释孤独的个体在世界中的独立存在意义。这些流亡者的经历反映了失去故国家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与历险。尽管流离失所、放逐流浪,却独立不羁、追逐自由。“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27]透过其笔下人物的形象映射,纳博科夫把流亡中无法弥补的损失与怀旧输入其毕生的艺术创作,在不断认知世界与探索存在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既带有诗性的、阿卡狄亚式的风景想象,还具有形而上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哲学命题。
四、结语:纳博科夫的世界遗产
国内外学界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历经长达百年的漫长过程,经过种种争议与正名之后,其遗留的文学佳作与科学遗产已经具有经典性和世界性。尽管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性”和“非俄罗斯性”颇受争议,*20世纪60—70年代,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享誉世界,对此俄罗斯侨民文学圈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作家,独立于俄罗斯文化之外,毫无“俄罗斯骨血”。这一看法将纳博科夫排除在俄罗斯文学边界之外。事实上,纳博科夫运用俄语和英语创作,同时将大量的俄语作品翻译成英语,代表作为详细注解的四卷集译本《叶普盖尼·奥涅金》,向西方传播俄罗斯文学经典与艺术成就。纳博科夫在艺术创作和俄罗斯文学译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作为一名世界文学大师的身份得以确立。他创造的多重世界涵盖着现实与虚幻、科学与艺术、诗性与哲性之间多维关系的边界主题。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不仅具有多元复杂的主题、意象、结构和游戏手法,还具有高度的诗性和哲性信仰。
总之,纳博科夫与俄罗斯、俄罗斯文化分离相连的失去故国家园,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戏剧性关系以及“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等三大主题的共同核心在于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被迫离开故国和族群,不仅要面临与祖国“物理边界”上的分离,还要面对语言的分离与本土文化等“内部边界”上的剥离。尽管如此,纳博科夫却超越了物理边界,依托其流亡体验、世界认知和艺术想象,创造出优秀的诗歌和小说杰作、文学讲稿和翻译诗作,为世界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文学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与其文学成就相比,纳博科夫对其在鳞翅目昆虫学上的贡献始终保持低调和谦逊。尽管他在科学界的地位未能达到其文学领域的高度,但是他在生物分类学上的成就让读者领略到了纳博科夫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生。
[2]MICHAELSEN S, JOHNSON D E.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2.
[3]张德明.流浪的缪斯——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J].外国文学评论,2002(2):54.
[4]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王家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NABOKOV V. Strong opinion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6]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7]赵君.纳博科夫对“文学枯竭论”的超越性思考[J].外国文学,2006(6):62.
[8]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艺术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54.
[9]STARK J O. 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Borges, Nabokov, and Barth[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4.
[10]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M].修订版.孙宏,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35.
[11]NABOKOV V. Nabokov: novels 1955-1962[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6: 291.
[12]黄艺聪.越界的叙事者——《微暗的火》中的可能世界模型[J].国外文学,2016(2):118-126.
[13]MATUZ R.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4[M]. Cambridge, UK: Cengage Gale, 1991: 330.
[14]JOHNSON K, COATES S.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M]. New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15]赵君.蝴蝶研究对纳博科夫小说美学的发生学意义[J].湘潭大学学报,2011(5):130.
[16]何岳球.纳博科夫的蝴蝶情结和美学意蕴[J].当代外国文学,2007(1):104.
[17]何岳球.洛丽塔:纳博科夫的“变态”蝴蝶[J].外国文学研究,2008(5):118.
[18]NABOKOV V. Lectures on literatur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19]GOULD S J. I have landed[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
[20]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1]BLACKWELL S H. The quill and the scalpel: Nabokov’s art and the worlds of science[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
[22]ALEXANDROV V E.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568.
[23]刘佳林.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7.
[24]刘佳林.纳博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J].外国文学评论,2010(2):87-99.
[25]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理[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9.
[26]戴卓萌,郝斌,刘锟.俄罗斯文学之存在主义传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58-259.
[27]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