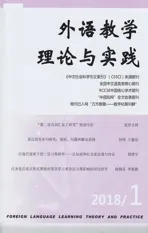后现代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认知派和社会派论战与对话*
2018-04-23北京外国语大学胡增宁
北京外国语大学 胡增宁
1 引言
二语习得研究历史虽然不长,但发展迅速,研究领域涉及应用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诸多学科,具备较完整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已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刘永兵,2010:87)。在此发展过程中两大阵营开始逐渐形成:认知派阵营和社会派阵营(文秋芳,2008)。在1990—2014年近25年间,二语习得顶级期刊《现代语言》(1997/2007)和《二语习得研究》(2014)专门组织二语习得专家(Firth & Wagner,1997;Kasper,1997;Larsen-Freeman,2007;Swain & Deter,2007;Hulstijn et al.,2014)展开讨论。早期认知派在二语习得领域一统天下,而社会派力求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论战还是显得火药味很浓(如Firth & Wagner 1998年文章SLA Property:No Trespassing!)。随着认知派和社会派的分化日趋明显,DeKeyser(2010:647)撰文中表达了担忧: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过度细分会使研究者的视野变得狭隘,不利于二语习得发展。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认知派研究局限和社会派的贡献时,双方论战开始变得势均力敌。2013年Dallas举办美国应用语言学大会,两派学者认识到各自研究局限并展开积极对话,试图寻求他们共同关注问题的完整答案。这次讨论聚焦到哲学层面:二语教学是否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有,这种差异是认识论层面的?还是本体论层面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些差异中可以学到什么?不同于以往两派交锋的架势,这次研讨气氛热烈且富有建设性。
为何双方在早期会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二十五年后为何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讨论?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我们需要回到哲学基础,特别是引发了这一系列讨论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本文通过梳理后现代思想的起源、核心观点、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影响,重新审视认知派和社会派论战,把握论战实质、全面评价二语习得发展动态。
2 认知派和社会派论战历程
为了跟踪二语习得研究最新发展,并探究引起这场讨论的根源,本文将时间范围锁定在1990—2014时段,以《现代语言杂志》(1997/2007)及《二语习得研究》(2014)三次专刊为线索,将这 25年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7:论战时期;1998—2007:关注时期;2008—2014:对话时期。三次专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二语习得发展的关键节点,且作者均为二语习得领域有声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声音能大体反映二语习得研究发展脉络。
1)论战时期
早期认知派(Beretta,1991;Beretta & Crookes,1993;Gregg,1993;Long,1993)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占主导地位。Diana Larsen Freeman在1991年TESOL Quarterly创刊25周年介绍了1970至1990年SLA重要话题,在此期间研究理论主要有UG、互动主义和连接主义;重点研究输入、输出和迁移。因此,二语习得被看作“内化的认知过程”(Zuengler & Miller,2006:36)。在1991年洛杉矶“二语研究论坛”上,Sharwood Smith将认知派二语习得研究比作“蛋糕”,而社会派研究仅是“蛋糕”上的“糖衣”(ibid)。该时期二语习得期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数为认知研究,像Language Learning和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这种顶级期刊更是认知派一统天下。因此,认知派对于社会视角的研究不太重视。Beretta(1991)认为二语习得理论不能太多,理论太多就会导致相对主义。Gregg(1993)也极力反对相对主义,并撰文“让几朵花盛开(Let a Couple of Flowers Bloom)”,显然,这些“几朵花”不属于社会派。当时,多数认知派学者坚定认为社会派研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科学发现。
在1996年国际英语语言学年会上,Firth和Wagner对认知派主导的二语习得研究现状表示质疑,引发在座学者热烈讨论。社会派学者开始对认知派发起挑战(van Lier,1994;Lantolf,1996;Block,1996)。Lantolf(1996)以“百花齐放(Letting All the Flowers Bloom!)”为题,从后现代主义批判视角,强调二语习得研究的多元性。Lantolf(1996:731)用 “相对主义恐惧症(relativaphobia)”讽刺认知派;Block(1996:64)则用“艳羡科学一族(science envy)”一词批判认知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套用在二语习得研究的做法。由于这些文章发表在不同期刊,难以引起高度关注,因此Modern Language Journal于1997组织特别专辑(focus issue),就此话题进行深入探讨。Firth & Wagner(1997)认为人类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形成认知,强调二语习得研究要更多关注语言使用;增加研究的内在视角(emic perspective);扩大传统二语习得数据范围。然而Long(1997)质疑社会派研究范式的代表性;Kasper(1997)也坚定地认为习得和使用是两回事。双方观点存在较大分歧。
2)关注时期
Firth & Wagner(1997)一文引发二语习得界持续关注。到2002年,该文在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下载量排名第三,并在1997—2007年间保持较高引用(Magnan,2007)。学界对F & W一文的反应大致分成三类:赞同派、部分赞同派和反对派。针对这些分歧,《现代语言》两位编委Morgnan和Lafford于2007年再次约稿,请11位学者就此话题再次展开讨论。2007专刊重点不再是认知派和社会派的对立争论,而是根据Firth & Wagner的建议,如何重新理解(reconceptualization)二语习得。虽然论述对象和观点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数作者认识到“社会视角对二语习得研究的价值”(Lafford,2007:743),反对把语言从社会文化情境中分离的结构主义语言观(Lantolf & Johnson,2007)。
1997—2006年间社会视角二语习得研究增长很快(Lafford,2007)。二语习得研究显示出社会派转向(Block,2003)。有些学者依旧对社会视角研究持有怀疑。例如,Zuengler & Miller(2006:35)将认知派和社会派研究看作“平行世界”,无法对话。还有学者认为两派有不同“本体论”(Lafford,2007:737),难以有真正的交流(Larsen-Freeman,2007)。尽管如此,Atkinson(2002)认为两派研究还是有相交的地方,提倡整合两派差异。Lafford(2007:751)希望二语习得不仅可以“百花齐放”,还能有机会“对话”。
3)对话时期
2007年专刊出版后,二语习得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理论(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身份认同视角(Norton & Toohey,2011)和话语分析视角(Kasper & Wagner,2011)成为二语习得重要组成。美国应用语言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2013 年会在Dallas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认识派和社会派是否可以彼此借鉴。因此,学者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派和认知派之间是否存在鸿沟?
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两派差异源自认识论层面,而Lantolf和Hulstijn认为是本体论层面。在Lantolf看来,本体论决定了认识论。如果人们把认知当作独立于外界的大脑功能,研究时自然不会关注社会文化因素。但如果把认知看作个体大脑和外部语言、社会和文化互动,那研究时就要纳入社会文化因素。Lantolf认为社会文化理论的优势在于将认知和社会因素整合。Ellis和DeKeyser也否认鸿沟的存在,认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认知视角和社会视角二语习得研究对立起来,实际上它们差别并不大。因此,Ortega提出摒弃认知派和社会派的对立思想,推动二语习得研究全面发展(详见Hulstijn et al.,2014)。会议邀请六位报告人阐述各自观点,集结成一篇特殊文章,刊登于《二语习得研究》。三位主编为文章撰写引言和结论。文章主体分别从“哲学与理论构建”、“数据与研究方法”和“待解决的问题与疑问”角度展开讨论。学者们从社会和认知不同侧面撰写,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这种特殊写作形式本身就体现了两派的建设性对话。
3 哲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
1)哲学视角与范式
首先,简单介绍哲学视角的重要概念:范式、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据库恩观点,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某一共同体成员提供一套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王冰、宋云霞,2011:141)。研究范式包括“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三方面的理论视角与概念假设”(龚嵘,2013:39)。本体论涉及知识的本质;认识论回答人与知识间的关系;方法论关注如何获取知识。范式包括共同体成员共有信念、价值观、研究对象、概念框架、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对理解社会派出现和发展尤为重要,当原有范式无法解释一些反常现象时,新范式就会出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向就恰好体现了范式的转变。下面将介绍后现代思想的产生过程及其重要观点。
2)后现代思想起源与核心思想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运动从法国兴起,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学界研究。为了准确把握后现代思想和二语习得关系,首先简要介绍该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后现代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详见王寅,2012),其核心思想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西方现代性的主要观点有:科学的真理性;社会的进步性;人类本质的一致性(林新华,2002:73)。西方哲学的现代性体现在对“逻各斯”的盲目崇尚。逻各斯的理念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词语、一个支配力量、一个潜在的神”(南佐民、范谊,2007:5)。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力图解构这个所谓中心,因此,“后”既有“在……之后”的意思,也有“反对”、“超越”意涵(许力生,2008:165)。后现代思潮力求推翻那些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那些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事实、或者被当作决定范式有效性的基础因素现在都成了有问题的东西,研究中热衷于普世化、规律化的科学范式和轻视人类多样性的倾向都受到了挑战”(许力生,2008:166)。
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对思想的束缚,是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深刻理论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反叛,不再像现代主义那样总是期望统一性、有序性、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性及永恒性,而是追求多样性、非连续性、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差异性、零散性、特殊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廖巧云,2013:9)。后现代思想还“强调研究主体对问题的体验、直觉和阐释”(叶洪,2012:15)。因此,后现代思潮打破了人们固有思维习惯,拓宽了思维视野,增强了宽容和理解,提升了人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3)后现代主义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受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和差异性思维的影响,二语习得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研究视角从认知为中心,逐渐扩大到社会视角,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研究主客体关系及数据收集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1)研究对象
后现代思想拓宽了人们对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的认识。Watson-Gegeo(2004)认为传统认知理论把知识当作客观“实体”(real entity),存储在大脑中,学习过程即为将外部知识内化,而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看作参与过程中个体的变化(Lave & Wenger,1991)。
以认知为主导的二语习得研究多以本族语者为参照,忽略了当前英语的各种变体以及广泛存在的双语或多语状况。Labov就曾经说过一个经典的论断,任何群体都不能用另一个群体的规范去衡量,而在二语教学和研究领域,二语学习者却经常被拿来和母语者对比(Cook,1999:194)。受后现代主义去中心论的影响,社会派不再将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做不平等对比,而把学习者看作具有多语能力的使用者(ibid:204)。后现代思想改变了对学习本质的认识,扭转了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2)研究主客体关系
就研究过程而言,后现代思想打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为了保证研究结果客观和可信,认知派研究要尽量保持与研究对象的独立关系,通过严谨、客观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从复杂世界剥离,以揭示内部规律或是解释因果。然而,社会派质疑这种主客分离的研究,认为单一、片面的结论无法反映真实世界,而更加看重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陈向明,2010:7—9)。因此,研究者不再是局外人,需要参与意义构建过程,研究对象也不再是独立于外部环境的客体,而是处于丰富情境下的主体。
(3)研究方法
后现代思想让人们认识到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认知研究的局限性。认知派关注语言能力(competence),常使用客观、量化研究方法,但量化研究不足以揭示事物复杂的关系和过程。因而Lave & Wenger(1991)认为把研究对象当成小白鼠,使用脱离现实情境的诱导方法(elicited method),难以获得有实际价值的结果。
因此,质性研究开始受到二语习得学者重视。但早期Davis(1995)认为学界对质性研究认识非常有限,认为质性研究就是非量化的研究方法(访谈和其他自然数据),但忽略了质性研究的哲学和理论基础。就认识论而言,量化与质性研究存在本质区别:量化研究强调研究结论的科学普遍性,而质性研究强调局部特异性与主观建构性(龚嵘,2013:45)。质性研究者要特别具有全局观念。“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问题选择恰当、多样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接近事物复杂多变的本质,并使用多元的方法对资料进行诠释和表达”(叶洪,2012:20)。
总之,二语习得学者逐渐意识到,任何单一视角和研究方法都难以获得全面、深刻的理解Lafford(2007:751)。强调“辩证统一”的思想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作用,提倡认知和社会视角“有机结合”。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二语习得研究和二语教学的发展(Canagarajah,2016)。
4 评价后现代思想与二语习得研究
认知派和社会派的论战体现了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为代表的相对主义之间的斗争。针对二语习得不同理论视角,学者们持有不同看法。理性主义强调真理的客观唯一性,因此,Long(1993)认为理论过多会削弱理论的竞争力,希望理论能够“去芜存菁”(邹为诚,2008:46)。诚然,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加入到二语习得研究,带来“新鲜的思想和活力,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但也可能引起“研究范围的片面性”(戴曼纯,2010:51)。也有学者(Jordan,2004;Hulstijn et al.,2014;Ortega,2011)认为众多理论有益于二语习得研究,有助于更深刻了解复杂的二语习得现象。还有一些具有后现代思想的二语习得学者则强烈呼吁保留社会派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合法地位(Block,1996;Lantolf,1996;Lave & Wenger,1991)。Lantolf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话语(Lantolf,1996),如果按照认知派观点压缩二语习得理论数量,就可能导致刚起步的社会派研究受到排挤。
认知派和社会派力图扩大各自范式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双方并没有两败俱伤,而是在此过程中互相学习,不断发展。究其原因,应该归功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首先,后现代思想让人们看到了二语习得研究的复杂性,需要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认知派关注语言知识在大脑中的表现形式(Larsen-Freeman,2007);而社会派关注个体在特定环境下与外界交互的过程。两种理论在解释上各有侧重,部分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因此,两种理论视角互为补充,有其各自价值。
为了进一步认识两派互补性,表1参考“认知派和社会派关注焦点”(Larsen-Freeman,2007:781)及“认知派和社会派的主要分歧”(文秋芳,2008:15),从哲学视角对比两派差异。

表1.认知派与社会派的哲学差异比较
就本体论而言,坚守客观主义世界观的认知派认为,语言客观存在于大脑,通过语言输入和加工,改变大脑语言状态。认知派强调人脑的重要作用,因此,是一种理性主义认识论。而社会派认为语言不只是独立存在于人脑的机能,语言学习是一种社会参与,学习者在参与过程中构建新知识。就方法论而言,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认知派,主要通过量化研究从宏观角度审视理想学习者,研究学习者对语言结构的掌握及复杂度变化;社会派则从功能主义角度研究交际过程话语行为,借助质性研究揭示语言互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总之,认知派受现代主义哲学倾向影响,坚持真理的唯一、确定,属于一元论。而社会派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质疑真理的永恒和确定性,体现相对主义多元论。
鉴于两派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差异,Ortega(2005)提出三条原则来指导我们看待差异: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应用;任何研究都会受到不同价值判断的影响;认识论多样化是有益的。作为一位认知阵营研究者,Ortega逐渐发现认知视角局限,并展开反思。他认为这可以增进二语习得不同视角对话。因此,分歧和对立恰好为学科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有益于开辟发展的崭新道路(邹为诚,2008)。
其次,后现代思想有助于消解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虽然认知派和社会派隶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但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取彼此观点(Hill,2006:821)。以二语习得研究热点——互动为例,认知派从学习者心理认知过程解释互动,将一切社会因素排除在外。社会文化派则认为互动为二语学习者提供“脚手架”,使中介语接近“最近发展区”(喻红,2014:184)。Pavlenko(2000)则认为语言、种族、民族、文化等资源都会对二语习得互动产生影响。从互动研究发展可以看出,对互动界定逐渐从认知扩展到人际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多个层面,研究也愈发呈现多元化和动态变化趋势。
因此,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以发生转化。Holbrook(2013)提出了“反思创新模型(reflective invention model)”。Holbrook认为从属于不同阵营学者有不同思维方式和话语特征,肯定会有交流不畅(communicative breakdown)。此时,具有反思力的研究者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时机,认识到两派的优势与不足,成为连接两派的媒介,便可以为通约创造机会。很多情况下,不可通约是因为研究者将自己封闭于固有研究范式,失去了解其他范式的机会。因此,后现代思想提倡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想,有助于打破范式之间不可通约。
虽然后现代思想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要回避后现代思想可能带来的不良倾向。首先,避免极端相对主义思想。极端相对主义容易导致“怀疑论”和“诡辩论”。虽然社会派思想从后现代主义汲取了丰富营养,但决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认知派研究。其次,避免将两派差异绝对化。Ortega认为不要把两派差异看作不可调和,他认为这种差异恰好为互相学习创造机会(Hulstijn et al.,2014)。如果大家看问题视角毫无差别,研究很难继续向前推进,因此,不可通约有其积极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想提醒我们避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想,让不同研究倾向和研究范式具备包容心态,互相批判和借鉴。最后,后现代思想并不能保证和真理更加靠近。后现代视角作用能促进“复杂化”“多元化”和“专业化”(黄春芳,2010:173)。Davis(1995:448)认为不同范式研究差别在于研究目的。从这个角度看认知派和社会派研究并无优劣之分。社会派作为新范式并不意味着把握更多真理,他们凸显了认知派忽略的现象,丰富了学界对二语习得现象复杂性的认识。
5 结语
本文以三次专刊为出发点,梳理了1990年至2014年二语习得认知派和社会派的论战和对话过程,评价后现代思想对二语习得研究对象、研究主客体关系、数据收集三方面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多元化和突破常规的视野为社会派发展创造了机会。正是由于后现代思想对多元性的包容,认知派和社会派从早期的激烈争辩,逐渐走向对话与合作。借用王寅(2012:15)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学术探索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而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学术研究不是“风景这边独自好”,而应“风物长宜放眼量”。此观点也非常适用于二语习得的研究。无论是认知派还是社会派都不应该固守各自研究视阈,而是要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真理观,认识不同视角的优势与不足,用开放心态了解他人领域,展开建设性对话。近年来,基于脑神经机制的二语习得研究正成为新兴热点(毛伟宾、顾维忱,2008;袁博平,2016),相信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包容精神会促进二语习得研究更为多元化。
Atkinson,D.2002.“Toward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dern Language Journal86.pp525-545.
Beretta, A. 1991.“Theory construction in SLA:Complementarity and opposition”.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3.pp493-511.
Beretta,A. & G.Crookes.1993.“Cognitive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discovery in SLA”.Applied Linguistics14.pp250-275.
Block,D.1996.“Not so fast:Some thoughts on theory culling,relativism,accepted findings and the heart and soul of SLA”.Applied Linguistics17.pp65-83.
Canagarajah,S.2016.“TESOL as a professional community:A half-century of pedagogy,research,and theory”.TESOL Quarterly50.pp7-41.
Cook,V.1999.“Going beyond the native speaker in language teaching”.TESOLQuarterly33.pp185-209.
Davis,K.A.1995.“Qualitative theory and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TESOL Quarterly29.pp427-453.
DeKeyser,R.M.2010.“Where is our field go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4.pp646-647.
Firth, A. & J. Wagner. 1997. “On discourse,communication,and(some)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1.pp285-300.
Firth, A. & J.Wagner.1998.“SLA property: No trespass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2.pp91-94.
Gregg,K R.1993.“Taking explanation seriously;or,Let a couple of flowers bloom ”.Applied Linguistics14.pp276-294.
Hill,K.2006.“Comments on J.Zuengler and E.R.Miller's‘Cognitive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Two parallel SLA worlds?’ A reader responds: 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The best of both worlds”.TESOL Quarterly40.pp819-826.
Holbrook, J. B. 2013. “What is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Reflections on the very idea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Synthese190.pp1865-1879.
Hulstijn,J.H.,et al.2014.“Bridging the gap”.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36.pp1-61.
Johnson, M.2004.A Philosoph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Jordan,G.2004.Theory Constru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msterdam:Benjamins.
Kasper,G.1997.“‘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1.pp307-312.
Kasper,G. & Wagner,J.2011.“Conversation analysis as an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D.Atkinson(ed.).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 York:Routledge.
Lafford, B. A.2007.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conceptualized?”.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pp735-756.
Lantolf,J.P.1996.“SLA theory building:‘Letting all the flowers bloom!’”.Language Learning46.pp713-749.
Lantolf,J.P. & K.Johnson.2007.“Extending Firth and Wagner's(1997)ontological perspective to L2 classroom praxis and teacher education”.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pp877-892.
Larsen-Freeman,D.2007.“Reflecting on the cognitive-social debat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pp773-787.
Larsen-Freeman, D. & L.Cameron.2008.“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a complex systems perspective”.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2.pp200-213.
Lave,J. & E.Wenger.1991.Situated Learning: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g,M.H.1993.“Assessment strategie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Applied Linguistics14.pp225-249.
Long,M.H.1997.“Construct validity in SLA research: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1.pp318-323.
Magnan,S.S.2007.“Presenting the focus issue”.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pp733-734.
Northon,B. & K.Toohey.2011.“Identity,language learning and social change”.Language Teaching44.pp412-446.
Ortega,L.2005.“For what and for whom is our research?The ethical as transformative lens in instructed SLA”.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9.pp427-443.
Ortega,L.2011.“SLA after the social turn: Where cognitivism and its alternative stand”.In D.Atkinson(ed.),Alternative Approach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 York:Routledge.
Pavlenko,A.2000.“Access to linguistic resources:Key variabl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Sociolinguistic Studies1.pp85-105.
Swain,M. & P.Deter.2007.“‘New’mainstream SLA theory:Expanded and enriched”.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pp820-836.
van Lier,L.1994.“Forks and hope:Pursuing understanding in differentways”.Applied Linguistics15.pp328-346.
Watson-Gegeo, K. A. 2004. “Mind, language, and epistemology:Toward a 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88.pp331-350.
Zuengler,J. & E.R.Miller.(2006).“Cognitive and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Two parallel SLA worlds?”.TESOLQuarterly40.pp35-58.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戴曼纯,2010,二语习得研究理论建设几个核心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49-53。
戴运财、王同顺、杨连瑞,2011,跨学科的二语习得研究——对二语习得学科属性的思考,《外语界》第6期:89-94。
龚嵘,2013,二/外语教育研究范式的哲学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设计决策的交互制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3期:39-46。
黄春芳,2010,论现代语言学的变迁: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170-175。
廖巧云,2013,后现代哲学视域中的认知神经语言学进路,《外语学刊》第5期:8-13。
林新华,2002,后现代主义对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启迪——读《后现代转向》有感,《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3期:74-76。
刘永兵,2010,西方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两种认识论取向,《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86-92。
毛伟宾、顾维忱,2008,关于二语习得关键期的脑神经语言机制研究及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2期:38-41。
南佐民、范谊,2007,论外语学科的研究范式创新,《外语界》第1期:2-8。
王冰、宋云霞,2011,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与范式,《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140-143。
王寅,2012,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主义,《外国语文》第2期:9-15。
文秋芳,2008,评析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20年的论战,《中国外语》第3期:13-20。
许力生,2008,从现代语言学走向后现代语言学,《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160-168。
叶洪、Julia White,2012,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向,《东南学术》第3期:15-21。
喻红,2014,二语习得互动分析:核心问题与发展方向,《外国语文》第2期:183-185。
袁博平等,2016,专家视点:语言习得研究前沿,《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03-113。
邹为诚,2008,论二语习得理论的建设——兼评《二语习得之问题》,《中国外语》第4期: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