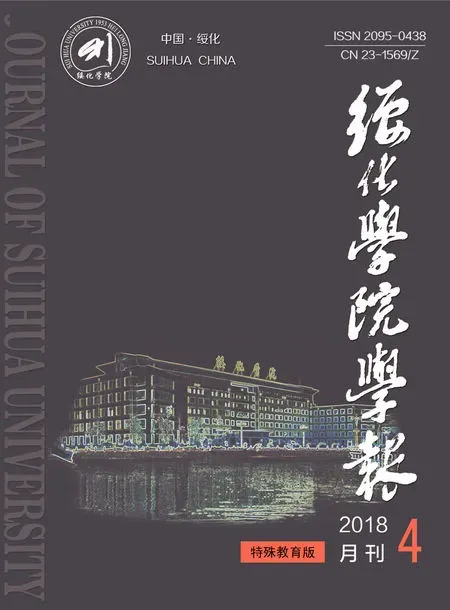培智课程的生活化与游戏化
2018-04-04许小燕
许小燕
(如皋市特殊教育学校 江苏如皋 226572)
生活化与游戏化是培智课程的双重属性,生活化指向课程的内容和目标,游戏化体现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生活化与游戏化共同构成了培智课程的基本属性,使得智障学生“具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具有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适应生活、社会以及自我服务的技能;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公民”成为可能。
一、培智“生活化”课程实施现状
自2007年2月《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颁行以来,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培智教育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都是围绕“生活化课程”展开的。[1]《方案》旗帜鲜明地将“生活化”作为“培养目标”“实施原则”“课程设置”的重要表征:培养“具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具有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适应生活、社会以及自我服务的技能;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公民;遵循“生活适应与潜能开发相结合”的原则;设置“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等一般性课程。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将“生活化”作为课程实施与评价的重要衡量标准:培智学校课程(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设置应着眼于学生的生活需要,按照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生存需要,以生活为核心组织课程内容,注重学科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在生活实践中要注重拓宽学科知识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意课程的整合,既注重现实生活的需求,又注重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据培智学校学生的能力和生活环境,充分利用一切教育资源、社区资源和现代化信息资源,实现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多元化。[2]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秉持“生活化”的课程理念,以“生活化”为课程设置与实施的圭臬,对“生活化”进行深度挖掘和极度解读。“把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适应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把生活经验知识化,知识问题生活化”[3],导致了“生活化”培智课程的“简单化、狭隘化、机械化、庸俗化”。[4]过度关注“课堂活动的现实性、真实性、情境性,忽视了课堂教学的目的性、实效性和客观性,让‘生活化’喧宾夺主、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导致了培智课程‘极端化’”。[5]
(一)生活外延简约化。“生活”是“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境况;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圆满的、完整的生活是“人类所有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总和,包括人类在社会中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日常活动和心理影射。”
部分实践者将“生活化”的概念外延简单地化约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把培养智障学生“冷暖、温饱、安全、休闲”的生活常识和“吃饭、穿衣、如厕、购物”的生活技能作为课程的核心目标和重点内容,缺少对传统文化、理想信念、内心世界等层面的聚焦和关注。在以“生活化”的名义设置和实施培智课程时,实质上是把智障学生个体纷繁复杂的多样化、个性化“生活”统一化、集体化和简约化了。在培养和训练他们掌握自我服务的生活技能的同时,忽略了他们身心的体验和探求的欲望,混淆或模糊了“生存”与“生活”的界限,剥夺了他们“生活于生活之中”的需要和权利。
因此,有研究者发出了“不能简单地将教育还原于生活,再现为现实的生活,否则儿童就不能实现教育性生长”[6]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
(二)生活范畴扁平化。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里。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之为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时间维度)”五个维度。在众多课程研究者的理论阈限和课程实施者的视野范畴里,智障学生的“生活”主要是指“微观系统的生活”,即智障学生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家庭、社区和学校。除此而外的生活与智障学生无关紧要,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对智障学生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研究者与实践者对中间系统(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外层系统(学生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宏观系统(存在于以上微观、中间、外层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无视与忽视,导致培智课程“生活化”从顶层设计到操作层面的集体坍塌,立体而丰满的“生活”范畴,被人为地压缩成为扁平化的“三点一线”——家庭、学校和社区。贯穿其中的“生活教育”也与书本知识、科学原理对立起来,甚至有意识地去知识化、去科学化、去学校化。生活教育沦为了“生下来,活下去”的功利教育,生活化课程沦为了“功能第一、实用至上”的实用课程。
(三)课程活动碎片化。受“任务分析法”的影响,基层课程实施者在对智障学生进行生活技能的养成训练时,往往将特定的学习任务(概念、知识、行为或技能)分解成为若干步骤(程序、环节或组成部分),从最基本的开始,按层次加以安排。[7]更有创新者,将步骤编成琅琅上口的儿歌或口诀,要求智障学生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模仿动作要领。例如训练智障学生掌握穿衬衫的生活技能,被分解成为:1.双手抓衣领;2.反手披身后;3.右手钻山洞;4.左手捉迷藏;5.整理前后襟;6.纽扣排排座。甚至连日常的教学常规活动也被严格地程序化了。回答问题时,先举手,再起立,然后向左前方或右前方斜跨一步(为了防止遮挡后排同学的视线),接着侧身(面对全体同学),最后回答问题返回座位。写字时“头要正,背要挺,身体坐正纸放平,提起笔,写认真,横平竖直按笔顺”。在此基础上,机械重复,轮番训练,不断强化,即使学生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技能,也要按照这些固定的程式来操作,以达到“整齐划一、严格规范”的极具观赏性的可视化效果。这种“按程序、分步骤;小步子、多循环”的课程实施活动,对长于形象记忆、动作记忆和瞬时记忆的智障学生来说,短期内或有立竿见影的显著成效。但从长远看,是将完整的知识框架和技能体系肢解成相对独立的碎片,阻断并割裂了前后的联系,学生建立的是关于“第一步、第二步……”的条件反射而非建构了知识和技能本身。
(四)课程功能标签化。“以儿童生活为依据设置课程”是现代课程理论的基本出发点。[8]从《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2007)》到《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三门一般性课程均被冠以“生活”的标签,对课程的功能与价值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标示与不容置喙的指定。诚然,生活是课程的一部分,课程的内容来源于生活,课程的价值超越生活,课程的实施基于生活,课程的目标回归于生活。然而,站在“课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立场和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所有儿童的课程都应该与他们真实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其课程的价值与功能,不仅指向“为生活做准备”,使“儿童的生活”向“成人的生活”转变,还应该贯穿于他们人生的始终,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等课程冠以“生活”标签初衷是为了彰显课程与生活的紧密联系,那么,运动与保健、绘画与手工、唱游与律动、艺术休闲、第二语言等课程门类,是不是也要贴上“生活”的标签,称其为“生活运动与保健”之类呢?如此这般,生活岂不就是一个筐,任何课程都可以往里装?实践中,“大单元主题”“培智综合课”等教学模式(模型)使得培智各课程门类之间“相互串联、相互混淆、大量重复”。“生活”的光环掩盖了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自身属性,模拟演示、技能训练成为了课程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吃”和“玩”掩盖了“学”与“思”的光彩,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的边界被模糊和侵蚀,成了“亦是亦非、似是而非”的“四不像”。
二、培智课程“生活化”的理性回归
生活是课程实施的基础,也是课程实施(教学事实发生)的场所。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强调教育的生活意义,揭示了教育与生活的本质联系。陶行知借鉴、吸收并发扬光大了杜威的观念,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概念。他主张“我们所过的生活及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东西,便是我们生活教育的内容。”但如果将课程或教学等同于生活,或者将课程教学当作生活的复制,便是对“生活教育”“生活化课程”的曲解与误会。
真正生活化的课程是“来自生活,通过生活,为了生活的”,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基于生活、归于生活”。这里的“生活”应该是圆满的、完整的生活;是动态的、连贯的生活;是“我的生活”“你的生活”“他的生活”的横向联结;是“过去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未来的生活”的纵向贯穿,既指向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又立足学生当下的现实生活,同时还瞄准了学生未来的生活样态。既是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所说的“教育应尽的职责是为我们的完满的生活做准备”。又是“现代课程理论之父”博比特所说的“教育主要是为了成人的生活,而非为了儿童生活”。[9]也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指向学生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还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基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培智课程在去简约化、扁平化、碎片化和标签化的同时,其内容、目标、环境与活动实施依然要向“生活”这一内核聚集和靠拢,从智障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以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为根基,将课程活动置于学生当下正在经历和体验的现实生活这一宏阔背景之下,将课程内容、目标、环境、实施活动与学生生活和现实社会有机结合、充分融合、完美整合,将智障学生从抽象的文字、概念、符号学习系统中解脱出来,真切感受、充分体验自然、社会、事实、事件的过程。
(一)课程内容的生活化。课程内容的生活化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智障学生当下生活中迫切需要学会的生活知识和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二是智障学生未来生活可能需要或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三是智障学生在“医(康)教结合、潜能开发”时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如在教学《我爱我家》时,教材所呈现的爸爸、妈妈、小区、住址等信息与智障学生个体的实际信息是不匹配的,在实施课程活动时,课程内容一定要与学生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实际相联系、相吻合,这样的课程内容,才是生活化的,是源于生活的也是归于生活的。
生活化的课程内容关注并密切联系智障学生的日常生活领域,如家庭、学校、社区、休闲和公共场所等,是“共性生活”下的“个性生活”,有“智障学生类群(我们)”的共性需求,也有“智障学生个体(我)”的独特需求;是“我们的”也是“我的”;是刚需的也是个需的。基层实践者在实施课程活动时,要针对智障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二)课程目标的生活化。培智生活化课程的目标是为了让智障学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未来社会生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生活化课程目标的确定,应紧扣“生活”这一主题,着眼于智障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源于生活),立足于充盈而丰满的当下现实生活(基于生活),最终提高他们未来生活质量和品位(归于生活)。
例如,生活语文课程将“认识常见的地名、会写简单的便条、会编辑发送微信短信、拨打常用的服务电话、会与医生、营业员进行对话”等作为课程目标;生活数学将“认识超市物价标签、认识人民币、数字的排列与组合、生活中的数字”等作为课程目标,都是课程目标生活化的直接体现。
(三)课程环境的生活化。课程环境的生活化是以智障学生的真实生活为基础,营造或创设有助于他们主动参与、充分体验、积极探索的氛围或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和心理氛围两类。
物理环境是指校园、教室、个别辅导室、功能教室等课程实施的场所布置和物品摆放。物理环境的创设要有情感的温度,充盈温馨宜人的生活化气息,与智障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通。有必要时,可以根据课程实施的需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营造与课程密切相关的情境或场景,让智障学生在仿真、拟真的环境中参与课程活动。例如,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创设宾馆、商场、影院、菜场、医院、银行、餐厅等体验情境,培养智障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10]心理环境也是课程环境的重要体现,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师生双方在宽松、民主、和谐、融洽的氛围中,重温生活、感受生活、再现生活、经历生活、表达生活,消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隔阂,达到“师生之间其乐也融融,生生之间其乐也洩洩”的境界。
(四)课程实施的生活化。培智生活化课程的实施包括课堂和课外两个活动时空。课堂活动可采取单元主题教学或分科教学两种方式进行。单元主题教学是指把符合智障学生生活需要的课程内容以单元的形式呈现,将不同的课程门类和科目串联起来,各科目承担同一主题框架下的对应教学内容。[11]如《美丽的春天》主题单元,生活语文实施与春天相关的识字、说话、写话训练;生活数学计算花朵的数量,解决植树栽花、春游分组等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绘画与手工用线条和色彩表现春天的色彩斑斓;唱游与律动用歌声和舞蹈表达春天的婀娜多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乡约在春季”等主题活动,等等;培智课程分科教学大多采取“综合课”的方式进行,根据课程内容和活动需要,融“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绘画与手工、唱游与律动、运动与保健、艺术休闲、康复训练”等课程元素于一体。课外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综合实践活动,引导智障学生观察生活、参与生活、体验生活、探究生活,在活动中解决实际问题,锻炼实践能力。如,《超市购物》《医院看病》《车站乘车》,等等。
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课程“不仅是让智障学生学习日常生活常识和基本生活技能的工具、途径,也是智障学生思考生活的意义,确立发展的方向,学会生活,主宰生活,成为生活的主人的载体和平台。”[12]
三、游戏化:培智课程再出发
游戏是儿童的本质属性。游戏不仅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儿童学习的重要方式。明代王守仁在《传习录(七)·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对儿童的游戏天性进行了生动的指认和诗性的确证,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13]现代学前教育鼻祖,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主张“系统研究儿童的游戏并把游戏与教育结合起来”,他指出“游戏是儿童内部需要和冲动的表现,游戏作为儿童最独特的自发活动,自然成为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福禄贝尔眼里,一个游戏着的儿童,一个全神贯注地沉醉于游戏中的儿童,正是幼儿期儿童生活最美好的表现。
游戏是“儿童认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工具”,为儿童“理解世界,以社会交际的方式与人交往、表达及控制情绪、发展象征力提供机会”。所谓儿童从来都是游戏着的儿童,而游戏的状态就是儿童存在的状态。游戏精神代表了儿童心智发展的态度。珍视游戏与生活的价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设计和实施课程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也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实践。[14]培智课程的游戏化,不纯粹确指教师在平时教学中所采用的“丢手绢、开火车、摘果果”之类的游戏方法与形式,而且泛指鲜活的游戏思想、自由的游戏精神、生动的游戏姿态、丰富的游戏形式以及“课程即游戏”的游戏性课程范式。[15]培智课程的游戏化是游戏精神与游戏形式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渗透与体现,不仅指向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方式,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是“游戏化教学、游戏性课程、游戏式教育”的集大成。
在培智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中,研究者与实践者都要准确把握“游戏化教学、游戏性课程、游戏式教育”的内涵,用游戏的思想和精神指引课程实施活动;站在智障儿童的立场,用游戏的视野解读课程内容和目标;用丰富多彩的游戏形式和手段活化课堂,构建游戏教学的常模,实现课程与儿童、课程与游戏、游戏与儿童的高度契合、深度融合。
(一)正确理解游戏的自由精神。当前,培智课堂游戏活动存在两种倾向:“高度的控制”与“极度的放任”。前者是“一定框架和体制内的自由”,具有鲜明的“中国培智教育特色”;后者则严格遵循美国游戏课程设计“无干扰原则”,体现了“游戏的无目的性”。“高度的控制”缺少了游戏的意义,“极度的放任”则失去了游戏的价值,只有“无目的的合目的”,在“无目的”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目的”才是游戏自由精神的精髓、要义和内核。虞永平教授指出,课程游戏化不是用游戏去替代课程活动,而是要把游戏的理念、精神渗透到各类课程活动中,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同时提升课程建设和实践水平。培智课程设计者要形成科学、系统、成熟的教育观、游戏观和儿童观,为智障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和“有目的的自由”,让他们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经验技能的习得与自我认知的建构。[16]
(二)严格遵守游戏的秩序规则。赫伊津哈说,“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游戏的秩序即规则,一切游戏都有规则。规则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协调人们之间关系和行为冲突的社会性标准。在游戏中,秩序和规则是“公平与公正、自由与平等、竞争与发展等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体现,也是游戏得以顺利进行的约束机制和制度保障。遵守秩序和规则,可以获得成功、愉悦身心、获取奖励;不遵守秩序和规则就会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并非“人为的、额外的强加”,其本身就是游戏的组成部分,也是游戏的秩序和规则之一。正如卢梭提出的“自然后果法”那样,“我们不能为了惩罚孩子而惩罚孩子,应当使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2007)》提出让智障学生“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公民”这一培养目标,进一步突出、强调了“规则意识”在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鲜明意义和重要作用。可见,培养智障学生的“规则意识”是课程设计的旨归,也是课程实施的基点。在课程设计的游戏中,智障学生通过游戏形成“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公正平等”等道德品质、秩序规范及相应的行为价值,而违反这些社会行为准则所造成的后果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自食其果。所以,强调并严格遵守游戏的秩序规则,有利于培养智障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促进他们的社会性发展,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三)准确把握游戏与生活及课程的关系。“游戏产生并发展于儿童的生活,并且赋予儿童以童年的生活、有灵性的生活”,从这一意义来说,游戏就是儿童的成长方式,构成了儿童生活的全部。从儿童的视角来看,游戏与生活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个面,完全融为一体,无法完全剥离,而这枚硬币就是儿童。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就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站在培智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课程的游戏化并不排斥和摒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知识与技能都是课程建设的中心和重点。课程的游戏化强调了“知识技能的体验性与内生性,而这种体验性与内生性必然要求课程与生活之间建立起自然、和谐、互动的联系”——即课程的生活化或生活化了的课程。
詹姆斯·汉斯说,“游戏就是制造意义,是解释及操作‘给定’世界的方式,是不断适应和操纵规则的方式;知识不是什么‘外在’的需要人们去把握的东西,它是在游戏中行动的产物。”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游戏的目的和意义——游戏与课程互为生长点,课程生成游戏的同时游戏也生成课程。
游戏、生活、课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想要完全厘清并加以区别,几乎是一种一厢情愿式地想当然,只能从理论上进行假设与自证。而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者与实践者适宜采取“边界模糊”的处置方式,以规避或减少思想混乱、认知粗陋、实践肤浅的问题。
在培智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广大研究者与实践者应然秉持“课程生活化、课程游戏化”的教育观、儿童观、课程观,以“生活化”为课程的内容和目标导向,以“游戏化”为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原则,让“生活化的课程”和“游戏化的课程”成为智障学生“维持生命和身体生长的奶水”,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成长的需要和社会性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辉.我国培智学校课程改革研究的现状、反思与展望[J].中国特殊教育,2010(12):47-5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教育部关于发布实施《盲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的通知[EB/OL].http://www.moe.edu.cn/srcsite/A06/s3331/201612/t20161213_291722.html.2016-12-01/2017-10-05.
[3]吴春艳.论培智学校教学生活化[J].中国特殊教育,2012(3):28-32.
[4]邓猛,景时,李芳.关于培智学校课程改革的思考[J].中国特殊教育,2014(12):28-33.
[5]王亮.如何构建培智数学生活化的高效课堂[J].读与写,2015(12):224-232.
[6]张楚廷.课程要回归生活吗?[J].课程·教材·教法,2010(5):3-7.
[7]朴永馨,顾定倩,邓猛.特殊教育辞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0):319.
[8]唐斌,朱永新.杜威“教育即生活”本真意义及当代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11(10):84-87.
[9]郑国民,刘幸.博比特以及他所开创的现代课程理论[J].课程·教材·教法,2016(8):122-127.
[10]许小燕.应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创设多感觉融合情境[J].现代特殊教育,2015(9):53-55.
[11]黄春娣.培智学校多学科生活化教学的探究[J].工作研究,2012(9):194-195.
[12]傅王倩,莫琳琳,肖非.从“知识学习”走向“完满生活”——我国培智学校课程改革价值取向的变迁[J].中国特殊教育,2016(6):32-37.
[13]王守仁.传习录(七)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贵在引导[EB/OL].http://www.99lib.net/book/6340/219662.htm.2017-10-06.
[14]丁月玲.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的推进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5(12):64-66.
[15]李继东.“游戏式”:语文教学新视角[J].教育研究与评论(小学教育教学),2015(9):50-56.
[16]徐皇君.让孩子在有准备的环境中成长[J].学前教育研究,2014(3):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