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背景下书写中国文学史
2018-04-02戴燕
戴燕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
一
一九○二年三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第一场丁龙(Dean Lung Professor)讲座的报告,他的题目是China and Chinese(傅尚霖译作《中国与中国人民》,见其《英国汉学家翟里斯教授的生平和著作》,《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二期,1935年6月;罗丹、顾海东、栗亚娟所译题作《中国和中国人》,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一讲介绍中国的语言,开始就说汉语分两种,一种是口语,一种是书面语,口语基本上三个月后就能应付日常,书面语却要活到老学到老。

《中国孤儿》1797年皇家剧院演出本扉页
对于想要认识和研究中国的西方人来说,汉语是必备的工具。翟理斯曾说如果懂汉语,西方人便能与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做生意,也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了解曾国藩、李鸿章他们何以让西方外交官相形见绌。基于这样的意识,像翟理斯这样的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家,有不少首先是汉语的语言学家。他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西方语言学知识,对汉语加以描述和分析,也会编一些英汉词典,例如理雅各编有《英汉及马来语词典》(1814)、马礼逊编有《英华词典》(1817-1823)、威妥玛编有《语言自迩集》(1867)、卫三畏编有《汉英韵府》(1874),翟理斯也编过一部《华英字典》(1892)。而在卫三畏的《中国总论》(1848)等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语言的看法,大体上是认为中文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单音节,没有时间性,书面文字和口语有差別。在翟理斯看来,中文的书面语两千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口语里却有八大方言,现在是以北京方言为普通话即官方语言,他建议“打算学习中文的学生都应该学习普通话的口语”(罗丹等译《中国和中国人》,10-11页)。
其次,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家有很多也是翻译家,如理雅各就是在王韬的协助下翻译了《中国经典》(1861-1893),包括有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和《太上感应篇》等;而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翻译及流传,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元杂剧《赵氏孤儿》。《赵氏孤儿》早在一七三二年至一七三三年即由耶稣会士马若瑟译成法文,因这一译本被收入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1735),随着《中华帝国志》很快被译成英文,它也有了英文本,随之又有了德文、俄文本,并同时有了英国人、法国人的评论。法国作家伏尔泰认为它可以“使人了解中国精神”,于一七五五年将这一“历史悲剧”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一七八一年,歌德又据以写作了Elpenor(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29年《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与《赵氏孤儿》一样在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的,还有清初署名名教中人所编的《好逑传》,它一七一九年由住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詹姆士·威尔金森所翻译,起初只是为学习中文而作的翻译练习,后经配尔西整理出版;一七六六年又有了法文本,然后是德文本。歌德在与席勒的通信中就提到过德文本《好逑传》,据说他还读过元代武汉臣的《老生儿》(德庇时英译,1871)以及《花笺记》(汤姆士英译,1827)、《玉娇梨》(雷慕沙法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德庇时译法文本《今古奇观》选)等。二十世纪以前,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戏曲,欧洲评论家对于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如《幸运之盟》《玉娇梨》等较有兴趣,当儒莲将《平山冷燕》译成法文(1860)后,就有评论家称赞它的文体、结构可以媲美欧洲的任何一部小说。翟理斯也翻译过相当多的中国典籍,有如《古今诗选》(1898)、《佛国记》、《庄子》,也有《聊斋志异选》(1880),还有包括《三国演义》片段的《古文选珍》(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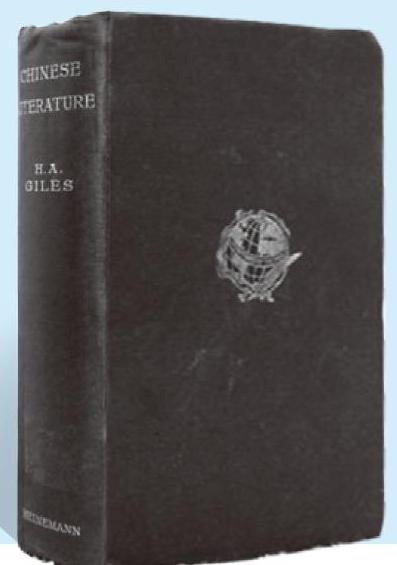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英文初版,1901
二
到哥伦比亚大学讲演的前一年,翟理斯应“世界文学简史”(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丛书主编艾德蒙·高斯(Edmund W. Gosse)的邀请,编写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William Heinemann & Co. 1901。参见王绍祥的博士论文《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第四节《一部〈中国文学史〉》,267页,2004年),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学史”的编写潮流中,中国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的初版序言中就说:这部书代表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过去的英国读者,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整体文学(the general literature of China),即便是浅显地了解,都无法在任何一部书中得到(郑振铎《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22年9月21日《文学旬刊》第五十期)。
《中国文学史》(刘帅译中文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按时代顺序分八个章节:
第一卷分封时代(前600-前200)从传说时期讲起,以公元前六世纪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起点,而以孔子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人,介绍五经四书、孙子、荀子、《尔雅》、《穆天子传》,以及诗人屈原、宋玉和铭文,也介绍“与儒家分庭抗礼”的道家文学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
第二卷汉代(前200-200)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讲起,提到李斯、晁错、李陵、路温舒、刘向刘歆、扬雄、王充、马融、蔡邕、郑玄等一系列作家,诗人有汉武帝、班婕妤,史家有司马迁,还有编纂词典的许慎,佛学方面则有法显、鸠摩罗什至含玄奘。
第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00-600)主要介绍建安七子、曹操曹植、竹林七贤、陶渊明、鲍照、萧衍、薛道衡、傅奕、王绩的诗,经学和一般文学则有皇甫谧、郭象、郭璞、范晔、沈约,最后是编了《文选》的萧统。
第四卷唐代(600-900)仍以诗为中心,谈到王勃、陈子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崔颢、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马自然等诗人,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谈到作为学者的魏征、颜师古、李百药、孔颖达、陆法言,有道家倾向的张志和,还有散文作家柳宗元、韩愈、李华。
第五卷宋代(900-1200)首先谈到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史学、经学和一般文学领域有欧阳修、宋祁、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郑樵、朱熹,诗人有陈抟、杨亿、王安石、僧人洪觉范、叶适等,但诗整体进入衰落期。有《广韵》《六书故》等几部字典,也开始出现对文学影响颇大的百科全书,如《事类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通典》。又有一部神奇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
第六卷元朝(1200-1368)首先介绍诗人文天祥、刘基,同时指出元代的诗已经不像汉族政权统治时期那样丰富,质量也有所不及,但戏剧和小说的产生,却足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两个重要领域而被铭记。戏曲有《赵氏孤儿》(纪君祥)、《西厢记》(王实甫)、《合汗衫》(张国宾)等,小说则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第七卷明代文学(1368-1644)首先介绍了宋濂、方孝孺、杨继盛、沈束、宗臣、汪道昆、许獬、李时珍和徐光启,不过重点还是在小说和戏剧。小说提到《金瓶梅》《玉娇梨》《(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平山冷燕》《二度梅》,戏剧提到《琵琶记》。诗人有解缙,又有赵彩姬、赵丽华这样的妓女诗人。
第八卷清代文学(1644-1900)重点介绍了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也讲到康乾时代编纂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文学大工程。学者提到顾绛、朱用纯、蓝鼎元、张廷玉、袁枚、赵翼、阮元等,又提到道教的《感应篇》《玉历抄传》,而以一八四九年阮元去世作为中国“与外国直面相对”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以后开始出现公告、翻译等新的文体。

《中国文学史》[英]翟理斯著 刘 帅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整部文学史篇幅不大,点到名字的作家很多,却蜻蜓点水,只有三言两语的介绍,占比重较大的是作品,不光有诗文,还有戏曲和小说的节译。
三
翟理斯无疑是当时最具声望的西方汉学家,他在中国也很有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他去世,在中国几乎就有同时的报道。潘文夫在《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去世》一文中介绍他“关于我国语文的著作”就有二十三种,又有“如老庄及我国诗文的翻译,都是艰巨的大业”,他的代表作为“空前未有”的《华英字典》,而他所著《中国文学史》,“亦为同类西文著作中的杰构”(1935年4月10日《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七期)。同年,傅尚霖撰文评介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教授的生平及其著作概略,说他能用“流利之标准国语谈话”,也能讲广州、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方言,“对中国的文化经典,能有充分的敬重和赏识”,同时有“西方治学的科学脑想”,所以能成汉学家,而非“字纸箩中讨生活自炫深博的腐儒”,并且他“先有良好的中英文基础,进而从事编译;由编译而创作;由创作而升为教授;为教授而宣传中国文明;由其宣传而令中国文化得欧西人士普遍的鉴赏;由鉴赏而令汉学成为欧美大学中一种科学,其功非常伟大”,是“汉学史中一个不朽的人物”。(傅尚霖《英国汉学家翟里斯教授的生平和著作》,1935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二期)赵元任晚年回忆一九二四年他去欧洲游学,与翟理斯有一面之缘,也表扬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老人”,《华英字典》迄今仍是权威性的参考书。(罗斯玛丽·列文森《赵元任传》,焦立为译,15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
而最早对翟理斯加以评论的中国人,也许要算是辜鸿铭。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又名《春秋大义》,北京每日新闻社1915年首版)一书中,辜鸿铭批评翟理斯“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也“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他还说翟理斯英文流畅,也能翻译中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他所有的著作,“没有一句能表明他曾把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的事实”。由此,他更质疑“所有外國学者关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缺乏人道的或实践的意义”。虽然他称赞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堪称“中文英译的模范”,但又指出“《聊斋志异》尽管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却仍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最上乘之作”,言下之意,便是针锋相对地批评翟理斯缺乏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和判断(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序言》4页、《一个大汉学家》122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辜鸿铭是通晓中西文化的晚清学者,在他看来,西方世界除了法国,英、美、德国人都不能理解中国文明,可是在当时,又唯有中国文明能够拯救欧洲文明于毁灭。而所谓中国文明就是“义与礼”,他说中国人因此有着成年人的智能和纯真的赤子之心,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的完美结合,在文学艺术中,也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使人得到愉悦和满足。他还谈到中国的语言,称之为一种“心灵语言”,说外国人以为汉语难学,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太多的教育,受过理性与科学熏陶的缘故(辜鸿铭的论文《中国人的精神—在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载《中国人的精神》29-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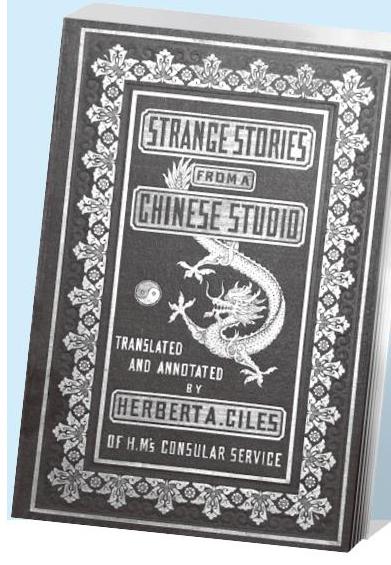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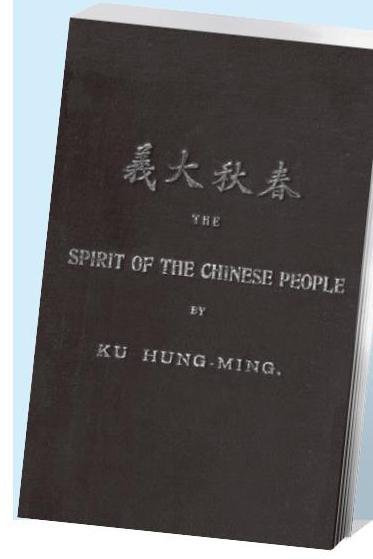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版
如果说辜鸿铭评论翟理斯这位“大汉学家”有借题发挥之意,目的是要说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不准确,评价也并不公允,那么,郑振铎的《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大概算是中文世界关于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篇真正的学术书评。不过,与辜鸿铭的结论一样,郑振铎也说翟理斯对中国文学“实在是没有完全的研究,他的谬误颠倒的地方,又到处遇见”,而由于他写的是第一部英文本中国文学史,他个人最近“且因研究中国文学的功绩,受了尊贵的勋位”,所以必须要加以批评,以免他“以误传误”,使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产生误会。他对翟理斯的第一个意见,就是对作家的选择“太疏略”,好些影响大的作家如谢灵运、李义山、元好问、王渔洋、方苞等都未提及。不仅如此,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他对李白、杜甫的关心不及司空图,他谈《红楼梦》也谈得太多,尤其奇怪的是对“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极模糊”的《聊斋志异》“推崇甚至”。总之,这部《中国文学史》“百孔千疮,可读处极少”,根源在于翟理斯“对于中国文学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当时庸俗的文人太接近”。郑振铎最后表示,应该有中国人写出英文的《中国文学史》来,“矫正他的错失,免得能说英文而喜欢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类,永远为此不完全的书所误”,但他又说“中文本的中国文学史到现在也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所以“这恐怕是一种空幻而不见答的希望”。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中华书局2016年版
郑振铎后来果然出版了四册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1933),这一文学史,是要记述“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一方面“给我们自己以策励”,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的邻邦以对于我们的往昔与今日的充分的了解”。(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绪言》,8页,朴社1932年)
四
然而,一部完备的中国文学史并不可能一蹴而就,按照批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似乎连给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资格都没有的吴世昌的说法,那必须要等到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完备以后,才可能“有像样的整部文学史出现”,而比郑振铎更为理想的文学史,一个是王国维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又名《宋元戏曲史》),一个是胡适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吴世昌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1933年3月《新月》第四卷第六期)。
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有学者认为是受了日本汉学家的影响,并通过日本汉学家间接受西方学者的启发,表现在对《窦娥冤》《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样的评价上(黄仕忠《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导读》,21页,凤凰出版社2010年);而更早在傅斯年的推荐评论中,则是特别强调王国维研究元曲“具世界眼光”。傅斯年说“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日”,王国维论元曲,“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傅斯年《评〈宋元戏曲史〉》,1919年1月《新潮》第一卷第一号)这里所说的世界眼光,是指研究中国文学,同时了解外国文学,即是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重新解读、重新评价。而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谈论中国文学,王国维首先看到的便是“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很早便有《赵氏孤儿》,还有《老生儿》《汉宫秋》《灰阑记》《连环计》《看钱奴》等,“《元曲选》百种中,译成外国文者,已达三十种矣”,他自己读这些为曾经的儒硕所“鄙弃不复道”的元杂剧,“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宋元戏曲史》《余论》《自序》),因此有志于探究它的渊源、变化。
元杂剧的文学价值,王国维说在其文章自然,“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又曲中多用俗语”(《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杂剧之文章》)。这个评价,已经相当近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标准:一是从文学中看到中国社会,二是从文学中学习汉语。
五
当王国维一九一三年于日本撰写《宋元戏曲史》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他和赵元任都是利用庚子赔款一九一○年到美国的第二届留学生。赴美之前,胡适在上海的一位英文教员正是辜鸿铭的学生(胡适《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九一五年,他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也跟德国籍的首任丁龙讲座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辅修汉学(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胡適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留学期间,胡适因教人汉语,总结了一个教学方法,是“先授以单简之榦子。榦子者(root),语之根也。先从象形入手,次及会意、指事,以至于谐声”,这个方法,他以为“亦可以施诸吾国初学也”。这是他开始借用英文“语根”的概念来分析汉字结构,而且认为不光可以此教外国人,也可以教中国人,就是说中国人也可以接受这一分析。他和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时,经常一起讨论中国语言问题。他以希腊、拉丁文来比拟中国的文言,说前者已为死文字,文言尚且在用,是半死的文字。教文言时,第一要“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第二在童蒙阶段,应从象形指事字入手,到了中学以上再习字源学,使人由兴趣记忆字义;第三要借助《马氏文通》,以文法教国文;第四要采用标点,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二]》卷十一,1915年8月26日记《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这几条,都是挪用了西方的语言分析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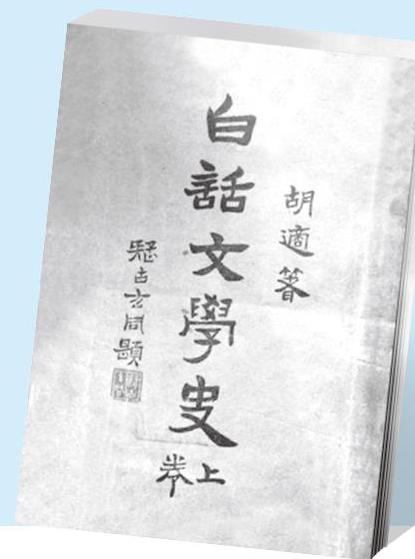
《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著 新月书店1923年版
在美国七年,让胡适在审视自己的母语汉语时,也逐渐带上了西方人的视角。一九一六年,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1916年2月3日胡适寄陈独秀,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便是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种转变。这也是胡适与年长他三十多岁的辜鸿铭之间的很大不同,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胡适认为西方文学及文化更值得取法。但是,在对待西方汉学家的态度上,他却和辜鸿铭一样不免心存怀疑。他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读到翟理斯之子Lionel Giles发表的《〈敦煌录〉译释》一文,发现它“讹谬无数”,以为“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于是为文正之,为该会报刊载,这让他一面有“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的感慨,一面也得到“西人之治汉学,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的经验,并且相信“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胡适日记全编[一]》卷五,1914年8月2日记《解儿司误读汉文》;《胡适日记全编[二]》卷八,1915年2月11日记《西方学者勇于改过》)。
就在这段时间,由于主张“文学革命”,胡适提出了“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样一个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中国文学的历史看成是中国文学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变迁的趋势是活文学代替死文学。所谓活文学,即是白话所写,死文学指半死的文言所写。他以但丁创意大利文、乔叟等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创德意志文为例,说中国文学应该是“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因当时的词曲和剧本小说,“皆第一流之文字,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日记全编[二]》,1916年4月5日记《吾国历史上的文學革命》)这恰好与撰写《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意见相近。而在与任叔永等人讨论过后,他又指出白话是文言的进化,文言的文字可读不可听,无法用于演说、讲学和笔记,白话的文字却是既可读又听得懂,“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语言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胡适日记全编[二]》卷十三,1916年7月6日追记《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
一九二二年,胡适在当时教育部的国语讲习所讲了他的“国语文学史”,后来他自己整理修订正式出版时更名为《白话文学史(上卷)》。这一文学史虽然只讲到汉唐部分,可是在一九二○到一九三六年间,胡适还是花了很多精力在元以后古典小说的研究上,写下涉及《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镜花缘》的三十多篇论文,同时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印行采用新式标点并分段的白话小说。在为亚东出版的《水浒传》写的《〈水浒传〉考证》(载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亚东图书馆1920年)里,他特别交待新的版本删去了金圣叹的总评和夹评,是为了避免读者受旧式读法的影响,而能够以新的历史眼光去看梁山泊故事由南宋末至明代的演变。而他对《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续作者的考证,也得到过鲁迅“较然彰明”的肯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新书局1927年4版)。
不管是不是赞成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理论,从“语言工具”入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完全改变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看法。正如一九三二年胡适在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胡适文集》5)写序时所说,“十四五年前我开始作小说考证时,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种《水浒传》,一种《三国演义》,两种《西游记》,一种《隋唐演义》”,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水浒传》明刻本就有六种之多,《三国演义》靠着日本所藏几个古本,也“差不多可以知道元朝到清初三国的故事演变”,《西游记》在日本已知有七部明刻本,加上宋刊的两种《三藏法师取经记》和盐谷温印行的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从此《西游记》的历史的研究可以有实物的根据”。现在“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我们可以了解孙楷第“渡海看小说”使命的重大!而中国学界对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实在是既受到过西方汉学家的启发,最终也超越了东西方汉学家的水平。
二○一六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