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受词语监禁的大师
2018-04-02张洪凌
张洪凌

威廉·H.加斯(William Howard Gass1924-2017)
二○一七年十二月美国后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和批评家威廉·H.加斯(William Howard Gass)去世后,最先报道他离世消息的居然是欧洲的媒体,然后才是美国的各大报刊杂志。跟伍迪·艾伦一样,他在欧洲的名气要大于美国。不过我读的第一份讣告不是欧美的大媒体,而是本地的《圣路易斯邮报》。倒不是因为加斯在圣路易斯市居住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是因为早在二○○八年,差不多十年前,《圣路易斯邮报》负责文艺版的记者简·亨德森就告诉过我,她已经将加斯的讣告写好,只等他去世就发出来。那一年加斯已经八十四岁,做好他随时去世的准备似乎也不过分。简大概沒想到她的这份讣告得等九年之久。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加斯又出了三本书,一本随笔集《终身监禁》,一部长篇小说《中央C》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眼睛》。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一五年,在他的新书《眼睛》的朗读会上。他确实比以前衰老了不少,没有印象中那么强悍了,如果在街上碰到他,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认出他。但一旦接近他,你会感到过去的加斯仍然在你眼前,那对灰绿色的眼睛依旧那么逼人,像老猫的眼睛不敢让人对视。我送了他一本我翻译的王小波中篇小说集,觉得他应该会喜欢。如果他年轻一点,我会要求再上门拜访他,听他谈谈对王小波的看法,甚至要求他写一篇书评。但他已经高寿得让人不忍心去打搅他,不过我以为自己还能再等到一本新书,但这次传来的终于是他瓦斯告罄的消息。

威廉·加斯《隧道》(The Tunnel),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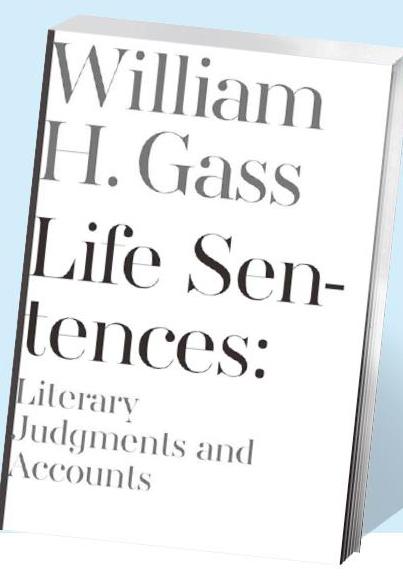
威廉·加斯《终身监禁》(Life Sentences:Literary Jugdments and Accounts)2015
贴在加斯头上的标签很多: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领军人物、元小说(meta-fiction)的创始人,长篇小说《隧道》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文学批评家,曾三次赢得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随笔散文家、哲学教授,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职位其实一直在哲学系。关于加斯,人们还有很多固定成形的印象,比方说他写的小说没几个人能读得懂;他虽然写小说,其实他写得最好的是随笔散文,是当代美国最好的随笔散文家—这点倒是和王小波的情形有点类似。自然,和王小波一样,他本人对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经常强调哲学是他谋生的手段,文学是他的隐秘激情所在。随笔散文是约稿,有完成的理由和期限,而小说没有;他对语言和比喻极为痴迷—有人比喻他像一台发动机,一旦发动就停不下来;他对德国诗人里尔克和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极为推崇。因为对里尔克英译诗不满,他开始学习德文,并在本校一名德语教授的帮助下翻译了里尔克的诗歌。不过,他翻译的里尔克并没有得到好评,证明大作家不一定是好的翻译家。第一次读斯泰因害得他生了一场病,他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他的作品想要娶的女人。斯泰因对加斯的小说创作影响深刻,她认为情节和语法都是人为的机巧,不是文学的自然要素。加斯在语法上虽然没有斯泰因走得那么远,但在打破传统的情节方面确实可以看到斯泰因的影子。他曾经写道:“我的故事是恶毒地反叙事,我的散文是恶意地反说明。我不假装自己拥有任何秘密;我不信仰任何主义;我不敢去改造读者,也不想去恭维他们的自我。”
他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过他对语言的终身迷恋来源于不幸的童年。加斯于一九二四年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城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钢城沃伦度过童年时代。母亲是家庭妇女,酗酒,性格极端被动,是“一汪沉默的水”;父亲是失败的建筑师,在一战中受过伤,思想右翼,脑子里充满偏见和种族歧视,阅读报刊杂志不过是为了寻找发泄仇恨的目标,对幼小的加斯和酗酒的妻子常常实施语言暴力。父亲的语言虐待在他心理上造成巨大伤害,让他意识到语言的巨大能量。他声称他后来投身写作是为了“扯平”,为了把过去从记忆中抹去,为此他坐了终身的语言监。

华盛顿大学国际作家中心(International Writers Center)活动海报
我有幸结识加斯并做了他几年时间的学生。认识他是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当时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创意写作班,朋友自告奋勇地将我的申请作品送给加斯看。我本来没抱太大指望,谁知第二天便接到他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比尔(他身边的人都叫他比尔)想见见我,跟我谈谈我的作品。我就这样找到加斯当时主持的国际作家中心,跟他见了面,听他谈了对我的作品的修改意见。然后在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很随意地说,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写封推荐信。我当时只是芳邦大学英语系的一个本科生,能得到像加斯这样大作家的推荐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后来,除了最好的爱荷华创意写作班以外,我申请的其他学校都接受了我。加斯的推荐信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我选择了华盛顿大学,除了丰厚的全额奖学金以外,能继续跟加斯学习就是第二个重要原因了。
加斯当时主持的国际作家中心不在华盛顿大学的主校园,而是在被他认为是没有历史的克莱顿城,周围都是商业大楼,街上是行色匆匆的中青年白领。中心在一栋大楼的地下室,被边缘化的意味十分明显。里面倒是宽敞明亮,有许多散乱的书籍,墙上挂了一些摄影作品,不记得是不是加斯本人的—他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摄影家,多次举办过个展。中心由加斯在一九九○年创立,目的是把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作家带到圣路易斯,介绍给当地的读者。我记得他提到的中国作家有王蒙和张洁等,都是老一代的作家。他夸奖过王蒙的聪明和张洁的美丽。但国际作家中心请来的英语作家都非常前卫,比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迈克尔·翁达杰以及莉迪亚·戴维斯,还有一个我的同龄人本·马库斯,戴眼镜,光头,一张忧伤的脸。他的父亲是数学家,母亲是研究伍尔夫的学者,本人的专业是哲学和创意写作,当时来朗读的作品是他的处女作《线绳时代》。虽然他十分年轻,加斯对他却非常重视。某种意义上讲,本可以被看作是加斯和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两者常常被人弄混)等晦涩难懂的实验派小说的传人。朗读后加斯还在家为他办了一个派对。加斯家离华大不远,走路就可以到,是一栋乔治王时代建筑风格的房子。我第一次见识了加斯两万册的私人藏书,但最让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惊叹的是他家墙上挂的一幅胡安·米罗的巨幅原作。我们几个窃窃私语,说光这幅画可能就价值五十万美金吧。米罗也是我非常喜爱的抽象派画家。这个巧合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相遇并非偶然。
国际作家中心的地下办公室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就是在这里,我跟加斯上了一门对我影响至深的独立研究,选题是欧洲的现代派作家。我们选择的作家有格拉斯、卡尔维诺、米歇尔·图尼埃等,都是深受王小波喜爱的一些作家,但当时我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王小波,也可能刚刚听说。上课的方式非常随意,就是我读他们的作品,然后去国际作家中心跟加斯一对一地讨论。我读得很细致,不过再细的细节加斯也是如数家珍。最愉快的阅读是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加斯曾经给华大建筑系的学生专门开课讲过这本书,认为每一个建筑师都不仅应该阅读还应该相信这本书。我在国内已经读过中文译本,这次读的是加斯推荐的资深意大利文學翻译大家威廉·韦弗的译本,诗一样的语言。加斯告诉我,马可·波罗在书中提到的那座水像风一样从房屋中穿过的Kin-sai城就是杭州。他曾经有个心愿—在杭州桥头阅读《看不见的城市》。去中国的时候他还真带了这本书,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加斯认为《看不见的城市》是对但丁《神曲》的重新书写和回应,维吉尔和但丁,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文本中的九个章节和《神曲》中的九层地狱都是互相对应的关系。书中的可汗应该是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坐牢时的狱友。当我们被墙监禁时,对墙外的世界,对看不见的城市的梦想就变得异常重要。然而借助梦想我们就能自由了吗?我们不过是从由砖墙砌成的监狱逃到了由语言建成的监狱,从监禁我们的身体逃到监禁我们心灵和想象力的看不见的城市,逃到欲望之城和死亡之城,逃到轻盈之城和符号之城,连绵不断的城市,一张无所不在的蜘蛛网。迄今我还记得我们对小说结尾的讨论,地狱究竟在哪里?加斯说地狱就在人间。地狱就是这些看不见的城市。我记得自己听到这里颇为不服地问,如果我们就生活在地狱,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如果我们就生活在地狱里,那希望在哪里?加斯用卡尔维诺结尾的话回答了我:“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事,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希望在那些还有信念的人身上,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那些还相信的人。加斯显然属于后一种人。
人间这个“地狱”可能跟但丁笔下的炼狱可比性不大,应该更接近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概念。后来我读到加斯的同名随笔《看不见的城市》,对卡尔维诺和加斯的地狱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加斯在这篇随笔中发明了一个叫弗朗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名前程远大的青年律师,是年轻的丈夫和初为人父的父亲,是棒球迷,是只穿棕黑两色裤子的白领,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卡尔维诺笔下,放在一座只由楼梯和过道、大街和小巷、通衢和马路、电梯和滑梯、人行道和电车线、抽屉和地铁站、公车站和起重机、裤子的拉链和马桶的拉线构成的城市里,他只有一个身份:通勤员,穿行于办公桌、玻璃窗、秘书和复印机之间。在这座城市里,弗朗克只是循环线上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城市这座巨大身体中的一滴血。
有时候加斯也会谈到一些作家的趣闻轶事。比如君特·格拉斯如何对人不信任,要做他的朋友得通过很多考验。加斯十分幸运地通过了格拉斯的考验,成为他的好友。他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笔会曾在纽约举办了一个豪华的筹款晚会,邀请了世界的顶级富豪和顶级作家,他和格拉斯都有幸应邀出席。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格拉斯置身于富豪和社交名流之间,跌坐在过道的红丝绒靠椅上,苦不堪言。
除了这门欧洲当代作家的独立研究外,我还在一九九九年春季选过他的一门“哲学与文学”的大课,探讨哲学和文学的相互渗透以及它们和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哲学和文学都是虚构的观念艺术,跟我们通常的看法“小说是形象的艺术”相反。当然,如果你对他的作品足够熟悉的话,对他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看法就不会觉得奇怪。这是他在退休之前开的最后一门课,选课的学生有一百五十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他自然没有精力看每个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本科生的论文由他的助教看,但研究生的论文还是他本人看。我记得他在我的一篇论文的某处批过这么几个字:“精彩的误读!”让我不禁莞尔。他上课时不太喜欢学生发言,不喜欢被打断,基本上是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跟现在流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完全相反。他的幽默也非常黑色,心灵脆弱一点可能会觉得受到冒犯。“一个孩子会报销掉你一本书,”他对着一百多号青年学子这么说,“而我有五个。”在形容某个东西很糟糕的时候,他说“跟高中生演的戏剧一样糟”。这是他上课时说的话,还比较收敛,课外的话更尖锐。翻读《巴黎评论》一九七七年对他的一个访谈,他居然说如果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会选择一个不同的阴道来到人世。问他写作的动机,他引用笔下一个人物的话,“我想飞得高高的,这样我在拉屎的时候,一个人都不会错过”。

本·马库斯《线绳时代》(The Age of Wire and String)

《看不见的城市》[意]卡尔维诺著张 密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这门课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在众星璀璨的美国现代派作家中,他只选了四位女作家来讲述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其中两位是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玛丽安娜·穆尔,两位是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和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都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加斯除了要求学生阅读她们的作品选集之外,还专门为玛丽安娜·穆尔的诗歌编了一本词典,六十二页,分四个栏目:人名、地名、植物和动物。玛丽安娜·穆尔的诗歌用词冷僻,词汇量相当大,没有这本词典还真没法读懂。读毕肖普,他强调要慢读,说她是一艘缓缓移动的船只,非常注重事实和用词的精准,为了确认新不伦瑞克十月是否还有花儿开放,她可以翻阅很多资料。对波特他的话最多,不仅因为他见过她,并且受过她的推崇,还因为这个南方女人也最有趣。她美丽,风情万种,光丈夫就有过四个,且不提那些跟她有过短暂风流韵事的情夫。一生不断发明新我,因而也小心翼翼地抹去旧我。加斯敏锐地指出波特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她想要公众看到的自我,补偿她真实自我的缺陷。她在生活中没有耐心等待理想的丈夫,但在写作中却十分从容,可以耐心等到那个能教会她某个写作技巧的阅读对象出现,选择最适合她的写作导师。作为南方作家,她不师从福克纳这样跟她秉性相近的大师,而是向跟她截然相反的国际型作家詹姆斯和伍尔夫这样的大师学艺。在生活上她被戴上出身低等、作风放荡这样的标签,但在写作上她是不容置疑的贵族,从容,优雅,完美无缺,从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是当之无愧的皇后。她用写作上的完美隐藏了生活上的不完美。
我非常喜爱加斯私印的内部书或由他任职的机构出版的这些小众读物。比方说他在国际作家中心任主任期间编写的《文本的庙宇:五十根文学支柱》,与中心副主任洛丽·谷柯(Lori Guoco)合编的《政治中的作家》《双重缪斯:作为艺术家的作家與作为作家的艺术家》和《文学圣路易斯指南》。最后一本书特别值得一提,它介绍了五十多位在圣路易斯出生或居住过的已故作家的生平和他们对圣路易斯的写作,这其中有马克·吐温、凯特·肖邦、玛丽安娜·穆尔、T. S.艾略特、田纳西·威廉斯、项美丽、托马斯·沃尔夫、约瑟夫·普利策(就是创立普利策奖的那位)、威廉·巴勒斯、史丹莱·埃尔金,都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头,尚不算没有编选入书的活着的作家,包括加斯本人。遗憾的是,现在加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圣路易斯,这座在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繁华熙攘的城市,衰败的痕迹现在处处可见:生锈的铁轨,废弃的桥梁,荒凉寂寞的密西西比河,大片大片被逃离的老旧居民区,曾经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古老建筑,现在任由老鼠、流浪猫狗和毒品贩子出没。加斯曾经说过,他跟埃尔金一样,憎恨圣路易斯却又终身沦陷于兹,如同一只想要跳离池塘的青蛙,无论怎么拼命往空中跳,最终仍然落回池塘。现在我似乎也要遭遇相同的命运。但把青蛙们拉回来的一定不止地心引力,还有密西西比的河水,有昔日的历史和繁华,有失落了的梦想和荣光,有荒原般的记忆—这样的感伤一定是加斯不乐意听到的,我最好打住。

加斯在课堂上
加斯在文中多次提到,大哲学家也好,大作家也好,都是某种独特意识的创造者,而加斯常常能深入到这种独特意识最核心的部位。他说爱默生的散文是互动的,可以打造一个能思考它们的大脑(Emerson?s essays build the mind that thinks them),可以让你发现自己身上的爱默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浪漫主义秉性的理性主义者,用脖子挂在绞架绳索上那样的绝望和专注来思考他的哲学问题;里尔克的哲学思想完全是无稽之谈,作为哲学概念它们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但作为诗歌概念它们绝对美丽。加斯在书写这些哲学家或作家时,从不孤立地谈论他们的思想,而是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生活的物质世界结合起来。他寻找的第一件事是引领他们走上思考与写作道路的弱点,他自身所蕴含的内在冲突以及跟外在环境的格格不入。对尼采而言,他的弱点是他的疾病和健康,他在思考的现代性和情感的传统性之间的挣扎。在《尼采:疾病与健康》一文中,加斯指出尼采在情感上有将一切偶像化的倾向,而在思想方法上他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研究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的批评方法。用世俗的方法来研究宗教的教义,偶像便不可避免地会被拉下神坛。在写作风格上,尼采用的是格言和夸张手法,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来限制他无限夸张和膨胀的思想与自我,如同用小拳头去握一个大气球。“尼采的慢性疾病,他那如水银般快捷和难以把握的思维,他嘲弄一切的态度,还有他内心的冲突,都把他放在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一种关于角度的角度。”这也就是超人的角度。尼采的秉性是浪漫主义的,期待他人变成跟他一样的超人。尼采最超人的一点就是他看别人跟看自己一样清楚。尼采憎恨撒谎,特别是自我欺骗的谎言。加斯指出尼采的很多思想和证据都来源于将自己作为一个心理观察对象,而休谟可能只这样观察过自己一次,然后便将目光投向他的先驱,从他们的短处里寻找证据。自然,加斯不会遗漏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尼采。他认为尼采不是一个主语和谓语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动词的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寻找规则的语法学家,而是一个对许多重大的形而上学原罪的句法产生怀疑的革命家和发明者。但人类给每个动词都分配了动机(理由)和责任,否则动词们会跟翻牌一样任性和无法预测。尼采最终没能逃脱疯狂的命运,余生受母亲和妹妹照顾。当他想要尖叫时,母亲便将切碎的苹果塞进他的嘴里。加斯说他更喜欢嘴里没有塞满碎苹果的尼采。

加斯在他的个人图书馆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我是在通过加斯的眼睛来看哲学和文学,哲学家和文学家,而对于加斯本人最看重的小说家身份,我却基本没有涉及。我得坦白,他的小说我也没有读完,倒不是因为读不下去,而是它们确实需要你拿出几个月甚至整年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阅读,这样的时间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奢侈。他说过他的写作通常始于某个形象,比方说蜘蛛;他关心的是写作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情节和意义;他热爱比喻如同某些人热爱垃圾食品;对他来说,句子不是建造房子的一块砖—它本身就是一栋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说过如果由他来谈自己的作品,他会写如何写句子。句子们有心理,有灵魂。一个理想的句子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词语自己选择住进去的。这一切的一切,又如何能在一篇小文里写尽呢?如果说加斯是大海,我只是撷取了大海里的几朵小浪花。《书城》编辑约稿时,我就表露过自己的惶恐,怕自己的笔不足以展现他的丰富和深刻。编辑说,就写你心目中的加斯好了。这句鼓励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就有了这么一篇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