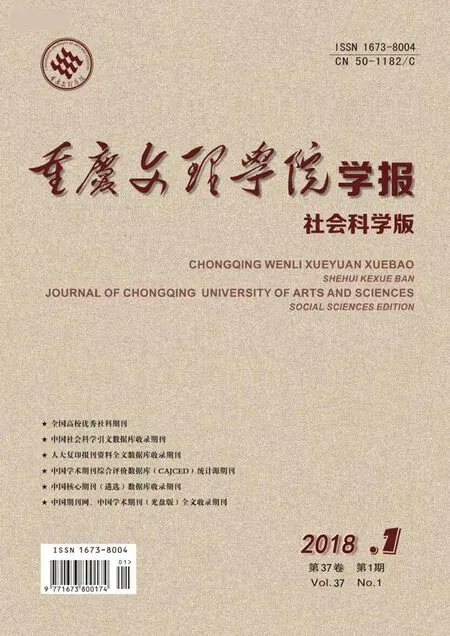麦尔维尔小说中边缘人形象魁魁格的形象隐喻
2018-03-28沈进宇
沈进宇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在目前国内关于《白鲸》的研究成果中全文涉及魁魁格形象的文章共有200篇,但是专门针对魁魁格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解读的只有杨丽的《再读梅尔维尔的〈白鲸〉——魁魁格人物形象解析》一篇文章[1],可见出魁魁格形象在前人的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因此这一人物形象还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杨丽在其文章中主要从种族平等的角度对麦尔维尔塑造的魁魁格形象给予了正面评价,使用的是较为传统的批评视角,对后学有一定的启发,但是没有完全发掘魁魁格形象内涵。后殖民主义研究者认为西方作家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会在创作中带有潜在的意识形态,而殖民者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叙事来作为文化侵略手段从而达到在潜移默化中为自己的殖民扩张进行正名和美化。因此,对于那些经典文学作品如今应该带着辩证的眼光去重读,把它们放在后殖民语境下进行解读,揭示文本中潜藏的表述和意识形态。关于《白鲸》中魁魁格这一人物形象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解析,就能挖掘出形象更加丰富的内涵。本文将从文本、文化和作者创作意图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为这一长期遭到忽视的人物形象正名,也为《白鲸》的研究视野拓展一个新的维度。
一、被嘲弄的文明朝圣者
魁魁格形象在文本中的出场是充满悬念的。大鲸客店的老板把他描述成一个提着人头到处兜售,只吃半生不熟牛排的野蛮生番,与其说是客店老板跟以实玛利开的玩笑,不如说是他对魁魁格的蔑视嘲弄。在这种描述的暗示下以实玛利对魁魁格展开了想象,对还未谋面的睡伴充满了戒心。这是一种典型的白人中心思维,对于非白人进行主观的想象判断从而带有一种原初的偏见。就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讲到的,西方世界把东方当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探索、描述和还原,所有这些再现会在力求客观的基础上展开,但是所有这些再现也都维持了西方世界的主观色彩,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知识,所有的所谓客观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因而在以实玛利和魁魁格没有真正接触之前,魁魁格的一切都是任由以实玛利想象的,在这种想象中他无疑扭曲了魁魁格的真实形象。
作者借以实玛利的口叙述了魁魁格的身世。魁魁格是罗科伏科人,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岛屿,是岛上国王的儿子,但一心想到文明世界长长见识。“在魁魁格雄心勃勃的灵魂深处已经潜伏着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到文明世界多见识见识。”[2]46可见魁魁格对文明的渴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偷偷离开岛屿攀上一条来自文明世界的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在船上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因为“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在激励他,就是学习文明人的技艺,好使他的人民生活得比现在更快活一些”[2]48。对于魁魁格来说文明世界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他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不顾一切地进入文明世界,抱着一颗朝圣者的心学习文明社会的一切。然而,这种淳朴的思想和行为在让以实玛利感动的同时也成为他嘲笑的对象。在文本的第四章以实玛利就站在一个真正文明人的角度对魁魁格穿鞋和洗漱的行为进行了点评,把他称为是“一种处于过渡期的生物”,“他的文明程度还只刚刚进化到以最奇特的方式来显示其蛮夷风尚的地步”[2]23。“在清晨这个时候,一个文明人是会洗脸的;可让我大为惊异的是,魁魁格只洗了洗胸脯、胳臂和双手就算完事。”[2]23到第五章早餐的过程中以实玛利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对魁魁格鄙夷的态度。“确实,他的教养我无法恭维。他带着标枪来进早餐,毫无顾忌地使用它。”[2]25这些表述都无不透露出一种鄙夷和嘲讽的情感。在以实玛利了解魁魁格以前,他眼中的魁魁格只是一个拥有黑里透出紫色的脸,紫色秃头,全身遍布文身的物种,甚至断定“他肯定是个什么可恶的野蛮人搭上了南海一艘捕鲸船,就这样来到了这个文明国家。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发抖”[2]18。以实玛利为什么要“浑身发抖”?就像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对非洲土著人进行描述时写道“他们嚎叫着……做着各种可怕的鬼脸。然而想到他们是人——与你一样也是人——想到你与这些野蛮而狂热地喧嚣着的人有着远亲关系,这才是真正让你心惊肉跳的,令人厌恶”[3]46。无论是以实玛利的“浑身发抖”还是马洛①的“心惊肉跳”,这样的表述无疑都充分表达了文明人对非文明人的嫌恶。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可怕的不是非洲人和野蛮人本身,而是这些生物和自己地位相等或者同自己有一定关联。在文明人具有优越感的思维中,自然而然把非洲人和野蛮人排除在外,视他们为劣等人种。而非洲人和野蛮人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观看,被书写,被表达。
作为未开化人的魁魁格没有选择,他不具有表述的权利,甚至不能为自己申辩。即使是后来以实玛利接受了这个生番朋友,但这也是在确定魁魁格善良无害后才有的行为。他表面上接纳魁魁格,但实际上处处与他保持着距离。他观察魁魁格的言行,在内心嘲笑他的滑稽。当魁魁格对他发出甘愿为他赴死的承诺时,他带着怀疑的心情接受;当魁魁格邀请他一起祷告时,他寻找借口拒绝。他认为魁魁格虽然拥有高贵的血统,但未接受良好的教育所养成的生番习性把他给损坏了。而作为魁魁格本人,从以实玛利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自卑。当他得知以实玛利还要和他同睡时“他听了似乎很高兴,也许还有点儿引以为荣”[2]42。为什么要“引以为荣”?是否魁魁格自己也认为野蛮人的身份低于文明的白人,所以他才为自己交了一个文明人朋友而感到荣耀?这其实只是作为叙述者的以实玛利的主观判断。相反,从中透露出潜伏在作者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即白人优越论。在第十三章中,这种白人优越感表现得更为明显。魁魁格和以实玛利一同推着独轮车在街上行走,引来众人侧目。人们对野蛮人并不好奇,好奇的是一个野蛮人竟然和白人关系亲密,“好像白人总得比白化了的黑人高出一头似的”[2]51。他们一同上船时,船长对魁魁格的粗暴态度更是体现出白人对非文明人的蔑视。
“魁魁格只身来到了基督教所代表的文明世界。他本来相信能够在基督教世界里学到足够的东西回去‘启蒙他愚昧的同胞’。”[4]97事实上,魁魁格努力学习文明知识努力融入文明社会并没有真正获得他人的认同,反而是受到嘲弄和一如既往的轻蔑。以实玛利对魁魁格的态度也正如《黑暗的心》中马洛对那个烧锅炉的非洲土著人一样,“尽管那个部分西化的舵手对马洛很有用处,他还是被人以模仿来嘲弄”[5]223。“看到他就像看到一只狗在拙劣地模仿人……他本应该在岸上拍手跺脚,而现在他脑子里塞满了令人进步的知识,在辛辛苦苦地干活,仿佛被一种奇怪的魔力所奴役。”[3]47作为西方文明人,一方面他们指责非文明人的野蛮,要求他们通过对西方的摹仿来“自新”,但是另一方面又恰恰经常以学样来嘲弄或嘲笑野蛮者所具备的不同之处。
二、文化身份无所归依者
魁魁格一心向往文明世界,但是却始终不为文明世界接受。是什么让他认为文明的就是好的?这背后所隐藏的正是美国殖民者留下的文化后遗症。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极力主张他的读者将文学作为一种存在于其他文化现象中的文化现象来研究。”[6]89因此,对于文学文本的探讨无法规避其文化根源的考察。“法侬从心理学的角度,在较深层次上探讨了文化后遗症在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问题中的体现。”[7]35他一次次地证明了殖民主义不光影响社会,而且还影响到个人,从而揭示了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白鲸》中的魁魁格正是遭受了这种文化后遗症的影响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他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而萌生了学习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但当他真正进入所谓的文明世界时,看到的却是残忍的杀戮、贪得无厌的掠夺以及虚伪的人情。“可怜的魁魁格怅然若失。他心想,这个邪恶的世界没有一处是干净的,我还是一辈子做一个异教徒吧。”[2]48然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异教徒!“他担心的是,文明的影响……已经使他不适合于登上那在他之前已经有30位异教徒国王登上过的圣洁的宝座。”[2]48虽然魁魁格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但是他却生活在文明人中间,学文明人穿衣服,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礼仪。这样努力的结果使他显得不伦不类。如果他没有稍稍被文明化,他就不会觉得当着别人的面穿鞋是不礼貌的;如果他已经学会文明社会的一套,他就不会为了遮羞而躲到床底下去穿鞋,床下穿鞋的举动恰恰暴露了他的野蛮习性。可以说魁魁格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身份地位之中,既无法融身于文明社会中作一个真正的文明人,也无法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度作一个纯粹的野蛮人。这种身份上的无所归依是殖民者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主要文化后遗症之一。“事实上,殖民主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化目的不是对殖民地进行彻底的白人化……而仅仅是在控制的欲望驱使下力图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7]68
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字意蕴丰富,时间上来说表示殖民主义结束之后产生的替代性思潮,空间上来说主要是指从早期宗主国相对的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思想潮流,还有一层含义是指殖民主义所留下来的在文化层面的后遗症,以及由文化后遗症带来的政治、经济后遗症。关于文化上的后遗症问题,斯皮瓦克提出了“认知暴力”的概念,“在斯皮瓦克看来,认知暴力之影响深远,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政治受到控制、经济产生依赖及在文化身份上难以表述的后殖民状况的重要因素”[7]100。但是这种“认知暴力”并不是单向发生作用的硬暴力,而是一种双向作用的软暴力,它以先进的文明自居,打着为蛮荒之地带去光明的旗号向第三世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学校、教会等方式的教育去取得殖民地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白鲸》中的魁魁格正是这种软暴力下的牺牲品。
文化身份上的无所归依使魁魁格沦为文明世界的“属下”者。“属下”这一概念是从葛兰西那里借用来的,但是斯皮瓦克在运用时赋予了这一术语新的内涵。所谓“属下”,也就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权力,在文化上具有顺从性和依附性,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组织无主体性的群体。失语、沉默是“属下”者的特点之一。在《白鲸》中,魁魁格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即使有自己的语言也被描述成“奇怪的咕哝声”,或者是不标准的文明语言,类似于“你的究竟是谁”[2]19“我懂得很”[2]20这种蹩脚语法表达。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曾指出“没有什么比一个黑人正确表达自己更引起轰动的了,因为他真正地安于白人世界了”[8]23。也就是说,当一个黑人能够说一口正确的法语或者英语表达自己时,那就表明他已经真正融入白人世界,成为完全的白化人。然而,魁魁格并没有成功跻身文明世界取得自身的话语权,而更多的则是以实玛利的代替表述,也就是直接取消了魁魁格的话语权,因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
言语上的无法自主源自文化霸权的压迫。自魁魁格进入文明世界起,就已经遭遇了文化霸权。不论是表面上尊重魁魁格的以实玛利还是本质上蔑视魁魁格的其他人都企图对魁魁格进行文化改造,想用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去同质化这个食人生番。这种最显著的冲突体现在宗教文化上。魁魁格作为一个异教徒需要每年在特定的日子进行斋戒,对此以实玛利虽然口头上说“我对别人的宗教义务,不管它有多可笑,我都非常尊重”[2]69。但事实上他却忍不住要以文明人的科学知识去改化魁魁格的宗教习惯。他从原始宗教的兴起和发展讲到现代各种宗教,再到身体循环规律等知识,对魁魁格进行洗脑,可谓苦口婆心。这样煞费苦心的劝说和引导表面上看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实则隐藏着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即以一种文化去压制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意图。以实玛利口口声声说尊重魁魁格的信仰,但是内心里却是希望将他同化,使他彻底变成一个“黑皮肤的白人”。不仅如此,沦为“属下”者的魁魁格在文明世界中只能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受到无尽的压榨。魁魁格在“裴廓德号”上是大副斯达巴克的标枪手,所谓标枪手就是听从指挥对大鲸进行直接攻击的人,从事的是超一线的危险工作。但身为标枪手的魁魁格工作内容并不只是在高度危险中对大鲸进行攻击,他还需要完成许多其他体力活儿,比如在阴暗的底舱里搬动笨重的油桶、在完成捕鲸之后不得休息马上投入到鲸尸的分割工作中等。和魁魁格一样受到压榨的还有印第安人塔希蒂格、黑人达格,他们分别是二副斯塔布和三副弗拉斯格的标枪手。作者特别指出,达格是一个强壮的大块头黑人,但是他却不得不听从于弗拉斯格这样一个白人小个子。不难发现,在“裴阔德号”这艘捕鲸船上,从事最危险工作的都是非白人,而白人都处于支配地位,传达出一种黑人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愚蠢生物,即使有高大的外形也不得不受制于矮小的白人的白人优越感。
身份上无所归依,没有话语权力,遭受文化霸权,受到残酷压榨,这都是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对于殖民地的很多人来说,殖民历史最初的尖锐痛苦,后来竟慢慢变成了‘享受’”[7]95?为什么《白鲸》中的魁魁格、塔希蒂格、黑人达格等,他们不仅甘愿从事最危险的工作、甘愿被奴役,然而还要感谢白人们慷慨给他们一份工作?正如斯皮瓦克认为“话语权也好,文化霸权也好,其复杂性都不在于其暴力之‘暴’,而在于其暴力之‘软’”[7]98。这正是后殖民主义带来的文化后遗症,它以一种无形、温和的方式进行“文化殖民”,并且没有遭到反抗和抵制。
三、帮助白人建构自我的他者
法侬认为:被殖民者具有“被殖民”与“主体”的双重身份,是一个永远无法给自己的角色正确定位的“他者”。然而,“身份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维系、巩固帝国主义者对自我身份的界定”[9]286。因此,“裴廓德号”上人种和信仰的多元化看似是得益于美国文化的包容性,但在这种包容性中掩藏的是以“他者”来完成自我建构的意图。对于以实玛利来说,渴望出海是因为希望到海外世界进行冒险,他对海外岛屿充满好奇。这样的好奇不仅是为了冒险也是为了自我证明。当一个社会自身发展达到高度成熟并且拥有巨大的力量时,它就会走向殖民,对外冒险,入侵未开垦的处女地,征服未开化的人群都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在魁魁格与以实玛利的相处中,以实玛利随时无不都在表现自己的文化优越性。他嘲笑魁魁格的不伦不类,企图改化他的宗教信仰,通过和魁魁格的差异对比来突显自身的先进性。从一开始对魁魁格充满戒心,到后来慢慢成为朋友,以实玛利的态度虽然有所转变,但他始终没有像看待其他白人朋友一样看魁魁格,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把魁魁格称为“野蛮人”,对于以实玛利来说魁魁格始终是一个用以自我参照的“他者”。但是魁魁格的善良淳朴也确实打动了以实玛利,他用野蛮人的纯真天性帮助以实玛利完善了自身人格,并且最终全靠魁魁格的棺材救生圈使他死里逃生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因为魁魁格的存在,以实玛利实现了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自我重生。
仅从文本的层面来说,魁魁格帮助以实玛利完成了自我建构。那么从作者的创作层面来看,麦尔维尔在作品中塑造魁魁格以及塔希蒂格、达格、皮普、费达拉等非白人的意图是什么呢?“文学时常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在海外的扩张,因而制造出了威廉姆斯所说的‘感觉结构’。这个‘感觉结构’支持、表现和巩固了帝国实践。”[10]16换言之,西方作家会因受帝国意识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意识地透露出一种潜在的态度与指涉,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表述起到了为殖民扩张美化正名的作用。“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建构和书写着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权威,并掩盖和美化对外侵略的暴行和罪恶,以达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殖民地人民的控制,为自身的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11]3“各种叙事体的作品,不管是虚构的、抑或政治的、经济的都是靠压制、使边缘化、争得机遇、观点以及资料来建构自己。”[12]222《白鲸》中的魁魁格以及塔希蒂格、达格、皮普、费达拉等人物,在作者笔下被表述为和白人一起并肩捕鲸,吃苦耐劳,甘愿牺牲自我的形象。但是这种表述却隐藏了白人对非白人殖民压榨的真实情况。“麦尔维尔是那种极少数的人之一,他拥有敏感的灵魂,能够穿透表面的真实看到这个世界真正运作的样子。”[13]10真实的情况是:“殖民者创造出一种文化‘幻影’,而这种幻影是殖民者赖以巩固自身存在价值的‘另类’——以黑色来印证白色,以东方来印证西方”[14]38,也就是说殖民者在文化上把殖民地人客体化了,并以“他者”来建构自我。斯皮瓦克指出“第一世界把第三世界作为他者的这种仁慈的利用和重新刻写,是今天美国人文科学中大多数第三世界主义的基本特点”[15]128。正如麦尔维尔的研究者杨金才教授所说:“麦尔维尔笔下的异域和19世纪那些操持‘开发异域、拯救外族’信条的作家笔下的异域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想象结构。正是这种想象异域的塑造才使得当时殖民主义者的自我认同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巩固。”[16]68也就是说文学文本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了帝国政策叙事的连续性,并起到了巩固帝国地位的作用。因而,帮助白人世界进行自我建构、自我认同正是诸如魁魁格这样的人物所具有的潜在内涵。
艾勒克·博埃默在其著作《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指出“书写也是一种统治工具,它是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手段”[17]13。欧洲人在开始殖民迁移时就已经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已知的修辞表述来对多种多样的观念形态做出描述。如此一来,殖民文学就呈现出两种形态,即“想象的”文学和“象征的”文学。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就介绍到英国和法国的霸权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比如狄更斯和福楼拜作品中的文化象征层面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而“美国在文化领域中的合法性阐释和文化优越性展示、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范围都是此前的帝国主义所不能比的”[7]69。《白鲸》创作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正在大肆进行海外扩张。对这部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殖民隐喻,而这种殖民隐喻并不是作者有意设计的,恰是潜藏在作者文化认同中的无意识。“对于美国对外扩张特别是文化扩张的负面影响的关注,对于被扭曲表现的东方的态度,以及对东西方关系的探寻。麦尔维尔是最早把这方面关注转化为文本的美国作家之一。”[18]7
作为一个具有前瞻思想的作家,麦尔维尔并不赞同美国人的殖民扩张,甚至在作品中对这样的肆虐行为有所批判,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站在殖民主义的对立面并与之决裂,而是保留了一种暧昧态度。所以在《白鲸》这部作品中,他把白鲸塑造得既无辜又恐怖;把亚哈塑造得既残忍又可敬;把以实玛利塑造得既真诚又虚伪;把魁魁格塑造得既友善又野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双重性的书写,是因为“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麦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16]69。这是他无法超越的文化局限。在麦尔维尔早期的作品“波里尼西亚三部曲”中殖民思想更加显著,到了《白鲸》对魁魁格的塑造时已经带有了一种辩证的意识,不过也难免流露出一种隐约的帝国优越感。“在麦尔维尔笔下,边缘地域都是蛮荒的、蒙昧的,他们的文明史应该从美国意识形态介入的那一刻开始书写。”[19]68所以他笔下的魁魁格也只是为帝国意识服务的配角。
四、结语
以往的《白鲸》研究总是忽略其中的非白人形象,或者把这些次要人物形象视作是麦尔维尔宣扬民主思想、种族平等的正面书写。然而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魁魁格这一形象起到了调和文本中帝国意识和殖民后遗症的作用,具有诸多潜藏的内涵。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在通常认为与帝国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早期叙事与后来十分明显的帝国叙事之间有一种有机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不是通过外力,而是通过每一种媒介或历史语境而逐渐形成的。他强调,这些结构性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必须从小说的具体分析中得出”[7]63,所以,把经典文本放置在后殖民语境中进行解读,具体分析其中隐藏的内涵和意蕴,揭露文本中歪曲的、边缘化的表述,才能够清晰地把握帝国叙事的潜在线索,使霸权式的阅读关系变得透明。
注释:
①马洛: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叙述者、主人公。
[1]杨丽.再读梅尔维尔的《白鲸》——魁魁格人物形象解析[J].名作欣赏,2011(9):77-81.
[2]麦尔维尔.白鲸[M].罗山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康拉德.黑暗的心[M].孙礼中,季忠民,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4]朱喜奎.小说《白鲸》中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J].名作欣赏,2013(21):96-98,108.
[5]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M].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YANG JC.Projections of Moby-Dick“After Theory”in the United States[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09(1):88-94.
[7]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9]ZHU 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1]马慧珍.后殖民理论语境下的文本解读[D].兰州:兰州大学,2013.
[12]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M].杨乃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HAYESK J.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Herman Melvill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14]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5]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6]杨金才.异域想象与帝国主义——论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波里尼西亚三部曲”[J].国外文学,2000(3):67-72.
[17]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67.
[18]周新.麦尔维尔小说中的后殖民主义[D].黑龙江:哈尔滨,2005.
[19]王彦兴.《白鲸》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视野[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6):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