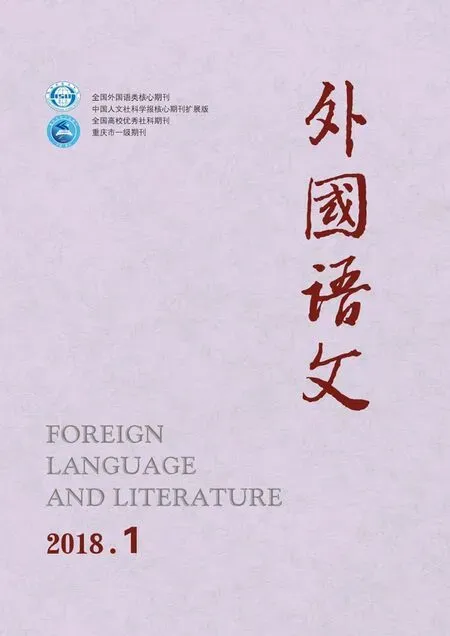东方乌托邦
——欧洲中世纪旅行文学中的北京形象
2018-03-07田俊武陈玉华
田俊武 陈玉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0 引言
“旅行与旅行叙事不仅表现出空间的移动及其地理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内在精神生活的深入过程,因为旅行与旅行叙事在探索世界的同时也在探索自我,旅行本身就是一种隐喻。”(Robertson,1994: 2)作为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一种文学范式,旅行文学不仅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的地理景观、风俗人情和社会生活,更将触角深入到遥远的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帝都北京。以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曼德维尔为代表的中世纪欧洲旅行家,都在自己的旅行作品中将最好的赞誉给予北京。他们看似在描写汗八里的繁华景致,实则表达的是欧洲人自己的内心渴望。“异域形象是本土社会文化无意识的象征,它可以将特定时代本民族精神与现实中一些刚刚萌芽的隐秘期望或忧虑的、尚未定型或成形的因素,转喻到关于异域的想象中去……中世纪晚期西方在自身文化视野内塑造中国形象,中国形象表达了他们的缺憾与期望,是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评价,也是他们试图超越既定历史现实的乌托邦。”(周宁,2006: 33-34)不论是“汗八里”、大都或是北京,他们只是一个浓缩了中世纪晚期西方集体欲望的名词,北京的形象就是在这几个世纪的旅行文学作品中逐渐沉淀,固化,最终升华成为西人眼中的东方乌托邦的。
1 西方旅行文学与比较文学形象学
旅行文学也叫游记文学,它“记录了作者从此地到完全不同的彼地的旅程见闻,不论其是正式的或是基于内容的创作,都能对不同时代的有着不同兴趣和背景的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力”(Brown, 2010:viii)。旅行文学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学范式,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的。西方学者坎托曾经这样描述旅行文学在中世纪欧洲产生的背景:“商人们长途跋涉,从欧洲和地中海的边缘地带运回货物;朝圣者去远方朝拜,传教士寻求异邦的归化……骑士到遥远的国度充当雇佣兵;农民为了经济利益,也拖家带口地向边陲迁徙,商人们甚至游历到西欧之外,寻找新的商品和市场,使得拥有最诱人的丝绸、香料和珠宝的东亚,成为这种商业性远游的目标。而当商人们到达东亚以后,中产阶级的好奇心又超越了商机,刺激出学习异域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努力。”(Cantor, 1994:79)欧洲中世纪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对异域世界尤其是遥远的东方充满了认知的遐想,这些遐想通过旅行家、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的旅行得以证实或证伪,他们的旅行书写成为欧洲人认识外部世界的绝佳材料。
苏珊·巴斯内特指出:“从旅行家对其旅行的记录中,我们能够追溯文化刻板印象的存在,个人对异域做出的反应实际上折射出了旅行者自己所属文化的倾向。”(Bassnet,1993:93)也就是说,旅行文学,尤其是一国作家所写的关于另一国见闻的文学,最能体现两种文化的比较。因此,旅行文学自然地与比较文学形象学结合起来,让-玛丽·卡雷将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Guyard,1951:6)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更进一步确定了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定义,那就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这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非文学的,且能说符指关系的表述”(Pageaux, 1994:60)。在比较文学形象学家看来,以游记为代表的旅行文学是向那些尚未踏足异国的人们展示异国形象的绝佳材料,这种文学范式无形之中将本土形象与异域形象进行比较。正如克里斯托弗·凯文·布朗所言,“大多数旅行家的故事中都有一条关于(异国)显著不同点的共同主线:他们将熟悉的祖国的概念作为画布来描绘外国的形象”(Brown,2000:x)。
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60多年的定都史,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数目最多的城市之一。虽然早在马可·波罗之前便有传教士柏朗嘉宾和外交使节卢布鲁克来过中国,“但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对东方城市的描述,因为他们所见到的草原帝国首都不过是一片大帐篷。见过罗马、威尼斯和巴黎的欧洲人不会对此有兴趣。只有等欧洲人来到汗八里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的城市视野太狭隘了”(吕超,2008: 8)。这里所说的“汗八里”,就是元朝时期北京的称呼。作为“沟通东西交流的第一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详细记叙了忽必烈统治下的汗八里形象。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传播激发了更多的欧洲人踏上了探索神秘东方的旅程。在本文所选择的三部不同时期的游记作品中,虽然作者的身份各有不同,游记内容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论他们的作品是写实还是虚构,他们笔下的北京形象都展现了当时欧洲大众的主观意识形态。
2 《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汗八里: “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帝王之城”
1299年,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出版,北京第一次以“汗八里”的名称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意为“大汗之城”或“帝王之城”。对于从未到过东方的欧洲人来说,马可·波罗书中的这个东方城市既遥远又神秘,那金碧辉煌的“大汗城”、贸易繁盛的经商地、开明圣贤的忽必烈大汗等,无不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显得新奇和不可思议。《行纪》发行之后流传甚广,但是质疑的声浪也很高。据说在马可·波罗临终前还曾被亲朋好友劝说收回谎言,但波罗却回道:“我书中描述的还不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可见在当时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相信波罗书中所言。约翰·拉纳指出:“真正难以让读者相信的就是(此书)揭示了一个有着乡镇和城市的崭新世界。”(Larner,108)这种崭新的世界与当时欧洲诸城的形象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无法从自身的认知来理解这样一个存在。《行纪》全书共计515章,描述汗八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83章《大汉之宫廷》到104章《契丹州之开始及桑干河石桥》。《行纪》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汗八里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貌,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的民俗风情。当时的中国正值鼎盛时期,忽必烈治下的蒙古铁骑威震欧洲,这个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对外形象最完美的时期。然而当时的欧洲正值中世纪晚期,十字军东征的硝烟未散,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有了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对比,便可明白缘何在波罗笔下不论是契丹的“汗八里”还是蛮子省的行在(京师),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地方”(周宁,2004: 18)。
巴柔认为:“异国形象也可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注视者’文化)有时很难设想、解释、承认的东西。异国形象可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换到隐喻层面上去,这些尚未被明确确定,因为它可属于某些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范畴。”(2001:123)所以波罗笔下的汉八里不仅仅是座东方城市,它也是波罗对自己美好愿想的一种投射。波罗对汗八里城市布局、皇室宫廷、政体制度、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社会生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字里行间满是溢美之词。“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二十四里,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里。”(波罗,2001:210)这便是1264至1267年间,忽必烈汗于燕京旧城东北面所建的新城。自1271年开始,汉人称此城为大都,蒙古人则称之为“汗八里”。马可·波罗的这段描述便是对这座新城的宏观印象,不论其描述的面积是否失实,“汗八里”这座新城之宏大依然震撼了这个来自欧洲名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时代的汉八里总体上呈“方形”、以“棋盘”状划分整个城市。波罗对汗八里城市布局的细致刻画很大程度上源自东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形态的差异。“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儒家思想强调重礼,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 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张洛锋,等,2005:78) “汗八里”的城市布局完全体现了儒家礼教思想侵染下的中国城市风格,规则的城市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无处不在的皇权意识。反观西方,他们普遍受神权思想影响,上帝在他们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教堂、庙宇在城市处于中心位置。他们认为:“西方中世纪城市建设的主线多为有机生长,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 建筑群具有优美的连续感、丰富感和活泼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城市景观统一且多样化。”(张洛锋,等,2005: 79)中世纪建筑的这种灵动、环绕与波罗所见之“汗八里”的规矩、工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也是为何马可·波罗反复提及新城的规则布局,因为汗八里的风格与波罗所在威尼斯相距甚远。除城市布局之外,马可·波罗(2001:170)用大量篇幅刻画了汗八里的宫廷:“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忽必烈汗的宫殿不仅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而且宫墙、房壁以及屋顶的天花板还是金银的。这不仅仅是对忽必烈汗治下的元朝财富和物质的简单表述,更多的是在反应中世纪晚期西方人在禁欲思想遏制下对物质财富生出的无限渴望。马可·波罗(2001:170)不仅把汗八里宫廷形象物质化,而且还进行了夸大:“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此者。”马可·波罗的夸张性描述,尽管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是仍然符合旅行文学的叙事特征。正如布朗所言,“我们还必须记住,旅行文学绝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文本始终是一种感知的表现,因此,它有一个显著的主观性元素包含在内”(Brown,2000: vii)。
由于波罗(2001:199-200)本身就是商人出身,汗八里繁盛的经济贸易自然便是其重点着墨的对象:“郭中所居者,有各地往来商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每一附郭或街道有华厦甚众,各地往来之商人居焉,每国之人各有专邸。”汗八里的这种商贾形象,基本上是当时北京的写照。当时的北京是北方重镇,金、辽两朝曾经移都于此,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汇集之地。繁荣的经济必然带动着各族之间频繁的互动和交流,使得文化融合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忽必烈定都大都后,随着大规模的新城建设,人口相应增加, 商业贸易亦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各国商贾,往来频繁,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新城的房屋住宅兴建。整个汗八里便以“贸易发达户口繁盛”之景呈现在马可·波罗(2001:199)眼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波罗所运用的数字描述极具夸张性,开启西方人描写帝都北京繁华之先河。“从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对帝都北京的记述便充斥着夸张的数字,这既是旅行者随意猜想的结果,也体现着当时西方人的艳羡想象。”(吕超,2008: 13)马可·波罗的夸张是为了达到震撼欧洲的目的。当时的欧洲处于封建分裂的状态,长期的内战和混乱导致欧洲经济凋敝,贸易衰微,而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汗八里则是波罗期待在欧洲看到的面貌。另一点体现汗八里商贸繁荣的便是纸币通行全国。“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幅最小之纸币值秃儿城之钱(denier tournois)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gros vénitien)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波罗,2001:201)贸易的频繁往来要求更为简洁有效的货币模式,而货币兑换又反过来继续推动贸易的发展,这些纸币可与当时西方的货币进行兑换,足见当时贸易得繁荣程度。欧阳哲生(2016:109)指出:“《行记》对纸币制造和兑换的记载之细较中文文献更甚,表现了马可波罗作为商人的特殊敏感一面。”
除了对称工整的城市布局和繁盛的贸易以外,政治制度和开明的君主也引起了波罗(2001:244-245)的注意:“大汗所选任强大男爵十二人,决定关于军事之一切问题,如遣调驻所,更迭主将,抑调动军队于认为必要之地,征发战时所需之军额等事是已……此十二男爵所组织之高等议会,名称曰台(thai)。此言最高院所,缘其上除大汗外,别无他官管辖也……除上述之男爵外,别有十二男爵执司指挥三十四区域之一切政务……此高等会议组织之所,名称曰省(singh)。此言第二最高院所,盖其亦直隶大汗,不受他官管辖也。”马可·波罗描述的“省”“台”对应的是元朝的枢密院和中书省,前者专掌军务,后者司职政务。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以来,便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巩固在全国的统治,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 000多年。忽必烈汗治下的汗八里同样延续了这种中央集权制。枢密院和中书省虽然享有军事和政务方面极大的权利,但是最终都得听从大汗的安排。这种自上而下的政体制度,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一个作家笔下的对象,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在场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表现。”(孟华,2001: 9)汗八里的这一政治制度对波罗来说极具吸引力,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封建割据、战事频繁的年代,没有一个国王能像忽必烈汗那样来一统各国,也无法实行类似汗八里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开明君主的忽必烈,自然是波罗重点表现的对象。忽必烈不仅在军事上强势,而且也关心民生。在粮食歉收、牲畜频亡以及物价腾贵时,忽必烈能够散麦赈恤灾民。“大汗在此城中,选择贫户,养之邸舍之中,每邸舍六户、八户、十户不等,由是所养贫民甚众每年赈给每户麦粮,俾其能供全年之食,年年如此。此外凡欲逐日至宫廷领取散施者,每人得大热面包一块,从无被拒者。盖君主命令如是散给,由是每日领取赈物之人,数逾三万。是盖君主爱惜其贫民之大惠,所以人爱戴之,崇拜如上帝。”(波罗,2001:217)
作为基督徒,波罗(2001:161)在游记中也不忘谈及汗八里的宗教信仰:“大汗届时召大都之一切基督徒来前,并欲彼等携四种福音之《圣经》俱来……然大汗有时露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实最良之教之意。盖彼曾云,凡非完善之事,此教决不令人为之。”在忽必烈汗统治时期,不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社会各界对各种宗教都秉持包容的态度,当时主要的宗教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但是忽必烈本人却并不信仰任何一种。可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字里行间,忽必烈汗显然是倾向于信仰基督教的,这样的东方君主更容易受到西方人的尊敬和热爱。来自强大东方帝国的君主也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君主无疑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是他们集体想象的集中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游记》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周宁,2005:101)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间,北京继续以“汗八里”、大都或直接以北京的名字出现在各类游记和传教士们的作品里,虽然名称和时代在变化,但是北京所承载的意义变化却很小。“汗八里”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就是当时的西方所向往的乌托邦:城市宏伟壮丽,街道笔直,往来贸易繁荣,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君王骁勇睿智,人民富裕安康。“汗八里”这个词俨然成了形象学中所说的套话,即“在一个社会和一个被简化了的文化表述之间建立起一致性关系的东西:次要部分、表语被提高到了本质的部位,这就要求社会-文化要尽可能广泛地取得一致”(巴柔,2001:160)。这个套话浓缩了中世纪的西方人对东方的集体遐想,在中世纪后期的作品中继续传播。正如周宁(2004: 20)所说:“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是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
3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汗八里:西方视野中的东方“上帝之城”
继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方济会士鄂多立克于1322年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了三年,回国之后口述了《鄂多立克东游录》。迪鲁·努卡(Luca,2013:4)认为:“为了保持中世纪游记所谓的共同约定,旅行家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异国的)城市,关注的就是城市规模、食物、男人和女人或各式各样的商品。”鄂多立克便是循着前人马可·波罗的模式在书写自己在汗八里的旅行足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鄂多立克的 《东游录》证实并补充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甚至增添了传奇的色彩。在他的眼中,汗八里“是座高贵的城市,有十二门,两门之间的距离是两英里……大汗在此有他的驻地,并有一座大宫殿,大宫墙内,堆起一座小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总之,宫廷确实雄伟,世上最井井有条者”(鄂多立克,1981:72-75)。作为西方的一名方济会士,鄂多立克早先过着清苦的生活,终年打赤脚,穿褐衣,以面包和白水度日,立志做一位苦行修士的旅行家,世俗的繁华似乎与他无缘。但是来到中国后,鄂多立克还是为汗八里这座高贵的城市所震撼,以至于他对这座东方帝都的热爱之情随处可见。在描述汗八里的宫殿和宫墙上的红色皮革时,鄂多立克分别用了“全世界之最美者”“最井井有条者”和“世上最佳者”来表示。他数次用“最”来形容这座东方城池和其中的宫殿,似乎此处就是凡人无法想见的世俗天堂。此外,这位方济会士还多次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呈现汗八里的繁华,例如在谈到宫殿、筵席时,鄂多立克(1981:73-75)写道: “宫中央有一大瓮,两英尺多高,纯用一种叫作密尔答哈(Merdacas)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致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已婚者头上戴着状似人腿的东西,整个腿缀有大珠;因此全世界有精美大珠,那准能在那些妇女的头饰上找到……当大王想设筵席的时候,他要一万四千名头戴冠冕的诸王在酒席上伺候他。他们每人身披一件外套,仅上面的珍珠就值一万五千弗洛林。”
鄂多立克对汗八里的宫廷和筵席的夸张形容展现的不仅是自身对这座城市的狂热喜爱,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世纪欧洲人内心对世俗繁华和物质财富的极度渴望。巴柔(2011:121)指出:“异国形象应被视作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支配他者的基本态度分为四种,第一种态度便是“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此种情况体现的就是作家或集团表现出一种‘狂热’,他们对异国的描述更多地隶属于一种‘幻象’而非形象”(巴柔,2001:141)。不论是马可·波罗还是鄂多立克,他们的夸张描述反映的都是他们内心对强盛帝国和繁华世俗的渴望,所以他们专注对绵长的城墙、笔直的街道、宏大的宫殿、大汗的宫廷的刻画等便也不难理解。正如穆尔(1984:221)所言:“从鄂多立克对汗八里的描述不难体会浓重的世俗情怀,这和理应恪守方济会托钵僧艰苦生活的修士风格明显相悖。基督教修士偏偏愿作俗人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东方帝都文化对西方人强大的影响和同化作用。”对比马可·波罗的叙述,鄂多立克对汗八里的描述篇幅稍短,大部分都是在证实马可·波罗时期的宫廷布局、皇室盛宴、可汗出巡的仪仗、大汗狩猎的情形以及大汗所保留的节日等。但是在马可·波罗的基础之上,鄂多立克(1984:74)似乎增加了对汗八里奇闻轶事的描写,例如:“宫殿中尚有很多金孔雀。当鞑靼人想使他们的君主高兴,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拍手;孔雀随之振翅,状若舞蹈。那么这必定系由魔法驱动,或在底下有机关。”于是,鄂多立克笔下的汗八里除了在世俗繁华之外增添了一抹奇异传奇的色彩。“当鄂多立克以这种传奇的方式叙述大都时,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也许便是他的潜意识北京,同样地虚无缥缈而又令人心驰神往。”(吕超,2008:20)总之,《鄂多立克东游录》的问世,即是对《马可波罗行纪》真实性的一种强有力肯定,又拓展了《行纪》中对汗八里的描绘,将奇异色彩赋予这座东方帝都,并将这种形象传播至欧洲,激起更多西方人的探索欲望。
4 《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汗八里: 一座虚构的“黄金之城”
14世纪的欧洲除了鄂多立克外,还有一位作家也“到过”大汗之城,他就是约翰·曼德维尔。“尽管曼德维尔被珀切斯誉为继马可·波罗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但他充其量是个乘上想象的翅膀、身在座椅上的旅行家。”(葛桂录,2010:4)这番评价可以看作是对曼德维尔及其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以下称《游记》)最好的注解。与同时代的鄂多立克不同,曼德维尔本身就是一位作家,但是从未游历过东方。他是在阅读前人旅行著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享誉欧洲的《游记》。“据统计,现存的《游记》版本,手稿有300余种之多,与《马可·波罗》的77种版本,《鄂多立克东游录》的76种相比,曼德维尔的《游记》称得上是中世纪最流行的非宗教类作品。”(葛桂录,2010:13)一部虚构的作品何以有如此的魅力?艾尔米·席维格(Scheiger,2007:127)认为:“刊印于1480年的《曼德维尔游记》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他对于一个远离海洋边缘的具有异国情调和童话色彩的国家的描述,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旅行或经历之上,而是在图书馆里广泛阅读的结果。那是纯粹虚构的东西。描述的东西地理位置相距越远,愈能显出神奇与美妙的效果。”也就是说纪实的作品即便真实可信也未必能俘获读者,但是像《游记》这样虚构的作品却能在欧洲畅销,这完全得益于其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帝都的一种预期。
《游记》关于中国的叙述大多取材于《鄂多立克游记》,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的差异。首先是在人称叙述上,曼德维尔采用第三人称,而鄂多立克常用第一人称叙述。曼德维尔的第三人称拉开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让自己的描述表面上显得客观公正。但是曼德维尔(2010:84-85)对“大都”的描述较之鄂多立克更为夸张,他用了更多的黄金和珍宝润饰着前人对大汗富丽堂皇的宫殿的记述:“宫殿的大厅有24根金柱,墙上有挂满名豹的红色毛皮……宫殿的中央有一个专门为大汗所设的大瓮,全是由金子、珍石和珍珠制成。在这个大瓮的四角各有一条大龙,大匹网状丝绸、黄金和大珍珠装饰其上。”此外,对大汗宝座和宗室夫人的发饰描述也是如此。“这个宝座由碧玉做成,在宝座边缘镶嵌了珍石和黄金……所有已婚者头上戴着一个像男人的脚一样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大概长一腕尺,由又大又圆的珍珠制成。”总的来说,曼德维尔笔下的汗八里依旧延续着前人一贯的描述,着眼点仍然落在宫殿、城墙、宫廷筵席、各种金镶玉制的器具。在这位作家的想象中,东方帝都似乎遍地都是珠宝,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黄金城”。与鄂多立克的另外一个差异就是, 曼德维尔将基督教文化传统与大汗的来历用神话故事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旧约中上帝的一场洪水要将所有的人和飞禽走兽都除灭,唯有挪亚一家蒙恩得以存活。曼德维尔(2010:87)就大胆地将亚洲与挪亚的儿子含联系在了一起。“含是三人里的反面角色,但他依然是最伟大、最强大的,并且正是由于他的残暴而得到最好的领土——在东方,被称为亚洲的地方……含的后代分成七支部族,在这七个部族中,最高、最值得一提的是鞑靼部。”至此东方帝都便染上了浓重的基督文化色彩。在文化接受视野里,期望之中或欲望改造过的信息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它经过自身文化传统的组构,编码,变成信息准确和有说服力的东西了。“曼德维尔正是在基督教义和骑士道视野内改造了契丹大汗的形象,同时展现着欧洲人集体记忆的传统欲望。”(周宁,1999:123 )
5 结语
如果说《马可波罗行纪》打开了欧洲人认识世界的视野,让他们知道在欧洲之外还有一座富裕繁华、奇妙迷人的东方城市,那么其后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和《曼德维尔游记》则分别从旅行纪实和虚构想象的层面上固化了汗八里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帝都形象。“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后一词充分表达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它唤醒和激起我们不受冷静的理性控制的好感,因为这种诱惑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梦幻和欲望的喷射。”(布吕奈尔,2001: 113-114)汗八里这座世间最繁华的城市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不断美化、提升,最后演变为神话和传说,成为后世航海家们探索寻找的世俗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形象的形成和固化是饱受宗教禁锢和战乱摧残的人们内心欲望的强化和外化。“旅行家无疑在中国发现了更繁荣、更先进、更有秩序的文明,但他们的描述又多少进行了夸大,而夸大的内容主要在财富和君权两方面。”(周宁,2006:28)财富和君权的夸大构筑了汗八里,也构筑了他们想象中的世俗乐园。不难发现,这三部游记在解读汗八里时始终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或是模式化方式:绵长的城墙,笔直的街道,宏伟的宫殿,金碧辉煌的宫廷布置,奇幻的魔术表演,贤明善治的君主,基督教的传播,等等。“中世纪的欧洲构筑中国形象的典范性文本,具有一些不约而同的话题或主题。从这类惯例化或套话般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西方有关异域中国的报道,又可以体会出欧洲文化本身的置换性表现……他们不厌其烦地描绘渲染蛮子国的财富与大汗的威严,无外乎是在这种形象中置换地实现自己文化中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周宁,2008:28-30)这种形象的置换既展现了欧洲人的集体欲望,也奠定了汗八里作为世俗乌托邦在欧洲心目中的形象。
参考文献:
Brown, Christopher K. 2000.EncyclopediaofTravelLiterature[M].Santa Barbara: ABC-CLIO.
Cantor, Norman F. 1994.TheMedievalReader[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Pageaux, Daniel-Henri. 1994.Lalittératuregénéraleetcompare[M]. Paris, A. Colin.
Larner, John.1999MarcoPoloandtheDiscoveryoftheWorl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Luca, Dinu.2013.China as the Other in Odoric’s Itinerarium[M].ComparativeLiteratureandCulture, 14(5): 1-10. Print.
Guyard et al.1951.Lalitteraturecomparee[M]. Paris : P.u.f.
Schweiger, Irmy.2007.China[G]∥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Imagology:TheCulturalConstructionandLiteraryRepresentationofNationalCharacters.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125-131.
Robertson, George.1994.As the World Turns[G]∥Robertson.Travellers’Tales:NarrativesofHomeandDisplac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阿·克·穆尔. 1984. 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 郝镇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
巴柔.2001.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G]∥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巴柔.2001.形象[G]∥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布吕奈尔. 2001.形象与人民心理学[G]∥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鄂多立克. 1981.鄂多立克东游录[M]. 何高济,译. 北京:中华书局.
葛桂录.2010.《曼德维尔游记》中译本序[M]∥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游记.郭泽民,葛桂录,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克里斯托佛·道森. 1983.出使蒙古记[M]. 吕浦,译;周良宵,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雷蒙·道森.1999.中国变色龙[M]. 常绍民,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
吕超. 2008.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M]. 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
吕超.2006.“东方帝都”——欧洲中世纪晚期游记中的北京形象[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马可·波罗. 2001.马可波罗行纪[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孟华,2001.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G]∥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欧阳哲生. 2016.马可波罗眼中得元大都[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1):102-116,15.
张洛锋,张仁开.2005. 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J]. 城乡建设(5):78-80.
周宁.2005.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J].东南学术(1):100-108.
周宁. 2006.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宁.1999.跨文化的文本形象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1):120-124.
周宁.2004.契丹传奇[M].北京: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