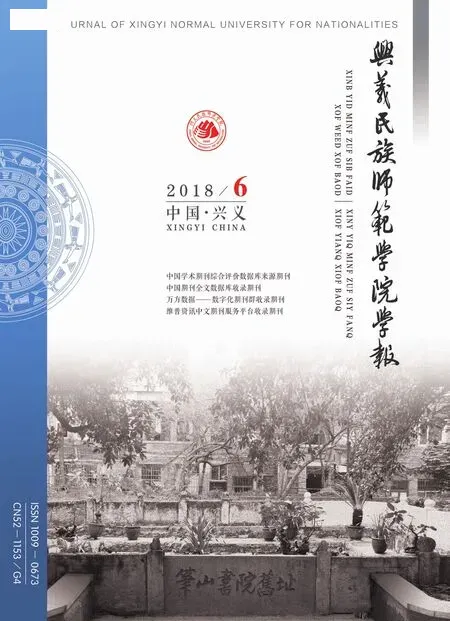花实与根本:王阳明的学问观
2018-02-26王安权叶冬梅
王安权 叶冬梅
(1.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2.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3.贵阳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5)
关键字:王阳明;《传习录》;学问观
王阳明思想的开端,是从对“学”的困惑里产生出来的。两百多年之后,在学问思想体系上与陆王迥异的戴震,同样是也在少年时期就明显表现出了对学问宗旨路径的困惑与思考。在程朱理学之后,同时也在程朱理学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分别作为明清两朝思想界的杰出人物,王阳明与戴东原都是最先将思考聚焦到如何理解儒家经典的路径上。但从一开始,阳明与东原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王阳明的问题直接指向朱子“格物”之说,他追问物理与我心、与古圣贤之心如何统一;戴震的困惑则是对经典文献诠释原则与方法的追问,即后世对经典之解释如何才能够符合古圣贤之意。前者导向反求诸己的心学路径,亦逐渐形成有次第的为学工夫论;后者则发展出“以词通道”的经学之途,亦有其特定而严格的理论方法。无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跟以戴东原为代表的清代经学在思想史上如何具有不同的色彩,都难以否认两者从本质上都是在学问观上具有深刻儒学意图的思想实践。相比而言,学界多措意于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对其学问观念讨论较少;本文尝试梳理《传习录》反映的阳明论为学工夫的次第与细节,对王阳明的学问观念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为学须有本原
《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1]40
“本”为根本,“原”即“源”。阳明在此处既是强调为学须有本原,也是强调为学须有次第。须有本原也即先有本原。有本原即意味着有渐进之次第,为学最先着力处应在本原,学问之根柢既立,则勿须作未来花实之悬想而花实自然依次而来。他同时在此条中借用了道家对婴儿的比喻,“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1]40树之本根即学之本原,亦即人之本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2]289-290在经历了格竹事件而内心却没有因此得到安顿的王阳明看来,为学之本原只能是在心体,而不能是经由其他外物来寻得。
又,《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1]37。
在阳明看来,心体本原具有无穷之力量,人不能“预其力”,灌溉乃其工夫,不能亦毫无必要刻意追求结果,“下学”与“上学”为一,行便是知。用功灌溉,心体明澈,则自然“条达畅茂”。
又,《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1]57-58。
心体活泼畅达,万物之理即处处施行得去;心物分裂,则一切知识与道理“与己原不相干”,对己而言即是支离破碎的,实际上也就等同于晦暗不见,“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1]63。
阳明惯于用也擅于用种树与川流的比喻,其他又如“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1]81为学之“本原”的说法,即植物之根与源头活水,均是有生而能生;人之活泼心体也正是如此。惟有于心体上不断用力之学,才是有根之植有源之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1]58又如《传习录》(下)之“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1]190既有生生之意,则自然源源不断而不能不有进,也必定会是《孟子》所言“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二、为学须有个头脑
“为学须要本原”是点出良知作为学问本原,“为学须有个头脑”则是工夫落实于事上,事事要“致良知”的更为具体的准则。《传习录》102条薛侃录: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①。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着,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1]75。”
又,《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1]41。”
又《传习录》第168条《答欧阳崇一》: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哉第二义矣。近日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工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1]143。
“头脑”又作“本领”,《传习录》(上)薛侃录:
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1]82。
阳明之谓“头脑”“本领”,即“关键”之意,应是“本原”落实在事上的体现,是心体所具有的判断力,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与之相对而言的,则是由于心体不明故而不够通达、不能触类旁通、不能无所依傍而只是因袭旧说的各种蔽见,源头不对,工夫便无从有着落。具体在体会经典上,若心体不明朗,则容易落入文字穿凿附会的困境,工夫沦为徒劳,茫茫然无所得。
《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律吕新书》,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冬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1]55。”
此条与上卷陆澄所录“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所论可参照。阳明在具体的学问进路上,并非全然不讲求具体知识,而是强调“学者当务为急”、“知所先后”。原因就在于,漫无目的格物的路径可能导向思想的窒碍不通,用力纵勤,工夫也无着落。所以他不断强调学者为学要先“致良知”,寻得自家心体,方能寻得经义本原,没有到达这一层,则是工夫太浅,不是读书应具有的良好境界。
正如《传习录》(下)黄省曾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主要明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1]190。”
因而,在对待“识见”与“涵养”这两者的关系上,阳明亦有说法。
《传习录》113条薛侃录:
黄诚甫问“汝与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识见上。故圣人叹息之,非许之也[1]80。”
又第116条薛侃录:
因论先生之门。某人在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识见上用功。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1]81。”
此两条足可近一步表明王阳明在具体为学上主张首先从“心体”上用功,之所以说“日不足者,日有余也。日有余者,日不足也”,原因就在于“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1]71这种“只求日减不求日增”的工夫正是阳明用以应对无头脑无目的之为学的良方,因而徐爱言“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1]71《传习录》第239条记载阳明论学问之根本,以无根之树喻无根之学,又以无根之树移栽水边喻暂时求得知识滋养之学,可谓精辟警醒:“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1]185。”
三、真切立志
《传习录》(上)陆澄录:
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1]34。”
《传习录》(上)陆澄录: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1]53。”
此两条中,王阳明所言之“立志”是为“念念要存天理”,“志”是可“存养扩充”的凝聚的念,具有本体的意味。且阳明仍用树之根芽喻之,为学立志,发念作圣人,则能常存善念天理,其原因在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因为其心纯乎天理,既然“圣人可学而至”,则在为学当中应“念念存天理”,存养己心,方能使吾心亦如圣人一般。无论是于“本原”上用力也好,还是常存善念立志也好,都是阳明向内反求诸己,廓清内心以利学的工夫。
《传习录》(上)薛侃录: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1]81。”
阳明用树木根本喻为学“本原”,旨在谈灌溉根本,使心体本原充明无碍。此条立志工夫亦用种树之喻,重在谈刊落繁枝,使志专一;繁枝既去,则根干能大,利于为学。
《传习录》(上)薛侃录: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1]75。”
又,《传习录》(下)第241条: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作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先生曰:“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只为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1]186。”
志之专一、志之真切,是为学过程中所要秉持的。阳明解释《孟子》“夫志至焉,气次焉”为“志之所至,气亦至焉”[1]60,提倡持志而养气其中。
四、内省立诚
《传习录》(上)39条陆澄录: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1]44。”
又,《传习录》(上)129条薛侃录: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1]92。”
阳明提出为学之初,心意不定、不一、不专,可先使“静”。但他接着说静仅仅是“息思虑”的一个手段或最初的准备阶段,更重要的在于心意稍定之后自我返向内心的省察。从阳明的语气来看,“静坐”是相对为了方便初学而采用的办法,而不能滥用,重要的还在于克己。这是因为,“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亦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1]39因而内省克己不仅仅是在静坐阶段,还需要事上磨练,“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36。”
“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则是对为学诚意工夫非常精到的一段记载。“诚”之语源在于“聚集充实”,由此引申出的“(心志)专一”、“(德行)专一”的意义,在中国哲学上其内涵便是“实”与“一”。“实”即内充盈外不能侵,“一”即不二。内省立诚,克己之私欲私蔽,则无穷之“道”逐渐可得而见:“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砌方可”[1]56,“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精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欲到之处”[1]57。
《传习录》(上):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比来精察,乃至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1]76”
又《传习录》(上)陆澄录: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傍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1]34。”
“好名”是为学中最常见之私欲。阳明指出了克治好名之病的根本途径在于“务实”。就事上磨练而言,“务实”有不同的具体;就心体存养而言,“务实”即也是“立诚”的工夫。
阳明又用精金喻圣,无杂之精金正可作为“诚”、“专”、“一”语源内涵之极为贴切的比方。第107条言“只论精一,不论多寡”[1]76,批判“后儒只在分两上计较,所以流入功利”[1]76,“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作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1]77。”
五、余论
阳明在种种人生境遇之后,以坦诚而强大的人格力量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指点学者作存心、立志、立诚之工夫并于事上磨练,救前学于支离割裂无所统领,使反求诸身心的心学成为新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无疑具有不容低估的生命力,后来就最直接地影响了于嘉朴学兴盛之期提倡“性灵”的章学诚②。不同时代之思想学问各有其风采,就一个学派而言,辉煌的顶峰之后亦不免有暗淡、有偏歧,而杰出的思想家往往能既吸纳前学之精华,又能洞悉前学之困境,从而纠偏救蔽,阳明之于他的时代是如此,戴震之于他的时代是如此,章学诚之于他的时代也是如此。
注释:
①此句断句参照邓艾民《传习录注疏》。
②章氏说:“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之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于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于古所云乎?”参见《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下》,中华书局,2014,页 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