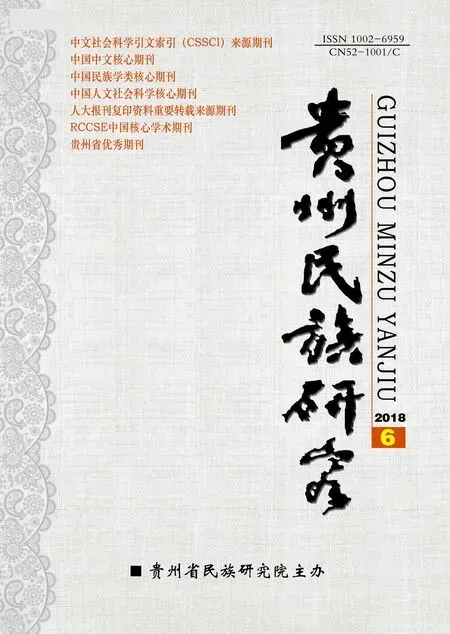国家在场:地方治理视野下清代湘西苗疆之集场交易
2018-02-22张晓燕暨爱民
张晓燕 暨爱民
(1.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2.吉首大学 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吉首 416000)
在嘉庆初年湘西苗疆边墙体系基本完成之后,苗疆地方社会治理渐次推开,从苗疆地方各级政治权力、军事体系重构与运行,到苗疆社会经济与保障体系、族群关系、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等,形塑了此后湘西苗疆近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基本格局。由此,边墙体系作为国家力量象征,在体现地方治理中之国家在场的同时,也确定了国家主导下地方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和性质。
一、民、苗集场交易之兴
清王朝建立后,随着湘西苗疆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国家与苗疆地方、民人与苗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诉求日益明确——之于国家,表现为湘西苗疆地方政治中枢的重建与秩序归复、政治与文化权力的下探和渗透;之于苗疆地方社会,则是民、苗百姓对社会生活和其间交往交流正常化的期待。
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参将朱绂抚剿镇筸红苗事后,湖广总督郭琇等人的奏疏中,就已见一些民、苗交易的相关规制。地方官员基于苗疆力量构成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在汉、苗居住之地设立市场,明定“每月三日,听苗、民互市,限时集散”。但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奸民”私自贩卖火药军械以及迎娶苗人妇女等事。[1](圣祖实录·卷二百零一,P57)这里,清朝政府对民、苗每月三日互市异常谨慎,严格规定了交易的具体地点、日期,以及市场交易时间的长短,交易物品的种类与范围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时,湖广总督郭世隆又要求民、苗贸易开展,须以“塘汛为界”,“苗除纳粮买卖外,不得擅入塘汛内,民亦不得私出塘汛之外,违者各照例治罪”。[1](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五,P355)从郭琇到郭世隆等地方大员关于民、苗交易管控之举,不难推见当时国家于苗疆社会治理之深层考量,民、苗划界分治已初现端倪。具体在社会经济活动层面,地方政府将民、苗的基本经济活动纳入直接监控之下,除了禁抑苗疆不同族群之间直接的社会与文化冲突外,也还有防止民、苗“构衅”或联合反抗官府之虑。
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年),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形成了由地方而中央的直接管理模式。显然,此举对于苗疆地方的国家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由于数百年来地方社会的权力架构、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地方力量与族群本就结构复杂的湘西苗疆,并未呈现出太平景况,反而是随着国家权力的进入而致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在政治与文化权力、经济利益分配、民苗族群关系上表现激烈。如后来有人在记述当年永绥苗峒情势时所言:“永绥所属各苗,自开辟六里后,照前明例,设百户以约束之。又汉民自内地徙入者,盘踞苗寨,负贩以逐什一之利。故乾隆乙卯之变,苗众辄以百户作威、汉民盘剥为词当事,据其说入告。”此情之下,清朝政府只得在苗疆勘定后复谋民、苗区隔规禁之策:“革百户,设苗官,徙各寨汉民于边内。沿边一带,自老石山以至跃马卡,先后安设营屯,以严防范,凡属边外汉民所置土田,悉归诸苗,以为羁縻之计”。[2](卷之六·苗峒,P115)
雍正五年(1727年),湖广总督傅敏在其治苗“五款”中,曾提出“请禁民、苗结亲”之议。傅敏等人担心民、苗密切往来,将会对管控地方秩序带来较大麻烦。因为一直以来,苗疆常常出现“民以苗为窟穴,苗以民为耳目”,若“民娶苗妇”“生子肖其外家”“虏杀拒捕”等情况。所以政府对民、苗姻娅严加禁止,除“凡已经婚配者,姑免离异”外,“其聘定未成者,自本年为始,不许违例嫁娶,犯者从重治罪”“已经婚配之兵则远移别汛,民则著保甲取结,汛守弁员稽其出入”。傅敏又要求对兵、民与苗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严加管束,“尤宜禁绝”“兵、民与苗借债卖产”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汉民柔奸,利愚苗之所有,哄诱典卖田产,或借贷给银谷。始甚亲暱,骗其财务后即图赖。苗目不识丁,不能控诉。即告官无不袒护百姓者,苗有屈无伸,甚则操刀相向,伏草捉人,报复无已”。所以,自后兵、民与苗人之间的往来交易,除“粜籴粮食、买卖布帛等项,现钱交易,毋庸禁止”外,其他类项必须严格禁止。若出现“民与苗卖产借债”,将“责之郡县有司”;“兵与苗卖产借债”“责之营协汛弁”。规定“自本年为始,许其自首,勒银索还。犯者照例治罪,失察官弁,严加参处”。[3](卷三·征服上,P127)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苗民至民地贸易,请于苗疆边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互相交易”。苗民“不得越界出入”,州县须得派“佐贰官督视”。同时,民、苗交易物品,明确限定为“日用所需”。[1](世宗实录·卷八十三,P112)总体看来,清朝政府对这些民、苗往来交易,控制异常严格:“苗民往苗土贸易者,令将所置何物、行户何人、运往何处,预报地方官,该地方官给予印照,注明姓名、人数,知会塘汛,验照放行,不得夹带违禁之物”。[1](世宗实录·卷八十三,P112)
此举较于康熙时期之民、苗区隔和地方控制,从划界、设市、限期到派员督视,再到查验物品、登记报告等诸般举措,管控程度显然又推进了一步。不过,从湘西苗疆秩序与稳定的角度而言,规制严格的集场交易、政府禁令和控制,给苗疆民众带来一些实际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湘西苗疆的社会经济活动。
乾隆时期,国势日隆,湘西苗疆民、苗关系趋缓,呈现出短暂的太平气象,政府边地政策亦稍显宽松,民、苗婚禁有所松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朝廷“以苗人向化日久”而“准与内地民人姻娅往来”以“渐资化导”。[4](卷八·屯防一,P130)即如川督和琳在其《善后章程》中所言:“弛苗民接亲之禁,客、土二民均得与苗民互为姻娅”。[5](P74)然而,今人对其时民、苗姻娅开禁也不可高估,国家对民、苗往来交流的实际控制依然很严。史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政府就因为其时各省番、苗、民之间“常有肇衅之事”而要求“定番界、苗疆禁例”。明定民、苗不得越界往来,如有“民人无故擅入苗地”或“苗民无故擅入民地”者,都将按例治罪。对民、苗之间的交易活动,更是实行三重监管,即往来贸易者,首先须得邻右保结,然后报官给照,最后由塘汛检查验证后方能前往。[6](卷一百二十·志九十五·食货 (一),P3482)
但在湘黔边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许多官员认为此次苗疆“变乱”,其主因是民、苗在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引起的矛盾冲突,故而要求将二者严格区隔开来。这样,以往关于民、苗往来交易之规禁,又被苗疆地方官员重新执行,民、苗交往再次受到限制。曾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一度开放的民、苗通婚又被禁止,建在苗地的集场都被迁往民、苗交界之处。如和琳在《善后章程》中,就明确要求在民、苗交界之处择地设立集场,将民、苗交易仅限于所设集场内定期进行,且严控交易过程,尤其禁止苗人以田亩土地与民人换取其所需物件。又规定,逢左丘场期,碉楼、哨台内驻守兵丁,“只准一二人赶场”“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不许多人远出,其出外者,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5](P81)
在当时管理苗疆的地方官员看来,如此严明规定,即可杜苗地“侵占盘剥衅端”,亦能使苗、民彼此相安,边隅自可期永靖。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时,傅鼐据有深巢苗民惮于远涉而私行于寨内开场交易情况,重申“在沿边开设集场,按期赴趁”之苗民贸易定例,严格禁止苗人于苗寨内私开集场,言:若苗地私设集场,或有奸民“借赶场为名,混入苗地”,引发民、苗纠争。他强调,此事虽“难以稽查”,但“所关匪细”,“不可不欲为防范、封闭”。故他一面明令禁止,一面“饬各地方官随时查禁”,要求苗官具订切结,“不准再开集场”,“以杜后患”。[3](卷四·征服下,P208)
清朝政府对民、苗私下的各种交往显得非常紧张而严格限制和监控。不过,苗疆各地方官员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完全、彻底地将民、苗隔离开来,固定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不利于清朝政府在苗疆边地的统治和秩序。因为,在根本上,清朝政府治理苗疆,不只是国家权力在苗疆地方社会的顺利运作,实际上还有苗疆地方民、苗百姓一体对国家政治与文化体系的集体认同,以此获得其苗疆治理权力、能力发挥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国家权力能在地方的顺利流通所需之支配结构的正常化。所以,虽然国家严格限制民、苗各种联系,但又并非完全隔绝两者,而是在具体的地方治理举措中,仍设置某些能使两者相互交通的管道,以保障苗疆社会民众生活之正常化,而苗疆社会的内在张力也由此得以缓减。当然,这些有限的放松,仍然不妨碍清朝政府对苗疆地方的严控。
二、苗疆集场交易之管理
苗疆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苗交往,成为当时清朝政府治理湘西苗疆的必然选择——在苗疆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和安抚政策直接推动下,沿边设立了相对稳定的用于民、苗交易的集场。实际上,在清代苗疆依托边墙的集场形成以前,民、苗之间的交易就一直以一种非正常的形式悄然进行。从相关文献记载并参诸实地考察,这些集场大都分布在汛堡或哨卡附近。汛堡附近的集场,其源起可上溯到明代卫所制之时。明朝在边地确立卫所制之后,驻守者便世代生息于此。因为生活所需,其驻屯汛堡附近,各类交易活动相应兴起。至清,随着边墙体系完竣,这类集场得以再兴。初期,进入集场的交易者主要为驻守边墙沿线的丁勇及其家眷。显然,他们对这种集场市易的依赖程度远大于苗疆土著民户。但随着苗疆秩序归复和社会生活需求扩大,周边苗、民也逐渐进入集场参与交易。
这些集场建设实在有些简陋,多由夯土围墙圈成,场内或搭草棚或堆乱石,用于杂陈货物,买卖人或蹲或立叫卖、交易。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集场一般位于汛堡外城之内或紧邻汛堡内城,或位于边墙外部靠近苗人地界一面,旁边往往设有瞭望台、护城壕等防卫设施。集场之如此布局和设置,主要还是基于安全需要——防止交易期间“不法”民、苗勾结“构乱”,或苗人闯入墙内劫掠。而如此布局之后,即使交易期间有苗人于场内“构乱”,其驻防兵勇也能很快介入管控。在碉楼、哨卡附近也设有集场,其形状结构与汛堡附近的集场大致相同。但交易双方身份与汛堡附近集场刚起时稍显不同,主要为民人与苗人。不过,仍有不多的哨卡驻守丁勇前往赶趁,只是由于加强集场管理和监督的原因,赶趁人数和在集场上的逗留时间被严格限定。如前所言,碉楼、哨台内只允许一二人赶场,“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禁止多人同时远出。外出赶场者,“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5](P81)
实际上,在民、苗交易中,清朝政府的严格管制在某些时候也会有一些灵活变通的情况。如在淮盐不能及时满足苗疆民众生活需要时,允许部分食盐商人进入苗疆挑卖川盐。当然,这一例外主要是由于苗疆远处边隅,淮盐不能及时运到,“若不量为变通,民、苗诚有淡食之虞。然听其买食私盐,又恐侵灌日甚,于淮纲殊有关系。应请查照湖北归州、巴东等州、县之例,如遇淮盐不能接济,听民买食川盐。不得过十觔之数,以便民食而资调剂”。[4](卷九·屯防二,P152-153)
清朝地方政府对湘西苗疆集场交易的监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限定集场交易地点、场期。因苗地常有“奸民出入”,“始则以贸易而利其财,继则因账债而占其地”,造成苗民穷困而生“变乱”。所以,地方政府明确规定,民、苗交易,应在设立于交界处之集场内进行,官方加强监管,维持秩序,随时“弹压”。[3](卷三·征服上,P136、P139)
其二,严控集场交易过程。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地方政府恐民、苗混杂再酿事端,专责营弁在集场交易过程中擒拿违犯各项规制之“奸民、凶民”。在集场之日,于集场附近派驻兵勇监管。如原筸子坪集场,即设在有兵勇驻守的老爷坡营盘脚下,每逢集场之日,便由这些驻守兵勇负责维护集场秩序,防卫“凶苗”闯入滋事。民、苗人众进入集场后,须接受巡查兵勇的检查。尤其是对前来交易的苗人,监控更为严格,不仅须具行切结,报官给照后由塘汛验放,而且在他们进入集场时,由集场巡查人员查明其进入人数,在交易结束离开集场时,则逐一登记核对放行。甚至有的地方官员规定在集场开市之日,由苗长、寨长“押苗民以同来,复押之以同往”。嘉庆十年(1805年),湖南巡抚阿林保在其苗疆《经久章程》中要求集场附近之“汛屯弁员”亲为监督,云:“惟各处集场,原许民、苗按期赶趁,以有易无。应令汛屯员弁亲为弹压。无许市侩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4](卷八·屯防一,P131)实际上,政府此举已不止于加强对某一集场或那些所谓“奸”“凶”民、苗的监管,而是将整个湘西苗疆民、苗社会生活过程纳入国家的监控之中。
其三,严管集场交易物品。清政府允开民、苗交易,主要是基于“苗地之盐斤布疋等物,胥藉客民负贩以供日用,如一概禁绝,多有不便”之实际。如前文所言,为抑止、防维民、苗矛盾冲突,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时,傅敏即提出民、苗交易仅限“粜籴粮食、买卖布帛”,而严禁民、苗之间的田产买卖和“借贷”行为。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在其苗疆《善后章程》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限制。[3](卷三·征服上,P139)嘉庆五年(1800年),傅鼐在办理苗疆均田事务时规定:“每逢场期,准令民、苗两相交易。各卡门务须查明,不准苗人混带枪械进内,民人及勇丁等与苗人买卖,须皆照时价公平交易,不得欺骗肇衅。倘有滋事者,立即严拿重究”。可见在交易物品上,主要还是限于盐、布等日用必需品,严禁私贩火药军械等物。[3](卷六·均屯二,P264)
在沿边兵、民、苗的交易往来中,边墙与集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墙—集场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集场成为湘西苗疆兵、民、苗交易和联系的合法平台;边墙则被赋以新的角色和意义——不只是作为“国家”与地方关系紧张的符号与象征,它还是民、苗交往交流的依托,因而也可视为民、苗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言,湘西苗疆社会边墙的定位与意义,不只在于界分、区隔民、苗,同时也是湘西苗疆边墙内、外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的保障,反映了湘西苗疆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的机制与功能。
三、苗疆集场交易之价值
乾嘉苗民起义被平息后,清朝政府完成了边墙、碉卡,将湘黔边苗疆从西到东、从南而北圈围起来,界划民、苗各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空间。这不妨认为是清朝统治者对自明以来治苗策略的承继与发扬。但是,在加固界分民、苗围墙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开放一定的民、苗交往,对苗疆社会稳定有序同样重要。而前述之边墙—集场结构体现出来的民、苗交易形式的规范化甚至制度化,正是这一考量的突出表现。若自国家建构视角而观,可以说,政治、社会、文化之国家一体化目标也在其中。以此而言,集场设置与规范交易体现出国家之苗疆地方治理的努力。
虽然清政府对湘西苗疆的民、苗交易严格限定,但作为民、苗社会经济生活重要内容的往来交易一直没有被中止。这主要是因为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若能规范民、苗往来交易,或更能有效掌控民、苗动态。以是在乾嘉苗民起义爆发后,曾有官员上奏乾隆皇帝,提议断绝民、苗所有交易时,即遭到乾隆皇帝的反对。后者认为剿苗和民、苗交易是两码事,不能因为“平苗叛”而终止其间交易往来。应该说,这一鼓励民、苗经贸往来之举,显然又异于以往苗疆地方治理策略。在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中,一般对所谓的越境贸易是严格限制的。因为在统治者看来,那些跨境贸易及其参与者往往被视为王朝国家某种潜在的隐患。但在清代于湘西苗疆开展的集场交易,却是一种例外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交易形式,所以清朝政府对这种民、苗之间的跨界交易,虽严格管控,却并没有加以阻止、封闭。笔者以为,这虽然很难说是其时统治者对边地社会治理的理性认知结果,但是,他们显然也认识到,民、苗往来交流,对湘西苗疆社会整合、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据道光《凤凰厅志》载,凤凰厅所设集场,主要有:南门外场(附城保百日场),廖家桥场(城南二十里,三、八日期赶),落濠场(城南三十五里,五、十日期赶),鸦拉营场(城南四十五里,二、七日期赶),新寨场(城西七十里,四、七日期赶),新厂场(城南四十五里,四、九日期赶),杜望场(城南六十里,三、八日期赶),永新场(城南七十里,五、十日期赶),长凝哨场(城北十二里,一、六日期赶),得胜营场(城北四十里,五、十日期赶),筸子坪场(城北六十五里,四、九日期赶),水打田场(城东三十里,三、八日期赶),强虎哨场(城北九十里,三、八日期赶),江家坪场(城南四十五里,二、七日期赶)。[4](卷二·集场,P44)
集场分布,以厅城为中心,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等四个方向、不同距离的地域范围内,都设有集场。尤以城南、城北方向集场最多,城东、城西方向集场则相应较少。这种布局,与当时凤凰厅境边墙、汛堡的地理位置、道路交通,区域内民、苗人口的分布情况呈正相关。不同集场的赶趁日期错开设置,方便相应范围内民、苗赶趁交易,满足所属地域内民、苗社会生活的需求。
政府依托边墙体系对苗疆集场交易的管理与监督,使国家权力切实深入到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促进苗疆地方社会体系、族群关系和文化的一体化整合。国家通过驻守在苗疆边地的百户长、千户长、寨长还有办苗的外委、屯守备、苗守备以及集场上梭巡官、经纪人等,在湘西苗疆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运作机制,将官、民、苗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苗疆社会内部流动加速,苗疆紧张的族群关系、矛盾冲突因此而得以缓解,文化交流加强,社会经济获得发展,边墙沿线一些重要地区(如民人聚居区或民、苗交界处)的集场因为商业贸易而逐渐成为一定规模的集镇,如凤凰之阿拉、吉信(得胜营),乾州、镇溪所(今吉首)等,大都是在集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集场交易的过程中,关于交易物品、价值和交易方式等,苗人也逐渐有了自己的“操作技术”。史载:“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如杂粮、布绢诸类,以趋集场。……届期毕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初犹质直,今则操权衡、较锱铢,甚于编氓矣”。[7](卷八·风俗考上,P565)可见,苗人入市从事各类交易,从“初犹质直”,到后来也能如民人般“操权衡、较锱铢”,表现为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这显然是民、苗长期往来交易的结果,在表征苗疆社会经济形式的多元发展与族群交往加深的同时,也提示湘西苗疆社会结构与苗民生计方式的悄然变化。
不管是设于汛堡还是哨卡附近的集场,都是在湘西苗疆沿边秩序逐渐稳定,民、苗关系相对缓和后,应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生的。从湘西苗疆地方治理角度看观,清朝政府在边墙沿线建置集场,作为民、苗交易平台,边墙、碉卡则成为其时民、苗交易的重要依托与保障,此举意义重要。一方面,推进了苗疆地方社会的治理,有助于稳固清朝政府在苗疆边地的统治,重构苗疆社会之有序格局;另一方面,密切而稳定的民、苗往来交流,在促进苗疆社会体系与族群关系整合的同时,又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从社会整合的视角来看,湘西苗疆区域范围内的集场网络及集场交易的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权力从上至下渗入湘西苗疆边地的最底层,应对苗疆社会变化。清朝地方政府根据苗疆兵、民、苗实际社会生活需要,边墙体系结构与具体布局,民、苗人口分布与物产构成,选择屯堡、碉楼、哨卡附近作为民、苗交易之所,制定交易规则,严格规定交易时间与物品,安排管理人员加强集场监管,维护集场秩序。较于清朝政府依托边墙而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民、苗区隔情势,在湘西苗疆定期设集,则体现出清朝政府基于苗疆社会经济与族群交往的实际需要而采取的灵活性政策。如果说前者是国家对地方社会采取的刚性措施的话,那于苗疆设集开市则不妨认为是统治者苗疆社会治理举措中的柔性一面,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的“灵活性”运作,也可视为对苗疆民、苗分隔而治之纠补,以此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常态的同时,也推进苗疆社会的交往交流。
从国家之地方社会治理视角来看,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体系的完成,是国家力量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置集场,为民、苗提供了一个交往交流平台,也就是在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有效折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边墙附近的集场活动被融入到国家的地方社会治理举措之中而成其重要一环,或言构成边墙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通过这种机制,湘西苗疆呈现出相对安定气象,社会经济、族群、文化交往加深,民、苗社会之族群与文化边界在集场运作过程中被忽略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推进了清代湘西苗疆边地的社会整合。
湘西苗疆这种集场交易管理中的严、弛交替,体现了国家权力基于地方实际而调整的运作情势。于国家而言,苗疆边地的国家化进程中,地方的秩序与稳定是其力量运作的直接目标,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政策措施,大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调整,因而地方社会治理中呈现出严、弛交替的特征。事实上,湘西苗疆的地方统治者也正是出于边地社会治理落实的考量,视民、苗交易为“厅之大政”,尤为着意于集场地点、位置的选择,如“大村寨适中之地”或“民、苗交界之地”,其中虽有民、苗赶趁方便的考虑,但对地方政府而言,更在意的或许是直接对集场的有效管控。可以推见,集场所择之地,其实大都为靠近边墙沿线或碉卡附近。惟其如此,才能直接监管民、苗交易,遇有紧急情况能即时弹压。以此而言,国家对苗疆边地的治理,在这样一种貌似松弛的情境中得以深入,苗疆社会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集场交易,成为基于苗疆社会秩序目标的一种“工具合理性行动”,反映了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社会的治理策略。随着集场交易的日益规范化,它在苗疆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民族融合的程度亦随之加深。由此而言,彼时开展的苗疆集场交易,也不只限于苗疆社会经济层面的价值,应该还有加强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推进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