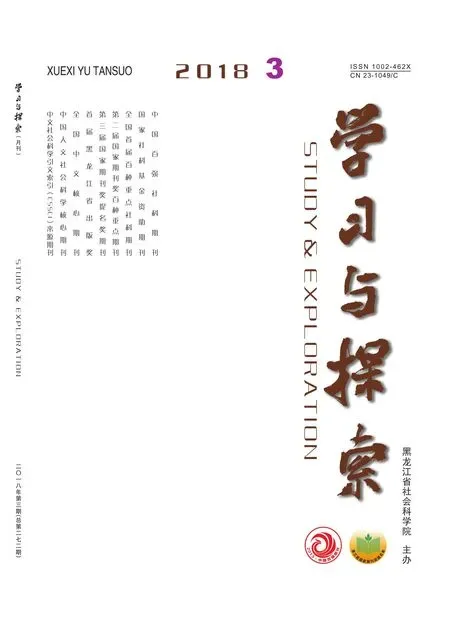如何在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经济范畴
——以卢卡奇、阿尔都塞和列宁对《资本论》的解读为例
2018-02-19李慧娟
李 慧 娟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史上,呈现出繁多的异质性的解读模式和解读路径。在这些解读模式中,试图对《资本论》做一种哲学解读时,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资本论》中的“概念”问题。如何在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经济范畴,成为这种解读模式的一个重要聚焦点。那么,为什么只有从概念入手解读《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才能解读出《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和真实意蕴?本文试图从卢卡奇、阿尔都塞、列宁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入手,以窥见概念在《资本论》中的重要性。
一、事实与现实
正如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堆砌一样,《资本论》中也充满了各种经济范畴。如何理解这些经济范畴,是理解《资本论》性质的关键。卢卡奇对于《资本论》的解读是从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入手的。
在卢卡奇看来,之所以要提出现实的问题,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晦暗不明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可见的,而是掩藏在对象性形式之后的,物的关系给人造成了超历史的纯客观的错觉。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透过物看到人,才能认识现实,“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1]64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就直接脱胎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拜物教的思想。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物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商品形式具有普遍性,劳动成为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具有统一的形式。这样一来,产品就变成商品,而劳动对象也由于分工而丧失它的独特的质的区别,成为相似且没有区别和联系的个别的存在。“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表面上人人平等;直接决定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经济关系日益消失。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对人说来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1]10现实的这种显现,又是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消失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确立为前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立使得人不再仅仅作为自然存在物而成为社会存在物时社会对于人来说才具有现实的意义,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关系还是以自然关系为主的。卢卡奇通过对于物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事实的虚假性、非历史性、非时间性和量化的特征,这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表现出片面化、孤立化的特征,他们没有办法从总体上去把握现实,而只能看到物化之后所提供给他的事实。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概念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现实的各个环节统一起来,只有把经济范畴理解成概念,才能实现思维的逻辑对于存在的逻辑的把握,“这样它就能把单纯的事实,单纯的存在提高为现实”[1]74。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是对于资本关系本身的生产,即产生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只有在思维中再现现实,才能把握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概念的层面上来把握现实。观念中再现的现实使得孤立的事实和没有联系的事实在具体的总体中产生了联系,这是黑格尔给出的对于现实的把握的道路。但卢卡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1]68。在马克思这里,现实不仅仅是思想所反映的那个现实,现实还是“力求趋向于思想”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一个在改变中的、有着终极目标的现实。“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1]50马克思哲学跟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朝向过去的,而在马克思这里现实是朝向未来的。
要想使对事实(fact)的认识成为对现实(reality)的认识,需要的是历史的和总体的方法。卢卡奇把“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和“在观念中再现现实”[1]56画上了等号。“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1]58,现实不是事实的堆砌也不是经验的罗列,而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总体的把握。所以,如果单从表面上看,似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现实的反映不够确切,实际上马克思要呈现的现实从来不是那个琐碎的经验事实,像照相机一样去复写它,而是进行了几重抽象,最终以概念的方式在思维中再现了现实,而这个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之所以理解和看到的只是事实而不是现实,只看到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不是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是因为没有辩证的总体观。只有从总体的观点出发,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作为资本主义整体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每个环节都看似自主,实际上又都必须依赖于其他环节才能完成。
从事实和现实的区分出发,要达到对于现实的认识,必须采取理论的方式,对《资本论》来说,就是要在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经济范畴,因为经济范畴不仅仅是物与物的关系的反映,更是人与人关系奥秘的揭示。但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现实必须以概念的方式才能被认识;而另一方面,概念又容易陷入概念的神话。对于对象的不理解,会使人们以概念神话的形式去构造现实。“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1]69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握现实,在卢卡奇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前的哲学都是从个人来考察和切入问题的,而马克思则是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考察的。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资本论》中。“在现代社会中,唯有诸阶级才提出作为主体的总体的这种观点,因此,由于马克思特别在《资本论》中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每一个问题,他在这一点上比在‘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上更坚决和更卓有成效地(尽管他的后继者理解得很差)把观点还动摇于‘伟大的个人’和抽象的人民精神之间的黑格尔纠正了。”[1]79
二、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
与卢卡奇把关注点聚焦在事实和现实的区别上不同,在阿尔都塞看来,“真正的文字游戏不在于现实一词,现实一词只是这种文字游戏的假面具,而在于对象一词。”[2]35因此,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对象”上,认为《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对象上,《资本论》的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经济现实,而不是经济事实,“最终从概念上鉴别马克思的对象同其他对象的区别”[2]80。
阿尔都塞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即“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2]2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全部哲学批判是直接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事实”,所以它是一种对于事实的反映,它所使用的经济范畴还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对于存在逻辑的思维把握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关心的是既定的当下的经济事实,这个事实是可以量化的,而马克思关心的则是这个经济事实背后的概念。“现代经济学家指责这些概念是表现非经济现实的‘无针对性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计量的,没有数量的规定。这种指责暴露了他们从自己的对象及其相应的概念中得出的观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2]83《资本论》不是从物与物的关系入手,也不是从纯粹的经验物质对象出发,而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的社会关系出发。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超越了他们。
阿尔都塞用“平面的同质性”[2]206来概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特点。按照他的分析,只有是一种平面的空间,才能够使对象具有同质性,而这样一个同质性是进行量化和比较的前提。“如果经济现象的‘领域’不再具有平面的同质性,那么它的对象理所当然不再在所有场合是同质的,因而不再能够以同一尺度进行比较和计量。”[2]206而“深刻的和复杂的空间”[2]207是马克思《资本论》对象的特点,这种对象只能通过非量化的方式即概念来认识。因此,“经济学家所指责的马克思理论上的缺陷和弱点恰恰是马克思的力量所在。”[2]8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来不是要在描述的意义上去量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他要做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批判。“由于看的缺陷,斯密不能看到的东西,马克思看到了。斯密没有看到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并且只是因为它可以被看到,斯密才视而不见,而马克思却能够看到。”[2]9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是通过这个概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并洞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连的新的概念体系”[2]163。但是这个概念又是一个受到最多质疑的概念,最重要的质疑声音就是它的不可计算性。而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正是这个不可计算性,才使得这一概念成为《资本论》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不是一个可计量的现实,那是由于它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的概念”[2]203。
阿尔都塞提出“认识的生产”来标识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性。“认识就是把现实对象的本质抽象出来”[2]30。人的思维面对的对象永远都不是那种纯粹的现实对象,而是人们的认识对象。“现实对象是经济事实,而认识对象则是哲学概念”[3]。对象和认识是同一的,因此,对于理论来说,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看到,而在于对象是在思维把握存在的同时被生产出来的。在他看来,现实具体只有前进到了思维具体,才是对于现实的认识,也由此在实际上区分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的不同的生产过程。两者是两种顺序的生产,一种是按照历史的现实的顺序生产,一种是按照人的思维的顺序生产。“‘再现’‘现实’范畴的思维范畴在这种顺序中的位置不是现实历史发生过程顺序中的位置,它们在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使它们获得了完全不同的位置。”[2]36在《资本论》中,一方面,马克思在生产领域内部进行了抽象,在研究价值的时候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关注交换价值,在研究商品的时候关注的不是商品的不同的质而是商品的形式。但马克思做的最大的抽象是对于资本主义总的生产过程的抽象。另一方面,当研究生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悬设了流通和分配领域的问题,存而不论。但马克思又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悬设了生产问题去研究流通和分配的问题,这样才组成了对于整个的资本主义总的生产过程的抽象。马克思所做的抽象并不是一种在纯粹的主观世界当中的抽象,这种抽象是思维的逻辑对于存在的逻辑的把握。“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时代,应该在它的概念中建立起来。”[2]109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经济生产时代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在某一过程中直接阅读出来的时代。这是一个在本质上不可见的、不可阅读的时代,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现实本身一样是不可见的和不透明的。”[2]110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时代,我们必须在概念中才能使它可见。正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际上是相通的两极一样,对于现实的把握也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意识形态这两个相通的两极中。“‘经验主义’不过是历史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表露”[2]115,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他们所追求的纯粹的概念实际上也蕴含着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永恒性的证明。“对虚幻永恒性的偏好从政治上说根源于他们希望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永久化”[2]184,这种纯粹的经验主义又倒向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根本的责难,是指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只有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的性质才能说明和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2]98按照阿尔都塞的判断,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对待现实问题上都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黑格尔的历史也变成了一种把它嵌入哲学之内的历史。“历史现实就其本质来说反对任何定义式的处理方法,而定义的固定的、‘永恒的’形式只能葬送历史生成的不断变动的性质。”[2]125
《资本论》是马克思以理论的方式实现的对于现实的批判,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离不开对于范畴的使用,只有从经济范畴入手,才能把握“现实的人”。《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既是对现实的描述、更是对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正是在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实现了“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把单纯的经济范畴上升为概念,赋予了经济范畴以哲学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观念论的批判道路缺乏对于现实的穿透力,他要做的是直面现实的存在,以理论的方式实现对于现实的历史的批判。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存在方式的改变,使得《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获得了全新的内涵。《资本论》的目的是要实现对于现实的历史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是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
三、唯物主义的“同一个东西”
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即“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357。从时间的序列上来说,列宁对于《资本论》的这一解读在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之前,但是从逻辑序列上来看,列宁这一判断又可以作为前两者的合题。
在列宁这里,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就是《资本论》的逻辑,而逻辑的现实表达是概念,从概念入手来理解《资本论》的逻辑,这是列宁给出的对于《资本论》理解的路径。马克思是用“抽象力”来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么这些经济范畴就不能仅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证和经验的内涵,而必定包含有批判和反思的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做的也不是截取一些经验的内容或者截取一部分他所需要的内容,然后套在现有的方法和公式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去把握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断裂,它是一个表面上具有人身自由和个人独立性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是作为一个具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原子式的个人存在的,这种在交换领域中的平等掩盖了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而要揭示所有的秘密,只能回到生产领域。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从商品的二重性到货币的二重性、资本的二重性,最后的落脚点是对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的考察,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是要在理论中重现资本主义的现实。这个理论现实和资本主义的经验现实是有区别的。它不是以常识的方式把握到的经验具体,而是在抽象的和概念的意义上的理性具体。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不是直接和可见的,而要把这种对抗揭示出来,只有通过概念才能完成。人的思维的逻辑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的逻辑的把握,是对于总体的逻辑的把握,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给出的对于总体和本质的认识。事物中有矛盾存在,才能使得事物有所发展。矛盾是关于对象自身的矛盾,即事物的本质规定性的自相矛盾。只有用概念、用辩证的方法,才能把握住既是自身又不是自身的矛盾的关系,才能理解事物的发展并在概念当中把它表达出来。一个概念凝结了人类的认识史、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发展,概念能够达到对于存在的矛盾的理解。“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4]194认识是无限地接近存在的过程,是以概念的方式所给出来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
在概念的意义上来理解《资本论》的经济范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都有所涉及,而列宁关于《资本论》的论断就直接是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给出的。列宁揭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概念,即使发现了事实,也不能用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获得它的真实的全部的内涵,概念本身不是一种形式的抽象,而是包含着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的概念。概念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认识论是人以思维的逻辑去认识外在事物的本质的方法,我们去把握事物,不能停留在表象和经验,而要用我们的思维的逻辑去把握存在的逻辑,这是在黑格尔那里所给出来的方法。“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410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等同起来,是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有价值的东西;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找到了他的中介——实践,这样理论就不是概念的抽象构造,而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理论通过中介达到了和现实的统一,“把黑格尔的概念的具体性唯物主义地变革为思维反映存在所构成的具体性”[5]。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辩证法,并不是要否认物质世界本身和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但是这种作为自在意义上的辩证法,必须要用自为意义的辩证法去把握它,只有通过概念的辩证法才能把握住。“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4]233逻辑的格,凝结着人的实践、历史和文明的发展。逻辑的格有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在人的意识中固定下来的以实践为中介的逻辑的格。因此,按照列宁的观点,《资本论》的概念既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对于挑选的片面经验的抽象,而是在存在的逻辑和思维的逻辑的关系中把资本主义的总体用理性的具体再现出来。因此,对于《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理解,不能单以一种事实性和经济学的逻辑来展开,马克思都把它们上升到了概念的层面,从而揭示了经济范畴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3] 王庆丰:《〈资本论〉的对象问题——阿尔都塞哲学解读的切入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2页。
[4]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 孙正聿:《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逻辑学〉与〈资本论〉双重语境中的〈哲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