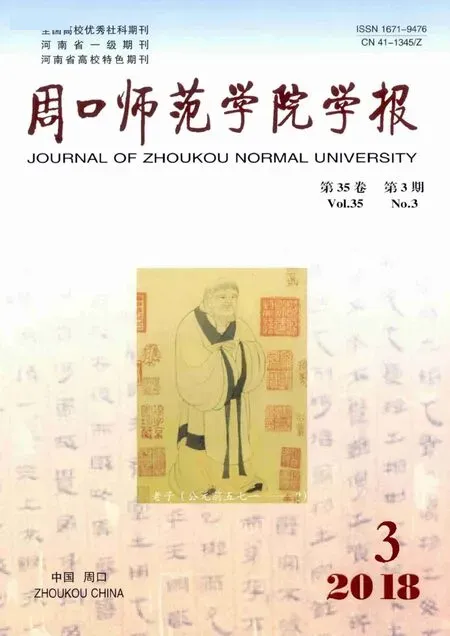论《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表演性
2018-02-09王艳荣
王艳荣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田纳西·威廉斯被评论家誉为美国二战后继“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之后美国剧坛第一人。《欲望号街车》(以下简称《街车》)是他的代表剧作。1947年12月3日《街车》在纽约市巴里摩剧院首演,打破了当时美国戏剧演出的最高场次纪录,并为威廉斯赢得三个重要戏剧奖项:纽约剧评界奖、戏剧普利策奖和唐纳森奖。由于《街车》的独特魅力,国内的学者也运用各种理论对该剧进行了解读,如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女性主义,荣格的心理学角度,异化理论,空间理论,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等。李尚宏认为,在布兰奇的悲剧中,“斯坦利充其量只是压垮骆驼背的最后那根麦草而已”,而真正的根源则是“美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对同性恋的排斥和打压”[1]113-121。但是作为压垮布兰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利是如何使得布兰奇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及他们之间行动的社会文化内涵却没有得到进一步阐释。戈夫曼认为,“‘表演’可以定义为,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2]14。也就是说,表演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交往活动。那么,当布兰奇从南方家乡来到位于新奥尔良的妹妹家,并以“南方淑女”的形象对周围人进行自我呈现并实现交往互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演。本文试从戈夫曼的表演论视角来分析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面对压倒布兰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利,她是如何表演的;其次,布兰奇的表演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么导致布兰奇表演崩溃的因素有哪些;最后,布兰奇为何这样表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来揭示布兰奇的表演中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布兰奇的表演策略
根据戈夫曼的观点,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这个“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通过不同程度自我印象的管理来有意识地呈现自我。布兰奇离开熟悉的南方家乡后,带着自己的道具来到新奥尔良这个新舞台。在这里布兰奇的观众主要有三人:斯黛拉、斯坦利和他们的朋友米奇。在斯黛拉和米奇看来,布兰奇就是一位文雅脆弱的南方淑女。但是布兰奇外化的淑女面孔背后却是对各种印象管理策略的运用,即表演手段。宋林飞教授将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策略明确分为四种:“理想化表演”“误解表演”“神秘化表演”及“补救表演”[3]288-292。布兰奇在表演过程中对这些策略都有运用。
首先,理想化表演。戈夫曼认为在表演过程中,为了使表演有效,表演者会“掩饰那些与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不一致的行动”[3]288。这种表演不可避免地要在演出中隐藏某些事物。在《街车》的第一场,刚从南方老家来到妹妹斯黛拉的家时,布兰奇就告诉自己:“我一定得把持住自己。”[4]13由于她之前因生活淫乱而被赶出劳雷尔的事实,既会使自己所维护的淑女形象大打折扣,又不兼容于演出,所以她对此只字不提。接着,布兰奇趁着斯坦利夫妇不在,偷喝斯坦利的酒,为了隐藏自己酗酒的恶习,她将杯子洗净并放回原处。布兰奇采取的这些措施实质上是为了掩饰与自己所要展示的理想“南方淑女”形象不符的表演。其次,误解表演。这种表演的目的是让别人产生错觉并得到假印象。布兰奇对米奇就是这种表演,她主要是让米奇产生错觉。为了给米奇留下一个规矩淑女的印象,她从不在亮光下与米奇约会,并对米奇谎称道,自己讨厌喝酒;斯黛拉比她还大一点;自己是个教书的老姑娘,还没结婚。布兰奇对米奇的这种误解表演带有明显的目的——获得米奇的爱。因为米奇“好像是这个乱石丛生的世界上我(布兰奇)可以借以藏身的一道缝隙!”[4]174此外,布兰奇也对米奇坦言道:“我可不想脚踏实地。我要魔法巫术!对,对,就是魔法巫术!我一心想给人的就是这个。我误导他们。”[4]172再次,神秘化表演。这是一种“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别人产生一种崇敬心理的表演”[3]291。在戈夫曼看来,对于一个人越熟悉,就越容易轻视他。可以说,布兰奇穿着与斯坦利的汗衫截然不同的华美服饰,买来中国的彩纸灯笼对妹妹家的灯泡进行装饰。这些表演可以产生区隔,使得布兰奇与别人的距离拉大,其目的不乏使得别人对她的淑女身份更加认可,产生崇敬心理。最后,补救表演。这种表演是“用来应付一些未预期的行动的,如无意动作、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当众吵闹等”[3]291。戏剧的第四场,在布兰奇认为斯坦利还没有回来,但他在火车声的掩护下已悄悄回家的情况下,布兰奇把妹妹视为自己的剧班成员,将斯坦利“缺场对待”,用贬抑的措辞大谈自己对斯坦利的看法:他天性中没有一丁点绅士的成分,“举止行动就像是野兽”,“有一种——类人猿一样的东西”[4]98。布兰奇冒失的行为和侮辱的话都被斯坦利抓个正着。斯坦利虽然装作若无其事但顿感威胁,随后便问布兰奇是否认识一个叫肖的人。尽管布兰奇予以否认,但她觉得自己的表演快要露馅了。为了规避表演失效的风险,她便跟斯黛拉讲了一些关于自己过去的事实,对米奇打了强心针,企图对自己的表演力挽狂澜。
通过分析布兰奇表演策略,不难发现,布兰奇通过自我“印象管理”,以期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纯洁、优雅、年轻,来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是她的表演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在《街车》中,布兰奇对自己的表演有这样的评价:“我觉得我从来都没像这次这么努力地强颜欢笑过,可结果还是弄成了一团糟。我真是尽了十分的努力了!——我确实是尽力了。”[4]120那么导致布兰奇表演崩溃的因素有哪些呢?
二、布兰奇表演崩溃的原因
导致布兰奇表演失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布兰奇与斯坦利的相互污名;布兰奇表演过程中无意的“流露”;斯坦利的侵犯。首先,在《街车》中,从布兰奇和斯坦利两人在争吵中道出的第一印象就可以判断出,他们两人一碰面就产生了戈夫曼所谓的相互污名。布兰奇对米奇说,“看到他(斯坦利)的第一眼,我就对自己说,这个人就是我的刽子手!这个人会毁了我,除非——”[4]132而斯坦利在随后的争执中对布兰奇说道:“我一开始就把你看得透透的!”[4]187戈夫曼认为,“污名在形式上是一种群体的划分”[5]107。两人的相互污名使得他们互相将对方划归为与自己不同群体的人。这从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衣着就可以看出。布兰奇第一次出现在斯坦利面前时,“穿一身讲究的白色裙装,外罩一件轻软的紧身马甲,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还有白色手套和帽子”[4]8,而后者穿着自己打完保龄球后汗涔涔的衣服,并当着布兰奇面换掉自己的脏衣服。两人的这种个人特质就表明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这使得他们将彼此视为一种不大值得羡慕的并会威胁到自己的人。这样,他们各自心目中的彼此瞬间成了一个有污名的、被轻视的人。这时,两人本身是否有缺陷或者有污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在交往关系中被对方视为有缺陷、有污名的人。戈夫曼指出,污名的存在并不是污名者的问题,而是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的缺陷。导致布兰奇和斯坦利两人相互污名的原因主要是两人来自两个不相容的阶层:南方贵族阶层和北方工业阶层。深受南方贵族价值观念的影响,布兰奇刚来到斯坦利在贫民窟的两间破旧的公寓房,就挑剔道,“哪怕在最可怕的噩梦里我也从来,从来都想象不到——只有坡!只有埃德加·爱伦·坡先生——才喜欢这个调调!”[4]15这两间公寓对布兰奇的南方贵族身份的优越感造成了巨大的减值,布兰奇通过对斯坦利进行污名,就可以将他驱逐出自己所属的贵族“内群体”并稍微提高自己的自尊。同样,由于布兰奇所代表的南方文化价值观念对斯坦利的家庭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使得斯坦利将布兰奇列为来自不受欢迎的阶层的人,并处处提防。斯坦利通过对布兰奇施以污名,就可以暂时缓解布兰奇对他造成的威胁感,强化他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提升自己在与布兰奇的相处中社会场景的控制感。这样,两人在一开始的相互污名导致了布兰奇在斯坦利家的表演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
其次,布兰奇通过刻意表演来给别人留下淑女的印象。这种表现是“行为个体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的表达,包括各种语言符号或它们的替代物,这是明显的表达,即给予的”;另一种“则是行为个体似乎不甚留意或没有加以控制的流露”[2]8。戈夫曼将人们通过控制自己给人以印象的这种表现分为两种——“给出”和“流露”,并认为“与其相信给予的表达;还不如信赖流露的意义更为可靠”[2]8。也即,“营造的印象基本取决于社会所接受或理解的符号,因而呈现的是社会现实,而人的本真现实,则往往是通过一些符号的丑闻而展示的,但这指向了人的自然形态”[6]10-13。那么,布兰奇通过控制自己的外表与自己的角色行为呈现自我越是有意识,她的表演越是不可信,而她无意识流露的信息却更有意义。作为一个精明的北方工业社会的推销员,斯坦利深谙此理。面对布兰奇南方淑女的表演,他对布兰奇有意给予的表达是否可信的兴趣不大,并认为她“傲慢无礼、装腔作势”[4]163。相反,他以布兰奇无意中流露的信息为基准,去检验她有意呈现的表演是否可信。在剧中第一场,当斯坦利邀请布兰奇喝酒时,布兰奇称自己极少沾酒,斯坦利看到酒下去不少后,讽刺道:“有些人极少沾酒,可是酒却常沾他们。”[4]31她蹩脚的表演使得自己的酗酒恶习无意流露,成为被怀疑的人。
最后,面对布兰奇的出现而造成的威胁,斯坦利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对布兰奇予以猛烈回击,以确保自己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斯坦利对布兰奇的侵犯主要通过任意处置布兰奇的私人物品、干涉布兰奇的前后台行为和强行占有布兰奇的身体来实现。第一次是在剧中第二场,斯坦利听说妻子失去了南方的庄园贝拉里夫时,他冲进布兰奇的卧室,没有得到布兰奇的允许,就擅自打开她的衣箱,“一把拽出一大抱衣服”[4]40。将布兰奇的假皮草、人造珠宝玻璃头饰都任意翻出来,试图找到庄园的销售契约。“戈夫曼基于对一家精神病院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人具有一种认同其私人物品的强烈倾向,诸如对自己的化妆品、服装,以及服饰物等等,具有很强的保持和认同的心理,并借此构建其私人性、自我,甚至身份,从而有别于他人。”[6]10-13在布兰奇的表演中,她的假皮草、人造珍珠等都带有私人性质,是她自我身份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她存在的一种方式。布兰奇借助于这些东西来掩饰她后台的真实,同时也借助这些物品在前台的呈现实现她对观众的演出。斯坦利对布兰奇私人物品的侵犯,不仅仅意味着对一种物品的强制性处理,而几乎等同于对人的人格、性格,乃至身份的剥夺。当斯坦利随意去翻布兰奇死去的丈夫艾伦曾写给她的情书的时候,布兰奇一把夺过来,并称斯坦利玷污了那些信。布兰奇夺回自己的信,不仅是布兰奇对自己私人物品的维护,更是她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
接着在第三场,斯坦利与他的牌友在家打扑克时,布兰奇遇到了米奇,为了吸引米奇的注意,她两次打开收音机放曲子,斯坦利先是“跳起来,冲到收音机前把它关掉”[4]66,接着又“怒冲冲地穿过帘子闯进卧室。几步走到那个白色的小收音机前,一把把它从桌子上抓起来。大骂一声把它扔到了窗外”[4]74。戈夫曼将表演区域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观众看得到,并从中获得一定意义的舞台部分。斯坦利这次对布兰奇前台行为的强行介入是两人对米奇的争夺引起的。相对前台而言,“后台”是指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舞台的部分。布兰奇的后台包括南方家乡以及斯坦利家的浴室。在知道妻子家的庄园在布兰奇的手里已经被抵押出去后,斯坦利就开始暗中调查布兰奇过去的社会资料。如果他拥有这种信息,便能知道与布兰奇互动期间活动的最终结果,这样他便能在与布兰奇的较量中应付自如。而过去的不堪却是布兰奇不愿让别人知道的。很快,他就了解了布兰奇的堕落往事,并将这些告诉米奇。这种无情的揭露,不仅破坏了布兰奇与米奇的关系,还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严酷的处境。同样,斯坦利家的浴室是布兰奇退到后台,从这出戏中抽身出来获得片刻休整的场所。当她躲在里面时间长一点也会受到斯坦利的干扰,引起他的不满。
在《街车》的第十场,斯坦利直接冲上舞台,对布兰奇进行了身体上的侵犯。尼采认为,身体是个人的决定性基础,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7]37。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体不仅是布兰奇生命进行扩大活动和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出发点,而且是布兰奇存在意义的源头,即她的主体意志。那么,斯坦利对布兰奇的身体侵犯在某种程度上就完成了对布兰奇精神的彻底打压。在第十一场,布兰奇离开斯坦利家,被送往精神病院的时候,“他(斯坦利)走到梳妆台前,抓住那个纸灯笼,一把把它从灯泡上扯下来,伸手递给她。她大叫一声,仿佛那个灯笼就是她自己”[4]208。当斯坦利撕毁了布兰奇的纸灯笼后,也摧毁了布兰奇与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布兰奇最终由于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疯人院。她的表演也结束了。
三、布兰奇为何这样表演
其实,无论是布兰奇还是斯坦利,他们的“自我是依据框架所提供的规划或规范在行为中展示出来的”[3]284。可以说,布兰奇和斯坦利都是社会情境的产物,在他们个人“前台”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只掌控着他们的无形巨手——社会体系。他们“表演的方式大多受制于文化和传统的限定,即个体表演很多时候不过是对宏大的集体性的文化表演的微妙注解[8]62-67”。威廉斯在一次访谈中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我不相信‘罪恶’。我也不信人有恶棍和英雄之分——人只有走对了路和走错了路的分别,而且这对错并非源自他们自愿的选择,而是出于必须如此或者受到他们自身的某种迄今仍旧不可索解的影响,受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的先辈所限而迫不得已的结果。”[4]218可见,作为社会情境产物的布兰奇是无法摆脱南方贵族社会所赋予的阶层社会文化属性的塑造和控制,这些文化因素始终影响着她表演的内容与形式。在《街车》的第四场中,布兰奇嫌弃斯黛拉家是“既不欢迎我又让我引以为耻的地方”[4]96。斯黛拉反驳道,“那么你不觉得你那副优越的谱儿有点摆错了地方吗?”[4]96正是南方社会文化体系所赋予布兰奇的优越感加速了她最后的疯癫。
通过戈夫曼的表演学视角来审视布兰奇的表演,那么她的表演就不能只机械地从对不同表演策略运用的层面来解释,其中往往带着其他的社会诉求。布兰奇的表演体现着两种非常矛盾的社会诉求:区分与认同。这两点正是布兰奇表演的深层心理动机所在。
一方面,布兰奇通过自我呈现来显示出与自己所不愿与之为伍的群体或个体的区别。当布兰奇来新奥尔良时,她带着自己十年来没增加过一盎司的身体和“趣味高雅”[4]20的衣服,来会见斯黛拉的朋友,但是斯黛拉的朋友种族混杂,并且粗俗。这时布兰奇的身姿与服饰也是她表演的道具,强有力地言说着她的品味、身份、个性等。戈夫曼认为:“任何具有某种社会特性的个体都具有一种道德权力,要求他人以恰当的方式评价和对待自己。”[2]12布兰奇通过展示自己优雅的个人前台,或隐或显地表明自己是优雅的南方贵族小姐,不同于也不属于斯坦利等粗俗的人的群体,她就无意识地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道德要求,迫使他们以她这种人有权利期望得到的方式来评价她和对待她。然而,以斯坦利为代表的“类人猿”拒绝履行布兰奇施加给他们的道德要求,同时,为了维护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感,他们撕下她的淑女面具,将她彻底赶出他们的内群体。
另一方面,布兰奇通过表演重塑自我身份,寻求社会认同。布兰奇通过运用各种表演策略,使自我的呈现与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相一致时,她在向观众传达着实现他人和社会对自我认同的愿望,也即对自我“南方淑女”表演意义的肯定。可见,表演是在向观众表达某种意义。韦伯曾说过,“人是一种悬浮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我把文化视为那些网络”[9]5。那么,布兰奇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通过自我印象管理进行“淑女”的表演,就可以看作她编织自己的文化之网,进而构建自我意义格局的途径。她的表演与意义的构建同步;布兰奇的表演是自我意义从构建走向分享和理解的过程。布兰奇是通过表演带来的意义感受存在的,他人也通过布兰奇的表演去把握她的意义格局。斯坦利对布兰奇私人物品的侵犯,前后台行为的介入,口头的侮辱都是对她表演意义的入侵、抽取和破坏。事实上,布兰奇的表演也是她追寻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表演背后隐藏的是她内心的痛苦和悲伤。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只为掩饰她内心的脆弱与无助。罗伯特·帕克说过:“面具是我们更真实的自我,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2]19也就是说,戴着“假面具”表演的意义不完全在于通过自我呈现实现交往的目的,这种表演更是个人道德属性的管理,它通过对真实自我所固有的冲动、不安、随心所欲等非社会化因素的约束,来达到一种规范意义上的自我约束的作用。但是,“成为某种人就是被‘他人’承认为某种人”[10]108。斯坦利作为反映布兰奇的他人之镜,并没有让布兰奇找到她的自我。相反,他无情地戳破布兰奇无关紧要的误解表演,并恶狠狠地骂道:“全他妈撒谎骗人耍花招!”[4]187这使得布兰奇的表演成为矫情的、歇斯底里的“拿姿作态”[4]172。最后,布兰奇的疯癫事实上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是一种在强权面前,个人的言说被消音后,找不到言说策略而不得已的滑稽表演。但是,这种表演却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和存在方式,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布兰奇的表演策略、布兰奇表演崩溃因素和布兰奇为何这样表演的原因的探析,布兰奇的表演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可以被更好地理解。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北方工业社会这个剧场所承载的价值和权力关系中,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表演与社会剧本不断协商来追寻自我却失败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了社会强势话语对弱势个体言说的打压。这种打压在威廉斯看来,就是宣传机器“总是竭力教育我们、奉劝我们去恨、去害怕跟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人”[4]218的结果。田纳西·威廉斯在剧中也对这种强弱关系的对比做了隐喻性的安排。布兰奇的一袭白裙与在斯坦利家玩扑克的几个男人“纯蓝、紫色、红白格子和浅绿色”[4]55的衬衫形成鲜明对比。“这几个正当壮年,正处在体能的巅峰时期”的男人“就跟这几种基本的色彩一样粗犷,直截而又强壮有力”[4]55。与他们相比,布兰奇犹如一只纤弱的白蛾,她飞到新奥尔良这个粗俗的七彩大染缸里,却要以自己的淑女角色对北方的社会环境生成的脚本进行反抗,最终只能落得个以卵击石的下场。正如威廉斯在一封给友人约瑟夫·布林的信中所说,“《街车》的意义在于表现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的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11]26。其实,在这出被称为“带有一种刺目、冰冷、暴力和愤怒的令人不安的调子”[4]163的剧作中,威廉斯通过布兰奇的遭遇不仅控诉了这个社会中的野蛮势力,而且表达了“唤醒大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倍地去更好地认识自己、相互认识的迫切需要”[4]163。
参考文献:
[1]李尚宏.悲剧并不发生在舞台上:《欲望号街车》主题辨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8(3):113-121.
[2]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宋林飞.西方社会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E Goffman.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Sutton Valence:Touchstone Books,1986:107.
[6]卢德平.从索绪尔到戈夫曼:符号学的转折[J].当代外语研究,2013(9):10-13.
[7]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林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7.
[8]刘涛.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J].现代传播,2017(1):62-67.
[9]G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Basic Books,1973:5.
[10]彼得·伯格.与社会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8.
[11]Gerald Wealse.Tennessee Williams[M].New York:North Central Publishing Company,St. Paul,19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