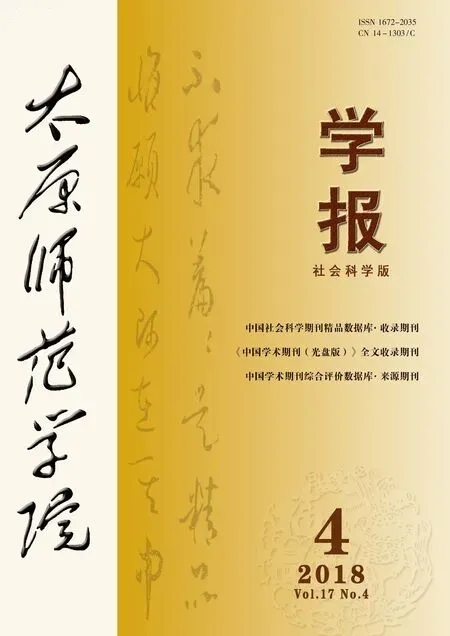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安世房中歌》与汉初政治文化
2018-01-29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汉书·礼乐志》开正史乐志收录歌辞之先河,后世史家在编纂乐志时,无不遵循班固创立的书写模式。此种模式大抵有其经学渊源,班固在《礼乐志》中收录的乐章,皆类似于典雅隆重的《诗经》“颂”诗,而与汉帝国的礼仪空间有着密切联系。汉高祖时代的唐山夫人创作了《房中祠乐》,此乐章之形式正是高祖刘邦最为痴迷的楚声。惠帝二年(前193),乐府令夏侯宽遵照朝廷之命令“备其箫管”,将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乐》改为《安世乐》。[1]1043班固综合了唐山夫人与夏侯宽的创作,用更具文学性的“歌”字替换“乐”字,题名曰《安世房中歌》。萧涤非认识到此诗为汉代礼乐文化之源头,将其尊为汉帝国三大乐章之首,亦是贵族乐府中只允许汉家天子使用的祖庙之歌。[2]34据许云和考证,《房中乐》本为姬周王朝之宗庙旧曲,唐山夫人用汉初功臣喜好的楚声改其为《房中祠乐》,而《礼乐志》收录的《安世房中歌》则是以夏侯宽为首的乐府官员新采选的乐曲与歌词,词作者是惠帝时期一批与朝廷关系密切的文人。[3]张树国不同意许云和的观点,他认为《安世房中歌》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唐山夫人在高祖年间所作“房中燕乐”,另一部分为叔孙通在惠帝年间所作“房中祠乐”,这两个部分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有着较大差异,唐山夫人创作的是杂言楚声诗歌,叔孙通创作的却是四言雅诗。[4]298帝国音乐系统的秩序化实际上反映出礼仪的逐渐完备,《安世房中歌》在汉代思想世界里的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如何用史学逻辑对《安世房中歌》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宗庙祭祀的书写模式何以成为隐喻帝国政治的工具?笔者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结合汉代基本史料对《安世房中歌》作进一步探讨。
一、帝国的政治文化困局
刘邦集团以布衣将相格局建立了汉帝国,中国社会亦在秦末汉初完成了阶层的一次剧烈变动。汉初君臣面对百废待兴的时局,尚无时间与精力去重新设计新制度,而是基本上继承了秦制。从汉家天子的称号到帝国百官的设置,乃至于长安宫殿之名,都很少有变化。此外,汉帝国承袭了秦之军功爵制,在全国范围内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以此作为帝国统治的政治军事根基。当此之时,民众刚从楚汉之际的兵燹中走出,帝国朝廷也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农业生产。然而,秦帝国制度中的许多弊端仍旧存在,高祖刘邦面临着许多秦帝国来不及解决的问题,秦短祚而亡的时代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若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对汉初的文化格局作一重新评估,最为明显的即是思想文化的“折中色彩”。[5]194“轴心时代”激烈的学术争论渐渐演变为诸子百家百川汇流的融合,战国思想世界的创造与革新亦渐渐销声匿迹。姬周王朝通过礼乐制度建立起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宇宙秩序,臣民的身份尊卑亦通过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与“天地差序格局”相对应。宗周礼乐制度与王朝封建制度相辅相成,成为周王室君权、族权、神权之文化根基与制度保障。《礼记·乐记》将礼乐制度中那些充满神秘主义的仪式与规则用儒家道德加以阐释,强调先公先王制礼作乐之目的不是为了王室成员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要让臣民在神圣体验中辨识美好与丑恶,并在崇高的仪式象征中“反人道之正”。司马迁认为君王应该在功成治定之后为后世制定礼乐,这是天子在天地秩序中的职责。礼与乐有着不同的神秘力量,君王作乐是为了应天,君王作礼则是为了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6]1417-1418可见,礼乐之重要性在汉代人的思想世界里仍旧不可动摇,完备的礼乐制度始终是圣王事业的伟大标志。宗周礼乐制度在历史书写中被塑造为一个秩序神话,《汉书·艺文志》将春秋战国思想家的师承都归于周代之王官,“周道”亦是汉帝国君臣心中的“普遍真理”。无论是用“礼崩乐坏”还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都无法准确定位春秋战国的文化格局。当周王室的封臣开始以傲慢的政治姿态逾越君臣法度,曾经神圣的礼乐制度逐渐被当作旧时代迂腐的象征,尤其受到法家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虽然后世书写中的“焚书坑儒”可以重新评价,却很难否定被法家思想与阴阳家五德终始理论塑造的秦帝国意识形态对礼乐的废弃。另一个毁灭因素来自秦末战乱,项羽军队对咸阳藏书的燔烧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汉初的文化萧条景象与此有很大关联。
秦帝国的政治凝聚力为何远逊于周王朝?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思考宗周礼乐制度对人间秩序的整顿。我们在梳理导致秦帝国迅速败亡的复杂历史原因时,必须重视帝国文化建设彻底失败这一事实。汉帝国的建立实质上是秦征服事业的翻版,刘邦集团在反秦战争与楚汉战争的血与火中取得最终胜利,建立了丝毫不逊色于秦的军事帝国。汉帝国建立之初,军功受益阶层以参与政权的方式,掌握着帝国的中枢权力与地方权力,亦凭借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7]255军功受益阶层以武人为主,他们对于文化事业十分陌生,亦对典雅肃穆的政治仪式缺乏兴趣。据司马迁记载,汉高帝五年(前202),“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6]3296不仅武人功臣对帝国政治权威毫无敬畏感,连身为皇帝的高祖刘邦也厌恶知识分子,乃至于不顾身份在儒生的冠帽里小便。[6]3262帝国君臣的文化修养与文化态度与其底层出身有关,他们在建立新政权时无需遵循“旧世族的踪迹”,[8]46自然也没有必要依靠神圣仪式建立政治权威,因为此种权威早已通过赫赫军功树立起来。然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征伐只是权力的来源之一,礼乐文明的秩序、规范、礼节才是华夏统治秩序的基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6]3270陆贾的名言成为两千多年帝制社会的永恒困惑,无论是来自底层的揭竿而起的当权者,还是入主中原的胡族政权,皆需要在军事权力与礼乐文明之间找寻制度的平衡。要而言之,对以高祖刘邦为核心的汉初开国君臣而言,若不改变其轻视礼乐文化的固有心理,极有可能在军事极权中走上秦帝国土崩瓦解之旧路。汉帝国初年的政治文化危机实际上正是王朝“瓶颈期”的必然,陆贾与叔孙通等思想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积极游走于公卿列侯之间,希冀以此影响汉帝国的文化政策,使汉室吸取秦亡之教训。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1640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各地区风俗之形成既离不开水土,也和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是分裂割据的时期,秦统一时间又十分短暂,汉初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习俗差异仍巨大。比如:天水、陇西之民“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巴蜀之民“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吴粤之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1644-1667此外,汉代地域社会的学术思潮与春秋战国时期一脉相承,例如三晋与关中地区的学者多属法家,作为孔孟故里的鲁国有着发达的儒学,齐地的稷下学者接近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杂家”,[9]荆楚社会的思想世界则是道家之天下。地域社会的文化差异在汉代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连汉武帝刘彻亦深受影响。据《史记·三王世家》记载,当戾太子刘据在巫蛊之乱中身亡,帝国储位暂时空虚。燕王刘旦遣使者至汉廷,“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希望武帝立自己为太子。武帝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6]2575燕赵之地好争斗,齐鲁之乡尚礼义,此种空间差异本是战国旧俗,但却以一种文化逻辑在历史中延续,建构起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地域秩序。
陈苏镇认为秦汉帝国的历史大趋势是统一,但高祖时代的汉帝国只完成了政治与军事的统一,文化之统一还远未完成。[10]秦之殷鉴不远,汉初君臣常以“过秦”思想警醒自己,未像秦帝国那样施行过激的文化政策,而是以无为而治的制度设计保持着地域社会的文化分裂。“后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若长久发展下去,势必造成皇帝权威的丧失。当地域社会的离心力无限膨胀,汉帝国极有可能重蹈成周之覆辙,使春秋战国天下纷乱之局面再现世间。礼乐文化的缺位使汉帝国在政治上缺乏凝聚力,导致地域社会的分裂倾向进一步加剧,而文化分裂的现实局面又阻碍了精神与政治权威的融合,不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更为致命的是,文化困局还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问题。例如,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度本是汉廷对东西文化异质的一种政治妥协,却造成同姓与异姓诸侯王的尾大不掉。“思想的统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灭为代价的”[5]199,汉帝国初创时期的每一次历史抉择,都笼罩在亡秦的阴影中。秦汉帝制与华夏上古政治传统的调和与冲突,决定着汉代历史的走向。如何走出汉初政治文化困局,完成对周秦制度的扬弃,是汉帝国君臣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
二、宗庙祭乐里的治天下之道
(一)重建礼乐制度
宗庙祭祀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礼记·祭仪》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郑玄注曰:“周尚左也”。可见在周代人的世界观里,王室宗庙的地位甚至高于象征国土与农业的社稷之神。宗庙祭祀仪式以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沟通祭祀者与祖灵,王族之荣光亦由此传承。高祖刘邦很早就认识到宗庙的至高无上的意义。汉高帝二年(前205),当汉军与楚军在彭城等地相争正酣,刘邦即命令留守关中的萧何为汉室立宗庙社稷。[6]2447汉高帝十年(前197),当刘邦之父在关中的栎阳宫去世,汉廷下令帝国境内的同姓与异姓诸侯王皆须在自己封国之中为太上皇立庙祭祀。[1]68当此之时,刘邦继续对军功受益阶层施加恩惠,他在诏书里向昔日并肩作战的功臣们许诺,要与他们共享长久富贵,“世世奉宗庙亡绝也”[1]71。这是刘邦对功臣的政治表态,表明汉帝国对华夏宗庙祭祀传统之尊重,而不是像秦帝国那样废除旧贵族的宗庙。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去世,惠帝刘盈下令立高庙于境内各郡国。[1]88此外,惠帝还将刘邦家乡的沛宫改为原庙,并常备一百二十人的歌者“习吹以相和”。[1]1045《安世房中歌》始以宗庙祭乐之性质进入高庙,成为帝国礼仪空间里的神圣乐章。作为帝国宗庙祭祀的文学书写,全诗整体呈现出典雅肃穆的艺术风格。第二章开篇曰:“《七始》《华始》,肃倡和声”,刘元城认为其有着高严的格调和简古的规模,接近上古的商周之颂。[11]16《安世房中歌》对《商颂》与《周颂》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一些诗句甚至刻意追求“高严”与“简古”,而不符合汉代通用的表达习惯。在汉帝国礼乐制度草创的年代,《安世房中歌》书写了帝室的文化认同与血缘凝聚,亦体现出帝国重现宗周礼乐文化盛况的决心。
(二)书写文化融合
考究汉帝国开国元勋的地域构成,可以发现其高层人物以丰沛楚人为主。高祖刘邦“据秦之地”,与项羽及六国贵族后裔逐鹿中原,秦人在刘邦集团中所占比例随着战争进行而逐步提高。汉帝国全面继承秦制,又定都于秦国故地关中长安,秦文化亦以政治优势成为帝国文化版图中最重要的一环。然而,由于“折中”与“融合”是秦汉思想世界的主要趋势,[5]199《安世房中歌》早已冲破了函谷关的文化界限,吸纳了东方诸国的大量思想文化元素。在《安世房中歌》典雅的诗句中,最能突出反映帝国时代文化融合的,是其中浓重的楚文化色彩。先秦时代的芈姓楚国有着强盛的国力,在与商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对峙中丝毫不落下风。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6]2043鼎盛时期的楚国,势力范围遍及整个南中国,甚至一度饮马黄河。在此国力基础上,楚国统治区域里形成了发达的楚文化,李学勤认为荆楚文化之影响力覆盖了半个中国。[12]12汉代的楚国是帝国境内最重要的封国之一,担负着为汉廷守卫东方国土的重任,首位封王为高祖刘邦之弟刘交。王子今高度评价了汉代楚国的行政建置与文化风貌,认为楚国在汉代政治史与文化史上皆有过醒目的表现。[13]据司马迁记载,当刘邦预见到戚夫人母子在未来的悲惨命运时,他让失意的戚夫人跳起了“楚舞”,自己则唱“楚歌”相和,以抒发心中之伤感。[6]2486
至于《安世房中歌》创作之缘起,亦是因为刘邦喜爱故乡的楚声音乐。《安世房中歌》第六章至第九章为杂言楚声作品,诗中大量运用三言句式,如“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1]1048,把这样的句子加上楚辞中惯用的“兮”字,即可变成“大莫大兮成教德,长莫长兮被无极”,这样就和楚辞里的《山鬼》《国殇》等篇章形式相同了。可以推测,“兮”字作为楚地方言,在写进宗庙祭乐时被省略了,而在用楚声演唱这些诗篇时,仍然会加上“兮”字。另一方面,诗中运用的“百卉”、“飞龙”、“丰草”、“女罗”等意象,继承了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式文学传统,符合楚文化对自然与想象的追求。正如楚王熊渠所言,先秦时期的楚国被中原华夏诸国视为南方蛮夷,即使楚国的芈姓王族可能是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在华夏世界的礼仪空间里,正统的宗庙之乐应该是《商颂》《周颂》《鲁颂》的形式,此种规范而有序的乐章象征着商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当汉帝国在神圣的宗庙祭乐中使用楚声歌辞,本质上是对古老礼乐制度的一次大胆革新。这表明汉帝国不仅是中原商周王朝的继承者,亦传承着南方楚国的伟大文明。若将此放置于更为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上古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存在了千年的文明对峙,终于在此时被统一的汉帝国终结了。
纵观《安世房中歌》之诗句,最能体现周秦文化精髓的是对“德”的无比崇尚。“德”是先秦思想家建构宇宙秩序的关键词,亦为周代信仰世界的核心理念,代表着沟通天地神灵的神秘品格。《尚书·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易》亦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外,嬴秦宗室自春秋时代起就对“德”之思想钟爱有加,秦德公嬴嘉是整个东周时期唯一以“德”为谥号的君王。彼时的秦国还在渭水流域的群山中与戎族缠斗,尚无被中原诸国接纳的文化底蕴。秦帝国以“皇帝之德”为立政基础,王子今认为这是帝国统治者对秦政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理解。[14]7在篇幅并不算长的《安世房中歌》中,“德”字竟然出现了十四次,现列举如下: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第一章)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第四章)
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第四章)
诏抚成师,武臣承德。(第五章)
民何贵?贵有德。(第六章)
大莫大,成教德。(第八章)
明德乡,治本约。(第九章)
德施大,世曼寿。(第九章)
慈惠所爱,美若休德。(第十一章)
告灵既飨,德音孔臧。(第十三章)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第十三章)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第十四章)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第十五章)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第十七章)[1]1046-1051
从宗庙祭乐对“德”的反复吟唱中可以看出,汉帝国承袭了上古知识世界的大传统,帝室亦服膺周秦贵族的普遍信仰。汉初南北文化的“折中”与“融合”成为时代大趋势,这在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中也有所体现。《安世房中歌》将荆楚文化与周秦文化皆囊括其中,书写了汉帝国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由楚地走出的汉室皇族,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南北文化差异,并把此种文化态度通过宗庙祭乐昭告天下。
(三)塑造高祖形象
汉帝国君臣的发迹方式开中国历史之先河,这在贵族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是缺乏合法性的。《安世房中歌》第六章曰:“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1]1048此章用《诗经》式的比兴手法赞颂高祖刘邦之“德”,将他比作众水归流的海洋与生养百卉的高山。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与秦二世以残暴形象广为人知,秦帝国的历史形象已然定格于“暴政”。[14]3汉初民众经历了秦政的折磨,也见识过项羽的嗜杀,迫切希望能有一位施行德治的君王重建人间秩序。《安世房中歌》赞颂刘邦之“德”,正是为了将“受人爱戴”的刘邦与秦始皇、秦二世、项羽进行对比,尽管此种书写的真实性颇有可疑之处。为了塑造高祖刘邦的崇高形象,《安世房中歌》罗列了刘邦一生之功绩。例如第三章里的“我定历数,人告其心”即是指刘邦任用张苍定历数之事。[1]1047第五章中“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肃为济哉,盖定燕国”,[1]1047是指刘邦平定燕地叛乱之事。燕地位于华夏北部边疆,《汉书·地理志》称其民风“愚悍少虑,轻薄无威”[1]1657。战国以降,燕地战乱不断。燕国太子丹曾派遣勇士荆轲入咸阳刺杀秦王嬴政,汉初的燕王臧荼与燕王卢绾也相继谋反。刘邦彻底平定燕地,使创建之初的汉帝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东北边疆,此后汉帝国对匈奴的各种政策方能顺利施行。
三、儒学昌盛之先声
《安世房中歌》还十分推崇孝道。纵观全诗,“孝”字一共出现了六次,现列举如下: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第一章)
大矣孝熙,四极爰轃。(第三章)
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第四章)
孝奏天仪,若日月光。(第十章)
孝道随世,我署文章。(第十章)
乌呼孝哉,案抚戎国。(第十二章)[1]1046-1051
这些“孝”字都出现在汉惠帝时代创作的四言雅诗之中,表现的应该是惠帝刘盈的孝道。汉帝国的创建者刘邦是不太注重孝道的,这一点常被后世儒生诟病。当汉军与楚军相持于广武,项羽为逼迫刘邦投降,曾在阵前威胁要烹杀刘邦之父刘太公。在父亲的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刘邦却以一种近似无赖的逻辑说自己曾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故刘太公亦是项羽的父亲,如果项羽真要烹杀刘太公,希望能分一杯羹。[6]416而当他称帝以后,他又在未央前殿当着诸侯群臣的面调侃自己的父亲,使在场的群臣大笑为乐。[6]486这些行为在儒家学者看来,必然是大逆不道的。刘邦出身市井,有着戎马征战的经历,这使他很难在思想与行动上履行孝道。刘盈却完全不一样,在五岁的时候,其父就被项羽封为汉王,他也在一年之后被立为汉王太子。我们可以推测,他从小就接受了和刘邦完全不同的教育,在性格和为人处事方面与刘邦大相径庭,刘邦也因此称其为“不肖子”。商山四皓比较了刘邦和刘盈在性格上的不同,他们认为刘邦“轻士善骂”,而刘盈则有“仁孝”和“恭敬爱士”的优点,因此天下人都愿意为刘盈效死命。[6]2486班固也在《汉书·惠帝纪》的赞里写道:“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1]92由此可知,《安世房中歌》里皇帝的孝道,完全是“仁孝”的刘盈的真实写照。
孝是儒家最为核心的思想之一,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秦汉之际,儒学虽然式微,但孝道思想仍然盛行于社会,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就成书于此时。《安世房中歌》作为汉家宗庙祭乐,其对孝道的推崇贯穿全诗。沈德潜认为此诗“屡称孝德”,自此开出了汉朝四百年之家法,故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之外的所有汉帝庙号都冠以“孝”字。[15]38有汉一代极为崇尚孝道,乃至于举孝廉成为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孝道和官员仕途因此联系在一起。汉代社会处在浓厚的孝文化之中,后世所谓“二十四孝”的主人公就有许多汉代人物,例如刘恒、董永、江革、蔡顺、黄香、姜诗、丁兰等。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曾编《孝子传》,东汉更是连期门军和羽林军的士兵也能诵读《孝经》。[16]1125追溯此社会现象之源头,《安世房中歌》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它以宗庙家法的形式,成为整个汉代孝文化的基石。
由此可知,以崇尚孝道为标志的儒学在汉惠帝时代已经开始复兴。四言雅诗为叔孙通所制,叔孙通则是汉初儒学的代表。叔孙通投降刘邦时,随从有儒生弟子一百多人。他最开始穿着儒服,让刘邦感到十分厌恶,因此不得不改穿楚制的短衣。此后叔孙通因为知识极其渊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徐广认为这是指叔孙通的德业可以承袭齐国稷下学宫之风流。[6]3296由此可知,刘邦在某些方面已经认可了儒学,叔孙通也被徙为太子太傅,成为太子刘盈的老师。刘盈有着“仁孝”的品质,恭敬爱士,在位期间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妖言令、诽谤法,这可能是受到了叔孙通的影响,司马迁亦称赞叔孙通为汉家的“儒宗”。[6]3301《安世房中歌》作为汉家宗庙祭乐,将儒家思想纳入其中,对儒学的发展是一件大事。汉代儒学能走向昌盛,最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汉初的叔孙通可谓功不可没。
汉初的政治文化困局由来已久,文化的衰落与分裂使国家困难重重。军国主义的秦朝曾经希望用法家思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繁琐严酷的秦法。这和关东诸国的文化产生了冲突,其中与楚国习俗的矛盾尤为激烈,从而使秦被以楚人为首的武力反抗推翻。汉初又以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治国,但这只是为了适应文化分裂下的郡国并行、东西异制。这样的治国思想注定无法长久,因为走出政治文化困局,实现文化的繁荣与统一,是历史赋予汉帝国的使命。儒家的理想是帮助君王“顺阴阳”与“明教化”,其学问“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1]1728是先秦诸子百家里最看重文化的。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在儒家这里得以保存,《诗经》、《尚书》、三《礼》、《易经》、《春秋》等诸多华夏文化元典也被儒家奉为经典。汉帝国只有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才能真正走出政治文化困局,避免走上秦朝的老路。萧涤非认为,唐山夫人生活在贵黄老的汉初,却能以儒学制歌,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后武帝尊崇儒术,也是“自夫人开其端也”[2]36。儒学在汉武帝时代成为汉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但这是《安世房中歌》成形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安世房中歌》是首倡孝道思想的帝国家法,不仅是汉代孝道昌盛之先声,也预示了儒学的兴盛。
综上所述,作为汉帝国礼仪空间里的神圣乐章,《安世房中歌》是解读汉初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面对周秦以降的政治文化困局,汉帝国统治者以祖宗家法之形式,为未来的政治文化构建指明了方向。此诗提倡重兴礼乐促进文化繁荣,又倡导融合各地文化以实现文化统一,还塑造高祖刘邦的圣人形象,这些皆是汉帝国治天下之道的文学书写。除此之外,《安世房中歌》推崇的儒家思想,最终成为了后世汉帝解决政治文化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