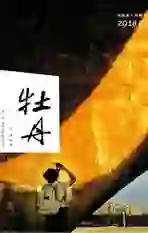老街人
2018-01-22杨永磊
杨永磊
“洛阳酱油洛阳醋!洛阳辣子酱、豆瓣酱、花生酱!”一大早被外面的叫卖声惊醒,我才意识到,在外漂泊一年的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吆喝着卖洛阳酱油洛阳醋的是一个从汝河北骑着摩托三轮过来的干巴老头,瘦小,头发斑白,满脸深深浅浅的皱纹,像枯树皮,一双小眼睛却滴溜溜的有神。他一年之中只在过年前的几天来叫卖几次。因此,洛阳酱油洛阳醋的吆喝声一起,乡亲们就知道离过年越来越近了。他吆喝的腔调独一无二,“酱油”和“醋”的发音总是要斜向上扬,像极了豫剧中的唱段。
我住的村子叫河沿村,在汝河南岸。这条母亲河哺育了两岸的人民,两岸人民经常互通有无。河沿村的村民世世代代以耕田为业,春夏秋冬,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有的人几乎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有的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县城。
村子里有一条最古老的街,大家称为老街,住着杨氏宗族里面最有权势的人。居于核心地位的当然是成有爷,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了。他是全村人和村里整个杨氏宗族的精神领袖。因为他在县粮食局工作了一辈子,见多识广,为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村里所有的大事,都要由他裁决,或者听听他的意见。他身材魁梧,鹤发童颜,相貌堂堂,再加上像毛主席一样的发型和洪亮的声音,使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成有爷喜欢摇着蒲扇,坐在大街上给乡亲们讲国家大事。他家门前的那把靠背椅,永远是属于他的,别人无权坐。两侧的小凳子,谁都可以坐。乡亲们有的端着饭碗,有的抱着孙子、孙女,有的拿着旱烟袋,或坐或站,都听得津津有味。一碗面条吃完了,或者还没吃完但辣子放少了,回家再盛一碗,多放点辣子,又过来边吃边听了。
村子里的执行领袖是全父爷。没错,他的名字是叫杨全父。村里人经常调侃他:“你的名字起得好哩,谁见了你都得叫爹!”
全父爷蹲在大街上抽旱烟,脸黢黑,双眉紧锁,眼袋垂着,慢吞吞地吐出一口烟,轻描淡写地说:“你这鳖孙!有人见了我还得叫爷哩!”
全父爷说得没错,我就必须管他叫爷,辈分儿在那儿摆着呢。有人则开玩笑说:“你的儿子叫全吧?你叫全父,全的父亲嘛!”
村子里的红白喜事,原则、方针由成有爷确定之后,剩下的大小事务就由全父爷来决定了。谁家死了人,停灵几天,待客几桌,甚至包括送葬路上在哪儿撒纸钱,在哪儿下跪,墓坑挖多大,都由全父爷全程指挥。遇见哭得过于伤心的逝者老伴儿或者儿媳妇,全父爷就会脸红脖子粗地斥责她们:“瞧你们那点出息!能干成啥事!给我咽回去!”说着就扬起巴掌,假意要打。
全父爷年轻的时候是个牛经纪。所谓牛经纪,就是负责在买牛者和卖牛者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据说牛经纪有三个特点,一是狡猾,二是脸皮厚,三是能说会道,三者缺一不可。买卖牛的时候,三方称过牛的体重,观察完牛的成色之后,牛经纪先面对卖牛人,背对买牛人,伸进卖牛人袖中,摸他的手指和拳头,探出卖牛人愿意卖的价钱,然后转身,面对买牛人,背对卖牛人,用同样方法探出买牛人愿意出的价钱。这项活动最需要的是耐心,谁先失去耐心谁就输了。因为这样的讨价还价往往要持续十几次,大半天。三个人各自抽着烟,蹲着,仇人似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就这样从正午僵持到日落西山。最后发怒的往往是牛经纪,把买卖双方都训斥一番,假意要走,暗中察言观色。即使买卖双方都没挽留,他也要黑着脸回来,重新蹲在地上抽烟。等双方都熬得差不多的时候,牛经纪的口才就派上用场了,巧舌如簧地讲出各种利害关系,撮合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当然,自己费了半天口舌,也是要捞上一笔的,至于钱多钱少,那就不好说了。
全父爷依靠牛经纪这个职业在十里八乡出了大名,自己也有吃有喝,三天两头下馆子。下了馆子,点上半斤猪头肉,一瓶白酒,再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吃饱喝足,拍着肚皮志得意满地往家赶。路过我家的时候,往往扔过来一小袋东西,对我妈说:“晓芬,这是些碎牛肉,让孩子们解解馋,都正长个子哩!”
按说成有爷和全父爷各司其职,不会有什么矛盾,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两人起了大的冲突。
故事还得从家乡的煤矿说起。我的家乡号称“百里煤海”,大大小小的煤矿遍地开花,村里的很多男人都在煤矿上挖煤,用家乡话说是“下窑”。但也有很多劳力不下窑,因为实在太危险,几乎每年都有因为瓦斯爆炸和透水事故死人的。有的矿工即使没死,也被落下来的煤块砸得手脚稀烂。父亲五十岁之前曾经下窑十二年,深知矿井下的危险。每天父亲起床,都阴沉着脸,开始回忆昨晚做过的梦。如果按照周公解梦的解法做的梦比较凶险,父亲就不去上班了,捂着被子睡一天。靠这种迷信的办法,父亲十二年中没有遇到过大的事故,最严重的一次是煤块砸伤了脚,在卫生院挂了一周的针。
我家东山墙挨着一条小巷,小巷深处是站柱家。站柱跟我爸一样,都在矿上下窑。站柱身材高大,为人老实,除了抽烟之外,喝酒、打牌、赌博一概不会,也从不打诳语,老实到了骨头缝里。但站柱憨人有憨福,娶的妻子极其娇美,打扮也时尚入流。论辈分我应该叫她颜嫂。颜嫂虽是农家妇女,但每天必化妆,九十年代刚时兴脚蹬裤那阵,颜嫂就买了好几套,换着穿,上衣也是紧身,前凸后翘加上美腿以及披肩长发和漂亮脸蛋,生生把人迷死。很多女人说她是妖精、狐狸精,但颜嫂依然我行我素。虽然打扮妖艳,但颜嫂干起农活和家务活来,丝毫不输给其他女人。站柱天天下窑,每天一回家,洗脸水已经打好,捞面马上做好,辣子油汪汪,红得喜人。站柱也不多说话,匆匆洗把脸,端起碗来就扒面条。吃完面条,热腾腾的洗脚水已经准备好,洗完脚,疲劳已消了大半儿。关灯上床,等孩子们睡熟,两人就开始在床上折腾起来。有这样甜美贤惠的娇妻,站柱心里能不美吗?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噩耗传来的时候,颜嫂正在择菜,愣了一下,嘴张了一下,昏倒在地上。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了好多天,眼睛肿得像烂桃子似的。处理完丧事几个月后,颜嫂才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穿衣打扮又精致起来。她好像并没有失去什么,生活依然自在而平静。她对公婆孝敬如初,每天端茶端饭,对自己的孩子也疼爱有加,一周从代销点提回来一箱AD钙奶。但她渐渐开始沉默寡言,也很少在大街上出現,行踪变得神秘起来,关于她的流言也多了起来。终于,流言被坐实了——颜嫂每晚跟一个外村的男人幽会。
那个男人叫李生,丧妻一年有余,比颜嫂大了四五岁,还未续弦。李生早年去过深圳、珠海一带,做生意发了大财,回到家乡开了一家石料厂,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九十年代有一辆桑塔纳轿车,绝对是财富和实力的象征。李生听说颜嫂丧夫未久,就有意跟她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每天深夜,颜嫂伺候公公婆婆和孩子睡下,就开始精心梳妆打扮。等她打扮好,小轿车已经悄悄地停在了巷口。颜嫂跳上车,去往他们的幽会地欢度良宵。第二天天未亮,小轿车又把他送回了家。
两人原以为天衣无缝,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拾粪的老光棍最先发现了这个秘密,接着全村人都知道了。全父爷听说后火冒三丈,大骂两个人不要脸,坚决要把颜嫂驱逐出河沿村,赶回娘家去;成有爷则不动声色,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人都是丧偶,况且都三十出头,年轻人做这事,于情于理有何不可?两人就此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大吵了一架,事情就僵了下来。无奈,全父爷只得请出村里的几个“元老”来,商量此事。
所谓“元老”,实际是村里几个超过八十岁的老人,其中就包括我的三爷。我的爷爷是老大,弟兄四个,爷爷和二爷早在文革前就去世了,三爷成了我家的家长。由于年事已高,被村里人尊称为“元老”。元老们商量的结果是:全父爷纯属多管闲事,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年轻人的事,管那么多干嘛,公道自在人心。他俩若真有意,就撮合两人结婚。从此之后,全父爷蔫吧了好多天,见到谁脸色都很难看,一副悻悻然又心有不甘的样子。
颜嫂和李生自知两人的事情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于是约定一段时间内不见面,等风头过了再说。看颜嫂这边,依然每天深居简出,偶尔出来倒尿桶被人撞见,一脸平静,还是那么花枝招展,跟平常毫无二致。村里人也不好说什么,只在背后戳戳她的脊梁骨。回望李生这边,也变得低调了很多,极少开着桑塔纳出现在河沿村。过了没多久,李生突然决定要出钱把老街的土路修建成水泥路,而且是全资。老街一下子沸腾了,整个河沿村都沸腾了。有人感念李生致富不忘本,想着乡亲们,有人在背后说风凉话,说这小子是“赎罪”来了,站柱刚去世没多久,李生就跟颜嫂好上了,修路是应该的。但李生不管这些,只管把路修好。二十年过去了,李生出资、监工修的那条路,依然平整如初。
村里人是最講究实惠的,有了这条平整光滑的水泥路,谁还会再提颜嫂和李生的过去?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接纳了李生。李生来到河沿村,再也不用像过街的老鼠、霜打的茄子了,恢复了往日的光鲜和气派。但李生不变的是他的谦逊,每到老街入口必定下车,让司机开着桑塔纳在前面慢慢走,他在后面跟着,拿着一盒烟,见到乡亲们就热情地打招呼、散烟。大家看李生这小子品行不错,相貌也和颜嫂是一对,于是让媒人撮合,让李生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把颜嫂娶回了家。
你以为李生把颜嫂娶回家之后,颜嫂的公婆就没人照顾了吗?错了。这个问题李生在结婚前就想好了。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把颜嫂公婆家的草房、瓦房全部扒掉,小半年时间就盖起了一栋漂亮的平房,堂屋、东屋、里屋、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每周周末必定和颜嫂一起回来看望两位老人,给老人送来水果和牛奶。但他们很少开着车回来,经常是李生开着摩托车载着颜嫂,“嘟嘟嘟”地来,“嘟嘟嘟”地回。上小学的时候,每当我趴在东屋的桌子上写作业,听到小巷里摩托车的声音,我就知道,李生载着颜嫂回来了。
从小巷出来,横穿老街,正对着的是老四婆家。为什么叫她老四婆,我也不知道,村里男女老少都这么叫,我也只好这么叫了。我只知道她已年届九十,是一个裹脚的小老太太,五保户,无儿无女,无亲无故。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去她家门前玩,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门边,慢慢地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看着我。大人见了必定要呵斥我,让我不要靠近她,说她身上有虱子。她早就聋了,别人再大声跟她说话她都听不见。她住的草屋已经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床单和被褥脏得油亮。偌大的院子里,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与她为伴。村人常说,活这么大年纪干什么,白遭罪啊!何况还无儿无女!但村人说归说,对待高寿的老人,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种敬畏。民政所的工作人员一个月才来看望她一次,给她送来油盐酱醋和一些生活用品。乡亲们买完菜,往往会在她门边放一棵葱,或者一颗小白菜,她眯着眼睛看着施舍的人,脸上现出感激的神情,但已经说不出话了。谁家包了饺子,给她送去一碗,以为她吃不动了,过一会儿再去看,饺子已经被她吃完了。
老四婆生命力的顽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有时候好几天不见她出屋,以为她死了,到她屋里一看,在床上坐着打盹呢!夏天下大暴雨的时候,村里总有劳力去查看老四婆的房屋,有危险情况会立即把她抱出来。有一次民政所的工作人员去看望老四婆,见她已经完全糊涂了,屙在床上,尿在床上,屎抹得满墙都是。民政所的工作人员把她训斥一顿就走了。颜嫂的公婆听说后,赶到老四婆家,捏着鼻子把她的床单和被褥拎出来扔掉,把自己盖了多年的被褥给了老四婆。颜嫂和李生听说后,专门赶到老四婆家,给她买了一床新棉被,还把她的破屋彻底打扫了一遍,把墙上的屎刮得干干净净。要送她敬老院,才知道老四婆三十年前就明确表示过,这辈子打死不去敬老院,所有的罪让自己受。
老四婆又奇迹般地活了好几年,但终究没有迎来新世纪。一个出生于清末宣统年间的老人,生命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晚年虽凄苦却如此顽强,这常常让我唏嘘感叹。在她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两年,她已经成了一个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事实上,那时候她已经很少吃喝了。听人说她一辈子很少害病,最后也是老死的。
老四婆死的时候,一辈子几乎从不流泪的成有爷、全父爷和我三爷都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村里很多人都哭了。尤其是成有爷,更是动了真感情,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一滴滴砸在黄土上。从此以后,成有爷再也没有在大街上高谈阔论过,每天吃完饭就拄着拐杖在庄稼地里闲逛。我上高中的时候,成有爷去世了,八十九岁。
如今,三爷也离我而去了。曾经孔武有力的父亲,也头发斑白了。我家也从老街搬到了村西头一处偏僻的地方。我常年在外上学、工作,半年或一年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能看到老街的变化。现在的老街,草房、瓦房早被扒掉,盖起了整洁、漂亮的平房,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有小轿车的人家也越来越多。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的媳妇生孩子了,谁家的老人去世了,每次回家,父母都会把老街的情况告诉我。我也会专门赶到老街,找还健在的老人聊聊天,跟儿时的玩伴叙叙旧,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养分。老街和老街人,早已熔铸在我的血肉里,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责任编辑 杨丽秀
实习编辑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