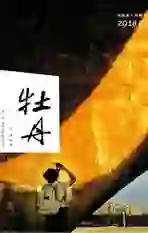和逝者的交流
2018-01-22刘军
刘军
般对般的老哥们、老姐妹都躺在坟里睡大觉了,他还漫山遍野地捡干柴呢。看着一个个大大小的坟包,觉得他(她)们还没死,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的身边:王海生啦,耿殿君啦,徐亚珍啦,马素琴啦,马老黑啦……哪个死了?哪个不活蹦乱跳、大眼瞪小眼地盯着他看呢?就是他刘福德,一天吃了睡、睡了吃地和死有啥区别?只不过换个地方,各过各的日子,各进各的家门,稀里糊涂地自己的梦自己圆呗。
1
话说回来,同样是老社员,说道可大得去了:王海生张嘴就能说出哪块地哪块地应该种啥,哪块地哪块地不应该种啥;哪块地去几个社员出活儿,哪块地去几个社员窝工;哪个牲口适合犁地,哪个牲口适合拉车……他能说出个啥?除了一问三不知,再就磨道驴听喝,满肚子除了稀粥再就稀屎,还有一副清汤寡水的大肠,外加一脑瓜子糊涂糨子。所以王海生一直当着队长,他只能当个老社员。
当队长也不是闹着玩儿,除了上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关键看你能给大伙儿分多少口粮,撑起他们那个永远也填不饱的稀屎肚子。比喻你队里有三百口人,秋后打了二十万斤粮食,上缴国库五万斤,去了种子、饲料一万斤,剩下的十六万斤才能分给社员。如果那样,每人至少能分五百多斤,事实上每人最多不能超过四百五十斤,剩余的只能继续上缴国库。相反,如果你只打了十万斤,上缴国库五万斤,去了种子、饲料一万斤,剩下的只有四万斤。如果还是三百口人,每人只能分二百斤,二百斤能吃个屁?别说喝粥,吃屎都找不着热乎的。上边就适当调剂,或允许你少缴公粮,以保证每人每天不低于一斤口粮。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够不够三百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别三百六,就是四百五,也不够干啥,一年除了吃粮,也只能吃粮,至于鱼、肉、蛋啥的,不是没有,主要得看你的运气:比如吃鱼,只能趁下雨阴天队里没活,自己去河里捞或水沟里抓,至于能捞、抓多少,除了技巧,全凭运气;吃蛋就得看你家那几只老母鸡的心思了,有的小孩馋急眼了,早上一起来就趴在鸡窝前监视,老母鸡一进窝就以为人家要下蛋了,一起身小手就伸进去掏,掏着了乐得直蹦高儿,掏不着大嘴一咧就嚎,弄得老母鸡都咯哒咯哒直叫;吃肉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只能盼着队里死驴烂马地分点;别的有啥,别说没钱,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要像现在想吃啥有啥,想买啥来啥,别说三百六,二百六,一百六也能吃出个大肚子,混出个糖尿病来。话说回来,即使那三百六或四百五,也都是皮粮,去了皮糠还有个屁?连皮带糠一块吃进肚里,能有多大油水?那叫时节,起早贪黑干的都是体力活呀!
除了粮食,再就吃菜,等粮菜接济不上,大不见小不见地就得偷摸,抓着算你倒霉,抓不着算你走运。此外,最大的盼头就是赶个好年头,好年头不光能吃到四百五,还能让你东张西望地胡思乱想。
看着漫山遍野的五谷,和满场满院的粮食,大伙儿除了想到那势在必得的四百五十斤口粮,还有不能言说的梦想。梦想不光社员有,队长也有,只是角度和范围不同罢了。
不能言说不等于不说,王海生先是犹犹豫豫、半吞半吐地向外释放,说上缴公粮,为国家多作贡献好是好,没大油水,上缴再多,每个人也得不着多少(上缴公粮虽然也按斤算钱,价格比私下交易至少低40%以上),饿肚子自己遭罪。“那咱们就私下分点呗……”有人悄悄地献计献策。王海生说谁敢分,炒豆大伙儿吃,炸锅一人事,出了事谁挑头谁倒霉。献计献策的人就说得大伙儿都得,谁能说,没长人心咋的?王海生说十个指头伸出去还不一边齐呢,谁知道谁心里咋想,万一谁嘴散给嘚嘚出去就完了。于是不光献计献策的,凡是知道信儿的都给王海生打气儿:“没事,你只要有话,咱们就干,谁要烂屁眼子敢说出去,你看大伙儿整不整死他!”王海生心事重重,进退两难。
大伙儿齐心协力地出谋划策:应该咋整,不应该咋整,谁说出去咋整,出了事儿咋整……条条是道,句句在理,还讲了很成功例子,如某某大队某某小队,人家是咋分的,具体是咋保密的,老百姓的日子是咋过的……听得王海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人煎熬得死去活来;一天天已箭在弦上。
等公粮缴得差不多了,再不分就没机会了,王海生一咬牙在儿子的算草本上扯下几页,悄悄地交给几个组长。几个组长悄悄地找到所辖街道的当家人,一个个签字画押。
一天早上,耿殿君亲自找社员们个别谈话。耿平时不笑,有人说他不会笑,所以才当了大队书记。大伙儿见他都绕着走,也没啥短处,也不是害怕,就是打怵,说他身上有瘆人毛。这会儿却笑呵呵的,一点不像个大队书记。被谈话的人都莫名其妙:耿书记咋了?咋成这德行了?两句话不来,突然拉下脸子,一点笑容都没有了,好像变了一个人,比耿殿君还耿殿君了,“听说你们私分粮了?”被谈话的人本来就懵,这下更懵了:耿书记咋提这事儿?这是他该提的还是他该回答的呀?是自己露了马脚还是人家发现了啥呀?一下子脸也白了,嘴也瓢了,平时很溜的话到嘴边上也打起秃噜滑了,结结巴巴地磕巴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了些啥,有的当场就尿裤子了。前后不到半天,王海生苦心经营了一个来月的堡垒,就土崩瓦解了。王海生开始死不承认,耿殿君笑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们怎样酝酿、怎样串联、怎样分粮、在哪儿分粮、每人多少、具体时间……都说得一清二楚。王海生当时就迷糊了,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脚跟,连回家都是耿殿君扶着才找到家门口的。
当晚就召开了批判会。参加的都是二队社员,有人建议全大队社员都来参加,一块受受教育。耿殿君说不用,事儿出在二队,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
会上除了大队干部和耿殿君偶尔发言,都不吱声;除了煤油灯吱吱地呻吟,再就玻璃罩上摇摇晃晃地往外冒烟,像招魂幡在随风摆动。
一个大队干部质问王海生,“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王海生在煤油灯下站着,低个头,不吱声,脑仁上露着头皮,像长势不好的坡地。大队干部接着质问:“叫你说话呢,没听着咋地?装啥糊涂?”王海生挪了一下身子,还是不吱声,脑仁上的头皮閃了一下,像飞过一个萤火虫,瞬间就消失了。耿殿君接着说:“大伙儿都得发言,展开批判,说说王海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多数人都低下头,还是不吱声,像参加追悼会,好像批判的是他们自己。耿殿君就提高了嗓门,“都得发言,谁不发言也不行!这叫什么性质?全队三百多人,七十多号劳力,出这么大事,没一个检举的,无产阶级思想都跑哪里去了?毛主席是怎么教导你们的?”齐刷刷的脑瓜,像参差不齐的黑土堆。
“没人说话一直开到天亮,明晚上继续开,看说不说!”除了煤油灯吱吱地呻吟,再就玻璃罩上摇摇晃晃地往外吐烟,可能没多少油了,灯捻子叫得越来越响,烟吐得越来越重,像爬坡的火车头。
“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打个人小算盘,互相包庇,欺骗国家,这是什么性质?咋就认识不上去呢!”头越来越低,矮个子没了脑袋,高个子成了竹弓,亮晶晶的汗珠像一只只惊恐的眼睛,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眨巴。王海生又往前站了站,“我说,事儿都是我主张的,和大伙无关……”会场轻微地骚动起来,人们都把眼睛偷偷地看向王海生,像看着一个人大步地走向悬崖。耿殿君说你主张的就有理了?国家的粮食政策这么严厉,你作为队长,不仅不自觉地执行,还干扰破坏,这是什么性质?你说!会场重新冷清下来。大队干部鼓励社员们要积极发言,同王海生的小集体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场冷冰冰的,像座凄凉的坟。
僵持中,灯火渐渐暗下来,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忽然亮了一下,然后灭了,屋子立刻漆黑一片,像星星掉进了深渊。人群低声嘀咕,小小地骚动。不知哪个大队干部啪地按亮了手电,还有的划着了火柴。耿殿君大声地喝问:“张德海,你是干什么吃的,光喂马,啥也不管,灯没油了也不早点看住!”会场后边很快响动起来,一个老头在手电光的闪耀下慌慌张张地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油渍斑斑的小铁桶。不一会,屋子重新明亮起来。
王海生当晚就给拿旧了帽子,也没啥结论。据说有人想把他定成坏分子,耿殿君说王海生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长,没功劳还有苦劳,又是贫农出身,不能因为一件事就把他推到阶级敌人那边,再说事情很复杂,揪起来打击面很大,还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最后不了了之。
看着王海生的坟墓,刘福德总觉得心里有愧。那么大个会场,连男带女七十多号劳力,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王海生三孙子似的站在那里,没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还说别人,你刘福德不也连个扁屁都没放吗?真是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人事,出头的椽子先烂。当了十几年队长,竟应验了,冷不丁下来,搁谁也不好受,也不至于那么脆弱,才四十出头的年纪,说不行就不行了。开始还好人似的,起早贪黑地和大伙一样干活,等发现毛病,就落炕了。前后不到俩月,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大家人,腿一蹬,说走就走了。
刘福德每次上山,绕道也要到王海生的坟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不是给坟头割割青草,就是往耗洞里填把黄土,天冷了还要拢一堆旺火,自己烤烤,也让老队长和他一块热乎热乎。
2
徐桂珍的事情有点突然,像好好的房子忽然就着火了。
眼看要过年了,场院里的粮食也打得差不多了,大份儿只剩下黄豆。打黄豆占地方,场院的大部分面积都铺了一层厚厚的黄豆杆子,一个社员赶着五六头牲口,每个牲口后边都拖着一个石头磙子,一圈一圈地在黄豆杆子上压来压去。要么压得差不多了,赶牲口的社员就喝住牲口,让旁边干零活的社员过来把黄豆杆子翻个个儿,接着再压。反复几次,黄豆杆子就压成饼了,豆夹上的黄豆粒儿也都脱落了,赶牲口的社员把拉磙子的牲口赶到一边,卸下套,牵到马号(饲养棚)去。场院里的社员呼啦一下围上来,连男带女的二三十人,用木叉把黄豆杆子抖落干净,挑到一边,把下边的黄豆撮到一起,很快就堆起一座金灿灿的小山。期间有心眼多的,趁人不备,把棉鞋往黄豆堆里一插,再拿出来,鞋窠里就装了一窝黄豆,下工时顺便就带回家了。
徐桂珍就是这么干的。当时天已经黑了,撮完黄豆就下班了。她慢腾腾地走在人群中间,不显山不漏水地就把黄豆带回家里。
进屋前先四下看看:不懂事的孩子不能让他们看见,胡诌八扯地乱说一气,真不真假不假地满城风雨;耿殿君更不能让他看见,看见就翻天了。不懂事的小三、小四都不在跟前,大姑娘、二姑娘不用背着,她平时上队里干活,家里做饭看孩子啥的全靠她俩,百精百灵地啥事也不用她操心。不仅如此,还让她俩看着点她爹,回来提前告诉她一声。
她着急忙慌地把黄豆倒出来,差不点装了满满一大碗,她又紧张又兴奋地还没等搁起来,黑克朗就从圈里钻出去了。大姑娘一边吆喝,一边喊妈,二姑娘也门里门外地往外跑,徐桂珍扔下二大碗也往外跑。败家的玩意可野了,稍不注意就钻出来,出门就是苞米地,钻地里逮啥吃啥。耿殿君家里的事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猪圈门子早就松懈了,跟他一说一哼哼,今儿个整明儿个整地一直拖到现在,说和没说一样,一出事就不是他了。
等徐桂珍和姑娘们把黑克朗圈进圈里,耿殿君也回来了。她急急忙忙地往厨房走,耿殿君前脚后脚地也进了厨房,“做啥好吃的了,赶紧放桌子,吃完饭还得开会呢。”徐桂珍支支吾吾地应着,慌慌张张地拿起那个大碗就往背人地方搁,耿殿君正好看见了,问她在哪整那些黄豆?鬼鬼祟祟像小偷似的?徐桂珍咯噔一下,顺口说捡的……耿殿君问在哪捡的?那么老些?挺立整、挺干净呀?徐桂珍这时候已经很紧张了,磕磕巴巴地说二姑娘捡的,谁知道她在哪捡的……脸吓得煞白,一看就是撒谎。外面已经很黑了,厨房也点着灯了,就准备收拾桌子要吃饭了嘛,亮堂堂地格外显眼。耿殿君歪着头看了看媳妇,啥也没说,抹身就出去了。
不一会西屋就传来了二姑娘的哭叫声:“爹,别打了,我说……我说……”
不一会耿殿君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来到厨房,“徐桂珍,把黄豆给队里送去!”
“我不送,愿送你送!”事情已经这样了,徐桂珍反倒冷静下来。
“妈了逼的,我偷的咋的,我送!”耿殿君伸手就打。
“站着说话不腰疼,光我自个吃呀!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你一天除了开会就是开会,家里像没你这个人似的,孩子一个个饿得黄皮拉瘦地你眼睛瞎呀!”徐桂珍也豁出去了,他打她也打,两个人撕撕巴巴地扭打起来。
最后耿殿君自己拿着黄豆送到了队部。
当晚全大队召开了批判会。批判对象就是徐桂珍。
有的都躺下了,硬给喊起来,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啥事。
大队书记召开会议批判她媳妇,谁能说啥?一个个大眼瞪着小眼,谁也不吱声。整个会场只有耿殿君一个人发言,鼓励大伙儿不要把徐桂珍看成是他媳妇,要把她看成是个满肚子私心的落后分子。徐桂珍說你才是落后分子!耿殿君说不是落后分子为啥把生产队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拿?徐桂珍说饿的,不饿请我拿我还不拿呢!耿殿君说全大队就你饿吗?别人都吃香的喝辣的了?徐桂珍说吃不吃香喝不喝辣的你问问大伙儿,问我干啥!耿殿君说这么说你还有理了?徐桂珍说我哪有理,有理能让人家批斗吗?耿殿君说你是不服啊?徐桂珍说就是不服!两口子三说两说凑到一块,大队干部赶紧把他们拉扯开。直到最后,会议也没开出个子丑寅卯来。
徐桂珍当晚就喝了半瓶敌敌畏。死前再三和两个姑娘说:“你们记住,你妈就是让你爹给逼死的!到下辈子我也饶不了他!”
耿殿君家的坟地离刘福德家不远,祖祖辈辈地好几十座。奇怪的是他和徐桂珍东一个西一个地像牛郎织女,中间隔着十好几棵半搂多粗的猪毛松。刘福德咋瞅咋别扭:这哪像个两口子,两口子哪有不合坟的?据说在合坟的问题上子女们分歧很大,最后只能尊重母亲的遗愿。
刘福德不由得感叹:人活着吵吵闹闹、你是我非地争论不休,眼睛一闭就剩堆黄土;现在的干部,能赶上耿殿君的——从头到尾,你就可劲儿地数吧!
3
看人家的笑话,自己这坛醋还不知道咋做呢。
每次走到自家坟地,他总要唉声叹气,好像媳妇让人拐跑了。
马素琴是他主动追求人家,开始说啥不干,直到结婚,还说他脑瓜子和面碱了。人啥说的没有,住家过日子勾噶不舍,淘米水都沉下来下顿熬粥,在队里扛麻袋大小伙子都不是个儿。说半天还是为了鼻子下边那张破嘴。
新粮一下来谁也不找那二皮脸,苛惭巴拉一讲一嗡嗡的,全家老小都抬不起头。一进二月门儿就开始出动静了,大手大脚的就开始东挪西借,挪不着借不着的就开始想歪歪点子了:谁家的仓房上挂着干白菜了,马号里切好的豆饼了,大队仓库里储存的战备粮了……都得加点小心。到五黄六月青黄不接,几乎遍地是贼,你偷我偷看不见就偷,可谓丑事人人有,不露是好手。刘福德也怪痒痒的,看着一家人无精打采、软丢当一个个面条儿似的,恨不得把能吃的东西都划拉到自个儿家里才好。上真章就鼠迷了,一听说谁谁谁偷土豆让人抓着了,谁谁谁偷苞米让人家游大街了,谁谁谁偷仓库让人家把胳膊给打折了……大气儿都不敢出,裤裆湿乎乎的,好像他偷东西让人给逮著了,要不咋说他脑瓜子和面碱了呢?这时候马素琴就该出场了,只见她胳膊一撸,脚一跺,“偷!大不了游街、挨揍,起码闹个饱死鬼!”说来也怪,很多人一整就露,不是半道上让人抓着,就是完事儿露出马脚,马素琴每次都全身而退,毫发无损。看着全家人敞开肚皮可劲儿地吃顿饱饭,他心里那个乐呀!还用那,就是歇气时摔跤,一般人都不是他的个儿,吴大个子平时和他摔跤每次都是他倒,吃饱饭吴大个子一摔一个跟头。大伙都很奇怪,说刘福德神了,抽大烟还是扎吗啡了?他美滋滋地啥也不说,说啥,那事能往外说吗?后来有人就半言半语,“这年头,能卖逼也行,往地垄沟里一躺,大苞米就送到家了……”他有点犯膈应,他媳妇就是偷苞米全家人才吃个溜饱,难道她也躺地垄沟里了吗?又一想算了,谁也没把手指到你头上,何必把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呢?再说媳妇也不是那种人呀!渐渐地看大伙的眼神,还是觉得不对,回家半真半假地跟马素琴套话。媳妇一蹦多高,“这年头有愿当官有愿发财的,没听说还有愿当王八的!你愿我让人抓住,满堡子游大街就好受了?”刘福德龇龇牙,说那倒不是……稀里糊涂地就算过去了。久了心里还是划魂儿,别家老娘们偷苞米时常让人抓住,我媳妇咋就抓不住呢?再想想媳妇当时那眼神,咋想咋觉得不对劲儿。
他想探个究竟:等媳妇前脚出去,他后脚跟着,从头看到末尾,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夜太长了,他也太困了,等着,等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睁开眼睛,媳妇正一下下地推他,“都啥时候了,还睡!”他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做梦竟吃好东西了,嘴里现在还有股香味儿。一抽鼻子,妈呀,哪是做梦?啥也别说,媳妇又得手了。
憋呀,憋呀,实在憋不住了。等孩子们不在,就他们两口子在家,他一咬牙把媳妇逼到死角,“你说,到底咋回事儿?”手里攥把镰刀,像个土匪。“咋回事儿……啥事儿也没有……”徐桂珍恐怖地看着丈夫,像看到了死亡。“别他妈狗戴帽子装人,你说!你说不说?!”他一把揪住媳妇的衣领子,刀尖对着媳妇的鼻子。徐桂珍后脑勺紧紧地挤着墙壁,眼睛看着刀尖,像到了自己的尸体;刀刃扎在她的身上,一直凉到她的心上。
刀尖划破她的鼻子,腥甜的血水流到她的嘴里。她忽然倒了,一米七三的女人瞬间堆成一摊稀泥。刘福德浑身发抖,恨不能一刀宰了这个败家的女人!突然手一软,丢下刀,对着媳妇拳打脚踢。徐桂珍像个沙袋,任丈夫怎么踢打,没一点反应。打着,打着,刘福德一屁股坐到旁边的锅台边上,呼呼直喘。媳妇才哭出声来。
看着浑身是伤,委屈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女人,刘福德再没动媳妇一个指头。他觉得自己窝囊,窝囊得像一摊狗屎:媳妇一天拳打脚踢,屋里外头,不忍心大人、孩子一天天地挨饿、等死,才半夜三更地跑出去……他如果像个男人,家里有吃有喝地啥也不缺……
他咽不下这口气,找机会和马老黑干了一仗。
“狗娘养的,你也太不是人了,看个青,就那点权力,还能干啥?”
“我就那点权力,啥也不能干,你能把我咋地!”
“你不是棍儿吗?我今天就撅撅你这根棍儿!”
“我看你咋撅我这根棍儿!”
两人三说两说打到一起。虽然一肚子稀粥,都是干活出身,都一米八十的个子,直打得天昏地暗,精疲力尽,也没分不出个胜败。
刘福德憋气上火,总觉得肚子里这口气出不来。一想起媳妇让人压在身上,呼哧呼哧的样儿,就想杀人。
4
都说坟茔地埋桃木橛子灵验。
他给马老黑家的坟茔地里就埋了桃木橛子。
看来挺准。马老黑没咋地,他媳妇秋后就病了,第二天一开春就进了茔地。两年不到,马老黑也完犊子了。开始病怏怏地还能干活,渐渐就落炕了,等送到医院,大夫说治也没用了。
他出了这口恶气,又有点阴损,马老黑是干了不是人干的事情,也不至于要命;他媳妇有啥罪过,也跟着背个黑锅?
等徐桂珍不知不觉地开始蔫吧,半年后就起不来炕了,他觉得老天爷报应他了:不就那点破事,干啥害两条人命?你刘福德没和长贵媳妇勾勾搭搭?谁给你埋桃木橛子了?
听说小颖和马老黑的孙子正处对象,他急得火上房子:可别扯了,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自个儿好坏不说,孙儿嫡女地都跟着遭殃……
马老黑没个人样,坟茔地埋得也跟人两路,他就是不吃不喝,一口气不歇,也得走一两个小时往上。
责任编辑 杨丽秀
实习编辑 刘水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