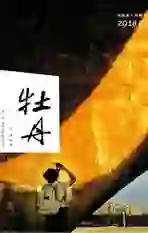三岔口
2018-01-22牛冲
牛冲
一
哥哥坐在床的左侧,姐姐坐在床的右侧,父亲和母亲斜倚着床背而坐,我坐在床对面的破沙发上。
父亲胡子泛白,脸瘦削如骨,自然卷相互缠绕如霜打的鸡窝。他两眼红肿,满脸不甘和委屈,直勾勾的瞪着窗外。老李欠账不还好像都是他的错,自己年轻时腾云驾雾为儿女摘果子的情谊如今荡然无存。父亲不想像泼妇一样的去要钱,毕竟他曾经是乡村里的一个小老板,如今尽管一败涂地,架子还是依然如故。
母亲每天晚上做梦银行来没收房子,母亲害怕他们来便把大门锁的结结实实,自己买水泥把墙顶埋上碎玻璃,又买了一把大号的锁加固大门,让蚊子都飞不进来。银行穿墙而过,用铁针撬开抽屉,把户口本,身份证全部翻了出来,再翻開《养猪指导手册》,翻了半天就只翻出一张五块的人民币,怒不可遏遂转身要掐母亲的脖子,母亲抡起胳膊挥了起来,把空气搅动的“咚咚”乱响,这响声把她吓得一屁股坐了起来,汗水在脑袋上肆虐如洪流,酒红色头发里露出大股大股的白。
哥哥整天都觉得老李很无辜,时也命也,人家不还钱说不定比我们还要苦,苦得没法活,抽屉里连五块钱都没有,我们还有五块,比他们要好很多,市里的房子不要了我们还可以住老家。
姐姐心疼母亲,看到母亲每天揣着绝望做饭、洗衣、下地干活就难受,只有给她钱让她心宽。给着给着姐姐也没了钱,自己家缺钱也不能直说,就死劲劝着要跟老李要钱。
我才不管那么多,我的三万块钱给了我妈,我妈就得赶紧还我,我刚毕业,好不容易攒了三万块钱,全喂银行破嘴里了,我恨得牙痒痒,没钱还谈个屁的女朋友,买包烟都得借,老李个混账,害苦了我。
我们各怀心事,一起骂老李是个混账。
两年前父亲与老李搭伙做生意,父亲出了三十万,全权委托了老李,因工程周期长一直结不下钱,期间父亲得了糖尿病,喝酒喝到脑血栓,于是要撤伙回家,钱一分钱没落到,还变卖九成新的汽车还了银行贷款,但是仍有部分未还,抵押的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被银行没收。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我们一大家子,于是你便看到每逢过年我们家就像服丧一样,满眼的哀泣和愤怒,像一群发了疯的豺狼,张牙舞爪,恨不得群起而攻之,让老李七窍流血,肝肠寸断。
二
父亲说,老李不会不给的,他说这两天就打过来。父亲的语气柔软无力像海绵。自从他捅出来这事后,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负罪者,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居高临下地指责他。
这两天…这两天…就老李那个混账,五月份就说打过来,推到七月份,七月份推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推到十月一,后天就是大年三十。我明天就带着老鼠药到他家,不还就死在他跟前。母亲早已失去耐心。
父亲显然被母亲吓住了,他一把推开紧挨着他的母亲。
传出去好听,是吧!父亲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脸上的青筋跳了出来,像一寸寸的刀疤,锋利而又恐怖。
你不要总顾面子,面子能值几个钱,老李把你欺负成什么样了?三十万,两年了,一分钱见了吗?他说没钱你就信,他开着三十万的本田,养着小老婆,每天赌赌钱,旅旅游,他说没钱就没钱。姐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老李的事情,这些事情听起来很真实,我能够想象到老李拿着一沓红色百元大钞扔给小老婆的样子,既得意又无耻。
自从老李不还钱以来,我们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刻画了老李的形象,这形象错综复杂,像滚滚黄河水那样浑浊,泥沙俱下,综合起来老李是一个混账无赖。他聪明,骗术高明,拥有逃跑的奇门遁甲之术,无论如何和他辩解你都不是对手,他油嘴滑舌,尖嘴猴腮,欺骗朋友,是一个天生的坏蛋。
就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老爸维护良好形象,和老李面子上还能磨得开,老妈就得说家里称盐的钱都没了。一边维护老爸形象不至于关系弄僵,另一边要狠狠的塑造母亲这个“泼妇”形象,如果不还钱,就把他们家搅的天翻地覆,在村里拉条幅,搞臭他们,大不了同归于尽。我心中全是我那三万块钱,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的钱要回来,我恨不得成为父母的角色,毅然决然的拿起一把斧头跑去老李家让他断子绝孙。
对,对,对……我不仅带着老鼠药,我到老李家就躺在他家地上。母亲看着父亲。
你躺在……躺在老李家有什么用?不够丢人是吧?父亲涨红了脸。
丢什么人,这还丢人,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妈是怎么过的吗?你说你做生意,我妈给你去银行办贷款,老李不还钱,银行借款到期,马上就收房子,我妈去舅舅家,姨夫家,连邻居都借了两千去凑,我妈去借,你在干吗?破罐子破摔,在家躺着,什么也不干,你做什么事都是我妈在后面兜着。要个钱怎么就那么难?老李是什么人,是不折不扣的混账无赖,他不还钱有一千万个理由,我们要不回来钱就一个理由——我们没有去要。姐姐站了起来,为了还清银行贷款,她出了七万给母亲,把她全部的家当都拿了出来。
哥哥说,老李说不定是真有难,不然去年为什么过年都不敢回家,听咱爸说他每年都要堵到厂门口要钱直到大年三十,说不定过两天就打回来了,这都说不准。
你脑子有病吧,他没钱,他没钱还开着本田到处转悠,我们到处借钱为了谁?还不是你那城里的破房子,这都是为了谁啊?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愤怒极了,恨不得跟老哥干一架。
秀娟,就你,揪住个事不放,几个小孩都听你的,就你会鼓捣,你鼓捣他就还钱了?他当然要给,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怎么可能不给,我这还有欠条。父亲怒不可遏地面向母亲。
还欠条,那算是欠条吗?有欠条怎么不还,有用吗?
你再说,你再说……父亲说着就站起身子,攥紧拳头。
你想干吗?你想干吗?打我妈?姐姐立马向前拥去,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父亲眼里充满血丝,他恼羞成怒,他从没有想过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末期遇到如此惨重的滑铁卢,他不允许自己失败,可是他分明感觉他的力量在一点点丧失。他不敢给老李说狠话,比如,去你娘的,老子告你,哪怕一句“老李,你不还不行”都没有,越是要不回来钱,他心里越没信心。父亲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我和姐姐,定定的看着。
我挣了一辈子的钱,我挣钱的时候,你们都高兴,我不挣钱了你们都逼我,还让我过不过,孬孙。
可是你看咱家都成什么样子了,你不要怕老李这个混账,你越怕他越不还你钱。姐姐顶着父亲说。
谁怕他?我怕他,中国哪个省我没去过,你说我哪个地方没去过?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的经历仿佛让他找到了一块可以立足的石头。
你不怕他,怎么不要,你不去,我去,我带着老鼠药去?母亲恶狠狠地说,脸一阵红一阵白,像得了哮喘一样,怒气在她的五脏六腑左右乱串,上突下跳。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家里的年货还没买,外面雪花骤停,鞭炮骤响,空气凝出冰来,寒冷刺骨,几只麻雀从电线上飞上飞下,整个大地浸在冰碴子里。
从村西到村东的马路牙子边停着各式小车,唯独我家的哈弗消失了,整个村子寂寞辽远仿佛此刻父亲的胸腔。一只乌鸦从上空掠过,我仿佛听到了一声鸟鸣回荡在空中,尖锐的声音在空中凝结成刀。
三
父亲正准备动手打母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手机铃声,声音夹在寒冷的空气里显的沉闷无比,像从远处传来的回声,但同时这个声音让我们都感到了亲切友好,仿佛远处飞来的信鸽。
是不是老李打来的电话?已经无数次打他电话都不接,发短信不回了。母亲从床上霍地站了起来。
我们的眼睛都聚焦在了父亲那部手机上,这部手机承担的太多了,一家人各式各样的希望、各式各样的仇恨。如果是老李来的电话,那一定是要还钱了,如果还不还,母亲明天就要带着老鼠药一早就去老李家死在老李跟前。
父亲捏起电话,当我们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我们禁不住又失望了,是老韩,老李的跟班,不过很快母亲的心中便燃起了希望,他希望老韩成为一个传话筒,老李不接父亲的电话,但是总接老韩的电话。老韩这个小跟班肯定会把话传到老李耳中,这无疑为要账往前推进了一步,只要老李听到母亲准备带着老鼠药死在他跟前,老李无论如何也会心有所动。
去球个孬孙,王八蛋,他到现在都没给我钱!父亲只有面对老韩的时候才会发这么大的火,在我们看来,父亲就像一只被老李这只猫捉住的老鼠,玩弄于鼓掌之间。
父亲说着要把手机摔到地上,母亲一把夺了过来。
老韩,我跟你说,你告诉老李,说我明天就带着老鼠药死到他跟前,后天就是大年三十,我看他这年过不过,我们家称盐的钱都没了,母亲说。
死什么死,就知道死,死到他家钱就回来了?父亲怒不可遏,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我们仨。
你们也不是什么好货。父亲说着走了出去,夺过绿漆斑斑的堂屋门,一小会就消失了,留下母亲和我们在屋子里呆坐。母亲擦掉眼角的眼泪,她的面容比之去年老了太多,粗大的泪珠顺着脸颊一泻如注,脖子上青筋暴露,皱纹丛生。
我追过去看到父亲慢慢地向村西头走去,渐渐的消融于远处积雪返照的光明之中,这个一辈子要強的父亲变的越来越小,他走南闯北的勇气在这两年里消磨殆尽。
母亲的策略果然奏效,老李这个混账准备给我们一个三万的承兑。两年了就只给我们一个三万的承兑。
三万块钱也是钱,可是什么是承兑?
我赶紧掏出手机上网查,承兑即承诺兑付,是付款人在汇票上签章表示承诺将来在汇票到期时承担付款义务的一种行为。承兑行为只发生在远期汇票的有关活动中。承兑行为是针对汇票而言的,并且只是远期汇票才可能承兑……
我念给父母听,可是他们听不懂,我也不懂。我又找人问,问过之后知道商业承兑不能要,银行承兑才能要。父亲又打电话问老李是商业承兑还是银行承兑?老李说是银行承兑,父亲这才放心,
你拿来吧,我去兑换,家里真是一丁点钱都没了,年都没法过,银行的利息还要还,父亲有气无力地对老李说。
母亲双目盯着父亲瘦削的脸,她脸上的皱纹稍微松弛,像初泡的毛尖微微的展开,我眉开眼笑,好像我的三万块钱很快就到我手里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胜利。
四
约定的地点是三岔口。
大年三十,一早我和父亲就出发了。
北风把街道两边的枯枝刮得东倒西歪,父亲骑着电动三轮车,我戴着帽子,围着围巾,北风呼呼地往里面灌,不时有辆汽车从我们身边飞过,我整个人卷缩在车子里面,看着路边一闪而过的“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白色宣传标语,不知为什么,总感觉我的整个身子被车子抽离飞向了别处。
我一定要看看老李这个混账到底有多混账,这个混账王八蛋。
车子抵达三岔口的时候是早上八点,从八点到十点我和父亲就坐在电动三轮上顺着路口遥望,等着那三万的承兑。积雪被人们推到了路边,成了一座一座的小山,路边的小店大半已经关闭,只有路边小摊上摆放着大年三十要放的鞭炮和要贴的对联,偶有几个老太太冒着严寒铺开长布摆放着一些蔬菜。
因为冷,我从车子上下来到处走走,我看着路两边光秃秃的杨树,看着背后父亲那张瘦削的脸,他坐在电动三轮车前面掌舵,佝偻着身子,将自己缩成一团,两只眼睛定定的看着前方。
远远看到一辆本田SUV向这边驶来,我和父亲将车子停在路边向西走去,再向前一些,车子很快减速了,我知道老李就要下车了,他就要把三万的承兑给我们了。
我曾无数次幻想老李的模样,我不知道这个让我们家陷入痛苦境地的混账到底长什么样?凶神恶煞,脸上有刀疤,尖嘴猴腮,油嘴滑舌。我也曾无数次幻想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他把我们家给毁了,当了八年农村阔太太的母亲现在去县城卖面条了,我想拿着斧头让他肝肠寸断,恨不得让他去坐牢,让他出车祸。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我不知道我会说些什么,我仿佛能够感受到我的血液在沸腾,真希望把老李那个混账大卸八块。
老李打开车门,从车里走了下来。
他穿着风衣,绒裤,灰色皮鞋。脸白皙,八字胡,虽然看起来已不年轻,但有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在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尖嘴猴腮,这让我大失所望,我想他肯定说起话来满脸杀气,外表是遮掩不住他内心的萎缩和无耻的。
老李从车里拿出那一张薄薄的、小小的承兑纸片。
父亲接过承兑,拿到手心里翻了几下,和老李攀谈起来。
你说啊,妇道人家知道什么?她准备过年跑你家我拦也拦不住。父亲的策略是对的,说好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那边说一直结账,可是就是不给钱,房地产不景气。对方一旦结钱肯定给你,不然我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才回家。 嫂子的心情我也理解,日子这么难过我更是理解,我日子也不好过,我也是到处借过桥款,希望这个工程早日结束,我也能对得起兄弟们。老李说话语速平缓,温和如玉,看不出有任何的着急,他面对着我和父亲像谈心一样。
到底出什么状况?一点也没结吗?父亲在他面前戾气少了很多。
唉……就是不景气,这两年国家一直说要去库存,可是我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房子卖不出去,咱们的钱也没法结,但是咱又不能半途而废不供货,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借钱往里砸。
父亲说,这是我的小儿子,现在也到了谈婚的时候了。
我说,是啊,我该到谈婚了,可是咱家没钱。我望向老李,想看他的反应,老李并没有愤怒,他微笑了起来。
老弟,现在老哥确实深陷困境,工程周期太长,这个谁也左右不了,你放心,只要钱一结算我立马把你爸的钱给补上,同时赚多少钱也一并给。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老哥,我给你包个大红包。老李边说边拍着我的肩膀。
我一时语噎,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似乎明白了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为什么在老李面前温顺如绵羊,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混账。倒是我们,要账像混账一样。
承兑得在三月三日之前必须兑换掉,不过要花点小钱,老李向父亲说。
这我知道,那剩下的钱什么时候结算,年前你就说今年肯定结算,这都一年了,父亲无奈的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唉!你看我,到了今天才从江苏回来,昨天去跟老韩借了五千块买点东西,不然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老李向父亲诉苦,表情温和,吐语不急不慢。
老李抖了抖他的风衣,看起来要走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就在那迟疑着,心里面有千言万语,可是就是吐不出一个字,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来之前母亲,姐姐都交代了我很多,可是此刻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父亲从始至终也没有说一句硬话,这和他在家里吆五喝六的表现有着天壤之别。而我则低声细语,在老李面前似乎那些混账话一个字都说不出。仿佛父子俩被老李制服了,这很像你练了绝世武功要挑战一个高手,却被他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一样。
我看着老李突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不知道说些什么,放他走吧,很可惜,因为他一年都拖着你不还钱,总说还,可是就是不还。给了这三万承兑,还有二十七万,这二十七万拖一次一年,货币还在贬值,就越发不值钱,最重要的是把我家拖垮了,再也翻不了身。
我看着父亲,父亲也没有要说狠话的意思,风从四面八方涌来,远处传来鞭炮声。
我得赶紧走了,家里都等着我回去,老李向父亲说。
什么时候能结算完啊?两年才三万,这……父亲仿佛在最后一次质问。
明年,明年……应该就差不多了,老李从车里搬了一箱王老吉、一箱王中王火腿肠、一箱营养快线放到了父亲的三轮车上。
给嫂子,给嫂子……听说嫂子的腰不好,代我向她問好。过年我就不去了,一出初六我就赶紧跑过去要钱,一要回来就给老哥打过来。
老李说着打开车门,不忘再跟我的父亲寒暄几句,今年你放心,我一定给要回来。
三十万的本田车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留下一缕烟尘。
我操他祖宗,我心里默念,可我说不出口。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我能感受到他的沉重,每一步都像走泥沼一样。三万承兑,去掉手续费将近一千,只有两万多,三十万,要了两年,只要了两万多。我们坐在电动三轮上,一路沉默不语,不知道说什么好。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