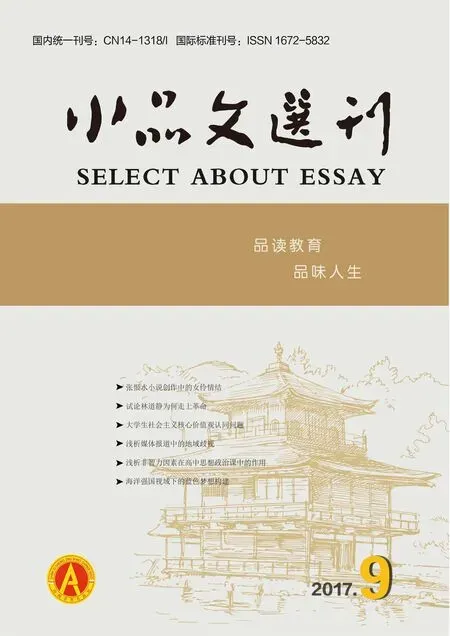亦媒亦阻
——浅析《墙头马上》墙意象之内涵
2017-11-24刘运巧
刘运巧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00)
亦媒亦阻
——浅析《墙头马上》墙意象之内涵
刘运巧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00)
引言
《墙头马上》是元代杂剧作家白朴之传世佳作,此剧缘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咏《井底引银瓶》而得其名,是谓“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白朴以墙为媒,亦以“墙”为阻,写尽了一双痴儿怨女的离合悲欢。而“墙”作为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蕴含了是时婚恋状况的双重内涵。
1 男女大别礼教墙
自先秦时代始,“礼”便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男女大别”为基础,将两性分别归属于“内外”两个生存空间,所谓“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①p335正如《国语﹒吴语》中载曰:“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见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阖左阖,填之以土。去笄侧席而坐,不扫”。②p410塞门为墙,重礼之甚令人唏嘘。自彼时起,墙便不仅仅是“垣壁也”,更是纲常礼教之墙,以其有形之身置男女于异境,以其无状之影缚两性之自由。换言之,礼制是宗法制下封建家长保护世俗婚姻强有力的武器,也是自主相恋的男女试图挣脱其牢笼桎梏最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
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旨在“止淫奔”。所谓淫奔者,即相恋男女未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自相授受、私定终身的“逾礼”行为。有史可证,自古私奔者不可胜数。如《左传﹒成公十四年》中载曰“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③p445礼教对婚恋的约束力可见一斑。自“墙”始砌,便踰者辈生。亦正是缘于此,白居易以诗谏世人。但值得肯定的是,白朴的《墙头马上》虽题目缘于《井底引银瓶》,但其旨意却与之大相径庭。
《墙头马上》讲述了一段痴情男女与“墙”博弈的爱情。尚书之子裴少俊代父买花于洛阳,与总管之女李千金“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厢“落红踏践马蹄尘”,那厢“手拈青梅半掩羞”。一墙之隔,咫尺难近。可谓墙为媒人亦为阻,上墙两厢悦,下墙不同天。
在中国文学史上,为墙所阻的爱情屡见不鲜。《诗经﹒郑风﹒将仲子》中畏于父母威严与严苛的礼教,苦劝情郎:“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⑤p111再者,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欲与张生密约,故由红娘传诗,启其踰墙而至,却又因内心真情与守礼的抉择中几经徘徊。不同于此二人的软弱被动与消极矛盾,李千金大胆主动地传情于裴少俊,且寄诗以约佳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裴李二人不但以踰墙的方式克服了实际空间上的困难,亦以“逾礼”的方式挑战了礼教的尊严。不料佳期被撞,二人据理力争,遂学卓文君夜奔相如而说得嬷嬷心软而放其归之长安。
正如《诗经﹒鄘风﹒柏舟》中所呐喊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⑤p65。不得不说,私奔是礼教压制下不能婚姻自主的男女为保护自主婚姻所采取的无奈之举。而在和现实与礼教的双重壁垒的较量下,《墙头马上》在前两折实现了阶段性胜利,裴李二人选择义无反顾的私奔,给予世俗婚姻一记重拳。
2 阳台路上雨云墙
郑光祖在其翘楚之作《倩女离魂》中借倩女之口道出男女婚恋路上的另一道“墙”,即“俺娘向阳台路上,高筑起一堵雨云墙”⑥p11。剧中倩女与王文举本有婚约,且二人互生情愫,怎奈老夫人蓦然搬出“三辈不招白衣秀士”的名由横加干涉。换言之,这堵墙便是世俗婚恋中的“门当户对”的观念。
“门当户对”的观念始于宗法制确立的西周,为确保家族兴旺,以尊卑考论姻亲,逐渐演化成社会观念中衡量男婚女嫁条件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白朴的另一剧作《东墙记》中,马文辅与董秀英亦是有婚约在前,无奈门第不等,不得不考取功名,以求得两家门当户对,唯有如此,方能成全自己的爱情。
不言而喻,《墙头马上》中的一双儿女在勇敢追求幸福的路上自然也受到了“这堵墙”的阻挠。在剧作的第三折中,裴李二人奔赴洛阳后,隐居于裴家后花园中度得七年光景,“过了些不明白好天良夜”,虽诞下一双儿女,却不知“甚日得离书舍”。不想适逢清明节令,尚书游园惊好梦。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私情来往,其罪逢赦不赦”。李千金被误认作淫奔娼妓,绝非“门当户对”的上乘佳妇,难之以“玉簪磨针、银瓶取水”,最终以畏于父命的裴少俊修书出妻赞结。
显然,裴尚书之于李千金的不满,较之私奔之举,料其出身于“娼优酒肆之家”者更甚。当然,在他看来,也正是那般低贱之人方会行淫奔之事。其实,从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也正是裴尚书之于对“门当户对”的执着追求,方给予戏剧第四折中峰回路转的契机。
棒打鸳鸯后,裴少俊状元及第,“亲捧丹书下九重,路人争识五花骢”,欲寻回爱妻,再续前缘旧梦。而裴尚书亦方知李千金乃同僚李总管之女,不但实属官宦之家,且之二人此前亦早有结秦晋之意。一来爱子高中榜首,二来亲家门楣相当,如此这般,于是戏剧反转。“一个是八烈一个是八烈周公,一个是三移孟母。我本是好人家孩儿,不是娼人家妇女,也是行下春风望夏雨。待要做眷属,枉坏了少俊前程,辱没了你裴家上祖!”李千金难以释怀当初休弃之辱,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裴氏父子拒于千里。却又拗不过一双儿女膝下央求,最终一家人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
静心思之,其实这段姻缘在与“保守派大家长”的博弈中得以再续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者门当户对,二者状元及第。前者是后者的结果,而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换言之,只有符合了裴尚书之流的价值观念,所谓自主的婚姻才能得见天日。在白朴的另一剧作《东墙记》中亦是如此。白朴似乎对“墙”这一意象情有独钟,《东墙记》亦是讲述了一段以墙为媒的爱情,不过角色颠倒,此番为书生难配小姐。马文辅与董秀英由双方父亲自幼定亲,不料秀才父母双亡,前往松江府问亲,投宿于董府隔壁人家。秀英游园散闷,恰巧马文辅立于东墙赏花,二人一见钟情。即便有婚约在前,无奈书生家道中落,故不能“门当户对”,难成“白衣女婿”。不难猜测,马文辅果中金科,方与秀英破镜重圆。再如《西厢记》亦是如此,不做赘述。
所谓“阳台路上云雨墙”,门第观念反远胜于礼教约束,因为面对这一重阻碍,相恋男女往往会被迫妥协。而逾越此墙的唯一出路,便是考取功名。只有状元及第,方能实现门当户对,或还能得“皇上赐婚”这一“尚方宝剑”,这也正是李千金得见裴少俊前首先关切其“穿着甚么衣服”的原因,显然,若是身着官袍则困境得解,不然则回天无力。其实,反面观之,这般妥协,并非绝对的软弱,以退为进,何尝不是保护自身爱情的方法,时代的局限让他们难以横跨世俗的门槛,毕竟生存的现实性让他们难以安放自主的爱情。其实,并非仅是白朴,元杂剧作家的“科举情节”显而易见,这并非仅是作者的保守,而是时代使然。
[1]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5.
[2] 左丘明.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10.
[3] 白朴.墙头马上[M].吉林:长春出版社,2013.
[4]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45
[5]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5,111.
[6] 郑光祖.倩女离魂[M].吉林:长春出版社,2013:11.
刘运巧(1989-),女,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向。
G41
:A
:1672-5832(2017)09-0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