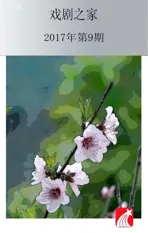《可以吃的女人》中的抵抗话语
2017-11-16赵琪
赵 琪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30)
《可以吃的女人》中的抵抗话语
赵 琪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30)
在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中,女性的身体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含义,是男女两性权力角逐和权力抵抗的场域。《可以吃的女人》正是这样一部处处弥散着性别政治与反抗话语的文本。小说中女性的厌食、逃离和拒绝传统婚姻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操控行为而迸发的抵抗话语。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阐释小说中的女性如何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试图打破两性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从而构建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
抵抗话语;厌食症;凝视与逃离;女性身体
作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特伍德从不否认自己对身体的关注,她曾经表示:“身体是我始终关注的概念”(Princeton, 1990: 187)而权力与身体的关系更是她关注的焦点。但她的权力观关涉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关系,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微观权力”。就男女两性的关系而言,由于女性长期以来在经济、人格等方面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则表现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统治与反抗,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恩斯丽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主体地位,利用自己的身体,有意或无意地对自己的从属地位进行反抗。前者在婚期临近时突然出现了厌食倾向,面对未婚夫彼得的凝视,联想到自己婚后将要落入结婚生子,彻底失去自我的境况,于是数次逃离;后者则思想激进,不愿接受传统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角色,千方百计利用男人,实现了做母亲的梦想。
一
在阿特伍德多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面临人生际遇的重大改变之时饮食习惯常会发生改变,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厌食倾向,如《可以吃的女人》中的玛丽安,《神谕女士》中的琼,以及《使女的故事》中的奥芙雷德等。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主人公玛丽安大学毕业后工作与爱情似乎都很顺利,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未婚夫彼得是一个正派英俊,前途光明的律师,“他后来告诉我,他喜欢我就因为我有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女子绝不会企图对他的生活横加干涉。”“我们彼此采取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这样我们就相处得很好。自然我得顺着他的脾气,但所有男人无不如此。”(阿特伍德,2008:69)彼得的择偶标准在父权社会中极具代表性,正如约翰·罗斯金所说:“女性的权力不是用来统治的,不是用于战争的,她的智力也不是为了创造发明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甜蜜地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需要。”(Ruskin, 1899: 23)取悦男性,服务于家庭,“屋中天使”般的女性没有言说的权力,其存在的意义是工具性的,即为家庭和男性服务。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无力掌控,她能控制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自己的身体。(吉尔伯特,2008:497),作为一种反叛行为,厌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传达出女性通过禁食和饥饿与男权社会抗争,并借此表达语言无法表述的潜意识。玛丽安对食物的排斥始于一次与彼得的聚餐,目睹彼得切牛排的行为,她的头脑中出现了活牛排队等着被宰杀的血腥场面,顿时觉得眼前的牛排难以下咽,而彼得却吃得津津有味。餐桌边的玛丽安把彼得的切牛排行为视作“间接暴力,心灵暴力”,暴力受害者显然是毫无反抗能力的牛,玛丽安由此联想到了自己的前途,“玛丽安越来越将自己认同于被消费的物品,导致她成为自己的受害者”(Palumbo,2000:74),这种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感在婚期将至时达到顶点。“我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了,连橙子汁也不行。事情终于发展到这一地步了……一切食物都被排除在外了……”(阿特伍德,2008:318)玛丽安对食物的拒绝意味深长,是一种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依附地位的无意识的抵抗策略。通过对异己的食物的拒斥,主动挨饿,女性企图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摆脱男权社会的藩篱和拘囿,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小说末尾,玛丽安做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自称这人形蛋糕是自己的替身,当作圣餐一般恭恭敬敬地献给彼得,请他吃掉,“毁掉、同化自己”(阿特伍德,2008:337)最后玛丽安吃掉了蛋糕的大部分,将自己的化身吃掉,吃者与被吃者都回归了玛丽安的身体,她的食欲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人形蛋糕被自己吃掉,与彼得分手,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来说,玛丽安都摆脱了被消费、被控制的命运,也暗示着对传统女性被动身份的拒斥和反抗。
二
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照相机、望远镜、摄像机等意象反复出现,如《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彼得爱好摄影,《浮现》中的大卫随身带着他的摄像机,《肉体伤害》中的保罗拥有一架高倍望远镜,甚至短篇小说《真实蠢故事》中也多次出现男学生利用望远镜偷窥女服务员的情景描写。在这些作品中,代表高科技的照相机等主要用来凝视、窥探,甚至监视女性,而技术和设备的拥有者都是男性。科技的发展使男性监视女性的权力进一步升级。这种不平衡的权力配置必然招致女性的反抗,而出逃是女性表达自己抵抗话语的主要方式。阿特伍德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Literature)里曾说:“如果说文学中的动物永远是象征,在加拿大的动物故事中它们经常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Atwood, 1972: 71)在男性面前,动物和女性都处于受害者地位,动物面临男性猎枪的威胁,随时有丧命之虞;女性则在男性的照相设备前被摆弄和操纵,成为被审视的客体。小说中玛丽安的逃离一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彼得向伦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射杀兔子,并将其开膛的血腥场面时;感觉自己就是彼得的猎物,她必须马上逃离,否则也将被射杀、开膛并拍照,落得同兔子同样悲惨的命运。对自己命运的恐惧促使玛丽安在马路上狂奔起来,而彼得则开车追逐,场面与猎人追杀猎物惊人的相似。这次出逃的结局是以“猎物”的束手就擒告终,玛丽安被彼得“接住”了;第二次逃离发生在伦的家里。当两个男人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相机的功用时,玛丽安“发现在床铺和墙壁之间有条黑洞洞的缝隙,那里凉飕飕的,看来挺舒服……一分钟过后我已经从床铺和墙壁之间的狭缝中溜了下去……”(阿特伍德,2008:87)潜身于床底下是玛丽安是对自己即将到来的主妇身份的否定和忤逆,然而这次出逃仍然以失败告终。在模糊的意识到自己即将跌入到彼得的圈套中,成为他的猎物(妻子)后,玛丽安实施了两次出逃,“但究竟逃脱了什么,或者要逃到哪里去,我并不清楚。尽管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干吗要这样做,至少我已经付诸行动了。”(阿特伍德,2008:91)第三次出逃则发生在彼得的单身派对上。派对上当彼得举起相机瞄准她的时候,玛丽安忍不住惊恐地尖叫起来。在得知彼得还没有给她拍照片后,她决定“趁早脱身”,当她在雪地里奔跑的时候,时刻担心彼得会尾随:“他也许静悄悄地在后面追赶着,时机一到就下手,就像他在厅里静悄悄地盯在客人身后抢镜头那样。这个黑色的射手隐藏在伪装的后面,一直全神贯注地瞄准着她,等她走到靶心当中来,这是个手上拿着致命武器的杀人狂”(阿特伍德,2008:304)
在高科技工具——枪支、相机的目光审视下,女性被物化、工具化,成为任男性摆弄的物件:“他在掂量她,就像是买了一架新照相机,先要把机子的工作原理摸一摸……”(P182)。值得一提的是,英文中的“shoot”有“拍摄”和“射击”双重含义,而这两重含义都暗示了男性的权力和欲望。男性通过照相设备对女性进行身体的审美消费和控制,正如猎人对猎物的追杀和射击,女性则成为这种视觉暴力的受害者。在这种语境下,玛丽安的逃离作为对彼得权力和控制的抗争手段已经不言自明了。
三
约翰·兰登·戴维斯曾警告妇女说,“当人们不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不为人所需了。”(伍尔夫,2014:122)将女性工具化,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很多女性长期浸淫在这种极端男权主义观点中,并自觉将其内化,默默接受了生育工具这一角色。玛丽安就是一个例子,她“从高中时就知道自己以后会结婚生子,因为人人如此”。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性恩斯丽则不同,她是主人公玛丽安的室友,思想激进,反对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想要自己的孩子,却不想承担婚姻的责任,因此她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助力其完成要孩子的任务。在对伦进行考察后她得知:“他父亲上过大学,据我所知,他家里没有低能儿,他也没有什么过敏病史……他是搞电视的,那就是说他身上一定有些艺术家的气质。”(阿特伍德,2008:100)恩斯丽把男人当成生育工具,在为自己将来的孩子选择父亲时精心挑选,考虑到外貌、遗传和气质等方方面面,这不得不说是对男权社会的反讽和戏谑。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后恩斯丽果然成功怀孕,同样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恩斯丽的反抗更加彻底和具有颠覆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吃的女人》中充满了男女两性间钳制与抗争,凝视与逃离,消费与厌食等二元对立话语。两性关系是充满权力之争的政治关系。性别政治无所不在,渗透在文本的主题和细节中。面对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女性唯有以身体为抵抗,从而避免被消费、被吃的命运,为重构女性的主体意识贡献一己之力。作者阿特伍德也以文学创作为手段,表达了自己为女性的权力和平等地位而发声的政治诉求。
[1]Atwood,Margaret.Conversations,ed.Ingersoll,Earl G. Princeton[M].Ontario Review Press,1990.
[2]Atwood,Margaret.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M].Toronto: Anansi Press,1972.
[3]Palumbo,Alice M.“On the Border: Margaret Atwood’s Novels” Margaret Atwood: Works and Impact[M].ed. Nischik, Reingard M., New York: Camden House,2000.
[4]Ruskin,John.“Of Queens’ Gardens,” Seasame and lilies[M].New York: Charles E.Merrill,1899.
[5]丁林棚.阿特伍德小说中“潜入地下”主题的反复再现[J].国外文学,2002(1).
[6]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吴晓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7]黄新辉.华裔女性文学中的食物叙事与性别政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2).
[8]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以吃的女人[M].刘凯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桑德拉·吉尔伯特.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0]王韵秋.隐喻的幻像——析《可以吃的女人》与《神谕女士》中作为“抵抗话语”的饮食障碍[J].国外文学,2015(4).
[11]张海兰.《可以吃的女人》中女性身体的抵抗[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2).
[12]张雯.身体的囚禁,精神的逃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I106.4
A
1007-0125(2017)09-02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