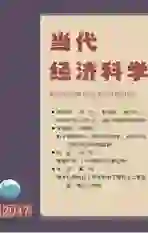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
2017-09-25尹雷杨源源
尹雷++杨源源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关键词: 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数量型; 价格型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7(04)-0019-10
一、 引 言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维持经济总量大体平衡。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分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目标之间既一致又有矛盾,即存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状况,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就是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克服“短期内”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以改进经济的“跨时期效率”[1]。如果经济能够以较高速度平稳增长,同时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社会就业状况得到改善,即表明宏观经济调控較为有效;反之,经济在“短期内”大起大落,则说明宏观经济调控效率较差。宏观调控目标的宽泛化虽然会给予相机抉择更大灵活性,但目标越多会导致目标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并且,不同时期目标的变化也会产生动态不一致问题,这些均会显著降低宏观调控效率[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充分展示出灵活性和针对性,货币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直被央行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两大类: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货币政策传导和执行依赖于所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效果和货币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选择怎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才能产生最佳政策效率,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复苏不及预期。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强调未来宏观调控应以“盘存量,控增量,提效率”为主要着眼点,财政政策要更有效,货币政策要更灵活;继续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注重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率。“政策效率”成为焦点,并已频繁进入中国政府文件之中。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决策部门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效率,注重宏观调控提质增效的转变,力图通过效率调控摆脱政策调控有效性不佳的窘境。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推动下,政府决策层要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博弈中寻求平衡,如何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明确何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政策效率,有利于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作出正确的决策,更精准有效地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鉴于此,本文以效率视角为切入点,试图探寻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以克服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研究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问题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也是我国政府部门未来关注的重要命题。首先,从效率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为宏观调控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向,推动财政货币政策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其次,研究货币政策效率问题,是对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框架的完善与发展,破解政策困境,助力宏观调控提质增效,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 文献回顾
有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最早可追溯到Poole提出的“普勒规则”,这一规则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以政策工具作用于宏观经济效果以及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作为判断标准。沿用这一规则,诸多学者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主要是基于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大小作为政策工具优劣的判断标准,进而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3]。Taylor将利率设定为通货膨胀和产出对其自然水平偏离的反应函数,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名义利率,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对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进行判断[4]。Walsh认为当货币需求不稳定时,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好;而当短期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总支出时,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效果更好[5]。Svensson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通货膨胀目标制模型转化为一个动态优化问题,构建了最小化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成本的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从而得到了货币政策的最优反应函数,即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进而参照调控效果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选择[6]。国内学者,例如赵昕东等、陈飞等、王君斌等、陈浪南和田磊通过选取宏观经济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考察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效果[710]。Zhang、马文涛、胡志鹏、刘喜和等、卞志村和胡恒强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进而甄选我国最优货币政策工具[1115]。伍戈和连飞结合中国现实特征,运用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模型,比较混合规则、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下的政策效果[16]。
继基于调控效果问题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改善视角考察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沿用Woodford提出的关于福利损失的评价模型标准,即通过估算产出缺口和通胀率波动来评估社会福利损失,认为最优货币政策是使得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17]。Cecchetti等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际数据模拟得到最优货币政策操作,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现实数据的差异作为判断现实货币政策操作范式优劣的标准。他们认为若二者相差不大,表明现实货币政策在该时期内福利损失较小,反之则认为在该时期内福利损失较大[18]。Hoffmann和Kempa在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利用Poole的分析框架,在受到外部冲击后发现在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要优于利率工具[19]。国内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大多也沿着福利思路展开。刘斌在估计混合模型基础上以福利为基准,通过随机模拟得到最优前瞻性区间和最优前瞻性货币规则,认为前瞻性规则优于其他规则[20]。赵伟等运用扩展的普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进行展开研究,认为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要优于数量型操作,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更为明显[21]。奚君羊和贺云松、王详和苏梽芳、伍戈和连飞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下,运用福利损失函数和脉冲响应方法研究了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研究发现利率规则要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2223,16]。endprint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学者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当前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发现科学合理地评估何种货币政策工具最优问题,重点是考察其作用宏观经济的效果、效益(福利)与效率三个方面。然而,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当前研究主要从效果与效益两个方面展开,鲜有基于效率视角研究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这也是相关研究需加强之处。鉴于此,本文将从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视角去分析我国货幣政策工具选择问题,首先尝试构建包含了两种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与价格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采取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然后,结合动态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结果与宏观调控效率数值分析;最后,系统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冲击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工具的调控效率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基于中国实际经济运行数据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两种货币反应规则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已有基于新凯恩斯模型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具有主观色彩的校准方法;二是通过构建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函数以从效率视角考察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这可能是以往研究尚未涉及的,本文基于效率函数视角的分析可丰富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三是研究视角丰富,本文综合采用动态脉冲效应模拟、预测方差分解、效率函数分析以及政策乘数分析以全面评估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研究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三、 基准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本文所构建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主要包括三类经济主体:家庭、厂商和中央银行。家庭部门通过供给劳动、消费商品以及持有货币和债券,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贴现值;厂商部门在商品市场上销售产品,使其利润最大化;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名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稳定宏观经济,使经济在一个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下平稳运行。
(一)总需求:新凯恩斯IS曲线
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t、实际货币余额Mt/Pt,以及劳动时间Nt以最大化其终生效用:
为重点比较货币政策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熨平经济周期以及调控宏观经济效力的差异,本文对模型进行简化,假定消费Ct为以社会总产出衡量的广义消费,也即Yt=Ct。消费由不同垄断竞争厂商生产的连续统产品cj(j∈[0,1])构成,对于进入家庭效用函数的消费品构成和消费品总量价格指数,本文采用CES函数形式:Ct=∫10c(θ-1)θjtdjθ(θ-1),Pt=∫10p1-θjtdj11-θ,θ>1为单个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家庭面临如下跨期预算约束为:
其中,Bt为代表性家庭一年期债券持有量,Πt为从企业获得的真实利润,Wt、Rt分别为名义工资和毛利率,β为主观贴现因子,σ、b、η分别为跨期消费替代弹性、货币需求利率弹性和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倒数。
在家庭预算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家庭的期望效用函数依次可得一阶最优跨期消费配置、最优货币持有、最优劳动供给方程为:C-σt=βRt-1EtPtPt+1C-σt+1;γMtBt-bC-σt=Rt-1Rt;χNηtC-σt=WtPt。对数线性化家庭效用函数一阶最优条件,得到如下形式:
其中,t=t-ft表示产出缺口;dt=ρtdt-1+εdt表示总需求冲击,εdt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相互独立正态分布。
(二)总供给: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考虑到模型未考虑家庭投资行为,本文假设代表性厂商j遵循以下形式的生产函数:Yjt=ZtNjt,其中Zt为外生技术进步。厂商通过选择劳动要素最小化其成本函数:minNt(Wt/Pt)Njt-φt(Yjt-ZtNjt),其中φt为拉格朗日乘子。优化求解可得企业真实边际成本为MCt+i=φt=(1/Zt)(Wt/Pt)。根据Calvo黏性价格模型[24],本文假定每期有1-ω比例的企业可以调整其价格,其余ω比例的企业无法调整产品定价;参数ω度量了名义刚性程度,其值越大表示每期调整价格的企业越少。据此粘性价格假定,总量价格水平的演进形式即为:Pt=ωPt-1+(1-ω)P*t,其中P*t表示所有在t时期可调价厂商的最优新定价格。对总量价格水平的方程对数线性处理可得:
Gali & Gertler、卞志村和高洁超等认为兼具前瞻型和后顾型特征的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更符合现实经济运行特征[2526]。为此,本文假设经济中存在前瞻型和后顾型两种类型的调价厂商,其中前瞻型厂商所占比例为1δ,后顾型厂商所占比例为δ。
对于前瞻型厂商,本文假设其调价时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最优价格Pft:Et∑∞i=0ωiβi(Ct+i/Ct)-σ(Pjt/Pt+i-MCt+i)Cjt+i,其中厂商面临的需求函数满足Cjt=(Pjt/Pt)-θCt。优化求解即可得最优价格
对前瞻型厂商调价方程对数线性化处理可得:
区别于前瞻型厂商,后顾型厂商依据简单原则调整价格,其新定价格为上期调整价格与上期通胀率之和:Pbt=P*t-1+t-1。对后顾型厂商调价公式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可得:
由此,市场新定价格指数满足:
假定稳态时通货膨胀率为0,由(7)、(8)、(9)、(10)式以及边际成本方程可得通货膨胀对其稳态偏离的表达式,也即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方程:
πt=k1Etπt+1+k2πt-1+k3t+st
(三)中央银行的决策问题
虽然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广泛认为,今后央行应逐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但有不少研究认为央行在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的同时仍不应放弃数量型调控[15,2728]。为此,本文立足宏观经济运行现实,在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基础上系统探讨货币政策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以期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提供有效参考。
参照马文涛[12],本文假设价格型货币政策满足具有前瞻性预期的泰勒规则形式:endprint
其中,φi∈(0,1)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平滑系数,φiπ>0和φix>0分别为利率对通胀预期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ζit为外生利率冲击,ρi∈(0,1)为外生利率冲击一阶自回归参数,随机冲击υit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相互独立正态分布。同理,本文将数量型货币政策设定成如下形式:
其中,m∈(0,1)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平滑系数,mπ>0和mx>0分别为货币供给量對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的反应系数;ζmt为外生利率冲击,ρm∈(0,1)为外生货币供给冲击一阶自回归参数,随机冲击υmt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相互独立正态分布。四、 参数设定和模型适用性
(一)参数校准
本文在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前,首先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校准。校准的参数主要来自有关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经验文献和宏观数据,同时在对参数校准的过程中,保证了模型存在唯一稳定均衡解。对于居民跨期贴现率,本文借鉴马理和娄田田[29]取β=099。对季度稳态名义利率值,本文取iss=1/β-1=001。参照Zhang[11],取跨期消费弹性倒数σ=2,取货币需求利率弹性的倒数b=313。对于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参数,本文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进行校准,取k1=053、k2=01、k3=06。
(二)货币政策参数估计
本文分别假定经济中存在价格型以及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基于中国现实经济运行数据对两种规则进行估计,并据此比较二者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和宏观调控效率。为避免参数校准的主观性和研究过程中参数的非可变性问题,本文采取贝叶斯方法对主要分析的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参数进行估计。即给定先验分布,然后基于MCMC模拟方法进行MH随机抽样,得到后验分布。估计过程中本文选取的观测变量主要包括名义利率、名义货币供给量、产出、预期通货膨胀率。由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仅自1996年才开始公布,我们取观测变量样本区间为1996—2015年。由于本文模型为封闭经济模型,因此需剔除GDP中进出口部分以得到产出数据。观察产出数据可知其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故在模型估计前先进行季节调整。对于预期通胀率,本文假设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形式满足理性预期特征,即Et-1πt=πt;通过对季度内各月通胀率取均值即得季度通胀率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7天期银行同业拆借量和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可测算季度加权平均利率:
其中,i1、i2、i3分别为各季度内第1、2、3月的平均利率,f(t)为各季度内对应月度的拆借交易量。
对于所有观测变量,均取对数并用HP滤波过滤后再用以估计参数。参照郭豫媚等[30],我们假定货币政策平滑系数φi、m均服从贝塔(Beta)分布;假定货币政策变量对通胀预期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弹性系数φiπ、φix、mπ、mx均服从正态(Norm)分布;假定外生货币政策冲击一阶自回归参数ρi、ρm均服从贝塔(Beta)分布。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先验均值,本文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近似取φi=07、φiπ=016、φix=077;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先验均值,本文根据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近似取m=07、mπ=01、mx=014。
(三)模型适用性判断
本文在以上部分采用贝叶斯方法对我国数量型货币调控和价格型货币调控下的政策行为参数分别进行了估计,但这一过程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为此,在对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调控效率进行模拟比较分析之前,本文参照杨源源和于津平、朱军[3132],进一步基于后验估计概率讨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范式属性。根据前文,我们简记价格型货币调控框架为模型M1,数量型货币调控框架为模型M2。根据贝叶斯法则,我们可以计算两个模型后验概率的比率(Posterior Odds Ratio):
其中,P(M1)表示现实模型为M1的先验概率,ZT为本文贝叶斯估计时所使用的数据集,P(ZT|M1)表示数据集ZT拟合模型M1的后验概率密度。如果后验概率的比率(Posterior Odds Ratio)大于1,则说明模型M2较模型M1更符合中国的数据特征和宏观经济状况。假定模型M1和M2的概率相同,则模型的选择直接取决于相同数据集下各模型的后验边际概率密度①:P(ZT|X),X=M1或M2。表4列出了不同类型货币规则模型下的边际概率密度。
观察表4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何种算法得到的边际概率密度,数量型调控规则情形M2得到的边际概率密度值均最高,这表明数量型货币规则形式的模型设定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最好,价格型货币调控规则对现实经济运行的拟合程度最低。由此,可得到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我国央行主要采取了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操作范式,价格型调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若在货币政策分析时直接参照国外研究假定我国央行遵循以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型调控,将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力的认识产生较大偏误。五、 数值模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分析
货币政策被各国央行作为熨平经济周期的主要手段,因此平抑经济波动的能力是评估货币政策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将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调控效率测度分析以及政策乘数分析等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进行全面评估。
(一)动态脉冲响应分析
将上文校准和估计的经济参数代入本文所构建的一般均衡系统中,据此进行动态模拟分析,可得到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分别面临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时的宏观经济效应,如图1、图2所示。图1刻画了外生总需求冲击分别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总需求冲击造成的通胀和产出偏离更小,也即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能更为有效的吸收总需求冲击。图2刻画了外生总供给冲击分别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总供给冲击造成的产出偏离明显小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但其所引致的通胀偏离更大。这说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易熨平总供给冲击造成的产出波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易吸收总供给冲击对通胀偏离的影响。endprint
进一步考察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发生后通胀和产出偏离收敛到稳态的速度,我们可以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明显快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首先观察总需求冲击对通胀和产出偏离的动态影响路径,可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产出约在18期回归稳态,通货膨胀约在20期收敛稳态;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产出约在11期回归稳态,通货膨胀约在14期回归稳态,较数量型框架分别提前3889%、30%。其次观察总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偏离的动态影响路径,可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产出约在19期后收敛到稳态水平,通货膨胀约在20期后回归到稳态;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产出约在15期回归稳态,通货膨胀约在14期回归稳态,较数量型政策框架提前2105%、30%。这些数据再次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更易消化和吸收经济冲击造成的宏观波动,能更快促进经济收敛于稳态。
① 王国静和田国强[33]指出,对模型不同的设定进行甄别比较有力的工具就是进行边际概率密度的比较,贝叶斯估计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模型设定下的边际概率密度来选择哪种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实际数据,边际概率密度越高的模型,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越高。
图2 不同货币规则下总供给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
(二)经济冲击的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表5、表6分别描述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经济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影响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
如表5所示,在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名义利率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程度分别为342%、168%、9490%。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比较微弱,总供给冲击影响程度最小,而名义利率冲击对产出影响明显。对于通货膨胀而言,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名义利率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程度分别为069%、627%、9305%。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比较微弱,总需求冲击影响程度最小,而名义利率冲击对物价影响明显。这一结果表明,产出和通胀的波动主要表现为名义利率调整的影响,外生总需求、总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价格型货币政策能较好抵消外部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
进一步考察表6,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名义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程度分别达7176%、2805%、018%,三种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的贡献程度依次为7781%、2192%、026%。这一结果表明,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较易引致产出和通胀波动,名义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微弱。通过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下产出和通胀波动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我們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受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的影响,这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宏观经济现实再次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能较好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对经济周期的熨平效果较差,即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相对较低。
(三)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分析
本部分通过动态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并基于Krause所构建的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函数[34],进一步考察与估算两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分别面临总需求、总供给冲击时的调控效率,以此遴选出最优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函数表达式为:
根据Krause对货币政策效率函数(EMP)概述,其测度值越大,货币政策调控效率越高,表明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可以更有效地吸收总供给或总需求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34]。
表7刻画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分别吸收和消化总供给、总需求冲击的能力。可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其货币政策调控效率(EMP)值均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亦即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更高;但EMP值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应对总需求冲击时的差别,此时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率约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9729倍(前者为33272,后者仅为00342),而二者应对总供给冲击时的效率则较为接近(价格型货币政策为07487,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03674)。进一步分析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各自面临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的货币政策效率值,不难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应对总需求冲击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明显高于其应对总供给冲击的能力,约为其444倍;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降低总供给引致经济波动的能力远高于其应对总供给冲击的能力,约为其1074倍。
根据实证结果再结合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进过程(见图3)。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10%左右,但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最高达到15%的增长率,最低处于38%的增长率。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波动幅度也较大,如1985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但在1988年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随即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以控制通胀,结果导致经济迅速下滑。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席卷下,1998年起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在此采取多项扩张性举措,但收效甚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央行果断降息降准,国内经济探底回升,但却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CPI持续处于5%左右。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并步入“三期叠加”的深入调整时期,在稳健货币政策调控下我国货币供应增长较快,但经济增速却不断下降。2014年M2增长122%,GDP增长73%,2015年M2增长133%,GDP增长69%,CPI长期处于2%区间徘徊。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特征显露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时常盯丢,并出现了顾此失彼症状,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不佳。根据图中走势,不难发现我国物价、GDP走势在部分时期与货币政策执行方向呈现非一致性,尤其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例如,在1987年至1989年时期,M2下降,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部分时期M2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出现较大幅度背离,如1987至199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图中走势显示,虽然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功效也并不显著,但其关键原因还是我国多年来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利率走廊不通畅。endprint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使用央行福利损失方法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进行评估。参照郭豫媚等[31],央行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及参数设定如下:L=Var(x)+μVar(π),其中μ=05。表7中的测算结果表明,无论面临何种冲击,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的社会福利损失值最小,也即价格型工具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占优于数量型工具;从单个货币政策工具来看,价格型货币工具消化总需求冲击的能力最强,数量型货币工具则更易消化总供给冲击引致的经济波动。这与基于EMP值的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分析结论一致。为此,综合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分别面临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时的调控效率和央行社会福利损失情况,我们认为当经济主要面临总需求冲击时,中央银行应主要采取以价格型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而当经济主要面临总供给冲击时,中央银行可考虑搭配使用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以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合力作用。
(五)货币政策响应乘数分析
为增强本文关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率评价研究的深入性和广泛性,在分析两种货币政策机制降低外部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所引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
本部分主要参考Leeper et al[35]测算了20期内名义利率、名义货币供给冲击分别对产出的价格调控的累计响应弹性乘数,具体如表8所示。可发现,基于政策响应乘数的分析亦表明,名义利率冲击对产出和价格的调控效果均远高于名义货币供给调控。为此,当宏观经济偏离稳态水平抑或经济周期发生时,中央银行应首先采用以调整名义利率为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
六、 结论与启示
在当前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新常态下,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主要经济体复苏不及预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并且,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策调控效果不佳,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在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冲击下,创新与完善调控方式、遴选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将有助于货币调控提质增效、促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不同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估计;然后,通过对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工具进行动态脉冲响应、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最后,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函数,系统考察了经济面临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情形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率。
综上所述,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1)贝叶斯后验估计表明,1996—2015年間我国央行主要采取了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操作范式,以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型调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故单纯基于价格型货币框架的分析难以真实反映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实践。(2)动态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总需求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能更为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冲击,总供给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易熨平总供给冲击造成的产出波动效果更优,且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明显快于数量型框架。(3)基于预测方差分解结果比较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程度,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4)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公式进行测算,我们发现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还是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值均高于数量型工具。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新常态经济下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坚定不移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第二,寓改革于调控之中,进一步疏通和完善价格型调节和传导机制,探索利率走廊机制,降低私人部门对央行利率调整的反应粘性。第三,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宏观调控要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多重目标,可以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政策调控的取向与基本要求。第四,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处于基本完成的初期,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还不健全,央行在此情形下还应注重加强预期管理:一是加强与市场的信息沟通,特别是事前沟通与事后解释及时公布货币政策相关操作及意图;二是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强央行的独立性,保障政策制定的客观性与专业性。参考文献:
[1] 陈建斌, 郁方. 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的一个数量评价: 1985—2005年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7(9): 1323.
[2] 陈彦斌, 刘哲希, 郭豫媚.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问题与转型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1): 106112.
[3] Poole W. Optimal cho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in a simple stochastic macro model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 197216.
[4] Taylor J B.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R].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993, 39: 195214.
[5] Walsh C E. Speed limit policies: The output gap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265278.
[6] Svensson L E O. Inflation targeting: Should it be modeled as an instrument rule or a targeting rul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6(4/5): 771780.endprint
[7] 赵昕东, 陈飞, 高铁梅.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7): 103106.
[8] 陈飞, 赵昕东, 高铁梅.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2(10): 2530.
[9] 王君斌, 郭新强, 王宇. 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选取、宏观效应与规则设计 [J]. 金融研究, 2013(8): 115.
[10] 陈浪南, 田磊.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研究 [J]. 经济学(季刊), 2014(1): 285304.
[11] Zhang Wenlang. Chinas monetary policy: Quantity versus price rules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9, 31: 473484.
[12] 马文涛. 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调控绩效比较: 来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证据 [J]. 数量经济技术研究, 2011(10): 92110.
[13] 胡志鹏. 中国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条件是否成熟?——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2(6): 6072.
[14] 刘喜和, 李良健, 高明宽. 不确定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稳健性比较研究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4(7): 717.
[15] 卞志村, 胡恒强.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5(6): 1220.
[16] 伍戈, 连飞. 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研究: 基于数量与价格混合规则的探索 [J]. 世界经济, 2016(3): 325.
[17] Woodford M.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 Cecchetti S G, FloresLagunes A, Krause S. Has monetary policy become more efficient?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6, 116: 408433.
[19] Hoffmann M, Kempa B. A poole analysis in the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framework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17(5): 10741097.
[20] 劉斌.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及在我国的应用 [J]. 经济研究, 2003(9): 313.
[21] 赵伟, 朱永行, 王宇雯.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1(8): 1326.
[22] 奚君羊, 贺云松.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及中介目标的选择 [J]. 财经研究, 2010(2): 8998.
[23] 王详, 苏梽芳.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与政策规则选择 [J]. 南方经济, 2014(2): 2137.
[24] Calvo G A.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3, 12(3): 383398.
[25] Gali J, Gertler M. Inflation dynamics: 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 44(2): 195222.
[26] 卞志村, 高洁超. 适应性学习、宏观经济预期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J]. 经济研究, 2014(4): 3246.
[27] 谢众. 对当前货币调控工具选配的思考 [J]. 金融研究, 2008(5): 203206.
[28] 肖争艳, 刘哲希, 邓敏婕.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有效吗?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6(2): 5979.
[29] 马理, 娄田田. 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宏观政策传导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5(11): 94105.
[30] 郭豫媚, 陈伟泽, 陈彦斌.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6(1): 2841.
[31] 杨源源, 于津平. 新常态下中国最优货币调控范式选择——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互动视角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2): 7286.
[32] 朱军. 债权压力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互动效应——一个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J]. 财贸经济, 2016(6): 517.
[33] 王国静, 田国强. 政府支出乘数 [J]. 经济研究, 2014(9): 419.
[34] Krause S.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quivalency between the onePeriod ADAS model and the forwardlooking New Keynesian model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6, 13: 540544
[35] Leeper E M, Plante M, Traum N. Dynamics of fiscal finan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0, 156(2): 304321.
责任编辑、 校对: 郑雅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