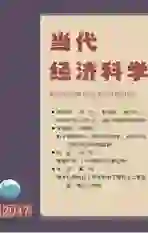服务价值链分工是否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理论及经验
2017-09-25张雨戴翔
张雨++戴翔
摘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并形成相应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借鉴现有文献构造了“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以及“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测度指标,并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绝对地提升了服务出口复杂度,但对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影响不一,在发达经济体表现为正向作用,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上述结果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面临“扩张陷阱”和“低端锁定”的风险和可能,同时也说明如何抓住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发展变化的重要机遇,在实现服务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提升服务出口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关键词: 服务业; 全球价值链; 服务出口复杂度; 低端锁定; 相对复杂度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7(04)-0087-11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不断“软化”,通讯信息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不断推行,服務业发展只能局限于一国国内的传统模式被打破,日益呈现“全球化”和“碎片化”的重要发展趋势,推动着全球贸易结构从传统货物贸易为主导不断向服务贸易方向倾斜。在此背景下,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日益成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包括服务在内的出口贸易,不仅其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出口什么或者说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同样对经济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13]。因此,在实现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如何提升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正成为发展服务贸易所面临的紧要课题。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虽然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扩张速度较快,并于2012年“跻身”世界前三,且2013年、2014年、2015年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三的“大国”,但是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于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因此,如何在实现服务贸易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加快提升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已然成为理论和实际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依托服务贸易发展促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目标。
显然,如何提升服务出口复杂度,关键在于识别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做出的初步尝试和探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较为零星。Cheah着重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4],实证分析了其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一国利用外资规模即人均外资存量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长期且非线性影响。尹忠明等则着重从实证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影响[5],研究结果发现,如同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同样是决定服务出口复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戴翔则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其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影响[6],并总结出比较优势分工原理作用机制、跨国公司基于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的协作机制以及分工演进的动态发展机制三种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主要作用途径。张雨等基于112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7],计量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总之,目前针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问题,学术界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仍然存在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代中强等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探讨了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8]。
实际上,与制造业国际生产分割一样,当前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的实质,也是服务业价值链的全球拓展。因此,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不仅影响着一国服务贸易规模扩张,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同样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遗憾的是,这却是既有研究尚未关注到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着重研究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这一特定视角,分析服务业价值链嵌入程度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首先力图在理论上明晰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影响,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对理论分析所得结论,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第三,在研究设计方面。尤其是指标测度方面,本文借鉴现有文献构造了测度“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的指标,并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进行定量分析。二、 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说
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拓展和演进,本质上就是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阶段,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得各国优势更多体现在服务业价值链条上的某一或某些特定流程和环节阶段。包括服务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本原理仍然遵循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因此,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具有不同要素禀赋国家和地区而言,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会不尽相同。从微观角度看,依据比较优势所进行的服务业价值链全球分解,其实就是跨国公司不断将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进行分解和“剥离”的过程,即将部分提供流程和环节“外包”出去。显然,剥离出去的通常都是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而保留下来的往往就是比较优势的部分。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由于其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其往往在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要素密集度的服务提供流程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分工原理作用下服务提供流程的分解、剥离和外包,必然意味着“保留”下来的环节和阶段更具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即“保留高端的,外包其余的”,从而必然在整体上意味着其技术复杂度水平更高。而对于分解出来的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的承包方来说,也就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企业而言,虽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承接的是“低端”部分,但是与以往在没有服务业价值链分解条件下所从事的服务提供相比,承接的通过“国际梯度转移”而来的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可能更具“高端”特征。因为相比传统分工模式,服务业价值链分解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一种是比较优势的激发效应。所谓创造效应,主要是指原本在整个服务流程上不具优势的,现在由于服务提供流程分解从而在某个环节和阶段上具有了专业化优势,从而出现了比较优势的“从无到有”。所谓激发效应,主要是指服务业价值链的分解往往伴随着服务要素的跨境流动,外来流入的服务要素与当地服务要素相结合激发了新的服务提供能力。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从绝对的角度来看,显然有利于承接方即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endprint
由此可见,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无论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还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从绝对角度看,均有利于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并且,遵循前述变化逻辑,容易理解,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程度越高,也即服务业价值链越是分解,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也就越明显。这是因为,嵌入程度越高,其实就意味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依据“边际原理”分解、剥离和外包出去的服务提供流程越来越相对“高端”,因此自身保留下来的“高端”部分比重就越来越大,从而在整体上必然表现为更高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与此相对应,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承接方来说,由于所承接的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相对“高端”,因此在整体上也必然表现为更高的技术复杂度水平。
当然,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除了具有绝对效应外,从相对角度看,则有可能会呈现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相对走高,而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相对走低的变化趋势。这不仅是因为在比较优势分工原理作用下,发达经济体更加专业化于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高和信息含量高等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放弃原有比较劣势的低端要素含量特征的流程和环节;而与之相对应,发展中经济体则在比较优势分工原理作用下放弃所谓比较劣势的诸如高端要素含量特征的流程和环节,而更加专业化于劳动等要素密集型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因此,这种“反向”专业化选择从相比较的角度看,可能会使得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会相对越来越高,而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会相对越来越低。此外,犹如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一样,发达经济体专业化的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可能面临着更为广阔的技术进步空间,而发展中经济体专业化的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由于其低端特征,面临的技术进步和提升空间则相对有限,甚至可能存在同样的所谓“低端锁定”。上述作用机制也就意味着,从相对变化的角度看,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程度对两类经济体会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假说1:从绝对角度看,无论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均有利于其服务出口复杂度水平的提升。
假说2:从相对角度看,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会相对提升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但却相对降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三、 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测度及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本文着重研究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不言而喻,服务出口复杂度即为被解释变量。至于服务出口复杂度(记为ES)的测算,目前学术界普遍借鉴Haussman提出的测算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1],来测算服务出口复杂度。尽管这一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进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出现了诸多改进之处。但是相对于较为详尽的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而言,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较为宏观且相对粗略,因此将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诸多改进方法拓展运用至服务贸易领域还不太现实。这或许正是为何目前学术界仍然普遍采用Haussman[1]提出的针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的根本原因[2,4,7,9]。考虑到服务价值链分工的影响,采用传统的总值核算法测度服务出口复杂度必然产生偏误进而误判。为此,本文在传统测度方法中引入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以替代传统总值核算法来测算服务出口复杂度。具体而言,首先利用式(1)测算某一分项服务的技术复杂度(记为TSI):
TSIk=∑j(edvajk/EDVAj)Yj/
∑j(edvajk/EDVAj)
(1)
其中TSIk即表示分項服务k的技术复杂度,edvajk代表国家j的服务分项k出口国内增加值,EDVAj代表国家j的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额,edvajk/EDVAj代表国家j服务分项k出口国内增加值在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额中的占比,Yj代表国家j的人均GDP。其次再利用公式(2)计算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记为ES):
ES=∑kedvakTSIk/EDVA
(2)
ES表示所测算的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其中,edvak表示该国服务分项k的出口国内增加值,EDVA代表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额。
2.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即为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因此如何度量一国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程度极为关键。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有关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能够为本文研究提供借鉴。为此,本文借鉴Koopman et al提出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10],测度一国服务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并借鉴Koopman et al[11]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测度“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记为SVS):
SVS=1-[(IVi,r+FVi,r)/Ei,r]
(3)
其中,IVi,r和FVi,r分别表示间接增加值出口部分和国外增加值部分,Ei,r表示服务出口总额。显然,(IVi,r+FVi,r)/Ei,r指标测度值越低,或者说SVS的测度值越高,表明一国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程度就越低。
3.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这一关键解释变量外,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参考现有关于服务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45,7],本文还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如下控制变量,包括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变量(记为FDI)、制度质量(记为INST)、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记为PC)、人力资本变量(记为HU)、人口规模变量(记为POP)、创新能力变量(记为RD)、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记为OPEN)、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记为SERV)以及基础设施变量(记为INF)。其中,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变量为了消除国家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服务业人均外资额存量表示;制度质量采用目前学术界使用较为普遍的世界各国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数据库中的政治风险指数(记为PR)、经济风险指数(记为ER)以及金融风险指数(记为FR)三种指标作为替代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以人均GDP变量表示;人力资本变量采用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表示;创新能力变量采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表示;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以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服务经济总量之比表示;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以服务经济总量占GDP总量之比表示;基础设施变量采用每百人中因特网使用人数表示。据此,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endprint
ESi,t=α0+α1SVSi,t+γZi,t+μt+νi+εi,t
(4)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Z表示前述各控制变量,μ表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ν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变量,ε表示误差项。由于不同变量水平值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为了平抑数据的波动性而又不影响估计结果,对部分变量在实际估计过程中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包括服务出口复杂度(ES)、服务业人均外资存量额(FDI)、经济发展水平(PC)、人口规模变量(POP)等均取了自然对数。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选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这40个国家包括27个发达经济体和13个发展中经济体。样本区间设定为1995年至2011年。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测算要使用到各国服务出口额以及人均GDP数据,这两项数据来自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 Database)。其中,需要指出的是,与现有测度服务出口复杂度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并非使用11大类服务部门1分位层面数据,而是采用3分位层面的分类数据进行测度,因为使用越为细分的统计数据,所得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测算结果也就越精确。测度“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所使用到的原始数据,来自于欧盟支持的11个机构联合体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服务业人均外资存量额、人口规模变量、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所使用的服务经济总量和GDP总量,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测算使用到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服务经济总量等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 Database);人力资本变量、创新能力变量以及基础设施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B Database)统计数据库。作为制度质量替代变量的政治风险指数、经济风险指数以及金融风险指数均来自于世界各国风险指南数据库。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避免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对计量模型中的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关键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在02之下,说明上述计量模型纳入的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OLS估计结果
由于考虑到仅以所选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而展开计量研究,因此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上计量模型(4)进行估计,所得结果报告于表1。
首先,从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第1列至第3列的结果均显示,变量SVS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前所述,由于SVS指数值越低代表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程度越高,因此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再从分样本的回归结果看,第4列至第9列报告的结果同样显示,无论是以发达经济体为样本,
还是以发展中经济体为样本, 相同之处在于,变量SVS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如果进一步比較两组样本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应列的SVS系数估计值大小的话,容易看出,发达经济体样本组的SVS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要略高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的SVS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这一差异性意味着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作用要强于发展中经济体。总之,无论是否考虑到组别之间的差异性,第1列至第9列SVS的系数估计值基本表明,前文理论假说1较好地通过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基于全样本的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其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显著正向作用;无论是以经济风险指数,还是以政治风险指数抑或是以金融风险指数表示的制度质量,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制度质量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关键作用;类似地,人力资本变量、创新能力变量、服务贸易开放度变量以及基础设施变量,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均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之相比,人口规模变量和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虽然为正,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种因素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前述各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因此对于可能的原因,本文不再赘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从分样本回归结果的对比角度看,估计结果发生明显变化的就是人口规模变量和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具体而言,这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中不仅为正且基本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发展中经济体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种差异性可能意味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规模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能够真正转化为市场规模优势,从而对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进而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拉动作用,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规模由于受到收入水平限制未能真正转化为市场规模优势,因而对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够;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规模在发达经济体可能更多的是产业高级化的结果和表现,而在发展中经济体则可能存在着普遍的“低端扩张”现象,甚至存在学术界早已发现的所谓“成本病”现象,因而在两类经济体中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表现出不同的影响。
(二)全样本系统GMM估计结果
对面板数据采用OLS估计法进行计量分析,可能会遭遇扰动项自相关等影响估计结果的不良问题。况且,由于出口贸易通常具有惯性特征,因此服务出口服务度可能也具有持续性影响特征。换言之,滞后一期的服务出口复杂度可能对当期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影响。为此,有必要将滞后一期的服务出口复杂度作为解释变量而纳入到上述计量模型中。据此,可以构造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endprint
ESi,t=β0+β1ESi,t-1+β2SVSi,t+γZi,t+μt
+νi+εi,t
(5)
显然,由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被纳入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中,从而产生了与扰动项的相关。此外,由于服务出口复杂度与部分解释变量间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使用OLS估计法可能产生“动态面板估计偏误”问题。为此,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中除关键解释变量外还包括其他控制变量,因此在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时还有必要对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进行类型选择。考虑到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我们将“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视为内生变量,而将其余控制变量当作外生变量。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均采用稳健估计量。回归估计结果呈列于表2。与此同时,在表2最后几行还给出了模型设定的主要检验结果。数据显示,AR(2)统计量均不显著,表明模型的水平方程误差项并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Sargan检验结果则表明模型工具变量的选择在整体上是有效的。
基于表2呈列的回归结果,基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无论是在总样本组,还是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抑或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滞后一期的服务出口复杂度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并且都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表明服务出口复杂度确实具有“惯性”影响和特征。第二,就SVS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而言,在总样本组和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中均为负,且至少在5%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意味着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再次表明了假说1较好地通过了逻辑一致性检验。第三,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能力、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等变量,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结果与表1相比也未发生本质性改变,意味着上述各变量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同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四,控制变量中的人口规模变量和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在不同组别间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中上述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復杂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中,虽然系数估计值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尚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这一差异性与表1的估计结果基本也是一致的,
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前文已有阐述, 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的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前文理论假说1较好地通过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三)相对变化的系统GMM回归结果
仔细观察前述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SVS的系数估计值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中,要略高于在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这一差异性是暗含了前文理论假说2,即从相对的角度看,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的相对提升,而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的相对提升。当然,对于这一判断,还要展开进一步的计量检验。为此,本文构造了“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指数”(记为RES),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RESi=ESi/∑nj=1wjESj
(6)
其中,当i∈发展中经济时,j∈发达经济体,反之则反是。上述测度公式的含义在于,首先将全样本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组,并分别计算各组的服务出口的加权平均复杂度,权重即为各组内每个国家服务出口额占该组所有国家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在分别计算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的服务出口平均复杂度后,则计算发展中经济体某一国家的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即为该国服务出口复杂度与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平均复杂度之比。同理,计算发达经济体某一国家的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即为该国服务出口复杂度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平均复杂度之比。以RES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为样本组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5)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呈列于表3。
从表3呈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以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SVS的系数估计值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和在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中,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在发达经济体样本组中,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均表明,SVS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对其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组中,第4列至第6列的回归结果均表明,SVS的系数估计值却均为正,且均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对其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这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效果,说明了前文理论预期的正确性,即从相对角度看,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会提升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但却降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此外,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无论是影响的方向性还是显著性,与前述各表均无本质差异,在此不再赘述。唯一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两个样本组中,同样呈现出方向相反的影响效果,即在发达经济体中对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作用。这种变化或许说明了在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发展趋势下,尽管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规模扩张可能面临着重要机遇,但是相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规模扩张可能更多是“低端嵌入”的结果,甚至可能存在着“低端锁定”的风险。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对前述各表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进一步检验,接下来本文再利用关志雄给出的测算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方法[12],重新估算样本期内各国服务出口复杂度,并继续利用式(6)计算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各国服务出口的相对复杂度,据此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5)进行重新估计,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估计结果呈列于表4。endprint
表4报告的结果中,第1列至第3列基于总样本并以ES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第4列至第6列的结果,以及第7列至第9列的结果,分别是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为样本组,并均以RES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将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与前述表1和表2相对应的各列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容易看出,无论是本文最为关注的SVS这一解释变量,还是其他控制变量,虽然系数估计值大小方面略有变化,但就其影响的方向性及其显著性而言,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而就第4列至第6列的回归估计结果而言,与表3对应各列结果进行简单比较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SVS这一关键解释变量,还是其他控制变量,也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总之,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表明前述分析结果是稳健的,也再次说明了前文理论假说1和假说2较好地通过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五、 简要结论及启示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和内容,就是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从而使得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得以拓展。毋庸置疑,各国通过融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获得了服务贸易的快速扩张。本文理论分析认为,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从绝对角度看,对于各国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从相对角度看,会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的提升,却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借鉴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测度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新方法,并首次构造了“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嵌入度”的测度指标,以及“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的测度指标,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在绝对层面上的确有利于各国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然而,从相对变化的角度看,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相对复杂度提升,但却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理论假说较好地通过了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能力、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等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而服务业发展规模变量等对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呈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却呈显著负面影响。因此,综合来看,嵌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在实现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可能面临着“低端嵌入”带来的不利影响,甚至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
上述研究所得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而且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政策含义。尤其是对于亟待转型发展的中国而言,作为外贸转型升级重要内容和方向之一的服务贸易发展,被视为是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培育新增长极的重要着力点。然而,真正实现上述重要目標,其实不仅要在融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中抓住机遇实现规模扩张,更应注重在迈向服务贸易“大国”的同时,提升服务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水平,从而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不断拓展的分工背景下,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全球服务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如此,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才有可能避免重蹈以往备受争议的制成品出口贸易所谓“低端锁定”和“比较优势陷阱”的老路和风险。当然,提升服务出口复杂度并非一蹴而就,应该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其中,技术先行极为关键,即依托技术进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专业化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特色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提供流程和环节的优势和水平,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外包业务比重,如此才能在扩大服务贸易发展规模的同时,实现服务出口“量质齐升”的重要战略目标。当然,除此之外,如何营造有利于服务发展中技术先行的优良市场环境、如何创新服务出口发展模式、如何培育技术先行的市场微观主体、如何借助国际先进要素和创新要素提升服务业发展的技术含量、如何通过提高便利化水平完善财政税收等支持体系等,都是提升服务出口复杂度这一系统工程中需要回答和探讨的关键问题,也是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参考文献:
[1]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1): 125.
[2] Gable S L, Mishra S.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uropes new growth model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5793, 2013
[3] 戴翔. 服务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一项跨国经验研究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5(4): 95106.
[4] Cheah W J.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ffect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J]. Rein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BCUR/ICUR 2013 Special Issue,
[5] 尹忠明, 龚静.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80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4(5): 6674.
[6] 戴翔. 服务业“两化”趋势与我国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战略 [J]. 国际贸易, 2015(5): 6066.
[7] 张雨, 戴翔. 什么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全球112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7): 8796.
[8] 代中强, 梁俊伟, 孙琪.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J]. 财贸经济, 2015(7): 109 122.
[9] 程大中. 中国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国际比较分析——兼对“服务贸易差额悖论”的解释 [R]. 经济研究, 工作论文No.WP456, 2013.
[10] Koopman R, Wang Zhi, Wei Shangjin.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w18579, 2012.
[11]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hi, Wei Shangjin.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w16426, 2010.
[12] 关志雄. 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 [J]. 国际经济评论, 2002(4): 512.
责任编辑、 校对: 郑雅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