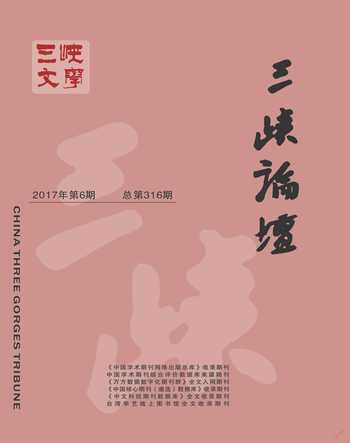土司文化的形态及多样性传承
2017-05-30罗维庆
罗维庆?
摘 要: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阶段的专指,以物质、制度、精神等不同的形态而存在。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形象地表达了土司内心的自我价值期望,以及用这刻意创造的文化,去引导民众对土司权威的认同。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代表着朝廷意志对本民族族众进行治理;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用礼制、习俗规范促进社会有序发展。不同形态的土司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呈现出民族性、地区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多样性传承。
关键词:土司文化;存在形态;相互影响;多样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6-0022-07
土司文化产生于土司统治时期,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阶段的专指,也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在人文领域中遗留的标志。它集本民族的传统、家族、政治等多元文化为一体,涵盖着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强烈的念旧情结与守土情结,体现着特定时代的灵魂与精髓,代表着特定的民族、地区和阶层的生存方式,具有独特的阶级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民族心理及功过是非。这些属性与特点,决定了土司文化具有认同传统、认同地方、认同家族、认同族群和认同国家的多向性,并以物质、制度、精神等形态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呈现出多样性的传承。
一、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
文化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或创造出来的,物质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物质,文化无以表现。此处的物质,是指经过人类有意或无意加工制作出来而非自然的存在物。只有经过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才具有文化,仅有自然存在物,则不具有文化。如泥土不是文化,但青红砖的制作是文化。自然植被不是文化,而园林设计就是文化。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也即如此,是由所在民族创造出来的。
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被誉为“中国的马丘比丘”、“南方故宫”、“全国保存完好的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等。其中的土司衙署、九街十六巷、寺庙牌坊、金石碑刻等,体现着土家族独具特色的創造,在物质形态土司文化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老司城遗址由老司城山水、中心城址及外围遗迹三部分构成。城池位于合称为“三星山”的福石、禄德、寿德之下,称为“三星拱聚”。宫殿群位于城北高端,枕山临水,气宇轩昂,俯瞰着其下的居民区,隐含着面南称王之意。整个宫殿群由高大的城墙围成椭圆状,建筑面积达14000平方米,融土家族传统建筑特色与汉族建筑特色于一体,既有因地形而建造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吊脚楼,也有讲究地基风水源于汉族地区的青砖黑瓦封火墙。宫殿外围墙体用本地赤砂涂为红色,在黢黑的山岩和翠绿的山林衬托下格外显目。以蝙蝠、仙鹿、白鹤、葫芦等动植物形象而体现出的土司“福、禄、寿”思想观念,反应了汉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引导和感染。司城周边高大雄伟的太平山、玉笋山、将军山、麦坝山、金花山、天马山、美女山、仙人山、贺虎山、九肇坡山、送答茄山等,连绵成屏,被称为“万马归朝”,表现了土司无上的威严。为深化和神化这威严,土司借物喻义,对于不朝向司城的飞雅角山头,铸造了一条大铁链将其锁住,其喻意十分明显:即使是山头,不臣服者也应罪之,何况人乎?“万马归朝”的想象是建立在彭氏土司强力统治基础上,它形象地表达了土司内心的自我价值期望,以及用这刻意创造的文化,去引导民众对土司权威的认同。
居民区内有正街、新街、河街、五铜街、紫金街、左街、右街(御街)、鱼肚街、半坡街等九条大街。主要大街都通向宫殿衙署区的正门大西门,显示出土司的崇高地位。各街又被众多巷道相连,仅仅今天所统计的巷名就有:南门、半坡、五铜、雅草、杨士庙、朱家堡、周家湾、城隍庙、张家、润家湾、午门、堂坊堡、王家、西门、陈家湾、秦家等十六条巷。还有狮子口、马蝗口两个重要津渡,称为九街十六巷二口,依山傍水布局井然。以宫殿衙署区为核心,形成蛛网状向外漫延。在外则被东北——西南——东南流向的灵溪河围绕,形成一个半岛状,具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功能。《永顺县志》赞曰:“凭山作障,即水为池……巍巍乎五溪之巨镇,郁郁乎百里之边城。”[1]堪称锦绣之城。
因对山、水、城自然交融的重视,老司城的风景十分优美,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被称为“灵溪十景”,即“福石乔木”、“雅意甘泉”、“绣屏拱座”、“玉笋参天”、“石桥仙渡”、“翠窟晴岚”、“羊峰毓秀”、“龙洞钟灵”、“榔溪夜月”、“铜柱秋风”等。十景均有大量同名诗作,如周惠畴的《福石乔木》、《榔溪夜月》、《铜柱秋风》、《绣屏拱座》,唐寅的《雅意甘泉》,张明的《玉笋参天》,顾清的《石桥仙渡》,许宽的《翠窟晴岚》,谭玉衡的《羊峰毓秀》,安佑的《龙洞钟灵》等,至今在民族研究中仍被多次引用。老司城堪称文化之城。
老司城留有土司时代的大量题名碑刻,其金石铭文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在我国各族土司中居于前列。据《老司城遗址周边遗存调查报告》不完全统计,在45个地点遗留文物多达187件,分为铭文、墓志铭、碑刻、题刻四大类。[2]99-139自老司城逆水而上至吊井岩古城,十余里河道的两岸石壁上,现今仍可辨认的明代土司题刻达十多处,记录了土司们与亲属、宾客闲暇游玩的情况及所作的诗词,是研究土司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史料。铭于后晋天福五年(940)所立“溪州铜柱”之上的“复溪州铜柱记”,全文共2614字,完整记录了五代时期楚国与溪州之间战争、和谈、结盟等化干戈为玉帛的过程,弥补了正史与方志的不足,是研究土家族地域确立及彭氏土司由来的第一手文物史料。重要的土司墓志铭,有卒于明嘉靖壬辰年(1532)九月七日的彭世麒(思斋)、卒于嘉靖甲辰年(1544)五月二十一日的彭宗舜(忠轩)、卒于明隆庆丁卯年(1567)六月十一日彭翼南(侯)等。这些墓志铭的字数均达数千之多,撰写的文体不仅仅表现出当时土司们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还记录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征调、抗倭、献木、土司婚姻等,可信度极高,可以核实家谱和方志的讹误。重要碑刻如《钦命世镇湖广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都督府致仕恩爵王爷德政碑》、《世守湖广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彭公德政碑》等,在歌颂土司的德政中记录了大量的土司政治、经济、刑罚等制度。老司城堪称历史之城。
二、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
土司代表着一种社会制度,既体现民族地区的传统行政职能,又体现中央王朝的专制管理职能。因此,土司与其所属的民族,既有关联性又有区分性。关联性是土司经济利益与本民族紧密相连,作为本民族的上层人物和民族代表,他们被包容在其民族之内,应按民族传统行事,如果没有所属民族的基础,也就没有土司生存的基础。区分性是土司政治利益与朝廷紧密相连,作为朝廷命官,土司游离于其民族之外,当民族传统与朝廷旨意相悖之时,他们必须违背民族传统而遵朝廷旨意行事,共同治理本族民众。因民族地区经济、环境、传统的不同,土司制度表现出的区域政治特色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无论差异如何,其共同点是无疑的,即用代表着朝廷意志的政治制度对本族族众进行治理。政治制度是国家行为主体,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族际关系相互作用的不同、制度设计者利益集团的不同、主体民族执政意识的不同,都会对不同的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出现产生深远影响。
制度形态土司文化的作用,主要是在于民族内部关系的凝聚与融合,但也会根据朝代的变化、君主的更替或土司袭职的不同,相应影响到一些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调整,从而导致民族内部自古以来存在并实行的习惯法产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朝代、新君王所颁布的新法令。如清朝取代明朝后所颁布的剃发令、易服令等,直接影响着不同民族的土司文化的异变。
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统治,虽然意在“以其故俗治”,但为了约束土司们的行为,制定了土司们必须遵行的种种法规和律令,如土官承袭即有一整套可行的规定。不论官职大小,升职、袭职必须进京受职谢恩,“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其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3]土司反叛、不遵法令等,则要从重处罚“或诛、或降职使用”。土司拥有的土地,朝廷明确规定不允许自行典卖,私自典卖者必受严罚。土司拥有的武装,在朝廷需要之时,必须奉旨征调,不如期到达者必受严惩。土司需按期去京城朝贡,如朝贡失期将受严究。朝廷以种种形式告诫土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时警示土司为官的宗旨是“忠君效国”。
土司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区域统治,还会根据统治阶层的需要,制定了一些规则以调整族属关系、维持统治秩序,自行设有不属于朝廷职官系列的自署职官。“司内之员,亲莫亲于护印,而权司、总理次之;贵莫贵于权司,而总理、中军次之。权司、总理、中军,为司职极品。”[4]老司城彭氏土司在对辖区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总司、州司、旗峒、村寨的管理等级和管理体系,由彭、田、张、向、黄、汪六大姓分别统辖永顺宣慰司,南渭州、施溶州、上溪州等三州,腊惹峒、驴迟峒、施溶峒、白崖峒、田家峒、麦着黄峒等六长官司,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峒。土司的亲属,土民亦要敬重有加,“其妻曰夫人,妾曰某姑娘,幼子曰官儿,女曰官姐,子弟之任事者曰总爷,其次曰舍人”。[5]严格的等级是各项制度得以推行和落实的基本保证。
在经济制度方面,因土司没有薪俸,公务支出和生活费用,均在土地收入中解決,所以土司把大量的良田沃土占为“官田”,“凡成熟之地,多择其肥沃者自行耕种,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6]。“官田”由土民耕种,收入全部归于土司所有,其余土地称为“役田”,分配给土民耕种,服兵役者、抬轿者、吹鼓手、舂米者、摆渡者等,也可分得一份“役田”,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土民经土司允许,可开垦一部分山地,由开垦者自行耕种,收获物归自己所有,但必须缴纳一定的实物或银两给土司,称为“秋粮银”。永顺府“所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向来三土司每年秋粮共银二百八十两,永顺一百六十两,保靖九十两,桑植二十四两,皆由土司交纳,虽有秋粮之名,实不从田亩征收。永顺则名火坑钱,民间炊爨,每一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坑相等。所交秋粮,即于此内量行拨解。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择其肥饶者自行种收,余复为舍把头人分占,民间只有零星琦角之地。每年杂派数次,任意轻重”。[7]除了繁重的“秋粮银”外,土司还向土民征收实物。“土司旧例,每年每户,派送食米并鸡鸭肉肘,自土官、家政、总理以及该管舍把四处,断不可缺,虽无力穷民,亦必拮据以供。商贾客人,每逢年节,俱须馈首家土官、家放、舍把、总理等礼物,名曰节礼,倘有不同,非强取其货物,即抄掠其资本。”“查土官向日凡畜养蜂蜜之家,每户每年征收蜂蜜、黄蜡若干,令家政经管,迨日久弊生,每有无蜂之家,因其曾经畜养,俱令买备供给。”[6]
土司均有一支武装,称为“土兵”,其制度也极为严密。“中军辖五营。五营有总旗,旗长次之,旗鼓又次之,千总、把总为弁之末。至若内侍之千总,出入护卫,外委之把总,奉使出差,较之各营千、把,伊则尊焉。司以外,佥事为一房首领,见五营而却卑,临巡抚而民右,职同峒长,权亦无异。署事、马杵,虽曰兄弟,究分低昂。署事次于巡捕,马杵次于署事。各房外峒长,为一峒之主,无征伐之权,有刑名之任,旗长与之敌体。长官又系属员。总之,五营以上,非舍不用,总旗以下,异姓同官。除新、江两峒外,自权司至千、把,贤能则委任终身,不肖则革职另选”。[4]土司对于土兵的选拔极为严格,“初檄所属照丁拣选,宣慰签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银付之。下令曰: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吃此牛首。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其节制甚严,止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皆斩,故凡战必捷,人莫敢撄。”[8]土兵的职能是征调时出征,平时则把守关口,盘查过往行人,捍卫辖地安全。对于土司武功的宣扬,不仅在家谱上比比皆有,而且还铭于金石碑刻之上以图传之万代。如老司城关帝庙内一万历丁亥年(1587)所铸的铜钟,其上铭文曰:“考之志曰:钟,西方之声,以象厥成,谁功大者?其钟大,垂者为钟,仰者为鼎。万历丁亥(1587),予掌篆之次岁也,梦帝锡予以大刀红马,予即刻象,立殿于将军山顶,书其额曰‘神武祠。又蒙神节降护持:酉之役,三战三捷;播之役,捷音屡奏;保之役,十一战十一胜。且旦夕赐佑,魑魅魍魉,莫施阴谋。予蚤无子,又蒙赐之上,题其殿为圣英宝殿,乃命工范铜铸钟鼎,悬于庙,用彰神武,而为之铭:洪惟圣常,惟心天日。默佑于予,魍魉无济。镇我边廷,时和岁利。亿万斯年,彭氏永祀。”
土司社会亦存在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社会组织,如村寨的领导人,主要是村寨民众自行选举出来的,而且这些被选出来的领导人,因能尽心尽力地为民众办事,从而获得大家的推崇和爱戴。但这种民间社会基层组织并不能代替土司行使权利,只有在土司们思考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土司不愿意管理的地方,村寨才能选出自己的组织形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所遇上的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和睦相处,维护地方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在处理本民族的一些社会事务时,这些被推选出来的首领,还往往奔走于本族与邻近民族之间,起到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
三、精神形态的土司文化
倡导礼制规范和促进社会有序发展,是精神形态土司文化最重要的举措。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俗”,即以礼乐制度去教化、同化、风化本族百姓或异族民众。礼乐制度的核心是以哲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等说教形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而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倡导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正是通过这种说教及相关礼仪定式和礼制规范,朝廷得以限制人们的思想,规范百姓的行为,维护礼制的神圣,体现皇权的威严。
土司社会也不例外,永顺土司在其境内以碑刻、墓志铭等形式宣扬礼制。其表象是通过碑刻来记载功德,彰显伟绩,表达对长辈、兄弟生前的孝顺、友爱之心。其实质则是固化家族意识,强化族群意思,以期实现土司社会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如《永顺宣慰使司彭氏祠堂碑记》显扬其彭氏地位的显赫:“我明高皇帝混一中原,鼎革之后,与远臣更始,乃铸铁券,给土田,锡弓矢,敕彭氏都永顺,至是彭氏仍守封疆,赫然为世臣矣”。以朝廷“铸铁券,给土田,锡弓矢”的荣耀,显示彭姓土司“守封疆,赫然为世臣矣”合法性。《钦命世镇湖广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都督府致仕恩爵王爷德政碑》更宣扬“吾永建自东汉,为朝廷南服世臣,迄于今且千载,其间执圭守土,代不乏人。咸以苗蛮之故,用法峻严,服民以威,不以德也,是也治乱相寻,无息肩日。自我恩爵嗣世,天性仁厚,举无失轨,去猛存宽,用贤退吝,易杀戳为鞭扑,而犴狴形消,开入告以听民,覆盆无枉。虑民之荒于业也,而自勤稼穑。恐俗之流于顽也,而申之孝悌。节用以恤民膏,轻赋而苏物力。崇俭抑奢,弋缇之袍不厌,修文偃武,刁斗之警无闻。和邻而睚眦之边衅自弭,乐天而虞芮之质成屡至。凡举措设施,皆以养民守土为事,以故宽仁镇静之恩,生息庶富,甲于诸司。”赞扬“孝悌”、“用贤”“崇俭”、“抑奢”治政的德政。碑文后所铭姓名有中军、旗长、家政、州司、内使等官员,达369人之多。众多的人民为之铭刻歌颂,彰显出土司的地位尊严。
土司礼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隆庆二年(1568),吏部尚书徐阶撰写《皇明诰封昭毅将军授云南右布政使湖广永顺宣慰彭侯墓志铭》,以勤、义、礼、和、孝、忠的“六德”标准评价彭翼南的一生:“侯为儿时,性颖敏,举动不凡。及少长,务学不倦。喜诵诗评史,延巨儒为师友,资如东廓、念奄、则远、宗之、道林、华峰,皆及门受学。刊阳明《遵诲诸集》以思贤,修司志、家谱诸书以传后。他如当路群贤曾侍侧者,罔不师法之,故多闻见,而不富学识,非敏而勤者乎?席祖父丰盈场,强盛而不侮邻,封不钤民庶。凡送迎,出予必裕,故士夫工贾胥得其欢心。军中饷犒,靡不分給,故士卒用命而所过不扰。广积布粟以赈饥寒,大施财木以修学梵,自备资粮采进大木,助建朝殿,直拟万金。至于自奉饮馔,未尝兼味,衣服不着锦绮,仪从惟尚简朴。尝获贼中美姬,督臣以充赏,侯即沉之江,其不心骄贵而迩声色。每如此,非富而义者乎?”从上所引的不论是土司生前所铭的“德政碑”,还是死后他人所追述的“墓志铭”。无一不是以较大的篇幅来颂扬土司的“宽仁镇静之恩,生息庶富”的德治。
但土司的“德治”并非一味“天性仁厚”,以礼服人,礼制的实施更多是维护土司统治的威严。“土司自称本爵,土民称之曰爵爷。赋敛无名,刑杀任意,抄没鬻卖,听其所为。每出则仪式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而伏,俱言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故畏之”。[6]以“用法峻严,服民以威”来使“德治”得以推行。
宗教信仰是土司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永顺土司司城中遍布宗教祭祀的建筑,这些建筑既有祭祀汉族宗教神衹的祖师殿、观音阁、圣英殿、神武祠、城隍庙、水府阁、五谷庙、稷神坛、崇圣殿等。也有祭祀本民族神祇的土王祠、吴着祠、吴着庙、八部大王庙等。这些建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雄伟庄严、十分壮观,最为著名的祖师殿,坐落于老司城下游二华里的灵溪东岸,面对灵溪河坐东朝西,其建筑群自西向东依次为祖师殿、皇经台、过亭、玉皇阁,均系明代修建。据县志记载,明代天启元年(1621),张天师授以玉皇真经三卷,上有天帅珠印,虽历经二百余年,但仍鲜明如故,天师珠印和玉皇真经均藏于玉皇阁内。圣英殿为明万历年间修建,又名关帝庙,供有关羽、周仓和关平三座铜像。庙内大铜钟高2.03米,钟体阳刻铭文记载了修建此庙的原因及时任土司彭元锦的武功。“土王祠”里面安放的是彭公爵主、向老倌人、田好汉神象,因每年的“摆手舞”均在其地举行,也俗称为“摆手堂”。摆手堂有大摆手堂和小摆手堂之分,堂前留有宽大的坪场,周围蓄植有许多树木,供村寨展开祭祀先祖、欢庆丰收、传授耕猎技艺等活动之用。也是村寨内的民众,遇到难以判明的是非直曲纠纷时,饮血赌咒,请求神判的场所。
“厚葬”是精神形态土司文化最重要的体现。土司对墓室的建筑十分讲究,如紫金山彭世麒夫妇合葬墓,此墓为三室合葬石室墓,墓前有长7.4米,宽4米由石供案、石香炉、八字山墙组成的拜台,整个拜台古朴典雅。墓室有墓道,墓道尽头是墓志铭,墓志铭上部是墓盖,两者用宽3厘米的钢条箍住。墓志铭后是雕花石墓门,上刻有上中下三组图案:上部是四瓣花连续图案,中部为“宝相花”,下部雕刻有一男一女人像,上中下部各有长方形画框间隔。其人物雕像中,女子头梳盘发,短衣,圆领,下穿八幅罗裙,足踏祥云,右手高托玉瓶,面容慈祥。男子垂眉,短衣长袖,下穿八幅罗裙,脚踏祥云,手持元宝。墓门的背面亦有雕刻图案。墓门采用高浮雕方法,图案富有立体感,雕饰精美,技艺水平较高。打开墓门是长6米的廊道,廊道两侧各用两根高1.5米的石柱撑起,上搭石质横梁,石柱顶部雕刻有变形龙头,龙口张开,舌头卷曲。廊道底部为石板铺的地面。经过廊道,就是左中右三间墓室,墓室头部设有神龛,神龛飞檐翘角,两边饰有兽吻,神龛两边装饰有高浮雕牡丹花。室内棺床为平铺红砂条石,上凿有七星图案,中室为男主人彭世麒,左右两室为其两位夫人,整个墓室装饰华丽,雕刻精致。
四、土司文化多样性传承
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在进化过程中的经验与知识,经过不断积累和衍生而创造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传承过程推动着它的发展,而发展则促使了文化的变化。上代人的传统文化,并非由下一代完全继承,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经验,每一代人都会多少不一地对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并对与现时需要不相符的内容加以改造或遗弃。更为重要的是,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文化是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某个民族祖祖辈辈所创造并为该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具有鲜明特色、博大内涵、悠久历史、传统优良的民族特征结晶;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体现本民族特点的各种思想及观念形态的概括性表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民族文化体现着该民族历史发展水平,维持着该民族独立性的主体地位,引导人们区分“我族”和“他族。”[9]因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就出现了民族性、地区性、时代性和阶级性的特色,土司文化也即如此。
老司城土司文化多样性传承首先表现的是其民族性。明代永顺土司聘请南昌人刘继先所修的家谱世系式的史书《历代稽勋录》,在我国少数民族所修谱书中独树一帜,其人名的记载是标准的“土汉合流”。“既有姓名俱全的汉名,也有褒贬善恶的谥号,最奇的是还有至今尚难尽释其意的土家语记音的土名。使今天的我们知道了彭氏土司的奠基者、生活于一千多年前的彭士愁,土名叫‘墨帖送。其后来的继任者彭允林土名‘麦即把、彭儒猛土名‘夫送、彭仕羲土名‘福送、彭师晏土名‘惹帖送、彭师宝土名‘惹帖恶、 彭安国土名‘打恶送忠等。”[9]而以汉姓加上土名的大小土司人名,如“彭慨主俾”、“彭大虫可宜”“彭惹即送”、“彭始主俾”、“彭南木杵”、“彭莫古送”、“彭药哈俾”、“向尔莫踵”、“向达迪”、“向麦帖送”、“向麦和送”、“田麦依送”、“向麦答送”等,更比比皆见。将土司祖辈们的土名记载下来,应是得到时任土司的同意,甚至是他们主动要求这样做的,也许在土司当时的意识里,留下土名仅仅是为了对先辈的尊重,承袭先辈们的习俗,知其根之所在,并非有保存本族文化的意向,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但这无意之中的“土汉合流”之举,却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代土家族语言和人名,为今天研究土家族古代语言及了解土家族姓名由“土”而“土汉结合”而“汉化”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在土家族历史上一年一度的“摆手调年”中,土司文化民族性传承表现的也极为典型。不论土司统治时期,还是封建官府治理时期,老司城每年正月的“摆手调年”风雨无阻:“新春摆手闹年华,尽是当年老土家,问到村人为何事,大家报赛土王爷”。摆手之日,“梯玛”(土巫师)会唱“迁徙歌”,向后人讲述着人类的起源、毁灭与再生,讲述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的同种与各自形成;老人们会表演“毛古斯”,展示土家族的繁衍与迁徙;众人会同跳“摆手舞”欢庆一年丰收,再现渔猎、采集、农耕的场景。每当摆手之日,周边村寨土家人均会相邀前往,规模盛况空前:“山叠绣屏屏尾拖,滩悬石鼓鼓音和,土王宫里人如海,婉转缠绵摆手歌”。改土归流以后,各级土司以罪徙、发配、归籍等不同形式迁居外省后,宫殿区地面建筑被官府拆毁,老司城逐渐荒废。但摆手歌舞依然年年不息。土家人在竹枝词中仍怀念着老司城当年的繁华盛景:“灵溪水畔古城墙,剑插群峰万马昂,十八土司都护府,一千年里夥颐王”。“溪州曾记古州名,福石犹留旧郡城。灵溪溪头花虽谢,望夫石畔月长明”。“野藤花漫土王祠,旧姓相沿十八司,除却彭家都誓主,向田覃冉互雄雌”。显示出文化的传承代代相继、世世相传。
老司城土司文化多样性传承具有地区性特点。明朝正德年间,宣慰使彭世麒编纂了《永顺宣慰司志》,原書虽然已经佚失,但现在还有残存的清代抄本。记述了永顺土司建置、辖地、所设官员及辖境内山川、风物、民俗等内容。其中“三州六洞长官司的沿革、形胜,向、田、黄、江、张等五姓土官姓名及世袭,玉极殿、崇圣殿、水府阁、观音阁、城隍祠、福民庙、八部庙、伏波庙、吴着祠等祠庙的方位及供奉,绳武堂、纯忠堂、筹边堂、都督府、寿禄堂、永镇楼、奉先堂、迎宾馆等公廨房屋,城外周边五十六旗旗名,福石、宝瓶、纳溪、西古、贺山、瑙峨等三百八十蛮洞寨村,以及“多者百家、五七十家,少者二三十家、五七家为村为寨”的村寨规模”[9]。《永顺宣慰司志》是土家族第一部地方志,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是研究土家族政治、经济、风俗、地理及老司城建设基本面貌的珍贵古籍。
老司城土司文化多样性传承具有时代性特点,在传承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彭氏土司在其统治时期,曾引进许多汉族文人作其谋士和助理,这些文人们对土司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功作用。“司城十景”、“颗砂八景”的命名与诗咏;土司家谱与墓志铭的撰写;衙署的设计与修建;书院的建立与任教;崖石题刻上的诗词唱合等,都与他们密不可分,并有着突出的业绩。如江西南昌人刘继先,他于明朝末年来到永顺宣慰司福石城,因施教的原因,与宣慰司衙署官员、土舍和族人交往甚厚。在阅读《永顺宣慰司志》、《土传》、《土记》等本地史籍和全面考察永顺宣慰司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撰写了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该书采用了大量的汉、土文献资料,如《资治通鉴纲目》、《史记》、《纲鉴》、《大明一统志》、《水经注》、《皇明通纪》;《永顺宣慰司志》、《土传》、《土记》;及外地谱书与方志《吉水谱》、《黄堂谱》、《硕字谱》、《莲塘谱》、《吉州志》等。开创了“汉土合流”式编纂土家族土司家谱的先河,使《历代稽勋录》留下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区性特点。土司及其继任者在阅读该书时,不仅熟知其先祖们的业绩,而且还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土司时代是民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是许多民族形成及定型的重要时期,土司文化当然也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司文化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基于一种以自己及族群的生活经验而体会到的,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的结果,彰显出民族本身独有的、与他族不同的特征。它不仅仅是民族成员个体对自己族属的认同选择和情感依附,也是同族成员相似性的认知和情感接纳,并形成“同族”的集体观念。它还是本族成员对他族的差异和民族边界的觉察和主观认定。土司文化本身就是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变化、交流的阶段性综合产物,其多样性的传承,表达的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记忆与反省,以及自我建构的情感与归附,民族就是以这种记忆与反省、情感与归附为标志,连接各成员为一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虽然,土司文化已成为过去式,但其内容及影响在民族地区社会文明发展与承继中,仍具有潜在影响的主体价值。
注 释:
[1] (清·乾隆)《永顺县志》卷四。
[2] 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等:《老司城遗址周边遗存调查报告》,岳麓书社,2013年。
[3] (清)汪森:《土官承袭例》,《粤西诗载》卷二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清·康熙)《卯洞司志》卷六。
[5] (清·乾隆)《鹤峰州志》卷一四。
[6] (清·乾隆)《永顺府志》卷一一。
[7] (清·同治)《保靖县志》卷一。
[8] (清·乾隆)《永顺县志》卷二四。
[9] 罗中:《土司遗址:历史封存与文化传承》,《三峡论坛》,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黄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