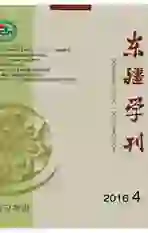《热河日记》中的辽宁形象解读
2017-04-15华云松赵旭
华云松++赵旭
[摘要]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从社会面貌、民族关系与关帝信仰三个方面描写了辽宁形象。他写出了乾隆时期辽宁的盛世繁华与治政弊端、各民族之间的友爱亲睦与冲突摩擦以及关帝信仰的普及化与世俗化倾向。这些辽宁形象的塑造,主要源于朴趾源“求真”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与实用主义的社会理念。虽然朴趾源的时代局限性使他对辽宁存在着误读,但《热河日记》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热河日记》;辽宁形象;解读
[中图分类号]I31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3805
[收稿日期]2016-03-13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课题“域外华文写作视野中的辽宁形象研究”,课题编号:L15BZWOO3;2016沈阳市社科联课题“沈阳地域文学现象与文学史构建研究”,课题编号:sysk2016-18-36。
[作者简介]1华云松,女,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沈阳大学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沈阳110036);2赵旭,男,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学。(沈阳110044)
《热河日记》是朝鲜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朴趾源(1737-1805年)的作品,记录了他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随朝鲜使团出访清王朝的经历。当时,朝鲜为庆祝乾隆皇帝七十寿诞组成了专门的使者团,朴趾源的堂兄朴明源被任命为正使,应其邀请,朴趾源随使团游历了中国,历经辽宁、北京、热河等地区,他根据这一段行程经历写成了《热河日记》。[1](3~4)这部书是朝鲜众多燕行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朴趾源因为此书而声名远播。学术界对《热河日记》进行了文艺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天文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但是,目前并没有相关学者对《热河日记》中的辽宁形象进行专题研究。而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视角,缘于辽宁是清王朝的皇权统治发源地,朴趾源对这一地区的“他者”视域,将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清代辽宁的地域文化乃至于清王朝的时代文化特色。
一、《热河日记》中的辽宁形象类型
朴趾源在燕行的过程中,主要经过了辽宁的凤凰城、辽阳城、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城、广宁城、闾阳驿城、大小凌河、松山堡、杏山堡、宁远城、中后所、中前所城等地,基本相当于今天辽宁的凤城、辽阳、沈阳、新民、黑山、北镇、锦州、兴城、绥中等地,所涉地域不可谓不辽阔。在这辽阔的行文视野中,作者对辽宁的自然与社会生活进行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极力叙写,笔触涉及辽宁城镇与乡村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方面面,人物形象囊括了官吏、士人、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民族形象包含了满、汉、蒙、朝等各民族。在这众多辽宁形象的塑造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社会面貌、民族关系与关帝信仰三个方面,当然这三方面内容在行文中是交相混杂的,为了论述方便,现逐一分析。
(一)乾隆盛世繁荣与治政弊端
朴趾源出使清朝之前,在朝鲜朝并非一介小卒。他生于贵族潘南朴氏之家,学通经史,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与朝鲜著名的思想家洪大容等探讨利国利民的实学思想,是一位颇有阅历的贵族文人。[1](3)值得品味的是,他在未到盛京之前,做过一个有关盛京的梦:其中“宫阙城池,闾阎市井繁华壮丽,余自谓:‘壮观!不意其若此。吾当归诧家。”[2](27)其潜意识中对盛京乃至清王朝的肯定表露无疑。通览《热河日记》,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乾隆盛世的繁荣景象,有关辽宁的繁荣刻画也是俯拾皆是。这种繁荣在乡村表现为青山绿水间的安宁平静,如使团入关后,但见“西南广阔,作平远山、淡沱水,千柳荫浓,茅檐疏篱时露林间,平堤绿燕,牛羊散牧,远桥行人有担有携。立而望之,顿忘间者行役之惫。”[2](13)边关乡野尚且如此安宁,城镇焉能不繁华。入关后使团先至凤凰城,作者写道:“缓步出门,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皆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2](15)至辽阳,“其繁华富丽十倍凤城”;[2](29)至新民屯,“市肆闾阎,不减辽东”,[2](51)“沿路二里三里之间,闾井断续,车马连络。左右市铺,无非可观”;[2](52)至小黑山城,“闾阎栉比,市铺繁华不减新民屯。绿芜中,马骡牛羊千百为群,亦可谓大去处矣”;[2](55)至广宁城,“入两重门,穿过市铺,有繁华不减辽东”;[2](62)至闾阳市,但见“百货凑集,车马填咽”。[2](69)遼宁最繁华的所在仍属盛京,作者写道:使团入得瓮城,但见“楼下出十字路,毂击肩磨,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充仞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2](37)作者盛赞:“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2](67)朴趾源不仅写出了辽宁的繁华富庶,还谈及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初入关时观察到的凿井法、[2](13)在凤城看到的屋室营建法、[2](15)在通远堡所见的建窑之法[2](22)与造炕之法、[2](26)在一板门与二道井间见到的造桥之法[2](54)以及专章讲述的车制之法等。在论及这些生产技术时,他的笔法是颇为细腻的。
朴趾源通过对社会景观的勾勒,充分展示了乾隆中后期辽宁的繁荣富庶。但是,在盛世繁华的背面,朴趾源也留意到了清王朝治政的种种弊端。如在边关防备方面,朴趾源在路上亲见“五六胡人,皆骑小驴,帽服褴褛,容貌疲残”,其皆“凤城甲军,往戍爱刺河而雇人倩往”,[2](8)保卫边疆如此重要的事情,凤城甲军竟然雇佣褴褛疲残之人,无怪乎朴趾源感慨道:“东方则诚无虑矣,然中国边备可谓疏矣。”边关的治政问题还不止防备疏松一项,小吏对朝鲜使臣的勒索也令人发指。他们欺朝使汉语不娴熟,在礼单上妄增名目,以讹钱财,若被朝使识破闹起来,则“众人自沮,皆面面相顾,无聊却立”。吏治不严,使这种敲诈明目张胆,已成惯例。清朝最高权力中心在政令发布上亦有弊端。如高桥堡地区,当地人视朝鲜人为仇敌,原因竟是因为皇权中心的“秉公执法”。是因往岁曾有朝鲜使团在此地丢失了公款一千两白银,于是呈文上报当地官方。窃贼究竟是什么人并不明晰,朴趾源也听说朝鲜有一大批窃贼“专以燕行资生”,“全没羞耻,公行剽掠”,所以窃贼可能是朝鲜人。但当时的朝鲜呈文上报地方官后,“则转报中后所参将,中后所转报锦州卫,锦州转报山海关守备。数日之间,转报礼部而皇帝批下,不一日而至”,命令地方官以官银赔偿,地方官被革职查办,店主与嫌疑人被抓捕,“死者四五人”,而且“行使未及到沈阳而皇旨已下”,如此仓促武断,草菅人命,难怪使团译官曰:“其举行之神速如此。是后,高桥堡人之仇视我人,无足怪也。”[2](75)以上实例一失在基层,一失在中央,其中隐含的清朝治政弊端,可谓广矣!
(二)各民族之间的友善亲睦与暗潮涌动
朴趾源在辽宁的游历中,记录了中朝、中蒙甚至朝蒙之间的多重關系,人物涉及满、汉、朝、蒙各族各阶层,头绪繁多,着墨最多的还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如使团初入关时,“有十余骑扬鞭驰过,皆绣鞍骏马,意气扬扬”,见朴趾源独立,则“滚鞍下马,争执余手,致殷勤之意”,“余画地为字以语之,皆俯首熟视,但点头而已,似不识为何语也”。[2](13)又如朴趾源在盛京大街上偶遇两人,似文人,他“乃前揖,两人解臂答揖甚恭。因入药铺,余遂跟入。两人俱买槟榔二个,刀劈为四,各以半颗劝余嚼之,又各自嚼吞。余书问姓名居住,两人俱谛视茫然,若不解者,因长揖而去”。[2](38)这两次交流虽以失败告终,但通过对人物行动细节的刻画——如“滚鞍下马”、“争执余手”、“俯首熟视”、“答揖甚恭”、“长揖而去”等——仍可令人感受到当时那种热烈融洽的气氛。最有代表性的是朴趾源与盛京古董铺子艺粟斋、锦缎铺子歌商楼商人的良宵夜话,作者以笔记的形式记入《粟斋夜话》中,席间彼此致礼殷切、笔谈甚欢,皆有“依依相惜”之情。[2](41)在众多商人中,艺粟斋商人田仕可的形象最有光彩,他不以假古董蒙骗朴趾源,甚至为他详细解说勘别古董之道,并应朴趾源之请,为其开具一篇“古董真伪名目”,同时还在信中明言其“所以眷眷贡愚者,诚为异邦君子他日东还,庶不都诬大国无人也,并布赤心”。[2](50)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华民族以诚待人的优良传统。另外,《热河日记》中有一段涉及朝、蒙、满人共处的文字更是颇为生动有趣。使团在从辽阳到盛京的路上遇到一队蒙古运砖车队,蒙古人“衣帽褴褛,尘垢满面”,朝鲜侍从们“岁见蒙古,习其性情”,故而“与之狎行,以鞭末挑其帽弃掷道傍,或球踢为戏”,由于这只是一种玩笑,并非恶意挑衅,蒙古人遂“笑而不怒,但张其两手,巽语丐还。”朝鲜侍从“或从后脱帽,走入田中,佯为蒙古所逐,急转身抱蒙古腰,以足打足,蒙古无不颠翻者,遂骑其胸,以尘纳口”,嬉闹引得一众满人“停车齐笑”,“被翻者亦笑而起,拭嘴着帽,不复角胜”。[2](34)这一场充满了粗犷豪放之气的斗闹虽然拳来脚往,但在一片笑声中洋溢着友善与亲睦之情。
在各民族友好氛围中也有不和谐的别调。如在新民屯,朴趾源遇到一位跪在他马前告状的老瓜农,垂泪申述有高丽人哄抢其所种甜瓜。但老者又向他索要清心丸,未索到便以高价强卖其甜瓜,朴趾源不觉暗叹,“始见其垂泪而哀之,末乃勒卖九瓜,坚讨近百高价,殊可痛叹。然我隶沿路行劫,尤可恨也。”[2](53)这场争端,也是各有错处,值得深思的是,朝侍从时大总结云:“此汉即汉人也,满人无似此妖恶事云。”[2](53)其言语中又含有明显的对汉族的歧视。中蒙之间也不太平,朝使在渡过小凌河时,见“河边居民数百户,去岁为蒙古所掠,尽失其妻,撤移数里地。”又闻“数日前,蒙古数百骑猝至河边,见有守催而遁去”。[2](73)看来,蒙古对清边境亦有抢掠。
(三)关帝信仰的普及与世俗化倾向
将三国时期大将关羽推上信仰的神坛,并把这种信仰推展到极致,是清朝的一项统治策略。其明显的表象就是关帝庙的大量建造。朴趾源在《关帝庙》一文中曰:“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徼,数家村坞,必崇侈栋宇,赛会虔洁,牧竖饣盍妇,咸奔走恐后。自入栅至皇城二千余里之间,庙堂之新旧,若大若小,所在相望,而其在辽阳及中后所,最著灵异。”[2](347)在中后所,作者确实记录了当地的关帝庙,“壮丽胜于辽东,甚有灵验”。[2](80)另外,在使团经过辽宁的林家台、范家台、青石岭、辽东城外、广宁城外、沈阳城外等处,朴趾源都或多或少地提及到了关帝庙。由此可见,关帝信仰在辽宁地区是相当普及的。
从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的记录来看,当时辽宁的关帝庙当有如下用途:
叩拜祈祷场所。除前文提及到辽阳、中后所关帝庙颇为灵异之外,在凤凰城与辽阳城之间的青石岭上亦有一所极其灵验的关帝庙,引得使团中的“驿夫马头辈争至供桌前叩头,或买供青瓜。译官亦有焚香抽签,占验平生休咎者”。[2](28)
村间教学场所。使团一行从青石岭奔辽阳城,途中因大雨滞留通远堡,在当地店主的指引下寻一在村间设村塾的秀才,得知塾堂在关帝庙里。入得庙来,但见“寂无人声”,“右厢里有小儿读书声”。[2](23)可见,关帝庙有作为塾堂之一用。
娱乐场所。《关帝庙记》云,出旧辽东城门,有关帝庙,“庙堂壮丽,复殿重阁,金碧璀璨”,“庙中无赖游子数千人,热闹如场屋。或习枪棒,或试拳脚,或像盲骑瞎马为戏。有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滑溜,亦如我东巷肆中口诵《林将军传》。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人响叠钲”。[2](32)在这一段记述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此处关帝庙能容纳数千人在其中游戏玩乐,其建筑当占地甚广;其二,数千乡人在其中习武游戏,又有说唱《水浒传》、《西厢记》者,而《水浒传》、《西厢记》在当时的清朝是禁书,更遑论付之于演出。有学者指出:由于违碍之故,清代人一般不敢将这类实情形诸笔墨,朴趾源生动而具体的描述,给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3](190)敢于在皇权与神权都同样推重的关帝庙讲唱禁书,数千人处之泰然,关帝庙在民众心中的娱乐场域价值不容低估。除了习武、游戏、听书之外,关帝庙与其他神庙一样,还具有演剧功能。在广宁城外,“关庙壮丽,伯仲辽阳”,“庙门外戏台高深华侈,方聚众演剧,而行忙不得观”。[2](62)究竟具体情况如何?《戏台》一文对之作了补充说明:“寺观及庙堂对门必有一座戏台,皆架七梁,或架九梁,高深雄杰,非店舍所比。不若是深广,难容万众。凳桌椅杌,凡系坐具动以千计,丹艧精侈。”[2](67)若以此论,高深华侈的广宁关帝庙门外戏台当亦能容万众、桌凳千计。
从辽宁关帝庙在民间的上述用途看,当地关帝崇拜更多地服务于世俗功利化需要。人们向关帝求卦问卜,将关帝庙作为教学或娱乐场所,以实现其向神灵祈祷、学习知识或玩乐游艺的现实需要。朴趾源对关帝庙中道士形象的刻画,也有利于解读当地关帝信仰的世俗化倾向。在青石岭的关帝庙中,朴趾源看到“有道士敲钵丐钱”,“又一道士卖瓜及鸡卵”,[2](28)若不披道袍,他们可以直接被视为是小商小贩。在沈阳城外关帝庙中的道士,“尖鼻会晴,动止轻佻,全没款曲”,[2](37)其出场便是与盛京兵部郎中福宁一起研究朴趾源的鞋子材质,并对朴趾源的鞋子赞叹有加,并无宗教徒的精神气质。虽然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关帝庙中有一些道士是不以宗教修炼为务的,关帝庙只不过是他们的托身之所罢了,他们也不惮于表现其自身的这一特性。这也可以作为当时辽宁关帝信仰世俗化的一个辅证。
二、《热河日记》中辽宁形象塑造之成因有学者认为:意象的意义指涉至少应注意四个意义层面,即:语言媒介的意义、客观物象的意義、历史沉积的意义以及作者主观附加的意义。[4](304~305)《热河日记》中的辽宁形象塑造也涉及这些意义指涉层面,其中朴趾源附加在辽宁形象上的主观性更是占了主要地位。朴趾源的主观意向是非常丰富的,在其游历辽宁的日记中,就体现出诸如尊华攘夷、厚生利用、重儒轻利、贵族优越、朴素唯物等一系列观念,但归根结底,主要影响辽宁形象塑造的是其求真观与实用观。
(一)“求真”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
有学者引朴趾源的《赠左苏山人》诗——“即事有真趣,何必远古担,汉唐非今世,风谣异诸夏”——指出该诗从历史视角体现了“即事趣真”的文艺美学观念,并将之与朴趾源的实学思想相联系,[5](79)但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有对于求真理念的更为透彻的阐述。
文中写到:使团一行过三流河,行十余里,见前途“转出一派山脚”,“趣鞭行不数十步,才脱山脚,眼光勒勒,忽有一团黑球七升八落”,见此壮丽之景,朴趾源感慨道:“吾今日始知人生本无依附,只得顶天踏地而行矣。立马四顾,不觉举手加额曰:‘好哭场!可以哭矣。”在朴趾源看来,人生七情皆可以哭宣泄之,因为“至情所发,发能中理,与笑何异?”[2](28)他认为这种“理”在赤子出生时有最充分的体现。赤子初生的啼哭,并非“人生神圣愚凡一例崩殂,中间尤咎,忧患百端,儿悔其生,先自哭吊”,而是由于“儿胞居胎处,蒙冥沌塞,缠纠逼窄,一朝迸出寥廓,展手伸脚,心意空阔,如何不发出真声,尽情一泄哉?故当法婴儿,声无假做”,“今临辽野,自此至山海关一千二百里,四面都无一点山,乾端坤倪,如黏胶线缝,古雨今云,只是苍苍,可作一场”。从这一段文字可见,在朴趾源的理念里,面对辽野的壮观景色,令其觉得放声而哭最抒胸怀,最重要的不是“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其中蕴含的“当法婴儿,声无假做”的“真声”意识,这种“真声”,鲜明地体现了朴趾源从生命本体角度出发的“求真”的美学追求。在《热河日记》中,当这种本体论的“求真”意识与生活的表象相关联,并诉诸文学表述时,则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正是从这种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出发,朴趾源在塑造辽宁形象的过程中,能够既写出乾隆四十五年的盛世繁华与民族交流的亲睦友善,又能如实记录下当时清庭的治政弊端与满、汉、蒙、朝各族之间的冲突摩擦。即使是关帝庙那样神灵崇拜的场所,他也是既写出了关帝庙的数量众多与宏阔壮丽,也如实记录了其多样的世俗化功利性用途。这种“他者”的现实主义视野,为辽宁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材料。
(二)实用主义的社会理念
清代的朝鲜朝有着浓厚的皇明情结与小中华意识,其来源一为明万历二十年、二十七年明政府对朝鲜朝抗倭的有力支援,一为后金与清廷在1627年与1636年对朝鲜朝的两次征讨,前者令朝鲜朝对明朝感恩戴德,后者令朝鲜朝在屈从清廷后仍耿耿于怀、切齿痛恨。[6](166~169)有学者研究,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同样体现了鲜明的皇明情结。[7](54~57)不仅如此,这种皇明情结在他随使团游经辽宁时也同样有所表露。未入关之前,他听闻康世爵在辽宁的抗清事迹,深深地为之感佩;[2](7)在辽东旧城,他追忆天启元年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率军攻打明辽阳城时的酷烈战争,对为明殉节的明军将领深为哀悼;[2](31~32)在经过明清松杏之战的古战场时,见当地村市凋残,遥想当年明军“赴海死者甚众”,而“清军误伤者只八人”,对明的气数已尽充满了叹惋之情。[2](74)在宿新广宁的日记中,他将士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士认为:“一薙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2](60)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清廷的极大敌视与不满。但是,朴趾源并未局限于追恋明朝与敌视清廷,他认为:“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圣人之作《春秋》固为遵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2](61)这段文字屡为学界所引用,并认为这是朴趾源实学思想的生动体现,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振兴朝鲜朝的实用主义理念。这种理念包含三个概念:利用、厚生、正德,三个概念层层递进,以完成对朝鲜朝的国家建设,[2](12)很明显,“利用”观念为根本。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朴趾源以大量的篇幅写出了辽宁地区的繁华、富庶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暗含着向清朝学习借鉴的意味,其最终目的,当然是振兴朝鲜朝。
三、结论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与实用主义社会理念,他从社会面貌、民族关系与关帝信仰角度入手,生动展现了乾隆四十五年辽宁社会纷繁复杂的时代画面。但是,朴趾源作为朝鲜朝贵族文人,有着其不可避免的视野局限性。如其不谙辽宁民俗,为新民屯当铺主人题“欺霜赛雪”四字,店主认为其所题不当,他便在心中默骂店主是小去处做买卖的粗莽汉,[2](52)后来在小黑山首饰铺方知“欺霜赛雪”四字是当地为面铺题字所习用语。[2](56)他虽能知错就改,但对新民屯店主的误解中已表现出其不明辽宁民俗和自恃高贵所带来的局限性。这类局限性来源于朴趾源的国家归属与阶级属性,必然会使其作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当时辽宁真实形象的误读。
孟森认为:乾隆时期与康熙时已大不相同,“十全武功,铺张极盛,而衰象早伏其中”。[8](227)在朴趾源《热河日记》对辽宁社会面貌与民族关系的描写中,确实可以看到乾隆朝盛中有衰的社会状况。而在其对关帝庙功能的表述中,更是展现了一些不为清史料所载的民间娱乐活动内容,如公然讲唱《水浒传》、《西厢记》等禁书。从这些层面看,《热河日记》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辽宁的误读,但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朝]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3]陈大康:《〈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4]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5]姜日天:《燕岩朴趾源“即事趣真”的文学思想及其历史哲学内涵》,《当代韩国》,2001年第2期。
[6]王政尧:《朝鲜〈燕行录〉著者爱戏辨析》,《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五辑)》,2014年。
[7]董明:《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齐鲁学刊》,2015年第2期。
[8]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