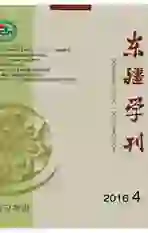《近思续录》与韩国的儒学本土化建构
2017-04-15罗海燕
[摘要]中国朱熹与吕祖谦所编《近思录》于元代传入高丽,对韩国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学者有关《近思录》的注释、解说、续仿之书众多,甚至超过中国。续书之中,朝鲜末期宋秉璿所辑《近思续录》尤具特色。该书既是中国儒学海外传承的产物,也是本土化建构的结果。对此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儒学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同时也能借此反观与省思当前复兴儒学、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使命与路径。
[关键词]近思续录;韩国;儒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1906
[收稿日期]2016-04-15
[作者简介]罗海燕,男,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与文献。(天津300191)
从韩国儒学发展史来看,其儒学传承行为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而本土化建构,亦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承传中国儒学时,高丽、朝鲜时期的士人,大多标举道学统绪,以完整接续朱熹之学为宗。但是,到了清代末期,中韩两国均遭遇列强入侵与西学东渐的严重危机后,朝鲜士人在寻找出路与力求突围时,本土意识与独立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张扬态势。他们以回归与坚守传统为旗帜,对本国儒学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本土化建构。这种建构,对近代以来韩国的国家独立与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效仿朱熹与吕祖谦所编《近思录》,朝鲜朝末期的宋秉璿编纂完成了《近思续录》一书。此书的编撰与问世,非常典型地展示了韩国自觉承传中国儒学,然后有意识进行本土化建构的过程。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可以从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角度去切实了解中国儒学的海外承传以及在接受国实现本土化的历程。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视野中,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与借鉴。目前,国内关于《近思录》在韩传播的研究较少,主要有陈荣捷《朱学论集》中的《朱子之〈近思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程水龙的《〈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与《〈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姜锡东《〈近思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的《〈近思录〉对东亚等国家的影响》等。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韩国宋秉璿所辑《近思续录》作一重点考察。
一、韩国“《近思录》热”与宋秉璿及其《近思续录》作为中国理学的基本读物、入门读物与概论性读物,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查洪德先生在注译《近思录》一书时,曾将其影响概括为“三多”:[1](7)一是刻本多;二是注家多;三是续书多。陈荣捷先生亦称:其“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以后《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之模型。《近思录》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2](267)
元朝时期,《近思录》传入高丽。今之治史者一般认为,安珦(又名安裕)最早把朱子学引进韩国,并开创海东性理学之端。据《高丽史·列传·安珦传》及《晦轩先生实纪·晦轩先生年谱》等载:“庚寅忠烈王十六年,留燕京,手抄朱子书,又摹写孔子、朱子真像,时朱子书未及盛于世,先生始得见之,心自笃好,知其为孔门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孔、朱真像而归。自是讲究朱书,深致博约之工。”[3](卷三)其所抄“朱子书”应包括《近思录》在内。《近思录》东传后,在丽、鲜两朝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正统元年(1436年),朝鲜世宗曾命大臣参校整理此书,以铜活字印刷发行。李滉、李珥等大儒均对其展开探讨,进一步扩大了《近思录》的海外传播,以致于韩国阅读、注释、评论《近思录》的论著,多达百种,比同一时期的中国还要多,形成了持久不息的“《近思录》热”。据周兴与韩国学者孙兴彻统计,现有韩国学者所撰有关《近思录》的各种著述至少有92种之多。数据参见周兴、孙兴彻所撰《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武陵学刊》2011年第6期)一文。即使在当代,韩国学者对于《近思录》的注释、导读类书籍依然很多。仅笔者所见,如有:成元庆译注本(三中堂1976年版)、都珖淳译本(瑞文堂1978年版)、李民树译本(乙酉文化社1984年版)、朴一峰译本(育文社1993年版)、成百晓译注本(古典国译编辑委员会2004年编辑本)、金学主译本(明文堂2004年版)、李范鹤译注本(首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英昊解译本(2005年版)等。
不过,截止到现在,韩国有关《近思录》的续书却较少,仅有五种,分别为:安鼎福与尹东奎《李子粹言》、李汉膺《续近思录》(又名《海东近思录》)、韩梦麟《续近思录》、任宪晦《五子粹言》与宋秉璿《近思续录》。其中,以宋氏《近思续录》影响最大。
宋秉璿(1836-1905年),小名九范,字华玉,号渊斋、东方一士,韩国忠清道恩津县采云乡人,为硕儒宋时烈九世孙。宋秉璿天资聪颖而读书刻苦至废寝忘食,青年时曾于宁国寺读《孟子》,家人送衣衾,衣中置糖一封,为其读书疗饥,而宋秉璿专心读书,置衣衾于架上,及其归后才发现衣中有糖,时已融化。宋秉璿先后历任经筵官、侍讲院谘议、司宪府持平、侍讲院进善、通政大夫、吏曹参议、侍讲院赞善、成均馆祭酒、右副承旨及同副承旨、嘉善大夫、工曹参判、司宪府大司宪、嘉义大夫等。生平以儒为尊,而尤重气节。1905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非法的《乙巳条约》,宋秉璿为此愤而自杀,时年七十。自绝前尝言:“勒约未缴,则五百年宗社,今日而亡矣;三千里疆土,今日而无矣;数百万生灵,今日而灭矣;五千年道脉,今日而绝矣;臣于今日,生亦何为!”[4](卷4)感于其气节,当时门人持服加麻者,殆三百余人,民众亦沿途追悼。朝廷曾特下旨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府议政,赠谥“文忠公”。宋秉璿一生著述宏富,前后编著有《近思续录》、《东儒渊源录》、《武溪谩辑》与《东鉴纲目》等所谓“四大编”,皆关乎儒言、儒行与儒家道统。卒后,其詩文被弟子门人结集为《渊斋先生文集》今有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后凡引《渊斋先生文集》皆出自此藏本。不再一一标注。,计24册54卷,于1906年刊行于世。生平事迹则见于其子宋哲宪所作《家谱》及其弟宋秉珣所撰《行状》。宋秉璿对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研读甚勤。据《行状》载,其每年盛暑隆冬,均携书入山房,讲磨不辍,而所携带书即《朱子大全》、《宋子大全》及《近思录》等。39岁时,《近思续录》已辑录成册,而到60岁时,他仍在对此书进行校勘、续补,前后持续达二十余年。
宋秉璿《近思续录》具体成书过程如下:先是,宋秉璿自早岁读书起,就用心抄录韩国儒者赵光祖(号静庵)、李滉(号退溪)、李珥(号栗谷)、金长生(号沙溪)及宋时烈(号尤庵)诸人文章,多达千余条。其《近思续录序》称:“秉璿自早岁,受读五先生书,而广大宏博,窃有望洋之叹。故积年随抄,得千余条。”[5](卷首)到清光绪十三年(1874)夏,与外弟金圣礼,对所抄千余条语录进行删定更改,编定是书,宋秉璿并为之作序。宋哲宪所作《家谱》亦载:“七月,《近思续录》成。”并注称:“先生就静、退、栗、沙、尤五先生遗书,纂辑其要领,与省斋金公,更加商榷。仿《五子近思录》之例,条分类别,编为是书。”[4](卷50)但是,此书当时并未刊版,而是仅以笔写本流传。其后数年,宋秉璿一直在对此书进行考阅删补。清光绪八年(1882)7月28日,宋秉璿在《上枕泉族叔膺洙》中说道:“《近思续录》,今更考阅,则删可为多,添亦有之,大费心力。”[4](卷6)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宋秉璿又会同李圣器、郑大卿、安稺章诸多好友,对《近思续录》进行集体商议校订。
在宋秉璿看来,这次会商,意义非凡:一是,在西学东渐的重压之下,朝鲜儒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在如此境地中纂成《近思续录》,其功重大。二是,此时朝鲜政局已陷入风雨飘零中,儒教同道能于末世相聚,实属不易。而此次团圆聚会,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勉励。三是,《近思续录》一书在集体商定后不久就以木板刊行于世。期间,宋秉璿尝作诗《与李圣器秉瑚、郑大卿、安稺章成焕诸君,会武溪山亭,校〈近思续录〉,拈韵求和》。其云:“乙未仲夏月,同志会三四。续编有校役,寒泉依故事。笔删用心苦,对床更相议。泉响入户冷,灯光到夜邃。叔季起淫辞,恒抱忧世意。纵有一苇力,难抗滔天水。愿言吾党士,经旨讲未已。”[4](卷2)诗中提及相与校订的情状,更表达出当时儒学之士身处纷扰乱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同仁之间彼此勉励的良苦用心。而在刊行后,宋秉璿又曾就书中一些字句进行更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答安稺章》,就已刻板《近思续录》卷一中金长生语录以及序中措辞等问题,向安稺章求教:
《近思续录》“道体篇”十一板,“自体之体”,考先祖手书真本,则初非所误,而又细究其文义,则用字亦不必为然。故磨灭其头注,且连“乡士友”。以序中“礼学”二字,为不满于沙翁,有所是非,故改以“实践”。盖“潜思实践”,是称横渠语。“笃实践履”,是称沙溪语。则“实践”二字,更无可议者否?细商以示如何。[4](卷11)
笔者所见有关《近思续录》的著录,主要为两大版本:一是手抄本。仅一种,且只存卷一、卷二,抄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而抄者不详。二是木版本,或标刊行年为1874年,或标刊年不详。而刊年为1874年者,应是将作序时间误为了刊行年,因为宋氏于《书武溪诗帖后》中已明言,昔年仅是辑录成书而已。笔者手中木版本《近思续录》,其第十一板“自体之体”头注尚存,而序中“礼学”两字依然。其云:“盖静、退作于前,抽关启键,若濂溪周子;栗谷之通透洒落,如伯程子;沙溪之礼学又似乎张子;而尤庵晩出,发挥运用,殆若紫阳之夫子。”该本藏于韩国圆光大学图书馆,题为《近思录》两册十四卷,前有宋秉璿1874年自序,木板本,而刊行地与刊行时间不能确定。故其应刊行于1895年至1901年间。而程水龙《历代〈近思录〉传本的序跋、题记汇编》所录宋秉璿《近思续录序》中“礼学”已改为“实践”,且少一“盖”字。故程先生所见本应是更为晚出者。参见程水龙所撰《〈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6页)一书。不过,程氏所录存有两处错误:一是将作序时间误为刊行年;二是抄录序言时“错简”,将书序与正文混在了一起。此外,初刊于1906年的宋秉璿本集所收《续近思录序》,又跟我与程先生所见之序不同。其云:“盖静庵、退溪作于前,抽关启键,有似乎濂溪周子;栗谷、沙溪继其后,阐明大备,又同于程、张夫子;尤庵晩出,发挥运用,殆若紫阳之夫子。”[4](卷23)于此可见,宋秉璿在临终前仍在修订《近思续录序》。《近思续录》在宋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亦由之可见一斑。
二、《近思续录》对《近思录》的直接承传与本土化建构韩国所存《近思录》续书有五种,均采用《近思录》体例。其中,安鼎福与尹东奎《李子粹言》(1754年)仅选辑李滉之语,类似清张伯行《续近思录》(1710年),只录朱熹语,难见韩国儒学之承传,故不免偏狭;李汉膺《续近思录》虽采录不同学者论著之语录,但仅为中国之学者,故只见承传而不见本土化建构;韩梦麟《续近思录》语录采自李滉《朱子书节要》、丘濬《朱子学的》与《四书集注》三处,但仍仅集中于朱子言论。任宪晦所辑《五子粹言》亦属韩国学者的《近思录》续书,却因为未以“近思录”为名,一直以来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其所谓“五子”即韩国之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与宋时烈,可体现出韩国学者心目中的儒家道统之序列,惜乎此书流传不广。较之于其他的《近思录》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宋秉璿《近思续录》则既能体现出其对《近思录》的直接承传,又能见出其明显的本土化建构。论其承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最明显的是两者的篇章体例相同。宋秉璿《近思续录》亦以《大学》为内在篇章脉络,又以《近思录》章目为章目。全书分两册共十四卷:卷一“道体”,共49条;卷二:“为学”,共111条;卷三“致知读书”,共83条;卷四“存养”,共69条;卷五“力行”,共55条;卷六“齐家”,共50条;卷七“出处”,共58条;卷八“治道”,共56条;卷九“治法”,共43条;卷十“临政处事”,共58条;卷十一“教道”,共22条;卷十二“警戒”,共58条;卷十三“辨异端”,共25条;卷十四“论圣贤”,共51条。宋秉璿《近思续录序》又直接提到:其书“仿‘五子近思之例,分类别编为一书”[5](卷首)。而以“五子近思”的书有两种:一是明代钱士升辑《五子近思錄》十四卷;二是清代汪佑编《五子近思录》。两书体例相近,但钱氏之书不见传入海东,而汪氏之书颇为韩国士子珍爱。由此可以推断,宋秉璿所仿之书应为汪佑《五子近思录》。此外,韩国也有“五子”之谓,不过,尽管宋氏《近思续录》与《五子粹言》所选学者完全一样,且《五子粹言》书在前,宋秉璿却直到1902年时仍未见到《五子粹言》。其《答沈中卿宜允》曾道:“《近思续录》是愚所不曾自揆,妄掇五先生书而成之者也。侧闻尝自星田有辑《五贤粹言》云。想亦此类,然恨未得奉读而质己见也。”[4](卷8)
其二,两者之纂集宗旨一致。朱熹《书近思录序》曾自道编辑缘由与宗旨,其称: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6](3826)
而宋秉璿《近思续录序》则云:“秉璿自早岁,受读五先生书。而广大宏博,窃有望洋之叹……凡于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道,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事,罔不备载,则可以为进学之阶级也。学者不以人僭踰而废之,循是而进,亦庶乎得其门而入矣。若不先力乎此,直欲求诸五先生全集,则地负海涵,未易见其涯际。必须由其要而致其博,然后可以尽得宗庙、百官之盛矣。窃尝闻朱子之言曰:《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也。五先生之学,即周、程、张、朱之道。而阐明四子之旨,则此书安知不为四子、近思之羽翼也欤。”[5](卷首)可见,两者均备载关乎“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道”与“辨异端、观圣贤之事”的语录,而且以所辑之书作为学者入门之阶梯。
其三,两者均带有强烈的宗法意识。早在朱熹等人之前,唐代韩愈感于佛、道二教炽盛,民众佞佛风气浓厚,为对抗佛教之祖统说,他建构起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孟轲一脉相承的儒道传授统绪,并认为自孟轲死后道统不得其傳,隐然以继承道统自命。其《原道》尝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7](122)朱熹在继承、总结前代诸儒道统说基础上,对儒家道统传授谱系作了更为明确、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自上古以来,道统便圣圣相传,一脉相承,尧传之舜,舜传之禹。其称:“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再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子思则传于孟子,孟子之后“遂失其传焉”。直到周敦颐、程颐与程颢兄弟起,才再续道统。其《中庸章句序》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7](14~15)而他又以二程承传者自居。《近思录》中也体现出了他的这种用心。宋秉璿亦有着自觉的宗法意识。在他看来,赵光祖、李滉似乎周敦颐;李珥、金长生仿佛二程与张载;宋时烈殆若朱熹。其前后之间,师承脉络清晰,道统次第井然。《近思续录》中,唐、虞、夏、殷、周,孔、颜、曾、思、邹、濂溪、程、张、朱,静、退、栗、沙、尤,形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道学统绪。
其四,推尊朱熹,重视《近思录》。《近思续录》中,尊朱之语,随处可见。或称:“先学朱子然后可学孔子。”[5](卷2)或称:“余幸生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5](卷2)韩国学者在为学过程中,非常重视《近思录》。《近思续录》还专门载记宋时烈于宋翼弼(号龟峰)处学习《近思录》的经过。宋时烈自道其:“尝受《近思录》于龟峰,龟峰极其英迈,看书无碍,谓人如己,故一番读过而专不解说。余初盖茫然如未学也,退而静坐,看来看去,十分辛苦。读而思,思而读,昼夜不已,然后渐渐通晓。千思百虑,终未透然后请问焉。读书勤劳,未见如我者也。今尔看得容易。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则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5](卷3)此外,他还曾将二程书与《近思录》比较,劝诫学者多读后者。他说:“二程书有时聱牙难读处,且其门人所记遗书时有违失先生本旨者。故朱子择其精要者入于《近思录》。不若先读《近思》知义理、意趣,然后可及全书也。”[5](卷3)
同时,就本土化建构而言,其主要表现亦有四个方面:
其一,《近思续录》具有明显的本土意识。宋秉璿在《近思续录》的序言中首先写道:“维我东方,自殷师以后,变夷为夏。而逮至本朝,道学彬彬,浸淫乎大宋之世。”[5](卷首)并且与韩国其他学者《近思录》释解、续补著作不同,宋秉璿仅选韩国五位学者之语录,分别为赵光祖《静庵先生文集》、李滉《退溪先生文集》与《退溪先生言行录》、李珥《栗谷先生全集》、金长生《沙西先生遗稿》与《经书辨疑》、宋时烈《宋子大全》与《筵说讲义通编》及《朱子大全札疑》。宋秉璿对李滉与宋时烈尤其推尊,认为其不让中国学者,称:“栗谷作于前,先生继于后。我国海外道学之传,岂天之正气东行,自不得不然耶。朱子之道至栗谷而复明,栗谷之业至先生而益广。栗谷如天开日明,先生如地负海涵。”[5](卷14)
其二,《近思续录》具体章目名称有异,既不完全同于《近思录》原本,也有别于叶采《近思录集注》本。如:卷三改“致知”为“致知读书”;卷五改“克己”为“力行”;卷六改“家道”为“齐家”;卷八改“治道”为“治体”;卷九改“制度”为“治法”;卷十改“政事”为“临政处事”;卷十一改“教学”为“教道”;卷十三改“辨异端”为“异端”;卷十四改“圣贤”为“论圣贤”。
其三,《近思续录》反对异端的态度更加强烈。《近思录》卷十三“异端”采语录13条,而《近思续录》所采条数达25条,多出近一倍。全书不仅排斥佛禅、方士与杨朱之说、墨翟之学,而且激烈地反对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诸人学说。把陆、王与程、朱严重对立起来。其称:“象山、阳明之说与程朱犹水炭熏莸,相为胜负消长。彼胜而长,此负而消,则其为害甚于洪猛。故孟子论异端之害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韩公亦曰:三纲沦而九法斁。”[5](卷13)又云:“禅学虽足以惑人,其言非儒,其行灭伦。世闲稍知有秉彝者,固已疑阻。又经程朱之辟,宜乎其迹若埽矣。陆学则不然,言必称孔孟,行必本孝弟。而其用心精微处,乃是禅学也。辟之之难,岂不十倍于佛氏乎。佛氏之害,如外寇之侵突。陆氏之害,如奸臣之误国。此不可不知,故并著焉。”[5](卷13)宋秉璿《随闻杂识》又尝论道:“明末诸子,专尚王陈之说。学术之害,竟亡天下。若使主彼说者,得位持世,则从心所欲,坦然由之,以致无忌惮之域矣。”[4](卷17)
其四,自宋时烈至宋秉璿,他们身上自始至终存在着明遗民情结。这种倾向也使得《近思续录》对中国的元儒与清儒多予否定,并有意忽略掉高丽时期诸多有影响的儒学之士。其论元儒许衡:“许衡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此甚可耻。”[5](卷14)而对于清儒竟只字未言。其评高丽时期的重要儒者郑梦周(号圃隐),则称:“我国理学圃隐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5](卷14)又如世所公认,高丽时期安珦(裕)为传韩朱子学第一人,其与白颐正、李齐贤诸辈,传承朱子之脉。但《近思续录》却评道:“安裕无与于斯道。”[5](卷14)在他们的道统序列中,朝鲜时期的赵光祖被视为道学开创者。
三、《近思续录》更重本土化建构的原因较之于其他相关的著述,宋秉璿《近思续录》更强调韩国理学承传的独立性与道学绪脉的正统性。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韩国儒学经过长期发展,在实际承传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中国理学的本土化特征。韩国儒学最初由中国传入,相对于韩国的固有文化,这是一种异质文化。从中国传承的儒学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中,在韩国学者细密的思维方式、精微的逻辑思辨,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影响之下,儒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带有韩国印记的儒学,实际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韩国儒学”。当代学者李甦平曾概括韩国儒学的独特品格,亦即韩国儒学的独立性,共分三点:重“气”、重“情”、重“实”。[9](2)故韩国儒学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但是绝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是宋秉璿本土化建构的理论基础。
二是,朱明王朝的灭国事实与晚清政府的無能表现,打破了韩国学者对中国儒学的神话想象,并由之强化了他们的“小中华意识”。明朝灭亡以后,清朝以武力夺取对朝鲜的宗主权。迫于武力,朝鲜在政治上对宗主国清朝示以认同,而在文化上,却不愿归附,坚持奉明代崇祯皇帝“正朔”达二百余年。宋秉璿《近思续录序》末时间即署为“崇祯二百四十七年”(1874)。在朝鲜士人看来,满清虽入主中原,但身为夷狄,无资格担当中华正统。在这种思潮下,朝鲜士人多具有尊周思明的倾向,并以中华自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小中华意识”。被誉为“朝鲜朱子”的宋时烈主张“尊周大义论”,他曾在《记述杂录之尹凤九》中宣称:“夷狄不得入于中国,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为第一义,为明复仇为第二义。”[10](569)朝鲜燕行使者洪大容亦曾为朝鲜慕效中华而感到由衷自豪,其《太学留馆录》称:“至于敝邦,专尚儒教,礼乐文物皆效中华,古有‘小中华之号。”[11](619)宋秉璿《随闻杂识》也曾评论道:“中国沦于夷狄久矣。西洋邪敎,因此闯肆,渐染弥漫。而惟我东土,保守先王礼义,诵法孔朱绪余,习化成性。”[4](卷17)这是宋秉璿本土化建构的历史依据。
三是,日本的野蛮侵略激发了朝鲜末期有志之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所谓“斥邪卫正”运动风起云涌。此风之下,金平默著《近思录附注》与《学统考》,朴世采编《东儒师友录》,宋秉璿撰《氵贝东渊源录》(或名《东儒渊源录》)与《皇朝遗民传》,河谦镇撰《东儒学案》,张志渊纂《朝鲜儒教渊源》等,社会上出现重建道统,回归传统的思潮。这是宋秉璿本土化建构的现实原因。
四是,宋秉璿思想相对保守,且生平尤重气节。他是朝鲜大儒宋时烈九世孙,生长于儒学世家。宋哲宪所作《年谱》称宋秉璿:“克述祖业,笃信好学。存天理而遏人欲,卫正脉而辟异端。叹王章伦纪之斁败,以守殷师之自靖。痛华夷人兽之无分,以明春秋之大经。”[4](卷50)生前对西方学说、西式服装颇多反对。郑思肖《心史》由李德懋传入朝鲜时,宋秉璿感激于此,多次以诗文题咏、评述之。及李朝被迫与日本缔结《乙巳条约》,继闵泳焕之后,宋秉璿亦服毒自绝,愤死殉国。这是宋秉璿进行本土化建构的性格因素。
四、结语
在中国儒学的海外传播史上,尤其是在韩国儒学的发展进程中,宋秉璿所撰《近思续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韩国儒学在承传中国儒学的基础上,已完成了本土化建构,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入20世纪,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大陆的传统儒学几乎凋零殆尽。相对而言,韩国儒学由于宋秉璿一辈人的努力与牺牲,却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更被当代人誉为“社会的良心”。所谓花开异邦,此之谓也。今日中国,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与必须提升国家“软实力”已成为共识,而复兴传统儒学也被更多的人视为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仍然有人认为传统儒学不过糟粕,于事无济。传统儒学究竟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如今黄海彼岸盛开的儒学之花,无疑给出了有力的回答。
参考文献:
[1]朱熹、吕祖谦编,查洪德注译:《近思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2]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朝]安克权:《晦轩先生实纪》,益山:韩国圆光大学图书馆藏1895年木版本。
[4][朝]宋秉璿:《渊斋先生文集》,首尔: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1907年木版本。
[5][朝]宋秉璿:《近思续录》,益山:韩国圆光大学图书馆藏木板本。
[6]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韩愈:《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9]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朝]宋时烈:《宋子大全》,《韩国文集丛刊》(115),坡州:景仁文化社,1990年。
[11][朝]朴趾源:《热河日记》,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4年。
[责任编辑全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