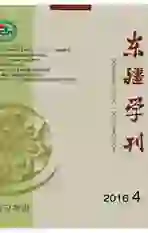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创作技巧及其手抄本的学术价值
2017-04-15韩东
[摘要]通过比较《热河日记》定本与手抄本的表述差异,可以发现,在定本中朴趾源出于“趣味性”的需要,运用了小说化的虚构手法进行了文学加工创作。同时,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虽然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不满与批判,但是出于“可读性”的需要,他对文字的创作遵循“一正一谐”的写作技巧,善于将严肃的问题与诙谐的表达结合起来。
[关键词]朴趾源;《热河日记》;手抄本;虚构;诙谐
[中图分类号]I31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3107
[收稿日期]2016-05-20
[作者简介]韩东,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与东亚文学关系。(南昌330000)
18世纪后期朝鲜实学家、文学家朴趾源的燕行记录《热河日记》,素来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到现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分类,可以发现,以“文化史”与“思想史”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是其主流关于国内学界的《热和日记》研究综述,可参看舒健、韩二帅:《国内学术界关于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研究综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56—59页。,而“文学”与“文本”研究一直不被重视。比如,朴趾源在创作《热河日记》时运用的文学手法与技巧问题;又如,以往研究的“文本”仅局限于1932年朴荣喆编辑出版的《燕岩集》中收录的《热河日记》定本,而对于并未公开刊行的诸多《热河日记》手抄本从未涉及。2013年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影印刊行了渊民文库所藏的朴趾源作品集,这其中就有几种《热河日记》的手抄本。韩国学者金明昊曾对这些手抄本与定本的差异做过介绍,但是不够详细,也未能说明这些差异背后所反映的问题。[1](1~19)所以,本文将以《热河日记》手抄本中的《热河避暑录》与《杂录》两种抄本为基础,通过比对与定本的差异,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并解读朴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写作手法,最后以此来说明《热河日记》手抄本的学术价值。
一、小说化的虚构情节
一般说来,燕行文献虽说都是作者身临其境,以记实的笔法对自己的体验所作的记录,但是作者要完成这种记录作品历来都离不开文学想象力。1765年燕行的朝鲜实学派先驱洪大容在北京与浙江文人严诚、陆飞等人结下深厚友谊,日后,当洪大容整理当时他们的谈话记录而创作《乾净衕笔谈》时,却遇到了大问题。
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但其谈草多为秋所藏,是以录出者惟以见存之草,其无草而记得者十之一二。其二十六日归时,秋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之一焉。且彼此惟以通话为急,故书之多杂乱无次,是以虽于其见存者,有问而无答者有之,有答而无问者有之,一语而没头没尾者亦有之,是则其不可追记者弃之,其犹可记者于三人之語,亦略以数字添补之,惟无奈其话法顿失本色,且多间现叠出或断或续,此则日久追记,徒凭话草其势不得不尔。吾辈之语则平仲常患烦故多删之,余常患间故多添之,要以干璿语势,不失其本意而已,其无所妨焉,则务存其本文。[2](174)
通过以上洪大容的自述,可以发现这个大问题就是由于“第一手资料”自身的缺陷,把这些杂乱无序、残次不全的资料整理成为一部记录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以致需要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力与技巧去填补资料的“空白”。也就是说,这些燕行记录的内容不是完全按照“写实”的原则进行的,其中有些部分是根据创作的需要添加了文学的写作技巧。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热河日记》定本的《避暑录》一篇中,朴趾源记述了自己在热河与清朝官员尹嘉铨、奇丰额交谈的场景,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清代性灵派文人袁枚的论述:
余问尹卿曰:当世诗人海内称首者,可得闻名欤?尹卿曰:以海内之大,固不乏鸿匠妙才,而敝年老断置人世事,年少才子未能相识。敝老友袁太史枚,字子才,高蹈不羁之士也,不乐仕宦,放迹山水,最工怀古之作。因高咏数句,余未晓听,请书示。其博浪城诗曰:真人採药走蓬莱,博浪沙连望海台。九鼎尚沉三户起,六王才毕一椎来。虎龙有气黄金尽,山鬼无声白璧哀。大索十日还撒手,如君终古尽奇才。观其诗可占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亨山之独咏此篇,其意尤著。然不讳于奇丽川,何也?[3](284)
以上内容主要谈到了朴趾源与尹嘉铨、奇丰额交谈时,尹嘉铨向自己介绍了袁枚的生平和他的怀古诗,而且这里朴趾源也表达了自己对尹嘉铨为何敢在满人官员奇丰额面前朗诵这首带有浓烈“挑衅”意味的怀古诗的“不解”。以上这段内容作为朴趾源认知袁枚的文献资料,被学界广泛引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怀疑这段材料的真实性。朴趾源真的和尹嘉铨、奇丰额一起谈论过袁枚吗?通过最近阅览到的《热河日记》手抄本资料,可以确定,定本中的这个场景,基本就是朴趾源运用小说化的虚构手法“杜撰”的。
韩国檀国大学渊民文库中有一本名为《热河避暑录》的手抄本,这个本子与定本中的《避暑录》不同,是由多条简短内容组成的。在手抄本的裱纸上,有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的题字。“避暑录手稿半卷,先王考手藁也,与今本小异而加详,未知元本初后更起此草者欤?当与今本参互,更为考定者。庚子暮春,孙珪寿识。”[4]从落款来看,可知题字时间为1840年,应当是朴珪寿偶然发现了与《避暑录》相关的朴趾源手抄本《热河避暑录》之后所写。对于为什么手抄本与当时已经流行的版本之间会产生差异,朴珪寿也一头雾水,他只是推测到这可能是自己的祖父在完成定本后,自己再写的一份草稿。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份手抄本应该是朴趾源在创作《热河日记》之前所用的笔记准备资料。比如这其中有一条名为“袁程陆汪褚蒋纪”,其内容如下:
李懋官与李雨村吏部语,雨村数称袁子才、蒋士铨俱翰林,而高踏不立于朝,放荡山水间。当今之博学如吏部主事程晋芳,翰林学士陆锡熊、陆费迟,翰林庶吉士汪如藻、少詹褚廷璋,翰林学士纪昀,而纪与陆锡熊方今总纂四库全书,皆海内名士也。其中袁子才当为第一,才子名枚,著述甚富,年今八十余,以庶吉士改上元知县,官止于此,然天下知与不知皆称袁子才云。雨村蔗尾轩闲谈,备言其事,最工怀古。[5](218)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袁枚的记述,但是根本找不到尹嘉铨与这些消息的关联性。事实上,在另一位朝鲜人李德懋的《清脾录》中也有关于袁枚及其怀古诗的记述。比如在《清脾录》的“袁子才”一条中有如下的内容:
袁枚,字子才,李雨村称之曰:子才当今第一才人,子才著述甚富,年今七十余,以庶吉士改上元知县,官止于此,然天下知与不知皆称道,余尾蔗轩闲谈备言其事。最工怀古,其博浪城诗云……雨村又曰:袁子才、蒋士铨,俱翰林而高蹈不立朝,放荡于山水江湖。如吏部主事程晋芳、学士陆锡熊、纪昀、陆费墀,庶吉士汪如藻,少詹廷璋皆当今现在之博学也。[6](58)
如果我们将《热河避暑录》中的“袁程陆汪褚蒋纪”与《清脾录》中的“袁子才”作一对比,可以发现二者的内容非常相似。李德懋《清脾录》的版本有朝鲜刊本,李调元的《续函海》本以及清刊本,朝鲜本为底本,《续函海》本为朝鲜底本删订再编本,而清刊本又是对《续函海》本修正后的三编本,朝鲜刊本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为1778年或之前,因为在这一年李德懋带着自己的《清脾录》踏上了燕行之路。[7](138~141)但是李德懋《清脾录》中关于袁枚的记述,有些是有误的,所以在《续函海》本《续函海》本中《清脾录》的内容,引自邝健行:《朝鲜人著作两种:乾净衕笔谈清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中,我们可以发现李调元删订的痕迹。具体情况如下表:
《青庄馆全书》本《清脾录》中的《袁子才》《续函海》本《清脾录》中的《袁子才》以庶吉士改上元知县以庶吉士改江宁知县余尾蔗轩闲谈备言其事余雨村诗话备言其事大索一旬还撒手大索十旬还撒手如吏部主事程晋芳,学士陆锡熊、纪昀、陆费墀,庶吉士汪如藻,少詹禇廷璋,皆当今现在之博学也。与吏部主事程晋芳,学士纪昀,皆当今之博学也。
从李调元的删订情况来看,李德懋对袁枚记述的谬误不少。其实,李德懋关于袁枚的认识是来源于朝鲜人柳琴。1776年,朝鲜人柳琴燕行时在北京结交了李调元,李调元在与柳琴的交谈中提到了袁枚是当今第一才子,并于1777年冬天,在寄给柳琴的信件中再次提到袁枚的情况,并录寄了袁枚的二首怀古诗。李调元当时寄给柳琴的信虽已逸失,但是对于这一往事,柳琴的侄儿柳得恭在《并世集》中却有详细记载。柳得恭的《并世集》编于1796年,所以李德懋不可能引用《并世集》的内容,柳得恭明确提到1777年李调元在给柳琴的信中提到袁枚,并附录了袁枚的怀古诗,由此可见,无论是李德懋还是柳得恭,他们对袁枚的认知都来自于柳琴,并且从他们对袁枚生平的一些错误记述如此雷同来看,他们应该都是从柳琴处听到了一些关于袁枚的错误“传闻”,这个错误的根源可能是李调元的误记,也有可能是柳琴的误传,但柳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李调元与柳琴相见的1776年,袁枚正好60岁,对于当时极力推崇袁枚的李调元来说,是不会记错这个信息的。而李德懋在1778年编撰的《清脾录》中误称袁枚70岁是因为他们无法考证袁枚的年龄,只能是从柳琴的口中得知。
因此,手抄本《热河避暑录》中关于袁枚的记述,实际上是朴趾源对李德懋《清脾录》的一种抄录和整理,即朴趾源对袁枚的认识是来源于李德懋,从文字的记述样式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同时,在《热河避暑录》中朴趾源写袁枚年“八十余”,这也是参看李德懋《清脾录》的结果。如按《清脾录》朝鲜刊本1778年完成算,那么《热河避暑录》的写作时间大致在1788年前后,这是符合《热河日记》的形成规律的。因为1791年朴趾源离开汉阳出任安义县监,1792年身在任中的朴趾源收到好友南公辙的书信。这是缘于《热河日记》脱稿后,因其“小品文”式的写作风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士人竞相传看,风气为之一变,当时的国王正祖对此相当不满,诏令朴趾源“改弦更张”,罚其重写“纯正”古文以赎其罪。朴趾源:《答南直阁书原书附》,《燕岩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252,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第35页。“近日文风之如此,原其本则莫非朴某之罪也。热河日记予既熟览焉,敢欺隐此,是漏网之大者。热河记行于世后,文体如此,自当使结者解之。仍命贱臣,以此意作书,执事斯速着一部纯正之文,即即上送,以赎热河记之罪。”由此可见,《热河日记》的脱稿时间肯定不会晚于1792年。所以,1788年前后完成的抄本《热河避暑录》便是定本《避暑录》的“前身”。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再看,朴趾源在定本《避暑录》中提到尹嘉铨当着奇丰额的面介绍袁枚,并朗诵其怀古诗的场景,便知这只是其在抄本内容上所进行的一种小说化“杜撰”,因为在袁枚的文集中并未提及尹嘉铨其人,反而与满人官员奇丰额颇有交情,互有寄书。无论怎么说,比起尹嘉铨,奇丰额反而更有发言权。
那么朴趾源为何这样费尽周折“杜撰”这样的故事呢?究其原因有二:首先,这与当时袁枚的名声在朝鲜广泛传播有关。1776年朝鲜人柳琴与蜀中才子李调元交往之后,朝鲜士人首次认识到了袁枚的名气与怀古诗,特别是以朴趾源为首的“燕岩集团”更是为之疯狂。比如,李德懋就曾在给清朝文人潘庭筠的书信中写道:“曾闻袁子才先生,文苑主盟,先生绍介之,则或有序记可得知端耶?先生其图之。”[8](263)他渴望得到袁枚亲自写的“序”或“记”,因而希望潘庭筠能为之引荐。但是潘庭筠和袁枚并无交情,且此时袁枚已離京寓居小仓山随园多年,潘庭筠最终没有允诺此事。柳得恭对此记述到:“李懋官因此书托秋欲得袁笔为集序堂记,秋复云:‘袁子才文名颇噪,欲其作序记仆不能作曹邱生也。”[9](109~110)“燕岩集团”的文人们虽然没能和袁枚建立直接的友情关系,但是他们总是会抓住一切机会显示对袁枚的“亲密感”。“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曾作《鬼趣图》,当时有名的文人墨客都有题跋,袁枚也题诗三首。而朴齐家、柳得恭于1790年9月与12月先后两次在袁枚的题诗左右进行题跋[10](579~580)。由此可见,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杜撰与袁枚有关的场景实际上与这一时期“袁枚”在朝鲜的影响力有关。其次,这与当时燕行录的创作特点有关。纵观燕行记录作品,对清朝事物的感知、满人的发型与服饰、汉人的不满与“思明”、文字狱的严酷与文人生活的束缚等话题一直是记录的重点。袁枚的《博浪城》怀古诗歌咏的是秦灭韩以后,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并最终全身而退的事迹,朴趾源杜撰汉人尹嘉铨在满人高官奇丰额面前高声朗诵这首具有“反抗”意味的诗歌,明显是有意以此挑逗读者的神经。
二、“一正一谐”的叙述手法
朝鲜时期的燕行记录文献多达500多种,而如果要说有哪一部作品从诞生之初就风靡一时,并且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话,那么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无疑堪当榜首。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热河日记》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文体。朝鲜后期文人金鲁谦就曾说:“大抵燕岩所著,热河日记最为盛行,脍炙人口……然以文诙谐,少谨严之意,故世或以小品目之,毁誉相半。”[11]“诙谐”气味太浓的《热河日记》在士人中争相传看的现象引起了当时朝鲜国王正祖的注意,《热河日记》最终成为了正祖推行“文体反正”的重要诱因。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写作方法不同于其他的燕行记录作品,明清小品文的“诙谐”式写作风格非常突出,而这一点常常体现在他讨论“严肃”话题时。比如,在《热河日记》定本的《还燕道中录》一篇的“二十日”记录中,有一段是朴趾源记述在主薄赵明渭卧室观赏古董之事,其内容如下:
即夕饭,赵主簿明渭,自讬其炕中陈设异玩,余即同赴。户前列十余盆花草,俱未识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许,沉香假山高二尺许,石雄黄笔山高尺余,复有青刚石笔山,有枣根天成魁罡,以乌木为跗座,价银为花银三十两云。奇书数十种,知不足斋丛书,格致镜源,皆值太重。赵君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为家,最娴汉语,且卖买之际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顾例于其所居为之陈列,以供清赏。而前年昌城尉黄仁点正使时,乾鱼胡同朝鲜馆失火,诸大贾之预入物货者尽为灰炉。而赵炕比他尤酷者,卖买物件之外,凡遭回禄者俱是稀奇器玩书册,兑拨则可值三千两花银,皆隆福寺及琉璃厂中物。而诸主顾即为借设,则无所征价,然亦不以此为戒,今其借排又复如昔,为娱心目,足见大国风俗不龌龊如此。夜留馆诸译,尽会余炕,略有酒馔,而行役之余,全失口味。诸人者皆睨坐右封裹,意其中有物,余遂令昌大解褓细检,无他物只是带去笔砚,垺然者皆笔谈胡草、游览日记。诸人者俱释然解颐曰:吾果怪其去时无装,归槖甚大也。张福亦怃然谓昌大曰:别赏银安在?[12](229)
韩国檀国大学渊民文库中有一本名为《杂录》的手抄本,在其下册抄录的《还燕道中录》“二十日”中也记载了朴趾源拜访主薄赵明渭,并观赏古董一事。其文如下:
即夕,赵主簿明渭自讬其炕中陈设异玩,余即同赴。户前列十余盆花草,俱未识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许,沉香假山高二尺许,石雄黄笔山、青刚石笔山、俱高尺余,有枣根天成魁罡,以乌木为底,价银三十两云。奇书数十种,价皆值太重,赵君燕行二十余次,最惯汉语,且卖买之际未甚高下,故多主顾例于其居为之陈列,以供清赏云。[13](361~362)
如将手抄本与定本中的记述内容做对比,可以发现手抄本《杂录》中的内容几乎与定本的前半截相同,不同的是手抄本中没有定本中谈论朝鲜馆失火与评论朝鲜文人喜好古董的风俗以及在自己居室里发生趣事的部分。据考证,《杂录》本的内容较定本简练,现在我们看到的《热河日记》定本的内容有很多是对《杂录》进行补充完善而来的,这里的引用部分也是如此。那么朴趾源为何要在原本简单的稿本中添加这么多的“故事”呢?首先,朴趾源在定本中添加朝鲜馆失火与评论古董喜好风俗的文字实际上与他对当时社会上盛行赏玩“古董书画”风气的看法有关。
18世纪的朝鲜社会有三种风气比较流行,那就是热衷明清小品文、西学知识以及嗜好古董书画的风气。[14](238)关于朝鲜士人嗜好古董书画一事有其特殊背景,是因为进入18世纪后,朝鲜的士人阶层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京乡”的差别,这主要是指生活在都城汉阳及京畿一带的世代为官、家庭富足的“京华世族”与生活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乡邑,严格奉行程朱理学的士大夫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差异。这些“京华世族”在燕行时亲眼目睹了清朝的文明兴盛,逐渐改变对清朝的看法,开始接受清朝的先进事物。加之,他们深受流入朝鲜书籍中的明清“赏玩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通过燕行时在清朝购买大量的“古董书画”,所以在当时的朝鲜出现了不少古董收藏家与藏书家。[15](66~75)他们对儒家强调的“玩物丧志”不以为然,在追求“古董书画”的赏玩中无法自拔。但是,朝鲜后期出现的这种奢靡之风给朝鲜社会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比如朝鲜后期文人李遇骏说道:
而见今公私日益荡残,财力岁渐消耗,此偈故焉?余常入燕,见译员中与群胡贸易,则无一养生日用之具,都是具玉香缎诸般奇货,而珊瑚一枝,琥珀一块,价至银三十两,有缨子一件,造以蜜花而呼价银子八十两,吸烟一个,煅以真玉,而论价银二十两,余外所买,莫非此类。饥者不得为栗,寒者不可为褥,而万里外国,岁岁来贸,以无用害有用,蠹国病民者,是孰使之然哉……每见我京钟街上,摆列百货误人耳目者,太半自燕都琉璃厂而来者也。至于服食器用之资,反为少利,而不甚取来。[16](121~123)
燕行时的贸易活动其初衷是为了在充盈国库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进入18世纪以后,朝鲜社会中嗜好“古董书画”的风气盛行,这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富有的京华世族把大量的金钱浪费在琉璃厂的奇珍异玩上;另一方面,商人为了求利,在进行贸易活动时,有意识地购买大量并无实际用处的古玩,却忽视了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物资。这两个问题就导致了国家的财富逐渐减少,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李遇骏对这些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事实上,当时的京华世族中就有因为追求这些奇珍古玩而散尽家财的。赵熙龙在《海外谰墨》中就曾写道:“近来,金杨根光遂,尚书东弼之子也。为人放旷疎雅,散尽家赀远购燕市,多致古书名画砚墨彝樽之属,终日吟弄其间。扁其斋曰:‘尚古,自作圹志,使李匡师书之。”[17](15~16)朝鲜后期文人把追求“古董书画”的奢靡之風,俨然当做是自己的“尚古”之道。
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比对手抄本与定本的差异,就可以看到,朴趾源对于这种风气也是担忧的。众所周知,朴趾源是朝鲜后期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空洞无用的“北伐论”以及轻视清朝的态度,主张学习清朝的先进文明,提出了“利用厚生”的理念。“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豚栅,莫不疎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皆精丽如画。嗟乎!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18](151)朴趾源认为实学的根本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清朝,并且学习的对象就应该是清朝人实实在在处理自己生活的方式与态度,对于朴趾源来说,追求奇珍异宝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在《热河日记》定本中,朴趾源在记述了去赵主薄居室观看“奇玩”一事之后,又着重对在往年朝鲜馆失火财物损失后,人们没有引起重视,反而继续“排借”奇珍异玩的现象进行了评论。其实朴趾源添加这段文字,是因为当他从清朝回来后,对朝鲜社会上嗜好“古董书画”的奢靡之风进行了反思,这种风气和“利用厚生”的主旨不符,朴趾源通过添加这些内容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担忧。
同时,在定本《还燕道中录》的最末部分,朴趾源又添加了手抄本《杂录》中没有的逸事,那就是关于大家疑惑朴趾源从热河带回来的包袱里究竟装了多少金银而闹出的笑话。其实包袱中本没有钱财,只有朴趾源带回的记录其在热河时与中国人交谈的“谈草”,由于纸张较多导致包袱隆起,这让昌大等人甚是期待,因而才有了末尾那句“赏银安在”?那么,朴趾源为什么要添加这段内容呢?其实无论是在定本还是手抄本中的《还燕道中录》“二十日”中都有描述下人“张福”与“昌大”相见时的一段话:
昌大见张福,不叙其间离索之苦,直言汝有别赏银带来。张福亦未及劳苦,笑容可掬,问赏银几两?昌大曰:一千两,当与尔中分。张福曰:汝见皇帝否?昌大曰:见之,皇帝眼似虎狼,鼻如火炉,脱衣赤身而坐。张福问:所冠何物?曰:黄金头盔,招我赐酒一大杯曰:汝善陪书房主,不惮险而来,奇特矣。上使道一品阁老,副使道兵部尚书,无非荒话,非但张福受诳,下隷之稍知事理者,莫不信之。[12](228)
昌大见张福,不索其间离索之苦,直言汝有别赏银带来。张福亦未及劳苦,笑容可掬,问赏银几两?昌大曰:一千两,当与尔中分。汝见皇帝否?昌大曰:皇帝眼似虎狼,鼻如火炉,脱衣赤身而坐。所冠何物?曰:黄金盔,招我赐酒一大杯曰:汝善陪书房主,不惮险远而来,可尚。上使道一品阁老,副使道二品兵部尚书,无非谎话以诳之,而非但张也福受诳,马头之稍知事理者,莫不信之,不觉绝倒。[13](358)
如果比对手抄本与定本可以发现,核心内容几乎一样,但是在个别用词,特别是问答的衔接上,定本修正、添加了不少名词与助词,使得语句的表达更加流畅完美。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在手抄本中,多了一句“不觉绝倒”,这句话起到了对张福与昌大的对话做总结的作用。所以在手抄本“二十日”的最后部分,就再没有关于赏银的笑话故事。而在定本中朴趾源删去了具有总结意味的“不觉绝倒”,在附加评论社会上“古董书画”嗜好之风的内容后,继续添加了富有喜剧效果的桥段。显然,这是朴趾源自己在添加比较敏感而严肃的话题后,出于缓和气氛而运用的一种文学写作技巧。实际上,因为有了最后一段众人疑心银两的场景,以及昌大喊出那句“赏银安在”?让整段文字的“诙谐性”得以显现。朴趾源比较善于使用这种“一正一谐”的创作手法。
再比如,同样在《还燕道中录》“二十日”的记录中还有关于对朝鲜饮酒习惯的论述。
东人饮酒毒于天下……必以大椀蹙额一倒,此灌也非饮也,要饱也非要趣也。故必一饮则醉,醉则辄酗,酗则辄致斗驱,酒家之瓦盆陶欧,尽爲踢碎,所谓风流文雅之会,非但不识为何状,反嗤此等为无饱于口腹,虽移设于鸭水以东,不能竟夕已打破器玩,折踏花草,此为可惜。李朱民,风流文雅士也,平生慕华如饥渴,而独于觞政,不喜古法,无论杯之大小,酒之清浊,到手辄倒,张口一灌,同人谓之覆酒,以为雅谑。是行也即定伴当,而有谗之云:使酒难近,余与之饮十年矣,面不潮枫,口不噀柹,益饮益庄,但其覆法少疵。朱民常抵赖曰:杜子美亦覆酒耳,呼儿且覆掌中杯,岂不是张口而偃卧,使儿童覆酒耶?尝大笑哄堂。万里他乡,忽思故人,未知朱民今?此刻,坐在何席?左手把杯,复能思此万里游客否?[12](228)
朴趾源曾在北京的酒肆中看到了中国人聚会时以小酒杯饮酒的风俗,由此以上的内容实际是朴趾源在批评朝鲜以大碗灌酒的民风。因为他认为朝鲜士人喝酒的模样不仅不够雅致,而且大碗狂饮易醉,醉后丑态百出以致斯文扫地,这里朴趾源还以自己的朋友李喜明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手抄本中,朴趾源表达了好友没能一同来中国的遗憾,因为他认为如果心慕中国的李喜明也看到中国士大夫是这么饮酒的话,肯定会改变以前豪饮的陋习。但是在定本中朴趾源删掉了这种遗憾的情感,又添加了李喜明自己谈论饮酒陋习一事,因为引用了杜甫的趣事,文章内容增添了不少的“诙谐感”。比较手抄本与定本中关于《还燕道中录》“二十日”的记事,可以发现定本不仅内容变得丰富,结构上也起到了前后呼应的效果,这就是朴趾源在创作《热河日记》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文章内容与写作技巧的体现。
众所周知,在《热河日记》中,朴趾源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但是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朴趾源是怎么处理这些严肃的批判意识的,朴趾源让原本严肃的话题变得具有“喜剧性”,这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在创作理论上,朴趾源虽然强调“真”的本质论与“法古创新”的活法论,但是他的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是脱节的,由于怀才不遇的个人际遇,他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透露着强烈的讽刺精神,他的创作走上了“以文为戏”的道路,[19](60~67)而“一正一谐”的叙述手法便是朴趾源“以文为戏”的惯用技巧。
综上所述,《热河日记》是朴趾源对文字进行反复推敲的一部作品,这从定本与手抄本的表述差异上就可以确定,而在这些推敲的过程中,朴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写作技巧被凸显出来。即《热河日记》并不是完全按照“记实”的手法来完成的,朴趾源出于“趣味性”的需要,运用了小说化的虚构手法进行了文学加工创作。同时,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虽然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不满与批评精神,但是出于“可读性”的需要,他的创作遵循了“一正一谐”的写作技巧,所以朴趾源的“以文为戏”并不全是“无实”之谈,他只是善于将严肃的问题与诙谐的表达结合起来。当然,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这些写作技巧的发现,离不开《热河日记》手抄本的发现与比对。因此,《热河日记》的研究应当注重手抄本的研究价值,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樸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心态与特点。
参考文献:
[1][韩]金明昊:《『』》,《东洋学(48)》,2011年。
[2][韩]洪大容:《乾净录后语》,《韩国文集丛刊(248)》,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3][韩]朴趾源:《避暑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4][韩]朴趾源:《避暑录手稿半卷》,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编,《渊民文库所藏燕岩朴趾源作品手抄本丛书(5)》,首尔:文艺院,2013年。
[5][韩]朴趾源:《热河避暑录》,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编:《渊民文库所藏燕岩朴趾源作品手抄本丛书(5)》,韩国首尔:文艺院,2013年。
[6][韩]李德懋:《清脾录(4)》,《韩国文集丛刊(257)》,韩国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7][韩]朴现圭:《清嘉庆续函海刊本李德懋<清脾录>》,《顺天乡语文论集(7)》,2001年。
[8][韩]李德懋:《潘秋庭筠》,《韩国文集丛刊(257)》,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9][韩]柳得恭:《并世集》,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0)》,首尔: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韩]郑珉:《18世纪韩中文人的文艺共和国》,首尔:,2014年。
[11][韩]金鲁谦:《梦呓》,《性菴集(卷7)》,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本,图书番号古朝—46。
[12][韩]朴趾源:《还燕道中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13][韩]朴趾源:《还燕道中录》,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编:《渊民文库所藏燕岩朴趾源作品手抄本丛书(3)》,首尔:文艺院,2013年。
[14][韩]正祖:《日得录》,《弘斋全书(5)》,首尔:太学社,1986年。
[15][韩]金熙敬:《明清赏玩文化对18世纪朝鲜文人之影响》,《中国学论丛(23)》,2008年。
[16][韩]李遇骏:《梦游野谈(上)》,首尔:宝库社,1994年。
[17][韩]赵熙龙:《海外谰墨》,[韩]姜明官:《朝鲜后期京华世族古董书画趣味》,《东洋汉文学研究(12)》,1998年。
[18][韩]朴趾源:《渡江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年。
[19]韩东:《谈朴趾源的文学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