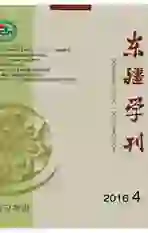论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新儒学思想倾向
2017-04-15金哲洙
[摘要]由金富轼主持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正史。从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视角看,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所应用的儒学思想综合地反映着高丽中期儒学所达到的水平。在《三国史记》中,既有汉唐儒学的影响,还有北宋时期勃兴的新儒学的影响。深入分析《三国史记》所反映的新儒学思想倾向,对于我们系统把握高丽中期儒学思想乃至朝鲜儒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富轼;《三国史记》;新儒学;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B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1306
[收稿日期]2016-05-22
[作者简介]金哲洙,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哲学思想史。(延吉133002)
《三国史记》是由朝鲜高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金富轼根据王命于1145年率领多名史书编修者编撰的一种官撰形式的史书。该书共50卷,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有关古代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历史的著作。它以纪传体的形式记载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上下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们研究朝鲜古代史不可缺少的著作。
从朝鲜儒学思想史的角度看,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所应用的儒学思想综合地反映着高丽中期儒学所达到的水平。因此,深入分析《三国史记》所反映的儒学思想倾向,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高丽中期儒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金富轼和《三国史记》的编撰
金富轼(1075-1151年),高丽中期著名政治家与史学家,字立之,号雷川,谥号文烈。1096年(高丽肃宗元年),金富轼科举及第,并开始走上仕途。金富轼先是到当时首都开京(今朝鲜开城)以西之海州“补安西大都护府录参军事”[1](376),俟“考满”后经时任枢密院承宣的魏继廷推荐,任“直翰林院”,而后二十余年历任右司谏、中书舍人等职。
金富轼曾经先后两次奉命出使宋朝。1116年(高丽睿宗11年,宋徽宗政和6年)7月,金富轼随同高丽王朝枢密院知奏事、正使李资谅及副使李永而出使宋朝,以谢宋朝赐大晟乐。此次金富轼一行在宋朝滞留半年以上,至翌年3月始回国。使宋期间,金富轼从宋朝得到了一部司马光所修《资治通鉴》,在史观及历史编纂乃至文风方面受到《资治通鉴》的重大影响。[2](475)1126年(高丽仁宗4年,宋钦宗靖康元年)9月,金富轼以正使资格再度使宋,以贺宋钦宗即位。当时的宋朝官府,却以高丽臣事金国为由,仅令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方官“递表以进,遣其使还”。
1142年(高丽仁宗20年),金富轼接连三次上表请求致仕,国王仁宗“许之,加赐同德赞化功臣号,诏曰:‘卿年虽高,有大议论,当与闻。”[3](222)金富轼致仕后,开始主持编纂“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史”,至三年后的1145年(仁宗23年)始得完成,并将其题作《三国史记》以呈国王。一年后的1146年(仁宗24年),国王仁宗去世,太子睨(又作微)继其王位,是为高丽王朝第18代国王毅宗(1146—1170年,在位:1147-1170年)。至1151年(毅宗5年),金富轼去世,享年77岁,毅宗赐谥号“文烈”,并赠职中书令,命配享仁宗庙庭。据《高丽史·金富轼传》,金富轼有文集20卷,今已失传,其诗文散见于《东文选》等著作之中。
根据历史记载,在《三国史记》之前就已经有了《旧三国史》。李奎报曾经说:“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踰世之所说者。……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1](33)由于《旧三国史》已经失传,所以我们难以了解《旧三国史》的全貌。不过,根据金富轼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到,金富轼是以《旧三国史》为基础来撰写《三国史记》的。
在撰写《三国史记》过程中,金富轼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写《三国史记》是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朝鲜留下历史记录。他指出:“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4](14)应当说,这一点主要反映了金富轼对本国历史文化的重视态度,也表明金富轼有着较为透彻的国家意识和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金富軾对高丽中期国际环境的认识,也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二,《旧三国史》有关“新罗氏、高句丽氏、百济氏”等“吾邦之事”的“古记,文字芜诎,事迹阙亡”。[4](14)试举一个例子。金富轼指出:“新罗古事云,天降金柜,故姓金氏。其言可怪而不可信,臣修史,以其传之久,不得删落其辞。”[4](119)这表明,金富轼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排斥不合常理的迷信思想或言论。
第三,鉴古戒今。从儒家的立场上讲,历史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关于这一点,金富轼有着自觉的意识。他说:“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4](14)这一点主要反映了以诗文名满当世的金富轼的文化观及史学思想。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就是为了整理历史文化遗产,以便树立东国意识,促进文化整合,并且为现实政治的发展提供借鉴。
此外,当时的高丽王朝,无论从疆域领土还是从文化传承上都是直接继承了此前的千年王朝新罗(前57—935年),即高丽是继承古代新罗王朝或“三韩”的国家。出身庆州(古代新罗王朝首都)金氏门阀贵族的金富轼,无疑是视新罗为正统的一个代表。《三国史记》之内容编排,以新罗为首,而后依次为高句丽及百济,即集中反映了金富轼以新罗为正统的历史认识。至于当初命金富轼编纂《三国史记》的国王仁宗,无疑也是这样一种新罗正统史观的支持者甚至提倡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国史记》的编纂及其刊印,是当时高丽王朝为确立新罗正统史观而着力推行的一项政治性文化工程,并对此后朝鲜半岛古代历史认识体系乃至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史记》是金富轼根据国王之命在8名官员的协助下编成的一部史书,不同于完全由个人编写的私史。因此,金富轼并不是以“监修国史”的官员身份主持编纂的,而致仕之际已经是年近古稀(68岁)的他也不可能亲自完成多达五十卷的《三国史记》的全部编纂工作。查《三国史记》第五十卷后列有参与编纂工作的相关人员名单,引述如下:
参考宝文阁修校文林郎礼宾丞同正臣金永温;参考西材场判官儒林郎尚衣直长同正臣崔祜甫;参考文林郎国学学谕礼宾丞同正臣李黄中;参考儒林郎前国学学正臣朴东住;参考儒林郎金吾卫录事参军事臣徐安贞;参考文林郎守宫署令兼直史馆臣许洪材;参考将仕郎分司司宰注簿臣李温文;参考文林郎试掌治署令兼宝文阁校勘臣崔山甫;编修输忠定难靖国赞化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太保门下侍中判尚书吏礼部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致仕臣金富轼;司管句内侍宝文阁校勘将仕郎尚食直长同正臣金忠孝;管句右承宣尚书工部侍郎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臣郑袭明。[4](514)
金富轼的职衔及“编修”之名不仅见于此处,还于孽卷之首分别署以“输忠定难靖国赞化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门下侍中判尚书事兼吏礼部事集贤殿太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致仕臣金富轼”[6](514)字样,从而无可辩驳地表明金富轼主持编修工作的总负责身份与地位。
上述名单中“管句”及“同管句”,性质上应相当于当时高丽王朝于宝文阁所设管句及同管句职。所谓“管句”,意即“管掌”,或作“管理稽句”解。而“同管句”之“同”则意同“副”字,职位低于“管句”。鉴于《三国史记》的编纂出自王命,这两名“管句”及“同管句”应是深受国王宠信的文臣,其作用应是辅佐金富轼来主持编纂工作。任“管句”之郑袭明就是当时科举出身的著名文臣。他不仅是国王之亲信,同时也是得到金富轼信任与赏识的文臣,而这正是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障。
至于以“参考”之名参与编纂工作的8人,都是品阶在从九品至正九品之间的低级文官。他们大体应是出身科举的文士,而且应是金富轼奉王命开始编纂工作之后亲自选拔的。他们在编纂工作中的主要作用应是从事整理与查核相关资料并进行校勘等辅助工作。这样一种编纂体制,与高丽王朝当时已然形成的史官制度并无直接联系,基本上可以视作由致仕元老金富轼个人主持并得到国王及相关人员支持的一种半官方性编纂工作。
这些低级文官的事迹不见于高丽王朝时期公私文献,足见其地位之低,惟有崔祜甫一人后世发现其墓志铭,其中即称“相国乐浪公金富轼被命撰三国史,公时为雠校,多所发明”云云。查阅《三国史记》中对有关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与朝鲜半岛古代相关记录的异同点,可以发现《三国史记》中的历史记载大都经过比较认真的核对鉴别,并广泛征引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朝鲜半岛的各种记载。如此艰难细致的基础性资料工作乃至后期的资料核对与文稿校勘诸务,显然不是当时已经年近古稀的金富轼所能独立完成的,无疑要借助于这些文士出身的8位“参考”的辛勤努力。
《三国史记》的编纂工作,大致开始于金富轼获准致仕的1142年(高丽仁宗20年),而金富轼最终完成编纂工作并将其呈献的时间是1146年2月4日(高丽仁宗23年12月壬戌)。由此可知,《三国史记》的编纂经历了近四年的时间。
二、儒家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史书不仅仅是历史的一个简单的纪录,而且也渗透着史家的历史观。众所周知,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深受儒家历史观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历史观的基本内涵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首先,儒家历史观以评判过去的善恶、是非、功过,并加以褒贬,劝善惩恶为宗旨,以鉴古戒今为目的。所以,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垂训、实用倾向的道德史观。儒家思想是把人类社会的秩序放在伦理道德层面上通过教育去实现的。其评判和褒贬的标准是经学的基本精神。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没有垂训功能的历史叙述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其书名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其次,立足于儒家史观的大部分史书都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而写的。这是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儒家史观的一个局限性所在。
再次,儒家的修史方法非常重视文献证据。儒家历史观要求修史者彻底遵守“以实直书”的原则,不允许无中生有或随意改变事实的做法。所以,儒家史观具有非常浓厚的实证性质。不过,重视文献实证,并非什么样的内容都被修史所利用。它不是机械地罗列资料,而是根据一定的标准严密选择资料进行排列并加以评价的。所以,儒家史观对于不合理的、荒诞不经的、严重与纲常相抵触的内容是不予记载的。这就是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的“笔削”原则。这样一个主观性的介入使春秋笔法難以保证普遍性和客观性,这是儒家史观的主要的局限性。
《春秋》多从“礼”与“非礼”评断史事,决定“书”与“不书”及如何“书”,甚至为尊、亲、贤者讳。明明是晋文公召见周天子,却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企图通过道德训诫,规范统治者的行为。就历史评断的手段来看,《春秋》寓褒贬于文辞,《左传》则改以史评方式,于叙事之后,或引用权威人物(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论,或直接议论“礼也”、“非礼也”。
修史时,于总结前朝得失和进行道德说教两者之间,或许有所侧重。唐初的唐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设史馆于禁中,以重臣参与监修前史,开官修史书之先河。魏征主编的《隋书》即注重取鉴。而唐太宗“御撰”的《晋书》则更多地从“敦励风俗”着眼,突出忠孝道德。
在新儒学兴起后,史学深受其影响。宋明新儒学的史学,一方面继承传统史学,把褒贬人物、劝善惩恶、探讨治乱成败作为史学第一要义;另一方面又接受理学言心论性、重视道德内省的影响,不再把治乱兴败的终极原因归结于政治与军事,而是归因于伦理道德,尤其是君主的个人修养与行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赐其名的。为达此目的,司马光还继承了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对前代统治者的丑行和失误予以披露与抨击。但是,司马光又认为历史著述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因而其在史料选择、史实确认、人物评断、治乱分析等方面都以儒家的礼乐教化为主要标准。南宋朱熹编写《资治通鉴纲目》则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并注意褒贬义法。他陈述自己的编纂目的与手法时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5](21)还有,用于褒贬的儒学思想的重心也从“忠孝”思想转换为以“德治”为内容的“仁政”思想。
应当指出,以历史为鉴戒,古今东西皆同,无可厚非。我们并不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但儒家学者的修史是以治者获得资政的启示为主要目的。因而,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写成的历史,或者成为只记述一朝一代成败的政治兴亡史,或者以典章制度的损益为主要内容,或者充斥对于历史的道德评价,都不足以引导人们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历史及其规律性。
三、《三国史记》的新儒学思想倾向
高丽中期,在儒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经世义理之学。换句话说,高丽中期儒家学者和统治者更为关注的是北宋新儒学倾向即经世义理之学倾向。如果说高丽中期的心性性理之学倾向只停留在抽象的谈论阶段的话,那么,高丽中期的经世义理之学倾向则直接落实在实践上。这种实践不但导致高丽中期出现了政治改革,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成果,即《三国史记》。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运用的儒学思想主要属于儒学的外王之学。因为儒家修史的目的就在于为统治阶级提供治理国家和百姓的方法和途径。儒家经典和史书在儒家知识系统中是一种体用的关系。儒家学者用什么样的历史哲学指导史书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想。
那么,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是以什么样的儒学思想作为编撰的指导思想的呢?儒家在褒贬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时经常使用的概念通常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勇、德、道,等等。下面,本文将考察《三国史记》中对这十个概念的使用问题,进而来了解金富轼的思想倾向。
(一)关于“仁”的概念。《三国史记》使用“仁”的频率比较高,金富轼在这里主要是围绕以国王为中心的统治者行为的德行使用的。如,“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6](68);“君不恤民,非仁也”[4](387);“新罗其君,仁而爱民”[4](367);“况闻高句丽王公,仁厚勤俭,以得民心”[6](513);“夫仁之心归于至仁”[4](387);“不义于国,不仁于民”。[4](516)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富轼在运用“仁”这一儒家核心思想时强调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行“仁”则“义”,否则就“不义”。作为君主必须具备的德行就是“仁”,如果君主不实行“仁政”就应下台,没有资格继续维持王权。这些都表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是非常重视“仁政”思想的。这些思想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君主应具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要实行仁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民心,国家才能富强。如果不实行仁政,人们有权发动改朝换代。
(二)关于“义”的概念。如果说金富轼关于“仁”的思想受了孟子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关于“义”的思想也必然受孟子思想的影响。在孟子的思想中,“义”是与“仁”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对“义”这个概念,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是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单独使用;二是与“仁”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来使用,即“仁义”。首先看一下“义”字单独使用时的含义。“义”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需要遵守的“规范”。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义”,《三国史记》中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存慰百姓,即“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其二,不可把国王陷于杀人之罪;其三,不可把王位传给不仁者,“今大祖王不知义,轻大位,以授不仁之弟”,[4](374)其四,废昏君而立明君,“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6](509)對于《三国史记》的编者来说,对“人民的义”优先于对“君主的义”。进而言之,人们有权撤换不能实践对人民的义的君主,认为这是“天下之大义”。
而就“仁义”这个复合概念而言,在金富轼看来,“仁义”乃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德行。“仁义胜,则难情消”[6](403)、“时称仁义之乡”[4](225)、“今大王不知义,轻大位,以授不仁之弟”[4](374)等说明,仁的实践就是义,不实践义则是不仁。仁君可以征伐不仁之君。换句话说,“以仁伐不仁”是“自古亦然”的“大义”。这就是说,统治者“仁义”与否,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必须的“德行”,还决定着王位的安危和国家的兴亡。这和《孟子》一书中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孟子说:“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7](33)在孟子看来,不具备仁义的君主根本没有资格当君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而已。
(三)关于“礼”的概念。“礼”在《三国史记》中勿庸置疑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问题是,能否把“礼”看成是支撑着《三国史记》儒学思想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在金富轼的儒学思想中“礼”是从属于“仁义”的下位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遵守上下秩序,依据身份的不同来加以对待”。如“葬礼”、“厚礼”、“备礼”等等,如不这样做则是“非礼”、“礼慢”。“礼”和“事大”问题有着密切关联,所以这里要论及“事大主义”问题。不过,“事大之礼”对于统治者并不是像“仁义”那样必不可缺的德行,而是“应遵守的好的规范”而已。还有一种含义是指“习俗规范”。如“商人之礼”[4](38)、“虽外国各异俗资之以中国之礼”[4](80)、“况妇人而夜行,岂礼云乎”[4](389)、“然礼不以日月为名”[6](353)等就具有这种含义。在这个意义上,金富轼主张“外国各异俗”,不必强求统一风俗。所以,“礼”并不是贯穿《三国史记》或贯穿金富轼儒学政治思想的普遍的、根本的原则。
(四)关于“忠”概念。《三国史记》中对“忠”的用法大致和传统的用法是相一致的,即强调小国对大国的忠诚和臣下对君主的忠诚。不过有一点比较特别,那就是金富轼有意强调君主要善于识别忠臣及要善待忠臣。如,“臣不谏君,非忠也”[6](482)、“忠言逆耳,利于行”[6](380)、“忠臣死不忘君”[6](116)、“远邪佞尽忠直”[6](380)、“李斯尽忠,为秦极刑”[6](473),等等。也就是说,金富轼在这里把“忠”的思想和“尚贤”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忠”成为君主识别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五)关于“孝”的概念。在《三国史记》中,“孝”常常是与“忠”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其用法也是和传统的用法大体一致。
(六)关于“智”的概念。《三国史记》中的“智”主要用于智略、智识意义,指的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智识过人”、“聪明多智略”、“身长而多智”,等等。
(七)关于“信”的用法。在《三国史记》中,金富轼对“信”并没有赋予特别的含义,它主要是国与国之间、君臣之间应遵守的德行。
(八)关于“勇”的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武勇,如“吾儿年才十六,志气颇勇”[4](141)、“有力而好勇”[4](344);二是实践义之勇气,如“见义不为无勇”。[4](280)
(九)关于“德”的概念。实践“仁政”的意义。“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4](113)。
(十)关于“道”的概念。“道”在《三国史记》中通常是与“仁义”的实现与否联系起来使用的,如“敌国无道”[6](355),“今国王无道”[4](410)、“初次大王无道”[4](387)、“王曰:本欲兴道而杀不辜,非也”[4](108)。
从以上的分析看,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比起“忠孝”,更加重视“仁义”,“礼”的思想也是从属于“仁义”思想的。换句话说,支撑着《三国史记》的根本的儒学思想是“仁政论”思想。这说明金富轼的儒学思想明显受到了北宋新儒学思想的影响,即重视《孟子》的思想。
众所周知,《孟子》一书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孟子》以仁义为基础,提倡依靠君子的王道政治和仁政论,提出了性善说(天命论)、革命论、人性论等思想,完成了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孟子》还具体论述了许多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等。与儒家的其它经典相比较而言,《孟子》一书更重视儒家的经世之学。
孟子在中唐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此外,在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中,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大约从中唐以后起,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地,孟子的名字侧于了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统治者封上了爵号,并从祀孔庙;孟子其书也被增选入儒经之列,并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了“五经”而跻身于“四书”,成为了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到明清时期,“孔孟之道”则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韩愈可以说是最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的人。韩愈推尊孟子的理由,椐他自己说主要是两点:其一,唯有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其二,孟子具有辟异端邪说的卫道之功。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从“周孔之学”向“孔孟之学”的转变,是汉唐儒学和宋明儒学的一大分界。[8](376)
金富轼特别重视《孟子》。在高丽中期,《论语》是国子监的必修科目,因此非读不可,而《孟子》却不是必读科目。然而,金富轼对《孟子》的认识已经達到了较高的水平。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的学问论、贤人论、人才论观点均受到了《大学》的学问方法论和《孟子》仁政论的影响,他的人民观也有着浓厚的孟子民本论、革命论思想的痕迹。
金富轼重视《孟子》一书,说明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了儒家学问中的“为己之学”、“经世之学”的一面,这与只重视词章学的汉唐学风有明显区别。
总之,《三国史记》是高丽中期儒学发展的产物,是高丽中期政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经世思想,首先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正是为了“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4](14)。笔者无意否定《三国史记》的诸多缺陷,但从儒学思想史角度来讲应当肯定金富轼及《三国史记》的历史地位。儒家史学思想之所以能在朝鲜扎下根基,金富轼是有贡献的。另外,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所运用或重视的是儒学思想中有关“仁义”和“仁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褒贬历史的标准。金富轼的儒学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而重视和强调孟子思想正是北宋新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周孔之道转向孔孟之道是汉唐儒学和宋明儒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界。金富轼能够把握这样一个分界,自觉地用孟子的思想来评断和褒贬历史,说明他对北宋新儒学的发展动向是有很深的了解的。不然的话,他是不可能熟练地运用仁义、仁政思想的。
参考文献:
[1][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国译东国李相国集(卷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6年。
[2][韩]权重达:《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首尔:中央大学校出版部,1998年第1辑。
[3][韩]金宗瑞编著:《高丽史节要(卷9)》,首尔:明文堂,1991年。
[4][韩]金富轼编:《三国史记(上)》,首尔:乙酉文化社,1996年。
[5]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自序》,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年。
[6][韩]金富轼编:《三国史记(下)》,首尔:乙酉文化社,1996年。
[7]《孟子·梁惠王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8]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