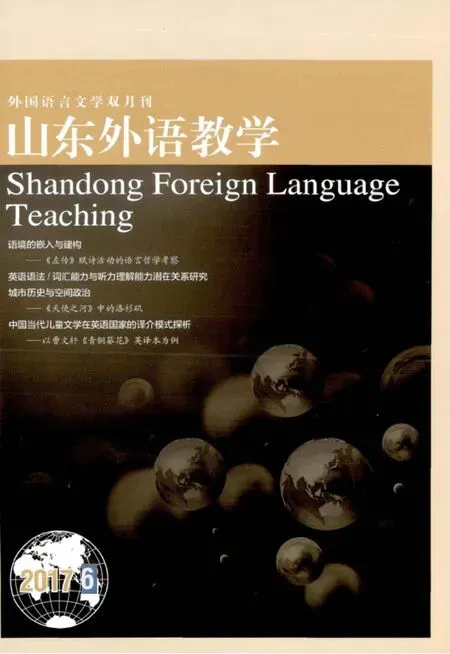爱与种族
——评莫里森书写人性镜像之《爱》
2017-04-10王玉括
王玉括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23 )
爱与种族
——评莫里森书写人性镜像之《爱》
王玉括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23 )
莫里森始终关注“爱”这一主题,在多部作品中书写爱的不同方面。作为新世纪的第一部作品,她的《爱》不仅深化了对“爱”的思考,而且延续了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中对“爱”的解放与疗救功能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爱与非裔美国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爱与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破解非裔美国社区中传统的“爱-恨”二元对立模式。
《爱》;种族;解放
1.0 引言
莫里森很早就明确陈述其创作主题是“爱或爱的缺失”(Taylor-Guthrie,1994:xii)。从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开始,爱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书写的对象,在不同的语境与社会环境下,莫里森对爱的表现各异,读者通常难以看到浪漫小说或言情小说中常见的温馨与浪漫,更多的是爱的“异化”与暴力,以及各种异样、暴力的爱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为何《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父亲居然只能用奸污她的手段才能表达自己被扭曲的爱,为何《秀拉》中的母亲伊娃为了让儿子活出男人的尊严,竟然不惜亲手结束意志废残的儿子的生命,为何《所罗门之歌》中奶娃的母亲需要近乎乱伦的表示才能体现自己对父亲的真情,都令读者感到惊悚。莫里森“爱”的三部曲中,《宠儿》主要聚焦美国重建时期,叙述母亲之爱,为自己的孩子免遭奴隶制的非人折磨,母亲居然亲手锯断年仅2岁女儿的喉管,十多年来独自忍受人们冷漠与不解的目光;《爵士乐》聚焦1920年代,叙述黑人男女之间忘年的浪漫之爱,男主人公因为对自己年轻的情人爱得太深,居然不惜枪杀她,在痛苦中独自忍受“爱”的折磨;而《乐园》则讲述上帝之爱,为了表达对上帝的虔诚,净化所谓社区的环境,竟然要杀害几个藏身于修道院中的无辜女子。这些浓烈到难以化解、几乎令人窒息的极端的“爱”及其表现方式,使莫里森笔下的文学世界异常诡异,更迫使人们思索这样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爱”?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爱的悲剧?这些困惑在莫里森聚焦民权运动时期的新作《爱》中有无了结,又有哪些新的特点?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继续聚焦“爱”这一主题,而且有所深化,不仅在主题方面一以贯之地予以拓展,而且在创作形式上,继续其勇于实验的特点。
2.0 爱及其发展
莫里森新世纪以来的《爱》(2003)、《悲悯》(2008)、《家》(2012)与《上帝保护孩子》(2015)继续向读者展示其高超的创作技艺与思考的深入。本文所关注的小说《爱》更是被《纽约时报》称赞为“这是她《宠儿》之后最好的小说”,和莫里森其他最好的小说一样,“这是一本体现乡村价值的小说”等,莫里森自己对这部小说也评价甚高,认为《爱》是本完美的书,之前,她只如此高评过《爵士乐》。但与之前“爱”的三部曲对非裔美国历史宏大主题的审视与追问相比,这部新作远远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审美期待,引发媒体与学者褒贬不一的反应。罗伊农(Tessa Roynon)认为,这部新作拓展了《柏油娃》的主题,对美国的“发现”与殖民历史进行去媚与重构(Roynon,2007:32-33)。角谷(Michiko Kakutani)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这部小说中虽有一些优美的段落,能够体现作者的标志性风格,可见福克纳、埃里森、沃尔夫与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整部故事像哥特式肥皂剧,女人热衷争斗,男人则到处寻欢作乐,“是《秀拉》与《柏油娃》的奇怪混合与翻新”(Baker,2011:2)。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也在《卫报》上发表书评,认为小说《爱》很“哥特”,作者莫里森的选择很局限,“尽管她可能会争辩说(当然她这么说也不错),非裔美国人可以为整个人类代言,但在《爱》中并非如此;她们深受自己文化的束缚,虽然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技艺娴熟,但是其完美之处也正是其局限所在”(Baker,2011:2)。因此,著名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贝克(Houston Baker)指出,肖沃特的评论与辛普森1963年对普利策获奖诗人布鲁克斯的评价一样自以为是,“我不能肯定黑人如果不让我们意识到他/她是黑人,能否写得很好,另外,如果成为黑人是唯一的主题,那么写作也就不重要了” (Baker,2011:2)。米勒(Laura Miller)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也认为,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中产阶级相互支持,赢得稳定的秩序——这在充满敌意的白人主宰的世界非常不易,但也因此失去了活力、野性甚至真实,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是如此,《秀拉》尤甚;而《爱》是其姊妹篇(Miller, 2003)。另外《星期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等也有一些负面评价。早在1970年代末莫里森就对类似问题作出过明确回应,当《纽约时报书评》撰文指出,莫里森“天赋异禀”,不应只“写”黑人时,她说,“成为黑人女作家并不意味着我的世界变得更小了,而是变得更大了。当我说自己写人时,我指的只是黑人”(Wanneburg,2003:136)。
虽然有这些“负面”评价,认为它不是关于爱,而是关于爱的缺失,哀叹全黑人社区的消失,基于对“爱”这个词的游戏,而非基于其与情感的联系(Alexandru,2008:199),但笔者认为,这些负面评价都源于对《爱》的片面认识,无法理解“爱”并非仅仅是抽象的、个体之间的情感因素,而是与美国黑人民族过去的历史经历,以及当下黑人社区内部男女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这部仅有208页的小说,题目虽然只有一个简单的“爱”字,但内涵却十分丰富,描述了人们相互热爱又相互憎恨的情感及其变化。这部类似爱的挽歌的小说,共分八章,描述发生于东部海滨一个黑人社区的故事,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告诉读者这家旅馆的具体位置,但我们大致知道它位于东海岸,是四五十年代为富裕的黑人开放的最好的,也最广为人知的度假场所。但小说开始时,这家度假圣地早已关闭,过去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海滨旅馆现已衰败,柯西大厦里住着两个长期争斗不休的女人,她们过着福克纳笔下穷白人的窘迫生活,一个是比尔·柯西的年轻遗孀留心,另一位是他的孙女克里斯廷——两人为了赢得家里的经济大权争斗不已。
虽然小说大部分围绕本世纪90年代进行,但是浮现于人们脑海的仍是已故柯西的身影,人们追忆着发生在过去的人与事。让读者好奇的是,作为黑人的柯西居然能在这个海边小镇建立度假地,在自己的王国里享受着极大的经济与社会权力,这在当时美国种族歧视依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是很难想象的。他具有超凡魅力,不仅由于仁爱厚道受人尊重,而且他那种吸引女性、占有女性的能力也令人羡慕。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对他十分迷恋,比如说曾经在度假地工作过的维达·吉本斯就只关注他好的一面,只记得老主人仁爱伟大,认为柯西家的女人都是“严格苛刻的毒蛇”;柯西去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由两个昔日的闺蜜,现在的“祖孙”两代女性来争夺、填补,她们围绕多年前柯西在一张菜单上匆忙写就的遗嘱斗得你死我活。
为了表现黑人社区复杂、难以简约的爱,莫里森继续选择复杂叙述形式,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人们熟知的浪漫或言情小说中“爱”的书写模式,挑战“主流”媒体对非裔美国小说创作的传统认知。为了展示人物的丰富与社会背景与环境的复杂,莫里森特别善于营造氛围,以倒叙方式,延长阅读的陌生化效果,并以诗意的语言叙述着人世间的繁琐与卑污。作为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核心人物,柯西的发迹、去世以及他的遗嘱十分令人怀疑——他的钱财来自哪里?是否有人杀了他,是否有人代写了他的遗嘱等。但作者更关心的是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受到来自家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比如柯西儿子的遗孀梅,由于害怕民权运动会破坏她辛苦获得的一切,竟然养成了盗窃僻,以至于后来精神崩溃;梅的女儿克里斯廷虽然是柯西唯一的嫡系后代,却在童年时就远离度假地,过着漂泊的生活,后来被剥夺继承权;柯西的年轻新娘留心出生贫寒,和孙女克里斯廷本是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伙伴,因经济原因嫁给可以做自己祖父的柯西;小说中的L可能社会地位最低——她是这家海滨度假地的厨师,却是整部小说的叙述者,通过她的视角,观察着这个家庭的变化,不仅她的第一人称叙述贯穿全书,起到概述与评说的作用,而且作为灵魂人物的柯西或许就死于她之手,那张重要的遗嘱,那张引起后来所有故事、改变相关女性命运的遗嘱,也很可能出自她的手笔,改变了表面风光无限的柯西等男性的主宰地位,让女性获得财富,贝克称之为再生的现代主义(Baker,2011:15)。读者不禁要问,为何莫里森要这么处理,效果如何?
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必须了解它与莫里森之前作品的联系与区别,并把它置于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序列中来认识。与作者之前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主要展示了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展现黑人男性人物由重视外在权力与力量的展示,转向关心男性人物内心对“爱”的感受并与之和谐的主题;其次,更加注重性别与经济而非种族因素对黑人女性人物的影响,以及她们之间对“爱”的执念与体悟;最后,几个世纪以来影响美国黑人生活的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社会大环境渐趋淡化,新一代的温柔与愉悦之“爱”更为凸显。
作者首先借助社会环境展现三个不同时代男性人物关于权力、欲望与爱情的故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黑人男性由绝对的支配地位(如柯西几乎神一般的存在,其典型特征为“不怒自威”),慢慢“弱化”为需要通过强力/强奸来体现自己的男性权力(如民权运动时期克里斯汀那些激进的黑人男性朋友),最后发展为罗门这一代年轻人对女性的迷恋与尊重,体现出不同时代黑人男性在权力、欲望与爱情主题方面的变迁。
作为黑人度假酒店的老板,柯西是这个黑人社区的中心,通过为其他富裕黑人提供娱乐服务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对那些希望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普通黑人而言,柯西可谓“成功人士”的典范,他也因此能够“居高临下”地与普通黑人如桑德勒等“平等”相处,与白人治安官成为朋友,更让桑德勒的妻子维达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小说以维达为例,描绘了柯西神圣的光环效应:“他几乎总是成功。和许多人一样,维达以崇拜的眼光看他,说起他时带着宽容的微笑。她们为他的能力、他的财富而骄傲,他让她们相信,只要有耐心、有智慧,她们一样可以成功”(莫里森,2013:40)。柯西是家庭的中心,无需过问酒店具体的日常运作,却占有、决定财富分配;但柯西的权力与影响力依然只能体现在当地黑人社区或黑人族群内部,虽然他很有社会信用,也依然无法从白人的银行贷款,但对黑人社群,柯西的权力与影响力无人能比:“柯西不会公开和本地人交往,就是说,他会雇佣他们,和他们开玩笑,甚至从困难中解救他们,但是除了教堂组织的野餐以外,他不欢迎他们来酒店吃饭跳舞。四十年代的时候,大多数本地人都负担不起酒店的费用,但即使一家人攒足了钱想去那里办场婚礼,也是会被拒绝的”(42)。
因此,柯西的主宰地位不是通过外在强力或暴力实现,而主要以温文尔雅的方式进行,并以周围其他黑人的顺从、甚至自责等形式完成。他选择自己孙女克里斯汀的儿童玩伴留心做自己妻子的过程,最能体现这种隐含的权力关系。在酒店遇到留心时,“他摸着她的下巴,然后——不经意地,依然微笑着——摸着她的乳头,或者说她泳衣下面会长出乳头的地方,倘若胸前的圆点会发生变化的话”(206)。可是留心却非常紧张,而且自责,因为虽然留心感到胸前灼热和刺痛,但却认为自己有问题,老头子一下就发现了,所以他要做的只是去摸她,“而且是她引起的,不是他。是她先扭屁股的,然后才是他”(207),他们身边的人也认为肯定是留心这个“小贱人”先起的意。由于留心与他结婚时太小,柯西没有强行进入她的身体,“没有血。没有疼痛和不适的喊叫。只有这个男人在抚摸她,怀抱她,给她洗澡”(81)。他婚后高兴地为小新娘买各种东西,一直把她当作孩子,当留心生气,耍脾气时,“爸爸”就会站起来抓住她的胳膊,“带着一种旧式的优雅,把她拉到膝盖前扇了她。不重、不狠。讲究方法,不太情愿,就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136)。
如果说柯西这代成功的黑人男性依然可以通过遵守美国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为自己谋取财富,在黑人社区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对黑人女性的权势与威严,享受着别人的“心悦诚服”,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在躁动,克里斯汀的那些黑人男性朋友则试图改变“固有”的游戏规则,为黑人族群的权益进行斗争,暴力化特征明显增强。而被家庭亲人“抛弃”的克里斯汀,也在这样的氛围里找到了自己新的奋斗目标与生活意义,特别是黑人激进青年“果子”的出现,“让世界在她面前清晰起来。”她“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是有价值的”(175-176)。但当这个激进的黑人青年团体中某位同志强奸了一个17岁黑人学生志愿者,而且“果子”们答应要关心这位姑娘,痛斥那个同志的所作所为、处罚并开除他时,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而且竟然如此解释:“不是他的错是那姑娘不戴胸罩衣冠不整地对他投怀送抱他甚至还拍了拍她的屁股警告她为了他着想结果她没有打烂他下巴而是偷笑着问他想不想来杯啤酒”(178-179)。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的强奸行为变成对女性的指责,认为是女性的风骚所致,其他姑娘也对这位女性受害者说三道四;更加恶劣的是,这个男性群体,这个标榜为黑人族群的权益斗争的激进组织,却害怕因处罚这位同志而伤害他们男性之间的友谊;另外,因为施害者不是白人,所以这个姑娘所受的伤害仿佛无足轻重。
强奸是体现男性对女性的征服与主宰地位,显示所谓男性气概的一项外在标志,也是美国奴隶制的一项“重要遗产”,奴隶叙事以来的多部非裔美国文学作品描写或涉及黑人女性遭受的性侵犯与性剥削,这也是莫里森关注的重要主题,更是《爱》关注的重要话题;但是与民权运动时期黑人男性群体的“抱团”与相互袒护相比,90年代的新一代黑人男性少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小说中的少年罗门可为代表。小说第二章“朋友”花了很大篇幅描写少年罗门外在、虚假的残酷欲望与内心真正自我的较量,因为莫里森想改变传统经典作品对强奸的浪漫主义处理,及其自得与自豪的语言表达,破坏这些表述。
当一帮男孩朋友轮奸一位少女时,罗门也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残酷、危险、放荡”的罗门(49),而且为自己的残酷找到了很好的借口,因为被蹂躏的女孩被捆住的手“好像某个荡妇在晾衣绳上歪歪斜斜挂着的手套,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说。……罗门简直以为她就是那个荡妇,那个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的人”(48)。但轮到他时,罗门看到女孩那只松开的手,他突然改变主意,帮她解开被捆住的另一只手,帮她裹上衣服,扶她起来并把她送出来。此后罗门成了笑话,与其他男孩的友谊宣告破灭,被这些男孩孤立,而且三天后,被这几个朋友暴揍一顿。
这场在别的男孩子眼里失败的成人礼,让罗门反思,自己是否真是那个“残酷、危险、放荡”的罗门?关键时刻为什么会心软?究竟是什么让他那么做?或者说,是谁让他那么做?莫里森不仅代读者发问,也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其实他知道是谁。是他内心那个真正的罗门,破坏了这个新来的残酷而危险的罗门。这个假罗门,这个在陌生人的床上得意扬扬的罗门,被那个真正的罗门打败了”(52)。莫里森通过这些场景,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黑人男性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答案。展现黑人男性权力与气概可能像过去的柯西一样让权力的主宰地位“自然”地发挥作用,或者像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肌肉男”赤裸裸的展现暴力,但是也可以像罗门这样展示内心的柔软,因为爱具有更持久的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他后来与朱尼尔之间性爱关系的和谐与爱情的疯狂生长,也体现在罗门因为爱情而快速成长、成熟、逐渐自信方面。比如说,他已经不记得因为几头“纸老虎”而在枕头下哭泣的窝囊废是谁,再也不用靠着墙鬼鬼祟祟地行走,在人群中寻找安全感,而是变成在贝休恩高中的走廊里踱步,迎接别人来瞻仰自己风采的王子。小说结尾处,罗门把留心与克里斯汀这对“宿敌”从柯西的大厦中救出来,对她们充满关爱与同情。
如果说莫里森之前多部作品中的男性大都沉浸于过去的不幸经历当中,那么《爱》中的三代黑人男性都活在当下,而且作者更加注重他们与当下政治与社会大环境或利用或对抗或漠视的关系;另外,这部小说展示了黑人女性之间关系的新维度。与过去小说中强调黑人男性或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女性的负面影响,或黑人女性因为内化欧美主流价值观而产生的很多悲剧不同的是,《爱》虽然也有关于黑人女性(比如梅)“奴隶”一般的辛勤劳作,但也着重体现女性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比如小说的叙述者L不仅是一位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厨子,而且是故事的叙述者,甚至是终结柯西生命、修改柯西遗嘱、影响柯西家族成员命运的人;更重要的是,《爱》特别关注富裕起来的黑人家庭内部两位昔日玩伴之间对亲情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财富的争夺,而且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体现经济因素对黑人社区及黑人家庭内部成员的影响。
因此,熟悉莫里森小说创作的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这部新作中的两位主要女性人物留心与克里斯汀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互动,而非与社会环境的对话。如果说留心因为家境窘迫,不得已或懵懵懂懂地嫁给柯西,有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或自然主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为了改善自己与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套路,却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因为追求经济方面的改变,而产生对自己及家庭的负面伤害。作为柯西的孙女,克里斯汀童年时期养尊处优,但随着爷爷娶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玩伴,她开始了没有生活目标的漂泊之路,经过民权运动时期短时间的亢奋与激动,最终失望地回家,并因无法继承家族财产,与昔日好友留心开启相互仇恨的漫长岁月。但小说没有以她们之间的怨恨与猜忌结尾,而是采取近似小说《秀拉》的收场,两个已经“恨”不动的“老”女人终于认识到女性之间友谊的重要,“我们本来可以手拉手生活下去的,不用到处找伟大的‘爸爸’”(205),但这位伟大的“爸爸”却剥夺了她们最美好的时光:一个说“他把我所有的童年都从我身边夺走了”,另外一个说“他把所有的你都从我身边夺走了”;她们放弃前嫌,开始怀念童年时代的美好时光,宽容并相互原谅。熟悉莫里森创作主旨的读者对此不会惊诧,因为她始终关注女性之间的友谊,曾经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仅次于男女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多年后,她再次通过《爱》重申不被男性主宰的女性友谊的重要性(Morrison, 1993:107)。
作者把小说背景放在1990年,新一代黑人男女如罗门与朱尼尔之间幸福、温馨的“情”与“爱”成为读者对比、反思过去两代人的重要参照,也是莫里森这部新作对“爱”的升华,体现了作者在《宠儿》中所表达的身体解放是爱的基础、心灵自由是爱的保障的思想。非裔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胡克斯认为,爱即为了有助于自己或他人的精神成长对自我的扩展,而虐待与漠视会抹杀爱的力量(Wardi, 2005:216);而以四五十年代的柯西和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成员为代表的前两代人,都不同程度地在思想上受制于过去关于种族、关于性别的桎梏与历史局限,更多地体现着“爱”的欲望甚至权力主宰关系,而以罗门与朱尼尔为代表的当代(新一代)黑人青年,更关注“爱”本身的情感因素及其催人奋进的力量,不再会因为爱得太浓出现《宠儿》中杀死自己女儿的母亲,不会因嫉妒得太深出现《爵士乐》中杀死自己年轻情人的丈夫,更不会因焦虑或恐惧过甚而出现《乐园》中黑人社区集体赶杀女性这样的群体事件。莫里森认为,由于黑人民族在历史上一直遭受别人的“恨”,因此,“爱”就具有颠覆性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我们说爱至高无上,那不只是说着玩玩,……当马丁·路德·金说爱时,他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植根于我们反对制度化仇恨的悠久斗争传统当中”(Morrison & West,2004:22)。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柯林斯也指出,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并非仅仅在于没有了任性的奴隶主以及无休止的体力劳作,而是重新获得了爱你所爱的权力:“这世上没有什么人我可以想爱而不能爱”(Collins,2000:149-150),当然也隐含着潜在的危险:即以爱的名义,自私任性地“爱”或毁灭别人,体现出爱的暴力与非理性。
3.0 结语
在非裔美国文化中,人们很久以来就使用爱-恨两分的修辞比喻,并在20世纪初争取美国现代性话语中达到第一个高潮,亚历山德鲁(Maria-Sabina DragaAlexandru)认为,非裔美国人的解放需要通过爱自己、爱自己的传统才能实现,比如说加维(Marcus Garvey)把非洲视为自己热爱的祖国,所提出的“回到非洲”运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渴望以兄弟之爱消弭黑白种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都旨在解决非裔美国民族爱的目标。韦斯特(Cornel West)在《种族确实重要》中明确指出,只有肯定自己价值的“爱的伦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人传统文化中的虚无思想,克服忧虑与疑惧,因为种族冲突的根源在于非裔美国人被系统地灌输仇恨自己的教条(West,2001:29)。而对应于非裔美国民族长期以来经受的自我仇恨教育,爱是一种颠覆状态而非仅仅是一种情感姿态,成为莫里森塑造的另外一种非裔美国核心比喻,并在《宠儿》、《爵士乐》、《乐园》与《爱》中不断演变发展(Alexandru,2008:191)。
莫里森在小说《乐园》中曾明确提出,“爱是最神圣的,也总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觉得爱很容易,你就是个傻瓜;如果你觉得爱理所当然,你就是个瞎子;爱需要学习运用,没有理由,没有动机,除非你是上帝”(Morrison,1998:141)。因此,亚历山德鲁指出,莫里森小说中的爱可能显得不正常、过度、异乎寻常,以缺失或反常、破坏性的方式呈现;但是如果把它简单地视为奴隶制历史对黑人社区所造成的多重创伤的现实评价则过于简单化了。因此,这部小说中的爱并不仅仅是个主题,而是一种修辞方式,既是庆祝非裔美国人之前被否认的爱的权利,也是对黑人文化中到处弥漫的非理性刻板印象的挑战。“无论表象如何,这种理性的、目标明确的爱,意味着为非裔美国社区赢得一种声音。……莫里森的爱因其缺席反而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修辞策略”(Alexandru,2008:204)。在接受采访时,莫里森进一步阐释了她对爱与性的认识,“我感兴趣的是性爱与其他形式的爱能够暴露自己的本性。人们本来极力想保护的东西为什么结果却毁了它们?”(McKinney-Whetstone,2003:206)因此,虽然《爱》篇幅较短,但再次证明了作者的创造力,在现实与过去的交织中展现人性的美与丑,不仅探察与揭露人类美好的感情及其阴暗面,而且为自立、责任与生存这些严肃的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考。
另外,一直关注社会环境对黑人个体与黑人族群影响的莫里森,在这部新作中揉进一些新的元素,对民权运动之前的岁月充满怀旧般的留恋,通过梅、L和克里斯汀等人对民权运动的“负面”反应,尝试传递历史的复杂性信息。莫里斯(Susana M. Morris)认为,《爱》拒绝对民权运动之前及期间的时代予以狭隘的概念化接受,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现在(Morris,2013:326)。新一代黑人少年罗门对外祖母“艰难时世”之类的老故事“哈欠连天”的漠然态度,仿佛也与美国“后-种族”,后-民权运动时代更大范围的文化现象紧密相关,对于盖茨教授之问,“美国是否已经超越种族,或者说种族是否依然定义我们,引导我们的国家叙述,塑造我们的生活?”(Gates and Burke,2015:xii),莫里森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能漠视过去, 因为“你杀死祖先时,也就杀死了自己”(Morrison,2008:64)。
[1] Alexandru, M. D. Love as reclamation in Toni Morrison’s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J].EuropeanJournalofAmericanCulture, 2008,27(3):191-205.
[2] Baker, H. A. The Point of entanglement: Modernism, Diaspora, and Toni Morrison’s Love[J].AfricanandBlackDiaspora:AnInternationalJournal, 2011,4(1):1-18.
[3] Collins, P. H.BlackFeminist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thePoliticsofEmpowerment[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4] Gates, H. L. & K. M. Burke (eds.).AndStillIRise:BlackAmericaSinceMLK[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5.
[5] McKinney-Whetstone, D. The Nature of Love[J].Essence. Oct. 2003:206.
[6] Miller, L. The Last Resort[N].TheNewYorkTimes, November 2, 2003.
[7] Morris, S. M. A Past Not Pure But Stifled: Vexed Legacies of Leadership in Toni Morrison’s Love[J].TheSouthAtlanticQuarterly, 2013,112(2):319-338.
[8] Morrison, T. “The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 with Elissa Schappell and Claudia Brodsky Lacour[J].ParisReview1993,128(35):83-125.
[9] Morrison, T.Paradis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8.
[10] Morrison,T. Rootedness: 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A]. In Carolyn C. Denard (ed.).ToniMorrison:WhatMovesattheMargin,SelectedNonfiction[C].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2008. 56-64.
[11] Morrison, T. & C. West. Blues, Love and Politics[J].TheNation, 2004:18-28.
[12] Roynon, T. A New “Romen” Empire: Toni Morrison’s Love and the Classics[J].JournalofAmericanStudies, 2007,(41):31-47.
[13] Taylor-Guthrie, D. (ed.).ConversationswithToniMorrison[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14] Wanneburg, G. Response: A response to “arrogant Western” criticism[J].Literator, 2003,24 (2):193-196.
[15] Wardi, A. J. A Laying on of Hands: Toni Morrison and the Materiality ofLove[J].MELUS, 2005,30(3):201-218.
[16] West, C.RaceMatter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17] 莫里森. 爱[M]. 顾悦 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LoveandRace:ToniMorrison’sLoveandHerReflectionofHumanity
WANGYu-kuo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210023,China)
ToniMorrisonfocusescontinuallyon“Love”,andrepresentsloveinmanynovels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Asanewnovelinthe21stcentury,Morrison’sLovenotonlyenrichesourunderstandingof“love”,butalsoemphasizesitsfunctionofliberationandsalvationinAfricanAmericanliteratureandAfricanAmericancommunity,whichcanhelpusunderstandmor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loveandAfricanAmericancommunity,andbetweenloveandAfricanAmericanliteratureandculture,anddismantlesthetraditionalbinaryoflove-hatemodalityinAfricanAmericancommunity.
Love;race;liberation
10.16482/j.sdwy37-1026.2017-06-000
2017-07-15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1BWW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玉括( 1965-),男,汉族,安徽霍邱人,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
A
1002-2643(2017)06-0060-07
王金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