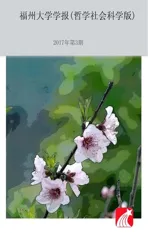艰难的转型:闻一多在武汉大学
2017-04-04陈卫
陈 卫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艰难的转型:闻一多在武汉大学
陈 卫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闻一多读书期间就有文学梦,为此他一直努力。留学美国以及回国后,他学美术、教美术;写诗、探索新诗新式;出诗集、评论集、办刊物;参演戏剧、推动国剧发展……各种活动的指向都是为了传扬中国文化,做一名文学教授。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前,这些工作使闻一多的人生轨迹越来越清晰,在武汉大学的授课与案头准备,终于成就了他后来的文学教授之梦,成为一位标新立意的新派国学教授。
闻一多; 武汉大学; 清华大学; 美术; 文学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在上海登岸,结束了他在美国三年的留学生活,他是带着一堆理想回国的。一上岸,他便把褂子当掉,与朋友们在餐馆痛吃了一顿。这个时候的上海,刚刚发生五卅惨案,这群带着热情和理想回国的海归们,亲眼看到地上还淌着鲜血。这也预示着,闻一多与归国的朋友们,将度过一段不是特别安定的日子。此年,离武汉大学成立尚有三年时间。
一、梦想与碎片:武汉大学任职前的闻一多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与清华学校的同学从上海乘坐海轮赴美。尽管那时的他不是很想留学,但觉得有公派机会去美国,走一趟也好。8月1日,他和同学抵达美国西岸西雅图;7日,再达目的地——中部的芝加哥。此时的芝加哥有中国留学生二百余人,闻一多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
闻一多来到芝加哥,正遇上“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的巅峰时期。虽然闻一多留学选择的专业是美术,但他心中已有明确目标:留学归国后,要做文学教授。在美国,他依然热衷写新诗,亲自翻译美国现代诗,钻研中国古典诗文。饭后,跟朋友上华盛顿公园“读杜甫、李白、苏轼”[1]。跟亲友谈的是他正在做的陆游、韩愈等诗人的读书笔记。家信中,他表达过专业学习与未来志向之间的困惑:“我在此习者,美术也,将或以美术知名于侪辈。归国后孰肯延我教授文学哉?求文学教员者又孰肯延留学西洋者教中文哉?我既不肯再没弃美术而习文学,又决意归国必教文学,于是遂成莫决之问题焉”[2]。到美两个月后,他给父母的信中明确写到:“三年之后我决即回国”,其理由是:“恐怕我对于文学的兴味比美术还深。我在文学中已得的成就比美术亦大。此一层别人恐不深悉,但我确有把握。”[3]
留美期间,闻一多对文学的兴趣一直未减。其宏愿在他与同仁们的通信中也可看到:1922年9月25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学的时候,闻一多给清华同仁的信,谈的依旧是文学问题,“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4]为此,他省吃俭用,张罗着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3,上海泰东书局)[5]。闻一多的重要诗篇不少出自留学时期,如《红豆篇》《孤雁》《太阳吟》《忆菊》《秋色》《也许》《大鼓师》《你看》《洗衣歌》等。文论方面,闻一多参与了中国早期的诗歌评论写作,1923年6月,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地方色彩》;1923年12月,《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泰果尔批评》等重要论文。
在美读书,闻一多三年更换了三处:芝加哥、科罗拉多和纽约城,从美国中部大城市游学到东部的大城市。这一段经历,使闻一多比其他同学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美国的文坛与艺术界,更多方面获取了异域的文学艺术信息及经验。从闻一多的信中得知,刚到芝加哥不久,经一位“支那热太太”——浦西夫人[6]介绍,他在芝加哥认识了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7]和门罗[8],这两位诗人正是提倡美国诗歌革命的新诗人。1922年11月,他结识了芝加哥大学法文副教授温特[9],他们讨论中英文的诗歌翻译,闻一多给他讲中国诗,他给闻一多介绍英国诗的格律。12月遇见美国女诗人Eunice Tietjens[10]。1923年2月,闻一多又认识美国意象派领袖爱米·罗艾尔[11]。转学到科罗拉多,闻一多与同校的好友梁实秋一同选修“丁尼生与伯朗宁”“现代英美诗”等课程。与美国诗人、学者的近距离交流,无疑给闻一多未来的诗歌写作和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经验,帮助他走上中西诗学合璧之探索道路。
闻一多在美国学习美术,并非一无所成[12],他的油画曾获过奖。赴美第二年,他顺利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虽没有拿到学士学位[13],但他的专业成绩非常优秀。闻一多的朋友们也知道他在美术上的特长。在清华学校时,学校的报刊由他画题头,朋友们演戏,舞台设计、服装设计、化妆都由他一人完成。据朋友顾毓秀、冰心等人回忆,闻一多曾为波士顿留学生的《琵琶记》演出帮过忙,他曾以油画方式为顾毓秀绘过一件龙袍和舞台上的大屏风,并替演员化妆。[14]
闻一多既然抱着到美国走一趟看看的想法,他没有完全遵照学校的安排,三年都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度过。他之所以三年换三个地方,有朋友的关系,更有兴趣的原因。因为好友梁实秋1923年赴科罗拉多留学,同年9月,闻一多也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然而一年后,梁实秋去哈佛大学继续求学,1924年9月,闻一多遂转学入纽约艺术学院,跟戏剧界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倡导国剧。不过,据梁实秋的描述,闻一多那时对政治兴趣浓厚,他热衷大江的国家主义,并且是中坚分子,热诚也维持得最长久。[15]在纽约,一年下来,闻一多并没有好好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索兴不去上学了,蓄起长发,做艺术家状,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闻一多认识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的留学生熊佛西之后,与他一起编写独幕剧,切磋戏剧艺术,排演戏剧,把剧本译成英文。化妆布景照旧是闻一多分内之事。
1925年,闻一多参与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这时,他的梦想开始飞腾,他渴望在复兴中华戏剧方面做一番贡献。他没有放弃诗歌写作,而是更加勤奋。当时与他居住一处的好友熊佛西在后来的追忆文章中写到:此时的闻一多“你终于觉得干戏不是你的本行,不久你仍回到研究诗的岗位上。自此,你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你往往从半夜写到天明。为了努力于诗的创作,你时常废寝忘餐”[16]。这些诗,多在国内发表,后来结集在《死水》集中。也就是说,闻一多虽留学美国,他的诗名却响于国内。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教育,有了最初的积淀。
1925年6月,闻一多携带不少现代英文诗集,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友人在上海登岸。后又一同赴北京,租屋而居,据说“景况相当凄凉”[17],然而他们是有梦想的人,想从文化上改变中国。
回到中国,闻一多的国家主义意识愈强,他写了爱国题材的《醒啊》《七子之歌》等诗,被当时的读者认为是“爱国诗”,认为与那些吻香的恋情诗、形而上的哲理诗、手枪炸弹的革命诗,都不同。
1925年7月15日,闻一多与他的朋友们继续在政治上努力。他们成立大江会,创办《大江季刊》,其《发刊词》由闻一多撰写,他们强调国家主义的立场为中华人民,他们的主张是“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为此,他们竭尽全力。同月,他们拟《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组织概略、剧场建筑、营业方法、练习生功课都有详细设计[18],准备设置一个将学习与演出兼顾、学校与剧院相结合的新形式。8月9日,这群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又一同加入新月社,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尽力。
回头仔细审视那一段历史,闻一多回国适逢国家最破败,也是最有发展的新时机。中国旧文化、旧体制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强力拆毁,处在一个创建时期。学堂教育向西式的大学教育体制学习,如1911年设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便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国立清华大学。处在起步阶段的大学,急缺教师,胡适、鲁迅、徐志摩等这些海归留学生,不一定拿到学位,但都通过特殊的举荐机制,同兼几所大学的教授。大学基本都为初设,师资严重缺乏,科目设立也没有具体的参照。闻一多到北京不久,机会就来了。
经新月社同仁徐志摩推荐,闻一多与一同回国的余上沅、赵太侔等被聘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后改为艺术学院、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委员,学校成立后,闻一多任教务主任,考试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学校开学,闻一多教美术史。虽然还不是从事他设想好的文学研究,但闻一多毕竟留学所学的科目是美术,他回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应该说专业对口,适得其所。然而,这所新办的学校遇到了经费上的难处,他们筹办的“北京艺术剧院”进展同样艰难。为了理想,闻一多在学校教务方面进行改革,招收旁听生,按小时收费。他的政治理想也没放弃。同年12月,闻一多与罗隆基代表大江会参与筹办北京国家主义团体,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国外受了极大刺激,渴望建立一个“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内部妥协,外不亲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的国家。
在北京这段时间,闻一多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了北京。下班时,他会和朋友在书房聚会谈诗、朗诵诗。徐志摩、沈从文等同仁曾在文章中都不约而同谈起过闻一多设计的黑色书房。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还提到过在闻一多那里听到朗诵诗的感受:“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和辞藻都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而言,似显得稍稍有点走回头路”。可见,闻一多工作之余在进行诗歌格律探讨。
好景不长,艺专戏剧系经费出现问题,学生只有二十来个,不太理想,尤其缺女生。不久,校长刘百昭表示要辞职。为新校长由林风眠还是蔡元培上任,大家又闹得不可开交,也有人以为闻一多要做校长。而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学校职员为新校长的事情又分成两派了。而自己对于报载要当校长之事,以为笑话,且无奈:“富贵于我如浮云”[19]。当艺专由林风眠接任后,闻一多请辞。在艺专期间,闻一多的诗歌产量明显减产,回国后只做了两首诗。闻一多那时醉心政治,热衷大江会的活动,据他给友人的信说,他为大江会写的《大江宣言》为人喜欢,有人手抄,有人剽袭[20]。除了参与大江社的工作,闻一多全身心投身文艺工作。1926年4月,他与《晨报》的副刊主编徐志摩一道创刊《晨报·诗镌》。他的代表作《死水》英译诗、“英译李白诗”和重要论文《诗的格律》都发表在此副刊上,这些工作,奠定了他在新诗界的地位。同时,他也刊发了同仁如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等文。闻一多在美国的文学理想,此时正在实现。
工作不顺,时局不稳,闻一多于1926年7月携家人回归故里。8月,他再次来到上海。受聘为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从他找工作看,靠的多是朋友关系,该大学校长张君劢是他同学的哥哥,学校同事多为清华校友,但终究因时局大乱,让闻一多不免恐慌,1926年冬,闻一多给饶孟侃的信中说谈及生活现状:“时局不靖,政大内部亦起恐慌……万一大局不变,君劢仍在彼方,弟自亦无问题。否则恐须另谋生路。这年头儿我辈真当效参军痛哭。”他的信一般涉及到写诗和未来前途,此时,诗思淤塞,倍于昔时。数月仅得诗一首,且不佳。中国文学研究,是他诗思枯竭后的一个补充,他对朋友说,“将来遂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乎?”[21]
饶孟侃[22]是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时结交的好友,由此信息可见,闻一多因时局、国家情怀、个人情况,他已有转向的打算。次年2月,春节过后,闻一多从故乡浠水到达武昌,真的参军,在邓演达的帮助下,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兼任政治部英文秘书,据说这是闻一多自己不愿提及的历史。这段从军经历只持续了一个月,闻一多再回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不巧的是,4月份政府取缔了这所大学,说这里是国家主义的据点。
闻一多只得赋闲在家,振兴戏剧、中国文化的大梦都暂时放下。这时,他继续了个人的文学梦想,通过翻译、写诗,表达对时局不满;此外,操刀刻印。在朋友们的印象里,他这时期总是栖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1927年7月1日,新月书店在上海开张,闻一多也入了股。
1927年7月14日,闻一多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诗经的性欲观》刊登在《时事新报·学灯》上。《时事新报·学灯》是张东荪等主持的一份报纸,提倡新学说。闻一多不仅观点出新,他的论文语言并非学究式语言,有诗意的描述,也有热情洋溢的议论;西方的科学术语在文学论文中引用,生理学的、历史学的、文化学、文字学的知识都拿来为他所用。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撰写的论文,与以往的《诗经》研究都不同,他提出《诗经》是一部淫诗。这种大胆的做法,意味着闻一多要在学术上做出巨大的努力。
期间,据梁实秋的《谈闻一多》所写,1927年暑期,闻一多由朋友介绍,到南京土地局任过职,时间很短,因为朋友离职,他也失去了工作,甚至都没有跟梁实秋具体谈过[23]。8月,闻一多与东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宗白华接洽过,准备到外文系任教授兼主任,后来东南大学并入新成立的南京第四中山大学,闻一多被聘。1927年11月,闻一多把家人接到南京,自己荣选为教授代表,有资格参加校务会议。在这里,陈梦家、方玮德等成为他的学生,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由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在南京,闻一多担任文哲学院的本科生指导员,上海创刊的《新月月刊》,也挂名编辑,他的文学理想再次起飞。他用格律的方式,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与叶公超合译《近代英美诗选》,当时此书刊登在《新月月刊》上的广告写到:这选本不但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一个人唯一的向导,而且是大学近代文学课程里一部必不可少的教科书;对闻一多的介绍是“闻一多先生在新诗坛里的地位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这时的闻一多除了译诗,自己也试写商籁体。
这是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之前的学习和工作。回国三年间,他一共任职过三所学校,从军过,进过政府机构。学校由于经费、政局不稳,他都没有待很长时间。无论从教还是从政,他都仰仗了校友与朋友的关系。可以说,带着梦想回来的闻一多,梦想碎了一地。
但是这些经历,也是闻一多能够到武汉大学工作的资本。在新建的大学,一切都是新的,闻一多较早地进入到行政管理阶层,因此他有行政经历,他上过美术、诗歌、英文课多门课程,他自己还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办刊、提倡新诗格律的写作、写刊物发刊词等,闻一多有一般年轻学者没有的经验。写诗、译诗,写评论,提倡新格律诗,反《诗经》的无邪传统观,提倡新的学术态度。进武汉大学前,闻一多完成了新派学者的初构。
这时的闻一多,对于中国的梦想,基于三个方面:一是自己比较容易做到,也一直在做的,即现代诗歌写作,这是从新文化运动之后便开始实践的。回国之后,闻一多的诗歌中爱国主义意识愈浓。与徐志摩合办《晨报·诗镌》,出版了11期,参与新月社的刊物出版与活动,这都是让他实现文学梦的机会。《死水》出版、《诗的格律》发表,实践了他在美国时的宏愿:径直开创一个流派,用自己的创作与理论主张,试图在中国格律诗与西方意象诗歌中找到一条新的路径。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歌导言》、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苏雪林《闻一多的诗》以及徐志摩等人的多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闻一多在《诗镌》中的影响力最大,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是不可忽略的新诗人。二是闻一多极其渴望中国文艺的复兴,他在美国最后一年,由戏剧界朋友引发出的对中国戏剧的强烈热爱,于是想借助戏剧,发展国剧。在《诗镌》结束后,他们创刊了《晨报·剧刊》,闻一多也参与组稿,发表过《戏剧的歧途》等文。无论是在北京美术学院工作还是设想北京艺术剧院的建设,闻一多都走在实现梦想的路上。闻一多这时也还作画,他的画作不是抽象或象征作品,而是关联着中国的文化。据朱湘的文章《闻一多与〈死水〉》中说到,他打算在屈原、杜甫、陆游的诗歌内,拣选出三个意象来,制成三幅图画。陆游的一幅是绘成了。[24]三是闻一多还在继续积累中国古代诗人的阅读材料。自陆游、韩愈后,他的兴趣转移到杜甫身上。在武汉大学上任前后,他有《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等论文发表,以后,这些研究将他从美术教学、英诗教学等看上去更专业、更有兴趣的工作中转移过来。相对新兴的学科,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才是正宗。然而,毕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闻一多不甘重复古人的做法,他的研究尽管也立足于《诗经》、楚辞、唐诗等文献,除了运用中国的小学研究方式,他也运用西方的新理论,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研究,在他论及《诗经》和宫体词时阐发出前无古人的新意。在学术上,他的大胆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风尚、新的潮流。
1928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亲自找到闻一多,谈武汉大学筹备事项。
二、煎熬与转型:武汉大学的闻一多教授
闻一多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一样,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艺术抱负,为此上下求索。闻一多没有在魔鬼靡菲斯特的引导下走,他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留学、回国。又成立社团、办刊,从军、当官,由于时局不稳,经费不足,兴趣不合,这些都没让他如愿实现梦想。故乡武汉大学成立,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亲自聘请他当文学院院长,这是命运给他伸出的绿色橄榄枝。
1928年7月,闻一多答应到武汉大学;8月,全家搬回湖北;9月,他出席武汉大学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任文学院院长;10月2日,第一次参加正式校务会议,工作进入正常状态;1930年6月,闻一多请辞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时两年不到。但在这两年间,闻一多完成了他的职业转变。
闻一多渴望做一名文学教授。赴武大之前,出版过两部个人诗集,与友人合译诗集(未出版),这些创作不足以在大学安身立命。闻一多一直没有放弃学术上的努力。除了1927年《诗经的性欲观》引来研究界的震动,1928年,去武大正式就职之前,闻一多的《杜甫》一文正好在《新月》上发表,这又是一次破天荒的写作探索。他运用了戏剧表现的方式,展现杜甫的一生。[25]
武汉大学由武昌中山大学、武昌商科大学、医科大学、私立大学等合并而成。作为新聘院长和教授,闻一多可谓事务缠身。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列出的一系列校务会议内容,大致能看到闻一多的付出,尽管他以前跟朋友抱怨过不想做这类事情。
了解武汉大学历史的人大多知道,闻一多为武汉大学的罗家山取了一个优美的名字——珞珈山[26]。不仅如此,他还为武大设计了校徽,书写了学校大名“国立武汉大学”——这都是些美好的记录。然而,繁杂的事项非常多,《闻一多年谱长编》根据《武汉大学周刊》刊登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记事录》记载,1928年1929年之间,闻一多参与的学校会议以及湖北省教育厅、美术方面的会议归纳如下:
(一)1928年9月-12月
1.9月10日,与同事组成武汉大学学生入学审查委员会,评阅上海考生试卷。
2.9月13日,出席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与刘树杞人等商量增设本科,举行编级试验,聘请教授、编制预算,筹备开学等事宜。
3.9月21日,聘教授28人,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一年级一个班。
4.9月26日,出席第三次临时校务会议,讨论各校毕业生诸问题。
5.10月2日,武汉大学第一次正式校务会议。
6.10月19日,湖北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决定聘请闻一多为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审查及评判委员长。
7.10月31日,出席武汉大学第六次校务会议,决定成立图书委员会,闻一多为委员。
8.11月14日出席武汉大学第八次校务会议,讨论组织群育委员会等方案,闻一多为委员会主席。
9.11月20日出席第九次校务会议,决定补行开学典礼仪式,闻一多被安排做主持筹备。同日,武大新校址勘定,珞珈山由闻一多建议改名。设计校徽、书写校名等。
10.11月2日 出席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审查兼评判会议,讨论审查评判标准及办法等。
11.12月24日,《武汉大学周刊》第四期刊登,闻一多任群育会主席和入学审查委员会主席,还担任图书、出版、训育各委员会委员。
12.12月31日,以文学院院长出任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二)1929年
1.1月5日,参加武汉大学开学典礼。
2.1月13日,出席第15次校务会议。讨论并入武大师范生毕业考试问题,组织考试委员会。
3.2月26日,出席第23次校务会。决定组织课程委员会,为委员长。
4.3月4日,出席武大第一次评议会议。讨论增设学院学系、经费预算、教员聘任规则、待遇规则等。
5.3月13日,出席25次教务会议,讨论增设音乐课程案,闻一多酌办。
6.3月26日,出席27次校务会议,参与筹划“总理奉安委员会总干事孔祥熙函转总理奉安赙赠物品及纪念树木办法请查照案”。
7.4月30日,出席32次校务会。讨论孙中山奉安典礼应办事,闻一多参与办理石碑事。
8.5月28日,出席36次校务会。讨论武汉奉安委员会为奉安典礼各界应各备祭文一份,并推主祭人案,议决结果是祭文请闻院长拟就。
9.6月1日,奉安典礼,祭文为闻一多所撰。
10.9月20日,出席武汉大学4次临时校务会议。聘朱湘为教授。
11.10月4日,出席48次校务会议。讨论国庆纪念仪式、刊行顶起刊物及五大丛书等决议,与陈源承担文学院季刊规划。
12.10月11日,出席49次校务会议,讨论关于军事训练实施办法等案。
13.10月25日,出席 51次校务会议, 讨论图书委员会内设置中文图书审查委员会。担任中文图书审查委员会委员长。
14.11月28日,出席56次校务会议,讨论审查文哲季刊规则等案。闻一多参与筹备。
这部分会议情况仅来自《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所展示的材料。是不是闻一多参加了每一次校务会议?或者还有更多的事情要承担?材料中是否有遗漏?暂不探讨。从已知的材料,可以看到,曾经有远大抱负的闻一多,现在开始承担一所学校中一学院领导所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招生、送学生毕业,备课、上课。为配合学校这台机器的运作,闻一多还要亲自承担图书出版审查、办刊以及审查、学生军训、奉安大典的安排、撰稿等多项事务。这些工作,足以证明闻一多的行政才能在武汉大学是得到公认的。
因留学所学的专业是美术,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开设的课程为西洋美术史。他还参与了湖北美术评价工作,担任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董,都与他原本的专业有关。
尽管理想是做一名古代文学研究者,终究由于专业和繁重的事务所限,使闻一多在武大开设的课,还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第一年他开设的只是选修课,如为文学院开设公共选修课“西洋美术史”,他的本行;给外文系开设的是“现代英美诗”,他的兴趣。第二年九月,闻一多开设的课程是“英诗初步”。
唐达晖先生为此做过考察,在他的文章《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事迹的几点考辨》中谈到:闻一多发表了杜甫的研究论文,上的是外文系的课“英诗初步”,但是他写了关于杜甫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27],这篇学术文章发表于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史哲》一至四期。
其后,闻一多又写了《少陵先生交游考略》,《闻一多全集》中说是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收入,于何年写并不知。《闻一多年谱长编》还提到,闻一多在这期间又发表了一篇论文《庄子》[28]。后来,围绕庄子,闻一多完成的工作有《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庄子义疏》《道教的精神》,收入在《闻一多全集》第九卷。
也就是说,武汉大学期间,闻一多仍处在文学研究的蛰伏期,做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案头准备工作,因有相对明确的方向,工作成效逐渐显现。
不得不提的是,闻一多在武汉大学任院长期间,经他之手,聘用过朱东润、游国恩两位讲师,他们对闻一多后来的文学研究有过很大的帮助。朱东润1896年生,留学英国,1929年,闻一多把他从南通师范学校调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因此成就了他。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也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他由此成为这学科的学术权威。游国恩生于1899年,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在江西的一所中学任教。1929年,闻一多把他聘至武汉大学做讲师,讲授《楚辞》,后来游国恩也成为德高望重的著名文学史专家、楚辞专家。同时,他是最早启发闻一多读《楚辞》的人。闻一多在楚辞方面取得的成就,堪比他的《诗经》、唐诗和《周易》研究。相关的成果有《离骚解诂》《楚辞校补》《读骚杂记》《什么是九歌》《〈九歌〉的结构》等[29]。闻一多后来的学术生涯,有文学史的研究,如《唐诗要略》《文学的历史动向》《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年表》《唐文学年表》等。闻一多在继承清代朴学大师考据的传统上,发挥了他的兴趣特长,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以及结构学、戏剧学的角度,解读研究楚辞,给学术界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当然这都是后话,他的广泛交友,善于使用人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使他自己后来成为出色的国学研究者。
在武汉大学,闻一多帮助过学生。有一个叫费鉴照的学生曾把自己写英国诗人的文章给闻一多看,闻一多给他鼓励,推荐到《新月》发表,后来在新月书店帮助下,费鉴照出版了《现代英国诗人》[30]。
三、离去与发展:离开武汉大学的闻一多
1930年6月,闻一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为何?是闻一多厌倦了会议多,责任重的文学院院长之职?还是学校待遇差,闻一多打算另谋高就?或是,闻一多已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学的研究者?
这些原因仅仅是猜测。季镇淮在《闻一多年谱》中提及:武大起了学潮,攻击先生,先生就贴了一张布告,说对于自己的职位,如“鹓雏之视腐鼠”,并声明辞职离校。后来学校挽留,到底没有留住。武大档案室保留的一份未刊材料《武大最初两事回忆录》中记录的是:闻一多不同意刊登同事刘华瑞教授的有关江汉文化的文章,引起刘的不满,他怂恿学生攻击闻一多。尽管文学院教授陈源、校长王世杰都出面挽留,但闻一多去意已决。第二说是闻一多侄子闻立勋回忆,闻一多离开是武汉大学文学院争夺院长之职引起的派系之争。[31]之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欲聘闻一多任教,遭闻一多婉谢。此时,恰好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振声受南京教育部指派,筹备国立青岛大学。杨教授于当年六月在上海见到闻一多,请他前往青岛大学主持中文系工作,并编辑《新月》。闻一多的好友梁实秋恰好也接到邀请,去主持青岛大学外文系,于是两位好友相约去青岛一看,杨振声设宴招待。就在宴席上,闻一多答应接受青岛大学聘书。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提请聘任闻一多为中文系专任教授,闻一多放弃了母校。
由这些材料大致可以推断: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是被迫选择的。到青岛大学,有时局的原因,也有他看重友谊的原因。
《闻一多年谱长编》[32]描述,《国立青岛大学一览·职教员录》中记载的是,闻一多于“十九年八月到校”,即1930年的8月。9月开学,他被聘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为中文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同时他还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诗课。同年11月,闻一多给饶孟侃的信中说“故纸堆终竟是把那点灵火闷熄了……关于乘舆和服饰,我正想整理一番”[33]。第二年,据好友梁实秋回忆,到青岛后,闻一多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即现存的《全唐诗人小传》,收集唐代诗人406位,字数达60万字。《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有具体的列举,闻一多留下大量的手稿,疏证方面有《唐诗笺证》《唐诗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辩证》《全唐诗校勘记》等;表谱方面有《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考》(附进士登第年龄考)《新旧唐书人名引得》《初唐四杰合谱》等;史料收集方面的有《唐诗大系》《全唐诗补传》《全唐诗续补》《全唐诗汇补》;札记方面有《唐风楼攟录》《璞堂杂记》《唐诗要略》《诗的唐朝》等,他的《诗经》研究也铺开了。[34]可见,青岛大学的工作,正是闻一多所渴望的,他终于转向了古代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故纸堆没有把他的灵火熄灭,而是点燃了。
闻一多在青岛的工作开始是惬意的,因为此地有很多新月社同人。闻一多的家在离浴场不远,梁实秋也在此处。除了招生阅卷,闻一多后来还参加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组织的翻译世界名著的工作。学生中他发现了臧克家这样的优秀学生,并促成他从外文系转向文学院,改变了他的一生。然而,在青岛大学的结果跟武汉大学类似,因学生的学潮引起。学生贴标语攻击闻一多,印出了《驱闻宣言》:“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
1932年7月,心灰意冷的闻一多拒绝继续应聘,只身赴北平。[35]
1932年8月,闻一多应聘清华大学,拒绝做系主任。[36]
在清华大学授课的闻一多教授,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课程”,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先秦汉魏六朝诗”等。他还与文学大家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等同堂入室,讲“大一国文”。从此,闻一多走上了国学研究者之路,他的学术梦想实现了。
美国学者易社强撰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谈到文学院,首席学者即为闻一多,有一段文字特别评价他:清华的闻一多是中文系大师级人物。抗战前,他在文艺界以多才多艺闻名,战后成为时代良知的代言人,名声大振。抵达昆明之际,他由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诗人,转变成30年代的古典学者。在昆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字学研究。在研究《诗经》《楚辞》《易经》《庄子》和《管子》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和哲学著作时,他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后来,对古诗的兴趣引导他转向社会、风俗和神话。闻一多的经历促使他从历史学、文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古代传说,尤其是屈原的传说。在同事白英(Robert Payne)看来,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并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比并论。抗战后期,他被视为联大的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楷模。[37]
国内学者研究闻一多学术的也不少,且不论郭沫若等人的评价,肯定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可以看到很多:如马达的《闻一多对楚辞研究的贡献》、文之的《生殖崇拜的揭示:论闻一多〈诗经〉研究的独特文化视角》、侯美珍的《古典的新意:谈闻一多解〈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梅琼林的《论闻一多诗骚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等,对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创新态度和一些观点,学术界一致肯定。
注释:
[1][4] 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80页。
[2][3]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108-109页。
[5] 此前,1922年1月,闻一多与梁实秋已合集出版了《〈冬夜〉〈草儿〉评论》,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
[6] 浦西夫人,即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信中提到的Mrs.Bush,《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7] 即闻一多《致父母亲》信中提到的山得北先生,Carl Sandburg,《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8] 即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信中提到的Miss Harriet Monroe,《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9] 后来闻一多与同学联名将温特推荐到清华大学任教。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10] 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11] 即闻一多《致家人》信中提到的卢威尔,Amy Lowell(1874-1925),《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153页。
[12]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2页有一个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的学习材料,系芝加哥美术学院注册干事致华盛顿特区中国教育代表团赵团长的信,上面提到闻一多于1922年9月27日至1923年6月1日间的成绩:生物速写、静物素描、雕刻字、艺术史、透视画法、设计、构图、研究等,得五个优,两个良+。信中还说到,如果他攻读完三年的绘画课程,将于1925年6月毕业。
[13] 1924年6月,闻一多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未获学位。他给家人去信的时候,说“学校大考已毕。此校今年中国人得学士学位者六人。我亦得毕业证书,习美术者不以学位论也。前月举行成绩展览会,以我之作品为最佳,颇得此地报纸之赞美”。见闻一多:《致家人》,《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14][15][16][17][18][23][24][26][28][30][31][32][34][35]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4,245,263,267,277-283,349,300,375,382,406,386,388,413,422-427页。
[19]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
[20] 闻一多:《致梁实秋、熊佛西》,《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
[21][33] 闻一多:《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251页。
[22] 饶孟侃:1902年生,1916年进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闻一多,1899年生,1912年进清华学校,1922年前往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
[25] 具体论述此处不展开,可参看笔者的《闻一多诗学论》的附录《中国诗学综论》,谈到闻一多对杜甫的研究以及对《诗经》的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9-256页。
[27]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的特点是采用考据方法,以传主为中心,将国家大事、国际文化交流要事作为专注的生存背景交代,方便了解作品的外部原因。此外还调动历史文化知识解释传主及其作品等。
[29] 参看《闻一多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6] 多年后情况有所变化,1940年6月8日,清华大学召开第三十次校务会议,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闻一多担任文学部主任。7月朱自清休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闻一多代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职务,闻一多表示不愿接受,而推荐王力担任。1941年朱自清休假结束,返学后请辞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正式接任。
[37]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1-122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6-10-26
陈 卫, 女, 江西萍乡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I206.6
A
1002-3321(2017)03-00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