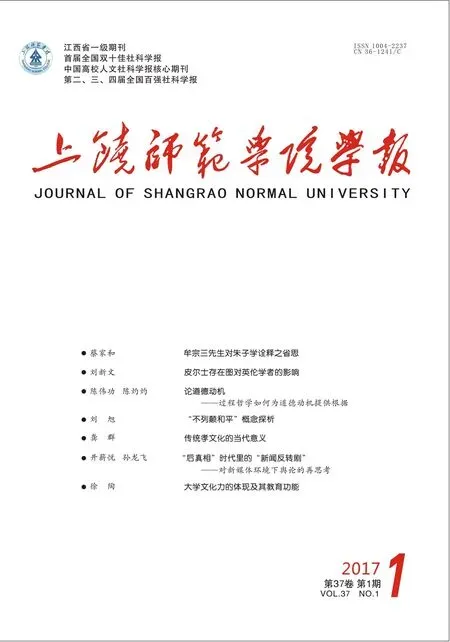浅议明代极端化女教
2017-03-30刘光华
刘 光 华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浅议明代极端化女教
刘 光 华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道德教育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明代的女性教育在中国古代女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朝廷对社会教化的重视使女教得到蓬勃发展。较之前代,明代的女教呈现出极端化的特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对明代女性提出了极为苛刻的道德要求,主要表现为贞节观的过分强调和缠足的风俗化。
明代;女性;道德教育;贞节观;缠足
在中国古代,正规的学校教育是与女性无关的,《中国教育史》中没有对女子教育的任何记载。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数目庞大的特殊群体,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女性的教育都是必要的。中国古代女子究竟如何接受教育,如何配合家庭、社会对其各种职责的要求,完成其历史使命,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对女子教育都有所涉及,主要是以家庭教育为主,对女性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工等方面的训导,其核心是女性应该秉持的最基本的“德性”,即道德人格教育,明代以前无大的变化。有明一代,女子德性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朝廷为了“励纲常”而“激薄俗”,社会教化渗透到日常习俗的各个领域和从皇室到民间的各个阶层。
一、明代女教的基本要求
古代女子的活动场所基本在庭院之内,女子教育主要目的是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对女子的教育是以“三从四德”为总纲领的封建伦理规范教育,主要教导女子在家庭中如何扮演合格的角色。明代女子教育亦如是。明代女教的基本要求是以“三纲五常”为基准做到“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女德。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一向以“德”为首,认为“妇女之美,不在于容貌娇冶,在于德行端庄”[1]。明代也毫不例外。明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中多次强调女德:“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故妇女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无陂,所以成德也”[2]。在皇室的倡导下,民间的女子教育把女德置于首要地位,极为强调。如吕坤在《闺范》中强调:“妇人者,优于人者也。温柔卑顺,乃事人之性情。纯一坚贞,则持身之节操。至于四德,尤所当知。妇德尚静正,妇言尚简婉,妇功尚周慎,妇容尚闲雅。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3]王相之母刘氏的《女范捷录》十篇之中的前四篇内容都与女德相关。由此可见明代女子教育以德为先的要求。明代对女子德行的要求细致至极,从言行举止、穿衣戴帽到待人接物无不涉及,如“语莫掀唇,坐莫动膝,……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藏,窥必藏形”[4]。而且规定女子要学习家务劳动、学习如何伺候公婆丈夫等。在明代,“德”是衡量女子的首要标准,女子可以无才无貌,但绝不可以无德。
虽然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很多家庭不教女子读书识字,但是并不反对女子学习文化知识。“女生八岁外,授读女教、列女传,使知妇道。”[5]只不过读书的内容要以女德教育为主。明代出现了大量女子教育类书籍,如《闺范图说》《女四书》《女儿经》《女小儿语》等,以“三从四德”为指导思想,以“男尊女卑”为主要内容,以古今列女事迹为例,极力宣扬封建礼教,教导女性要恪守本分、顺从天命,勤俭持家等。明代虽不反对女子读书识字,但是反对女子学习诗文,指出“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6],认为女子对文学的追求会妨碍其家庭角色的完成,会影响女德的养成,风花雪月的诗文会让女子多愁善感,甚至会诱导女子做出有违伦理纲常的事情。尽管如此,明代中叶以后,还是出现了不少女性人才,只不过大多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如明末文学家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及其三个女儿都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明代女教对女子的众多道德要求中最为重要的是贞操要求,国家对贞女节妇进行褒奖,社会对女性“三从四德”要求与以往各朝相比大大加重,把女子的贞节凌驾于其生命之上。在社会如此教育下,失去贞节的女子别无选择,唯以死殉节。
二、明代女教极端化的表现
不可否认,明代女教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处不再赘言。明代女教较之以往各朝女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代对女子德育的要求更加苛刻,对妇女的迫害至深呈现出极端化的特点。其极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极其强调贞节观,二是妇女缠足的习俗化。
1.贞节观念的极端强化
贞节观是古代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大部分朝代并不反对女子改嫁。至明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反对女子改嫁,在贞节观上对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女范捷录》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7]在明代的女教书里面都极其强调贞节观,《女论语》《内训》皆以贞节教育为大务。《女儿经》讲到:“习女德,要和平,女人第一是安贞。”“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8]强调“从一而终”,即使是在丈夫死后,也要为夫守孝(其中包括订婚未嫁夫亡的情况),坚决反对妇女改嫁,甚至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直到明代晚期,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对改嫁妇女的要求仍然相当的苛刻,“凡妇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9]。
明代守节的形式、花样之多为各朝所不及。守节女子除了常见的不改嫁的节妇之外,还出现了以死殉节、自残守节的烈女和守志室女,守节形式的多样和节烈程度的惨烈无不体现出此时女子贞节观的极端化。其中自残守节是指自残身体甚至自杀以明守节之志,其惨烈程度难以想象。如《明史·列女传》记载:
欧阳氏,九江人,彭泽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抚遗腹子,纺绩为生。父母迫之嫁,乃针刺其额,为誓死守节字,墨湼之,深入肤里,里人称为黑头节妇。[10]
除自残守节之外,室女守节这一极度变异的贞节行为也在此时出现。所谓室女守节,是指女子终身不嫁,居住在家中,以这种方式赡养父母,达到恪守贞节的目的。明代之前室女守节行为极为少见,明代时期,随着女子贞节教育的不断发展,统治者极力颂扬贞节观念,众多的节妇烈女相继出现,各种守节行为层出不穷,室女守节的现象也逐渐增多。
在这种极端的贞节观念的教化和倡导下,崇尚节烈之风蔓延明代社会各个角落,节妇烈女数量急剧增加,明代女性被这种极端的贞节观束缚着推向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祭坛。董家遵对《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的节妇烈女做过统计,如附表[11]:

附表 历代节妇烈女数目统计表
由附表可以看出,明代节妇、烈女的数量激增至3万之多,为古代各朝之最,比所有朝代的节妇、烈女总数还要多得多,实在令人震惊。
2.妇女缠足习俗化
缠足,俗称裹小脚,就是用一条长长的布裹住双脚让其畸形生长成人们想要塑造的形状,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身心健康摧残的形式之一。女性缠足是明代对妇容的要求之一。关于缠足的起源,说法不一,此处不作考究,总体上看以往各朝对妇女缠足并无强行规定,只是作为一种时尚在上层社会流行,并未普及。至明代,妇女缠足之风进入兴盛时期,并在各地迅速发展,缠足成为明代社会普遍的审美标准,人们皆以小脚为美,以天足为耻。女子脚的大小在当时已经成为女子婚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不缠足的女子甚至面临嫁不出去的危险,备受歧视与耻笑。明代开国皇后马皇后就以一双大脚而备受当时的文人讥讽,笑其是“淮西好大脚”。缠足是对女性身心的摧残,民间一直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从女子四五岁开始,由长辈折断其脚骨甚至用刀或瓷片划破脚面和脚底让脚腐烂化脓而变小,一双合格的小脚需要历经数年才能成型,在此期间女子所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明代对妇女缠足有许多新的要求,在脚的形状上要求把四趾拳回固定,脚背上弓,只留拇指协助脚跟支撑一身重量,掌握平衡;女子小脚不但要小,要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总之,以小于三寸为美,缠足言必三寸就是始于明代。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进占四川时,大刖妇女小脚,及至堆积成山,名曰金莲峰,由此可见明代妇女缠足风气之盛。在明代,缠足已成为对各阶层女性的普遍要求,《明史舆服志》中就明确地记载着明代皇宫之人皆着“宫样鞋,上刺小金花”[12]。至明中叶,胡应麟在《采韭录·正编识小录》中曾提到宋代初期,缠足的女性并不多见,到明代时期,全国上下的诗词曲剧莫不论及缠足,连“五尺童子”都 艳羡“足之弓小”,可见明朝的缠足风俗已经遍及全国,深入人心。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女子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通过缠足这一简单却残忍的方式打造出一双双畸形的“三寸金莲”以满足社会畸形的心理需要。
三、明代女教极端化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对女性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明代女教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实为鲜见,对女性贞节的极端强化和对女子缠足的大力推广体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迫害至深至广。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朝廷的重视和倡导
“夫妇为人伦之首,闺门乃王化之原。古圣王施政家邦,未有不先及于妇人者。妇人化,而天下无不化矣。”[13]女子教育关系到对后代的培养、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得失,在“家天下”的古代中国,加强女子教化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故历来受到朝廷的重视,明代尤为如此。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决定了朝廷不得不重视社会教化。孟森先生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14]元代的无制度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极其混乱的局面。至明代得天下时,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礼崩乐坏。面对此种情景,朱元璋提出“为治之要,教化为先”[15]的治国理念。“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16]前朝的“女祸”之鉴,让朱元璋清楚认识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遂于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以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在朝廷的重视之下,思想家与教育家都格外注重女性教育,积极编写饱含封建礼教的道德行为规范,不断加强对女子道德修养要求,尤其是对贞节要求的强化。此时期大量以“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女教教材应时而生,据统计,明代的女教书籍近50种[17]。明代后宫之中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多位帝后亲自撰写关于女性教育的训言。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参照历代有关女性的教育教诲编写成《内训》,从进德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睦亲慈幼等方面指导后宫女子的言行。还有章圣皇太后的《女训》和慈圣皇太后的《女鉴》,都从各方面对女性提出道德要求,强调女德的重要性。明代朝廷还制定旌表制度褒奖符合贞烈条件的女子,借此引导女子遵守封建礼教的道德要求。比如将旌表节妇烈女立为常制,“使天下之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者咸知违理之可羞,而一惟礼义之是慕”[18],朝廷还派专职官员负责此类事宜,对事迹昭著者赐祠祀或树牌坊加以表彰,引导女子践行贞孝节义的女德观。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9]朝廷除了下诏表彰、赐予匾额或给银建造牌坊、祠祀等精神奖励之外,还会给被表彰的女子所在家庭免除徭役、赐予粟帛等物质实惠。由此带来的荣耀以及经济负担的减免使明代女子成为家族贪功图利的工具,因而更加注重对女子的贞节观教育。如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杨继盛在家训中有云:“妇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盖以夫主无儿女可守,活着无用,故随夫亦死,这才谓之死,死有重于泰山,才谓之贞节。”[20]是说,丈夫死了,若无子女需要照顾,女子就应该以死殉节。在明代士人的眼里,女性完全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毫无独立存在的价值。在如此的封建礼教教导和双重利益的驱使下,大量女子主动或被迫成为所谓的贞妇节女。尽管《明史·烈女传·序》所说“湮灭者尚不可胜记”,史书中只“存其什一”,其数目也是相当惊人,达数万之多。一些以死殉节,以及恪守礼教名节而自残或被杀的女子,亦被授予“贞烈”之名加以表彰。如《明实录》中记载:
洪武十七年,还旌表汝宁府汝阳县民庄十一妻范氏贞节。范氏,夫亡年二十七,舅姑老,子幼,贫无以为赀,所亲咸劝之他适,范曰:“妾闻烈女不更二夫。”遂截发自誓,纺绩以养舅姑,甘历艰苦,恪守妇道,至是年八十五。有司以闻,诏旌表之。[21]
山东兖州府齐氏,年二十八夫亡,欲自经,家人奔救获免,遂以“剪刀割左耳及发之半”。[22]
缠足与推行贞节观一样受到朝廷重视,成为明代的一种社会风俗和评判女子的重要标准。脚的形状与大小成为评价女子美丑的重要标准,一个女子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关系到其婚嫁问题,世人皆以娶得小脚女为荣。不仅如此,此时的缠足,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明人沈德潜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23],这里的丐户指的是吴王张士诚的旧部,朱元璋为了惩罚丐户不允许丐户子弟中的女子缠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缠足在明代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2.程朱理学思想的推崇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官学文化,程朱理学发展成为统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以“天理”为核心,极力倡导封建伦理纲常,为人们制定了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尤其是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更为细化,从各个方面加以严格限制,更对妇女贞节操守表现出狂热的关注。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极力宣扬“失节事极大,饿死事极小”,一味苛求妇女守节殉烈,包括要求未嫁女子守贞节,寡妇不得再嫁。此时朱熹极力宣扬的“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24]、反对妇女再适的贞烈观念已经为明代社会普遍认同。生活在明代宣德至弘治年间的陈献章说:“今之诵言者咸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5]而如何使女子保守贞节,成为理学家们费思量的问题之一。缠足可以限制女子的行动,减少其与外界接触的几率,在理学家们看来,这不失为保守贞节的好方法。元代伊世珍《螂环记》记载:“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阀之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邓之奔。’”[26]缠足将女子的行动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有助于女子遵从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保证“贞操节烈”这一最高道德标准的普遍实现。于是,缠足成为助使女子保持贞节的绝佳方式得以在明代大为推广。
有明一代,朝廷重视社会道德教化,在程朱理学的严格控制下,作为女教重要内容的贞节观念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断被推崇和强化,根植于民众之心,最终成为残害明代女性的重要方式。
3.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驭使然
首先,是受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对女子的要求是“三从四德”,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女子在长期男尊女卑观念的灌输及封建礼教的影响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夫妻关系上,男尊女卑尤为明显,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如《女论语》中写到“将夫比天,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若发怒,不可生瞋,退身忍让,忍气吞声”[27]。经济地位决定了明代女性只能依赖男性而生存,使其只能以男性的意志为转移。明代的贞节观是单就女性而言,对男性就没有忠于婚姻、忠于伴侣的要求,如《女范捷录》中所说“男可重婚,女无再适”[28]。男子不仅可以娶妻纳妾,还可以在外寻花问柳,只要会读书,其他“不拘”,女子对丈夫的言行只能是忍让和顺从,连抱怨都会被视为不贤惠,嫉妒在古代被列为休妻的七大原因之一。相比较于男性,对女子则要求“第一守贞,第二清贞,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29],不能轻易抛头露面,要求“从一而终”,把贞节视为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头等大事。缠足更是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等封建观念外化形式的载体。古代强调女子的卑弱,对女性美的要求一般是以纤弱为主。女性缠足后只能用脚跟缓慢行走,“摇摆如风中杨柳”,再则因行动不便、活动量少,身体素质一般较差,无疑使女性更具纤弱,男性的大男子主义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可以说缠足是为了满足男性虚荣心和变态审美观而催生出来的病态产物。这种病态的心理就连宋代大诗人苏轼亦不能免,他作词《菩萨蛮》大肆赞美小脚“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30]。这种病态的审美观直接影响到以夫为天的明代女性的行为,不惜以牺牲自我健康为代价博取男子欢心,缠足在对女性压迫到极致的明代成为社会风俗毫不为怪。
其次,是受男女有别的社会观念的影响。古代女子被视为男性的私有财产,除了自己的至亲和丈夫,女子不得与别的男性有交往,即男女有别。所谓“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男女不同行”等等,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表现。而缠足恰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达到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封建礼教用一道道看不见的枷锁把女子牢牢束缚在狭小、封闭的空间之内。如郑氏的《女教篇》中规定女子不能出中门,不能“窥穴隙勿”和翻越墙垣。缠足女性受身体条件所限,行动不便,要想走出中门与人随意出游自然比大脚女性更为困难,更谈不上“越墙垣”这等高难度动作了。通过缠足摧残女性身体,使其被迫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从而在闭塞狭小的空间内永远处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下,这有利于维护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符合男权社会的要求。
显而易见,无论是贞节观还是缠足,都是对女性的单向要求,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某种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是男性独占社会主导的必然产物。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明代女子被无形的伦理道德、有形的贞节牌坊推上了封建礼教的祭坛,成为明代统治者维护封建伦理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工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身心受迫害最深的特殊群体。
[1] 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6.
[2] 王相.女四书:内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28
[3] 吕坤.吕新吾先生闺范图说:四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544.
[4] 班昭.蒙养书集成: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9.
[5] 许相卿.许云村贻谋[M]∥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81.
[6] 陈弘谋.五种遗规[M].北京:中华书局,1989:225.
[7]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124.
[8] 新中国制糖厂工人理论组,等.《女儿经》批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4:6
[9] 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0.
[10] 张廷玉.明史:卷三零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14.
[11] 董家遵.家遵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32.
[12] 张廷玉.明史:卷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5.
[13] 张福清.女诫——妇女的枷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267
[14] 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
[1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5:65.
[16] 张廷玉.明史:卷一一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04.
[17] 丁伟忠.明代的妇女教育[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3):73-75.
[18] 丘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710.
[19] 申时行.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第 79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5.
[20] 杨继盛.杨忠愍文集[M].刻本.海阳:东里吴氏,1598(明万历26年).
[21]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八[M].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2570.
[22]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〇[M].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3923.
[2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78
[24] 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5
[25] 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52.
[26] 陈锋,刘经华.中国病态社会史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24.
[27] 宋若莘.女四书:女孝经女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88.
[28] 王相.女四书:女范捷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116
[29] 班昭.女四书:女孝经女诫[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9.
[30] 唐圭.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56:321.
[责任编辑 许婴]
On the Extreme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Guang-hua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s women are a special social group, the female moral education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by people. The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female education.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social education by the court made the teaching of women flourish.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showed extrem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keeping the justice and killing the human desire" put forward the extremely demanding moral requirements to the women in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chastity and the customization of foot-binding.
the Ming Dynasty; women; moral education;chastity; foot-binding
2017-01-05
教育部课题“个体道德态度养成”研究(2015YJC710065)
刘光华(1977-),女,湖北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E-mail:1158697594@qq.com
G776
A
1004-2237(2017)01-0067-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