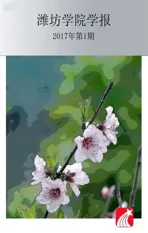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作为性
2017-03-09毕寓凡
毕寓凡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作为性
毕寓凡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本文试证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作为犯。本罪实行行为是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而非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在行为形式划分的诸学说中,规范说更合理;根据规范说,持有违反禁止性规范,故属于作为而非不作为;“不能说明来源”属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并非实行行为,但对不法判断仍有实质意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形式;规范说;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一、绪论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落马”的官员不可谓少。然而实践中,学界对本罪的可接受性、辩护范围和证据效力判准等多有争论。作为化解相关争论的前提,明确本罪性质,尤其是明确实行行为及其行为形式,显然至关重要。
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行为的形式,存在着作为说、不作为说、持有说、混合说的争论。有论者根据现行刑法对罪状的叙述,“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将实行行为定位在“持有巨额财产”,进而通过讨论持有属于作为、不作为或第三行为形式来化解争议。同时,也有论者认为,本罪实行行为系“不能说明来源”而非持有,故属不作为犯。他们的重要理由是,如果将“说明来源”理解为程序性要求、排除在实体要件之外,就表明本罪立法是对一种单纯的财产持有状态的犯罪化,而这种做法明显错误。
二、界定实行行为:“持有财产”而非“不能说明”
讨论行为形式的前提是界定实行行为的内容,故本文首先处理该问题。
(一)反省不作为说
如上所述,不作为说的核心,在于将实行行为界定为对显超合法收入的财产来源的“不能说明”,进而由于“不能说明”系不作为,本罪自然是不作为犯。有支持者认为,拒绝说明和虚假说明均在“不能说明”的合理解释范围之内;至于行为人拥有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而非行为内容。[1]
笔者认为,不作为说在作为义务来源和作为能力两方面均值得商榷。论证成立“当为、能为而不为”的不作为犯,需明确当为之义务和能为之能力,即“说明来源”的义务从何而来,以及“说明来源”的能力何以重要。不作为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令人不甚满意。
首先,作为义务来源不清。传统刑法理论将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归为四类,法律行为、职务行为、法律规定和先前行为。本罪显然不涉及法律或职务行为,所以此处仅余两种可能性,即先行行为和法律规定,两者皆有其拥趸。一些论者认为持有行为足以作为先行行为而提供说明义务来源,其他人则诉诸法规来解释说明义务。而关于究竟何种法规,此处又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义务就来自刑法第395条第一款,[2]另一种认为作为义务是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对讯问人员的“如实回答”义务,[3]还有人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或者司法人员的“责令”作为义务来源。[4]
笔者认为,以先行行为或法规解释说明义务均不合理。首先,持有行为不应被视为先行行为。先行行为的实质特征是造成危害结果出现的危险[5],换言之,作为义务来源的先行行为,必须满足“行为必然导致危险”和“危险必然导致危害结果”两重因果。而本罪中,持有行为与结果危险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否则责问就成了赘余,而且即便持有与危险的关联存在,它造成的危险也未必导致法益侵害,因为只要提供妥当的说明,法益侵害性就得以排除。据此,认为持有行为提供本罪作为义务的观点并不妥当。
另一方面,以法规作为义务来源也不可行。首先,将本罪之本条视为提供作为义务显然很荒谬,因为这意味着不履行作为义务即该当本条,但实际上不履行义务只是不作为犯成立的条件之一,即该当本条的条件之一。其次,以刑诉法的“如实说明”规定作为义务来源也不合理,因为该义务指向所有犯罪嫌疑人,不能解释本罪的特殊主体要求。认为申报制度提供义务来源的论者,其谬误则与先前行为论者相似。一来,逻辑上,从“禁止持有巨额财产,受到责问拒不说明”推不出“持有巨额财产要申报”的义务;二来,联系刑法第395条第二款“隐瞒境外存款罪”看,如果刑法有意将申报作为本罪的作为义务,就应与彼罪一样将义务的不履行表述为“隐瞒”这种更为主动的行为,而非拒不回答等被动情形,考虑到刑法将两罪规定为同一条的上下款,描述行为的不同措辞无疑是有意为之,是刻意将两者相区别,因此以现行申报制度支持该本条也难以成功。
此外,不作为说在作为能力问题上也存在疑问。尽管论者将实行行为概括为拒绝说明和虚假说明两种,[6]但根据本罪司法解释,“不能说明”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有四种:A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B行为人分辨不出财产的具体来源而无法说明;C行为人说明了财产来源,但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D行为人说明了财产来源,但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显然,在B情形下,行为人其实是没有说明能力的;D情形更将行为人说明来源而司法机关无法查实列为“不能说明”表现之一,而如果“不能说明”是本罪实行行为,那这岂非让当事人为“他人不能”负责?即便忽略法理上的疑问,将不能说明视为构成要件行为进而归入构成要件客观方面要素,D情形岂不也意味着控方对“司法机关无法查实”承担举证责任?这显然与司法实践相去甚远。
(二)持有的法益侵害性
综上可见,由于无法妥善解释作为义务和作为能力,不作为说实际相当脆弱。但正如开头提到的,很多论者坚持不作为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反对作为说,反对将一种单纯的财产持有状态设为不法。
但实际上,拒不说明财产来源和持有来源不明之财产,何者才是对本罪不法状态的正确描述,这点并非不言自明。认为拒不回答司法人员有关财产来源的追问即成立不法,[7]可能更不合理。这一切首先取决于对违法性的理解。违法性是规范违反和法益侵害之统一,[8]这表明不法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违反保护特定法益的行为规范而造成对该法益的侵害,即对本罪客体的侵害。①“欧陆学说中的客体分为‘保护客体’和‘行为客体’”(曲新久《刑法学(第四版)》,第64页),分别对应我国学说中的“客体”(即法益)和“犯罪对象”,本文“客体”采用我国语境下的含义,仅指一实行行为侵犯之法益而不包括行为对象。故问题在于,直接侵害本罪客体的是拒不说明财产来源还是持有来源不明之财产?
显然,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明确本罪究竟保护何种法益。学界对此亦广有争论。有人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9]有人认为是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更有论者以兼具这两种法益的复杂客体为然。[10]
笔者认为本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非司法机关监督权。根据司法解释,本罪包含行为人说明了财产来源、但司法机关无法查实的情形,该情形中司法机关的监督权没有遭到侵害。由于客体是个罪成立所必然侵犯之法益,故以监督权为客体与解释不符,而复杂客体的观点同理也失之谨慎。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是本罪必然侵犯的。这点是由该法益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很明显,职务廉洁性几乎是任何职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具备的,刑法也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等行为进行了犯罪化,但为什么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可能因持有巨额财产而构成本罪?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特殊,代表国家形象而行使公权力。出于身份的代表性,当国家工作人员坐拥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受到负面评价的就不只是行为人本人,也是他所代表的公权力即国家。这意味着,区别于其他职业,值得保护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不仅包括“廉洁之实”,还包括“廉洁之表”,因为多数民众没有能力深究官员的巨额财产来自何方,只能根据其拥有巨额财产这一事实本身给予负面评价,[11]所以拒绝说明财产来源和说明来源却无法查实,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形象的损害程度其实相差无几。概言之,本罪中,只要没有证明拥有正当理由,持有本身就具有法益侵害性。
由此可见,直接侵害本罪法益的行为是持有来源不明之财产,而非拒不说明财产来源。首先,与缺乏正当理由的持有状态不同,“面对司法机关的责问而拒不说明”直接侵犯的不是廉洁性,而是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其次,当财产来源得以查清,行为人的说明程度实际上就没有任何规范意义。此外,说明来源也不是行为人脱离犯罪风险的唯一选择。只是必须承认,由行为人自己妥善说明来源,正是为持有提供正当理由的最有效途径。而当持有巨额财产的正当理由得以证明,该状态自然不再具备违法性。据此,对财产来源的不能说明应被理解为本罪成立范围的限定条件,而持有状态才是不法之源头。
综上,由于本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能够直接损害它的是持有状态,不是不能说明财产来源,所以本罪实行行为应被理解为持有而非“不能说明”,进而以实行行为是“不能说明”为由论证本罪属于不作为犯的观点,也就难以成立。
三、持有的行为形式:作为而非不作为
既然将本罪实行行为界定为持有财产,其行为形式就取决于持有的行为形式。本章将处理该问题,明确持有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一)行为形式划分的学说:动静说与规范说
在行为形式划分方式上,主要学说可划归动静说和规范说两类。[12]前者主张从事实角度分析,以行为人身体的物理状态为标准,动为作为,静为不作为;后者主张从规范立场出发,以行为违反规范的类型为标准,违反禁止性规范为作为,违反命令性规范为不作为。
动静说的缺陷很清楚。一来,有生命的人在物理上不可能保持绝对静止,若把任何一种人体的积极运动(脉动、心跳、肌肉颤动…)均视为作为,那么不作为就会失去存在空间。[13]二来,刑法也没有必要关心行为人的一切身体活动,只需关心行为人是否履行其义务,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法秩序的规范性期待,至于是否从事其它活动无需计较。相比之下,规范说的思路更好地把握了刑法中行为的特征。如前所述,不法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违反保护特定法益的行为规范而造成对该法益的侵害。相应之,刑法的核心功能,便可被理解为通过调整规范性行为的特殊方式来实现法益保护目的。据此,规范性,即拥有评价意义上对规范的符合或违反之意义,可以说是刑法中行为的一个核心特征。因此,以这种行为规范划分实行行为形式,自然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规范属性的判准:文本论与功能论
认同规范说,意味着以行为规范的不同属性区分作为或不作为。这样,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判断规范属性。
早期学界通说以规范文本的表述方式为判准。据此,禁止性规范即表述中包含否定性语词(如禁止、不应当)的规范,命令性规范则包含肯定性语词(必须、应当)。[14]读者容易发现这种观点的乖谬之处。规范的表述方式是多变的,如果认为规范属性会随之改变,那以规范属性划分行为形式就不可能得到稳定有效的结论。诚如一些规范说反对者所言,如果命令性与禁止性规范可以随意转换——比如对他人生命权所负的义务,既可表述为命令性规范“尊重他人生命权”,也可表述为禁止性规范“禁止不尊重他人生命权”——规范说就是一种可疑的学说。
笔者已在别处详述过,这种将规范与其表述语句混同的文本论是错误的。[15]很明显,规范不是规范语句,而是语句的意义。由于同一意义可以通过不同语句加以表述,如果规范属性确实附着于规范而非规范表述,那么逻辑上同一规范就能产生不同的规范语句,同时保持其禁止或命令的属性不变。因此,一个包含否定性语词的规范语句和一个包含肯定性语词的语句(比如上面有关生命权的语句),实质上可能是同一个属性稳定的规范。不过这里的一个复杂之处是,尽管规范语句并非规范本身,却无疑是我们理解规范本身的重要依据。幸而,它不是我们理解规范的唯一依据。能帮助明确规范意义的不只有文本语句,还有特定规范的功能,即符合规范的行为指向。这种根据规范的行为指引方向划分属性的观点,可标记为功能论。笔者认为,由于对规范实质的理解应当聚焦于它指导实践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文本表述仅仅是实现该功能的方式之一,故属次级问题),因此功能论比文本论更为合理。那么如何认识能够区分实行行为形式的规范功能?——很明显,刑法规范的功能,自然是给刑事法官提供裁判指南。指引法庭的确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据此解读的刑法往往被称为“裁判规范”“罪刑规范”[16]或“刑罚法规”①德国学者宾丁在《规范论》中首先提出区分规范与刑罚法规。根据宾丁,“杀人者处死刑”是法规,这一法规背后蕴涵的“禁止杀人”命题是规范。因此,犯罪不是法规之违反,而是规范之违反。尽管后来贝林、麦耶对该学说的发展使规范内涵愈发抽象,但这种区分已被普遍认可。容易看出,宾丁那里的“刑罚法规”就是本文此处的裁判规范。另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的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并以实定法文本反映其内容。但这种裁判规范必定不是规范说的行为形式判准,因为它不可能被行为人所违反——行为人是因为符合、而非有悖裁判规范提供的构成要件,才进入法庭视野。不过,刑法的行为指引不可能止于法庭之内,因为向行为人提前宣告行为要求、并以违背该要求为裁判规范的适用条件,也是法治的题中之义。至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上文有关规范说优势的描述。既然规范说的合理性在于体现实行行为的特征,即违反保护法益的行为规范而造成法益侵害,那彼说的分类规范就理应被理解为这种通过指引社会一般人来保护法益的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范。
至此我们得到有关规范功能的重要信息,即通过指引一般人行为来保护法益。笔者认为通过这一功能划分规范属性是可行的。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之下的法益保护方向不同,因此行为选择的范围就有所不同。禁止性规范限制或禁止从事焦点行动,行为人因此有规避风险的诸多选择;命令性规范则要求从事焦点行动,行为人的行为选择较为单一。[17]以持有假币的禁令为例。该规范可以表述为“禁止持有假币”,也可表述为“如持有货币则只能持有真币”,但规范属性始终是禁止性的,理由在于:首先,禁令与假币取得的行为无关,所以规范从行为人实际控制假币开始生效,因此应当考察行为人此时的行为选择宽度;那么规范此时提供哪些行为选项?显然,行为人可以上缴假币,但也可以将其销毁或抛弃,鉴于禁止持有假币的义务推不出上缴假币的义务。因此规范提供的行为选择范围较宽,属于禁止性规范,进而持有假币的行为系作为。
(三)规范说下持有巨额财产的作为性
很明显,当以规范属性作为行为形式划分标准,就不可能将持有视为第三行为形式了。义务性规范的命令性与禁止性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由此推出的行为形式的作为与不作为也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是,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行为的“持有巨额财产”属于哪种?
笔者认为,规范说下持有巨额财产的作为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处与上文的假币持有禁令逻辑相同。当行为人发现其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他有着较宽的行为选择可能性——解除对巨额财产的持有状态、明示对持有财产的占有合法性、自行申报或在面对责问时说明来源并经过查实,这些均可排除人们对公职人员廉洁性的质疑。行为选择范围的宽度,向我们昭示了此处行为规范的禁止性,进而昭示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作为性。
不过,可能仍然存在这样的疑问:上述结论是否表明一种刨除其他条件的单纯财产占有状态也属不法?并非如此。体现本罪不法特征的是持有来源不明之财产而非不能说明财产来源,不意味着不法可以通过持有财产而个别地认定,因为成立不法需要同时满足全部不法要件,[18]而本罪中的相关要件除了持有,还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持有巨额财产状态和不能说明来源等等。正如行医与无照并存才是非法行医,持枪与无证并存才是非法持枪,不意味着未办执照、未办持枪证属于实行行为,更不意味着相关犯罪属于不作为犯。
尽管上述质疑不难回应,却毕竟表明合理安置“不能说明”要素的重要性。区别于其它诸多持有犯,“不能说明”意味着本罪包含一个其实是不作为行为,却并非实行行为的要素,难免令人困惑。另一方面,持有犯通常被认为是继续犯,比照继续犯模型“非法状态持续直到某一行为发生使之中止”,说明来源似乎也有着中止非法状态的重要功能。由此可见,任何探究本罪实行行为形式的努力,都应包含对“不能说明”的体系性位置的合理解读。
四、“不能说明”的性质: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有关本罪中“不能说明”处于犯罪论体系的什么位置,存在不同见解。除了认为“不能说明”是实行行为,还有论者认为“不能说明”是一种程序性条件,[19]或客观的处罚条件,更有人反向考察其地位,认为“不能说明”的意义在于将“说明来源”摆在正当化事由的位置上。[20]区别于这些看法,本章将说明,“不能说明”应被理解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
(一)对程序性条件说和客观处罚条件说的反思
认为“不能说明”属于程序性条件者为数不多,面临的挑战也明显。毕竟,围绕本罪行为形式的激辩本身就表明,将“不能说明”排除出实体要件范围是相当危险的举措,因为难以想象任何民主国会将公民对财产的纯粹持有状态犯罪化,仅仅给予程序性的免责。认为“不能说明”对本罪成立的意义与亲告行为对亲告罪的意义一样,与不法毫无关系,这种观点恐怕很难成立。
出于相同原因,客观处罚条件说也不可靠。客观处罚条件的情形是,“‘通常情况下,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且有责的行为成立后,就会出现刑罚问题’,但是,立法者有时出于不同的原因将行为的可罚性与无关构成要件特征的外在情形联系在一起”。[21]由此可见,客观的处罚条件是纯粹的政策性产物,虽然包含在实体法中,但不在犯罪构成之列,所以不参与决定实质违法性。既然认为“不能说明”对本罪不法成立具有实质意义,就不能将它放在客观处罚条件的位置上。
(二)正当行为说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说
认为“不能说明”的立法目的在于让说明行为成为本罪的正当化条件,这一思路令笔者赞赏。论者道:“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规定不是积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而属于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反过来说,“能够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成立阻却违法的事由。立法者之所以要在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中作特别宣示,是由于这一正当化事由仅适用于本罪,即它是一种只适用于某种犯罪的特定的去罪化事由,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总则中予以规定。这也是它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职务行为等一般正当化事由的区别所在。[22]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正当化行为可以自始阻却不法,将说明来源理解为正当化行为,就能在否定“无法说明”属于实行行为的情况下,使之对不法认定具有实质意义。不过问题是,为使说明来源有正当化能力,“不能说明”需要处于何种体系性位置?上述分析的逻辑是:因为“不能说明”是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所以“说明来源”是阻却违法性事由或正当化事由。
在笔者看来,上述思路中可能存在一种错位。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条件之一,而正当化行为却属于单纯的违法性评价。从缺乏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推不出成立正当化行为,因此从“不能说明”是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推不出说明行为属于正当化事由。导致这种错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作者其实试图将“不能说明”定位为消极构成要件,而非构成要件要素。消极构成要件是与构成要件该当性(积极构成要件)对应的概念,对应的正是传统三阶层中的正当化阶层。这样,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是消极构成要件,不过是说明合法来源属于正当化行为的另一种说法。
如此一来,单纯出于自洽,对该表述有两种可能的修正方式:其一是坚持正当行为说,认为“不能说明”系消极构成要件,即说明合法来源作为正当化事由否认不法;其二,改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说,认为“不能说明”系消极构成要件要素,即说明合法来源能通过否认构成要件该当性来否认不法。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其结论都符合作为说的期待——表明“不能说明”是一个并非实行行为的不法要素。
不过笔者认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说可能更优。因为它在符合作为说期待的同时,能更好地回应不作为论者的担忧。上文已经表明,本罪引起不作为论者激辩的重要原因,是对单纯财产占有状态的犯罪化有正当性不足的隐患。而较之将说明合法来源推到正当化位置上,使它直接否认构成要件该当性,显然对杜绝该隐患更加有利。毕竟,一定意义上,①毋庸赘言,此处的“一定意义”取决于如何理解构成要件该当性与正当化行为之关系。核心问题是,正当化事由阻却不法的实质,是不是否认行为因符合犯罪定义而具备的违法性。在笔者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考察正当化规则有没有能力取消前述行为规范。如果正当化情境中刑法的行为规范自始被取消,那么正当化事由就与消极构成要件要素拥有同等的否认犯罪化的能力,只是判断顺序上靠后而已。围绕该问题存在着消极构成要件理论、行为构成要件说、行为违法类型论等的复杂争论,本文显然不是讨论它的好地方。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说规避犯罪化风险的能力,必定不会低于正当行为说,反之却未必成立。尽管同样作为否认不法的“去罪化事由”,通过否认该当构成要件实现这点,直接意味着行为不符合犯罪定义,从而能直接否认对单纯财产状态的犯罪化。
五、结论
本文意在论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行为的作为性。为实现该目的,笔者先将客体锚定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从而通过与客体关系的分析,将实行行为界定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否认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作为实行行为的资格,从而否认将实行行为认定为不能说明的不作为说;其次,证明行为形式划分的妥当学说是规范说,且规范属性可以通过功能加以区分,从而确认持有行为由于违反禁止性规范属于不作为,得出本文结论;最后,笔者解释了“不能说明”作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体系性位置,表明它虽非实行行为却仍属不法要素,并妥善回应了不作为说的支持者有关本罪犯罪化正当性不足的担忧。
[1][2][6]余华,郭泽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持有型追问—兼与李宝岳教授、吴光升先生商榷[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4(1):132,133.
[3]孟庆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方面问题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3):11.
[4][7]侯国云.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个问题[J].政法论坛,2003,21(1):86,88.
[5]曲新久.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86.
[8]王安异.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J].刑法论丛,2007,(1).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u5236%u5EA6%u4E0D% u8DB3%u4E0E%u515C%u5E95%u6761%u6B3E.
[9][11]王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浅探[J].当代经理人,2006,(14):100,101.
[10]李宝岳,吴光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证明责任研究[J].政法论坛,1996,(6):68.
[12]聂慧萍.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7,(8):759.
[13]邓斌.持有犯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75.
[1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52.
[15]毕寓凡.论行为形式划分的规范说[J].研究生法学,2015,30(6):115-116.
[16]李金明.论不作为的行为性[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84.
[17]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88.
[18]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王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1:20.
[19]李宝岳,吴光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证明责任研究[J].政法论坛,1996,(6):66.
[20][21]劳东燕.揭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面纱—兼论持有与推定的适用规则[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6):54.
[22]哈德·施密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24.
On the Acting Character of the Crime of Huge Unidentified Property
BI Yu-fa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The essay is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form of the crime of huge unidentified property as an active one.The perpetrating act of the crime focusing on the possession of huge unidentified property,not the failure to explain its source properly.Of all the major theories aiming to distinguish the two forms of behavior the Norm Theory seems the most reliable,according to which possession,as a breach prohibitive norm,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kind of action rather than omission.Failing to explain the source properly,therefore,is not the perpetrating act of the crime,but a negative constitutive element,which can also play a substantive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unlawfulness of the possession.
the crime of huge unidentified property;the form of behavior;the norm theory;the negative constitutive element
D924.3
A
1671-4288(2017)01-0043-06
责任编辑:王玲玲
2016-08-12
毕寓凡(1991—),女,山东潍坊人,中国政法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