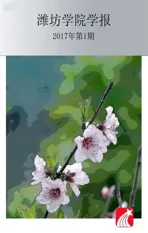陈介祺与全形拓
2017-03-09王俊芳
王俊芳
(潍坊学院,潍坊 山东 261061)
陈介祺与全形拓
王俊芳
(潍坊学院,潍坊 山东 261061)
全形拓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滥觞期、发展期、鼎盛期。在发展期阶段,陈介祺“以图取形”的拓技和“分纸拓”的拓法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全形拓的成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沿着全形拓的成熟过程来追溯陈介祺的贡献。
全形拓;陈介祺;器形拓;图形拓
在上个世纪初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照相技术还没有在中国推广,人们要欣赏一些名贵的青铜器形制与纹饰,只能采取传拓的方式,也就是以墨传拓青铜器全形,即本文所说的全形拓。全形拓,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全”是完备、齐全,形是器物的形状、形体。
全形拓是一种结合绘稿、剪纸等艺术,以墨拓技法,运用透视、墨色的浓淡变化以及拓技者的线描、裱拓等技法,尽可能完整地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一种特殊技艺。[1]对于同一件器物的传拓,由于墨、纸张的不同,还由于拓者的审美观以及椎拓轻重等方面的差异,每一次传拓都是“创作”的过程。它和平面拓片不同的是,全形拓一定要严格按照器物各部位尺寸的大小比例,仔细审查其向背并按照需要或浓或淡地进行施墨,尽量使得拓出的器物富含立体感。这一拓技出现于清代嘉道年间,其形成和成熟过程大致可分为滥觞期、发展期、鼎盛期。在其发展期阶段,无论如何都避不开陈介祺这一金石学大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陈介祺“以图取形”的拓技和“分纸拓”的拓法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全形拓的成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分纸拓”拓主陈介祺
自宋以降,传拓种类繁多。如宋代的毡腊拓、隔麻拓,明之色拓、套拓、烟煤拓,清代的镶拓、洗碑拓、堆墨拓等。这些拓法多以平面为主,是对器物上的文字或者纹饰进行拓印。限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它们基本都没有传拓立体的“器形”。对青铜器的器形进行传拓,即“传拓其立体全形”,就是本文论述的“全形拓”,它与平面拓有着质的不同。从传拓工艺流程看,拓器物立体全形是传拓中最难的一种,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和追捧。
从拓法上来说,全形拓一般分为分纸拓和整纸拓。“分纸拓”法是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拓出来的每个部位是相对独立的一张纸,然后用净毛笔蘸水划撕掉拓片周围的多余白纸,留下墨拓部分;之后,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形成整个器形图。由于分纸拓所画图稿比较准确,加之用墨的浓淡控制适宜,给观者以所拓器物跃然于纸上的感觉。晚清金石学家大师、传拓技艺的一代宗师的陈介祺发明并传播了此拓法。
和“分纸拓”对应的是“整纸拓”。该法首先是选择所拓器物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绵连纸上画出一个“⊥”形图,然后以它为基础画出线描图,随后把绵连纸覆在所拓器物上,再后面就是用蘸上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墨拓黑,最后把它揭下。这是在一整张绵连纸进行的因此也叫“整纸拓”。是周希丁等人吸纳了陈介祺的分纸拓之后,将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到了全形拓之中的产物。
分纸拓和整纸拓,是全形拓的两种不同拓法,笔者看来难分优劣。正如马子云先生所认为的,二者“各有所长,也有所短”[2]。陈介祺则说,“整纸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赏也。”[3]陈介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看来,制拓最主要、最核心的是尽量真实而准确地再现器物的原貌,较分纸拓而言,整纸拓法的变形失真程度更严重,即使它将所有操作都在古器物上进行(而事实上,这根本也是不可能的)。浙江博物馆的王屹峰也指出,“分纸拓的器形结构更为合理一点,也是事实,从技法而言毋庸置疑。”[4]诸多研究者常常由于整纸拓的技术难度指数更高而多推崇整纸拓,但客观看来,技术的难度和技艺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一回事。
二、陈介祺的“图形拓”是对“器形拓”的质的提升
而全行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具有明显差异的称谓:“器形拓”和“图形拓”。两种称谓有联系,又有重要不同: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重大突破和弘扬。前者代表了全形拓的滥觞阶段,而后者则是金石学大师陈介祺对这一拓技的质的提升,正是这一提升,才使得全形拓进入发展和兴盛阶段。也正是由于这两个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僧达受和陈介祺的杰出贡献,使得六舟和尚和陈介祺被并称为“开山祖师级别的标志性人物”[5]。
(一)六舟的“以灯取形”
处于全形拓滥觞阶段的“器形拓”的开创者,有两种说法:一为清代道光时期的马起凤,二是僧达受。他们的贡献为陈介祺的图形拓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先看马起风。浙江省博物馆学者桑椹在《全形拓之传承与流变》一文中指出,全形拓由浙江嘉兴人马起凤始创,制拓时间可能“早至乾隆年间”[6]。马起凤(1821-1850),字傅岩,生平不详。清代长洲(今苏州)人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亦云:“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凤所拓得汉洗……今马氏拓本,除金石屑所载外未见他器。”[7]《金石屑》所录汉洗,上有马氏题跋:“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8]
再看僧达受。达受(1791-1858)字六舟,又字秋楫,别号寒泉、南屏退叟、万峰退叟等。不少人认为他是马起风的学生。达受俗姓姚(也有姓陈之说),名峻,嘉兴海昌(今属海宁)人,出家后,主杭州西湖净慈寺、苏州沧浪亭大云庵、镇江焦山寺(定慧寺)。特别喜好金石,据其自编年谱《宝素斋金石书画编年录》中记载,凡是其所到之处,遇到摩崖或者钟鼎彝器一定亲自拓其全形。他留给后人“以灯取形”的制拓方法。
以焦山鼎为例,该法大致是这样的:达受以灯取形,把焦山鼎的尺寸量好画好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的六吉绵连纸做拓纸,以绸布包裹棉花作扑子,拓前先把白芨水刷在所拓器物上,再用湿棉花上纸,等纸干后,用做好的扑子将墨扑拓上去。达受的这一方法颇得藏家青睐,当时的金石家对此颇为赏识。如阮元曾在僧达受拓焦山鼎器形拓本卷轴上做了这样的题跋:“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本而印成鼎形,又以此折纸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器于无别,真佳刻也。”[9]
冷静分析,这种“以灯取形”的方法,是用灯照在所拓器物上,获取该器物的投影,再依照投影勾划出它的形状。这种方法的明显弊端是,当灯越是接近于器物时,器物越大,反之就越小。即便是用实际尺寸来较正也是难于精确的。“以厚纸做漏子”、“画图刻木而印成鼎形”、“并铭亦是木刻”等手法,也只能得到器形的大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灯取形”的确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以灯取形”制作的器形拓出现之后,“以图取形”的图形拓进入世人的视野并不断发展,它是全形拓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此间,陈介祺等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陈介祺的图形拓
被吴大澂誉为“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的陈介祺,人们常常缅怀其收藏与鉴别方面的贡献而不太提及其“拓本之工”的开创性功劳。事实上,这位金石学大师借助自己的富藏和精鉴的优势,为“全形拓”的推广、提升贡献了自己的全力。正如陈先生所言,“如果说六舟达受因为自己不是金石学家与收藏家,因此从事‘全形拓’还带有游戏性质的话;那么稍后的陈介祺,则是依托宏富的青铜器收藏,对传拓和‘全形拓’予以了专业水准的推广与细密分类观照。”[10]
的确,作为晚清的金石学大师,陈介祺对经史、训诂、义理、辞章、音韵等无不钻研,尤其对金石文物怀有特殊爱好。他竭力传古,而在当时,传古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制作拓片。在制拓方面,他力求“精拓”。而对青铜器等器物全形进行精拓也是其一直在考虑和实践的重要方面。图形拓正是他在六舟和尚“以灯取形”思路启发下,结合自己的大量实践和研究,将青铜器拓技进行质的提升的必然产物。
客观来说,“以灯取形”在更大程度上只能是写意的,因为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太多的可塑性,达受和尚穷其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极尽“似”。而陈介祺的“以图取形”则更接近真实了,因为:“拓图以记尺寸为主。上中下高低尺寸既定,其两旁曲处,以横丝夹木版中,如线装式,抵器,即可得真。再向前一倾见口,即得器之阴阳。以纸背挖出后,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素处以古器平者拓之。”[11]陈介祺在致潘祖荫的书信中也指出,该法(指的是“以图取形”的拓法)需要用尺子进行准确度量:“《作图说》鼎宜度以建初尺,尺有木者,有纸褙者,有三尺五尺者,乃便。耳、鼎上口(径、圜)、腹(深、圍、下垂之中),均须详度。”[12]用陆明君的话来说就是,“陈介祺这一方法……无疑更加准确,相应部位比例也更趋合理。”[13]从这些评断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陈介祺是在精细研究和大量实践后发明了“以图取形”的“图形拓”。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评断:如果说僧达受的器形拓是全形拓的滥觞(当然也是他那个时代的绝技),陈介祺时代的图形拓则是在僧达受之后的质的飞跃,大大推进了拓技的发展。诚然,和前人相比较而言,陈介祺的图形拓在取形上更为准确,用墨技巧上更加灵活。贾文忠专家亦曾对此进行肯定并专门介绍了陈介祺在这方面的特色,特别强调其所绘图稿的准确和用墨的浓淡适宜。
可以这样说,陈介祺“以图取形”的图形拓才使得全形拓的称谓名至实归。尉笑也有这样的评断:“清陈介祺对全形拓的技术进行了完善,并且著有《传古别录》专门介绍传拓技法。”[14]可以说,他从“术”的研究入手,精心研究“法”的运用,直至对“道”的驾驭,也就是沿着技法——艺理——精神的思路完成了对全形拓拓技的提升。
当然,图形拓仍然有提升的余地。陈介祺曾函告金石好友吴云和时任陕甘学政的吴大澂,谈及图形拓的“图甚不如法,未免怅歉”的遗憾等。后来,在经过了鼎形上的处理,如,“以建尺校其形,以黍重库权校其容”和结构上的原拓做图等工作后才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
三、陈介祺“作图用洋照”的设想为全形拓的成熟奠基
陈介祺所在的时代,恰巧照相术传入中国,陈介祺看到采用西洋照相术获得的盂鼎照片(的代表)及其他风景照片后,提出拓片“作图用洋照”的联想和构思。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陈介祺的这一构想,才使得全形拓的拓技走向全面成熟,全形拓也最终走向鼎盛阶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日,陈介祺在致潘祖荫的书信中写道:“做图用洋照,而勿令其传印,收版自存之。花文以拓本樽节上版为合,可做二图,大者用原尺寸,小者则以照摹刻,字亦可照,小者为一缩本图与字也。洋照能得迎面枝,且可四面转侧照之,作兰、竹、菊、梅谱尤佳。”[15]作图用洋照,正是陈介祺发现了洋照取形的长处和僧达受器形拓“以灯取形”之不足,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后提出的改进设想。这为全形拓走向成熟奠定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在陈介祺以后的很长岁月里,人们依然沿用陈介祺图形拓的方法,使用云规、刻板、纸漏、放大尺及幻灯机放大工艺。得益于陈介祺等人的努力,全形拓到民国时期最终定型并得以较为广泛的使用。因为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图片拍摄技术和素描理论更为广泛地传入我国,放大尺、卡尺、幻灯机等设备逐渐普及。在全形拓的制作上,有了更为准确的测量工具(陈介祺的时代测量基本使用自建尺),特别是西方焦点透视法的运用,使取形上更加准确,合理。这才真正实现了陈介祺的“作图用洋照”的设想,全形拓才进入成熟和鼎盛阶段。如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青铜器学术著作中,才最终实现了以形拓图,配上铭文原拓,取代了博古图和临摹的铭文。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澂秋馆吉金图录》一书。
陈介祺之后,全形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希丁①、马子云②等。周希丁,人称“周拓”,他对陈介祺等人的拓技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深厚的传统功力为基础,他又学习了西学透视,他的全形拓佳作由于借用西学焦点透视法而使得从局部至整体的取形上有了较大进步,因此其所拓器物的立体感更强,各部分比例也更为合理。不足之处是缺乏形神方面的灵活性。陈邦怀评其拓形方法“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16]。他曾手拓故宫武英殿、宝蕴楼及陈宝琛(徵秋馆)、孙伯衡(雪园)、罗振玉(雪堂)等诸家所藏铜器,尤其是多以六吉绵连纸淡墨精拓的陈宝琛徵秋馆的青铜器全形,可谓极品。周拓的弟子有韩醒华、郝葆初、宋九印、萧寿田、马振德等。其中小徒弟傅大卣善传师法,也是传拓拓彝器全形的高手。马子云1950年传拓的“虢季子白盘”采用了依摄影放大绘图然于铜器之上传拓的方法,构图透视比例关系几乎达到了摄影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以摄影为基础的西方复制技术的传入和应用,传统的传拓业衰落了。尤其是随着照相技术的普遍应用,全形拓原有的保存器形的功能已经大为减弱,全形拓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但从技艺上说,这仍是一门不可丢失的学问。庆幸的是仍有大家坚持传承这一技艺,如故宫博物院的纪农章先生(马子云先生弟子),他所传拓的西周才兴父鼎之全形原拓本(故宫博物院藏)是吸收西方绘画技法之后的一大创新。马子云先生的又一弟子,甘肃博物馆的周佩珠女士,也在传承全形拓技法方面颇有建树,其《传拓技艺概说》颇有影响力。
正如王屹峰所言,就技术而言,由于这时加入了西方的摄影、绘画等因素,全形拓技法越来越成熟,或者说更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但从艺术层面看,自陈介祺以来的作品也已与古拙韵味渐行渐远。这也的确是不争的事实。[17]的确,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在欣赏到更加逼真的器物的全形之时,也不得不唏嘘其古韵和神韵递减的遗憾。
[1]马子云.金石传拓技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18.
[2][11][12](清)陈介祺.簠斋鉴古与传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5,14-15,74.
[3][4][10][17]王屹峰.古砖花供:全形拓艺术及其与六舟之关联[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3).
[5]陈振濂.“全形拓”道古[N].杭州日报,2015—07—02(B07).
[6][16]桑椹.全形拓之传承与流变[J].紫禁城,2006,(5).
[7]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131.
[8](清)鲍昌熙.《金石屑》[C]//石刻石料新编:第二辑第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4612.
[9]童衍方.别开生面全形拓[N].新民晚报,2014—11—15(B12).
[13]陆明君.陈介祺与金石传拓[J].中国书法,2015,(3).
[14]尉笑.全形拓研究——以《剔灯图》为例[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2.
[15]郑尔康.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0-31.
CHEN Jie-qi and Stereo Rubbing
WANG Jun-fang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Stereo Rubbing was not mature overnight.It experienced the beginning period,developing period and peak period.In the developing period,"Taking Shape with Picture"and"Paper Rubbing"of CHEN Jie-q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and formed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beginning period and the peak period.This paper is toseek CHENJie-qi's contributions toStereoRubbingin the process ofits development.
stereorubbing;CHENJie-qi;configuration rubbing;graph rubbing
G264
A
1671-4288(2017)01-0001-04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6-09-12
王俊芳(1972-),女,山东临朐人,历史学博士,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