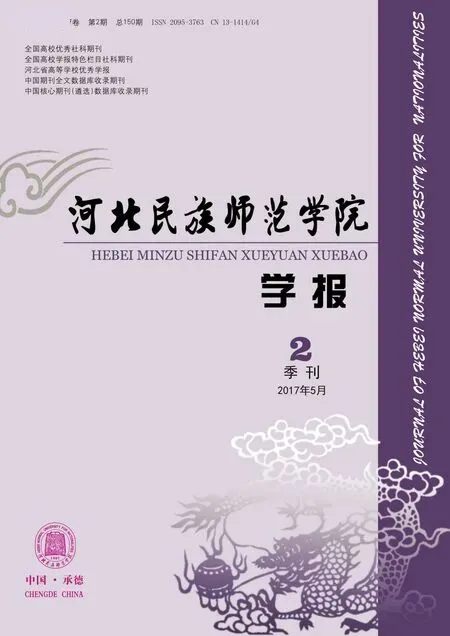文学的“形象”“语象”与“图像”
——评《形象诗学原理》
2017-03-08赵敬鹏
赵敬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文学的“形象”“语象”与“图像”
——评《形象诗学原理》
赵敬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形象思维”当属中国文艺理论热切关注的理论话题,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图像时代”的今天,《形象诗学原理》一书也就有了重新被研究的必要。西方文论的历史表明,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就是建立在对“形象思维”发难的基础上,直至后来的英美新批评,都很少论及“形象”。究其原因,所谓文学“形象”就是“音响形象”,即“语象”。由于当前愈加复杂的“文学图像化”现象,实则是语象的外化和实体化,所以,不同文体的语象容量,也就有可能产生类型各异的图像。
《形象诗学原理》;形象思维;语象;图像
如果不厌其烦地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论争史”,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学者纵然是不断变换热议的话题,但总会与西方之间存在某种“时间差”。“形象思维”或者“形象诗学”,就属于这样的理论话题。尽管“形象思维”不是现代欧美学界的常见术语,并遭到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批判与扬弃,然而,这没有影响中国“形象思维年”(1978年)的出现,更没有影响我们将“形象”理解为文学的本质,以及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标准。就此而言,《形象诗学原理》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图像时代”的语境中反思“形象思维”的诸多问题。
作者佩列韦尔泽夫(1882-1968),是一位与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同时代的文艺理论家。《形象诗学原理》属于作者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于1982年首次在前苏联出版。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形象的创作才是艺术的创作”,而艺术创作即“性格的刻画、性格的表达”,“无论刻画的对象是看得见的,或听得见的,还是既看得见又听得见的,其结果永远都是形象”。[1]50-51然而,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文学形象,只是坚定地认为诗学的研究对象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及其形象性”,而是“语言形象、形象的语言成分的特质”,因为“这些语言成分构成了由形象所体现的人类性格的统一体所决定的多样性内在统一体”。[1]41这种语焉不详,实际上并不是佩列韦尔泽夫一个人的问题,启发他研究“形象诗学”的别林斯基与什克洛夫斯基同样如此。
中国社科院曾在1979年编辑出版过一部《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编者在序言里谈到“形象思维”这一术语在欧美学界的处境:“英国现代作家杰克·林赛用了“形象思维”(imaged thought)这个名词,马上声明那是俄国文评里的术语;这也表示它在西欧至今还是一个陌生的名称。”[2]4而这里所谓的“俄国文评”,主要就是指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形象思维论”。
别林斯基前后写作了多篇论文,试图在文学艺术与科学(主要指哲学)的比较视野中论述形象思维。《智慧的痛苦》(1839年)一文首次指出哲学是通过“辩证法的发展形式”来表现观念,而文学则是以“形象的形式”直接体现。[2]57-58别林斯基的后续论文也一直延续对比文学艺术与哲学的思路,说明他关于这一问题有过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例如完整论述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艺术的观念》(1841年),《杰尔查文作品集》的第一篇论文(1843年),《普希金作品集》的第五篇论文(1844年),以及《俄国文学史试论》(1845年)皆是如此,甚至明确指出应该将诗歌与哲学“对立起来”。别林斯基之所以这般煞费苦心,旨在凸显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区别于哲学的特征和优长,这集中体现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1848年)一文。别林斯基认为,虽然哲学家与诗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但哲学是以“三段论法说话”,文学却是以“形象和图画说话”。换言之,哲学与文学“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然而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却大为不同——哲学“被少数人倾听和了解”,文学却“被所有的人倾听和了解”;[2]79-80前者“对于不明奥秘的人说来”是僵死的、无用的,但后者“对最粗野不文的人也会发生影响”。[2]74-75
显而易见的是,文学不可能存在视觉和“图画”,别林斯基所谓文学用“图画说话”,指的就是文学形象。事实上,无论是什克洛夫斯基向别林斯基的发难,还是佩列韦尔泽夫对什氏与别氏的折衷,他们都没有跳出“形象”的圈子,也都没有解释清楚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我们知道,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正是通过扬弃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而兴起的,但什氏在论述文学目的和效果方面,并没有彻底作到对后者的批判。例如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年)一文,就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3]22文学形象的核心不是“使其意义易于为我们理解”,而是“制造一种对事物的特殊感受”,即“产生‘视觉’,而非‘认知’”。[3]8-16
实际上,早在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中,什克洛夫斯基就已经与波捷波尼亚进行了“对话”。甚至可以说,这篇论文所隐含的“陌生化”理论雏形,就是建立在批判波捷波尼亚“对诗的语言与一般语言之不加区分”的基础之上。①然而,除了方珊先生《形式主义文论》一书的《前言:俄国形式主义一瞥》部分对波捷波尼亚作了一定的介绍之外,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此人及其启发“陌生化”的《文学理论讲义》(Из лекций по теори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Басня Пословица Поговорка,1894)与《文学理论札记》(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теори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1905)并不熟悉。即便是在国内的语言学界,波捷波尼亚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仅见于范丽君的《Потебня的词汇语义理论》(《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4期),以及《俄罗斯语言学通史》(郅友昌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尽管什氏一再否定“形象思维”之不是,以凸显其“陌生化”之确是,但并没有击中后者的要害,因为他所谓的“视觉”“可观可见”与别林斯基的“形象”别无二致,而且都止步于“语象”本身。[4]当然,“语象”作为表征语言与形象关系的重要术语,直到后来的英美新批评中才出现。
由于“形象”一词的含义过于混乱和容易混淆,“新批评的第一个语言分析家燕卜逊,就坚持抵制这个词。”[5]在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中,瑞恰慈曾解释道,“形象乃是感觉的残余,而且我们对它的智力和情感反应主要取决于它因此而代表着一个感觉,其次才是它和一个感觉的感官相似之处。”这种作为“感觉残余”的“视觉形象”,实际上是“心灵的眼睛中出现的画面”。然而,由于不同的读者所体验到的“将不是一幅共同的画面”,所以“设若诗篇的价值来源于它所唤起的视觉形象的画面的价值,批评恐怕就未免陷于绝境”。这就说明,文学的形象(即瑞恰慈所说的“视觉”和“画面”)不同于物质的、可见的绘画作品,如是所言,那些一直强调文学形象重要性的批评家,“像评判一幅画那样去评判形象将是荒唐的”。[6]112-115
及至《新批评》一书,兰色姆对瑞恰慈的上述观点给予了回应。前者指出莫里斯符号学的漏洞:虽然莫里斯“毫不怀疑任何一种诗歌都要使用图像符号”,但是,“诗歌如何可以通过文字编织的话语像一幅画一样很容易地将图像呈现给读者?”这当属莫里斯忽略的逻辑链条。兰色姆进而给出结论,所谓诗歌的“图像”,实际上是语言“在大脑中唤起的心理意象”。[7]192-196与兰色姆的这一观点类似,英美新批评的另一位主将维姆萨特,在1954年首次明确以“语象”(verbal icon)一词指称语言的“形象”,他将“语象”解释为呈现在头脑中“清晰的图画”(bright picture)。[8]如果我们沿着现代语言学的脉络一路爬梳,还可以有新的发现:从索绪尔的“音响形象”(images acoustiques)到化用皮尔士符号学概念的“语象”,它们都是同一所指的理论术语。进而言之,文学的“形象”就是“语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别林斯基、什克洛夫斯基与佩列韦尔泽夫在论述文学“画面”“图像”时都要加上引号的缘故,因为“语象”并不像现实中的绘画那样可见。
厘清了文学“形象”与“语象”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纠结”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部《形象诗学原理》,其中有一种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佩列韦尔泽夫在著作的最后一章指出,文学形象可以根据以下三个因素进行分类:“形象的容量”“形象所刻画性格的广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形象组合的复杂程度”。[1]56如果我们坚持所谓“形象”即“语象”的话,那么,文体语象的容量也就有可能决定了与其相适的图像类型,例如文艺史中常见的“诗意图”大多是对诗词歌赋等篇幅相对短小文体的摹仿,而小说、曲本等文体更多地会延宕出插图这类叙事图像,再如电影、电视图像一般是改编自小说而非诗歌,等等。换言之,文体与图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逻辑勾连。但可以肯定的是,谈论这些图像时无需再加引号,因为它们都是文学语象的外化和客体化。而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探讨。
[1](俄)佩列韦尔泽夫著,宁琦等译.形象诗学原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俄)什克洛夫斯基著,刘宗次译.散文理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4]赵宪章.语图叙事的在场与不在场[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5]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6](英)瑞恰慈著,杨自伍译.文学批评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7](美)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赵敬鹏.“文学图像论”与中国“诗画关系”现代学术史[J].学术论坛,2016(4).
The “Image”, “Verbal Icon” and “Picture” of Literature——A Review ofImaged Thought Poetics
ZHAO Jing-p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Visualization” is a hot theoretical topic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which can even be considered as a core feature to differentiate the literature from non-literature. Thus, in this “Image 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restudy the book Imaged Thought Poetic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rise of Russian Formalism is based on its bash on the Visualization. After that, even the New Criticism seldom discussed about “Visualize”.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is that the so-called “visualize” in literature is in fact the“image acoustique”, that is, verbal images. Nowadays, th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phenomenon of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is actually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verbal images; therefore, the capacity of verbal images in different genres may create different kind of images.
Imaged Thought Poetics; visualization; verbal images; image
I01
A
2095-3763(2017)-0081-03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11
2017-04-10
赵敬鹏(1987- ),男,山东莘县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形式美学、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学成像及其语图符号学方法研究”(2016SJD75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