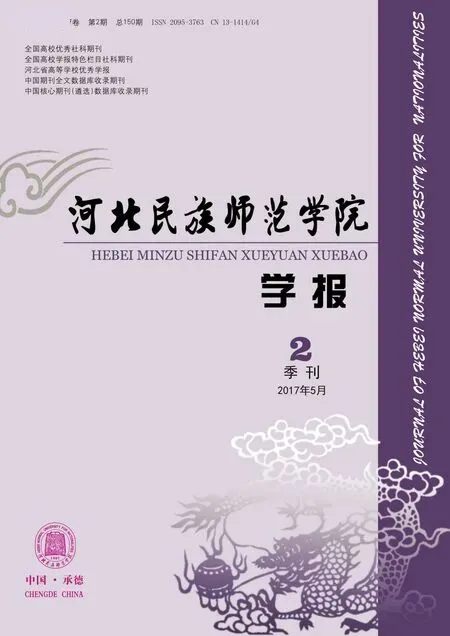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月亮神话的图文阐释
2017-06-05孙文起
孙文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文学与图像研究】
论中国古代月亮神话的图文阐释
孙文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主持人语: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可谓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从而决定了这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就其广度而言,无论是汉画对赋文的再现、唐宋以来蔚为大观的诗意画,还是“光芒万丈”的小说、曲本插图(郑振铎语),不同的文体及其图像作品建构了丰富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学与图像关系史”。就其深度而言,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界创刊的Word & Image,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纳入到符号学层面,从而开启了这一研究的新方向,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参照。本栏目所刊发的这四篇文章,从上述两个角度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并且全出自青年学者之手笔,令人振奋,“后生可畏吾衰矣”!(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
中国古代月亮神话源远流长,文字与图像是月亮神话的主要载体。两者的形式不同,对神话的表现也各有侧重。文字专注于具体的神话人物与神话故事,而图像注重神话形象的表达与神话体系的完整。图像与文字在对神话的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互证、互补以及繁衍、聚合的关系,由此带来月亮神话情节的增益与内涵的丰富。
月亮神话;文字;图像
一、图、文阐释对于神话研究的意义
图像对于研究中国神话,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着方法论意义。所谓的文献价值是指图像作为神话流传的载体,它以一种直观的形式构成了神话的物质存在,印证了相关的文字记载;而就方法论意义而言,图像艺术并非文字的附属,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为理解神话的衍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神话见诸文字者,多是经后人改造,而散存于杂史、说部文献之中,正如“黄帝四面”[1]“夔一足”[2]的阐解,已渗入圣王治道的思想,而与神话原貌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在传统话语背景下,神话作为“怪、力、乱、神”,仍不被正统学术所接受。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迎来了新思想、新方法的启迪,“神话”概念也随西学东渐而泊来。鲁迅、胡适、茅盾倡其先,顾颉刚、刘起釪、丁山、闻一多、孙作云继其后,神话一时跻身显学。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值得称道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在传统文字训诂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神话学普遍采用的词根学理论考证神话人物,如丁山西王母司天厉说[3]、孙作云“飞廉”[4]考等;其二是利用甲骨文、鼎铭等出土文献探索神话被历史化再造的现象,如顾颉刚的《古史辨》系列;其三是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比较中西神话,或从民族性及人文地理的角度把握中国神话的整体面貌,如茅盾的中国玄冥神话与北欧神话比较研究[5]。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神话研究肯定了神话的学术价值,在方法上基本以传统历史考据学为主,同时借鉴了近代西方人文科学新方法,奠定了中国神话学的基础。然而,由于学术发展的限制和相关材料(主要指出土文献及汉画像)晚出,图像依旧没有得到神话研究的充分重视。
新时期以来,神话研究再度兴起,学者开始注意神话的物质载体。借助于田野考古,摩崖石刻、岩画、出土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成为神话研究的实物资料,图像与文字资料相互参证,拓宽了神话研究的思路。近十年来,对于图像艺术形式的研究使得神话的美学阐释获得了更多的理论支撑,神话资料相对匮乏的不利局面有所改善。
相对于神话人物的历史考索与神话谱系的还原,神话表现的形式意义对于中国神话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史官文化的强势话语背景下,文字的实指作用会被放大,有关神话的文字文献也常被混同于“史载”,这种惯性思维使得文字的年代,成为衡量所指内容可靠性的标尺。当神话在“史载”中出现异文横生的局面时,现有文字的权威性便受到质疑,神话真相的获知便只有寄托于未知的更古老的“史载”文字的出现。
图像成为神话研究的对象,这在文献的层面意味着用于表现神话的文字记载有了实物的呼应,而在方法的层面,则引发出对神话表现形式的思考。现今所见神话事实上包含了神话母题以及神话母题的表现这两个部分。神话的母题根植于史前文化,它是民族心理结构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如对日、月崇拜、对风、雷的敬畏;神话母题的表现则可能是多样的,如日月之神,在甲骨卜辞中是东母、西母[6],在《楚辞》中成为羲和[7]。从形式的角度,图像与文字都是对于史前神话或是神话母题的摹写和再造,所不同的是文字记载试图通过意义的实指确立内容的权威,而图像所构建的神话体系则较为开放,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图像与文字在在神话阐释中形成互证、互补以及繁衍、聚合的关系,为中国神话内涵的衍生创造了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神话流传衍变的基本面貌。
二、月亮神话在图文阐释中的互证与互补
中国神话的传播媒介并不限于文字,刘魁立在《中国神话故事》前言中提到“(中国神话)通常以三种方式得以保存。第一种方式是保存在文献典籍之中。第二种方式是保存在民间的口头上,活在民众的记忆里。第三种是以实物的方式保存(岩画、画像石、壁画和地下出土的考古艺术文物)”[8]。在这三种传播方式中,口传状态下的中国神话已很难考察,可以暂且不论,除此之外,图像与文字就成了神话流传至今的主要载体。
进入的文字时代之后,图像并没有因文字的出现而退出神话的表现领域,许多实物文献,如帛画、画像石、画像砖的发掘,表明图像依旧是神话传播的重要媒介,一些文字文献对此也有所反映。
王逸《楚辞章句》对图像记载神话的事实更加言之凿凿:“《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7]《天问》所涉神话很多,对于这篇奇文的创作缘起,后人颇为关心。众所周知,上古时期的楚国文化弥漫着原始宗教的氤氲,在如此地域文化背景下,“山川神灵”自然可成为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壁画的主题,王逸所说恐非虚妄。
图像与文字的互证与互补的关系具体可从中国月亮神话中得到印证。相较其它文明古国神话中的月神——如古埃及月神孔斯、古希腊月神阿忒弥斯、古巴比伦月神南那以及古印度月神苏摩——中国上古时期与月亮相关的神话显得枝蔓庞杂,头绪不清,相关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以及汉代部分纬书;图像资料则主要见于画像石、画像砖、帛画、铜镜等出土实物。中国的月亮神话又由一批神话元素组成,如西王母、蟾蜍、玉兔、嫦娥、女娲等,就思想成分而言,其中既有原始神话思维的遗存,又混杂了巫术、仙道、谶纬等观念。面对如此庞杂的神话体系,图像与文字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图文互证,即文字文献对月亮神话的记载也能在图像中找到对应。
以上三幅汉代画像皆与月亮神话有关,在同时期文字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记载。其中,图1主要表现月中蟾蜍、玉兔,汉代《诗纬》云“月中有蟾蜍与玉兔何?月,阴也。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1];图2嫦娥奔月在秦汉许多文献均有记载,较为人所熟知的是《淮南子·览冥》:“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嫦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9];图3乃常羲捧月,《山海经》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10]

图像与文字的互证关系是研究神话重要依据,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为解读神话提供了二重证据。由于图像与文字的各自表现形式不同,两者在阐释神话故事时又呈现出来的互补的关系。这里不妨以嫦娥奔月神话的图文阐释为例作进一步阐说,嫦娥奔月是中国月亮神话的一个分支,由于其故事生动、形象鲜明,后世多以嫦娥为民族之月神。秦汉时期嫦娥奔月神话在求仙的文化语境下尤为活跃,除了图2汉画像石中嫦娥奔月之外,文字文献对其也不乏记载(不含前文所引《淮南子》):
王家台秦简(简称秦简)载《归藏》:“昔者,恒我窃毋死之□□奔月,而攴(枚) 占□□□”;“恒我曰:昔者,女娲卜作为缄□□”[11]。
《归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12]
《灵宪》:“嫦娥,羿妻也。盗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奔月。”[13]
在以上文字记载中,嫦娥奔月神话有三个重要情节:首先,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其次,嫦娥盗药而奔月;再次,嫦娥化为月之精华,即蟾蜍。
就表现形式而言,三条文字文献展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梗概。在这些文字记载的背后,神话的文化意义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归藏》称嫦娥奔月化为“月精”,所谓“月精”即月中之蟾蜍。蟾蜍寄托了初民的生殖崇拜,而后神仙家又将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演化为对长生的渴求。其次,材料中提到“仙药”蕴含着仙家祈求长生的愿望,秦汉时期方术颇盛,“仙药”之说实际上是古老神话主题的再创造。再次,嫦娥盗羿之仙药的情节在汉代又有新的衍变,《归藏》与《淮南子》皆未提及嫦娥与羿是夫妻关系,直到东汉的《灵宪》云“嫦娥,羿妻也”,奔月神话又被注入了夫妇伦常的观念。
反观图像对嫦娥奔月神话的表现则侧重故事的典型场景。如在图2中,图像抓住奔月主题,用简单的画面概括出故事的主干。尽管图像的形式在纵向的叙事表达中不占优势,但图像叙事善于抓住故事主要情节,概括故事整体,因此并不影响其内容的表达。图像对神话典型场景的凸显,反映了该神话在当时文化语境中已被广泛接受,图像与文字只是沿着不同的方向演绎共同的神话母题,文字在语义的层面展开神话的内涵叙述,图像则透过具体场景引发受众对于神话背后内涵的想象。
此外,图像对于神话人物的描绘上也是同时期文字文献难以企及的。据文字文献记载,月中的蟾蜍乃为嫦娥所化,并无过多的文字渲染。而画像在平面的空间里使用平铺情节的手法,将奔月与化为蟾蜍这两个在逻辑上处于一先一后的情节转化为平行并列的关系,这种阐释并没有引起视觉上的混乱,反而使得神话故事的表达更为凝练。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图像利用线条技巧生动地展现故事,因而更具有审美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已开始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嫦娥奔月的仪态美,如《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引郭璞《游仙诗》“翩翩寻灵娥,渺然上奔月”[14],婀娜之嫦娥颇合诗家之心,然究其渊源,则是图像首开嫦娥形象描写之先,将嫦娥神话引入文学的表现领域。
从上述图像与文字互证与互补的关系中,不难看出月亮神话的历史传承经历了图文互仿的过程。图像与文字的神话阐释无疑皆要基于一定的神话母题,简而言之就是“文图母题”,但二者在表现共同神话母题时并非平行的关系。例如在嫦娥奔月神话中,有关嫦娥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简《归藏》,因此可以断定嫦娥奔月的神话进入文字文献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末,随后《淮南子》《灵宪》等汉代文献也相继出现嫦娥的记载。嫦娥奔月的图像文献最早出现在南阳汉画像石,具体创作时间应在东汉。可见,文字文献对于这一神话的记载要早于图像文献至少三百年左右。在嫦娥奔月神话进入图像之后,其形象变得更富有审美价值,故在六朝以后的诗赋作品中,嫦娥神话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题材,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神话进入文学的有效途径。
嫦娥神话的图文关系史说明图像与文字是神话传播的载体,二者在神话阐释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神话的阐释体系。在这一阐释体系中,图像与文字在对共同神话母题的演绎中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构成相辅相成关系。
三、月亮神话在图文阐释中的繁衍与聚合
在神话的接受过程中,神话母题的再造承载着后人对神话的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学“土壤”与“武库”的经典论断也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神话研究都不同程度受到“古史辨”派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史观”的影响,这一理论揭示了中国神话在接受过程中繁衍与聚合的现象,由此引发后人对古史形成的再思考。然而,当疑古的风气渐趋平静后,神话的繁衍与聚合呈现给后人的主要已不是古史的虚妄与荒诞,而是神话传承过程的复杂与厚重。因此,图像与文字在神话阐释中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文献层面的互证与互补,两者为解读神话繁衍与聚合现象的带来新的思考角度。
图像与文字在神话传承中各有繁衍与聚合的现象,不过,由于形式的不同,图、文在神话传承中繁衍与聚合的作用各有侧重,以下将对二者分别论述。为了使研究对象更加具体,相关例证仍将以月亮神话系统为主,同时兼及其它神话。
首先是文字文献中神话的繁衍与聚合。依靠文字文献研究中国神话通常会在材料的理解上遇到困惑,那些零散不整的文字文献如果撮合起来,反而会使神话的本义变得愈加难以捉摸。例如后羿与羿便是一个难解的神话公案,《左传》《山海经》《天问》《淮南子》皆有“后羿”或“羿”的记载,但二者出入于史实与神话之间,历来对此聚讼不休。总其梗概,“后羿”的事迹较为质实,《左传》称其篡夺少康之位,又因荒淫而失国。不过,有关“羿”的文字记载则充满了神话色彩较,如“羿”射九日就是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另外,秦汉后的文献如《淮南子》《灵宪》又将“羿”与嫦娥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羿”成为月亮神话体系的一部分。文字文献对神话的演绎得力于不同文化语境对神话母题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在文献产生的先后顺序中又会体现出历时性特征。如在先秦文献《归藏》中,“羿”是一位射日的英雄:“昔者,羿善射,毙十日”[12],其与嫦娥奔月并没有联系,直至《淮南子》方才云嫦娥窃取了羿的仙药而奔月,东汉《灵宪》又称嫦娥为羿的妻子,神话由此平添了几分伦理色彩。对于月亮神话而言,“羿”的加入使得原有神话体系得到繁衍。
文字对神话的繁衍还体现在文字本身的多义性。德国神话学家麦科斯·缪勒的《比较神话学》认为神话是语言的疾病①刘魁立在《比较神话学》序言中对以麦科斯·缪勒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总结道:“这一学说(指比较神话学对神话的特性的认识便被归纳为语言疾病说。”参见(德)麦科斯·缪勒(著),金泽(译).比较神话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3。。口耳相传的不确定性,文献记载的疏漏、错误,以及古文字中普遍存在的“通假”“转借”现象都极易在神话流传的过程中给好事者留有以讹传讹的机会。例如嫦娥在《淮南子》中作“姮娥”,罗竹风的《汉语大词典》认为“姮”字不见于《说文》,故“姮”是“恒”的“俗字”[15]。嫦娥本应称作“恒娥”,后因避汉武帝刘恒之讳而改为嫦娥,后世文献中恒娥、嫦娥并提,当是源于一名。
文字文献在神话情节繁衍中起到的作用是针对神话内部而言,如果在肯定神话情节存在衍变的前提下,将“羿”的神话与嫦娥神话看作是两个神话系统,那么,上述文字记载的历时性变化,又可理解为文字对神话的衍变起到了聚合的作用。这种情况往往与古史神化有关,如儒家对于三皇五帝统序的建立以及道家对黄老渊源的追溯,大多是先对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而后再试图建立起服务于自家学说的神化了的历史。
文字在神话阐释中的繁衍与聚合的作用,与文字载体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文字文献对于神话的记载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对旧有神话进行新的阐释,如“黄帝四面”“夔三足”即是将儒家明君勤政的思想注入神话,这也造成了神话记载的散乱、淆杂。其次,神话在不同性质的文字文献中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例如“常羲”“常仪”同源于月神母题,“常羲”载于《山海经》,常仪载于《吕氏春秋》。《山海经》中的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实际上是对一年月有十二次盈亏的神话解释,而《吕氏春秋》所称常仪占月,则将常仪视为“月官”。众所周知,《山海经》乃巫筮之书,常羲浴月近于神话,《吕氏春秋》虽被归为杂家,但思想倾向于法家,因此常仪占月意在表达职官建构,而神话色彩渐少。
相对于文字记载,图像对神话的聚合与繁衍的作用主要源于图像的表现形式对不同神话更具兼容性。以马王堆帛画为例:

图4 马王堆帛画 汉代丝质帛画 上宽92厘米 下宽47.7厘米 全长20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马王堆帛画从结构上可分为三大板块,《西汉帛画》对该图说明如下:“最上从日月到天阔,是表示天上的境界;中部从华盖式的屋顶以下,包括着准备宴饮的场面,是墓主肖象及其生活环境;再下便是想象中的地下景物”[16]。其中,处于上部的神话事物有:烛龙、月中蟾蜍、日中金乌、应龙;中部涉及羽人、虬及鸱鸮;底部则是鲧、赤蛇等。对于这些神话的考辨,已有成果专门论述,本文在此不赘。需要指出的是,帛画中的神话元素分别属于不同的神话体系,图像对于神话元素的组合显然是不随意的,从上中下三层世界,到左右对称,帛画的构图透露出汉代人对神话系统的理解。这种系统的神话世界观并非一时形成,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衍变凝合过程,由此也可以推知神话的图像表达有着较长的创作实践积累。
相较文字记载,图像对神话体系的聚合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首先,图像对不同神话事物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是相对文字记载而言的。神话在文字文献中多非独立存在,而是要依存于上下文语境,即便是神话信息量十分丰富的《天问》也有其文本固有的创作思路,但这种创作思路多非因神话而设计,因此,文字记载中的神话受语义逻辑的限制。相对而言,图像中的神话并不依托文本而存在,因而更能体现神话本身的逻辑关系。
其次,图像对于神话的表达往往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如帛画中所涉及的神话内容十分丰富。这些神话在文字文献中的记载较为零散,因此,图像中每个单一的神话元素都蕴含了较大的信息量。例如东汉王逸《鲁灵光殿赋》描绘鲁光殿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17]可见壁画中的神话事物极其丰富,而且惟妙惟肖,十分生动。
再次,图像艺术的形象优势特别适合神话的表现,神话事物的产生离不开想象,在文史哲尚未各自独立的上古时期,文字对于神话的表现多侧重于义理,因而就表现效果而言,文字记载中的神话并未开始有意识的艺术创作。而图像除了要讲求神话事物的形象外,还要兼顾构图的和谐,这是图像艺术的自觉追求,因此,日月左右对称,天界、人界、冥界井然有序,不同神话元素所构成的整体毫无割裂感,这种严整的美感效应无疑使得汉代人的神话世界观得到更为有效的表达。
除了聚合作用,图像对神话同样具有繁衍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图像能够在平面的世界里将关联性不强的神话组合在一起,进而生发出新的意义。例如,月中蟾蜍、日中金乌以及人首蛇身的烛龙分别源于不同的神话母题,在图像中,烛龙居中,而月中蟾蜍、日中金乌分居左右,如此组合一方面基于构图的对称与和谐,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烛龙的神格地位。
月中蟾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天问》,烛龙、日中金乌的神话则见于《山海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10](《海外北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10](《山海经·大荒东经》)。据文字记载,三者并无神格的高下,然而在图像中,烛龙的地位有了提升。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据《述异记》《五运历年记》认为烛龙神“当即是原始的开辟神”。《述异记》《五运历年记》皆是东汉以后的文献,说明烛龙的神格在汉代有所提升,而图像则以有效的形式表达出这种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帛画底部的地下场景,《西汉帛画》联系《楚辞·天问》“鹤龟曳衔,鲧何听焉”,认为图像中手托大地的大力士是鲧。传统史家将鲧作为历史实有人物,《尚书·洪范》称“鲧则殛死”,《史记》也有鲧治水不成而被杀的记载。然而《山海经》称“鲧窃帝之息壤以陋洪水,不待帝命”[10],息壤即生长不息的土壤,因此《山海经》中的鲧则更近于神话。从文字文献的角度,鲧与金乌、烛龙并没有实际联系,然而,在帛画图像中,这些关联不大的神话事物聚合在一起,便勾画出汉代人对世界的想象。图像中的神话事物相互联系,组成新的寓意符号系统,并以此来诠释神性的世界,寄托世俗愿望。
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到“物体美源于杂多部分的和谐效果,而这些部分是可以一眼就看遍的。所以物体美要求这些部分同时并列;各部分并列的事物既然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所以绘画,而且只有绘画,才能模仿物体美”,“诗人既然只能把物体美的各因素先后承续地展出,所以他就完全不去为美而描写物体美。”[18]在莱辛看来,如果将要表达的事物看作部分,那么,属于图像艺术的绘画就是部分的和谐组合,这是文字艺术所不能有的效果,同样,文字在意旨上对神话的开拓也是图像所不具备的。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层累造成中国史观”实质上就是神话的繁衍与聚合在图文传承中的反映。
要之,中国古代月亮神话的传播存在文字与图像两种途径,文字记载中的神话由于受其所在文献性质的影响而呈现出情节衍变的多向性,从而为神话的再创造提供了条件。图像倾向于将离散的神话枝节重新整合一起,构成完整的体系。当文字与图像成为神话传播的方式,两者所寄寓的不仅是神话本身,而是神话背后的历史话语背景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情感。
[1]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7、22.
[2]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443.
[3]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书店,2011:69.
[4]孙作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455
[5]玄珠.北欧神话ABC[M].上海:上海书店,1990:32.
[6]罗振玉.殷墟书契[M].罗雪堂先生全集.第七编,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76:29.
[7]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16.
[8]刘魁立,马昌仪.神话新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2.
[9]何宁.淮南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501.
[10]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04.
[11]刘德银.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J].文物,1995(1):37.
[1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97.
[13]马骕.绎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145.
[14]虞世南.北堂书钞[M].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684.
[15]罗竹风.汉语大词典[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367.
[16]文物出版社编辑部.西汉帛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2.
[17]李善.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15.
[18](德)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1.
[19]陈雅.图文视域下文人画图文表征与内在张力[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2).
The Interpretation of Image and Text of Ancient Chinese Moon Mythology
SUN Wen-qi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Text and image are the carriers of ancient Chinese moon myths, which have a long history. Text and image are different in form, and they focus on the expressions of different facets of myth. Text highlights thinking and images is good at fi gure; text focuses on speci fi c myth and fairy tale characters and images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and the system integrity of myth. In the process of myth interpretation,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of text and image is form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myth is enriched.
moon myth; images; text
I01
A
2095-3763(2017)-0068-07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09
2017-02-23
孙文起(1981-),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叙事传统视域下的先秦两汉故事研究”(2014SJB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