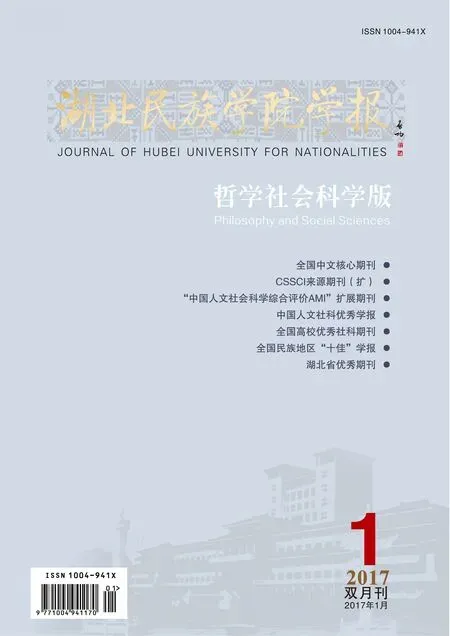热媒介·冷观察:《希望之乡》的景观表征
2017-03-07柯英
柯 英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热媒介·冷观察:《希望之乡》的景观表征
柯 英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苏珊·桑塔格在“赎罪日战争”尚未停火之际亲赴以色列,拍摄了纪录片《希望之乡》,借助于电影这个热媒介,对战争进行了一次冷观察。从电影地理的角度来看,该片不仅另辟蹊径地呈现了战争景观,无言地控诉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痛苦,而且还通过对地理景观和社会景观的细致刻画,将阿以冲突产生的后果以及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难以真正融合的困境展现出来。桑塔格刻意隐去自己的声音,任由影片自身去诉说,鼓励观众自己去思考和评判。
《希望之乡》; 电影地理; 战争景观; 地理景观; 社会景观
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尝试转向电影制作。不过她的影片不仅发行量小,而且在学院派的电影研究中遇冷,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它们“出自一名美国导演之手,然而第一部是讲瑞典语,起用瑞典演员,第二部是起用法国和瑞典演员,第三部是讲意大利语,是为意大利的电视台制作的,都不大可能会吸引放映商。至于纪录片,则几乎无市场可言。”[1]111其时的桑塔格,也许根本无意于迎合市场,她只是希望在电影界一展身手。1973年新年伊始,桑塔格就在日记里吐露心声,她一方面写道:“过去三年来我所经受的可怕的、令人麻木的自信感的失落:《死亡之匣》(Death Kit,1967)遭到的攻击、觉得自己是个政治上的跳梁小丑、《卡尔兄弟》(Brother Carl,1971) 一败涂地……”[2]351,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在日记里写下了关于接下来拍片计划的思考。1973年对于桑塔格来说,确实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一月份赶赴中国和越南,十月份前往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6日—10月26日),因为是在犹太人的假日赎罪日这一天发动的,因此得名。中交火最为激烈的戈兰高地和苏伊士拍摄纪录片《希望之乡》(Promised Lands)。由于拍摄初期交战双方尚未停火,危险不言而喻,而即便在停火之后,危险也仍然无处不在,桑塔格自己也承认“在整个拍摄阶段,战争正在进行,或随时爆发或步步逼近,(给我们的工作)设置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基调”[3]118。在西奈沙漠(Sinai Desert),摄制组的成员在雷区穿行,时刻面临着踩响埋在脚下的地雷的巨大风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桑塔格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望之乡》在芝加哥电影节上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被很多人认为是桑塔格最好的电影”[4]133,菲利普·洛佩特(Phillip Lopate)也表示,“她的电影,除了《希望之乡》之外,具有其小说一样的衍生的、费劲的、难以服众的特点”[5]9,虽然洛佩特评论的重点在于否定,但至少肯定了《希望之乡》的电影价值。
桑塔格的《希望之乡》“把在这个苦涩的纷争之地战争的现实、反复重演的历史以及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带回到美国”[6]116,其打动人心也是情理之中。时隔四十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在桑塔格的镜头里观看那一段历史的影像时,时空交错的距离感让我们有了更大的批评空间,电影研究中不断涌现出的理论也赋予了我们多维度的批评视角。本文拟以电影地理(film geography)为理论观照,对《希望之乡》予以分析,期望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部影片。电影地理是一个“逐步兴起的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把电影的空间性和日常生活的社会及文化地理连接在一起”[7]316,一般来说指的是“电影被赞助和制作的政治经济环境,电影产业展示出来的活动的差异程度,还有银幕上特定场地的再现,以及这些场景在设定人物、文化或情节的基调中所起的作用”[8]39。《希望之乡》既然是因战争而起,那么其最直接的表现对象自然也就是战争。
一、 战争景观:关于他人的痛苦
人们指望桑塔格在《希望之乡》里旗帜鲜明地表达一种立场,即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流血冲突中,她应该选择站在其中的一方。然而,自始至终,“遗憾的是,桑塔格小姐从未一览无余地表明她的态度。她最终的感情倾向有很多难以捉摸的暗示,但是几乎没有明确的指向。在《希望之乡》里我们完全看不到那个在其散文里态度鲜明、表现力强的桑塔格”[9]61。也有人认为,即便如此,桑塔格也还是有所偏向的,她“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去审视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而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让灰心失望的以色列人谈论这场战争,其结果就是让它变成了一部极度个人化的电影,展现的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情绪低落、无所适从和茫然无助,或者说变成了一篇散文,即便不曾承认以色列人是对的,但依然极具这样的倾向性”[4]133。这个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不过至少以色列人并未看出这部影片的倾向性,将它列为禁片,其情形与桑塔格的《河内之行》(“Trip to Hanoi”, 1968)如出一辙。桑塔格或许是从后者那里汲取了教训,不再对涉及意识形态和宗教这一类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妄加评论,她自己的解释是:“我力图在《希望之乡》中做到的是:呈现一种状况,而非一种行动”[3]118。不妨说,她是要借助电影这个“热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1964)中提出了“热媒介”(hot media)和“冷媒介”(cold media)的概念,电影被归入“热媒介”,因为其具有“高清晰度”(high definition),信息完备,观众参与的程度低。详见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Toronto, Lo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4, p.22.来进行一次冷观察。
当桑塔格带着摄制组奔赴以色列时,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给同事写信惊呼:“你简直不敢相信此事——坐稳了。苏珊此时正和一队人马在以色列西奈沙漠拍摄一部纪录片……!”[10]159桑塔格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确实令人敬佩,而她趁着硝烟未散,迫切地到达战场,镜头里捕捉的并不是血雨腥风的战斗场景,而是战争余威尚存时一幅幅已然静止的画面:暴尸荒野的参战士兵、千疮百孔的军车和坦克、散落一地的带着血迹的钢笔、笔记和钥匙。无论战争是否还会继续,死亡——这种无法挽回的结果已经成为事实,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已经变为荒凉土地上无处安葬的尸骸。桑塔格是众所周知的反战人士,她对战争的荒谬和残忍感到愤怒和悲伤,对战争的呈现方式也忧虑重重,指出“如今,战争也是客厅景观和声响。关于别处发生的事情的资讯,即所谓的‘新闻’,以报道冲突和暴力为主——‘有血才有看头’——被小报和二十四小时新闻摘要节目奉为金科玉律。随着每个不幸的画面映入眼帘,观众对冲突和暴力的反应是同情,或愤慨,或哗然,或认可。”[11]15她不甘于只是在“客厅”里观战,被血肉模糊的影像暂时打动,她要实地体验,亲眼见证,1993年她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惊心动魄的经历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亲临现场的勇气。
关于赎罪日战争,以色列突然受敌的“悲剧开场和其他情况已有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把这场战争界定为以色列的民族创伤”[12]3,而对于战争的全貌,“许多研究者、新闻记者和政治家说法不一,观点不一”[12]3。桑塔格应该深知以一己之力无法还原战争的真相,也无法轻率地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但她乐于走出“客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转化为图像和声音,作为一个记录者,而非义愤填膺的选择立场者。似乎是为了做出呼应,她的影片里有两位观点相左的被采访对象,一位是作家尤拉姆·卡纽克(Yoram Kaniuk),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尤瓦尔·尼曼(Yuval Ne’eman)。卡纽克解释“以色列建国是对大屠杀的回应,是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的发展……然而犹太复国运动也否定阿拉伯人的权利”[10]159;尼曼则为以色列政府辩护,称在阿拉伯人眼里,以色列人是入侵者,暗示阿拉伯人想和纳粹一样,要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所以要“实实在在地想出一种‘终极解决方案’”[13]58。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影片里交织,形成了一种争辩性的对话,影评家斯坦利·考夫曼(Stanley Kauffmann)认为这是该片唯一的可取之处,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他在此之前“还从未听过一个以色列人谈论过此事”[14]18。桑塔格能够做到这一点,证明她为了更客观地让人们了解这一场战争确实做出了努力。不过由于受条件所限,影片中没有来自阿拉伯一方的声音,这也正是有人以此为证据,说明桑塔格实质上是偏袒以色列的另一个理由,导致“与她许多的新左派同仁极为亲阿拉伯的情绪相左”[15]23。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桑塔格针对的是战争本身。2003年3月30日,在一个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桑塔格表示:
作为一个饱受创伤和恐惧的国家,以色列正在走出其动荡不安的历史中最大的危机,这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强在1967年的以阿战争中赢得的边界的定居点的政策实现的。随后以色列的一任任政府都决定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加以控制,从而否定了其巴勒斯坦邻居也拥有自己的国家的权利,这个决定是一大灾难——道德上、人性上和政治上——对双方人民来说都是。[16]xiii
不难看出,桑塔格力争做到就事论事,这个发言后来成了《拒服兵役者:以色列士兵的良心》(Refusenik! Israel’s Soldiers of Conscience,2004)一书的前言,以声援那些拒绝到占领区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人。*根据该书的说法,2003年夏天,有500多名接到服役通知的以色列人拒绝了服役,还有600多名同样已到服兵役年龄的以色列人正式宣布即便接到了通知也不会服兵役。详见Peretz Kidron compiled and edited,Refusenik! Israel’s Soldiers of Conscience,p.2.
无论参战的士兵是战死疆场还是九死一生,战争带来的都是难以抚平的伤痛。影片中既有痛失亲人的阵亡士兵家属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或默默流泪的画面,也有遭受弹震症(shell shock)之苦的士兵战场归来后接受治疗的场景,尤其是后者,桑塔格给了更多的镜头和时间,而考夫曼对《希望之乡》最激烈的批评也正是针对此处,斥责桑塔格如此大费周章“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窥视癖,与以色列的情形毫无关联。那间病房也可以在肯萨斯州或朝鲜半岛”[14]18。这个说法有失公允。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因为亲历过战友牺牲,亲眼看到各种血肉横飞的惨象而精神失常,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悲剧,然而他从战场回来后被施加的治疗方法却是模拟导致他精神失常的动作和声音,迫使他去面对和接受不堪回首的经历,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悲剧性。桑塔格用冷冰冰的医院取代血淋淋的战场,把这名士兵的遭遇展现出来,突出的正是战争的残酷无情和持久的伤害,也符合桑塔格一贯的反战立场,与所谓的窥视癖相去甚远。考夫曼认为病房没有代表性,不能反映以色列的问题,但这恰恰是桑塔格想要表达的,因为战争的阴影远非仅仅笼罩在以色列的上空,世界各地不安定的局面屡屡出现,事发之地人民遭受的苦难也远未结束。赎罪日战争背后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和博弈,正如在战争的第二年,英国《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的记者团队在合作而成的《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中东一个定居点的强制建立……看起来取决于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意志和努力。从短期来看,那也许是惟一的道路。可是对于未来来说,只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甘于接受作为一场归根到底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争斗中的傀儡角色,那么很难相信在中东会出现长久的和平。”[17]492-493时至今日,在美国的干涉和介入之下,中东的严峻局势被他们不幸言中,和平依然可望而不可即。作为“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桑塔格在彼时彼地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本身就是表明了一种极为明确的立场:“战争即地狱”[11]140。
二、地理景观:“希望”何在?
《纽约时报》的一篇影评与考夫曼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认为“由于这部电影枯燥无味,组织无序,使得战争看上去不真实……也许它应该是本书而不是部电影”[18]44。对于这种“不真实”,桑塔格以“9.11”事件为例所说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回答:“一场正被经历的灾难,反而往往怪异地变得仿佛是被表现出来的……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就近观看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11]18。现实变得像电影,而电影里展现出来的现实似乎是一种双重的失真。如果连亲历者都觉得虚幻,那么再现者再怎么力图还原,观影者也难以完全认同被重新建构出来的灾难性场面。与战争景观相比,地理景观的呈现就有所不同了,尤其是纪录片的地理景观,其“取材的真实性决定了其所塑造的‘拟态地理景观’在一定意义上比以虚构见长的影视剧情片更加接近‘客观地理景观’”[19]50。如果说在《希望之乡》里,战争景观的选材因为有人物的参与和评说而不可避免地渲染了一定的主观色彩,那么该片的非虚构性至少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地理景观的客观性。
《希望之乡》不是轻松的风景纪录片或旅游宣传片,因此影片里的地理景观不可能只是真空般的自然地理,桑塔格所关切的人的问题使影片的地理景观依然与人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伊始,随着耶路撒冷城里的钟声响起,分别代表着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十字架、星月架和大卫星交替或同时出现,随后就是一大片不毛之地,镜头由远及近,逐渐聚焦到一个带着头巾的阿拉伯牧羊人身上。荒凉的山坡上遍布土块和砾石,只有零星的、枯黄的草,羊群似乎难以找到值得驻足的地方,因此极不安分地跑来跑去,牧羊人不得不到处跑动,以聚拢他的羊群,影片中有一个他回首的镜头,无奈而茫然。在这个场景里,没有一句说明或解释的话语,但羊群在这个环境里的骚动不安以及牧羊人手足无措的东奔西跑似乎传递出了这样的“画外之音”:于人于动物,这片土地意味着与环境艰难的斗争。
影片另一处用移动镜头扫视的地理景观,依然是坎坷不平、了无生机的荒漠景象。而在此之前,桑塔格做了如下的铺垫:在一所被炮火轰炸过的残破的、废弃的阿拉伯学校里,一名以色列军官坐在教室里,翻阅着散落在地上的文件和课本,对着一个话筒读出这些材料上的文字,其内容无非都是反犹太人、激发仇恨情绪的。就在这位军官平淡乏味的诵读声中,画面先是切换到教室之外,几具焦黑的尸体一一出现,分辨不清是哪一方的阵亡士兵,有的衣着全无,开膛破肚,仰面朝天,像是向苍天呼吁,有的穿戴依稀仍在,但肢体残缺,扭曲变形。紧接着这些士兵丧生之处的地貌地形渐次展开,影片开头的钟声再次响起,单调的地理景观与尸体和钟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免会想起海明威那部名作的标题:《丧钟为谁而鸣》。与第一处衬托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艰难地谋求生计的地理环境不同,此处地理景象的呈现是通过平静得近乎冷酷的电影语言婉转地表达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带来的毁灭和破坏。
《希望之乡》的英文名是“Promised Lands”,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圣经·旧约》里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所谓的“应许之地”,从广义来说,根据《圣经》的记载,是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依照上帝的旨意,于公元前1900年带领族人前往之处,称为迦南,位于约旦河以西,包括加利利海以南和死海以北地区。从狭义来说,它指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应许之地”这个被犹太人认为出自于上帝的许诺“不仅成为流散的犹太民族的奋斗目标,而且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动力,身处异乡的犹太人彼此之间轻轻的一句‘明年在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助推剂”[20]65。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桑塔格的镜头下,这块被许诺流淌着蜜和奶的土地流淌的却是汗水和鲜血。值得注意的是,桑塔格的片名使用了复数,这就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不对称性,警示人们不可简单地把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因为她想要表现的,尽管是以一个特定的场域为依托,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指向更广的范围。从电影地理的角度来看,“电影里的风景不仅仅只是景观,而且还是隐喻,因此能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21]181。《希望之乡》的拍摄是利用有限的时间和财力最大限度地将镜头拉远,将景观深化,关涉的不是以色列这一个国家的状况,而是在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状况。战争加剧了这片土地的贫瘠感和死亡的恐怖气息,或许观众会情不自禁地发问:“‘应许之地’应许了什么?‘希望之乡’的希望何在?”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哈维·西切曼(Harvey Sicherman)1976年在其著作中称,“赎罪日战争把以色列从一个重要的、半独立的美国同盟转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依赖性的美国客户。这个犹太国家以巨大的代价获得军事上的胜算,比自194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外界的一个国家,几乎隔绝于主流的国际政治格局。”[22]77以色列的建国固然有其人民故园情结和宗教力量的驱动,但也离不开国外势力,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支持。英国在管辖巴勒斯坦期间,将其一分为二,分别作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地,但随着双方矛盾的升级,和平遥遥无望,英国于是抽身而出,将这个问题交由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大会1947年通过决议,认可了犹太人的建国权,然而阿拉伯联盟回应的是对以色列平民区为期三天的猛烈轰炸,由此引发了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巴勒斯坦也的确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栖居之所,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的决议中将巴勒斯坦55%的土地划分给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自然不难理解。卡纽克所说的以色列建国也意味着对阿拉伯人权利的否定也有一定的道理,影片中还有一处地理景观就是在他的评论声中展开的,而与布满砂砾的戈壁、风化的大块岩石、黄沙堆积的山丘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段带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情的电台音乐,如泣如诉,似乎在咏叹这个地区历经的沧桑。其后的画面也用力颇深:在苍茫的天地之间,镜头越拉越远,直到出现一群羊,由于颜色与大地接近,与周围的环境几乎融为一体。此处的牧羊人与第一个出现的不同,完全是远景拍摄,他带领着羊群,不疾不徐地骑行在黄土地上,似乎在宣告,他的生活方式乃是世代相袭,他的存在亦是这片土地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三、社会景观:难以企及的和谐相处
桑塔格认为《希望之乡》是她拍的最私人的电影,她解释道:“这种私人性不是指我出现在电影里(我没有),或像在大多数纪录片里那样担任‘画外音’的叙述者(该片没有解说)。之所以说是私人的,是因为我同电影素材的关系——是为我所发现,而不是为我所策划——也因为那些素材同我的写作以及其他电影的主题神奇地不谋而合。”[3]118,84其言下之意是这部影片依然渗透着她的个人风格,严肃冷峻,就像有篇评论所说的那样“既不尖刻批判,也不曲意逢迎,在分析阿以关系方面沉思默想,画面生动”[23]76。当然,论及私人性,其实还有另一个方面:桑塔格的祖父母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外祖父母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结婚的对象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922-2006)也是犹太人。亲赴以色列,记录在这个犹太国家的见闻也许一直就是她的夙愿。有人认为她“对材料的剪辑强调了她之前探索的主题——瑞典片里的那种个人的、性爱上的意志斗争在这里变成了政治的斗争”[6]116。此前的两部瑞典片是对她的文艺思想的视觉化演绎,而这部纪录片由于拍摄对象的特殊性有着更宏大的叙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是促成该影片产生的原因,也是叙事的主要内容。
在她展示的战争景观和地理景观中,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阿以冲突是通过一些间接的电影元素被体现出来的。不过在社会景观的拍摄中,她的选择就有所不同了。影片在十七分零五秒到二十三分二十七秒之间第一次集中在以色列的市井生活上,街道上井然有序:男人们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步态沉稳;女人们或驻足聊天,或在阳台上悠闲地张望,或从晾衣绳上轻松自在地收取衣物;孩子们在玩耍,一个个肉嘟嘟的小脸,衣着干净整洁。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愉快地高声唱着儿歌,一片祥和之气,可是突然之间,一个老年阿拉伯人出现在镜头里,他裹着头巾,佝偻着身子背着一个袋子,与街上的犹太人匆匆擦肩而过,与此同时,作为背景的儿歌声变成了孩子的哭闹声,和谐似乎被瞬间打破。随后就是卡纽克关于阿以关系的评论,镜头切换到以色列的一个集市上,画面的选择和剪辑也有一定的对比性:首先是犹太人,镜头用了很多全景和中景,市场上货源充足,人们在挑选和购买各式蔬菜水果;接着画面里出现了阿拉伯人,基本都是近景和面部特写,除了一个阿拉伯人举起小杯子喝咖啡的动作外,其他人在做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无论是衣着还是表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区别很大,前者服装多样化,神情悠闲,而后者的装束则千篇一律,面容也都是饱经风霜的模样。他们看上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没有交流,更谈不上融合。
与卡纽克的声音交替出现的是尼曼的阐述。他用了两个历史典故来形象地比喻阿拉伯人和他自己对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不同看法。阿拉伯人认为这无异于又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打着幌子强行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但东征军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他们需要的是耐心和努力,也许以色列也会遭到同样的结局。不过尼曼则更愿意把以色列比作是曾遭受伊斯兰近八百年统治的西班牙,从阿拉伯世界脱离出来并且“永远也不会再为其所收回”。也就是在尼曼坚决的语气中以色列的青年男女士兵出现在电影里,他们人手一支步枪,在公路上、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与阿拉伯人形成一种监视(监管)与被监视(监管)的关系。影片里还有一个片段完整地记录了阿拉伯人在边界接受检查的情景。一辆巴士驶过持枪士兵把守的大桥,阿拉伯人鱼贯而下,集中到一个地方由以色列士兵逐一进行人身安全检查,拿到一张表格后再将携带的物品送到另一处检查。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通过位于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国之间的边境检查站进入到以色列打工,桑塔格镜头下的场景每天也仍在上演。
无论是定居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还是穿越加沙地带到以色列谋生的阿拉伯人,他们与以色列人相处的画面不是互不沟通就是枪械相对,在动荡不安的复杂局势之下,双方的和平共处的确难以企及。桑塔格一言不发,但又说出了很多,正如一位观众评论道:“鉴于其制作者的身份,《希望之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影片对语言的依赖程度是何其之低。虽然有几个人发言,对政治和历史语境予以了说明,但是桑塔格那熟悉的声音却是完全缺场的——没有字幕也没有画外音——抑或说,桑塔格的声音被极其成功地、完全地转化为一种电影语言。”[24]
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David Rieff, 1952-)在整理母亲的日记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希望之乡》拍摄过程的专门的笔记本,只是找到了一本笔记上的寥寥数语,散落于“流散”、“犹太人”等零散的词句之间的有一句相对而言比较有连贯性的话:“少数裔的两种迷思:革命的、世俗的、社会性的;正统的、宗教的、保守的。消费社会(为二者所排斥)”[2]366。这里的两种迷思对应的是卡纽克和尼曼的观点,而桑塔格认为二者都排斥的消费社会在影片中也作为社会景观有一段集中的展示。在繁华的以色列商业区,高楼林立,供应各种食品和用品的超级市场、贴着驻唱歌手广告的酒吧、五颜六色的电影海报、闪烁的霓虹灯、旅行社、租车行、服装店、冰淇淋店……画面一幅幅密集地出现,令人目不暇接。卡纽克忧心忡忡地表示这种消费主义来自于美国,以色列就像是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个翻版,物质生活丰裕,但是在繁荣的背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退出,看似民主的政府实则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受同一批人的控制。他担心这个消费社会没有根基,随时都有可能被夺走。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程度极高的以色列城市风貌并存的,是传统的阿拉伯人的生活:简陋的帐篷、在地上玩耍的儿童、身着黑袍的妇女、骑着骆驼的男子……其中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两个牧民在户外准备做饭,除了一个面盆和一个水壶外别无他物。一个人坐在地上娴熟地揉着面团,另一个人在一旁根据揉面的情况往面盆里加水,二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完成了工作。这种需求被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与城里应有尽有的供应情况是以色列社会景观两面性的另一个写照,人们确实是在“共处”,但要达到和平或者和谐,却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结语
有人评价桑塔格的电影尝试是“一个以最精简的方式产生最佳效果的艺术品的范例,证明了她是一位敢作敢为的批评家”[25]H16。至少就以色列之行来看,她实至名归。她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式地对时事发表评论,总是力图克服一切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实地考察,获取一手资料,为自己、也为有志于研究同一题材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于敏感的国际争端,她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把那个爱现身于作品中的自己挡在电影之外,任由拍摄的对象去自我言说,去传达信息。在对战争景观、地理景观和社会景观的逐一呈现中,阿以冲突造成的破坏和创伤客观而真实,无须掩饰或粉饰,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生活方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看上去都是难以融合的存在。影片的最后,一辆辆满载着以色列士兵的坦克驶向沙漠,枪炮声慢慢变成一个男子的哀哭声,镜头特写了一个年轻士兵的脸,他腼腆地露出了笑容,和同伴一起,驶向不可知的命运,留在他身后的是漫天的黄沙。桑塔格的冷观察,此刻在这样的镜头里也慢慢化为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奈。
[1] Kaplan, E. Ann. Sontag, Modernity, and Cinema: Women and an Aesthetics of Silence[C]//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 Barbara Ching and Jennifer A. Wagner-Lawlor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Sontag, Susan.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64-1980[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3] Sontag, Susan. Susan Sontag Tells How It Feels to Make a Movie[J]. Vogue, July 1974.
[4] Schreiber, Daniel. Susan Sontag: A Biography[M]. Trans. David Dollenmay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5] Lopate, Phillip. Notes on Sontag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Maunsell, Jerome Boyd. Susan Sontag [M].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14.
[7] Lukinbeal, Chris & Stefan Zimmermann. Film Geography: A New Subfield [J]. Erdkunde: Archive for Scientific Geography. Vol. 60, Issue 4, October-December, 2006.
[8] Adams, Paul C., Jim Craine & Jason Dittmer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edia Geography [M].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9] Sarris, Andrew. From Holocaust to Hegira [J]. Village Voice, July 18, 1974.
[10] Rollyson, Carl & Lisa Paddock. Susan Sontag:The Making of an Icon [M].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11]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2] Lebel, Udi & Eyal Lewin eds. The 1973 Yom Kippur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Israeli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13] Gilliatt, Penelope. Promises [J]. The New Yorker, July 15, 1974.
[14] Kauffmann, Stanley. Stanley Kauffmann on Films: Promised Lands [J]. The New Republic, June 29, 1974.
[15] Rollyson, Carl. Reading Susan Sonta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 [M].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16] Sontag, Susan. Foreword [M]// Refusenik! Israel’s Soldiers of Conscience. Peretz Kidron compiled and ed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2004.
[17] The Insight Team of the London Sunday Times. The Yom Kippur War [M].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4.
[18] Sayre, Nora. Screen: Sontag’s “Promised Lands” [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4:44.
[19] 杨晓军.纪录片中的媒介地理景观研究 [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1):50-56.
[20] 王亚宁.犹太民族与土地的特殊关系[J].世界民族,2006(6):64-67.
[21] Zimmermann, Stefan. Landscapes of Heimat in Post-war German Cinema[M]//The Geography of Cinema: A Cinematic World. Chris Lukinbeal & Stefan Zimmermann ed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2008.
[22] Sicherman, Harvey. The Yom Kippur War: End of Illusion?[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6.
[23] Chaiken, Michael. Promised Lands[J]. Film Comment, January-February, 2011.
[24] Dennis, Lim. A Second Look: Susan Sontag’s “Promised Lands’” [EB/OL].(2011-02-06)[2016-07-18]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6, 201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feb/06/entertainment/la-ca-second-look-20110206.
[25] Thomas, Kevin. Movie Review: “Cannibals” Ends Egg, Eye Series [N].Los Angeles Times,May 23,1973:H16.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6-12-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景观社会的思想者:苏珊·桑塔格视觉艺术文论研究”(项目编号:12CWW002)。
柯英(1976- ),女,安徽望江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英语文学及视觉艺术文论。
J975
A
1004-941(2017)01-01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