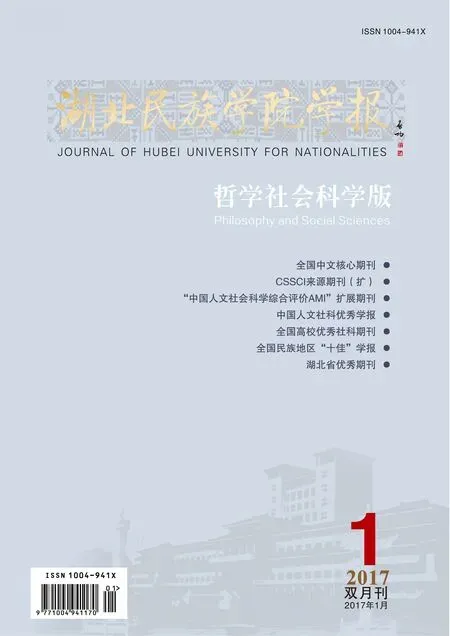土家族民俗事象的影像书写与文化迷思
——基于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的文本分析
2017-03-07罗翔宇
罗翔宇,彭 晨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土家族民俗事象的影像书写与文化迷思
——基于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的文本分析
罗翔宇,彭 晨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人类进入媒介社会,电影为民俗事象通过影像叙事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但是,民俗事象在电影中的呈现也必然会受到电影叙事框架的影响和改变。植根于土家族民俗文化语境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选取了“跳丧”“哭嫁”等土家族民俗事象作为影像叙事的文化符号,体现了民族地区电影的一种文化自觉,也为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影像文本。但从更大视阈来看,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与电影叙事的融合依然存在着基于不同价值逻辑的博弈与冲突。
少数民族;民俗事象;影像;《1980年代的爱情》
民俗(Folklore),即民间风俗,从本原的意义来看,意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正是这种文化,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确立的基本标志,并使得同一民族的成员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考察民俗文化,民俗事象无疑是一个重要视角,也是一个基本范式。所谓民俗事象,即民俗之外观,是以民风民俗形态呈现的行为文化符号,也是各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传承的大众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模式。不同的民俗文化有着不同的存续空间,《汉书·王吉传》中所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是对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描述。
人类进入媒介社会,大众传媒为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重要路径。我们生存在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没有人会否认大众媒介的发展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经验产生深远的影响。”[2]电影作为人类影像叙事的基本艺术形式,甫一问世,便本能地承担起人类民俗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重要使命。1922年,罗伯特·弗拉厄迪(Robert Flaherty)即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以影像真实呈现了爱斯基摩人的民俗事象,开创了人类学记录电影的先河。
现代的影像技术与人类传统甚至原始的民俗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民俗影视这一重要艺术类别,而民俗事象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民俗文化与电影影像之间的符号中介。近年,影视文本逐渐成为土家族民俗事象进行媒介化记录和大众化传播的基本渠道,为传统民俗文化通过现代视听语言在现代传播语境中实现活态传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媒介技术基础。
一、 民俗事象:电影叙事的文化符号
(一) 电影:民俗事象的影像传播路径
民俗是由群体成员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并共同遵循的习俗,承载着最广泛、最生动、最鲜活的民族文化。法国的山狄夫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向对民俗文化进行了分类。其实,不管属于哪种类别,民俗事象都能够给人带来强烈的美感和观赏性,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以土家族为例,吊脚楼、西兰卡普、撒尔嗬、摆手舞、女儿会、哭嫁等民俗事象,尽管种类繁多、性质各异,但都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审美需要,具有一种艺术审美的内在价值。但是,进入现代媒介社会之后,在大众文化强势入侵的总体背景下,土家族民俗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逐渐萎缩和式微,呈现出边缘化的濒危状态。这迫使我们思考,在人类进入到媒介化生存的当代,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应该如何通过现代传媒实现活态传承?
总体而言,民俗事象大致表现为两种基本符号形式:一种是语言符号,一种是视觉符号。而这两种符号分别从听觉和视觉赋予了民俗事像一种感性的形式,也为民俗事象通过电影视听语言进行传播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自电影诞生以来,民俗事象作为文化的一种表征,在我国各个时代的电影作品中都被广泛地应用。特别是对中国当代电影发展意义重大的第五代电影导演而言,民俗事象已经成为其电影作品重要的文化标签。他们“不再关注主流历史话语视野中的时代风云及其政治权力的更迭,转而将镜头聚焦于二千多年来这一大时空尺度下所积淀的民间仪式和民间风俗。”[3]无论是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抑或是田壮壮的《猎场札撒》《鼓书艺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民俗事象作为其电影叙事的客观社会环境的一种符号构成,并且力图使之承载更为丰厚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他们的电影也因此被称为“新民俗电影”。
那么,电影何以能够成为民俗事象重要的现代媒介载体?
从电影本身来看,电影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电影叙事实际上是以现实生活为摹本进行的,而民俗事象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是作为场景,还是作为情节,抑或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民俗事象都是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现实文化符号。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下,民俗文化的传播可以借助多种媒介技术进行,但是,作为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电影毫无疑问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从受众接受来看,电影能在特定时间内给观众带来一种超越现实时空,沉浸于民俗文化中的视听感受。“‘生活在别处’,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梦想,一个奢望,电影与民俗的结合正好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满足的可能。”[4]在电影中,民俗事象无论是作为民俗文化环境的能指符号,还是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可视化表征,都能潜移默化地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建构一个充满文化符号的拟态场景,给观众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和心理满足。
从传媒市场来看,近十年以来,电影产业处于快速发展和高度繁荣中,持续保持着高增长的态势。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艺术最大限度契合了读图时代的受众认知习惯,从而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也为民俗事象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途径。
随着媒介融合的逐步深化,电影传播的场景不仅仅存在于影院环境中,也通过网络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络进行了二次传播的多终端拓展。这无疑也为民俗事象的现代视听传播提供了更多、更便捷、更强大的路径选择。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民俗事象也因此而面临着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传播情境,民俗文化传播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媒介生态给其带来的挑战。
(二)复制与再造:民俗事象的影像书写方式
不可否认,在早已成为当下普遍现实的读图时代,视觉经验已经构成现代人类认知外部世界和理解文化传统的基本方式,图像也成了文化传播的基本模式。电影艺术与民俗事象的内在联系促进了二者的融合进程,并促使人们不断探索二者的最佳融合方式。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在《图像的生与死》中分析人类图像叙事的起源时曾指出:“图像的目的原在于拉近人和超自然的距离。”[5]那么,作为民俗的外在文化符号,民俗事象应该以何种方式进入电影叙事之中?换言之,在电影艺术规律和民俗文化价值的博弈之间,电影艺术应该如何呈现民俗事象?
本文认为,电影呈现民俗事象的基本形式在总体上可分为复制和再造两种。
所谓复制,即电影将民俗事象作为其故事情节或文化背景,不加修饰和改造地直接进行搬演。民俗事象中重要的一类——物质形态部分,在电影叙事中往往被直接引用,比如建筑、器具、服饰、饮食、生产等民俗事象,也有部分社会民俗和语言民俗在电影中被直接使用,比如民谣、方言、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等,往往被直接借用过来嵌入电影叙事之中。对电影而言,直接复制这些民俗事象能够有效地构建一个原生态的民俗环境,为故事情节营造一个植根真实民俗文化的现实情境。
所谓再造,即根据电影叙事的需要,或者为了迎合受众的审美需求,电影对民俗事象的内容或形式进行部分改造或重构后融入剧情的过程。比如,张艺谋在《红高粱》中表现的山东高密东北乡的“颠轿”习俗,其实就是基于莫言小说中的民俗线索进行的虚构创造。这种虚构创造的民俗同故事情节往往能够更加紧密地融合,也能形成更加流畅的电影叙事节奏。但是,由于民俗事象只是构成电影的文化要素之一,必须要受制于电影叙事的需要,因此民俗事象在电影中的呈现也必然会受到电影叙事框架的影响和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推手,电影对民俗事象的影像叙事也有陷入消费主义陷阱的风险。受资本市场逻辑的影响,或者出于某种特定文化心理,一些电影也往往把民俗作为吸引眼球和抬升票房的噱头,从而对民俗事象进行随意篡改甚至恶意捏造。这种基于娱乐化或妖魔化心态的影像表达,不仅不能推进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承,反而可能成为民俗文化被异化、文化价值被消解的罪魁。
二、 《1980年代的爱情》:土家族电影文本的民俗事象分析
2015年,由霍建起执导,上海大盈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天集团(甘肃)联合出品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正式公映。电影改编自恩施籍土家族作家野夫的同名小说,并以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州作为主要外景地取景拍摄。武陵山区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土家族集中聚居区,由于地理上的突出特征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沉积地带,同样也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 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 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6]作为取材于武陵山区并植根于土家族文化语境的电影文本,《1980年代的爱情》在叙事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融入众多土家族民俗事象。从某种意义来说,电影中呈现的民俗事象也为我们观察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媒介化文本。
(一)哭嫁:人类学意义的影像再现
哭嫁,作为一种婚俗,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曾广泛流行,我国许多民族也都保留着这种民俗。但是,“土家族的哭嫁歌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都具有代表性。”[7]在大多数文化里,嫁娶是人生大喜之事,哭是一个禁忌,但是在武陵地区土家族文化里,女儿出嫁却是以群体性歌哭作为一个基本仪式。这一独特文化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关注。关于哭嫁习俗的起源,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而言,哭嫁表现的是女性对男性霸权的抗争和对婚姻压迫的控诉。哭嫁歌的形式和时间随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据《利川市志》载:“‘哭嫁’时间一般3~7天,多则长达一月之久,每天傍晚开始,半夜方休, 哭时一般都有九个未婚少女陪伴, 俗称陪十姊妹。”[8]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一种产生并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少数民族民俗,“哭嫁”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渐渐淡化,面临着消逝的危险。
《1980年代的爱情》在电影的后半段展现了土家族“哭嫁”的典型场景。“高山下雨低山流,今夜配歌我开头。新打剪子新开口,剪出牡丹配绣球。哎呀,妈呀,青草绿草花。哎呀,妈呀,女儿要出嫁。哎呀,妈呀,养我这么大。哎呀,妈呀,舍不得离开家。”这段哭嫁歌唱词充分表现了即将出嫁的女儿对家乡和亲人的不舍。电影中的这个桥段可谓韵律优美,情真意切, 以歌代哭, 悲喜参半。哭嫁歌作为一个抒情的段落进入电影叙事之中,既可以作为男女主人公之间表达情感的桥段,更给电影带来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
从文化的层面来看,《1980年代的爱情》将“哭嫁”这一民俗事象借助影像技术复制到大众视野之中,其实是对土家族文化的一种电影化表达,是对土家族文化认识、描述和信息交流的一个影像化文本,从某种意义来说,电影由此具有了一定的影像人类学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原生态的土家族“哭嫁”时间持续时间较长,以对性别压迫的控诉为主题,其中既有固定仪式性的唱词和旋律,也有灵活变动的现场即兴发挥,但电影有着自身的叙事节奏和情节线索,不可能完整展现“哭嫁”繁杂漫长的过程。归根结底,民俗事象只能作为情节推进过程中的一个文化符号被片段性的呈现。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的爱情》中对“哭嫁”仅仅进行了开场部分的点缀性表现,并没有全面呈现其完整结构。这正体现了电影文本与民俗事象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难以回避的矛盾。
(二)跳丧:土家族生死观的影像呈现
如果说“哭嫁”体现的是一种对于权力和压迫的控诉,含有某种性别政治立场的话,那么,“跳丧”这种民俗事象则折射着土家族对于生死观的一种隐秘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弗雷泽曾指出:“在各种形式的自然宗教中,几乎没有一种形式像永生信仰与死者崇拜这样在人类的生活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9]
“跳丧”在土家语中称“跳撒叶儿嗬”。“汉语译名‘散忧祸’,其意为土家语‘散忧祛祸’。”[10]在传统的土家族“村落社会”里,“跳丧”已经成为体现土家族艺术、信仰和历史等深层文化内涵的重要民俗事象。在土家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死亡仅仅被看成肉体的消亡,对灵魂而言却寓意着新生。“土家人认为死亡实际上使人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快乐。”[11]可以说,“跳丧”集中体现了土家族人达观的生命意识。
雷吉斯·德布雷认为,图像源于丧葬——正是为了延续死者的“生命”才制作出雕像、画像等一系列的图像。将其珍爱但易朽的对象永远保存下来,这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的情感要求。《1980年代的爱情》在电影的尾声部分,通过男主人公关雨波参加女友成丽雯葬礼的桥段,很自然地嵌入了土家族“跳丧”这一民俗事象。电影从关雨波的叙事视角对“跳丧”进行了简约说明和精神提炼—— “跳丧,是我家乡的习俗。我一直觉得这种方式有种独特的美丽,人们用狂欢歌舞来让远去之人灵魂飞升,逃离疾苦。”——从这段跳脱出电影整体叙事节奏的旁白,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希冀借助电影文本传播土家族民俗文化的一种热忱。电影中以击鼓拉开序幕,乡民们头扎毛巾,循着特定的节奏和舞步,围着棺椁载歌载舞送别亡人。电影采用远景和特写交叉剪辑的手法,结合俯拍视角还原了体现独特文化模式和生命价值观的土家族丧葬民俗。这个段落在电影中是浓墨重彩的一幕,电影以丰富的视听语言再现了“跳丧”这一土家族民俗。这既是剧情合理发展的需要,也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视听效果,同时,还极大丰富了电影文本的文化意蕴。电影通过对这个土家族典型民俗场景的渲染和强化,使得电影文本负载起传播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功能,可以说,这背后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自觉。
从某种意义来说,《1980年代的爱情》可以被视为一部带有人类学基因的电影,或者说是一部用胶片书写的土家族民族志,通过一种旁观者的眼光记录着“他者”的生活,有效构建了武陵地区民俗文化景观,而电影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可视化艺术又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参与观察”的媒介渠道。
三、 少数民族民俗事象影像传播的文化迷思
电影艺术与民俗事象的融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电影创作的基本潮流,在这个潮流背后,“是世界性的原始主义文化思潮的滥觞和发展”。[12]不可否认,电影文本因为大量民俗事象的嵌入而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这既使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获得了一个重要推手,也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电影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视听合一的感受完全同构的物质技术手段,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与演化,使之成为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濒危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途径。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具有朴素的原生性,而电影艺术具有与生俱来的媒介性,加之电影产业还更需遵循大众文化的市场规则,因此,民俗与电影之间也存在着基于不同价值逻辑的博弈和冲突。
(一)刻板复制:民俗事象的在场与文化意义的缺席
在西方语境中,电影被界分为艺术电影和真实电影两大类别。真实电影即纪录片,艺术电影则是本文所讨论的虚构的剧情电影。在艺术电影中,由于剧情要在一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展开,就必然要呈现特定的民俗事象。但是,民俗事象作为民俗的外观,其实是习俗的外在形式符号。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的作用。”[13]电影表现的民俗事象能否真正体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涵,就成为考量民俗电影成败的关键。部分电影由于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理解不够深入,或在电影叙事中处理不当,对民俗事象的运用往往采用过于生硬的呈现方式,从而陷入机械的刻板复制,镜头中所展现的民俗事象成了一个缺乏文化意义的符号空壳。一种情形是作为物质民俗事象的场景、建筑、器物等,在一些电影中被以刻板的空镜头孤立地呈现,仅仅为电影情节的推进勾勒了一个空洞的外部环境,而无法与少数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建立有效关联。所以,民俗事象在电影镜头中的呈现恰恰反证了民俗文化意义的本质缺席。另一种情形是作为少数民族社会民俗事象的象征性、表演性的文化仪式,由于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在电影叙事中往往被浓墨重彩地强化渲染,但是,仪式作为一种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特定行为方式,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而言无疑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但对于此种文化语境之外的观众而言,则往往只具有作为审美对象的形式意义。由于被从其原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这种民俗仪式在电影中的存在,实际上成为了脱离民俗文化意义的空洞能指。
(二)虚构再造:民族心理的异化与文化消费的狂欢
在布迪厄看来,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电影构成了文化消费的重要领域。通过有选择地使用形象和声音,电影为人们建构了一种“现实”。但不可否认,无论建构何种现实和如何建构现实,电影终究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完成的也是艺术的表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进入电影叙事的民俗,已然不再是生活中自在天然的民俗,而是在个人意志的驱遣下,负有特殊的使命。”[14]娱乐至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文化表征,少数民族民俗事象在文化消费的整体语境中自然不能独善其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可以在电影的娱乐化叙事中被任意虚构的文化噱头。这正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当代面临的一个最大威胁——现代传媒以虚妄的民俗幻象替代了现实的民俗传统,以快餐式的大众文化取代了原生态的民俗艺术。比如,张艺谋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就虚构了山西地区本不存在的“点灯”“灭灯”“封灯”这样一套完整的民俗事象,以此来满足电影叙事的需要,从而构成一个对电影观众极具吸引力的性文化隐喻,随着电影的广泛传播和被消费,这一虚构民俗事象给大众带来了极大误导,可以说成了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媒介社会被娱乐和消费的典型文本。值得警惕的是,在追求视觉冲击或叙事效果的冲动中,电影往往会对民俗事象进行“必要的”虚构和导演。电影的这种基于票房考量的大众文化霸权不仅难以有效传承民俗文化,相反还可能导致本已弱势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媒介的集体误读中走向异化或者消亡。
(三)他者叙事:主体意识的消解与文化身份的虚化
在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所谓“文明”,其实“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15]这表明,“文明”一词实际上与西方的现代性自我认同相关。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里,“东方”被固化在原始、野蛮、不开化的刻板印象里,从而成为一个为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而存在的虚幻背景。这样的文化语境使得东方社会的民俗事象不可避免地沦为反证西方文化价值的空洞符号。而萨义德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自我东方化”的思维定式——由于失去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自信,而本能地将自己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而存在。其实,这种“他者叙事”的倾向在众多少数民族民俗电影中也屡见不鲜。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取悦主流文化或西方文化,一些电影主动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置于“他者”的尴尬地位,刻意展现甚至过分渲染一些民俗文化中的鄙陋。“以一种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成为西方视域中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16]就如电影《雪花秘扇》对“裹脚”这一摧残女性的民俗陋习不仅没有批判性反思,反而进行了细腻的展现和正面的刻画,甚至在叙事话语中对“裹脚”流露出一种偏好与欣赏的态度。这种隐含的文化立场在跨文化传播中极易造成现代受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和歪曲理解。归根结底,他者叙事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自我矮化,而其直接后果则是导致了对我国民俗文化的整体性伤害。
四、结语
人类进入媒介社会,民俗文化的存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的深刻影响。电影通过对少数民族民俗事象的影像叙事,为民族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但在大众文化的现实框架下,民俗事象的影像呈现也必然会受到电影叙事的影响和市场逻辑的左右,极易陷入刻板复制、虚构再造和他者叙事的迷途。电影呈现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体现了现代媒介传播、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文化自觉。但这种自觉需要建立在创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理解和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俗文化的媒介化传播和现代化传承提供真正符合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影像文本。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
[2] (美)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埃德温·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
[3] 许萍.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J].当代电影,2005(3):125.
[4] 何华湘.当民俗遇上电影:一种文化传播的视角[J].电影文学,2011(19):23.
[5] (法)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M].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
[6] 张正明.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M]//朱炳祥.土家族文化的发生学阐释.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
[7] 余霞.由文化事象深入到女性心理——关于土家族哭嫁歌研究的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3):32.
[8] 湖北省利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利川市志[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52.
[9] (英)弗雷泽.永生信仰与死灵崇拜[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56.
[10] 陈韵,陈宇京.土家族丧葬仪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调查资料解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1):1.
[11] 朱吉军.浅析湘西土家族丧葬歌谣中的生死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7):151.
[12] 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13]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上海:三联书店,1988:5.
[14] 何华湘.当民俗遇上电影:一种文化传播的视角[J].电影文学,2011(19):23.
[15]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1-62.
[16] 许萍.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J].当代电影,2005(3):125.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6-12-15
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09HB0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大众传媒与武陵山试验区原生态艺术的现代传播”成果(项目编号:2012D003)。
罗翔宇(1972- ),男,土家族,湖北建始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彭晨(1992- ),女,土家族,湖北鹤峰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G203.6
A
1004-941(2017)01-01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