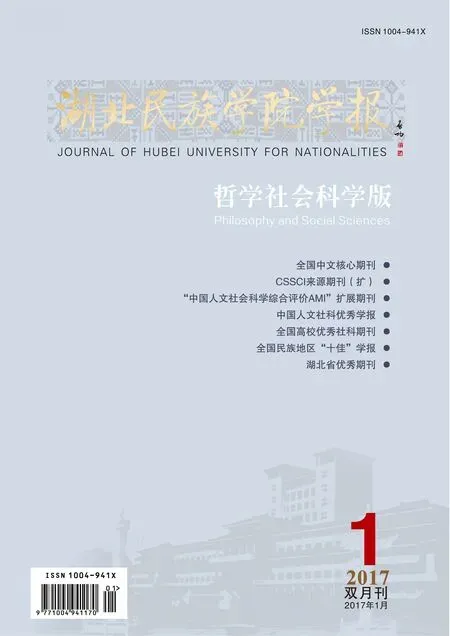论奥尔科特《小妇人》女性价值主张表达的路径实现
2017-03-07朱玉霜
朱玉霜
(江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论奥尔科特《小妇人》女性价值主张表达的路径实现
朱玉霜
(江汉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1868年,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发表了她的《小妇人》,这是一部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也被认为是初期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反映了在传统观念禁锢下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本文以作品的故事内容作为出发点,从成长教育、爱情婚姻、社会生活三个层面分析,认为小说中女性价值缺位呈现分别以父爱缺失、母爱凸显为设置;以抛弃财富、平等相待为设置;以男性弱化、女性张扬为设置。
《小妇人》;女性价值;表达;实现路径
发端于欧美的女性主义思潮,在其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里随着欧美社会生活的变革而不断推陈出新,辅以新义,形成了三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形成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其要义在于追求被制度性地排斥在权利系统之外的女性平等,开始要求女性作为人的、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受其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第一次妇女运动开始了,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即赋予其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同时赋予其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从而使女性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种现象也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当时的女性作家也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与探索,将女性主义追求平等的诉求延伸到更具普遍意义的领域——社会文化语境中去。[1]她们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改变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冲击和颠覆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小妇人》这部作品便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小说主要记叙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个普通家庭,在父亲常年参军在外,家庭基本只有母亲的特殊背景下,家中四个姐妹成长和成熟的生活历程。小说打破了当时社会关于女性角色定位的传统的和主流的意识,把四姐妹的角色赋予了独立自主的特性:四姐妹在作者的笔下勇于打破时代对于女性的局限性,在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断冲破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充分展现了女性不同于当时社会主流观念认同下的价值存在,迄今仍然带给广大读者强烈的共鸣和启发。作品故事的叙述过程,实际上也是作者关于女性应有价值观念的主张过程。[2]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故事情节的分析,可以探求出作者关于女性价值实现的主张,也可以勾勒出作品中女性价值表达的实现路径,从而充分体会到作者对于情节设置上的精心。
一、 教育成长层面的女性价值缺位呈现——以父爱缺失、母爱凸显为设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值夫权统治,人民群众的普遍观点是男性是家庭的主体和支柱,妻子只是丈夫的装饰及附属。为了打破这种传统的固有观念,作者在情节设置上直接选择了作为丈夫和父亲角色的马奇先生的缺位。作者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南北战争环境之下,但是其写作重点并不是突出战争的残酷,而是为马奇先生的缺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和借口,用马奇太太的原话来说就是,“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献给我心爱的祖国”。因此整篇小说除了第一章交代了马奇先生在服役,马奇先生一直都没有出现,直到第十五章才传来他生病的消息。即便是有马奇先生的正面描述,也着墨不多,而他在家的时间也很少,空闲的时候也是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沉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这种父权和夫权的缺位情节设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使得在四姐妹的教育成长中,女性价值实现的表达取得了如下效果。
(一) 作为女性价值最高表现的母爱得到凸显
作品中的马奇太太拥有女性可能拥有的一切高尚而可贵的品质。她的内心强大而又崇尚自由,在丈夫的缺席下,仅凭自己的力量为女儿们遮风避雨,撑起一片天,使她们得以拥有快乐自由的生活。同时,她还有着天生的好歌喉,在她的美妙歌声中,女儿们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因此在家庭里,母亲的重要程度远超父亲。这个情节突出了母亲的重要地位,也强调了母亲在孩子们成长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了对传统男权社会习俗的挑战。
(二)女性话语权力空间得以极大扩展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著名哲学家,他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话语即为权力,而权力亦存在于一切话语之中,掌握了话语权力,就可以主导话语。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剥夺了相关权利,那么想要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就必须要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把自己不同于男权的主张要表达出来,同时为了不被主流的话语声音所淹没,就必须掌握并强化话语权力。小说中父亲角色的缺席,使得整个家庭基本全部都是女性、没有其他男性的情况下,使得该家庭女性不会受到来自男权的强大干扰和阻力,从而轻而易举地、极大地扩充了女性话语权力的空间。而从整部小说来看,小说中的对话,绝大部分也都是女性之间的对话。通过女性话语权力的掌握,不给男性话语权力发挥的空间,在小说中实现了对当时社会男性主导话语权的既定规则的一种挑战和颠覆。
(三)女性经济地位独立得以实现
英国19世纪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散文《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论断,女人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此处的“屋子”理论,实则是一个具有强大隐喻意义的象征符码,暗示了女性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歧视或者说是不公正待遇。根据伍尔夫在文中所说,在经济上,由于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同时无钱亦无权接受教育,造成女性在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再加上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很多女性一辈子都只能在厨房和起居室里打转。因此,她呼吁女性必须争取“一间自己的屋子”,首先就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得到政治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旨在激励女性为自己的经济权益和社会地位而抗争。父亲和丈夫这个男性角色的远离,成了这个家庭的女性必须依靠自身努力去获得经济独立的客观前提。虽然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是由客观的情势造成的,但也为凸显女性的经济独立地位作了极好的铺垫,力求说明,没有男性的世界,女性也是可以生活的,而且会活得更好。在作品中,大女儿梅格始终是三个妹妹的榜样,其更是主动承担在四姐妹中的引导作用,主动找到一份在幼儿园做家庭教师的工作,对于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她也早有预感,却始终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成功。尽管在梅格的内心深处始终怀念和留恋着奢华的生活,却是一心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坚持培养自己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精神,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和目标。贝思是四个姐妹中性格最腼腆的一个,虽然一直没有出去工作,但是始终在自己的家庭中担任着缝缝补补的工作,凭借自己的微薄力量维持着整个家庭的平和,就像是一个默默奉献者,始终站在角落里,却始终为他人无私奉献着自己。乔则是四个姐妹中独立意识最强的一个,就因为看上了马奇婶婶的藏书室,就算马奇婶婶这个人非常让自己头痛,但是还是主动到她家做起了管家,并且还将这一过程认为是对自己的锻炼,非常乐于接受,认为这样的工作能够让自己更加独立。其实乔是认为自己能够有一份工作而拿到工资,就能够为整个家庭奉献自己的力量,也能帮助自己首先实现经济上的独立[4]。
二、爱情婚姻层面的女性价值破立呈现——以抛弃财富、平等相待为设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女性的爱情和婚姻主要由父母通过对男性财富地位等的考察来决定。因此小说在女性爱情婚姻的故事情节上采取了“以财富论英雄”的设置,不过是以财富少的男性作为最后的胜者,成为故事中女主人公们最终的归宿。通过这种情节设计,来表达对男权社会主导下主流的财富婚姻观的唾弃。同时,作者用作品中五个女性的形象向读者传达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独到见解,表达出来女性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个体独立性的观点。女性在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时候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而不能成为男性和金钱财富所奴役的对象。
(一)彰显独特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小说首先凸显的是马奇太太的家庭观和爱情观。通过她,把作者主张的爱情观和家庭观灌输给四姐妹。在对四姐妹的成长过程中,马奇太太就教育四姐妹不要把金钱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马奇太太告诉四姐妹说,宁愿看到四姐妹做贫苦人家快乐的妻子,也不愿她们做没有自尊和快乐的王后。马奇太大的这种爱情观和婚姻观念是四姐妹认识及衡量爱情和婚姻的标准,是四姐妹爱情婚姻生活的坐标。所以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四姐妹始终坚持追求真爱而非财富。[4]譬如,在爱情和婚姻上梅格选择了清贫的布鲁克,最终他们俩通过努力建立起了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曾经梦想嫁入豪门的艾米最终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嫁给了劳里,故事的结尾艾米拥有了温馨美满的家庭生活。
(二)寻求爱情婚姻中两性的平等
既然爱情婚姻不以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那小说中必须提出一个标准主张,那就是寻求爱情婚姻中两性的平等。这点在书中的主人公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为了达到爱情婚姻中女性价值主张的表达实现,在小说最后,设计了乔拒绝了青梅竹马的邻家男孩洛里嫁给了年纪很大的贝尔教授,以至于这种结局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审美上的遗憾。嫁给洛里,她将迎来的是衣食无忧的贵妇人生活,从当时的主流意识维多利亚式的妇女伦理观念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女孩所能够渴求得到的最美好的归宿。那么然后呢?结局不言自明,就像梅格一样,她将被终生禁锢于狭小的家庭空间里,而她唯一的人生追求就只是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看到了这一危险,因而拒绝了洛里。对于乔来说,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生活只是一把枷锁,她将不得不严格遵守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准则:虔诚、持家、纯洁、驯服,不得不泯灭自己的个性,安于狭小的家庭空间。而乔和贝尔有相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小说也强调了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和谐的,两个人在结婚之后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均能够相互帮助,从而将他们一致人生观结合下的美满婚姻完美呈现。[5]小说着重表达的就是:乔对于自由平等的热爱之情,对于自己事业的热爱之情,导致她不愿意作为一个男人的装饰品,毋庸置疑,她这一举动完全就是对当时男权社会的一个挑战。在乔和贝尔教授结婚之后,平等相待的理念也是贯穿始终,乔和自己的丈夫一起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并且在其丈夫的写作生涯中,乔始终给予其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在爱情婚姻层面的女性价值主张上,作者采取破立结合的呈现方式,破掉的是以财富多少为衡量标准的爱情婚姻观,立起的是平等相待的婚姻价值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情节的设置上是直接的,甚至有些粗暴。以至于在故事的结尾,当读者读到乔拒绝了洛里,这一完美的邻家男孩的求爱,反而选择了形如父辈的贝尔教授都不禁喟叹,感到遗憾。乔的拒绝不仅彰显了她的叛逆性格,彰显了她对于自由、女性独立空间和男性力量的深切而本能的欲望,也揭示了她不顾一切,偏执狂般的维护一个自我满足、充分独立的女性社区的欲望。她的拒绝是自我挫败式的,但也确实张扬了自己的个性。也使得作者关于女性在爱情婚姻层面的价值实现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三、 社会生活层面的女性价值对比呈现——以男性弱化、女性张扬为设置
传统观点一直强调两性对于家庭贡献的严格区分,划定女性的生活范围仅限于自己的家庭,因此女性的生活重心被迫囿于家庭事务上,而男性则负责在外工作养家糊口。针对这一观点,女性主义者在发表主张时,首先就批驳了女性只能做全职家政的观念。他们认为,妇女也有权利、有必要走出家门,从而开拓家庭以外的事业,她们应当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甚至可以像男性一样在工业、科技、宗教等领域干一番事业,或许可以表现得更好。小说的作者为了表达社会生活层面的女性价值主张,在此采取了弱化男性和张扬女性对比呈现的手法。
(一)弱化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
小说中,女性人物着墨明显多于男性人物,篇幅上的不平等导致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性格上非常不平衡。男性人物如马奇先生、劳伦斯先生在小说中不仅出现的次数少,即使出现也是为了突出描写其中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当马奇先生身染沉疴,是马奇夫人对他的悉心照料使他逐渐恢复健康;当劳伦斯先生因为失去爱女而一直郁郁寡欢,是贝思的关心使他倍感欣慰。而小劳伦斯,四姐妹性格的完善,生活的完成,跟他并无太大的关系。梅格和约翰的恋爱婚姻,他只是旁观者。[6]乔成长为一个作家,艾美成为一个地道的淑女,以及贝思的死去,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并不能影响姐妹们的生活,换言之,他对她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着意削弱男性人物及其感情的描写,即便提到也总是让人失望,他们无法满足爱人、女儿或伙伴在物质或者精神上的追求,也无法肩负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男性的社会生活功用几乎无从实现。[7]反观女性人物,尽管生活艰难,感情受挫,但她们依然积极乐观,勇于追求幸福,追求独立,她们不仅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和社会中的各种责任,还填补了男性在社会生活功用上的缺失。
(二)张扬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个性
通常女性的存在价值集中在容貌的妍丽上,而女性的容姿又往往笼罩在男性的视野打量之下。例如,秦罗敷的美丽在“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的驻足观赏中呈现,希腊第一美女海伦的美丽是在大臣们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打仗值得”的反应中衬出。在男性视野下,女性成为“柔桡轻曼,妩媚纤弱”“侍儿扶起娇无力”“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弱者”形象,而女性也逐步从与男性的平等地位降格成为男人的“肋骨”。女性美更一度被物化为“肤如凝脂”“指如春葱”“杨柳纤腰”的具体标准。[8]而《小妇人》的女主人公乔故意打破传统,穿着打扮向男性化发展,开始穿戴比较舒适实用的衣帽。在19世纪的美国,妇女在公共场合被要求穿束缚全身的紧身衣裙,并且配有厚重的花边蕾丝装饰,追求淑女化的打扮,作者对女主人公的设计也就体现打破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从外表、行动上追求自由解放的倾向。除了外形上的打破,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也打破了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生活区域和事业上的局限,马奇家的四个女儿各有其潜质,梅格想成为演员,乔立志成为作家,贝思和艾美分别想当钢琴家和画家。如果拥有机会,这些女性完全有可能取得像男人一样成功的职业生涯。其中,乔的写作最为成功,为家庭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譬如她为《鹰报》写的第一个故事使她挣得了一百元的稿费,最终成了母亲和贝思到海边度假的来源;《公爵的千金》为家里付了肉账;《幽灵的魔爪》为家里添了一条新地毯;而《咒语》一文则使马奇一家衣食无忧。在小说的第十一章《匹克威克和邮箱》中,四姐妹因为品读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有感,也组建了自己的匹克威克社团,并为自己起了笔名且创办了自己的匹克威克文选,使她们的所思所想可以像男性一般公开发表。四姐妹对于像男人们那样组团结社有着强烈的兴趣,渴望获得平等开设研讨会朗诵会和参与政治讨论时事的权利,这些都无形中打破了现实生活中女人只能出入社交场合或在家庭范围活动的禁锢,反映出了马奇姐妹的自我的意识觉醒,她们敢于冲破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在社会生活中为女性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9]
四、结论
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突破和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四姐妹的成长历程的描写,积极倡导女性应当独立自主,勇于追求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并且应当有家庭以外的生活。为了在作品中阐述自己关于女性价值实现的主张,打破当时社会关于女性的既有观念以及男性话语的统治,作者采取了缺位呈现 、破立呈现、对比呈现的情节设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这些情节的设置有些还表现得比较简单化、概念化和粗暴化,但这部作品不失成为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是早期女性主义思潮观点在文学作品中的一次集中体现,《小妇人》在婚姻观、爱情观、性别观等思想与理念上,在当时的时代都是先进的。
[1] 陈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1):150-152.
[2] 苏美妮.媒介形象与父权规制——论青春家庭剧中都市女性形象的父权制内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02-107.
[3] 马石子.美国文学中新小知女性特征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2014(3):137-140.
[4] 于倩.道德伦理与人生选择:论《小妇人》中乔的爱情与婚姻[J].世界文学评论,2011(1):144-147.
[5] 孙章萍.浅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8-101.
[6] 张元元.解读《小妇人》中的女性角色[J].芒种,2011(10):75-76.
[7] 何小颖.“新女性”:在传统与独立角色间做出妥协——析《小妇人》中的主要女性人物[J].时代文学,2011(10):150-151.
[8] 安昌光.从女权主义角度看《飘》与《小妇人》中的两位女性[J].时代文学,2011(8):123-124.
[9] 路易莎·梅·奥尔科科特.用心灵去感受少年时代美丽的时光——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男人》[M].陈玉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12.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2-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尚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ZX121);湖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企业国际化与‘科技武汉’国际形象的塑造”(项目编号:2016ADC078)。
朱玉霜( 1975- ) ,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I106.4
A
1004-941(2017)01-01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