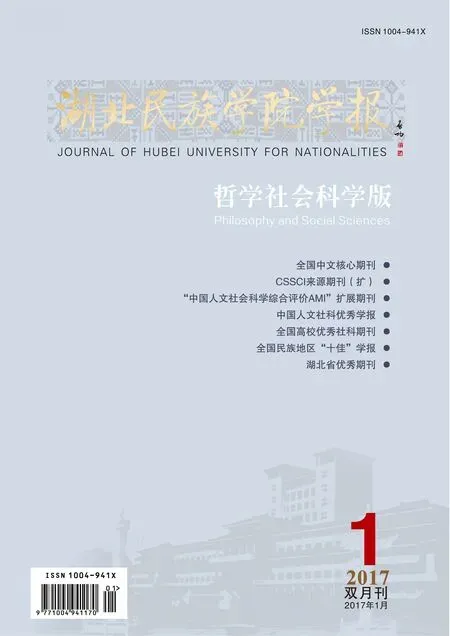南诏大理国的汉传佛教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2017-03-07雷信来
雷信来,葛 荃
(1.百色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2.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南诏大理国的汉传佛教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雷信来1,葛 荃2
(1.百色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2.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派佛教是南诏大理国佛教的三个来源,它们传入南诏大理国的大致时间、流行区域,以及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各不相同。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较早,盛行于南诏大理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南诏大理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也最强。南诏大理国借助佛教对社会生活实现了有效的控制。
南诏大理国;汉传佛教;政治功能
一、引言
南诏大理国佛教从来源上说,有三个来源地,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派佛教,有关著作和论文都认为南诏大理国佛教有三个来源。这三派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政治生活中各自的地位及影响力如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则不多。有论著指出汉传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最高,但是对于背后的所以然之故则没有交代。简单地说,以往研究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成果偏重于经验事实的描述,而对于事实背后深藏的根由挖掘稍显不够。在三派佛教中,汉传佛教被南诏大理国接受的程度更深,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控制力亦最强。
二、南诏大理国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播到西藏地区较早,由于遭到苯教的顽强抵抗,直到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才开始呈现渐趋繁荣景象。
西藏的佛教,其来源地并不仅限于古印度,中原地区也是其重要来源地之一。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佛教经典,包括珍贵的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佛像,这件文物至今仍保存在拉萨大昭寺内。文成公主曾慷慨资助过赴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侣,接受过于阗憎人来吐蕃避难。松赞干布曾经从汉地迎请和尚摩诃衍那大师,由文成公主及拉隆多吉贝担任翻译,翻译出大批汉地佛教、历算及医药之书籍。吐蕃统治的敦煌地区是中国与印度、中亚等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这里聚集了汉、藏、维吾尔等各族人民,这里开展的系统佛经翻译工作使唐藩之间以佛教为核心的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入蕃弘法的唐朝僧人摩诃衍那,出生于后藏达纳地区,在河西地区享有盛名的吐蕃大德管法成,均与这里有关。管法成把大量汉文佛经译成藏文,又把大量藏文佛经译为汉文,成为唐蕃文化密切交流的一个典型代表。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时,金城公主同样带去大批佛经。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密切了唐朝与吐蕃在佛教领域的交流,把唐蕃关系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上述论述说明,古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或者说,藏传佛教是在古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共同影响作用下成长起来的。这即是说,藏传佛教在进入云南之前,从形式到内容均受到了汉传佛教的深刻影响。
佛教在公元五世纪方传入西藏,初期受到本土宗教苯教的压制,六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才得以发展起来,其传入云南的时间在南诏初期。传入云南后,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滇西北的迪庆和丽江一带。南诏大理国的核心统治区域是洱海地区,其次是滇池地区,因此藏传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当不是很大。“藏传佛教是云南佛教也是世界佛教的三大支流之一。它源于印度,成于西藏,在云南主要流行于滇西北迪庆、丽江的藏、纳西、普米族地区。”[1]南传上座派佛教传入云南地区的时间稍晚,主要流行于今云南省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州地区,这两个地区对于南诏大理国来说属于“蛮夷之地”,故在此流布的南传上座派佛教在南诏初期虽然在南部边境地区获得发展,但并没有对南诏国及其后的大理国统治核心区域的宗教与政治生活构成实际影响。“11世纪以后,伴随大理国与蒲甘王朝的频繁往返,被蒲甘王朝奉为国教的小乘佛教不可避免地对大理发生影响,但由于受到已有大乘佛教各派的抵制,始终没有在大理统治的腹心地区扎下根来。与此相反,在大理统治的边夷地区小乘佛教却得到了广泛发展,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格局。”[2]
按照排除法推断,汉传佛教对云南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力,并对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道、释、儒三教中,儒和道属于土生土长的文化,唯有佛教系外来文化。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原介入汉文化圈层以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其演变和扩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佛教依附于本土文化并扎根于中原大地时期,这一阶段处于两汉、魏晋时期,佛教与黄老、道术和玄学相比居于附属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第二阶段,佛教开始摆脱对中国本土主流文化的依附,获得迅速发展。这一阶段处于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不统一为佛教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佛教发展成为足以与道教和儒教鼎足而立之程度,也在更高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整合。第三阶段,佛教实现了中国化阶段,即演化成中国式佛教。隋唐时期,佛教理论经过在中国长期的选择、进化和重构后,逐渐从印度佛教的教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基本实现了汉化,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完全汉化后的佛教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融摄性,即不断地协调佛教各种宗派的纷争,有选择地融摄各种异质因素,积极地会通中华文化和佛教文化。”“二是创造性,即在融摄异质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学说和理论。”“三是协调性,即除一些具体教义有所抗争外,佛教一直非常清醒地协调与儒教、道教的总体关系。”“四是适应性,即致力于从各方面适应皇帝制度和宗法制度的需要,形成内涵复杂的教义,使社会各阶层皆可各取所需,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3]
佛教汉化的过程始于西汉末年,发展到隋唐时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佛教在汉化过程中,会随着汉文化向四周的扩散而传播到其他地区。汉传佛教传入南诏大理国的通道主要是蜀道,其次是黔中道和交趾道。蜀道有两条线路,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终点是大理,此道途经灵关、清溪关,故又被称为“灵关道”或者“青溪道”。另一条亦是以成都为起点,终点是昆明,这条路又被叫作“僰道”或者“五尺道”。这两条蜀道是汉传佛教进入云南的最主要线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大概是唐初,也即南诏早期。徐嘉瑞认为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是唐高宗时期。“余谓中国(内地)佛教之入南诏,当在高宗时。《蛮书》云:‘细奴罗,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赏锦袍、锦袖、紫袍。’《旧唐书》云:‘盛罗皮至京师,赐锦袍。’当时佛教大盛成公主下嫁吐著,尚在此前,已携佛经像入西藏,南诏使者公有携佛经回国之事。则中国佛经入南诏,必当在高宗时,最远亦当在武后时,决非始于张建成。”[4]对此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同认识,如李京指出:“晟罗成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云南志略》)张道宗认为:“威成王诚乐(罗晟)立,遣相张建成朝唐……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图像而归。(南诏)王祟事佛教,自兹而启。”(《纪古滇说集》)李元阳亦持此说:“张彦成(张建成),……南诏蒙晟遣彦成使于唐,礼待甚厚,赐以浮屠像而归,南中佛事自兹始。”(《万历云南通志》)云南应该早就有佛教,认为始自张建成不可信。罗晟做王子时,就曾两次入唐朝贡,很可能在他第一次入唐(公元653年)返回南诏时,就把汉地佛教带回了云南。因为当时唐朝对佛教向四周传播很热衷,此前文成公主入藏时就携带大量佛教经典。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几乎同时传入云南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已经存在重要差异。佛教在公元五世纪时才传入西藏,接着从西藏传入云南的佛教究竟是什么形态的佛教呢?从学理上推论,当是一定程度的“西藏化”佛教,也有可能是没有经过“西藏化”改造的“原汁原味”的佛教。不论有没有经过“西藏化”整合,此时期的佛教在教义上一定还站在高贵的位置上,至少佛教还可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吐蕃王朝选择的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在这种体制下,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渗透,难分彼此,松赞干布本人就兼任佛教的法王。而在佛教的母国古印度,佛教可以凌驾于王权之上,由当时人们分为四个阶层,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可知,掌握宗教祭祀权的婆罗门阶层的地位高于掌控世俗政权的刹帝利阶层。佛教传入中国后,“沙门应否拜俗”立即成为一个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在佛教的母国是个无须讨论的命题,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王权宰制理性,无论什么观念、理论、学说和信仰,要想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可,只能选择为王权服务,不得与王权平起平坐,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在中原地区汉化后接受了忠君观念,屈从了王权和宗法。
三、汉传佛教的流行区域析辨
通过对藏传佛教与汉化佛教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如何对待王权与教权问题。对于南诏大理国统治阶层来说,他们更需要哪种佛教呢?或者说哪种佛教更有利于资治呢?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显然是汉传佛教,而不是藏传佛教,更不是南传上座派佛教。为讨论问题的方便,有个前提问题需要首先澄清,这个问题就是佛教发展到大理国时期究竟呈现出什么状态。元初的郭松年留下的作品为解答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元初郭松年到大理旅行写下了著名游记《大理行记》,其中关于大理地区佛教兴盛状况的叙述不能断章取义式地理解,必须要回溯到当时的历史时代,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分析郭氏的相关记述,才能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郭氏有言:“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5]136这里的“此邦之人”是指大理国全体人民?还是另有所指?对此问题下文将有释疑。“西去天竺为近”很容易理解,大理国与天竺国有天竺道相连,两地的距离确实不算遥远。“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意思是说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信众贫富老幼皆有,覆盖面很广。“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5]136此话意为一年当中,人们事佛的行为大约占据了近半年时间。事佛期间不饮酒只吃素,事佛结束后才搞生产劳动,那时才会吃肉饮酒。这些话语如果不进行仔细推敲,很容易得出整个大理国佛教繁盛、全体国人都崇奉佛教的结论。
接下来的记述是这样的:“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中峰之下有庙焉,是为点苍山神,亦号中岳。中峰之北,有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一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中峰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5]136-137郭松年游览途中发现寺院很多,难以计数,中峰之下有道庙,道庙是点苍神祠所在地。此山也叫中岳。中岳北边是崇圣寺,寺内有三塔,大塔高三百尺左右,有十六级,外观精致华美,此塔是在唐朝派遣的工匠恭韬、徽义的指导下建成的。塔建成后两人回唐复命。中峰南边有玉局寺,西南有上山寺。这里有两个信息需要注意:一是点明了参观的具体地点是苍山,因为苍山是大理国的中岳;二是苍山上不仅有佛教寺院,还有道观并存,有道观说明大理国时期依然存在道教信仰,以及忠实的道教信徒。
郭松年接着指出:“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而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5]137大意是说,山上寺院都是得道僧人居住,得道之人与师僧有很多不同之处,并对两者的主要不同点进行了阐释。最后是这样记述的:“此大理之大观也。南游则永昌、腾越,北走则鹤庆、丽江,周行数千里,皆莫若此也。”这就是大理的大致景观了,大理的南方是永昌、腾越,北方是鹤庆与丽江,周围数千里范围内,佛教的兴盛程度都不如大理。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第一,郭松年作为元朝初年的地方官,巡行云南时到过不少地方;第二,苍洱地区的佛教事业发展很繁荣,苍山上的寺院很多,也有道观存在,表明元初大理地区的道教还有一定市场;第三,苍洱地区的佛教事业在整个云南行省是最兴盛的,其他地区都不能和大理地区相提并论;第四,大理国佛教的繁荣在南诏国时期就打下了根基,事实上南诏国时期佛教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郭松年的《大理行记》作于大理国灭亡后三十年左右,他所描述的情景应该可以适用于分析大理国的佛教发展状况。因此,“妙香佛国”指的应该是苍洱地区佛教繁荣昌盛的景象,不能简单扩大为整个云南地区。大理国的政治中心在今大理市,佛教对大理国的统治阶层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而在大理国其他地区,佛教的兴盛程度和社会影响力当远不及大理地区。
四、汉传佛教的独尊地位和政治功能
在清晰解读郭氏《大理行记》中关于大理地区佛教事业发展情形的基础上,接着论证南诏大理国佛教对政治生活的服务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佛教能与政治生活走多近,取决于它自身理论的圆融精致程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政治生活之需要;佛教能对政治生活发挥多大作用,同时也取决于统治阶层对其的裁剪利用程度。南诏大理国佛教的命运地位即如此,南诏在统一云南的过程中,利用或得到了佛教力量的帮助,这是南诏国接受佛教的前提条件。南诏对佛教的利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南诏由最初的六诏之一,一步步扩张壮大,直至最终解体,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时间内,南诏统治阶层对佛教的政策以利用为主,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南诏初期,利用佛教为其造势,宣称蒙氏家族得到神僧或观音的点化,将来必然称王。这样的政治宣传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其目的不外乎是宣扬君权神授。在南诏主动发起的多次对外战争中,有一些战役的取胜得到了佛教僧侣的帮助。通过宣扬佛教僧侣在战争中的神异功能,意在表明南诏的战争行为具有神圣性。南诏中后期,佛教兴盛起来,王室在崇佛方面不惜花巨资建造佛寺、铸造佛像,有些国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在王权主导之下实施的崇佛行为,是欲以佛教作为驯化臣民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王权。
第二,南诏早期尊崇道教,中后期佛教受到尊崇,道教的地位相对下降,是因为南诏在统一云南的过程中,道教的利用价值较大,而统一云南后,佛教的利用价值变得更大。南诏前期,佛教刚传入云南,信众不多影响力不大,而道教则不然。天师道早于佛教传入南诏,在当时民间社会拥有大量信徒,以天师道为旗帜推进政治统一进程,容易得到普通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当南诏统一云南后,道教作为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的工具作用大打折扣,这时南诏王室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工具来佐助其治国安民,佛教正好可以满足南诏王室的需求。佛教治心的作用非常突出,佛教徒一般也是忠臣顺民,这样的人易于统治。南诏王室尊佛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乌蛮与白蛮之间的矛盾。南诏王室的族属系乌蛮,但是大部分贵族则是白蛮,南诏国是乌蛮与白蛮联合专政的国家。乌蛮很崇尚天师道,但是进化更快的白蛮贵族主要信奉佛教,南诏中后期,南诏乌蛮王室和白蛮贵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乌蛮王室做出让步,改为推崇白族信仰的佛教。
第三,大理国佛风更炽烈,但大理国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教合一制度。在整个大理国时期,在南诏大理国核心统治区域,上至王侯,下至布衣,都以崇佛为要务。木鱼声声,梵音沸天,一派“妙香佛国”的气象。大理国历经二十二位国王,有八九位国王被废为僧或逊位出家。大理国佛教事业确实很繁盛,但大理国并非以佛立国,佛教亦不能左右王权运作。国王带头宠佛,引得臣民投身佛教,收到了上行下效的政治功效。随着佛风释雨的不停熏染,信佛之人的名利之心逐渐淡化,甚至消失,这样的臣民无疑是最容易统治的。大理国国王可以投巨资为佛教做公德,但一般不会于在位期间担任佛教组织的重要实质性职务,这和松赞干布担任佛教法王不同。佛教的高僧大德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如董氏一门在大理国世代担任国师,为国王出谋献策,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归世俗统治者掌握。信仰佛教之人可以担任政府官职,但是在佛教组织中担承重要职务的僧人一般不被授予实质官职。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刻意在佛教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设计之目的是为了在佛教与政治之间划设一条红线,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目的是防范佛教宰制政治。
对于大理国国王被废为僧或逊位为僧之事件,也要辩证看待。大理国前期在段思平与段思良兄弟两系之间纷争不断,有实力的贵族高氏、杨氏也借机卷入其中。高氏还曾短时取代段氏,建“大中国”,后迫于形势,还权于段氏。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代专权,人称“高国主”。从公元937年到公元1253年,在大理国存续期间出现过二十二位国王,其中大概有八九位因政治斗争失利而遁入空门。他们遁入空门的具体原因,要么是年幼无知,要么是暗弱昏庸,要么系因为不理朝政寄情山水,当然其中也有有作为的。总之,他们在最高政治权力角逐中是失利的一方,而被赶入寺院,或寄情于佛教。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佛教徒,政治上的失意在佛教意识的安慰下,变得相对淡然一些。况且他们进入佛门,还可以享受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社会地位依然较为尊贵,能够为佛教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丧失国柄不至于丧命,他们还可以在佛教事业领域继续为国家服务。因此,“禅位为僧在任何时候都是帝王政治失意后的无可奈何的下场,越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如此。”[6]在大理国,对于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获胜的一方来说,关键是得到权力谋取自身利益,对于失败一方的处置不必过于残忍,没必要消灭政敌的肉体。参与政治斗争的人物基本都是佛门弟子,佛教讲究慈悲为怀,因此获胜方把失利方赶下王位后再推进空门不啻为明智之举。段思平对待政敌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的做法是废为僧,把他赶进寺庙令他忏悔,让其余生与青灯古佛为伴。这种手法,既是宽容,也是惩罚。这种政治景观与中原王朝完全不同。大理国围绕最高政治权力展开的争夺,以及争夺失败者的境遇,与中原王朝相对照的话,可以发现,大理国的政治斗争少了浓重的血腥味道,多了几许人道的抚慰温馨,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因于佛教对政治生活的调节润滑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佛教调节政治的功能是基于王权支配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佛教支配王权的结果。
第四,在大理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流行的是汉传佛教,对政治生活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汉传佛教。之所以这么说,重要原因是汉传佛教的发育成熟程度及对政治统治的可适用性远高于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派佛教。汉传佛教于唐初传播到南诏,这时的汉传佛教已经是在中原地区历经大约六百年风雨洗礼,基本完成汉化的佛教。此时藏传佛教才刚传入云南,因此它的发育程度要远低于汉传佛教。从汉传佛教的可适用性,即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看,汉传佛教已经实现了佛教道德宗法化,转变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当这种形态的佛教传入南诏后,当然会受到统治者的信赖。当汉传佛教在南诏国经受一二百年的地方化洗礼后,到大理国时期,汉传佛教基本完成了云南本土化改造,具体表现是密宗阿吒力教的形成,佛教发展进入繁荣状态。大理国云南化的汉传佛教对政治生活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实现大理国佛教的国教化。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与政治从来就不是天然二分的,而是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刚一产生就被统治阶级拉过去作为维护巩固其政治统治之工具。大理国对佛教的利用,焦点表现是佛教国教化,即“统治集团把某一特定宗教作为神学统治的精神力量,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结成君权和神权的神圣同盟。”[7]大理国没有议会,故不存在所谓的把佛教国教化的立法活动,但从佛教在大理国实际所发挥的作用看,佛教无疑是大理国的国教。
2.承担社会控制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宗教的核心功能是社会控制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佛教可以“使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神圣化,使个人愿望服从群体目标,个人冲动服务集体原则。”[8]大理国治下的民族或部族众多,这些被统治者对统治阶级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佛教通过教义、教规的传扬,把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加以淡化,同时神圣化等级观念,这样下层民众就会遵循社会秩序,把思想行为限定在统治阶级划定的轨道上,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稳定运转。
3.把政治斗争控制在斗而不破的限度内。大理国前期、中期,段思平和段思良两系虽然矛盾斗争不断,但并没有发展到影响国家稳定的程度,而且政权的交接或者转递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波澜不惊,没有酿成大的政治事件。后理国时期,国家的实权掌握在豪门望族高氏手中,高氏可以根据自己利益要求随意废立国王,这些国王都是段氏成员。这时期的段氏尽管只是名义上的大理国最高统治者,却可以一直干到大理国灭亡,高氏没敢再推翻大理国名义上的段氏国王。出现这种政治现象的重大原因,是佛教对政治纷争一定程度的化解使然。高氏掌权基本没有屠杀过段氏王族,段氏国王被废后踏入佛门,两派势力各得其所。大理国佛教兴盛的客观氛围,高氏和段氏都是崇佛教徒,因此两派冲突在浓厚的宠佛背景之下并非不可调和,始终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4.凝聚社会力量,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推波助澜。佛教组织系具有共同价值观,凝聚力超强的宗教实体,它有系统的教规教义、体系化的宗教组织、大规模的忠实信徒。因此,统治阶级往往会在必要政治关口,挥舞起佛教的大旗进行社会动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宗教在被操纵利用的情境下,往往具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性。南诏国曾经在多场侵略战争中对佛教加以利用,也曾与唐朝在佛教的旗帜下进行过外交谈判。大理国醉心佛教、以佛治心,从未发动过对两宋的战争。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保持和平,都需要凝聚社会共识,而在南诏大理国这样虔诚事佛的国度里,这些重大的政治行为背后都有佛教为之背书的成分在内。
[1] 王海涛.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516.
[2] 何耀华.云南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4.
[3] 张分田,张鸿,商爱玲.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83.
[4]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314.
[5]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6] 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56.
[7] 冯天策.宗教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84.
[8] 金泽.宗教禁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97.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12-15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3CMZ010);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雷信来(1976- ),男,安徽霍邱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少数民族史及民族政治问题研究;葛荃(1953- ),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行政文化等。
K244
A
1004-941(2017)01-00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