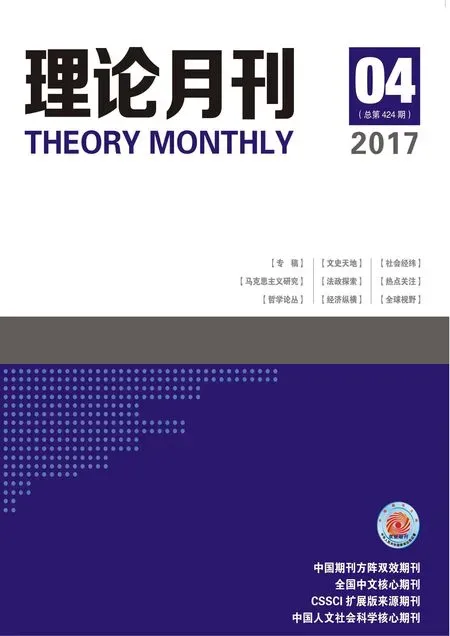“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五种表现形式
2017-03-07王俊杰
□王俊杰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五种表现形式
□王俊杰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史家除了尽可能地去秉笔直书以“实录”历史真相,还行使对历史的裁决权,评断历史的是非曲直以抑恶而扬善,而“春秋笔法”则是史家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春秋笔法”是孔子所开创,而由司马迁发扬光大。司马迁在继承“春秋笔法”精神本质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远远超越了“以一字为褒贬”的传统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展了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体制破例寓褒贬,编排次序蕴微义,互见法里辨人事,委婉曲笔明是非,只言片字别战绩。“春秋笔法”除了劝善抑恶的道德功利目的,还能使文章达到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审美效果。
司马迁;史记;孔子;春秋笔法
汉民族是一个道德伦理型的民族,中国史学也是道德伦理型的史学。史家除了尽可能地去秉笔直书以“实录”历史真相,还行使对历史的裁决权,评断历史的是非曲直以抑恶而扬善,而“春秋笔法”则是史家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春秋笔法”又被称作“春秋书法”或“春秋义法”,最早对“春秋笔法”加以概括的是《左传》。《左传·成公十四年》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870刘勰对“春秋笔法”也有论述:“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2]284刘知几也说:“《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3]591“春秋笔法”历来为史家所推崇。《史记》中关于“春秋笔法”记述的篇目有8篇:《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晋世家》《孔子世家》《匈奴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和《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眼中,《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以“当王法”,是“拨乱世反之正”的精神武器,“辞微而指博”是其修辞策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是“春秋笔法”的精髓。总之,劝善抑恶是“春秋笔法”的本质,史家的思想倾向不是用议论性的文辞直接表达,而是通过史事的记述排比自然显现,在谨严的措词中表达爱憎之情,微言大义是“春秋笔法”的灵魂。
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4]150邹方锷说得更明白:“《史记》书法,《春秋》书法也”(《大雅堂初稿》卷六)[5]132。《史记》中有“春秋笔法”,这早已为古人所指出,现在我们来讨论“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表现形式就有了前提,而不是自说自话、空穴来风。近代以来有关“春秋笔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厚(参见肖锋《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述评》,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而以“春秋笔法”与《史记》关系为主题的文章也有几十篇。这些成果或讨论司马迁与孔子精神上的相契,或追寻司马迁与《春秋》学的渊源,或解析“春秋笔法”与“史迁笔法”的关系。《史记》中到底有哪些“春秋笔法”?司马迁在继承“春秋笔法”精神本质的同时,如何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展了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对这样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文章加以研究,但往往是浮光掠影,缺乏厚重令人信服的成果,本文就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讨论。
“春秋笔法”是孔子所开创,而由司马迁创造性地发扬光大,在技术层面上远远超越了“以一字为褒贬”的传统手段,“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实现形式多姿多彩。
1 体制破例寓褒贬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与列传之间是有“尊卑”之别的,本纪叙天子,世家叙诸侯,列传写人臣,等级森严。三者之中,本纪是核心,是七星北斗,世家与列传则是环卫北斗运行的二十八宿,起到辅弼拱卫本纪的作用。同时,司马迁并没有严格地按照由后人总结出来的这种“成例”去做,《史记》出现了许多“破例”,这些破例往往蕴藏着司马迁的褒贬,从中更能看出他作史之用心。
破例之一,“越级”放入高一级的体例。秦始皇设为本纪殊无歧意,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本为诸侯,秦国本应设为世家,但史公却作《秦本纪》。孔子以布衣之身而位世家,陈涉出身垄亩身死无嗣而列世家,项羽并未做成天子而位列本纪,吕后并未如武则天般称帝而列本纪。司马迁对这几位都是给予了“低级高位”的破格待遇,细究史迁何以超越常理这样做,确实是有深意存焉。秦从献公以后就“常雄诸侯”(《六国年表序》),国势自非六国可比,正因为有了数百年的经营才有后来的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作《秦本纪》。参照《六国年表序》,寓意更明。该表表名六国,实列八国,周、秦都不在六国数中。第一栏列周,以示尊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第二栏列秦,日食灾异载于秦表而不载于周表,以示秦系天下之存亡,褒美秦之统一事业。孔子无尺土之封而列世家,是司马迁尊学统,视其为万世师。司马迁尊陈涉说到底是为了尊汉、反暴政、赞首难。项羽自命为霸王,曾为共主于一时,况且司马迁对这位悲剧英雄颇为同情,项羽虽败但其人格足以令其对手汗颜,将其放在本纪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贬抑刘邦之意。把吕后放在本纪,是因为吕后是当时最高统治者,是没有穿皇袍的实际意义上的女皇帝。她虽然毛病很多,并不讨司马迁喜欢,但她在位时对外不轻言用兵,奉行无为而治,继续了汉初休养生息的良好局面。
破例之二,“降级”放入低一级的体例。周朝与汉朝都有世家,而秦朝却无,世家是要“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6]3319,按这个标准,李斯、蒙恬都是秦朝的股肱之臣,是有资格享受位列世家的待遇的,而司马迁却把他们放在了列传,原因何在?李斯在秦始皇死后,私心太重,被赵高裹胁而立胡亥,继续实行严刑酷法,使一个强大的秦朝轰然崩溃,司马迁对之很是鄙薄。司马迁对蒙恬也很不满,他在《蒙恬列传》的论赞里严厉批评了蒙恬在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味阿意兴功而未能及时谏劝秦始皇改行仁政,致使国破身亡。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把他们降级放在了列传里。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为吴王,本应与齐悼惠王、楚元王同列世家,但由于他倡导发动七国之乱,故司马迁降之于列传。准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也都是刘氏宗亲并封土建国,本应列于世家,但因“谋反”,也只好屈居列传了。韩信、黥布、彭越也因“谋反”被降在了列传。这些人的谋反,有的是确有实据,有的则在疑似之间而显得扑朔迷离。对确实谋反叛乱者,司马迁把他们放入列传,并对之进行贬抑;对被皇家扣上谋反帽子者,司马迁把他们放入列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讳于时忌,孔子当年作《春秋》也不得不有所讳饰,司马迁作《史记》面临同样的问题时,也不得不效法孔子“春秋笔法”而有所忌讳。张耳立过军功被刘邦封为赵王,也曾是一方诸侯,其子赵敖也袭领赵国,赵敖又是刘邦所确定的功劳仅次于萧何、曹参的大功臣,按例张耳似也可列于世家,司马迁却将张耳放入列传,一则有便于叙事的考虑,张耳、陈余由生死之交发展到水火不容,二者事迹不可分离,另则更反映了司马迁对这种以势利交的厌恶。刘邦手下大臣所立功劳,萧何第一,曹参第二,周勃第四,此三人放在世家恰如其分。陈平功劳位居第四十七,张良为第六十二,二人功劳如此靠后尚列于世家,与此相比,功劳位居第五的樊哙,第六的郦商被放于列传,则显然是降级了。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在他看来,樊、郦诸人都只是“附骥之尾”,善于因人成事而已,沾了刘邦的光,其自身并没有特别称道的地方。陈平、张良功劳等级虽靠后,但他们却是奇才伟士。对人物所列“位置”的一降一升,体现了司马迁的论人标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3319,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太史公的赞赏。
破例之三,似应立传而未立传。汉惠帝身为皇帝而不立传,是因为他只是空担个皇帝的虚名,在历史中没有什么建树,不给他立传乃史公高识。秦楚之际的小楚怀王,被尊为义帝,他不仅是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且一度是有实权的,他也并非常人所想象的是平庸的傀儡,小楚怀王无传问题还要与范增之未立传一并讨论。范增是项羽手下第一谋士,还被项羽尊为 “亚父”,在楚汉战争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对范增之所以不立传,恐怕也是另有微义。范增的事迹主要附在《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笔下,范增并不是个好智囊,并没有提出什么奇谋良策,恰恰相反,他提出的最重要的谋略——立楚王之后以收民心,倒是个“馊主意”。王鸣盛曰:“六国亡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制人者变为制于人……范增谬计既误项氏,亦误怀王。”[8]11在史迁眼中,范增并非足与张良相媲美的谋略之人,不屑为之立传也便在情理之中了。由范增而引发了小楚怀王的人生悲剧,牧羊人成了军事斗争的牺牲品,不为小楚怀王立传,也隐隐透出司马迁对他悲剧命运的无奈之情。还有长沙王吴芮,他是刘邦所封八个异姓王中唯一的幸存者,并传了五世,朝廷还特别下令褒奖其“忠”,长沙国最后因无嗣而绝,后来其别系子孙又广被封侯。按吴芮的地位身份,似应放在世家,而实际上司马迁不仅没有把他列入世家,竟然列传中也不给他留个位置。吴芮对汉王朝只会俯首帖耳,没有丝毫奇行壮节,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家奴,故太史公不屑为之单独立传。
司马迁博采众长创立了五体结构,可贵的是司马迁并不为这种体制所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体例。那些“破例”往往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独到理解,正是这些破例使司马迁并没有成为中规中矩维护既有等级秩序的卫道士,恰恰相反,司马迁对现有秩序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挑战姿态。破例中有褒贬,破例中有深意,破例中见“春秋笔法”。
2 编排次序蕴微义
《史记》130篇,其编排次序也是暗藏玄机。关于《史记》编排顺序,有“次第皆无意义说”,其代表学者是清人赵翼,他说:“《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10]6-7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赵翼的观点,如汪之昌说:“据赵说,则编次先后本无义例。吾谓义例所在,诚无明文,而赵氏所举各传,则编次似非无意者。”[5]147朱东润曰:“曲解篇次,诚为不可,然遽谓其随得随编,亦未尽当。”[7]19《史记》编排次序并非无章可循,而是别有用心。
《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叔齐列传》分别被列为本纪、世家、列传的首篇,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司马迁推崇一个“让”字。此三篇之传主都是以“让”得贤名而闻于天下,司马迁特别嘉许他们的让国让天下。歌颂“让”其实是映衬和批判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争”,特别是司马迁所处的汉代,为了一个“争”字而发生了多少战争与屠杀:刘邦削除异姓王的战争,吕后执政时的诛“诸刘”,吕后死后“诸吕”又被诛,汉景帝时七国之乱实际上是刘氏宗亲的自相残杀,汉武帝后期因巫盅之祸而引起的太子集团与武帝集团的火并。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百姓死活,骨肉相残,父子相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桩桩一件件都令人悚目惊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对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首篇的处理,是效法孔子编排《诗经》各体开始之篇的处理。《孔子世家》首次提出“《诗经》四始”的概念,在司马迁看来,风、小雅、大雅、颂之第一篇至关重要,孔子如此编排存有微义。《五帝》为本纪始,《吴太伯》为世家始,《伯夷》为列传始,我们不妨也可称之为“《史记》三始”。“《史记》三始”表彰“让”德,其手法渊自“《诗经》四始”,这又是司马迁受孔子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
我们再看列传第四十八至第五十七篇目的编次蕴含的微义,这十篇的顺序依次为:《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这些篇目集中反映了汉武帝征伐匈奴及对四夷的用兵情况。韩长孺列首篇,除了因为该篇详述了揭开汉朝反击匈奴战争大幕的 “马邑之伏”,还因为韩安国总体上也实为反战人物,他和司马迁对匈奴战争的态度基本一致,以一个反战人物开场,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叙事定了基调。紧接着是李广列传,其传在匈奴传之前,飞将军镇守北边,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史公将其传列于匈奴传之前,以见北边非将军不可寄管钥。《卫将军骠骑列传》紧承《匈奴列传》以见卫青、霍去病之军功。司马迁对卫、霍二人虽然心存成见,对汉匈战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感到心痛,但还是如实地记述了二人卓绝千古的战功,汉匈战争收官于二将便是史迁如此编次的主要用意。《平津侯主父列传》列于汉匈战争篇目与少数民族列传篇目之间,是司马迁要再一次借他人之言以表明对汉匈战争及征伐四夷的态度,主父偃向汉武帝上《谏伐匈奴书》,公孙弘、主父偃都反对伐匈奴、打朝鲜及通西南夷,徐乐、严安的上疏也有这方面的言论。泷川资言亦曰:“偃等三人皆以文辞进,皆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其事相涉,此所以与平津同传。观次诸卫霍、两越诸传间,可以知史公之意也。”[9]5657接下来是四个少数民族列传,它们与汉之名臣传等列,反映了司马迁视各民族均为中国版图内的天子臣民的大一统观念。司马相如与唐蒙等人开通西南夷,开启了汉武帝征伐西南的野心而使兵民疲敝,司马迁追根溯源,不能不归罪于相如,故将司马相如传编于《西南夷传》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这十篇有关汉武帝对外用兵的篇目,环环相扣,先后次序大有深意,构成了一个自具首尾、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并且这样的“叙事单元”在《史记》中并不是个别存在。
《史记》编排次序有义例可循,这次序也着实蕴含着司马迁的良苦用心,虽然不能说所有次序都有用意,否则,就势必陷于穿凿附会,但说不少篇目的次序有深意,还是符合实际的。
3 互见法里辨人事
“互见法”是《史记》运用“春秋笔法”的又一特殊表现形式。最早提到《史记》使用互见法的是苏洵,见《苏老泉先生全集》卷九。苏洵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互见法”这一概念,但已道出了它的实质,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洵是把互见法当作“仲尼遗意”来看待的,认为互见法是孔子“春秋笔法”的后继,而苏洵的这种认识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忽视,他们只强调“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其精神本质是效仿“春秋笔法”以寓寄托。朱自清是深悟苏洵本义的当代学者,他指出:“互见的体例……又常用来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褒,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专述其人的长处;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贬,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专述其人的短处;遇到该褒的人确有短处,无可讳言,该贬的人确有长处,不容不说的时候,便也用‘互见’的办法,都给放到另外的篇章里去。”[11]朱自清是既知司马迁又知苏洵之学人。
辨人事、寓褒贬,才是互见法的精神本质。项羽是史公心仪的悲剧英雄,司马迁不仅破例把他列于本纪,还以列传法写本纪。在《项羽本纪》里项羽是个喑噁叱咤盖世无双的英雄,但项羽又是个有重大缺陷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缺点,司马迁则在《汉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加以叙述。《汉高祖本纪》中刘邦列项羽十大罪状,怀王诸老将指责项羽之暴虐;《陈丞相世家》借陈平之口点明项羽不能因功封赏,士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借韩信之口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汉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的规模宏远与雄才大略,而在《项羽本纪》则写出刘邦的贪财好色及流氓本色,《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对刘邦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有所忌讳。信陵君是司马迁极力颂扬的人物,在本传中极力写他的礼贤下士威震敌国,在《范睢蔡泽列传》则写了他因惧怕秦国威势而不敢收留魏齐的胆小懦弱。对项羽、信陵君采用互见法,显然是司马迁对之爱之太深而有所庇护。
互见法是司马迁匠心独具的创造。一方面避免了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传记中反复出现,通过“语在某某事中”以精简篇幅,尽量避免纪传体容易出现的重复冗沓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写出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层次性,在本传中着力突出其人的主要性格,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刻画在本传中不宜写出的其人性格的另外的方面。“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倘就单篇而责备之,他就太冤枉了。”[12]219互见法是《史记》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桥梁,历史性要求全面真实地叙写人物与史实,文学性则要求提炼主题塑造出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互见法就很巧妙地解决了历史真实与文学典型之间的矛盾,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化文史矛盾于无形。司马迁一手牵起历史,一手紧拉文学,让历史与文学在互见法这拱“鹊桥”上相会结缘,并最终导致“史传文学”的呱呱坠地。
只有掌握了互见法这把金钥匙,才能真正打开司马迁的历史大门,才能够真正洞悉其中的微言深意。互见法是“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又一表现形式,也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活学活用。
4 委婉曲笔明是非
史家笔法有所谓直笔与曲笔之分。所谓直笔就是依据史实秉笔直书,其特点是文义一致,明白显豁;所谓曲笔是史家用委婉曲折的笔法叙写历史,其特点是若明若暗,含蓄隐约。史家之所以采用曲笔,主要是因为种种“忌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认为《春秋》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司马迁曰:“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6]2919这种种忌讳,特别是“时忌”,迫使史家不得不特别讲究叙事策略,在冠冕堂皇的官样文字缝隙中变着法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达出来。直笔需要的是大义凛然的勇气,曲笔需要的则是迂回幽远的智慧。
曲笔在疑似之间幽隐之际寓褒贬,实乃 “春秋笔法”之变体。要想真正读懂《史记》,我们就要弄懂司马迁所用的曲笔手法,不为他的表面文字所迷惑,要读出隐藏于字缝间的本意。
其一,指桑骂槐。司马迁很会“骂人”,他把在文章中“骂人”变成了一种艺术。司马迁以秦讽汉是他“指桑骂槐”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秦始皇本纪》就是在含沙射影地指斥汉武帝。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又迷信神仙妄图长生,致使战争不断,民怨沸腾,并最终导致秦国被农民战争的洪流冲入历史的深沟。汉武帝与秦始皇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汉武帝讨匈奴伐四夷,企图建立不世之武功,与秦始皇如出一辙,但在司马迁看来却是用力勤而收效微,结果是士卒死伤惨重,人民不堪重负而民变不断,汉武帝如果不以秦为鉴极有可能重蹈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本纪》就是《今上本纪》的“副册”,秦始皇就是汉武帝的镜子,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骂”秦始皇,其实也是在“骂”汉武帝。
其二,故露破绽。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冤案,汉代亦是如此。汉高祖、吕后制造的淮阴侯韩信谋反案,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谋反案,都是疑点重重。从司马迁对两案叙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揣摩出他对两案的微妙态度。此两案都是钦定大案,司马迁自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它们是冤案,而是采取“故露破绽”的策略,借他人之言代为鸣冤,阳依成案而阴白其冤。《淮阴侯列传》引录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汉自立的大段说辞,韩信听后并没有为之所动,它表面上处处在说韩信谋反,实际上司马迁是在为其申白冤情;再如韩信教陈豨反汉“挈手辟左右”时所说的话,只有韩、陈二人知道,并没有第三者在场,这分明是当时欲加之罪而罗织的罪状。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也是借用人言以明其迹。刘安谋反的过程,全由自首者伍被口中道出,而刘安始终未发过一兵一卒,令人对其中众多破绽顿生疑窦。韩信案的实质是刘邦要铲除异姓王,以建立刘姓的家天下,淮南案的实质是刘彻要剪灭藩国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他们之“谋反”,实质上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案件本身破绽就极多,司马迁在叙录时又故露破绽,声东而击西,后世读者从疑点重重的文字间不难得出结论。
其三,釜底抽薪。司马迁对汉初封侯赐爵的达官显贵多有不满,这些人的传,前面罗列他们的战功奇谋,说上一大堆的好话,而在最后太史公又往往不露声色地添上寥寥几笔,而这几笔又使前面所有的溢美之辞都变得没了意义,从而达到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如《萧相国世家》中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6]2020这里说萧何因为沾了刘邦与吕后的光,帮助设计除掉了韩信、黥布,他的功劳才显得如此灿烂,语调充满嘲讽。《曹相国世家》前半截极力铺陈曹参的战功,而最后司马迁写道:“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6]2031曹参立了那么多的军功,原来是因为跟上了韩信这位名将而因人成事;韩信等人被消灭后,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曹参才显露出来。司马迁用语是如此热辣。《留侯世家》正文大写张良之奇谋良策,最后在论赞中突然来了这么几句:“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6]2049张良之功在于人谋,而太史公却把人谋归之于天运,这样就几乎把张良之功一笔抹杀了。《陈丞相世家》前面用力渲染陈平之“六出奇计”,而最后司马迁让陈平开口给自己作了评价:“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6]2062陈平一生最为得意的“六出奇计”,实为“六出阴谋”,这不仅会在他这一辈子遭“报应”,还会祸及他的后世子孙。司马迁揭出此语,含蓄无穷,垂戒深远。《樊郦滕灌列传》前文铺排他们的战功,最后司马迁在论赞里又酸辣辣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6]2673釜底抽薪之法,能给人造成前后极大的反差,前面铺陈传主的功高德重,后面的寥寥数语才真正揭出本相,前面铺陈得越多,后面落差就越大,人物摔得就越响。
其四,归诸天命。姚永概曰:“《史记》每于愤惋不平处,又难以明言,往往归之天命,其文最为狡狯深婉。如《项羽本纪》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六国表序》云:‘盖若天所助焉。’《秦楚之际月表》云:‘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李将军传》云:‘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惑失道,岂非天哉!’皆是也。”[5]73此外还有《卫将军骠骑列传》于卫青则曰:“天幸”,《傅靳蒯成列传》于傅宽、靳歙则曰:“此亦天授”,把他们的成功都归之于天命。司马迁以“天命”予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于失败的英雄,如项羽、李广等,表达了司马迁的痛心惋惜之情;另一种是用于成功的显贵,用天命解释他们的成功,意味着鄙视他们个人的奋斗,在司马迁看来,他们的成功只不过是运气好老天眷顾罢了,流露出太史公的愤慨不平之气。两类天命,两类人物,两类情感,深得春秋之义。
其五,虚字传神。司马迁用虚字最不苟且,在他手中,虚字已不仅是用来煞尾的语气词,而是常有深意存焉,时有太息之声。南宋的洪迈,明代的焦竑,清代的姚苎田、林纾,都曾对此有过论述。李长之对《史记》中虚字的用法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所论虚字有11个:矣、也、而、故、则、乃、亦、竟、卒、欲、言[12]289-293。其中“矣”字最能够代表司马迁的讽刺和抒情,是司马迁运用得最灵巧的一种武器。“矣”字用作讽刺的武器,在《封禅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集中,据笔者统计,《封禅书》共用了22个“矣”字。《封禅书》是司马迁讽刺汉武帝的一篇力作,频用虚字使文章营造出一种飘忽不定、似有若无的氛围,这既与求仙封禅的内容相合,又充满了讥讽意味。因李长之对此已有举证,兹不赘言,现就《高祖本纪》中的“矣”字作一简要分析,试看:
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6]348。
这个“矣”字是写刘邦编造故事以自我神化,俗人并不觉悟而被其蒙蔽。再看:
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6]391。
这是写刘邦为剪除异姓王,偏听一面之辞,并无实证就定卢绾谋反之罪。司马迁用一个“矣”字,慨叹皇家的忌刻无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看: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6]394。
这里的语气与《秦楚之际月表序》中的一段文字很相似: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6]760?
前段文字用“矣”字传神,后段则用两个“乎”与两个“哉”达难言之意。这两段文字究竟是褒还是讽,历来意见不一,我还是倾向于这是寓贬于褒,司马迁在反话正说,他是在讽刺刘邦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无赖”,靠着时运,居然开创基业当了皇帝,这天命忒是不公,也忒是滑稽!古代汉语中虚词非常丰富,在表情达意时往往起到实词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司马迁就是善用虚词的高手,虚词恰到好处地运用使他的文章一唱三叹,摇曳多姿,悠远疏荡。虚词不仅使《史记》增添无限声色,更起到一种言外之言、意外之意的修辞作用,这种作用又是其他笔法难以代替,甚至是难以企及的。以虚字传神,不仅是《史记》的一大艺术特色,还是司马迁一种曲折达意的“春秋笔法”。技乎?技矣!神乎?神矣!
司马迁不但有秉笔直书的胆量与勇气,而且有曲笔达意的圆通与智慧,直笔与曲笔共同拱卫起《史记》这部以实录著称的鸿篇巨制。
5 只言片字别战绩
《春秋》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作者的情感,“以一字为褒贬”(杜预《左传序》)是“春秋笔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几乎成了“春秋笔法”的代名词。
司马迁是语言大师,遣词用语的功夫臻乎化境,这种功夫的养成显然也得益于对“春秋笔法”中的“以一字为褒贬”的自觉师承。《史记》叙写战争特别是叙写战将军功时,措词很有讲究,对此前人多有评述。茅坤评《樊郦滕灌列传》记战功时说:“太史公详次樊、郦、滕、灌战功,大略与曹参、周勃等相似,然并从,未尝专将也。其间书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残’、曰‘先登’、曰‘却敌’、曰‘陷阵’、曰‘最’、曰‘疾战’、曰‘斩首’、曰‘虏’、曰‘得’,成各有法。 又如曰‘身生虏’,曰‘所将卒斩’,曰‘别将’,此各以书其战阵之绩,有不可紊乱所授也。”[9]4977-4978可永雪也指出:“汉初战将纪功,仿《春秋》书法,创为历叙体,用‘攻’、‘击’、‘破’、‘追’、‘围’、‘救’、‘下’等字序其事;又用‘定’、‘得’、‘取’、‘守’、‘虏’、‘斩’等字序其功;并以或“陷阵”、‘先登’,或攻城掠战中常‘最’、或‘疾斗’、‘战疾力’、‘以兵车趣攻战疾’表其人的个性特点,行文以简捷、简劲取胜。”[13]P345-346司马迁撮叙功状,用不同词语以区别不同的战绩,这些词语生动准确,简劲的字词中包蕴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微妙的情感向度。
“春秋笔法”除了起到劝善抑恶的道德功利目的,还能使文章达到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审美效果。《史记》体史而义诗,史蕴诗心,我们读《史记》要像听古琴那样善于捕捉弦外之音,又要像嚼橄榄一样回味那种难以捉摸的甘甜。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5]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朱东润.史记考索[M].上海:开明书店,1947.
[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9]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出版社,2004.
[10]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朱自清.略读指导举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1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3]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文 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4.009
I206.2
A
1004-0544(2017)04-0060-07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5WX019)。
王俊杰(1973-),男,河南鄢陵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