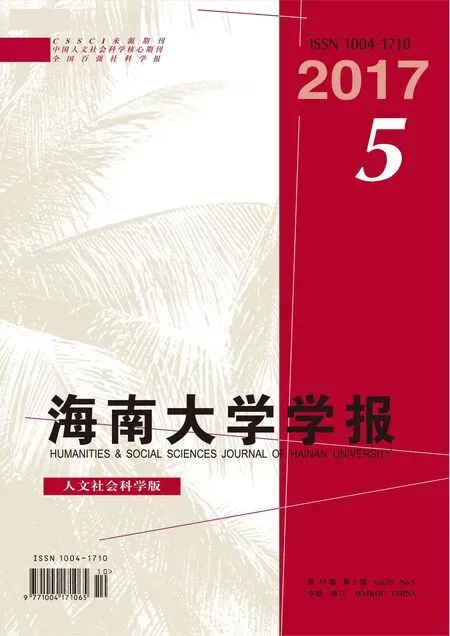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淮南子》对无为概念的新定义及理论贡献
2017-02-24李秀华
李秀华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淮南子》对无为概念的新定义及理论贡献
李秀华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淮南子》编撰者学派立场不完全一致,根据其主张的不同,可划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儒家派。老庄派在吸取老子、庄子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无为就是不在条件不成熟之前贸然行动,而是顺势因循或推动事物基于天性的自主行为,突出了无为由道化成术的一面。黄老派则大力发展了战国以来君道无为的观点,认为无为就是拥有权势和智力的人(以君主为代表)不因此而肆意作为,所有作为都不是从己意出发,而是一准于客观的法则,突出了无为即克己、自律的一面。儒家派则批评了流俗关于无为即静止不动、无所作为的错误看法,认为无为就是遵循客观的物理来行事,借助各种条件来立功,突出了无为成就大有为的一面。在古代思想史上,《淮南子》首次对无为作了精确的定义,也首次对有为进行了界定,大大强化了无为从道至事、由道化术的特征,使之实践性得到拓展,为无为思想的发展作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淮南子》;无为;有为;术数
作为一部杂家著作,《淮南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吕氏春秋》的翻版,有大量文字是袭自于它。从编撰的内容和体例上看,《淮南子》不如《吕氏春秋》严密,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书中不少观点互相抵触,例如,反对仁义与拥护仁义同时存在*《淮南子》中存在大量批儒言论(主要是批孔子、反仁义),有的措辞严厉,近于庄子学派。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可参看拙文《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福建论坛》2014年第5期,第57-62页。而《氾论训》《修务训》等篇则大力鼓吹仁义之道。。当然,这也可以说成是《淮南子》一书更具有包容性。尽管此书杂取各家言论,但仍然存在一个主干思想,即道家思想。高诱评论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叙目》)认为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辅,基本符合原书大旨。从这个方面说,《淮南子》又可以看成是汉代初期一部具有总结性的黄老学著作,其编撰者身份亦可大致划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儒家派*《淮南子》的编撰者身份各异,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高诱说:“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一作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淮南子叙目》)其中伍被等八人(后世称为“八公”)应是黄老道家学者及方术之士,大山、小山之徒应是儒家学者。老庄派,《要略》篇首次把老子、庄子合称为老庄,是指据《老子》《庄子》思想而议论的学者,其无为思想主要出现在《原道训》《诠言训》。黄老派,是指融合道、儒、法等家思想而主谈君道的学者,其无为思想主要出现在《主术训》《诠言训》。儒家派,是指融合孔、孟及荀子思想的学者,其无为思想主要出现在《修务训》。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并不截然对立,在许多方面反而具有内在统一性。本文如此划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清《淮南子》无为思想的体系。。无为思想是他们重点关注和论述的对象之一,也是他们罕见的一致推崇的思想。《淮南子》编撰者不仅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庄子以及黄老学者的观点,还结合儒家思想,历史上第一次对“无为”这个概念作出了不同定义,为无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目前,关于《淮南子》无为思想的专论文章为数不多,且基本上未作严格区分,把不同编撰者的不同言论混为一谈。这样显然并不利于我们对《淮南子》一书所包含的无为思想作出准确的把握,因此,有进一步梳理和研究的必要。
一、《淮南子》老庄派对无为的新定义:不先物为、不易自然
尽管老子首先把“无为”一词用作哲学概念,但并未对它作出过明确的定义,其后的先秦学者也同样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就现存文献而言,刘安和他的门人是最早对无为概念作出定义的一批学者。虽然他们意见不统一,但这种尝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淮南子》老庄派继承了老子、庄子关于无为的基本观点,并对“无为”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
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祼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老、庄多讲“不道之道”,多反对智巧伪诈和严法苛令,庄子学派更是强调以精神为本,这些都为《淮南子》老庄派所继承。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无为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刘笑敢先生说:“在老子哲学中,无为的一般含义是,静待自然之变而无所作为,而无不为则是指来自无为的结果和好处。但是在《淮南子》中,无为和无不为不再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两种不同的态度或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成了一回事,成了视条件而定的行为。而所谓条件,就是‘不先物为’或‘因物之所为’。这样,无为和无不为就都成了某种特殊行为的结果。无为也就从无所作为变成了某种类型的作为,即无为变成了有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对无为理论的理论化解释。”在解释上把无为转向有为,并非《淮南子》首创,韩非子、陆贾都早于它。《淮南子》老庄派所作的界定,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把无为(无治)、无不为(无不治)都解释成某种视条件而定的特殊行为。这一阐释上的改变,使无为这个概念褪去了形而上的色彩,转化成了一种可供掌握和操作的施为之术。
“不先物为”之“先”,表示时间或次序在前,与“后”相对而成,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在条件不成熟之前或事物行动之前而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不以自己的盲动去干涉事物的自主行动。“因物之所为”之“因”,表示前后相承之意,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事物根据自己的本性运作,自己只是顺承其成。“不易自然”,即不改变事物原有的自然之性。“然,犹宜也”,“因物之相然”即让事物自相适宜,自己也只是顺承其成。从逻辑上说,“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分别是“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的前提,亦即“无为”“无治”分别是“无不为”“无不治”的前提。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无为就不能无不为,不能无治就不能无不治。可见,尽管《淮南子》老庄派将“无为”“无不为”都看成是视某种条件而定的特殊行为,但仍然与老子、庄子思想的本质是一致的,都强调不争不先,强调自然法则。
“不先物为”是对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淮南子》67章)的发展,即不争不先防止了施为者的盲动;“因物之所为”是对老子“万物将自化”(《淮南子》37章)的改造,即因循、执后使事物有充分的空间自主行动。《原道训》说:“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又说:“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石靡坚,莫能与之争。”不先与柔弱、虚静,虽名异而实同,都属于“雌节”。为防止自己盲动,让事物根据自己的本性运作,就要抱守柔弱、虚静之“清道”,做到因循应变,常后不先,因为争先的人容易无路可走,后动的人常有广阔天地。在《淮南子》老庄派看来,执后并非机械地、一味地退后,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和遵守相应的规律情况下作出恰当的行为,与无为的内涵相一致,都是道之属性,所谓“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诠言训》)。可贵的是,他们的眼光并未停留在“道体”“道容”之上,而是下落至“术数”这个层面,主张以无为制约有为,以执后制约争先。这样,《淮南子》老庄派对无为的定义就由道而转为术了。
“不易自然”是对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淮南子》64章)主张的另一种表述,“因物之相然”是对庄子“因其固然”(《养生主》)主张的进一步发挥。老子讲自然比较宽泛,多指事物自己如此的状态,也指事物自化、自定、自正、自富、自朴的本能。《淮南子》老庄派讲自然,则从《庄子·齐物论》中得到启发,多指事物的自然之性、自然之势。
《原道训》说:“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跖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到生挫伤,鹰鵰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芄,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干、越生葛纟希,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上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鵒不过济,貈度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从这段论述来看,自然之性是指事物的天性,具体来说,就是事物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本性,如浮萍、树木、飞鸟、野兽、蛟龙、虎豹等,皆被赋予了各自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本性*这一观点应该自《庄子·齐物论》而来:“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人、鳅、猴各有自己相适应的生存环境,人、麋鹿、蝍蛆、鸱鸦各有自己相适应的食材。此即本性的体现。;自然之势是指事物在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有能力,如圆物滚动、空物漂浮、木摩擦生火、火能镕金,等等。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就是依靠自己的自然之性和自然之势而生存、发展、变化着。就像春雨时至则万物生育,秋霜时至则万物蛰藏,就像牛马宜陆,舟行宜水,就像匈奴出皮衣,干越出细布,就像南人多水事,北人多骑马。事物的自然之性和自然之势也不可被人力所改易,否则将失去赖以存在的本性,甚至死亡。因此,了解这些道理的有道之人就会顺承事物的自然之性、自然之势,让事物根据自己的本性运作,自己则不用奔命于外,只需体道守本,入于逍遥无为之境,正所谓“(真人)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精神训》)。这就是“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的思想内涵。
《淮南子》老庄派认为,得道的人能够“不先物为”“不易自然”,能够无为于万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治内”,换句话说,“治内”是其无为的根基。如果失掉了这一根基,无为而治就不能真正实现。《诠言训》说:“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可知“治内”对于无为而治的重要性。《本经训》又说:“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禨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苞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得道的人很注重“治内”,能身心和调,动静合道,能随顺事物的自然之性和客观的自然法则,天下自可不治而治。可见,“治内”主要是对道的体认和顺从。《说山训》云:“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无*“不能无”,原作“不能有”。高诱注云:“为者,有为也,有谓好憎情欲,不能恬憺静漠,故曰不能无。”据改。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06页。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载无”,即是对道的体认和顺从。人知有为而不知无为,则不能“载无”,即不能体认和顺从道。这样就颠倒了本末关系,不仅没有成效,还会对自己带来伤害。因此,有为要以无为为基础。《淮南子》老庄派的这一主张,显然是注重无为向无不为的实效转化。
无为要达成无不为,体道是根本,“循道理”“因自然”则是途径。《原道训》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与宇宙之总。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棰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循*“循”,原作“修”,据王念孙校改。见《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5-766页。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体道无为,落实在方法论上就是“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就如大禹治水是根据水的自然之性,神农播谷是根据禾苗的自然之性,只有这样才能逸而不穷。反之,不务道德之本,专任术数之末,倚赖个人的巧能,不仅治不了天下,还会劳而无功。
相对于老子、庄子的无为概念来说,《淮南子》老庄派所定义的“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等意涵,显然具有更加实际的指向,使得他们所主张的无为逐渐滑向一种“藏于无形”的施为之术了。
二、《淮南子》黄老派对无为的新定义:不以位为事、莫从己出
黄老思潮在西汉初期十分盛行,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皆受其影响。刘安和他的门人身处其中,毫不例外地表现出对黄老学的强烈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说,《淮南子》的编撰者就是黄老学者。
《淮南子》黄老派讨论无为,几乎都是针对君主而展开的。他们对无为也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为义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壹民。君执一则治,无常则乱。君道者,非所以有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则昌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一身之身既数变矣,又况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径衢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则乱,甚于无君之时。(《诠言训》)
君主的责任就在于给民众提供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要完成这个责任,他自己就必须先要遵从一个不变的道,即所谓“执一”。若不遵从这个不变的道,国家就将陷入混乱。因此,君主要守住的这个不变之道就是无为。帛书《老子》中已有“执一”一词:“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但没有直接与无为联系起来。把执一与无为合为一体的,则是文子,他提出了“执一无为”的观点。《淮南子》黄老派的上述说法,显然是受到了文子的影响。他们认为,无为就是执守一道,各安本分,不相僭越,即如智者、勇者、仁者,都不应以自身的地位和权势肆意作为。同样的道理,君主身居高位,势位至上,亦不可窃以变易常规,肆意妄为。君主若屡坏常规,不能无为,那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会比没有君主时更加严重。
《淮南子》黄老派用“不以位为事”“不以位为暴”“不以位为惠”来界定无为,其意在于制约君权,使之不得独断专行。《主术训》云:“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襃,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罪者而死亡,行直(者)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做君主就像做祭司,不过是上通下达而已,不能杂有丝毫的私心私意,更不能利用自己的权势肆意地“为惠”“为暴”,否则,就会产生奸佞、悖乱,国家就要灭亡。
《主术训》又云:“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以言其”,原作“以其言”,据王念孙校改。见《读书杂志》,第841页。莫从己出也。”社会有自下而上的层级架构,其目的就在于使每一个层级的人都不得自恣专行。君主处于层级的顶端,但并不代表其行为就不受任何约束,相反,他要带头遵守社会的法律制度和礼义规范,甘心执守于道,服从于理,依归于无为,这样才能够在处世行事时做到“莫得自恣”“莫从己出”。很明显,《淮南子》黄老派否定了法家学者把无为转化成权谋之术、驭人之术的做法,认为君主无为并非是死水般沉寂,而是不擅做主张,不固执己意,其一切行为皆依凭于道理和法则。
越有权势,有地位,就越容易自恣,容易专行,容易擅断。所以,《淮南子》黄老派强调君主无为的关键,就在于“莫得自恣”“莫从己出”。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君主首先要去掉自身的喜好、智巧。《主术训》说:“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立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君主本应无为无好,有为有好皆是个人私心私情的流露,容易干扰臣下的行为,甚至为臣下所利用。《诠言训》说:“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无所怨憾,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君主有喜好,则会随喜好行事,破坏公正,比如,好仁会破坏赏罚的公正,好刑会破坏法律的公正。只有消除自身的喜好,一准于客观的法则,抽身而退,才能像天地一样公正,才能使民无怨恨,社会合和。《淮南子》黄老派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道胜”,能顺道而行,则君主无事。
君主消除自身的喜好,也包括舍弃好智、好勇、好与。《主术训》说:“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诠言训》又说:“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智浅,以浅赡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穷术也。好勇,则轻敌而简备,自亻负而辞助。一人之力,以圉强敌,不杖众多而专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术也。好与,则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则下之望无止,若多赋敛,实府库,则与民为雠,少取多与,数未之有也。故好与,来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观之,贤能之不足任也,而道术之可循明矣。”不管君主个人如何强大,都不能凭一己之能治理国家。君主若好用智巧,就会违背时势,不顾规律,自恣专行;好尚勇力,就会轻敌自负,逞强斗胜;好行赏赐,就会取予不节,与民为敌。这些都是自取危亡之术。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就应该收起自己的聪明,抱守清静无为之道。
君主去掉自身喜好,只是“莫得自恣”“莫从己出”的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还需要君主懂得谨守规矩准则和善用众人之力。《主术训》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这里的“莫出于己”与“莫从己出”同义。可见,这是《淮南子》黄老派定义“无为”的核心要义。规矩准则一旦确定,就不应跟随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君主只需谨守不摇,就能不劳而成。《主术训》对此进一步论述说:“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此处,规矩准则不再是具体性的规矩准则了,已经与永久不变的道相通。谨守规矩准则即是谨守道,谨守道即可“无为为之”。此外,君主也应该以开放的心胸善用众人诸如师傅、行人、相者、执正的能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决策和行事的正确。君主在消泯自身意志和情绪的同时,能够善用客观的规矩和力量,社会事务自可井井有条,犹如自然而然。
值得指出的是,《淮南子》黄老派也讲自然,但与老庄派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万物固以自然”之“固”与“事犹自然”之“犹”所代表的意义不同。固,必也,常也。自然乃万物固有属性和必然趋势,这就叫“固以自然”。犹,若也,似也。事物的存在或变化像是自然而然,这就叫“事犹自然”。可见,老庄派主张不加任何干涉,让万物完全自然;黄老派则主张不彰显权力意志,让万物感觉是出于自然。
君主不彰显权力意志,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莫从己出”“莫出于己”,而“莫从己出”“莫出于己”的目的就是要善用众人之力。要善用众人之力,君主先要懂得分职、守职。这也是所有黄老学者一以贯之的主张。《主术训》说:“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有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又说:“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君道与臣道,就像圆与方一样,本质不同却又相辅相成。君主处虚位,执无为,无须承担具体事务;臣下处实位,执有为,必须承担具体事务。两者这种关系是确定而不移的,否则国将不治。君主必须在明确自己的这种定位之后,才能真正认识到善用众人之力的重要性。故《诠言训》说:“无以天下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之尊君也。辟地垦草者,后稷也;决河浚江者,禹也;听狱制中者,皋陶也;有圣名者,尧也。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淮南子》黄老派找到了天无为而贵、君无为而尊的根据。他们要君主确信,只有抱守无为之道,即使自身无能,也必可让那些有能的人为己所用。
那如何让有能的人为己所用?《主术训》说:“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通,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君主不应以自身的感官感觉和主观意志来观察社会,了解世界,而是把天下人的眼睛、耳朵、智慧、能力化作自己的眼睛、耳朵、智慧、能力,即如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为有能的人为己所用创造条件。除此之外,君主还要懂得“因”“积”“乘”的道理。《主术训》说:“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又说:“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循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因,依也,由也。依凭或通过一事物以认识另一事物,这就叫做“因物以知物”“因人以知人”。积,聚也,众也。聚合社会各方力量来行事,这就叫做“积力之所举”“用众人之力”。乘,借助也,利用也。借助或利用群众的才智,这就叫做“乘众人之智”。君主在掌握和运用这些道理之后,虽然一切行事“莫从己出”“莫出于己”,却能安享社会大治的成果。相反,不掌握和运用这些道理,强行不可为之事,即使是神圣之人也不能取得成功。当然,《淮南子》黄老派的这些主张也非凭空而来,是对《吕氏春秋》“执无为故能使众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三、《淮南子》儒家派对无为的新定义:循理举事、因资立功
如果把对孔子与仁义的态度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刘安的门人中还有一派学者,他们推崇仁义,赞美孔子,与老庄派、黄老派的立场鲜明对立。根据这个特征,笔者可将此派学者称之为儒家派。儒家派能够成为刘安门人中的重要成员,并不是偶然的。刘安及其门人活跃之际,正是汉武帝选择儒学、压制其他学派的时候。尽管刘安并非是从根本上喜爱儒学,但身处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他不能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关注和顺应。正因为如此,在《淮南子》中,儒家思想的地位仅次于黄老道家。《淮南子》儒家派认真地研究了当时的无为主义思潮,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为“无为”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
面对当时学者关于无为的一些曲解以及把神农、尧、舜、禹、汤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典范等错误观点,《淮南子》儒家派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反驳: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修务训》)
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无为就是垂拱端坐,静止不动,悄无声息,不与外界发生反应,甚至连意识思维都没有,将这种状况看作是得道的状况。《淮南子》儒家派以历史上被称为圣人的神农、尧、舜、禹、汤作为事实依据,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们认为,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这些圣人并不是无为主义者口中所宣扬的那样清静无为、垂拱端坐,而是劳形苦心,忧容满面。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不管是君主还是平民,若不劳心劳力,将会一事无成。《淮南子》儒家派的这些批驳,显然是针对当时黄老道家学者鼓吹君主清静无为以致于事事不理的现象而提出的。
尽管他们批驳了当时关于无为的流行观点,但并不代表他们反对无为。相反,他们对什么是无为这个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流俗的回答: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修务训》)
这段论述字里行间显露出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与老子、庄子关于无为的看法有着鲜明的反差。老子、庄子是要削弱人的事功精神,强调无事、无功,而《淮南子》儒家派是要激起人的事功精神,强调举事、立功。显然,他们摒弃了“道”这一形而上的笼罩和支配,完全突出了人的主导作用。但人的主导作用当然也不是盲目的、蛮干的,而是要懂得遵循物理,善用外力,即循理举事,因资立功。对此,儒家派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若要让积水流向低谷,人们就应根据水往东流的特点加以疏导;要让五谷长势旺盛,人们就应根据禾苗在春天的生长特点加以管理;如果听任它们自流自生,就不能让它们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也就举不成事,立不了功。
在《淮南子》儒家派给“无为”下的这个定义中,有几个关键要素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无为并非是不动不应,相反,它是要成就更大的事功。第二,无为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要避免个人意志、欲望和巧诈的干扰,另一方面要利用事物的自然属性,因循事物本身的道理和外在的各种条件。第三,无为就是要功成身退,事成而不自傲,功立而不自居,这一点与老子之无为无疑是相通的。为进一步说明无为的涵义,《淮南子》儒家派还区别了有为与无为的不同。他们认为,违背事物的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一意孤行,此即有为。比如,用火去烧干井水,把淮水引向高山,这些都属于有为;而在水中乘舟,沙地乘鸠车,草地乘秄,山地用蔂,夏天疏通沟渠,冬天整修陂塘,在高地造台,在低处造池,这些都属于无为,也是循理举事、因资立功的具体体现。《淮南子》儒家派的上述主张并非自创,明显受到了韩非子“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喻老》)观点的影响。只是他们在“用万物之能”这方面做了更具体、更精准的阐述。可见,《淮南子》儒家派对无为的定义,融合了儒家、法家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以及黄老道家的谦退精神和因循自然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儒家派也讲自然,但不是老庄所提出的事物本来如此(无需人为干预)的自然观念,而是指能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的事物的自然属性和成长环境。为此,儒家学派还批判了当时老庄学者主张自然属性不可损益的观念:“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吾以为不然。夫鱼者跃,鹊者驳也,犹人马之为人马,筋骨形体,所受于天,不可变。以此论之,则不类矣。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修务训》)他们一方面承认事物有些属性是受制于自然而不可改变的,比如筋骨、形体,但另一方面反对老庄学者以此作为事物不能被改变的理由。儒家派用马为例,来证明事物是可以通过人的教化加以改变的:当马还是马驹时野性十足,不受控制,当被人驯服后,却完全听命于人。所以,他们相信,一旦离开了人为的参与,事物的自然本性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显然,儒家派反对听任事物自生自长的主张,与老庄派“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显然,《淮南子》儒家派对无为的重新定义,完全立足于现实,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他们的定义,打破了老子、庄子为无为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之基础,使无为成了一种善用各种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大作为,并完全舍弃了老子、庄子虚静而无为的这一层意思,强调的仅仅是“动善时”这一面。这种解释上的变化,使无为观念更易于被人们(尤其是统治者)所接受。同时,《淮南子》儒家派把有为限定为一种错误行为,即出于私心私欲而罔顾事物的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的作为,只要统治者不去触犯,其他行为都可以排除在有为之外,避免了动辄得咎的担忧。可见,儒家派关于无为的认识,与老庄派、黄老派立场皆不相同,并不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而是对君主某些错误行为的限制。当然,儒家派的这些无为观念也适用于普通民众。
四、《淮南子》重新定义无为的理论贡献
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必定有一个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无为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就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期。它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在农耕文化下敬畏自然、依附自然、顺从自然的行为和心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暴政、虐民、争斗等乱象频发。一些知识精英,如文王、吕尚、管仲,开始反思人的行为,无为思想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逐渐萌生的。后来,更多的知识精英对此加以思考,其中以老子和孔子最为杰出。在老子这里,无为思想由萌芽而趋壮大,成为其标志性的思想之一;孔子则立足于德政和礼治两方面来申明其无为而治的主张。自此以后,两人的无为思想被不断发展和改造。尤其是老子的无为思想,关尹子、文子、列子、杨朱及其后的黄老学者、法家学者、庄子学派等,都各取所需,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关尹子、列子、杨朱和庄子学派大力拓展了虚静无为的内涵,文子重点拓展了无为之于治道的内涵,黄老学者又引入形名、法等概念来增其内涵,法家则融合上述各家思想,将无为改造成了一种较为阴暗的君人南面之术。到了西汉初年,无为观念更是风行一时。陆贾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吸取黄老道家的思想养分,提出了致中和、重德化的无为主张,曹参更是将清静不扰、守而勿失的无为理念应用到了治国实践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面对形形色色的无为观念,刘安和他的门人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理性的融通,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的立场首次明确定义了无为这一概念。可以说,这是先秦无为思想自出现以来所能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峰。
相对于以往的学者,刘安及其门人在无为理论阐述方面无疑有所突破。第一,更加突出无为从道至事、由道成术的转化。不管是老庄派、黄老派,还是儒家派,这种转化趋向都是一致的。“《淮南子》实际上是通过对‘无为而无不为’的积极解释,把《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对形上、自然之‘道’的描述,转化为对人间之‘事’的关注,从而搭建了从理念的‘道’走向实行的‘事’的桥梁。”从道走向事,由道化为术,虽然是先秦无为思想一个潜在的发展脉络,但在《淮南子》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是刘安及其门人有意追求的一个思想目标。这在《要略》篇体现得非常清楚:“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又说:“今谓之道则多,谓之物则少,谓之术则博,谓之事则浅,推之以论,则无可言者。”一改以前重道轻事、重道轻术的做法,把道、事、术放在同等地位来对待,强调三者之间的互存互助关系。他们在定义无为的时候,将这种理念贯彻其中。老庄派落脚在“物”,黄老派落脚在无己、用众,儒家派落脚在“事”“功”。这些皆是从道走向事、由道化为术的明显特征。《淮南子》对于无为概念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大大强化了它的实践性。第二,《淮南子》儒家派在定义无为的同时,也对有为作了明确的界定,这在古代思想史还是第一次。老子、庄子及黄老学者都没有正面阐述过有为的内涵,只是将其视作无为的对立面,或者说把它看作是不合于道的作为,显得玄虚、抽象,难以把握。到了庄子后学,甚至把人本能之外的一切行为活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视为有为,否定了人之于自然与社会的能动作用,从根本上堵塞了人的价值的外在实现。而《淮南子》儒家派以“用己而背自然”来定义有为,即因成见、私欲而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活动,显得明白、精确,易于把握。这样的界定,表面上是对有为内涵的限制,实际上是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无为概念的外延。
尽管《淮南子》的编撰者身份各不一样,主张亦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无为精神的把握是一致的。《要略》篇以和合立场总揽其他二十篇的内容,是全书的总纲。此篇特意阐述了无为的精神内涵,提出“通而无为”“塞而无为”的全新概念。这在古代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要略》云:“《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塞,壅也,闭也,用《淮南子》原话来说就是“底滞而不发,凝竭而不流”(《原道训》),就是“沉滞不通”“凝滞而不化”(《氾论训》)。浮浅之人大都受制于文辞,一见“无为”,就以为要清净、恬淡,最终流于懈堕慵懒。此即“塞而无为”,不通于道,固执不化,实际上与自然法则相乖违。“通而无为”正与之相反。通,达也,顺也。真正了解自然法则,去顺应自然法则,不固执,不僵硬,这样的行为即“通而无为”。一通一塞,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齐俗训》说:“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壹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可见,刘安和他的门人决非食古不化、固守一端者,而是能与世推移,兼容并蓄。他们所提出的“塞而无为”与“通而无为”,既是对以往无为思想的一种梳理,又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创造性主张,为古代无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这种定义无为的思路,也深刻影响了郭象对无为的新阐释。
ANewDefinitionofNon-ActioninHuannanziandItsTheoreticalContribution
LI Xiu-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The compliers ofHuannanzi,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academic schools and viewpoi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chools of Lao-Zhuang, Huang-Lao and Confucianism. Lao-Zhuang school, while absorbing the thought of Laozi and Zhuangzi, holds that non-action requires not to try abruptly under a poorly-prepared situation, but to follow the natural trend or push ahead the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attribute, which highlights the feature of non-action transformed from Daoism to technique. Huang-Lao school, while developing the view of monarchical non-action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 a large scale, holds that non-action means that one with power and talent (represented by a monarch) does not behave willfully and all his conducts obey the objective rules rather than his own will, which emphasizes the attribute of self-restraint and self-discipline. Confucianism school, while criticizing the secular, wrong views of regarding non-action as stagnancy and inaction, holds that non-action actually follows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ings to act, and appeals to all the conditions to make contributions, which stresses the quality of great action out of non-ac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hought,Huainanziprecisely defines non-action and a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greatly strengthening the features of non-action transformed from Daoism to thing and from Daoism to technique while extending its practicality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n-action thought.
Huannanzi; non-action; action; technique
I 206.2
A
1004-1710(2017)04-0092-09
2016-12-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W088)
李秀华(1976-),男,江西新余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