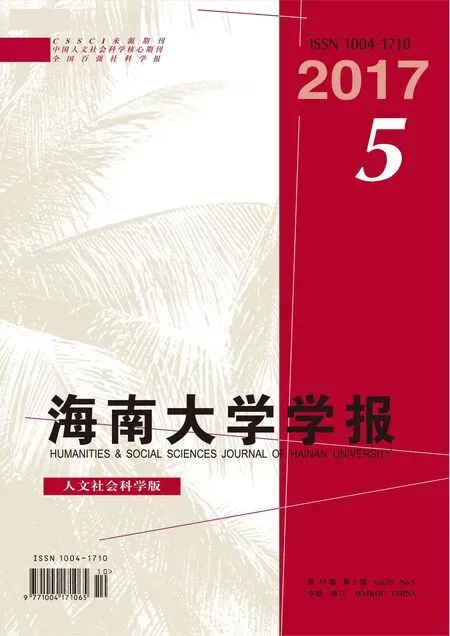乡村旅游本质的再思考
2017-11-09张金凤谢小芹
张金凤,谢小芹
(1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2.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乡村旅游本质的再思考
张金凤1,谢小芹2
(1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2.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本质问题贯穿始终,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主客关系”到“主主关系”的转变。现象学属于哲学范畴,对本质问题的探究较为深刻,这一方面源于“存在主义”的思辨高度,另一方面源于“关系主义”的优势视角。基于“存在主义”角度,杨振之提出了“诗意化栖居”是旅游本质的观点,大大深化了旅游本质的研究。然而,其对“关系主义”重视不够。乡村旅游是旅游的一种形式,但又有别于旅游。因此,乡村旅游本质的探究应该在进一步拓展“存在主义”高度的同时,将“游客-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主义”凸显出来。“主体间性”是探讨“主主关系”的一个哲学概念,尝试打破主客间的二元对立,重塑两者二重性关系。受益于此,笔者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是乡村旅游本质的判断。
本质;乡村旅游;主体间性
一、现象学视角下的旅游本质探究
西方哲学经历了“自然哲学—观念哲学—现象学”的演变历程。自然哲学从自然世界中来认识事物本质,如泰勒斯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水,阿那可西米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础等。观念哲学则从意识层面探讨本质,如柏拉图认为表示事物确定所是的那个东西叫“理念”。现象学则提供了一个研究本质问题的新视角,海德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并非单独的物,而是一种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上,本质问题讨论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康德说,“特征是事物中构成该物知识部分的那种东西……是一种部分的表象……所以,我们的一些概念都是些特征”*Kant I,“Logics”,Be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1,p.49.。康德将特征视为一种部分的表象,其言外之意是,特征是表层呈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特性,事物的特征可以有很多,但本质只有一个。
国外在探讨旅游本质时,大致有两种取向,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旅游中的权力关系不均等,如纳什指出旅游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第二,将旅游视为一种“朝圣”,探索旅游体验对游客的影响,格雷本的“旅游仪式理论”和“象征意义说”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国内,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旅游本质。在对旅游本质问题的考究方面,选择何种方法至关重要。近年来,现象学成为旅游本质探讨的一个较好视角。在此视角的关照下,王宁的“寻找真实存在”、谢彦君的“体验说”及杨振之的“诗意化栖居”将旅游研究从“物”拉向“人”,这成为目前旅游本质的前沿研究。
王宁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位探讨旅游本质的学者,他从存在主义哲学层面出发认为,“旅游地事物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关键是游客欲通过旅游来激发生命中的潜在状态及发现自我”*Wang N.,“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26,No.2,1999, pp.349-370.。他无意探讨旅游本质却真正触及到了旅游的核心问题,在他那里,旅游本质可被归结为“寻找存在的真实”,然而,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真实性”的辩论上,对旅游本质定义仍然较模糊且未能从经验层面继续深挖,这为后来学者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谢彦君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位从现象学角度明确给出旅游本质判定的学者,他认为“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而余暇和异地将这种体验与其他体验分离出来,赋予其独有的特征”*谢彦君:《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从学科自觉的角度看》, 《旅游学刊》2010年第1期,第29页。。然而,这一判断遭到了杨振之的质疑,他认为“我们可以说体验是旅游的基本特征,但却不是旅游的本质。因为,体验虽然是旅游的基本特征,但旅游不能因为有体验而使旅游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杨振之:《论旅游的本质》,《旅游学刊》2014年第3期,第16页。。通过梳理旅游的概念后,杨振之认为“迄今为止,都是对旅游表象的思考,是将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等表象来定义,而没有追问到旅游的本质”*杨振之:《论旅游的本质》,《旅游学刊》2014年第3期,第18页。。他认为“哲学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最好的方法和工具,社会学、人类学、逻辑学乃至管理学、经济学等无不源于哲学,且用这些学科方法研究旅游本质,最终必回到哲学”,借用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将人的存在归结为“人诗意地栖居”,杨振之认为旅游已经超越了体验,“诗意栖居”才是旅游的本质。
上述学者关于旅游本质的研究对笔者具有重要的启发。笔者也认为现象学是至今为止分析本质问题的最好视角,比较赞同杨振之对旅游本质所下的结论,但亦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现象学的两大优势在于蕴含着“存在主义”的高度和“关系主义”的新思维。杨振之凸显出了“存在主义”的优势,但却对“关系主义”的优势重视度不够,而这正是笔者与之的不同之处。乡村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到香港和澳门等大都市观光游玩可以被视为旅游,但不能被视为乡村旅游。可见,乡村旅游的范畴是乡村地区,它只是旅游的一种形式和一个子系统。因此,对乡村旅游本质的探讨可以在旅游本质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和补充。现象学蕴含着的“关系主义”倾向,有助于本文准确抓住乡村旅游的本质。
二、乡村旅游的本质是文化性和乡土性吗?
经过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动力机制探讨后,国内外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文化性和乡土性,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乡村旅游的表象和特征,并非其本质。那么,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入手论本质
在国内,吴必虎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发生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的旅游活动的总和。彭兆荣从人类学视角强调“‘乡村魅力’对于都市人而言,或者并不是换一个‘地方’,而是换一种体认‘价值’;与其说是在‘乡村空间’旅行,还不如说是在‘乡村概念’中旅游。这里强调了作为旅游主体的旅客对乡村的关照或印象的重要性”*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6页。。左晓斯在对国内外乡村旅游概念梳理后认为,“发生在乡村地区、主要以乡村性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一个相应的概念延伸便是‘乡村旅游区’,其特征是:(1)以农业文化、传统民俗及田园风光(乡村景观)为依托;(2)游客和居民活动均与农(林、牧、渔)业密切相关,活动范围大多限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林、牧、渔)业区;(3)农(林、牧、渔)业人口在区内占据绝大多数”*左晓斯:《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研究——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他将乡村旅游看成是“一种新旅游或者后现代旅游,他认为乡村旅游虽然历史悠久,但只是到了今天这个有点后现代味道的时代才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今日旅游正日趋走向‘乡村化’”。因此,他们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乡村性和文化性。
在国外,欧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世界旅游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以色列的阿里和奥迪和美国的阿当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位于农村区域的旅游。科若克认为“乡村(是)一种特殊的居住地;乡村社区(是)买卖的背景;乡村生活方式可以被移植;乡村文化的生活画面可以被加工、整体推销和出售”*ClokeP.,“Policy and Change in Thatcher’s Britain”,Oxford: Pergamon Press,1992,p.25.。同样,国外研究也大多将乡村旅游的本质归结为乡村性和文化性。
(二)从乡村旅游动力机制入手论本质
从动力机制入手探讨本质问题,国内可大致分为三派:一是怀旧主义。熊剑峰认为,“当旅游成为时尚,传统被再次认可、推崇,便不难理解由怀旧引发的怀旧旅游其最终的指向即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其最终之目的即对抗现代性对主体的异化,保持主体自身的本土感和本土性”*熊剑峰:《怀旧旅游解析》,《旅游科学》2012年第5期,第35页。。左晓斯认为“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都市社会的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面临经济的、社会的、环境和精神的四大危机,这些危机触发了人类灵魂深处的逃避主义本能,记忆中的田园牧歌开始产生魔力,这种怀旧情结成为今日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推力,这在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左晓斯:《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研究——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二是逃避主义。左晓斯对此则有系统性的研究,他认为“逃避主义成为应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一团的当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张力的最常用策略”*左晓斯:《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研究——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第96页。。三是体验主义。国内旅游体验研究开端于谢彦君,而后不少学者对此开展了不同深度的研究。彭兆荣认为“乡村旅游与地方性知识的吸引力有关。因为乡村可以被看成与传统文化的发生、与环境建立起来的自然关系以及‘面对面社群’的基本单位,对‘地方性’具有特殊的说明意义。他认为游客在乡村旅游可与传统和自然保持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享受宁静祥和的氛围,到大自然‘氧吧’获得身心的快乐健康。也可以是对都市喧嚣、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的淡薄与疏离的一种暂时的逃避。也可以是到乡村去体验和体会一种‘怀旧’的感觉;毕竟‘乡下’可以成为人们记忆中与‘过去’联系在一起的场景”*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第7页。,他认为“‘乡村魅力’对于都市人群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其意义更多的或许并不是让游客换一个‘地方’,而是换一种体认的‘价值’……游客在乡村旅游可以与传统和自然保持近距离的‘亲密接触’,享受宁静祥和的氛围,逃避都市喧嚣、快节奏的工作压力,暂时解脱现代社会淡薄与疏离的人际关系,体验和体会‘怀旧’的感觉”。
国外对乡村旅游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有逃避、怀旧、体验、学习、追求自由、生命的自我实现,等等,有些旅游动机是单一因素促发,但大多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同样,国外研究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是逃避行为。格雷本认为旅游者大多处于渴望逃脱当时当地的生活的心态。柔杰克则把旅游看成是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解脱方式。此外,科恩和泰勒也将旅游视为一种逃避行为。第二是怀旧情结。在旅游研究领域,对于“怀旧”这一主题的关注最早要追溯至布尔斯丁提出的“伪事件”,他将旅游视为一种失常的行为和时代的病症。纳什强调了旅游现象中的角色冲突问题,“旅游者在游玩、休息、治疗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其他人却必须工作、服务,这就是一种‘社会壁垒’”*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中译本修订版),张晓萍,何昌邑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怀旧”这一概念,但他的研究中已经认定了怀旧这一因素,他认为去殖民国家旅游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带有对旧殖民主义的一种“怀旧”。还有很多学者也认为旅游的核心隐喻是怀旧*纳尔逊·格雷本:《今日东南亚的旅游与人类学:几点比较》,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第三是朝圣、体验和寻求意义等。首先是朝圣说和仪式说。体验与“真实性”有关,麦坎内尔认为“旅游者是宗教朝圣者的现代化的化身,追求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董培海,李伟:《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旅游学刊》2013年第4期,第112页。,这是关于旅游是一种朝圣的说法。而格雷本将旅游看成是神圣的仪式。其次,多元体验说。科恩较早将“旅游体验”引入到旅游研究中,他将旅游体验分为“追求愉悦为目的和追求意义与真实性为目的的两种体验”*Erik Cohen,“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Sociology, Vol.13,No.2,1979,pp.179-201.。尤里认为旅游是体验一种异乎寻常。最后是意义说。科恩认为,“旅游就是在寻求一种意义的满足”*John Urry ,“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London:Sage,1990,pp.1-20.,格雷本认为旅游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
综上所述,学者们得出“乡村性和文化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的结论,这显然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观点,如左晓斯所总结的“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乡村性是吸引旅游者进入乡村旅游的基础,也是乡村旅游营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是区分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类型的最重要标志”*左晓斯:《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乡村旅游》,《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81页。。然而,有人提出了质疑,“事实上,这两种取向都以游客的观念、动机或行为为关切的焦点。也就是说在对旅游本质的问题上,学者们注意的是‘输出社会’的集体意涵的分析,而较忽略对‘接受社会’的探讨”*张廷国:《现象学不是什么是什么》,《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第8页。。其言外之意是已有研究仍将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表象来看待,并未对其本质进行深刻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乡村旅游的本质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挖掘。
三、乡村旅游的真正本质:“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
(一)旅游本质等同于乡村旅游本质吗?
在《诗·语言·思》一书中,译者说道“诗意和非诗意构成了人的存在和非存在,真理和非真理的绝对界限。非诗意的居住不是作为人真正的存在,它只是人自身无希望的繁殖。人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和对名声的疯狂追求,这在根本上背离了人的居住本性。它只会打破人居住的四维原一,从而征服大地,掠夺天空,远离神性,丧失了作为短暂者的存在。这样,世界幽暗、万物消失”*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杨振之借用“诗意栖居”凸显出游客从旅游中捕获的性灵上的感悟和体验,与理性、推理和逻辑不同,他认为“旅游的体验归根结底是心灵的感应,而心灵的感应是不可计算的,心灵的不可见性比逻辑的计算性更加不可测知”*杨振之:《论旅游的本质》,《旅游学刊》2014年第3期,第19页。。他从“存在主义”高度出发,将“人”置于旅游中的主要位置,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关于旅游本质较为精准的判断。乡村旅游同样是一种存在形式,从存在本体论来解读乡村旅游的本质,这是一种较好的思路。然而,如果将“诗意栖居”也视为乡村旅游的本质,这是否妥当呢?笔者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旅游包括乡村旅游和非乡村旅游,因此,杨振之主要从旅游者角度定义旅游的本质,忽视了“诗意”的生活方式“栖居”在谁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他只阐释作为栖居者的游客主体,而忘记了被栖居者是作为另一个主体而存在的,这另外一个主体就是当地人。当地人及其携带的地方性知识是人存在的意义之所在,是栖居的载体和依附所在。缺少了他们,“栖居将依附于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当地人在当地的环境中“诗意栖居”,文化是当地人长期诗意栖居的结果,这是乡村旅游的前提和基础,亦即没有一种真正的他者文化,乡村旅游也就是一种“伪旅游”。因此,乡村旅游的本质需要注意到“关系主义”。
(二)乡村旅游的本质:“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

延续杨振之提出的旅游本质是“诗意化栖居”的思路,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兼顾“存在主义”和“关系主义”的双重优势,这一论断兼顾了“输出社会”和“输入社会”,但更多侧重于后者,即长期栖居的当地人才是诗意化的关键主体,而作为短暂栖居的游客则是一般主体。
梭罗在《瓦尔登湖》有一段话,“接受和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将使我们重返人类家园,回归于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慢步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孙凤:《社会治理要关注消费文化建设》,《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第11版。。同样,孟德拉斯曾在《农民的终结》中写道“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的幻梦”。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在真切地传达着人生的真谛,而这也是乡村旅游的真谛。乡村旅游应该是:一种价值至善和人文关怀的理念;一种社会良心、社会责任和谋求福祉的行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笔者认为“主体间性的诗意栖居”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包含着“当地人的长期栖居”“旅游者的短暂栖居”及两者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场”。
“主体间性”是哲学的一个概念,是关于主体与主体间的一种关系。哈贝马斯将其运用于社会学领域中,他提出的交往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主体间性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而在乡村旅游中,主客之间在文化上同样是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而非一方压倒另一方。然而,文化是有关键指向的,否则文化对于游客而言也仅仅是供人观赏的吸引物而非体验的生活方式。当地人居于关键主体的位置,而外地游客则居于一般性主体位置,两者互动而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场”。
“我认为我们需要到农村地方进行旅游,就是去寻找一种价值和动力,我们很尊重当地的一些习俗和文化,喜欢跟本地人聊天。他们也会问我们一些问题,比如来自哪里的、有什么好玩的、人们讲什么话等之类的。通过平等聊谈,我们对旅游地就会有一种好感,就会推荐朋友也来玩。有时候也邀请当地人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来看看。”(游客,小樊)
“现在大城市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在钢筋水泥铸造的楼房里,很压抑,再加上平时的工作快节奏快,这也让人崩溃,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自由自在、和谐美好的地方来释放压力,进而提升自我,最后完成人生的一次蜕变”(河南游客,小康)
“工作一周了,身体是超负荷的运转,心里也会跟着很累。周末了,我喜欢去乡野看看,挖野菜、爬山、抓鱼、参加地方的一些民俗活动和表演。旅游的日子是很幸福的,感觉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回来后工作干劲十足,像打了鸡血一般。”(上海游客,小易)
游客们质朴的话语也透露出笔者的基本判断,这里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层面,谁具有诗意栖居的权利?即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这里不仅包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当地人,文化是他们祖祖辈辈保留和衍生下来的,是他们长期栖居的结果。此外,游客也理应享有诗意的栖居权,过一种短暂的、没有包袱和负担的诗意生活是他们进入到异质环境中的真实需求。“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大自然虽是一种原生态的东西,但多少令人感到有些乏味,因为人无法和大自然对话,即便你刻意用镜头去捕捉自然,或组织营火晚会去干扰自然,它依然是没有反应的。另一种接近大自然内部的方法则是与‘大自然之子’——那些被曾经称为土著或原始族群的人——接触,他们被认为是本能地生活着的人,与这些人交往是可能的。他们的自然与纯净体现了大自然本身的一切基点,还有什么比与这些可爱的人同吃同住、共交谈更令人向往和振奋呢?”*纳尔逊·格雷本:《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我每到一个地方,很喜欢跟当地人聊天,当地人很热情、也很聪明。聊天可以让外来人很快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会问他们本地人吃啥、喝啥、有什么节日活动、孩子们是如何教育的、有没有不赡养老人的情况等。如果找不到当地人,我就自己到处看看,不跟旅游团,跟着旅游团很不自由,出来旅游,就是应该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领悟地方人的智慧和热情。跟团的话,像有一根绳子捆在身上,如同被束缚住了一样”。(山西游客,小达)
由此可知,乡村旅游的本质蕴含一种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态度,一种对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一种对自由追求的崇高境界。
第二层面,诗意栖居的关键性主体是谁?如果说第一层含义区分出了旅游主体性的问题,那么第二层含义则对主体进行关键主体和一般主体的划分。关键主体是比一般性主体更加重要的主体。在乡村旅游语境中,关键主体是当地人,是他者的文化,是在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交汇中的地方性知识库。何景明指出“在发展策略上要变给予游客们想要的为生产我们能出售的”*何景明:《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旅游学刊》2003年第1期,第79页。,他的言外之意并非是真正生产和出售异域文化,而是要始终保持他者的关键主体位置,他者及其文化是乡村旅游之“根”,缺少了它,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消失了,同样,乡村旅游也就不再是乡村旅游了。关键主体和一般主体的区分并不是要在主体回归到主观意义的主客之分上,因为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是要更加强调和凸显旅游本质研究中忽视了的“当地人”这个十分重要的群体。
“我认为乡村旅游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展示一个地方特殊的风景、文化和人,应该被好好保存,因为这些都是值得珍视和回味的东西,都是有着人类深刻印痕的珍品,一旦丢失,也就永远逝去了。只有保存好这些了,我们才会真正愿意去看,如果都像是大城市的灯红酒绿,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什么好看的。我们需要吃饭穿衣,但我们也更需要诗和远方,那么,到哪里去找寻这些东西呢?那就是去乡间看看,去民间走走,边走边逛,饱览跟大城市容纳的不一样的异域风情,通过观看和欣赏寻求内在的宁静和性灵上的升华。”(北京游客,小曹)。
第三层面,游客和当地人互动所形成的一种新“结构场”。将大写的“人”凸显出来,这里的人就不仅仅指游客,也指当地人,还指两者在一个时空下充分互动而生成的一种“结构场”。当地人及附属的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根”,如果当地人缺失了,文化也就丧失了传递的载体。因此,文化之“根”是需要得到保护的,但“根”的保护需要得到外来游客的不断浇灌。
“我去农村地方旅游的一个最主要目标是看文化,看当地人和我们的文化有何不同。我认为文化这东西是相互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化,所以,一个地方的文化再好,也是需要变迁的,不然的话,就成老古董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这样的,需要跟别的地方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新型文化才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我们不担心文化会消亡,因为只要我们不断交流,新型的文化就会不断产生”。(河北游客,小张)
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和当地人始终不断地交流、谈话和互动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场”,在这个“结构场”中,有异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还有两者交汇后形成的第三类文化,“结构场”让旅游地更加具有持久生命力。
四、结 论
如何定义乡村旅游的本质,这是乡村旅游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本质研究贯穿始终,在研究范式上经历了从“主客关系”到“主主关系”的转变。现象学属于哲学范畴,对本质问题探究较为深刻。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源于“存在主义”的新高度,另一方面源于一种“关系主义”的优势视角。因此,将现象学的视角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意味着对旅游本质的真正探讨。与体验、逃避和怀旧等主流意识不同,杨振之基于“存在主义”的高度提出了旅游本质是“诗意化栖居”的观点,将旅游研究的关注点从“物”拉向了“人”,这就将旅游本质问题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受其启发,一方面,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是旅游的子系统,用杨振之关于旅游本质是“诗意化栖居”来关注乡村旅游的本质是较为妥当的。乡村旅游也同样是“人在旅游中”,需要规避风险和伤害,摆脱困境,获得平安和安全,享受自在和闲适,领悟神圣和灵性。另一方面,乡村旅游毕竟不是旅游,附加了“乡村”二字,因此,乡村旅游本质也需要在旅游本质大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框定和补充。杨振之在凸显出“人”的同时,也将“人”这样一个概念局限于小写的“旅游者”群体忽视了“当地人”,即忽视了“旅游者-当地人”主主间的关系形态。因此,这里的“人”应该大写,不仅仅指游客,也指当地人,还特指两者互动而形塑的一种“结构场”。当地人及附属的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根”,没有这些当地人,文化就丧失了流传的载体。而旅游者和当地人通过互动会产生一种新的“结构场”,这是旅游地生命力的表征和彰显。因此,笔者提出“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是乡村旅游的本质。
总之,兼顾“存在主义”和“关系主义”的双重优势视角,本文提出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的判断。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彻底和完全的创新,也并非一种新的发现和突破,而只是在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上的一种尝试。将“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概念引入,并不仅仅是为了区分乡村旅游本质与旅游本质的根本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关系主义”的新优势而拓展对乡村旅游本质的认识,打破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影响的二元性,强调两者之间在互构基础上的二重性。在这种视角的关注下,乡村旅游的本质更加强调“当地人-旅游者”之间的一种平等、互动和协商。
RethinkingtheNatureofRuralTourism
ZHANG Jin-feng1, XIE Xiao-qin2
(1.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Chi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The issue of nature, to some degree, runs through Western philosophy, whose paradigm of study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 to “the subject-subject relation”. Phenomenology belongs to philosophy and inquires the issue of nature more profoundly, which results from both the speculative status of “existentialism” and the advantageous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Yang Zhenzhi proposes that the “poetic dwelling” is the essence of tourism, largely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ourism essence,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relationalism”. Rural tourism is a form of tourism, but is different from tourism. Hence, the exploration of its essence, while further extend the height of “existentialism”, should also highlight the “relationalism” between the “tourists and the local”. “Intersubjectivity”, as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analyzing the “subject-subject relation”, attempts to break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reshape their duality relation. Accordingly, a judgement is make that the “poetic dwelling with intersubjectivity” is the nature of rural tourism.
nature; rural tourism; intersubjectivity
G 05
A
1004-1710(2017)05-0061-07
2016-12-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MZ067);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计划研究项目(ZK1091);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研究计划项目(17JK0023)
张金凤(1978-),女,宁夏中宁人,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乡村旅游、旅游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吴晓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