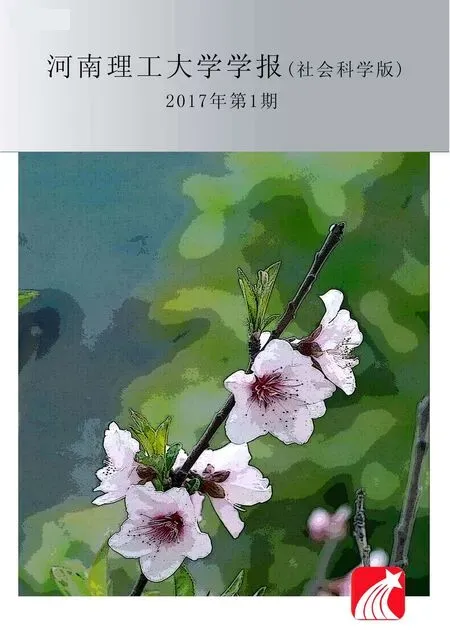《小鲍庄》的叙事艺术
2017-02-23史玉丰
史玉丰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小鲍庄》的叙事艺术
史玉丰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小鲍庄》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了寻根的故事,更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对神话的借用和置换形成了它宏大的书写视阈与审美气象,运用反讽艺术在显性和隐性的双重话语对峙中发现了失根的历史真相,通过多重象征意蕴探讨了人类命运、人类苦难、人类文化等宏大命题。在寻根与失根之间,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现实思考与文化焦虑。
小鲍庄;神话叙事;反讽;象征意蕴
王安忆1985年发表的小说《小鲍庄》是一篇“旧”的小说了,但它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小鲍庄》时,发现《小鲍庄》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寻根的故事,还在于它讲述故事的方式:对神话的借鉴和运用形成了它宏大的叙事视阈和审美气象,使作品具有辽阔性和神秘感;运用反讽艺术在文本中形成显性叙事和隐形叙事的话语对峙,让我们在寻根和失根之间做出深入思考;多重象征意蕴逐层深入挖掘,使作品具有纵深感,表现了作者对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现实思考与文化焦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 神话借鉴
(一)神话结构的借用
中国小说的神话结构由来已久,《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虽然如研究者所言,书写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历史和宋代水泊梁山农民起义的历史,但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却都是套用了神话:女娲补天炼五彩石以补苍天,剩下一块不堪大用,遗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而整个《红楼梦》便是由“一块石头引发的故事”;《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是天庭108个神仙下凡,由此引发的人间动荡。神话结构将浪漫与现实、幻像与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意蕴和抽象视界,从一个更为宏远的空间视阈里审视社会人生,《小鲍庄》也是如此。
《小鲍庄》本来是书写一个村庄遭到洪水的灭顶之灾、一个孩子为了照顾孤寡老人而牺牲的故事。故事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因为套用了神话结构,便使得一切都不寻常起来,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和宿命感,在美学上形成一种厚重的复杂意蕴,将小鲍庄的故事链接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也将其中的人物形象推向传统文化的源头,使之具有一种深刻的纵深感。正如学者所论:“宗教的神话模式的运用,不但使这部小说增添了现实的讽刺意义,而且超越了一般农村题材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容量,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人类苦难等一系列永恒主题的作品。”[1]
(二)神话意义的置换
1.洪水神话的置换
(1)由获罪—赎罪的转移。在鲧治水神话中,鲧窃取天帝息壤治水失败,遭到天帝的惩罚,天帝派祝融去将鲧杀死,显示了天神对人的惩戒。而在《小鲍庄》中,小鲍庄的祖先因为治水失败而自我惩罚,是为了赎罪才搬迁到低洼处而形成了小鲍庄。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洪水神话从获罪到赎罪的置换和迁移,说明小鲍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这是他们生活中一切苦难的源头。其中除了他们祖先的赎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捞渣了,他生来具有强烈的原罪意识,他的出生带有了赎罪的意义:一个孩子死了之后,他出生了。他的行事方式就是救赎,对鲍五爷像亲爷爷一样,对待他人一律好性子,像他的祖先一样,带着赎罪的姿态。
(2)由再生—死亡的转移。在东西方的神话中,洪水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也提供了英雄出现的大背景,并由此完成“拯救—再生”的意图。“显然, 洪水神话是世界的神话母题, 而且往往与人类的再造有关。世界许多民族的洪水神话都与创世神话连为一体, 其普遍的叙事程式是:创世—造人—人的罪过—惩罚性洪水—再创世。”[2]328在神话的“再创世”中,洪水的产生多是一种惩戒行为,是神涤除人间罪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洪水过后,绝大多数有罪之人死亡,品德良善之人仅存于世并且繁衍人类、发展世界,例如西方诺亚方舟以及中国葫芦造人的故事,都是新生的过程,“洪水象征着旧的历史时期的告终和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3]28。小鲍庄第二次洪水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天帝惩罚人类的一种体现。正如文中一再强调和宣扬的,小鲍庄是笃信家常伦理、具有传统儒家精神的村子,民风淳朴,极讲仁义。然而我们却在背后看出了有悖于仁义精神的现实行为,从疯妻、小翠以及拾来等人的遭遇中,我们看出小鲍庄人实在谈不上具有儒家仁义精神。从这个层面上说,捞渣的死亡不仅仅是救鲍五爷,而是救那些已经沦落的灵魂;捞渣的死亡结局使得二次创世神话发生了置换转移,也向我们昭示了儒家仁义思想的崩溃和消失,预示着一个真正的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
2.替罪羊神话的置换
替罪羊来源于圣经旧约故事,古犹太教每年举行赎罪祭祀时,要用羊来代替人类的罪过而被杀死和驱逐,羊以自我的牺牲来完成人类灵魂的救赎。在东西方的民族文化心理中,不乏替罪羊原型,例如中国也有献祭童男童女给河神或者妖魔鬼怪以免除灾难的神话传说。替罪羊原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反映,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书写,在《小鲍庄》中也得以体现。第二次洪水之后,代表着仁义精神的捞渣牺牲了,而其他有罪的人却活了下去,并且因捞渣之死获得了现实的物质利益,摆脱苦难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和二次洪水神话的内在精神是相违背的,这就使得捞渣成为带走小鲍庄罪恶和灾难的替罪羊:捞渣死后,他的“坟上长了一些青青的草,在和风里微微摇摆着。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在啃那青草”[4] 325-326,“雪白的小羊羔”这一意象再一次点明了捞渣“替罪羊”的身份。然而捞渣的死虽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却并未净化他们的灵魂,虽然他们已经逐步摆脱生活困境,人人如愿:建设子转正娶妻,文化子和小翠有情人终成眷属,鲍仁文得以扬名,鲍秉义摆脱疯妻……小鲍庄以捞渣之死使仁义之名继续远播。然而,精神的堕落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似乎已经无可救药,“捞渣的墓迁到小鲍庄正中来了,又大又高,像一座房子。砖砌的,水泥摸了缝,再不会长出杂草来了,也不会有羊羔子来啃草吃了”。在捞渣的英雄形象建立起来之后,代表赎罪的“洁白的小羊羔”却再也不会出现在这座墓碑之前。人们纪念着捞渣,却不肯从自己家拿一把扫帚来扫墓,怕沾染了“鬼”的晦气,这就使得捞渣的死亡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牺牲,也使得寻根行为变成一场失根体验,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仁义精神的式微和衰落,这让我们对失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充满疑虑和担忧。
二、反讽叙事
在中国和西方神话中,英雄拯救世界之后奏响的是胜利的凯歌;而在《小鲍庄》中,却没有这种胜利的喜悦,相反还有一种悲剧的隐忧。王安忆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运用了反讽的艺术技巧。
于全麻下采取腹膜后腹腔镜下右肾癌根治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右肾透明细胞癌I级”。术后留右肾窝引流管,两天后拔除,常规补液抗感染止血对症治疗,术后第七天拆线,隔一天出院,术后连续3年CT检查无异常。
(一)隐性叙事
在遥远的历史与当今现实之间,王安忆一再强调小鲍庄的“仁义”:鲍彦山收养了要饭女小翠,鲍秉义照顾疯妻,二婶和拾来破除世俗偏见勇敢结合,还有小英雄捞渣一系列的仁义之举 ……然而,在文本的隐性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捞渣,小鲍庄人的仁义实际上是大打折扣了,呈现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在捞渣仁义的对立面,是小鲍庄人的自私、虚伪、抓奸、狭隘、逼婚、遗弃、仇视外姓人、毒打老婆导致疯狂、遗弃亲人等。鲍彦山收养小翠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盘算:小翠再过几年就会成为家庭的劳力,没有教育费用,节省结婚费用。“童养媳”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对妇女的戕害表现之一,但在捞渣父亲这里,却成了仁义的行为。当我们去考察小翠内心的时候,觉得捞渣的父母对她的严苛甚至有虐待的嫌疑,鲍彦山家里的完全把小翠当作一个劳力,限制她的精神自由,不让小翠唱歌,她害怕小翠长大之后远走高飞,就拼命使唤小翠,似乎要在鸡飞蛋打之前把本捞回来。鲍秉义照顾疯妻的名声被鲍仁文传播出去之后,内心却怨恨着鲍仁文:“就是他想离也离不成了。就这么凑合过吧,只是鲍秉德一日比一日话少,成了个哑巴。”[4]257这与他后来迫不及待再娶之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再娶之后他兴奋得几乎成了话痨。而且我们看到,鲍秉德对于之前不能生育的疯妻,不仅用暴力使她发疯,还用冷暴力对她进行精神虐待,这就使得疯妻在清醒的时候产生巨大的负罪感和内疚感,为她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与其说后来的洪水给疯妻提供了一个自杀的机会,不如说鲍秉德早就用拳头和冷暴力将她杀死了。
(二)他者视角
以拾来这个外乡人的遭遇来剖析仁义精神,更可见其反讽之处。小鲍庄人对他采取排斥甚至迫害的态度让我们看到,在以“仁义”自居的文化中,包含着对人性和情感可怕的戕害的一面。当鲍仁文津津乐道宣传拾来和二婶爱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无奈的现实因素。爱情并不是二婶和拾来的全部,二婶更多的是看中拾来的年轻能干和老实善良,可以为二婶一家人缓解燃眉之急,她很大程度上是拿拾来当壮劳力使唤的,这也导致了拾来以后的离家出走;而当拾来打捞捞渣尸体出名之后,与二婶经常关起门来干架,已经与爱情相距甚远了。
(三)捞渣遭遇
捞渣的出生本来是意料之外的,人们并没有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日后的仁义行为虽然得到人们的夸奖,但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损害”的地位;他最后救助鲍五爷,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天性,从来没有想到要“英名远播”。当他死后被塑造成“小英雄”并迁坟之后,人们对于他的思念和感恩却已经大大让位于实际利益获得的喜悦,人们从内心里并没有将他当作一个神圣的英雄、而是当作“少年鬼”来对待的:捞渣的所有衣物用具都已经被烧毁,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证是在将要倒塌的厕所墙上刻下的名字。捞渣死后大家虽然去扫墓,但那不过是表示没有忘记恩德的做秀,人们甚至不愿意从自己家里拿来扫帚扫一扫,认为那样会沾染了鬼的晦气。捞渣所代表的仁义精神在现实中也逐渐衰微。
这种反讽的形成,是通过文本中相互对峙的两种话语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作者一边用正史话语建构仁义精神的中国形象,一边又用野史话语或民间话语进行了解构,形成了叙述本身相互对抗的矛盾和紧张关系,显示出《小鲍庄》显性和隐性的书写与价值评判,让我们陷于幻象与真像的吊诡:这到底哪个更权威,更反映了历史的真相?如果正史是宏大叙述,从主旋律角度来阐释历史,那么野史则从某些细微的方面反映了人性和人间的真实;或者说,两者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共同触摸了历史。在正史的光环之下,野史呈现出人性的瑕疵甚至人性的阴暗,一样故事,两种笔墨,王安忆在书写中对自己提出了挑战,这种叙述的吊诡性带来了丰富的文本张力,表现了王安忆对于苦难、赎罪、信仰等伦理问题的焦虑和关注。在历史的崇高影像之下,折射出现代人生活信仰的危机,这危机不光是指传统仁义精神的匮乏和崩溃,更在于现代人对待信仰危机的方式:任意拔高而不是深刻反思,用虚假的美好代替残破的真相,必将走向生存的困境。这反映了王安忆对宏大叙事合法性的反思和质疑,当她从微观的层面去反观传统文化时,发现生命的崇高与卑微同生、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共存,当她将这些“中国形象”放置在现代性背景下,就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宏观视野,对政治话语的逃逸和挑战显示了王安忆对自我的超越,开启了她塑造个人形象的新的美学手段和文化方式,显示了那个在历史中以“崇高”为名的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在王安忆的自述中,再一次彰显了小说的伦理、美学追求和写作目的:“其实小鲍庄恰恰是写了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我的基调是反讽的。那个结尾很重要:许多人都因捞渣之死改变了生活。比如鲍秉德重新娶妻,拾来也找到了冲破成规的机会,文化子娶了哥哥的童养媳为妻,这些在农村都是犯大忌的!鲍仁文也借捞渣的宣传满足了作家梦的幻想,等等。我想,捞渣是一个代大家受过的形象。或者说, 这小孩的死, 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 许多人从捞渣之死获得了好处, 这本身是非仁义的。”[5]31-32在仁义精神被大肆宣扬的同时,仁义之心的内核即对人、对动物、对生死的大义大爱却被忽略了,这显示出作者内在人性立场和传统文化立场的矛盾和分歧,更能够说明她反思的力度和深度。
三、象征意蕴
(一)小鲍庄象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小鲍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象征,空间逼仄,时间停滞,几十年如一日。小鲍庄的文化也呈现封闭状态,生活在其中的子民都是大禹的后人。小鲍庄同时又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具有博大的文化意识,是民族文化的积淀与载体。文本开篇引子和结尾颇耐人寻味,引子和结尾不仅是《小鲍庄》的重要内容,而且勾勒了文本的圆形结构,是从总体上对小说的观照,它不仅介绍了小鲍庄的历史来历,昭示了小鲍庄日后的历史命运,而且成为小鲍庄人命运的一种象征:“一头一尾, 一个象征着小鲍庄苦难的开始, 另一个象征着小鲍庄苦难的结束;一个象征着人类的原罪, 另一个象征着人类的赎罪;一个强调在洪水中生——那官儿在洪水期间生了三男一女, 标志了灾难的开始, 另一个强调了在洪水中死, 而他的死却消弭了小鲍庄的种种灾难。”[1]
(二)捞渣象征仁义精神
小鲍庄作为传统中国的缩影,是具有仁义精神的村子,其中最仁义的人是捞渣,他的身上全方位体现着儒家的仁义精神: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捞渣成为小鲍庄人的仁义楷模与价值标准,是千古仁义精神的化身,他的品质是与生俱来的,而非道德教化的结果。捞渣像是中国仁义精神的活化石,以此来教导人们仁义精神的真正含义:他待人和气,对别人总是忍让,只要对方高兴,他就高兴;他有好生之德,珍爱和尊重一切生命,虽然心里很喜欢蛐蛐,但还是高兴地把它放生;他虽然不是鲍五爷的亲孙子,但是对鲍五爷却像亲爷爷一般,陪着鲍五爷度过艰难孤独的时光,后来为了救鲍五爷,自己被淹死在树下……他承载的既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真正的仁义精神,也很好地继承了小鲍庄祖先赎罪的精神意旨。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捞渣的活着和死去都带有象征意味:他以牺牲自我来完成了小鲍庄人的救赎。从表面上看,这种拯救确实完成了,但小鲍庄人的这种得救仅仅是世俗的得救,一旦解脱了仁义这个紧箍咒,小鲍庄人的苦难似乎在瞬间消失瓦解。虽然是带着原罪出生,但小鲍庄人从来都没有一种赎罪意识,除了捞渣。小鲍庄人对于苦难的态度是痛恨,是诅咒,他们早已忘记了先民建立村庄的初衷以及他们来世间的赎罪任务,所以才会以苦难为负担。因此,作为“最后一个”的捞渣本身既体现了仁义精神,也见证了民间仁义精神的匮乏。作为仁义代表的捞渣一旦死去,也预示着仁义在小鲍庄的远离,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以仁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捞渣的过渡性和“最后一个”的意蕴不言而喻,伴随着捞渣的死亡,一切皆告结束,一切重新开始: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也开始进入“无根” 时代,在众人皆大欢喜的背后,是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枯竭、仁义崩溃的隐忧。
我们看到,逐渐拥有现代意识的小鲍庄人从封闭走向了开放,打开了从神话到历史、从远古到现代的口子,这不仅仅是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标志着时空意识的转变。历史从空间形式转变为时间形式,从共时状态转变为历时状态,标志着神秘、恒久的神话品格的消失和现代理性品格的开始。人们从对虚妄仁义信念的坚守到对实际利益的追寻,使小鲍庄从此踏入现代化的滚滚洪流,在追逐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在它将神话品格丢弃的刹那,我们也看到了民族失根的严重精神危机。
(三)洪水的象征意蕴
在《小鲍庄》中,洪水代表着四重意蕴,第一重代表洪水灾难,第二重代表人类重生,第三重代表政治灾难,第四重代表文化灾难。就灾难的程度来说,呈现出一个逐渐深化和逐渐严重的过程。
首先,小说象征性地再现了人类上古时期洪水的情形:“汤汤洪水方割, 荡荡怀山襄陵, 浩浩滔天。”[6]4洪水涤荡了一切,造成了人类历史的灾难,将世间万物全部纳入其魔掌之下,引出了小鲍庄祖先治水的故事,也开启了小鲍庄的苦难历程。
其次,洪水神话也代表着人类的重生。洪水是天帝对人类的一次惩戒行为,在中西神话中,都有二次洪水的情况发生。为了惩治人类的堕落和罪恶导致的社会无序和混乱,天帝再一次发动了洪水,但这次洪水除了是一场灾难之外,也是一次选优择善的行为,洪水过后,优良人种劫后余生,继续新的生活,创造新的世界。
再次,洪水代表着“文革”政治洪水。结合小鲍庄故事发生的年代,我们还可以看出,洪水在文本中还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即“文革洪水”,这一层象征意蕴是隐藏的,直到作者点出“在一千里外的北京,正进行着一场江山属于谁的斗争。一千里外的上海,整好了装,等着发枪了”[4]265。这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洪水”已经蓄势待发,与封闭的停滞的小鲍庄的时空形成鲜明对比,“文革”的暴力、非理性摧毁了人们关于人性与生命、生活的基本信念,为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洪水象征着新的社会思潮,即随着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商业文化大潮和现代文明。它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再创过程,而是一个涤荡和毁灭过程。如果说“文革”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有意识的灾难,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是一次由政治层面引发的文化断根的浩劫还是一个“伪命题”的话(因为“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很快进行了反思,进行了有意识的寻根,《小鲍庄》也被列为此列),那么随之而来的现代文明则是以一种无意识的侵袭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将这个伪命题变成了真命题:商业文化大潮正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冲洗涤荡着古老的中国文化,使之真正具有了断根的危机。这场唯利是图、以金钱和利益为基本导向的文化冲击波迅速地蔓延到小鲍庄,蔓延在神州大地,而代表仁义精神的捞渣已是斯人远去,他所代表的仁义精神也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这场外来的现代文明洪水的入侵,给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生带来了危机与挑战。
四、结 语
《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表现了“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7]116。但它并没有将寻根的笔触伸向“不规范文化”,而是寻找到儒家仁义神话的古老渊源,从而使得寻根文学具有了神秘莫测的神话品格。王安忆以现代意识为支点,在正史和野史的纠缠中,在虚构和真相的吊诡中,探索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续存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严峻性。当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人去寻根的时候,却发现了“根”的千疮百孔、逐渐衰微和丧失,与其说是一次寻根旅程,不如说是一次失根实录,王安忆通过她的作品反映出的现代精神危机和文化焦虑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1] 陈思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1986(1):16-18.
[2]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4] 王安忆.小鲍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5] 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6] 尚书[M]. 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
[7] 韩少功.进步的回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位雪燕]
The narrative style inBaoTown
SHI Yufeng
(SchoolofLiberalArtsandLaw,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The meaning ofBaoTownnot only lies in the story of seeking roots, but also its narrative style: forming a grand writing perspective and aesthetic style by borrowing myths, 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losing roots” by employing ironies in explicit and implicit discourse confrontation, and discussing such issues as human destiny, human sufferings and culture through multiple symbolizations. It showed the author’s pondering over the culture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cultural anxiety through “losing roots” and “seeking roots”.
BaoTown; myth narrative; irony; symbolic implication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1.010
2016-12-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ZX03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qn-645)。
史玉丰(1977—),女,山东平度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mail:ssyyff658@163.com
I207
A
1673-9779(2017)01-0054-06
史玉丰 .《小鲍庄》的叙事艺术[J].2017,18(1):054-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