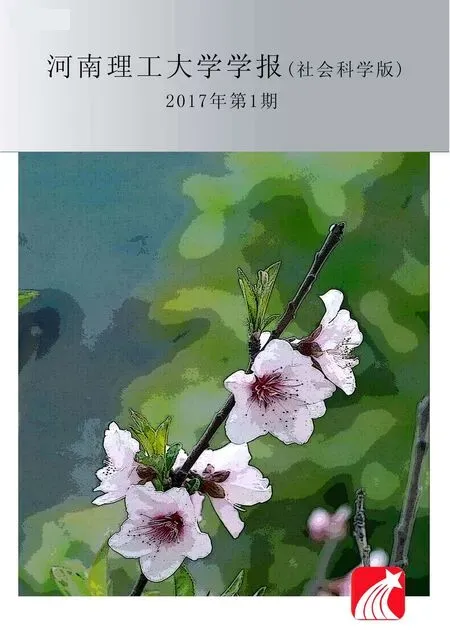衔接与动态透视: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
2017-02-23杨威
杨 威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衔接与动态透视: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
杨 威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教育根植于文化,同时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信息导向性,使得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发展成为了可能,“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将传统文化引进现代课堂教学。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教材开发权利的下放使得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成为可能,而民族文化的地域独特性,教材的科学性、严谨性等特征也要求具有媒介价值教材的开发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在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动态开发过程中管理协调至关重要,管理协调的内容包括教材开发标准的设定、教材开发的特殊性、教材开发的原则、开发过程全环节及保障性机制的完善等方面,为保障教材开发的合理性,应对各环节严格把握,管理到位。
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
西方学者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就其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1]作为“类”生活经验集合体,文化是“类的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的区别,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揭示了人的社会性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文化即人化[2]。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是其最持久、最稳定的联系。作为各民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智慧结晶的文化,是共同的民族心理形成的基础,是民族区分性最明显的特征,它产生于劳动人民生活的那片土地,是各民族人民与自然和社会不断斗争的产物。作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鲜明的民族展示特色、独特的延续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凸显[3]。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民间传统文化、技术知识等工艺文化、信仰崇尚文化、节日文化,教育催生文化的形成,创造文化,推动文化[4]。潘定智认为,民族文化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交通运输文化等;二是制度文化,包括社会形态、社会建构、传统习俗、节日文化等;三是符号文化,包括语言文化,文字文化等;四是宗教祭祀文化,包括鬼魂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五是文学艺术文化,包括文学、歌曲、戏曲、美术、工艺等[5]。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实现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提供服务的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基于宏观视角来看待目前已开发出的此类教材,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将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用于编排包含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内容的教材,以实现语言传承与文化普及的目的,此类的典型代表有云南省剑川县实施的“零障碍项目”“白汉英三语教学”和榕江县栽麻乡宰荡小学[6]。二是用汉字形式描述、记录、解释本民族文化,此类教材广泛使用于贵州省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中所开发的教材,较易为大众所接受。鉴于研究需要,仅以第二类教材的开发过程为理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尝试将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定义为:由民族地区的学校依据师资特长及地域文化资源优势等实际情况,以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目的,依靠本校教师、民间艺人等文化资源开发主体,挖掘整理开发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资源,依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教材编排顺序将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归类而形成的媒介,是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实施的重要媒介,在此将其界定为狭义的纸质式教材。
一、教材开发过程的特殊性表现
作为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经验总结的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其开发过程与一般校本教材有共同的因素,如教材开发队伍人员的配置、相应的经费划拨等资源保障性条件;但是,民族文化的不可复制性、地域独特性等特点也就要求其教材开发过程具备相应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教材开发主体:社会多样化群体参与
国家统一的课程教育体系中,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以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家庭、社区和村寨是其进行民族文化学习活动的主要场域;然而,商品经济大潮来袭带来的是大量成年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社会教化功能的重心开始由家庭转移到学校,然而,民族地区教师能力的有限性显然无法保障开发教材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他们虽然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条件下,就非常有必要吸纳教师主体之外的力量参与教材开发。
另外,民间艺人手中掌握着本民族的特殊技能,其技能见证了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大量鲜活的生产生活资料掌握在他们手中,吸纳他们参与到教材开发的过程中,教材的开发的内容会更加全面。
最后,作为教材开发成功使用者和受益者的主体——学生,是教材开发质量的检验者和鉴定者,而学生家长由于身处民族文化的环境之中,对于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鉴别力和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如果他们能够加入教材开发队伍,教材的可使用性及科学性程度有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如果民族文化理论研究者等人员能加入会使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及丰富性更加完备。
(二)教材入选内容把关:筛选设置标准高于一般的校本教材
从狭义层面来划分,民族文化有物质文化,包括饮食、居住等;社会文化,包括婚姻习俗、道德文化、节日文化等;语言文字文化,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等;宗教文化,包括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傩文化、人文宗教等;文学艺术文化,其包含内容之广,不易甄别[7]。在这些民族文化中,参差不齐,既有文化精髓,又有文化糟粕,民族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民族的历史,我们应在以传统的基础为起点去发展现代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是扬新弃弊。
作为标本教材的使用群体——青少年,青少年由于处于心理生理发育的成长阶段,群体性特征明显,其个体认知能力有限,对于新鲜未知事物的接受程度高,所以校本教材内容甄别筛选至关重要,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更应如此。我国民族众多,文化资源丰富性、多样性具有不可比拟性,但是,在我们的部分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很多的宗教祭祀文化,如傩文化、巫文化。在我国的教育大环境下,宗教不得进入学校教育制度也已固化,从纷繁的文化中将营养精华部分筛选并顺利让学生汲取,处理好学校教育与文化类传承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开发教程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二、教材开发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原则
(一)将地域特色资源挖掘整理与学生实际需要的满足相结合
拥有资源集合体的学校,是教材开发的组织机构,校长是校本教材开发的第一责任人,教师队伍是教材开发的主体力量,在教材开发过程对本校实际情况做出客观的评估,结合本校教学实际需要,对于教材开发的条件如师资特点、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民族文化传承定位等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同时,由于身处特定的民族资源氛围之中,学生或多或少了解相应的知识,在教学及教材使用中的阻碍力也相应地减少。例如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依托地缘优势,地处苗族武术之乡——青虎自然寨附近,凯里市鸭塘中学组织相应的人员开发本校的校本教材。苗拳是苗族重要的传统体育竞技活动项目,鸭塘中学学生生源大部分来自附近的苗族村寨,身处习武健身的氛围之中,武术基础较好,教师队伍中不乏有苗拳知识丰富者,校领导根据本校实际,将苗拳纳入校本课程计划,在科学文化课程学习之余设苗拳学习班,并将相关的教学内容总结编排出了本校校本教材《苗拳初级拳谱》,这样的教材是将地域特色资源与学生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典型事例。
另外,作为校本教材开发的最终服务者和评估者的学生,对于教材的使用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而校本教材开发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学生对于民族文化学习的需求,所以,对学生关于民族文化学习需求倾向性进行调查,是教材开发前所需完成的必不可少的功课,“以生为本”应始终贯彻于教材的开发使用过程。
(二)遵循青少年心理认知发展原则
不同阶段学习者的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规律存在差异性,在开发教材的过程中,应将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所应具备的心理发展特征纳入教材开发过程中,学生对于所要学习的内容应由经验的、具体的事实逐渐向内涵概括化的阶梯性发展,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可以根据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经验与知识,实现知识的迁移化学习,促进学生的认知辐射范围的扩大。
另外,遵循心理发展的逻辑规律,贴近学生的心理生活,合理安排相应的教材内容。这对于教材编排开发人员提出了要求:既要熟悉学生的认知能力、对于基础知识的把握程度,也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虑,使教材内容的“序”与学生身心发展的“序”有机结合,更加贴近学生实际生活,降低学生理解的难度[7]。
(三)科学性、文化核心至上的原则
教材具有受众性高等媒介载体应具备的基本特点,而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包含着科学的因素,这也是其能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如源于唐代的黔东南州丹寨苗族地区的石桥村古法造纸工艺,苗族先民以汉民族的造纸技术为基础,对技术进行改进过程充分利用当地构皮、杉银和清澈的河水等原料,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硾、硾杆、水轮、曲柄等在内的工艺技术,早在汉代文献《天工开物》就有发现,且石硾图使用原理一致,从现代的意义来讲,古法造纸过程中的物理化学知识已广为世人所接受,石桥村造纸产品销路顺畅,造纸技艺名扬海内外,曾多次被邀到加拿大多伦多科学中心表演。像此类文化应纳入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髓发扬的重任。教体编排的科学性是衡量教材开发质量的第一标准,而文化核心至上则是此类教材开发的最终归宿。
(四)开放性吸纳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原则
教材开发的多主体参与,可以丰富教材内容,避免教材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教师、学生家长、文化学专家、课程理论专家、民间能工巧匠、学生、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教材开发主体库中的一员,在开发教材的过程中,各主体地位均等。作为教材开发过程的重要环节的资料搜集,是教材内容的必要来源,但是,通过走访发现,资料搜集难度系数较高,商品经济条件下,民间工艺传承出现“断层”现象,对本民族文化怀着深厚情感的民间艺人为了让大家了解自己所掌握的技能文化,无偿地将自己所掌握的一手资料图案等讲述传授于“有心”的学习者,希望借此之手实现文化的传承与普及,但是部分商人却通过翻版、复印等方式将民间艺人的手绘作品进行批量化生产后低价出售,版权的盗取,手工制作被批量化生产取代,不可避免地使传统文化掌握者处于失落的境地。商业化大潮的侵袭加大了教材开发中资料搜集的难度,教材开发者在民间采风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着资料给予的不情愿,有时甚至需要签署诚信保证书。
(五)动态循环提升的原则
教材“再开发”被很多学者提倡,意为经过实践教学环节,发现教材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对其进行再修订。这个环节对于校本教材来说,重要性和可操作性程度远高于普通教材,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质量应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实践教学是检验开发质量的最终标准,而通过学生互动促进教材质量本身也是对学生探究世界和挖掘认知能力的提升,在课堂教学检验中发现问题,便于后续的订正、改进,这个过程需要作为教材开发者课程实施者——“教师”和学习者“学生”的双向互动沟通,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三、教材开发过程中相应的保障机制
机制原指机器的工作原理及其构造。教材开发机制是保障教材开发正常运行的基本结构与动力系统,具体来说,它包括教材开发程序的设置,特别是教材开发的前期物质、人员、方案准备工作、实施过程中方案偏差的纠正、运行管理中人员的培训、激励监督措施的出台等方面,在筹备教材开发的阶段,关于教材开发人员的相关领导小组人员的确定之后,关于教材开发过程相应细则的确定也会出台以便管理调控开发全过程,如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等。为了保障教材开发过程的顺利,将开发过程中的保障性措施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前置准备性机制
前置准备性机制指教材开发过程人、财、物等方面的物质和人员支持准备。确立教材开发首先面临的是经费问题,在争取到资金支持后,就涉及开发方案设计、开发人员选拔及培训交流机制的建立等等,这些内容都属于前置准备性机制。稳定的教材开发队伍是教材开发的主体构成,其作用至关重要,它决定着教材开发质量的高低。完整的前置准备性机制包括:统一教材开发人员选拔标准,摸排开发人员的技能知识结构;关于教材开发内容的培训方式;教材开发过程中对于外部智力资源的利用等内容。此外,明确的教材开发方案的确定,将为教材开发提供方向支持。
(二)中置匡扶性机制
(1)筛选机制的确立。对文化进行筛选始终贯穿着教材开发过程,民族文化范围广,数量多,有健康积极的一面,也有落后消极的一面,现有的教学管理实施的是学校与宗教相互独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入选教材内容的民族文化的科学性也随之提升。
以巫文化为例,对比一般民族文化,它的包容性、隐蔽性、混融性都较强,由于历史关系,其与民族原始医术、文学、艺术等关系密切。巫师,作为此文化的代表,具备多种社会身份,作为宗教巫术的施行者,威望较高,兼具医生、舞蹈家和歌手等多种身份,在实现民族文化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傩”意为“帮人避难,祛除鬼戾”之义,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傩文化最明显的释义就是祭祀稻神、田神等各神,祈祷五谷丰登之意。傩文化形式多样,包括傩戏、傩舞等。从生命意识的角度看待巫傩活动,它对信仰者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安慰,与传统习俗相结合,深入市井的传承与流布,信众辐射范围较广。
(2)激励机制的设立。激励机制是在主体系统中,通过整合相关的诱导性因素,使得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目的在于激发人正确的行为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力效应,以有效地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目标的系统性活动。根据激励形式的差别,可以将其分为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等层面。在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中,合理的激励机制可以为教材的开发提供坚实的保障,教材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的激励既可以包括教材开发与工作量的合理对等转化、绩效工资等合理的薪酬补贴等物质层面的内容,又包括教材开发理论学习指导等精神需求层面的自我成就体现。
(3)教材开发培训交流机制的设立。教材的特征决定了其开发过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所以单纯依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教材开发需要团队成员共同完成。教师、民间艺人等主体也被囊括进教材开发主体中,“重教育轻课程”的状态在我国的教师教育中广泛存在,加之应试教育考试使得教师的注意力较少地关注课程教材技能知识,入职后的培训也以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为主。在实地通过问卷分析可知:87%的民族地区教师存在理论水平低、精力有限等问题,对于教材开发一无所知,甚至对于日常使用的教材编排合理性说不出一二;而作为民族历史“活化石的”民间艺人,手中掌握大量鲜活的民族文化素材,但是由于自小学习某种技艺,文化水平较低,有些年龄较大的手艺人,甚至存在着语言沟通的障碍;所以,对教材开发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交流非常有必要。通过师资培训,博采众长,实施教材开发人员“走进来”“走出去”战略,互通有无,广泛进行校际互动,增加校内交流机会,打造出一支理论水平高、富有责任感的教材开发队伍。
(三)后置质量评估反馈性机制
(1)开发教材的评估机制。任何学校开发出的校本教材都不可能实现尽善尽美,这就对学校领导者和教材开发者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认识到教材的缺陷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内部质量评价与改进是相当有必要的。基于校本教材开发“校本”的独特性,与统编教材相比,校本教材缺乏统一的考试质量评估审核机制。所以,除了报备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考核管理外,教材质量的提升、内容的完善离不开学习者的自觉自律。教材质量的合理评估与自我内部评价与改进机制,对于教材开发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科学民主的评估机制离不开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它既是校本教材开发第一个阶段的终结,又是教材完善阶段的开始,因其开发初衷是服务学习者,所以在教材的评价中应着重吸纳其最终使用者——学生的意见,另外,评价主体中应吸纳民间艺人、教材理论专家、文化评估者的参加。
(2)后续上报审核认定机制。1986年之前,中小学教材管理实施国家统一认定标准,在此之后,中小学教材转变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出纲”,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此范围内进行教材开发,报备审核。在“一纲多本”的管理运营模式下,教材在中小学使用的前提是教材审定机构对于编写的教材进行审核认定。目前对于包括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在内的校本教材审定基本处于零起步状态。作为校本课程开设的产物的校本教材,受校本课程变动影响较大,缺乏政策方面的合法地位。
(3)反馈性导向机制。一般来说,反馈导向机制要依据评价机制建立的各指标体系进行,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的开发是一个循环往复的阶段性提升过程,在使用过程中施受主体对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的客观评价决定着后续反馈实施的效果。
四、完整的教材动态开发过程
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成果展示,校内师资是其开发的主要力量,为了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知识体系的逻辑完整性,应对教材开发过程的各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基于管理学视角看待,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的开发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层次:从宏观角度来说,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始终贯穿于校本教材的开发过程;具体来说,以下几个行为教材开发过程所必备的。
(1)前期准备性工作。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对本校的师资特长、学生年龄结构及心理特点进行摸排,确定教材开发的需求导向性,寻求相应的教材开发经费支持,“以校为本”是“校本”的根本属性,首先,对学校已有资源进行分析判断,已有资源包括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层次,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熟悉了解程度等内容;其次,开发教材的财力资源保障,教材开发过程中激励杠杆调节作用的发挥,教学样品素材的购买,民间采风的食宿交通费用,教材排版付梓费用等开支较多,如果缺乏相应的资金保障,教材的动态开发无法有效地进行。
(2)组建开发人员团队,确立教材开发目标。根据前期准备性工作的摸排,确立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包含的具体内容,制定教材开发预期目标,根据开发内容,吸纳相关主体参与,确立教材开发团队,包括民族理论专家、教师、民间艺人、课程论专家、社区居民、学生在内的多主体参与团队成员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各尽其用。
(3)根据个人所长,合理分工,通过培训交流实现资源的共享。合理的分工和明确的职责内容是团队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我国在校本教材开发目前还处于初始化阶段,关于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在探索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教材开发中相关知识的缺乏可以通过引进外部资源来平衡教材开发中相关理论知识的缺乏。
(4)走访民间能工巧匠,搜集教材开发所需素材。作为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与一般校本教材开发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此阶段开发过程决定着教材内容的丰富程度。由于目前的教学考评机制实行的成绩导向性,包括部分教师在内的教育管理人员对于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通过走访民族村寨中的民间艺人、能工巧匠能够获得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为后期的教材内容的完善做好准备性工作。
(5)设计编写。根据教材开发预备方案进行,按照分工进行撰写、设计、编排,在此阶段中,在注重教材内容充实性的基础上,可以多途径增加教材的美观、通俗性,如相关素材图案的讲解等,内部教研交流学习,定期专题学习分享、方案进程适时对比可以有效地确保教材开发进度的完成。
(6)投入使用。课堂教学的实践检验是检验所开发出教材的最终标准,学生作为教材使用主体的学生,对教材使用有最直观的感受;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大量的教育理论来自于鲜活的一线教学”,作为教材开发者和教授者的教师,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对于学生课堂表现状况比较了解,更容易发现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教材质量的提高。
(7)质量评估和修改完善。经过课堂教学时间的检验,教学效果良好的教材,在专家的审定和论证阶段后,可以联系相关出版社进行出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仅是教材使用范围和知名度的提升,更是对教材开发者劳动成果的认可,将会大大提高他们开发教材的积极性。
[1] 李鹏程.文化研究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07.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51.
[3] 刘茜.贵州省苗族地区中小学民族文化课程开发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5(1):147-153.
[4] 高宁.教育的嬗变和文化传承[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27.
[5] 潘定智.民族文化学[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24.
[6] 姚茉莉.贵州省宰荡小学双语文教学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7.
[7] 涂军.谈校本教材制定的原则及实施方案与模式[J].咸宁师专学报,2002(1):108-109.
[责任编辑 王晓雪]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school-based national culture textbook
YANG Wei
(SchoolofSocialandPublicManagement,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China)
Education, rooted in culture, provides information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making its preservation,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possible. Developing ethnic cultures on campus is an activity to int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modern classroom. Due to three-level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 school-based national culture textbooks are allowed to be designed by colleges, while the geographical uniqueness of national culture, scientific and precise nature of textbooks offer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iling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design of compiling criteria, principles,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national culture; school-based textbook; compiling process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1.020
2016-12-17
杨威(1988—),女,河南汝南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的研究。 E-mail:ywei12345@126.com
G463
A
1673-9779(2017)01-0119-06
杨威.衔接与动态透视:民族文化类校本教材开发过程[J].2017,18(1):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