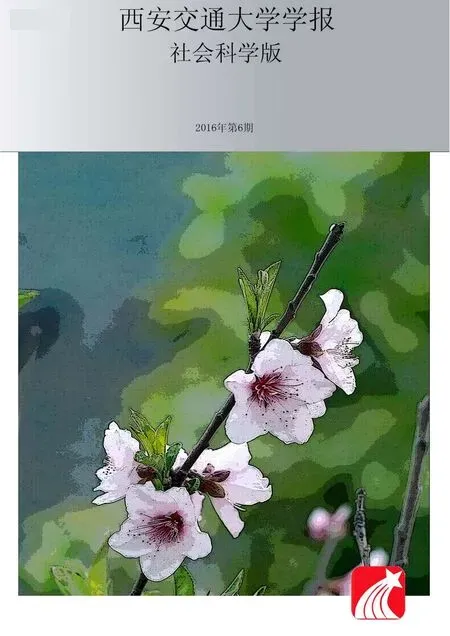中国当代家庭的发展困境
2016-12-23胡湛
胡 湛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当代家庭的发展困境
胡 湛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当代中国家庭经历了剧烈的变迁,它与人口转变互构,并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尽管传统文化惯性使中国家庭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竭力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抵御风险、适应变迁,却越来越不足以应对人口、家庭、社会多重变迁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中国家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
一、制度缺失下的“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
随着我国家庭户数的不断增加和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小,当代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尽管单身户比例持续升高和二代标准核心户比例在近20年内锐减,但总体而言核心家庭户仍是中国家庭户的主要形式。无论是其在家庭户总数中所占比例,还是生活在核心户中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50%[1]。基于此,相当多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已基本实现了家庭核心化。然而从本质上讲,这种核心化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核心家庭”概念来不仅是指居住模式,更与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西方发达国家近现代家庭核心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其相对完善的福利与保障体系,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核心家庭中的个体可以在不依赖于扩大的家庭亲属网或其他人便能够生活,并对个体的生老病死都有比较完整的保障[2]。但在中国,现有面向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仍重点关注问题家庭和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占主流的核心家庭户很难独立完成基本家庭功能,而不得不依赖其亲属网络获得支持,其家庭功能的完成呈现网络化特征。复旦大学2013年开展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YRST)表明,80后年轻夫妇中超过三分之二以上需要父母帮助照料下一代,甚至“父母能否帮助带孩子”已经成为影响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调查也显示,“家庭”和“家族/宗族”在14种人们“碰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去寻求并获得帮助的渠道”中名列第一和第二,远远超过“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3]。

表1 中国核心家庭户比例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1982-201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计算。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核心家庭的功能网络与中国传统家族亲属网络有着本质区别。其一,当代核心家庭功能网络较少蕴含传统网络中的大量伦理规范和道德绑架;其二,这一网络的形成逻辑较多地体现了“互惠互助”的“利益原则”[4];其三,当代核心家庭功能网络较多以亲子关系为核心,其互动具有典型的垂直性,即主要以核心家庭中的夫妇与其双方父母家庭的互动为主,并尤其体现在婚育、抚幼、养老等方面。
不难看出,在制度相对缺位的背景下,中国的家庭尽管在变小,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核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而其功能的完成却需要其亲属网络的参与,这种“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网络化”现象是未来家庭政策必须要正视的核心命题。
二、“少子化”背景下的“家庭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家庭“老龄化”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有老年人(65+)的家庭数量为8 803.6万户,占全部家庭的21.9%,比2000年有明显提升。按这一趋势测算,至2040年有老年人的家庭数量将可能超过1.3亿户[1]。从单个家庭来看,1982-2000年间的户均老年人数量稳定保持在0.22-0.24人,而至2010年陡增至0.41人/户;与此同时,户均孩子的数量却从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2],平均每个家庭少了差不多1个孩子。中国家庭正在经历“少子老龄化”进程。

表2 中国家庭户人口结构变动情况(单位:人)
数据来源:1982-201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在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将可能陷入前所未有的养老困境。制度的尚未完善使相当多的老年人在不能工作时必须依靠积蓄或子女,其中高龄老人更需要大量日常生活照料,目前这些服务大多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其子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的传统家庭居住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弱化。2000年和2010年,老人与子女同住比重相继下滑10个和5个百分点;2010年,高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更比2000年骤降13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包括独居老人家庭、老年夫妇家庭以及多人纯老家庭。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更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72.3%,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1]。
不难看出,在现有制度条件下,考虑到少子老龄化及居住模式变迁的现实,未来中国家庭内部代际转移的增幅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传统文化的惯性仍使大多中国家庭甘于承担养老责任,但即将“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的生活资源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公共转移支付[5]。尽管政府一直尝试改革甚至重构养老保障体系,但如果生育率一直过低的话,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很难具有持续性,这将成为未来老龄社会保障制度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三、“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的博弈
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一直呈现工具理性色彩,政府常会出于自身治理需要对“家庭-个体”关系进行功利化操作。尽管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补缺型模式的囿限,进而体现出“再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的博弈。
一方面,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家庭越来越多地替代国家或集体来担负个体的社会保护责任。但由于之前的中国政府几乎是维护大众福祉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福利制度的发育尚未能填补政府的退出所形成的空间,最终大部分国家所退出的公共服务,例如养老、抚幼、医疗、教育等,通过市场化而转由家庭承担[6]。这无疑使中国家庭被重新赋予了重要的保障和福利职责,政府和社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和依赖家庭,但面对风险与责任,家庭功能网络成为中国家庭应对风险和适应变迁的重要屏障,“再家庭化”进程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我们在强调重视家庭传统和家庭责任的同时,不仅缺少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予以制度性支持,“去家庭化”也在同步进行。例如:改革开放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迫使个体以不同方式从家庭和单位中脱嵌出来投入经济建设,在社会空前发展、女性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家庭功能普遍磨损。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同女性工作、老年人承担家庭义务有密切关联,“正是有这两项条件,我们在家庭没有崩溃的情况下,既实现了家庭的完整,又实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7]。又如:前文论述的“少子老龄化”就直接涉及我国自1970年代开始推行的具有“去家庭化”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却没有充分考虑其所催生出的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可能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即便是对家庭功能进行补充的社会保障政策(养老、生育、医疗等)目前也大多以“个体”为单位,极为有限的以家庭为主的保障政策主要表现为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注及介入(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这种政策取向其实是对家庭承担社会责任的惩罚[8],即拥有家庭的人反而得不到政策的直接支持。尽管有些政策在个别领域对于暂时缓解问题有所裨益,但就整体的中长期发展而言,未获得系统性支持的中国家庭依旧举步维艰。
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政策就是社会政策”[8],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只是政府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对家庭责任的分担。而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变迁过程中,制度的缺失与政府的工具主义已使中国家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家庭发展的乏力正对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带来挑战。破解这一困局,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的、静态的政策调节或调整,而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体系,以适应现代家庭与社会的发展需求。
[1] 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3):145-166.
[2]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蓝皮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5-68.
[4] 唐灿,陈午晴.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J].江苏社会科学,2012(2):92-103.[5] CAI Y,WANG F.China′s age of abundance:When might it run out.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J],2014(4):90-97.
[6] 唐灿,张建.家庭问题与政府责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5.
[7] 沈奕斐.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16-20.
[8]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84-96.
(责任编辑:冯 蓉)
10.15896/j.xjtuskxb.201606026
1008-245X(2016)06-01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