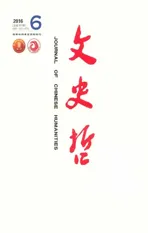“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
2016-12-19潘务正
潘务正
“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
潘务正
史传中经常出现历史人物“疽发背而死”的记载。此病在古代为膏肓之疾,死亡率很高。史传中这一叙事元素不仅仅为实录,往往还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意蕴:它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忧患意识,至明清之际成为遗民的一种隐晦死法;因患上此病时死相极为凄惨,故史家在此中融织了天道观念,至后世演化为诅咒之语。叙事手法上,“疽发背而死”含蓄地表达了历史人物的情感,流露史家的褒贬倾向,并渲染出浓厚的悲剧意蕴。这一叙事元素符合古代文史交融的传统,为史家青睐。
疽发背;忧患意识;天道观念;叙事传统
死亡乃人生大事,古代史家通常在历史人物之死的描写中展现其品节。因病而亡是司空见惯的死法,不过为了叙事的简洁,史书未必均交代其死因。然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史传中出现众多“疽发背而死”的记载,此始于《史记》,众所周知范增就是因此而殂;自此之后,史书提到人物之死时频繁出现这一病因,几乎无代无之。试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例,除去重复者,情况如下:

书名发病者书名发病者史记范增、周丘旧唐书张守珪、李洧、韩简后汉书朱穆、盖勋、刘焉、刘表新唐书孟浩然、薛存庆三国志曹休旧五代史阎宝、龙敏、和凝、胡进思晋书庾翼宋史韩令坤、张澹、何继筠、卞衮、明镐、唐介、王雱、种谔、宗泽、刘羲叟、张嵲、周克明、符惟忠、曾觌、留从效宋书刘禹、庾悦、姚绍金史田琢、移剌瑗魏书南安王桢、崔亮辽史萧陶隗南史萧明明史徐达、朱恩鑙、何申、李鋐、王鸿儒、杨一清、毛伯温、仇鸾、张慎言、张宗琏①万斯同《明史》(清抄本)中尚有胡海、章玉等因此病而死,分别见卷一六六、卷二〇七。本文所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为避免繁琐,不另出注。北史王勇、王士隆清史稿庄元辰、姚启圣、朱善张、张曜
“疽发背而死”受古代史家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文献记载中当同一人物有不同死法时,史家往往乐意采用这种结局。如唐代韩简,据《实录》记载,他是“为部下所杀”②司马光:《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288页。。然《旧唐书》本传云:“为(诸葛)爽军逆击,败之。简单骑奔回,忧愤,疽发背而卒”;《新唐书》本传、《资治通鉴》亦同。史家明知韩简还有另一种死法,却仍择定其为疽发背而死。又如宗泽,其死也有不同记载。南宋叶适仅云其“忿郁死”*叶适:《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第20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本,第7页。,明王祎亦云“遽属疾”,或云“以故忧愤成疾”*王祎:《义乌宋先达小传·宗泽》,《王忠文集》卷二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4页。,而不提所患何疾。但南宋王柏《宗忠简公传》云“疽发病甚,……薨”*王柏:《鲁斋集》卷十四,民国《续金华丛书》本。,《靖康小雅》更是明确记载“疽发背而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1页。,元初官修《宋史》承之。是否疽发背而死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宗泽的光辉形象,但史家似乎更“偏爱”其因此致命。
作为一个反复出现的叙事元素,这仅为实录,还是别有意味?因其始于《史记》,并大量出现在史书及传记类文献中,故本文以史传为中心,兼及其他史料,对这一问题试加探讨。
一、致命之因
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因疽而死的是晋国中军元帅荀偃,《左传·襄公十九年》载其“瘅疽生疡于头”而丧生,可见此病很早就给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古人通常以“痈”来解释“疽”,《说文解字·疒部》云:“疽,久痈也。”同卷又云:“痈,肿也。”*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5页。疽是在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段玉裁据《后汉书·刘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云:“疽,久痈也。”并解释道:“痈久而溃,沮洳然也。”同卷释“痈”云:“肿,痈也。瘤,肿也;痤,小肿也,则非谓痈也。”*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认为痈是人身上比较大的肿块,久痈引起溃烂即为疽。

据南北朝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所载,疽可以发在身上的任何部位,然疽发于背部以外区域,虽死亡率亦较高,但还有医治的可能。史料记载中亦不乏此例,如唐李疽发于首(《旧唐书·李质传》),南宋遗民赵元清(《宋遗民录》卷五)、明李震疽发于脑(《皇明大政记》卷十五),均未丧命。疽发于背亦有好转者,如清代江南歙县孝子汪龙“疽发背”,“越数旬始瘥”(《清史稿·孝义二》);不过从总体来看,治愈的可能极小,像汪龙这样不治而愈只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而已。
疽发背在古代几乎是一种绝症,宋洪适《跋痈疽方》云:“疽发背,三尺童子亦知为膏盲之疾。”*洪适:《盘舟文集》卷六十三,《四部丛刊》第193册,第5页。元谢应芳《赠钱隐居序》亦云:“夫疽发于背者,危疾也。”*谢应芳:《龟巢稿》卷十四,《四部丛刊》三编第6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重印本。究其因由,在于背部于人体的重要性。中医认为背是五脏穴位所在,《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引,第6083页。即五脏对应的穴位,均在人体背部,这个穴位又称为“俞(腧)”。《类经》注云:“五脏居于腹中,其脉气俱出于背之足太阳经,是为五脏之腧。”*张介宾:《类经》卷七《五脏背腧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6册,第137页。中医理论中,后背属阳,阳脉均循行经过,尤其是背正中的督脉,与两边对称的太阳膀胱经,五脏俞即分布其上,疽往往发于背部这些穴位,《诸病源候总论》卷三十三“疽发背候”云:“疽发背者,多发于诸脏俞也。”五脏俞反映对应五脏正气的盛衰,疽发于此说明所属脏器已发生病变,正气虚极,无力抗邪,故属于恶候。
疽发于背,堵塞经络的通畅,引起溃烂。《诸病源候总论》卷三十三“疽发背候”云:“五脏不调则发疽,五脏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于身。腑脏不调,腠理虚者,经脉为寒所客。寒折于血,血壅不通,故乃结成疽。其发脏俞也,热气施于血,则肉血败腐为脓也。”《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亦云:“痈疽发背,筋肉坏烂。”*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明洪武刻本。发病时因溃烂而产生剧烈疼痛,患者苦不堪言:“痈疽发背,溃后疼痛不止。”*朱:《普济方》卷三一四《膏药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7册,第240页。疽发背不但难以治疗,且死时极为痛苦,死相亦较凄惨,古代视之为恶疾,不言而喻。正因疽发背在古代属“膏肓之疾”,故众多历史人物因此而死就不难理解。
“疽发背”的诱因很多,古代医学家对此作了探讨,李迅《集验背疽方》归结为五个方面:“天行一,瘦弱气滞二,怒气三,肾气虚四,饮法酒、食炙煿物、服丹药热毒五。”元杨清叟《仙传外科集验方》亦云其源有五:“一天行时气;二七情内郁;三体虚外感;四身热搏于风冷;五食炙煿、饮法酒、服丹石等热毒。”*杨清叟:《仙传外科集验方》卷一《叙论·疽发背品第一》,明正统《道藏》本。也就是说,天气、情绪、体质及饮食等均可诱发此病。在五种病因中,史传记载最多的是因极度愤怒、悲伤、惊恐即“七情内郁”引发的疽发背。情感郁积会伤及五脏,《黄帝内经》云:“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皆志意为病。”*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卷三《五脏别论篇第十一》,明万历刻本。情绪波动导致五脏不调,引起疽发背。范增就因此致病而死,《史记》涉及此事有两处,一是《项羽本纪》:“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一是《陈丞相世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二者所记内容相同,稍异者在于范增辞归时的情绪,一则曰“大怒”,一则曰“怒”。就发病可能性来说,前者更为确切,因为此病“非愤极不成”*董其昌:《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容台集·文集》卷八,明崇祯三年(1630)董庭刻本。,只有愤怒到极点才易患是病。范增一心为项羽谋划,而项羽遭刘邦离间之计,竟然怀疑他,不但不用其言,反而稍夺其权;他辞归时项羽亦未作丝毫挽留。范增预感到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大业将彻底失败,其愤怒、悲痛、绝望可想而知。因此郁气内积,五脏失调,疽发背而亡。
与此类似,史传中描写人物疽发背时心理状态的不一而足,如“不得意”的盖勋,“不得志”的庾悦,“惭恚”致病的王勇,“忧愤”发病的王士隆、韩简,“惭愤成疾”的阎宝,与王安石争而“不胜愤”的唐介,奸情败露而“忧恚”的曾觌,“忧愤成疾”的宗泽,“心积不平”的张宗琏,国亡后“朝夕野哭”的庄元辰等。有些史料虽未明确描写人物发病前的心理状态,但由记载亦可推而知之。如张守珪,《旧唐书》本传云:“(开元)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张时任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因部下诈称诏命冒进败绩,为自保,他“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泄左迁,必定产生愤懑之情,以致疽发背而卒。再如辽萧陶隗,《辽史》本传云:“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陶隗不急追捕,罪当死,诏免官。久之,起为塌母城节度使。”史载萧陶隗乃极易暴怒之人:“陶隗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虽上有难色,未尝遽已。见权贵无少屈。”因此,受到奸臣诬陷,意气久久不平。故虽重新起用,但仍尚未赴任就“疽发背卒”。又《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云:“(仇)鸾奸大露,疽发背死。”仇鸾因外结掩答、割死人首以冒军功等罪行被人揭穿,其病显是忧惧所致。
由上可知,历史人物由于某种重大的变故,产生了或愤怒、或悲伤、或忧惧、或惊恐等情绪,使五脏失调发生病变,以疽的形式呈现于背部,并因此丧生。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很多人物死于此病不足为奇。然史家不厌其烦地提及此种病因,往往并非仅为“实录”,而是别有深意。“疽发背而死”不仅是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史学命题。
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为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认为“忧患意识”乃是由某种责任感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庞朴反驳此种观点,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收入《蓟门散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31页)。本文取前者的观点。,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自孔子见“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于是惧而“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至龚自珍阐扬的“良史之忧”*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7页。,均一脉相承强调此种意识。官修史书也本此意,新的王朝执政伊始,即着手编纂前代史书,体现出正如《诗经·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以史为鉴之意。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与这一意识有关。
史家的忧患意识通过史传中人物命运遭际加以呈现。古代忧患之士常常与疾病相伴,《诗经·小雅》中就有很多此类抒情主人公形象,如《杕杜》云:“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毛传云:“疚,病。”《正月》云:“哀我小心,癙忧以痒”,“念我独兮,忧心慇慇”。毛传云:“癙、痒皆病也。”郑笺云:“国家将有危亡,故念我独忧王此政兮,忧心慇慇然痛也。”《小弁》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郑笺云:“疢,犹病也。”*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九、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413、417、442、443、452页。忧伤国事而致生病,其忧可谓深矣。疾病与忧患之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孟子云:“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朱熹解释道:“孤臣,远臣;孽子,庶子,皆不得于君亲,而常有疢疾者也。”*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十三《尽心上》,《四书五经》上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29页。德慧术知之士预见到国家的危机,欲有所为又无法施展抱负,忧愤成疾。且疾病的轻重,又与忧患的程度成正比,疽发背这种致命的恶疾最能揭示历史人物深沉的忧患意识。此种描写,肇其端者为司马迁“发愤”而成的《史记》。在描写范增结局时,太史公特别加上“疽发背而死”一句,看似无心之笔,实则有意为之。

李陵之祸给司马迁造成的创伤时常流露在《史记》的描写中*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16页)对此举例云: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一云:“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得以货免;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叹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其‘羞贫贱’者,自伤贫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钱锺书先生认为所论二事“殊可节取”;又证之以张耒《司马迁论》谓《伯夷传》寓被刑之怨、《晏子传》寄无援之慨等。。他从国家利益出发为李陵辩解,却遭受耻辱刑宪,真乃“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也,其满腔悲愤倾注在有相似经历的屈原身上。范增在某种程度上与屈原、司马迁遭遇相同。其以七十高龄投奔项梁,此后处处为项氏谋划:立牧羊奴为义帝,以张举义旗;牧羊奴成为项氏心腹之患后,可能在他指使下将其弑于江中;刘邦的威胁更让范增为本集团担忧,设鸿门宴拟将其剪除。计划流产后,范增一再感叹项氏必为刘氏所灭,自己与同僚必定为其所俘。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心力帮助项羽,企图避免失败的结局。范增“奇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可以看出他的耿耿忠心。让他未曾料到的是,刘邦的离间之计竟轻易就让项羽怀疑他,“于是一腔为项热血,洒落无地,而乞骸骨,疽发背死矣”*徐允禄:《范增》,《思勉斋集》卷十一,清顺治刻本。。范增之死,正在于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产生的极度悲愤。从《史记》描写倾向看,司马迁对项羽的英雄气概持赞赏的态度,而“项以范增存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三,第1062页。,因此忠于项氏的亚父也是其颂扬的对象。“疽发背而死”不但揭示范增的无限悲愤与彻底绝望,也寄寓着太史公的深切同情及“悲世之意”*刘熙载:《艺概·文概》,《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4页。。史心史法,都在这寥寥数字中得以展现。明姚舜牧《范增》云:“唉!竖子不足谋,岂俟今日哉!入关以来,若此所为,便当知其不足谋矣。知不足谋而但欲杀沛公以取天下,及后楚受反间,始请乞骸骨,疽发背而死,此唉(“唉”为衍字)老子之所为痴也!”*姚舜牧:《来恩堂草》卷十一,明刻本。范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痴”中正可看出他的忠心,后世文学作品也将其视为忠义之士的典范。佚名《英烈传》引瞿佑诗云:“虎斗龙争既不能,鸡鸣狗盗亦无闻。陈平韩信皆归汉,只欠彭城老范增。”并在诗后按云:“是时张士诚据浙西富饶之地,招贤养士,凡人有不得志于元朝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及城破,无一人死难者,武夫徤将,唯束手卖降而已。”*佚名:《英烈传》卷五,明刻本。很显然此中范增是作为忠义之士得到赞扬。范增至死忠诚的品质,既为义士钦佩,也为史家激赏。
自此之后,史家继承《史记》以“疽发背而死”描写人物精神品格的传统。范增之后,因此而逝的著名人物是南宋爱国将领宗泽,史家以此病将其一生心事和盘托出。《宋史》卷三六〇本传云:
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每为(黄)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疽发背的描写,强化了宗泽的忧患意识、爱国之情,千载之下读之,犹令人感慨不已!
正如屈原的典范作用使得沉水自杀成为后世爱国者的死亡方式一样,范增、宗泽疽发背而死也成为史家笔下乱世或末世仁人志士比较普遍的死因。清初史学家万斯同《明史》卷一八七云:“何申、宋和、郭节,俱不知何许人,俱官中书。申使蜀,至峡口,闻变,恸哭呕血,疽发背死。”所谓“闻变”即时为燕王的朱棣发动的旨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变;同书卷三五八云,张慎言“流寓芜湖、宣城间。国亡后,疽发于背,戒勿药,卒”,二人事迹相同,均为忧愤时事而患上是病,并以此殒命。清道咸间史学家徐鼒著《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附考》,取“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世运”之意*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自叙》,《小腆纪年附考》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页。,记载了数位南明官员因悴心国事或国亡忧愤导致疽发背而死的事迹,除《附考》中的张慎言外,《纪传》中记载了四位:
(吕)大器知其(王祥)无能为,太息谓李乾德曰:“杨展志大而疏,袁、武忍而好杀,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为乎?”一日,于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独山州,郁郁疽发背。明年,卒于都匀。(卷三十)
(孙)嘉绩急还会稽,则监国(鲁王)已航海去,乃入舟山以观变。时已疽发于背,疾笃,谓子延龄曰:“倘闻王所在,宜急从之。”语毕而卒。(卷四十)
大兵东下,(庄元辰)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丁亥,疽发背,戒勿药,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犹可。”(卷四十一)


三、天道观念
古人将疾病视为上天降罪的征兆,血肉溃烂、疼痛不止的恶疾“疽发背”因此与天道产生联系。古代巫史文化形态决定早期史官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明天道”成为其职分所在,正如《国语·周语》记单襄公之语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云:“瞽史,大师,……诏吉凶;史,大史,掌抱天时,与大师同车,皆知天道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虽后世史官转向史事的记录或撰述,但此传统却延续下来,当《诗》、《礼》等“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之际,《春秋》仍“兼记天变”,此乃“三代以来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页。,即此可知该传统的沿承。究其所明之“天道”,一是天文知识,刘知幾云:“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十一《外篇·史官建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二是推知祸福,龚自珍云:“言凶,言祥,言天道,或验,或否,群史之世言也。”*龚自珍:《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第一辑,第8页。史官掌观望星象与占卜吉凶,所以司马迁才抱怨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史记·天官书》及后世史书《天文志》兼就天文知识与占卜吉凶立意;继承《春秋》频繁记载日食、地震等灾异,《汉书》及后世史书《五行志》则偏重吉凶的推演,均是“明天道”的史职体现。
随着学术文化的演进,史官所明天道之内涵中宗教神秘色彩减弱,人文理性意味增加,这首先体现在对天道的怀疑上。《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伯夷、叔齐“积仁絜行”而饿死,颜回“好学”却在贫困中早逝,天道不公之甚。忠心耿耿的范增、宗泽等人,在史家眼中无疑属“善人”之列,但却身患“筋肉坏烂”、“疼痛不止”的恶疾悲惨死去。善人而获厄运,史家如此处理彰显了对天道的质疑。

周丘亦死于疽发背。《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周丘)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日人泷川资言说:“范增……‘行未至彭城,疽发背死’,与此相似”*[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〇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4416页。,实则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范增是太史公歌颂的对象,周丘乃其集矢的标靶。《史记》突出周丘本为下邳“亡命之徒”,七国之乱时应吴反,以“能者封侯”为号召发动昆弟,一夜募得兵马三万,攻破城阳中尉军。势头正盛之时,闻吴王濞败走,知大势已去,“疽发背死”。惟恐天下不乱的周丘在维护大汉统一王朝的司马迁眼中,无疑是一位被贬斥的人物,其患恶疾痛苦死去,彰显出天道的公正。这与《汉书·五行志》所载梁孝王欲求为景帝之嗣而刺杀袁盎,事发后“发疾暴死”极为相似,秉承了《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及《易·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意。太史公以此达到“惩恶”之目的,也受其时研治《春秋》的大儒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只不过这层含义甚为隐晦。
《史记》之后,史家常以“天诛”、“天谴”之类用语将“疽发背而死”隐含的天道观明确表达出来。沈约《宋书·自序》云其祖上沈林子对刘裕说:“姚绍气盖关右,而力以势屈,外兵屡败,衰亡协兆,但恐凶命先尽,不得以衅齐斧耳。”不久姚绍就疽发背死。刘裕赐书沈林子云:“姚绍忽死,可谓天诛。”沈氏先祖根据秦将姚绍所为断定其不得善终,就是以天道观为基础;《魏书》卷十九下《南安王桢传》云:“(南安王)桢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邺城有石虎庙,人奉祀之。桢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当加鞭罚。’请雨不验,遂鞭像一百。是月疽发背,薨。”此中寓含着元桢乃触犯神灵而暴死之意。可见视“疽发背而死”为“天诛”乃南北朝时期比较普遍的观念,且又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结合。史家将此写入史书中,寓含劝惩之意。又,《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倧传》载,钱倧“性明敏严毅”,以礼法绳下,引起大将胡进思不满,于是发动兵变将其幽禁。此后不久,胡就“疽发背而卒”,越人拍手称快,视此为“阴灵之诛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载,王韶所奏多诬,“杀蕃部老弱不可胜数”,纵容部下滥杀无辜;所以当他死时,史家李焘写道:“至病疽发背,洞见五脏,亦其报也。”疽发背溃烂得能看清五脏,真是惨不忍睹。在史家看来,此乃造恶多端的报应。史传中那些冷静地以疽发背结束反面人物一生的写法,即使史家没有点明乃遭受天谴,其实也寓含这一意旨。
唐代以后,佛教典籍中亦出现以背疮或肤烂显示天道思想或果报观念的记载。唐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下《续补》载一僧徒杀蚯蚓无数,“未久僧忽身痒成疮,皮肉尽烂而死”;又载蜀僧仁秀杀虫无数,“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年,第823页。。元普度《辨远祖成道事》云惠琳著《白黑论》诋毁佛教,“即感恶疾肤肉糜烂而死”*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四,《乾隆大藏经》第147册,北京:中国书店,2009年,第71页。,这些都与史传中疽发背而死类似。民间亦普遍地将疽发背视作恶毒的诅咒,明清时期,这一观念更为盛行。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载,眉州知县沈福抓获贼妇七人,行刑时残忍地“用大杖击其首而毙”,不久,沈福就“疽发背死”。作者论曰:“轻视人命,淫刑以逞,其死也,谓非天道乎!”*戴冠:《濯缨亭笔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455页。谢肇淛评《魏书》中南安王元桢之死为“黩神之报也”*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受史学传统的影响,“疽发背而死”发展成为一种诅咒的方式。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人敷衍出努尔哈赤疽发背而死的说法。
努尔哈赤病疽而死*关于努尔哈赤死因的考察,可参看李鸿彬:《努尔哈赤之死》,《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最早见于袁崇焕的奏疏。他上奏朝廷说:“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六“天启六年九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690页。但袁氏所言,乃“四乡络绎皆云”之语,显然并不可靠。明御史汪若极亦云,宁远战役之后,“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七“天启六年十月戊申”,第3705页。。将其疽发而死归为“天诛”,实乃诅咒之语。此后这一说法在中朝两国都流传开来,并演变成“疽发背而死”。晚明史家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云:“本年(天启六年)八月初十日,老奴酋疽发背死。”*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56册,第734页。清初遗民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云:“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3页。朝鲜史书《丙子录》云:“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七,《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37页。这明显是一种诅咒,观其指称努尔哈赤为“老奴酋”、“建州虏酋”等语可知。因其带兵入侵,成为中朝两国最严重的边患,民间与朝廷对其极为痛恨,故而以“疽发背”诅咒其死。所以,这种说法含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极有可能为虚构,不能作为真正的死因。可以看出,“疽发背而死”已演化为咒语式的病症,天道观念不但影响了史书的叙事,也塑造了民俗信仰。
四、叙事传统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认为,文学作品中疾病通常被“当做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本文的论题。中国古代史学崇尚含蓄的叙事传统,“疽发背而死”为史家青睐,就在于对这种疾病的描写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


首先,就“疽发背而死”表达的历史人物精神状态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如前所论,此病“非愤极不成”,历史人物正是经历了情感郁积才诱发此恶疾,并因之丧生。从这个层面来说,“疽发背而死”强调的不是死的结果,而是死前的精神状态。它一方面是对“大怒”、“愤恚”、“忧愤”等抽象情感的具象化描写;另一方面,即使史传描写中没有这些词汇,但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病症仍能不动声色地传达人物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极度悲愤、惊惧等情感,并以其死将此种情感推演到极致。这些都符合崇尚言外之意的古代史学叙事传统。
其次,就“疽发背而死”体现的史家著述态度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寓含着褒贬倾向。近现代史学要求以客观之笔忠实记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然传统史学则更多地以史为手段,史著的编纂,往往出于一定的意图,“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认为此书意在“惩恶而扬善”,故有“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之说*范宁:《穀梁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9页。。但如果此类态度过于明显,则又有失史书的特性。在这方面,郑樵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郑樵:《通志总序》,《通志》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因而古代史学家强调在历史事件记录中不动声色地实现褒贬,正如刘熙载所云:“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刘熙载:《艺概》卷一,《刘熙载文集》,第64页。着眼点正在史意的隐微。“疽发背而死”就叙事手法而言无疑是客观记录,然在不同的语境中,褒贬之意分明:当“善人”不幸染上是病,则显然是褒扬其忧心国事,忠而忘身的品质,如范增、王士隆、宗泽、何申、张慎言、庄元辰等即是;当“恶人”患上是病,则显然借此贬斥其祸国殃民的卑劣行径,并能想象到其经受血肉溃烂、极度疼痛的折磨而死,不免大快人心,如周丘、张守珪、韩简、曾觌、仇鸾等即是。客观病情的记录中寓含着褒贬倾向,实现史学与文学的交融,符合史传的叙事传统。
第三,就“疽发背而死”的叙事效果来说,这一叙事元素呈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蕴。恶人患上恶疾,实属罪有应得;而善人患上恶疾,则体现了命运的不幸。弟子伯牛身患恶疾,孔子探视时说:“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邢昺疏云:“此善人也,而有此恶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8页。一般认为伯牛所患为癞,病发时腥秽触鼻,且有传染性,所以被视为恶疾。伯牛这样的“善”人却患上癞这样的“恶”疾,孔子的再三感叹,衬托出其殉道者式的悲剧意蕴。“疽发背而死”亦是如此。范增、宗泽等为国事忧心忡忡,然时局无法左右,他们或者被猜疑,或者被排挤,想有一番作为又无法施展怀抱;他们不是战死在两军对垒的疆场,也不是鞠躬尽瘁于官衙内,而是凄凉地亡于路途中或病榻上。他们死前不但情感上经受着极度悲愤的折磨,肉体上还要遭受着血肉崩溃的痛楚;他们不是体面地离开人世,而是以“一种很丢人的死(法)”死去*李国文:《疽发背而死》,《中华散文》2006年第10期。。这赋予他们浓厚的悲剧意蕴。正因如此,他们的病逝往往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宗泽“疽发背而死”就曾令人无限感动,他临终前嘱托诸将恢复故国,咏杜诗以表心事,不及家事而连呼“过河”者三,正可见其疽发背的原因。故其病逝时“都人号恸,朝野相吊出涕”,甚至连上天都被感动,以致“风雨晦冥异常”*王柏:《宗忠简公传》,《鲁斋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描写渲染出浓重的悲剧气氛。彭士望《首山濯楼记》状方以智“疽发背而死”时云:“此盖天欲天下后世人知其如此而生,如此而僧,如此而死,为之流连涕洟,悲吟思慕,互相淬厉。”对此余英时反驳道:“倘密之果系‘疽发背死’于舟中,躬庵是语岂非不词之甚乎?仅仅病死舟中何足使人‘流连涕洟,悲吟思慕’,更何能使人‘互相淬厉’乎?而所谓‘如此而死’者,必其事惨烈悲壮、惊心动魄,然后始有使‘天下后世人知之’之价值。此又岂‘疽发背死’所堪当者乎?”*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第175页。余先生有此疑问,在于不明这一符号所蕴含的意味。方以智因亡国的极度忧愤而致病,又痛苦地死去,爱国之情、忧患意识、悲剧意蕴体现无遗,因此不难理解他去世时众情感奋的场景。由此“疽发背而死”的描写就具有了“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的叙事效果,从而赢得崇尚意味深远之叙事效果的史家广泛青睐。
当然,“疽发背而死”在史书中反复出现,也与古人崇尚模拟的传统相关,特别是《史记》以之叙事树立的典范作用。而史家之所以竞相仿效,还是在于这一叙事元素能够以简洁的笔法含蓄地传达丰富深远的意旨,符合中国史学传统。同时,由“疽发背而死”的丰富意蕴与叙事策略也可更深刻地领会古代文史互溶的传统。这一叙事元素虽是个微小的符号,却具有多重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 刘 培]
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芜湖 2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