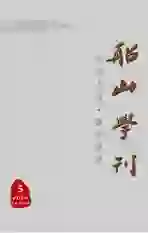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
2016-11-17李明军朱利侠
李明军 朱利侠
摘要: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
关键词:儒家诗学;道统;性情;文化内涵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从清初起,被称为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顾、黄、王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王夫之在明朝灭亡后,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他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因为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更为使诗中之情超越一己私情之关键,为通过个人审美体验实现对人类普遍价值关怀之途径。顾炎武则由明朝之亡总结出人心风俗关乎历史盛衰的规律。他认为,在风俗衰败之世,名教之倡导或可挽救世风。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明道之目的则在于治国,所以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将对私欲的肯定作为其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起点,将自私自利称为“天下之情”,以此对抗腐败衰朽的君主制,从而恢复道统至高无上的地位。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即为性情论。他认为诗之道甚大,不仅关乎一人之性情,更关乎天下之治乱,诗要表达者为“情至之情”和“万古之性情”,要通过一己、一时之性情表达更深广的社会内容,而此即兴、观、群、怨之内涵。
一、道统、治统与文统:顾、黄、王诗学的历史背景
异族入主中原与中原朝代更替有所不同,不开化的蛮夷既被视为文明的对立面,而其入主中原又往往大肆杀戮,不仅使百姓有生命之忧,更使士人有道统断绝之患。所以在明清易代之际,浸淫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有着更多的矛盾和困惑。明朝灭亡引发了汉族文人的文化反思,反思的结论是将明朝灭亡归因于思想混乱和道德堕落。明朝既已灭亡,汉族文人将救挽天下的希望寄托于儒学复兴。对明代遗民来说,坚守儒学又是精神寄托,以传统儒家精神为内核的道统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支撑。清初儒家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
顾炎武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在明时为诸生,与同乡归庄共同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清兵南下,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顾炎武和好友归庄参加义军,事败,顾炎武和归庄出逃,顾炎武之母不食而卒。顾炎武从此离乡背井,奔走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等地,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亡国破家之恨,使顾炎武不可能与满清妥协。顾炎武牢记继母王氏绝粒时的遗言,坚决不出仕异朝。他亲历明朝之亡,由此总结历代王朝兴替的规律,得出了人心风俗关乎历史之盛衰的结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①国家的昌盛首先要从“厚俗”始:“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②在风俗衰败之世,名教之倡导或可挽救世风于万一。所谓“名教”,即“以名为教”。所谓的“名”是指忠信廉洁等道德之名。之所以可以“以名为教”,是因为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追求名。君子求“名”,是求道德之实,而凡人求“名”实为求利。君子是以名为利,是求“没世之名”。以名为利的君子虽然为数寥寥,但其对世俗的表率作用至为重要。
在《日知录》的《正始》篇中,顾炎武探讨亡国与亡天下的分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③要保国,必先保天下,而所谓保天下,即匡复儒学,倡导仁义。顾炎武认为魏晋清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最终导致亡国与亡天下的恶果。顾炎武大声呼吁坚守儒家纲常伦理,他所做的也正是清理宋代的理学直到明代的“心学”对儒家理论的混淆和歪曲,探寻真正的名教之源。在《法制》篇中,顾炎武对以法治国提出质疑,认为以法治国的结果只能是权力移于吏胥,最为根本的还是正人心而厚风俗。在《郡县论五》中,顾炎武提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④而顾炎武所肯定的“一人之公”,实际上也就是天子的“一人之私”,这是顾炎武对家天下的新的理论层次上的肯定,只有真正的家天下,才会有三代、汉唐那样的治世。从维护推崇王道出发,顾炎武以纲常伦理作为衡量风俗善恶的标准,东汉末年朝政昏浊,国事日非,但士人依仁蹈义,王道未息,北宋时期,士绅以名节廉耻相尚,一旦国变,人人奋起勤王,与摒弃王道的战国时代,不谈忠孝的明朝末年,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值得肯定。
顾炎武认为,君子为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救世”,⑤而所谓的圣人之道,即“孝弟忠信”,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⑥文章的价值在于明道,而明道的目的在于治国:“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⑦顾炎武所崇尚的“文”为“人道之至文”,亦即“亲亲、尊尊、男女有别”之礼,而文的最高典范是《诗》、《书》、三《礼》、《周易》、《春秋》。从表面上看,顾炎武将夷夏之防置于纲常伦理之上,实际上顾炎武更重视的是纲常伦理,他在文章中阐述最多的是以君臣关系为旨归的“礼”,认为天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而君臣关系更在父子之上,所以顾炎武认为伍子胥为报父仇而鞭君主之尸为大逆。按照顾炎武的观点,无论身处夷狄还是华夏,坚守儒家的纲常伦理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顾炎武最后默认清人对中国之统治的底线,所以晚年顾炎武由立志复国转而以移风易俗、张扬人道为己任。
关于学术,顾炎武有“理学,经学也”的著名的论断,⑧认为真正的理学应该是经学亦即汉学,也就是实证之学,通过对经典的研究而恢复原始儒学。顾炎武之所以对经学如此关注,是因为儒家经典乃“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⑨在顾炎武看来,六经之指与当时之务紧密相关,研究六经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探求社会治乱之根源,以此解决当时之务,所以顾炎武不作性、命、道、理的空谈,其著述虽博杂,然宗旨则统一于“为万世开太平”。所以顾炎武所说的“理学,经学也”中的“经学”,既可视为“经典之学”,又可视为“经世之学”。顾炎武被后世视为实学之倡导者,即由于此。经典的讹误,开后世异端邪说之旁门,使原始儒学的精神和本旨湮没无闻,后世儒者因而失却安身立命、修己治人之本。要发掘儒学之旨,必须从拨乱反正、回归儒学元典始。被后世学者目为载道之书的“六经”,是士子治学问道之津梁。读经书首先要明了文义,要明了文义又须从正音始。这也是顾炎武究心于音韵之学的原因。endprint
在“性命”与“人事”的关系上,顾炎武认为“性与天道在文行忠信中”,⑩由此提出“心所以治事”的有为论主张,极言尽人事的重要性。与王夫之的观点稍微不同,顾炎武认为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淳化风俗的先决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B11在晚年,顾炎武在写给黄宗羲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王者兴起的期待:“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B12康熙二十年冬,李因笃在富平得知顾炎武在曲沃害病,写了五首七律赠给顾炎武。顾炎武收到李因笃的赠诗后,提笔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首诗。七十岁的顾炎武以恬淡的心境回忆一生,以“四海竟沦胥”一句将明清易代之事轻轻带过。此时满清统治已经巩固,四海走向升平,对于天下百姓来说,这已经够了,是明朝统治还是清朝统治,似乎无关紧要了。
和顾炎武一样,黄宗羲在明亡后参加了抗清斗争,眼看大势已去,他以保全家庭免受满清之毒手为由主动退出南明鲁王之军,回乡安居。1667年,黄宗羲与同门学友于在绍兴复兴“证人讲会”,系统地讲述蕺山之学。1668年,黄宗羲到达甬上讲学。五个月后,甬上“策论之会”改为“证人之会”,同年“证人之会”又改为“五经讲会”。隔年,黄宗羲在讲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证人书院。从1668年到1675年,黄宗羲主持甬上讲经会达八年之久。
黄宗羲早年师事理学家刘宗周,然意在实践,不喜空疏,虽未尽脱心学藩篱,但痛感晚明空疏的心学末流无益于世,因而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从“道问学”入手以达到“尊德性”。黄宗羲倡经世致用之学,又不非王学,他对理学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以“理气合一”来说明心、性、情的合一。由“理气合一”出发,黄宗羲赞同其师刘宗周的“理欲合一”之说。他不仅批判宋代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也批判王阳明的理欲对立观。对私欲的肯定成为黄宗羲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起点。自私自利被黄宗羲称为“天下之情”,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于是有人出来,兴公利而除公害,君主于是产生。就私欲之存在说,君主圣人与百姓并无区别,君主圣人能将一己之私欲推而及于天下而已,君主与臣子之间更是“名异而实同”,天下为主而君臣同为客,臣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而非为君主为一姓。B13后世的君主倡君权神授,以天下为一己之产业,禁绝百姓之私利以谋一己之利,原始君主的道德基础不复存在,道德的自我完善成为儒者的责任,文人反而成了道统的坚守者。黄宗羲所设想的理想政治为以文人政府制衡君主之权力,正是从此点出发。“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认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B14文人在社会中的中坚作用得到强调。在黄宗羲看来,将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视同腐鼠的君主为天下之大害,除去天下之大害即成为圣人之举。
从私欲观出发,黄宗羲推演出了与顾炎武相近的君臣、天下观。黄宗羲亦主夷夏之辨:“自三代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B15黄宗羲将宋明之亡称为古今之大厄会,把遗民看成是天地之元气。入清之后,黄宗羲拒绝出仕,并非出于对前明的忠诚,而是出于对自我品操之坚守。实际上,黄宗羲之天下君臣观即基于对明朝君主专制之批判。黄宗羲每每以死拒征,不愿出山修史,但又同意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入局编修《明史》。黄宗羲于《历代史表序》中云:“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B16黄宗羲同时允许官方派人就其家中抄写有关史料,并同意在家中解答疑难和审订史稿。其间接参与修史,亦于政治上对满清之妥协无关。正出于对“天下”之理性思考,黄宗羲对出仕异朝的汉族文人表示理解。当有人建议将仕于清朝的侯方域排斥于明文选之外时,黄宗羲回答说:“姚孝锡尝仕金,元遗山终置南冠之列,不以为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B17
康熙元年四月,桂王父子被吴三桂杀于昆明,同年南明鲁王死于台湾。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统治业已巩固,明朝复兴无望。清康熙二年,55岁的黄宗羲完成了《明夷待访录》。或以为黄宗羲明夷待访为名,“将俟虏之下问”,B18或以为黄宗羲作此书是为代清复明的君主提供治国之策。B19实际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于反思历史之基础上,阐发了关于未来社会之理想。书以“明夷”为名,取《易经》中“明夷”卦离下坤上意寓希望与光明。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自序》中云:“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又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余尝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B20在黄宗羲看来,明朝和代替明朝的清朝都是乱世。黄宗羲的理想是恢复三代之治,而非腐朽的明王朝,他寄希望于未来:“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B21顾炎武读了《明夷待访录》后,深有感触地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B22顾炎武作《日知录》也自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B23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没有等到其所希望的“王者”兴起,也许其所谓的明夷之世永远只能是理想,然正是此理想如离离之火,维持道统、文统绵延不绝。
崇祯十五年,二十四岁的王夫之中举人第五名。明亡后王夫之组织匡社,取匡复社稷之意,后于南岳组织武装抗清,失败后至广东肇庆,被南明桂王任命为行人司行人,协助瞿式耜守桂林。三次上疏弹劾王化澄,险遭杀害,脱险后回湖南,最后隐居于衡阳石船山麓,称船山先生。据说隐居后的王夫之无论阴晴昼夜,皆穿木屐、撑雨伞,示不顶异朝之天、不踏异朝之地之意。对道统的坚守,支持王夫之度过了晚年的艰苦岁月。道统之维持,道德理想主义之重建,归根结底是儒家学说之发扬光大,所以王夫之在前朝灭亡后,致力于儒家经典之研究。endprint
七十三岁时,王夫之完成了《读通鉴论》。在这部书中,王夫之表达了对治统的理解,认为手相授受者不一定为正统,“治相继”、“道相承”者方为治统。顺治三年,清廷组织翻译了《洪武宝训》,顺治帝写序,示清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亦当视为正统。王夫之之正统论或即由此而发。王夫之主张严格的夷夏之辨,将夷夏之辨称为维系人类秩序的“三维”之一。他将华夷之辨称为天下之大防,以为夷夏之大防远超过君臣之大义,为前者甚至可以放弃后者。王夫之说:“君子之于小人,犹中国之与夷狄,其分也,天也。”B24夷狄与中国不可同伍,小人与君子也不能同流。如果君子与小人同流,中国就会与夷狄无异,而这正是王夫之最为担忧的。王夫之于夷夏大防之强调,一方面因为蒙元对汉人之压迫歧视,给汉人留下永久伤痛,而清兵入关后对汉人的屠杀和压制,更让汉人对异族统治畏如蛇蝎。王夫之曾举兵抗清,事败后誓不降清,转徒苗瑶山洞,隐居著述,自然难以忘怀民族危亡之恨。但王夫之最为担忧的,还是礼乐之消亡,道统之断绝。在多数情况下,汉人君主失职于天、地、人三极的维护,才导致天下沦亡:“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害,摈其异类,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蕴也。今族类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B25在这样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之公,除君主一人之私:“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B26这个时候,君主就“可禅、可继、可革”。王夫之对文明毁坏的混沌之世充满了恐惧。王夫之之所以对儒礼如此执着,正是由于对夷狄入主中原而使文明失去依存的担忧。王夫之希望以礼义变化夷蛮之人,以化成天下。而以仁德化成天下的最好载体是诗乐,这也是王夫之对儒家诗学如此关注的原因。他在诗论中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分,一方面是基于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以君子小人之辨喻指中原和夷狄之分。
二、性与情:顾、黄、王诗学的哲学内核
在儒家思想中,性与情是两个重要的概念,而对性和情的内涵、性和情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别。宋代二程有“气禀”和“定性”之说,将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义理之性为至善,又称“道心”。气质之性为理气相杂而成,有善有恶,又称“人心”。“道心”为“天理”,“人心”产生不善即为“人欲”,从而引出“天理”、“人欲”之对立,须以“道心”统“人心”,以“天理”制“人欲”。朱熹承二程天命、气质之说,于此基础上更明白倡“存理灭欲”。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为血气心知之自然,为性之实体。“欲”指对声色嗅味之要求,“情”指喜怒哀乐之外现,“知”指辨别美丑是非之能力。声色嗅味、饮食男女等为人类自然正常之要求,亦为性之具体表现。以“心知”调节情欲即为善。“欲”与“理”之关系实即为“物”与“则”之关系。至于性与情之关系,程朱认为性情对立,性是体,情是用;性是静,情是动;性是未发,情是已发。
关于性情之关系,顾炎武引孟子之言云:“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B27顾炎武常用的概念是“心”,比如他论“情”与“心”之关系:“苟能省察此心,克伐怨欲之情不萌于中,而顺事恕施,以至于‘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则可以入圣人之道矣。”B28顾炎武承认自私为人之常情,是势使之然:“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B29人的私情不仅不能禁止,还要受到尊重:“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B30天子的职责就是利用天下人之私以治理天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天下人之私,“合天下之私,以成天子之公”。B31
黄宗羲由“理气合一”出发,赞同其师刘宗周的“理欲合一”之说。他不仅批判宋代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也批判王阳明的理欲对立观。黄宗羲又反对“以一己之利为利”而无视他人之利的“私欲”,将与“天理”合一的“欲”称为“公共之物”,即“各得其私其利”的“公利”。只有符合“公利”的“人欲”才是合理的欲。从“去人欲,存天理”到“物欲合理”,再到黄宗羲的“公私理欲合一”,既是哲学思考的结果,又是时代发展在文化中的显现。黄宗羲从“理气合一”出发,经过“心性合一”这一中间环节,进而引出“性情合一”。黄宗羲批评程朱性情对立的观点:“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略性是体,情是用;性是静,情是动;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他已不是性也。则性是一件悬空之物。其实孟子之言,明白显易,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发,而名之为仁义礼智,离情无以见性。仁义礼智是后起之名,故曰仁礼义智根于心。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先,另有源头为仁义礼智,则当云心根于仁义礼智矣。是故‘性情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气合一之说也。体则情性皆体,用则情性皆用,至动静已、未发皆然。”B32黄宗羲提出了“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的著名论断,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论提出异议:“盖人之为人,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外,更无别心,其憧憧往来,起灭万变者,皆因外物而有,于心无与也。故言‘求放心,不必言‘求理义之心;言‘失其本心,不必言‘失其理义之心,则以心即理也。孟子之言明白如此,奈何后之儒者,误解人心道心,歧而二之?以心之所有,止此虚灵知觉,而理则归之天地万物,必穷理而才为道心,否则虚灵知觉,终为人心而已。殊不知降衷而为虚灵知觉,只此道心,道心即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B33
对于“性”和“情”的关系,黄宗羲同意刘宗周的观点:“师以为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又言性学不明,只为将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钟虚则鸣,妄意别有一物主所以鸣者。夫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谓有义理之性不落于气质者,臧三耳之说也。”B34“性”在“情”中,通过情来体现,这正是诗道性情的内涵所在。
王夫之以儒学传统为依托,通过对《周易》、《尚书》、《春秋》、《诗经》及“四书”等儒家基本经典的阐述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理、性、情、欲之关系为王夫之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天理与人欲之关系,王夫之认为:“只理便谓之天,只欲便谓之人。饥则食,寒则衣,天也。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人也。”B35天理体现为人的自然之质、先天之性,又体现为“人之独”:“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B36理寓欲中:“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章其用。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B37endprint
与宋朝理学家朱熹相比,王夫之对性和情的分别更为严格,对情更充满了戒备。他认为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亦即仁、义、礼、智,皆属于性,与喜、怒、哀、乐等七情有严格的区分。他反驳朱熹所说的“情者,性之动也”,认为并非“性”发而为“情”,而是“性”内在于“情”之中,“情自情,性自性”,B38情为人心,性则为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见,普天下所见的皆为情,只有圣人儒者才能见到性。情有善恶,而性无恶:“大抵不善之所自来,于情始有而性则无。孟子言‘情可以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过、不及者亦未尝不可善,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情以性为干,则亦无不善;离性而自为情,则可以为不善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固未尝不入于喜、怒、哀、乐之中而相为用,而要非一也。”B39情、性的混淆,必然导致情的放纵和对性的腐蚀,从而危及道统。性有质有恒,而情无质无恒,尽性则知天,尽情则乱性。然情却又在尽性中有不可或缺之作用,情以显性,人心以资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其论才、情、性之关系云:“才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聪、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应效而奔命焉。”B40情以御才,才以给情,情和才同原于性,而性则原于道。所以王夫之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以道为终始的圆:“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B41
人先天之性有所感触则形而为情:“‘欲,情也。‘知知,谓灵明之觉因而知之也。人具生理,则天所命人之性固在其中,特其无所感触,则性用不形而静。乃必发而为情,因物至而知觉之体分别遂彰,则同其情者好之,异其情者恶之,而于物有所攻取,亦自然之势也。”B42而“发而不昧其节”的正声雅乐,可以防止“性”流变而为“淫情”,可以防止天理之亡:“好恶本性之所发,而吾性固有当然之节。唯不能于未发之时存其节而不失,则所知之物诱之以流。斯时也,大本已失,而唯反躬自修以治其末,则由外以养内,天理犹存者。苟其不然,纵欲以荡性,迷而不复,而天理亡矣。”B43情既不能绝,不能闭,那么就该加以利用:“情欲,阴也;杀伐,亦阴也。阴之域,血气之所乐趋也,君子弗能绝,而况细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启闭而消息之,弗能尽闭也,犹其弗能尽启也。……阴弗能尽闭,而君子重用之。”B44
三、性之情:顾、黄、王诗学的文化意蕴
性和情也是儒家诗学的核心概念。诗主性情,但性和情又有着严格的分别。儒家学者认为,情为人心,性为道心,道心微而不易见,普天下所见的皆为情,只有圣人儒者才能见到性。情有善恶,而性无恶。情、性的混淆必然导致情的放纵和对性的腐蚀,从而危及道统。性有质有恒,而情无质无恒,尽性则知天,尽情则乱性。然情却又在尽性中,情以显性。所以诗歌抒情的最终目的是表现性即道心,而不是容易流变为欲的情。虽然情、欲相关,遂欲才能达情,但欲有着放纵泛滥的危险。欲有公、私之分,情亦有正、偏之别。出于公欲之情为情之正,而正情即由喜怒哀乐而通向仁义礼智。诗歌所要表现的正是所谓的正情。
顾炎武论诗之本云:“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令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封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B45顾炎武强调“诗主性情,不贵奇巧”,B46诗所抒之情要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妄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B47顾炎武究心于音韵之学,然他又强调音律应该为诗义服务:“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B48“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者,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B49
顾炎武对杜甫之诗甚为推崇,其所作诗风格与杜诗相近,被评者称为“诗史”:“先生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抚时感事诸作,实为一代诗史,钟美少陵。”B50其所作420多首诗,多感事述怀、触物咏情,沉郁顿挫,接近杜诗。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注释、考辨。
和顾炎武一样,黄宗羲认为诗担负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功能:“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B51在《金介山诗序》中,黄宗羲提出了“有诗”、“无诗”的问题:“古人不言诗而有诗,今人多言诗而无诗。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于景,其次求之于古,又其次求之于好尚。……夫以己之性情,顾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为殉物之具,宁复有诗乎?”B52有诗还是无诗,关键在于性情。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情之至真,时不我限。”B53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形诸文辞即为诗,而“习心幻结,俄倾销亡”的矫情、伪情实际上不是情,所以也不会有诗:“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亲,思妇劳人,结不可解,即风云月露、草木虫鱼无一非真意之流通。……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随事转,事因世变,干啼湿哭,总为肤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败梗飞絮,适相遭于江湖之上。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然而习心幻结,俄顷销亡,其发于心,著于声者,未可便谓之情也。”B54
“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B55黄宗羲认为情有“不及情之情”和“情至之情”:“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无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波臣、戌客,无一非文人也。”B56“情随事转,事因世变,干啼湿哭,总为肤受”,这样的情是“不及情之情”:“不及情之情与情至之情较,其离合于长吟高啸之间,以为同出于情也,窃恐似之而非矣。”B57与“不及情之情”和“情至之情”相对应,黄宗羲又有“常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之说,常人之诗并非不欲言性情,但其性情不及情:“是非无性情也,其性情不过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谓之诗人。”B58黄宗羲认为,写诗者甚多,但可以称为诗人的寥寥无几,他甚至说:“千年以来,称诗者无虑百人,而其为诗人者三人而已,宋代高菊、明宋无遗及景州是也。”B59endprint
黄宗羲又有“万古之性情”和“一时之性情”之说:“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呕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之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B60诗可以表达怨女逐臣之情,但不能流于一己之性情的宣泄,要通过一己、一时之性情表达更深广的内容,而这更深广的内容也就是万古之性情。但能通过一时、一己之性情达到万古之性情者,只有具有“情至之情”的诗人,诗人之诗虽少而又少,却是天地之元气,直接关乎世风之维持:“元气不寄于众而寄于独,不寄于繁华而寄于岑寂,盖知之者鲜矣。”B61所谓的“独”与“岑寂”,与黄宗羲对心性的理解,对“慎独”之“独”的理解有关。黄宗羲引泰州王栋之言论刘宗周“慎独”之旨云:“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变,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作主张,自裁生化,故举之曰‘独。”B62与“众情”相对的是“一己之情”,与“万古之情”相对的是“一时之性情”,黄宗羲由此又有“一人之时”之说:“即时不甚乱,而其发言哀断,不与枯变谢者,亦必逐臣、弃妇、孽子、劳人,愚慧相倾,算相制者也。此则一人之时也。……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时同,而其间有尽不尽者。不尽者终不能与尽者较其贞脆。”B63
黄宗羲所主张的“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是因为孔子所说的性情,所说的兴、观、群、怨,强调的正是经由一己之哀怨而表现时代和社会:“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观也。善于风人答赠者,可以群也。凄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B64
王夫之认为,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诗对情感的表达和引导至关重要。情感不得表达即为匿情,而匿情之结果必然是上怒下怨,必然是情流而为欲:“匿其哀,哀隐而结;匿其乐,乐幽而耽。耽乐结哀,势不能久,而必於旁流。旁流之哀,鏙眎惨澹以终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於乐,迁心移性而不自知。”B65“情”是达性之途径,是理之具象,是礼得以延续之根本。如果情最后亦消亡,那么人就会最后变为非人,变为禽兽:“悲夫!情在而礼亡,情未亡也。礼亡而情在,礼犹可存也。礼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B66
王夫之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严格区分开来,反复强调诗的抒情性,虽有维护诗体纯洁之意义在,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突出诗的正情功能,其评徐渭《严先生祠》云:“诗以道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礼》、《书》、《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B67所谓的“性之情”,一方面强调诗要表达的“情”是发自本心的积极情感;另一方面亦为了突出诗由“情”而达“性”的功用。王夫之批评宋人的以意为诗,以学问为诗,甚至贬低杜甫的被称为诗史的诗歌,称其为“风雅罪魁”,因为其诗舍“情”而言“性”,实际上掩藏了性的光辉。王夫之反对以议论入诗,反对以章疏入讽咏,以尺牍为诗,认为以诗谈性理和情的放纵同样危险。在王夫之看来,天下的议论已经太多,如诗再放弃其导情、正情之作用,议论泛滥,乖戾之气充塞于两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其论《小雅》云:“议论多者,其国必倾。非议论之倾之也,致其议论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为悁急,则国家之舒气尽矣。”B68
“情”为王夫之所重构的儒家诗学体系之核心。王夫之所说的情,又不同于世俗所说的情。事实上,王夫之倡导情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世俗之流弊。王夫之强调说,他所说的情是性情,所谓的性情,指的是“性之情”。“性之情”实际上也就是以性节情,是雅化的情。“情之欲”是诗不应该表现的,诗情不包括私情、矫情、淫情、俗情等鄙俗之情。王夫之反复强调情感的净化,认为“惟能净斯以入化”,使情感由“自发”、“自溺”而变为“自戢”、“自养”。王夫之所倡导的情的雅化是传统理性精神复归的文学表现,这与黄宗羲所说的“情至之情”有相通之处。诗歌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忧乐,更重要的是天下之情,王夫之认为:“其忧乐以理,斯不废天下之理。其释忧以即乐也,无凝滞之情,斯不废天下之情。”B69
王夫之将一己穷通之情称为私情:“货利以为心,不得而忮,忮而怼,长言嗟叹,缘饰之为文章而无怍,而后人理亡也。……恤妻子之饥寒,悲居食之俭陋,愤交游之炎凉,呼天责鬼,如衔父母之恤,昌言而无忌,非殚失其本心者,孰忍为此哉!”B70王夫之一反习俗对杜甫之推崇,独独对杜甫大加以斥责:“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於金帛,设於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B71私情之宣泄,不仅失去其导情于理之职能,而且会导致私欲之泛滥,使诗永亡于天下,而天下遂亡。能救治天下的只有天下之情:“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则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情而宅天下之正。……君子非无情,而与道同情者,此之谓也。”B72诗人可以做到的,是以一己忧乐,达天下之情,而又不以一己之忧废天下之乐,不以一己之乐废天下之忧,是之谓“裕情”,“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B73以此而论,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皆为诗之罪人。
由其情理观出发,王夫之提出了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情要有所节,有所止,要善于忍情。情景互藏为节情、忍情以防止情感泛滥之一法。以景物作为情感抒写的媒介,既因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景物对情感的触发符合自然之理,更因为情与景之间的交流互动,使无法言传的隐幽之情得到抒发,又使这种情的抒发含蓄蕴藉,避免直露式的情感宣泄。以乐景写哀情,以哀景写乐情,通过反向的渲染,使情感更加突出,而这也是避免情感过分张扬的一种手法。景甚至是阐释理的媒介,所谓的以写景之心理言理,实际上是将以景抒情的情感表现糅进事理的阐发之中,达到感发意志之效果。endprint
正是本着对诗的抒情性的强调,王夫之将比兴作为诗之根本。诗要以个人情感的审美体验而实现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就不能离开比兴。“兴”是使诗中之情超越一己之私情的关键。王夫之将兴观群怨视为诗教之内核和评价诗歌功用之标准以及诗歌创作之准的,而四者之中尤为重要者为“兴”,兴不仅是观、群、怨的前提,更是诗歌教化作用的基础,因而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所在:“‘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B74之所以强调“兴”,因为诗不同于典册、简牍等的感发意志之功效源于“兴”,“兴”的感发作用能消除人的“卞躁之气”。
从调和性情出发,王夫之反复强调诗乐一体。王夫之说:“诗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声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声也。以诗言志而志不滞,以歌永言而言不郁,以声依永而永不荡,以律和声而声不。君子之贵于乐者,贵于此也。……以律节声,以声叶永,以永畅言,以言宣志。律者哀乐之则也,声者清浊之韵也,永者长短之数也,言者其欲言之志而已。”B75比起诗来,乐更具有“和”的功用,乐为作为世界本原的太和之气氤氲变化的和谐的体现。在《诗广传》中,王夫之论言与音之关系云:“未有其事,先有其容,容有不必为事,而事无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为言,而言无非音之成也。”B76之所以将音置于言之上,是因为音相对于言的普适性,而此普适性之根源在于“道”,言不尽道而无言之音可尽道。将诗与乐分离而空言“诗言志”,必然导致诗歌教化功能的丧失和风雅的沦亡。圣人治天下者以礼,以刑辅礼,以乐达礼,才能实现礼教治国之目的。
在清初,除了顾黄王之外,致力于儒家诗学体系建构的还有钱谦益。被清廷归入“贰臣”的钱谦益却被当世文人尊称为“宗伯”。他的文学成就及对后学之扶持为其在文坛上赢得了崇高地位。既经丧乱,又经灵魂之洗礼,钱谦益对儒家言志诗学有更深刻的领悟,于世运对文学之影响有更深刻认识。在其学术基础之上,钱谦益建立起以儒家诗教为内核的诗学体系,希望以儒家诗学之复兴,从救人性入手而达到救世之目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等对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既与明清易代有关,又与明清之际汉族文人的文化选择和人生境遇有紧密联系。明朝之灭亡,引发汉族文人的文化反思,思想之混乱和道德之堕落被认为是明朝灭亡之根本原因。明朝既已灭亡,汉族文人即将救挽天下之希望寄托于儒学复兴。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人的努力,至康熙年间,叶燮最后完成了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叶燮的《原诗》可谓传统诗学之集大成,对文学变革之规律、文学创作中主客观条件及关系、意境和形象思维、文学批评、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等问题皆有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而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贯穿始终。叶燮认为,以在“我”之“才”、“识”、“胆”、“力”衡在物之“理”、“事”、“情”,合而即为作者之文章。其诗学体系中之“情”,绝非一己之情,而实侧重于“志”,或近于黄宗羲所谓“万古之性情”、“孔子之性情”。在更深的层次上,儒家诗学之复兴实际上蕴涵着道统和政统的冲突,蕴涵着道义尊严和世俗功名的矛盾。文与道之关系,此前多有论述,然只有在清代才有如此特殊的意义。文与道的矛盾使统治者所倡导而成为时代审美风尚的“雅”走向“变雅”,儒家诗学由复兴走向变异,文学发展又走过了一个轮回。
【 注 释 】
①④⑤⑥⑧⑨B12B22B23B28B29B3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14—15、98、40—41、58、96、23、238—239、98、211、14—15、14页。
②③⑦⑩B11B27B30B45B46B47B48B49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8、756—757、1079、399、446、534、148、1167、1172、1095、1171、1192页。
B13B14B20B2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1、1页。
B15黄宗羲:《留书》,《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B16B34B52B56B57B58B59B61B63B64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55、92、18、50、31、15、108、48、86页。
B17全祖望:《鲒埼亭集》,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B18章太炎:《说林·衡三老》,《民报》1906年第9号。
B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B24B26王夫之:《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65—567、669页。
B25王夫之:《黄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38页。
B32B33黄宗羲:《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41页。
B35B37B38B39B4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41、912—913、1066、964—965、1067页。
B36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第1996年版,第121页。
B41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79—980页。
B42B43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97、898页。
B44B65B66B68B69B70B71B72B73B76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69、299、377、393、384、325、326、310、393、511页。
B50顾炎武著,徐嘉笺注:《顾诗笺注》清光绪,山阳徐氏味静斋 23—27 年刻本,第51页。
B51B53B54B60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7、338、336、363页。
B55黄宗羲:《金石要例》,《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B62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B67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41页。
B74王夫之:《诗绎》,《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6版,第808页。
B75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51页。
(编校:余学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