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谱对唐宋词选的接受
——以词调与例词的选录为中心
2016-06-16甘松
甘 松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明代词谱对唐宋词选的接受
——以词调与例词的选录为中心
甘松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唐宋词选为明代词谱的创制与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词学筌蹄》直接脱胎于《草堂诗余》;《诗余图谱》较之《草堂诗余》,新增不少词调和词作;《词体明辨》从《花间集》、《尊前集》、《花庵词选》等词选中采录大量词调、词作,既是建设词谱的需要,也反映明人对《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重视。
[关键词]明代词谱;唐宋词选;接受;词调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明代词创作与词学水平整体不高。近年来,随着明代词学研究深入推进,学界对明代词及词学的评价趋于理性与客观,认为明人在词学方面探索与建设的功劳不容抹杀,相关论著多有出版,如江合友《明清词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张若兰《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中华书局,2013年)、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明代词谱的创制与完善即为其中一端。在唐宋词乐失传的背景下,音乐谱已不可得或不可知晓,文字格律谱的编制则日益提到词学建设的议事日程,明人曾依托唐宋词选等词学资源编纂《词学筌蹄》、《诗余图谱》、《词体明辨》等多种词谱,《草堂诗余》、《花间集》、《尊前集》、《花庵词选》等唐宋词选对明代词谱的创制与编纂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本文试以明代有代表性的词谱为例,重点就其对唐宋词选中词调及例词的选录等情况展开探讨。
一、《词学筌蹄》:脱胎于词选《草堂诗余》的词谱
明代张綖编纂的《诗余图谱》曾被人认为是第一部词谱。明末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云:“维扬张世文《诗余图谱》七卷(按,应为六卷),每调前具图,后系辞,于宫调失传之日为之规规而矩矩,诚功臣也。”[1]清初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亦云:“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2]658张綖首先创制词谱的观点曾广为学者所接受。近年,随着明代词学研究的深入,张仲谋先生撰文指出,明人编纂的第一部词谱不是《诗余图谱》而是周瑛的《词学筌蹄》。[3]《词学筌蹄》以抄本形式流传,明代以来的目录书少见著录。当前比较常见的《词学筌蹄》是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本。
《词学筌蹄》编者周瑛(1430—1518),字梁石,晚号翠渠,福建莆田人。其生平事迹见《明史·儒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四库全书》本《翠渠摘稿》卷八附录郑岳所撰《本传》等。周瑛是一位理学家,不以诗文名世,今存词数首。《词学筌蹄》卷首有林俊《词学筌蹄序》,介绍该书编纂过程及体例:“旧编(按,当指《草堂诗余》等词选)以事为主,词系事下,平侧长短未易以读。蜀藩方伯、吾乡周先生翠渠以调为主,事并调下。调为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读以小圈,以便观览。……调凡若词干凡若干(据上下文意,当为“调凡若干,词凡若干”),厘为八卷。后学程度,较胜旧本,名曰《词学筌蹄》。阅而序之如此。弘治九年岁在丙辰,见素子莆田林俊书。”[4]宋原刊本《草堂诗余》早已佚失,周瑛等人在弘治初年所见的《草堂诗余》可能有两种刊本,一为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遵正书堂刊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一为明成化十六年(1480)刘氏日新书堂刊本,该本源自洪武本,题名,卷次,选录词作与洪武本相同,所以周瑛所依据“旧编”当是洪武本《草堂诗余》。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分前集二卷,后集二卷,共录词367首。此书是为应歌之需而编辑的唱本,为便于演唱者根据不同需要选择相应词作,故书中词作分类编排,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大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柳禽鸟七大类,每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甚为繁复。《词学筌蹄》的编纂目的是为初学填词者提供帮助和方便,所以改为按调编排,将词题附于词作之后,并且自创谱式符号,“圆者平声,方者侧声,读以小圈,以便观览”。卷一所录词调《醉花阴》谱式如下:
□□○○○□□。□□□○□。○□□○○。□□○○□□○○□。 ○○□□○○□。□□○○□。□□□○○。○□○○。○□○○□。 重阳
右谱一章十句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喷金兽。佳节又重阳,宝枕纱厨半夜秋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右李易安
《醉花阴》双调五十二字,前段五句,三仄韵,二十六字,后段同。上面的谱式对句读、平仄的标识一目了然,大体正确,但也有失察之处,如“瑞脑喷金兽”的“喷”字当为“销”,平声。此外,有的字可平可仄,没有标出,叶韵之处也未标志。可见《词学筌蹄》作为词谱是相当粗糙的,时有讹误,词谱草创之初恐怕在所难免。
早在宋代,随着词与音乐的逐步脱离,某些词人已开始唱和、模拟名家词集,将之作为创作范本。例如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唱和《清真集》,按照清真词作的平仄四声和韵依次填之,实际上已将《清真集》当作词谱看待了。这种创作方法在明代也甚为常见,如明前期著名词曲家陈铎有词集《草堂余意》,就是次韵唱和《草堂诗余》而成,明人张杞也有《和花间集》。明代前中期《草堂诗余》流行,明人将其改编成填词范本——词谱,就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周瑛明确交代编纂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学者按谱填词”提供范本:“《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5]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涉及词调182调,选词367首,《词学筌蹄》录词调176调,录例词354首。将《词学筌蹄》与《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据吴昌绶等《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二书所涉词调、词作比照一番,可以看出《词学筌蹄》的词调、例词来源以及编排上的某些特点。
《词学筌蹄》中的词调基本上源自《草堂诗余》,词调编排初看杂乱无章,但似乎有“以类相从”的考虑,即将词调中有相同或相近词语的排在一起。如卷一开头《瑞龙吟》、《水龙吟》、《丹凤吟》、《塞翁吟》4个词调的尾字均为“吟”字,接下来《帝台春》、《武陵春》、《绛都春》、《沁园春》、《汉宫春》、《海棠春》、《画堂春》诸词调尾字均为“春”字;卷二所列《青门引》、《华胥引》、《如梦令》、《梅花引》、《江城梅花引》、《六幺令》、《千秋岁引》、《阳关引》、《声声令》、《探春令》、《木兰花令》、《惜余春慢》、《丑奴儿令》、《品令》、《声声慢》、《石州慢》、《浪淘沙慢》、《潇湘逢故人慢》、《拜星月慢》、《兰蕙芳引》等26个词调,调名尾字多为“令”、“引”、“慢”字;卷四所列《天仙子》、《卜算子》、《捣练子》、《江神子》、《风流子》、《女冠子》、《八六子》、《更漏子》、《何满子》、《南柯子》、《南乡子》、《行香子》、《生查子》、《清平乐》、《西平乐》、《大圣乐》、《齐天乐》、《永遇乐》、《倾杯乐》等22个词调,调名尾字多为“子”、“乐”字,这种编排方法与明代后期的《啸余谱》颇有近似之处,只不过《词学筌蹄》尚未形成明确的体系。
《词学筌蹄》对词调的同调异名现象没有予以辨析。《草堂诗余》所涉词调中就有同调异名的现象,如《念奴娇》与《酹江月》,《玉楼春》与《木兰花令》,《菩萨蛮》与《重叠金》,《庆春泽》与《高阳台》,《桂枝香》与《疏帘淡月》等,作为词选,调名重出的问题不算太大。但是,作为词谱的《词学筌蹄》却不予以辨析,实足成为明显的疏误。
将《词学筌蹄》与《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所录词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书同一词调下所录词作基本相同,《词学筌蹄》在《草堂诗余》一书基础上进行了少量增删,如补录苏轼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但《词学筌蹄》也往往照抄《草堂诗余》的错讹之处,如《草堂》所录词作误题作者的情况较多,《筌蹄》几乎全盘照搬,跟着出错;《草堂》所录词作多不署姓氏作者,易让读者误认为是承前省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筌蹄》也不细察,故产生不少作者误题的情况。明代第一部词谱《词学筌蹄》由宋代词选《草堂诗余》脱胎而来,虽然该书比较粗糙,错漏甚多,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二、《诗余图谱》:增补《草堂诗余》未收的词调词作
与《词学筌蹄》比,张綖的《诗余图谱》也是在学习、借鉴《草堂诗余》等词集选本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但其体例更为细密、完善,影响也更大一些。
张綖(1487—1543),字世文,号南湖居士,江苏高邮人,其词学著述有《草堂诗余别录》、《诗余图谱》、《南湖诗余》等数种。《诗余图谱》三卷,初刻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张仲谋先生在台北“国家图书馆”见到明嘉靖十五年《诗余图谱》初刻本,并撰成《张綖〈诗余图谱〉研究》一文,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后又多次重刻。通行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谢天瑞《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十二卷,前六卷为张綖《诗余图谱》,后六卷为谢天瑞所增补,今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此外还有明末毛氏汲古阁《词苑英华》本。
词调的编排方式是编纂词谱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唐宋时期的部分词集即按宫调编排,按理说,词谱按宫调编排应是合理的选择,但在词乐失传、词已成为案头文学的大背景下,按宫调编排的难度较大,也不便初学者。明代词谱《啸余谱》对词调的编排,尝试根据词调名的字面意进行分类编排,没有把握住词调的体式特征,也不太可取。张綖找到了简便易行的方法,即以字数为标准,将词调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编排,《诗余图谱·凡例》指出:“词调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词,故谓之填词。今著其字数多少,平仄韵脚,以俟作者填之,庶不至临时差误,可以协诸管弦矣。”[6]张綖首创的“三分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清代词谱大多采用小令、中调、长调三类编排词调。
《词学筌蹄》已经开创前列图式,后附词例的词谱形式,张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试举卷一对《菩萨蛮》的标注:
《菩萨蛮》 一名《重叠金》,一名《子夜歌》,又与《醉公子》相近
前段四句四韵二十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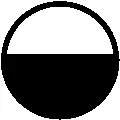
后段四句四韵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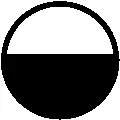
词李太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阑干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可以看出,《诗余图谱》每调先标示平仄谱式,平声用○,仄声用●,平而可仄者用,仄而可平者用,还标明词调的句数、字数、换韵情况,同调异名的现象也得到辨析。《诗余图谱·凡例》云:“词有同一调而名不同者,盖调有定格不可易,名则可易。如东坡赤壁《念奴娇》因末有‘酹江月’三字,后人作此调者,即谓之《酹江月》,又谓之《赤壁词》,又谓之《大江东去》,因其一百字,又谓之《百字令》之类是也。亦有同义易之者,如《蝶恋花》谓之《凤栖梧》、《鹊踏枝》,《红绣鞋》谓之《朱履曲》之类是也。今皆列注名下,云‘一名某,一名某’,使览者知其同调。”[7]这种谱式考虑到词调的多方面特征,对填词者的确会有较大帮助。
明代《草堂诗余》流行,颇受读者重视。有证据表明,张綖作词、选词以及编制词谱的词学活动与《草堂诗余》都有密切关系。张綖于嘉靖十七年(1538)编成《草堂诗余别录》一书,这部小型词选共选录唐宋词79首,选录词人40余家,苏轼入选13首,秦观入选8首,远多于其他词人的选词数量(其他词人大多只选录一、二首作品),《别录》所选北宋词明显多于南宋词,这与《草堂诗余》的选词倾向基本相符。张綖《别录》自序明确指出,其编选《别录》的目的是删除《草堂诗余》的“猥杂不粹”之作,而保留“平和高丽之调”:“歌咏诗余者,唐宋以来之慢调也,吴文节公(吴讷)于《文章辨体》亦有取焉。虽亦艳歌之声,比之今曲,尤为古雅,故君子尚之。当时集本亦多,惟《草堂诗余》流行于世,其间复猥杂不粹。今观老先生朱笔点取,皆平和高丽之调,诚可则而可歌。复命愚生再校,辄敢尽其愚见,因于各词下漫注数语,略见去取之意,别为一录呈上。倘有可取,进教幸甚。”[8]朱崇才先生认为,根据序中语气和“老先生”等称谓来看,《别录》很可能是张綖年轻时学词的“作业”,“老先生”极有可能就是他学词时的业师王磐(号西楼)。[9]张綖曾从同乡前辈王磐学习词曲,朱曰藩《南湖诗余序》曰:“先生从王西楼游,早传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第几声,出人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10]84从二篇序言可看出,张綖在创作上比较注意词体的音律规范,这为其编纂词谱奠定了较高的词学素养。
《诗余图谱》初刊于嘉靖十五年(1536),在此之前张綖能够见到的《草堂诗余》版本一为洪武本,一为成化十六年(1480)刘氏日新书堂刊本。由于成化本源自洪武本,所以张綖阅读、研习的《草堂诗余》当为洪武本。兹将二书所录词调、词作予以比照,就会有所发现。《诗余图谱》共录词调149调,例词223首。张綖对《草堂诗余》所涉词调及所选词作的借鉴、增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诗余图谱》沿用《草堂诗余》已有词调,但抽换了所录之词。如《草堂诗余》中《长相思》一调,选录的是冯延巳“红满枝,绿满枝”和李煜“一重山,两重山”二首词作,《诗余图谱》则将冯词更换为张先的“蘋满溪,柳绕堤”一词;又如《清平乐》一调,《草堂诗余》原选赵令畤“春风依旧”一词,张綖换为黄庭坚“春归何处”与韦庄“春愁南陌”二词。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词调下录有多首词作,每首词代表了不同的体式,如《南乡子》一调录词3首,苏轼“霜降水痕收”词为双调五十六字,前后段各五句四平韵;李珣“烟漠漠”词为单调三十字,六句两平韵三仄韵;欧阳炯“画舸停桡”词为单调二十七字,五句两平韵三仄韵。这表明,张綖选录词作时已经注意到同调异体现象,虽然尚未象后世词谱(如万树《词律》、《康熙词谱》)中明确标示“又一体”,但其编纂词谱时已经有意选择更多体式的词作以备读者参考。
《草堂诗余》无相应词调,《诗余图谱》新增了若干词调、词作。新增词调为:《上西楼》、《恋情深》、《绣带子》、《望仙门》、《相思儿令》、《洞天春》、《秋蕊香》、《醉红妆》、《恋绣衾》、《钗头凤》、《唐多令》、《系裙腰》、《金蕉叶》、《定风波》、《凤衔杯》、《黄钟乐》、《解佩令》、《谢池春》、《看花回》、《感皇恩》、《殢人娇》、《两同心》、《小桃红》、《连理枝》、《粉蝶儿》、《忆帝京》、《师师令》、《剔银灯》、《御街行》、《一丛花》、《山亭柳》、《柳梢新》、《拂霓裳》、《雪梅香》,共计34调。如新增《恋情深》词调,录五代毛文锡词一首;《绣带子》词调,录黄庭坚词一首;《相思儿令》词调,录晏殊词一首;《洞天春》词调,录欧阳修词一首;《醉红妆》词调,录张先一首;《恋绣衾》词调,录陆游词一首;《黄钟乐》词调,录五代魏承班词一首;《御街行》词调,录柳永词一首;《山亭柳》词调,录晏殊词一首。值得注意的是,《草堂诗余》本有相应词调,张綖并未采录,如若干常见常用词调如《西江月》、《如梦令》等,《诗余图谱》却未收录,不知何故。
从词调与例词的选择来看,张綖编纂《诗余图谱》时,词学视野已较开阔,不再局限于《草堂诗余》一书,还参考其他唐宋词选或词集文献。如《诗余图谱》所录词调《黄钟乐》,仅见《花间集》魏承班一首,宋之后别无作者,所以,张綖编《诗余图谱》时参考过《花间集》,当属无疑。张綖还从《花庵词选》、《乐府雅词》等总集以及词人别集中选录了部分词作,进一步充实《诗余图谱》的词例。有意思的是,《花间集》中有诸多词调可供增补,《诗余图谱》却未予充分采录。稍后的《词体明辩》则充分重视和收录《花间集》、《尊前集》等词选中的词调,弥补了这一缺憾。
三、《词体明辨》:增录《花间集》、《尊前集》等词选中词调
张綖《诗余图谱》问世三十余年后,又有一部词谱问世,并在《诗余图谱》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这就是徐师曾编纂的《词体明辨》。徐师曾(1516—1580),字伯鲁,号鲁庵,江苏吴江人,一生勤于著述,撰著颇丰,著有《文体明辨》等。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明,其书乃据明初吴讷《文章辨体》一书增删订补而成。该书《附录》卷三至卷十一为《诗余》部分,列出词体谱式,实际上是一部词谱。如清人沈雄指出:“柳塘词话曰:徐师曾鲁庵著《词体明辨》一书,悉从程明善《啸余谱》,舛讹特甚。”[11]806张仲谋先生指出,《文体明辨·诗余》这部分后来很可能以名为《词体明辨》的单行本行世,却受到人们误解,因为程明善《啸余谱》中词谱内容乃是辑录徐师曾《词体明辨》而成的,可能因为《文体明辨》卷帙繁重,传本甚少,前人未细察二者关系而导致误解。[12]
徐师曾编纂《词体明辨》时,张綖《诗余图谱》已开始流行并产生影响,所以《词体明辨》对《诗余图谱》多有取资借鉴,并提出自己制谱的新思路。其《诗余序》曰:“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句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过,则本方之意失矣。此《太和正音》及今《图谱》之所为作也。然《正音》定拟四声,失之拘泥;《图谱》圈别黑白,又易谬误。故今采诸调,直以平仄作谱,列之于前而录词其后。若句有长短,复以各体别之。”[13]序言中可看出,徐师曾对《诗余图谱》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不同意其用黑白圈的方式标示平仄。《词体明辨》在词调编排方式上,也没有借鉴张綖按照小令、中调、长调的编排方法,而是采用以类相从的标准,将词调按“歌行题”、“令字题”、“慢字题”、“近字题”、“犯字题”、“遍字题”、“儿字题”、“子字题”、“天文题”、“地理题”、“时令题”、“人物题”等25类排列。这种编排体例与明前期《词学筌蹄》的词调编排方式有近似的地方,但显得更为细密周详;与《诗余图谱》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相比,则显得繁复冗杂,有些混乱。例如,“令字题”至“子字题”是按词调名末字相同者分类编排,“二字题”至“七字题”则是以词调名字数分类编排,读者就不免疑惑:“子字题”中所列词调名都是三个字,如何不列入“三字题”中?所以《词体明辨》的词调编排方法并不合理,不便检索和使用,所以此种词调编排方式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和仿效。但是,《词体明辨》在平仄标注方式上进行变更,并明确列出同调异体的谱式,成为该谱的显著特点和创新之处,这种制谱体例对后世词谱编纂者有较大启示,如清代《词律》、《钦定词谱》处理同调异体时,即标注为“又一体”。
《词体明辨》所录词调数较《诗余图谱》(嘉靖初刊本)明显增多。《词体明辨》共录词调329调,421体,与《诗余图谱》所录词调比照,可以发现《词体明辨》将《诗余图谱》所录词调悉数收录,仅《阮郎归》、《桃源忆故人》等词调未收。《词体明辨》较《诗余图谱》新增一百多个词调,这部分词调和例词从何而来呢?
《词体明辨》参考了《花间集》、《尊前集》、《花庵词选》等唐宋词选,并从中大量采录词调、例词或其他词学资料。例如,《荷叶杯》、《上行杯》、《杨柳枝》、《竹枝》、《归国遥》、《柳含烟》,《赞成功》、《献衷心》、《定西番》、《接贤宾》、《感恩多》、《西溪子》、《赞浦子》等词调乃从《花间集》中采录,词调后的例词也从《花间集》中选录。该书所列《荷叶杯》谱式中的4首例词,均录自《花间集》;又如《竹枝》一调,共录词8首,其中刘禹锡、白居易所作的5首录自《尊前集》;《杨柳枝》一调,录词5首,刘禹锡所作2首录自《尊前集》,其他3首录自《花间集》。《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标志着词体文学在文辞、风格、意境等方面文体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也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词体明辨》从《花间集》中大量采录词调和例词无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对进一步丰富词谱中的词调具有积极意义。
《词体明辨》还注意参考《花庵词选》。如《雨霖铃》一调,录柳永“寒蝉凄切”词,当取自《花庵词选》;又如“歌行题”《瑞龙吟》一调附周邦彦“章台路”词,词后有注文:“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此谓之双拽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今诸本皆于‘吟笺赋笔’处分段者,非也。”[14]103其实,此段文字录自黄升《花庵词选》对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一词的尾批。
除了唐宋词选,《词体明辨》也采录其他词集所涉词调与例词。值得注意的是,《词体明辨》中新增的《千年调》、《昭君怨》、《六州歌头》、《锦帐春》、《寻芳草》等词调,例词都只选录辛弃疾词,当是依据稼轩词集录入的。《草堂诗余》选词较多的是周邦彦、秦观、苏轼、柳永等人,辛弃疾仅有10余首词作入选,《词体明辩》收录辛词多达40余首,数量仅次于北宋周邦彦词,这表明明代中后期,稼轩词受到词坛的注意,制谱者也及时跟进。
总体而言,从《词学筌蹄》到《诗余图谱》,再到《词体明辨》,明代词谱所录词调与例词趋于丰富,参考的唐宋词选等词学资料趋于多样,制谱的体例也趋于细密,为清代词谱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M].明末翁少麓刊本.
[2]邹祗谟.远志斋词衷[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张仲谋.《词学筌蹄》考论[J].中国文化研究,2005,(秋之卷).
[4]林俊.词学筌蹄序[M]//词学筌蹄.续修四库全书.
[5]周瑛.词学筌蹄序[M]//词学筌蹄.续修四库全书.
[6]张綖.诗余图谱[M].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五年刊本.
[7]张綖.诗余图谱[M].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十五年刊本.
[8]张綖.草堂诗余别录[M].明嘉靖二十六年黎仪抄本.
[9]朱崇才.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J].文学遗产,2007,(1).
[10]朱曰藩.南湖诗余序[M]//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沈雄.古今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张仲谋.论徐师曾《词体明辨》的词谱性质——兼论《啸余谱》与《词体明辨》之关系[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13]徐师曾.文体明辨[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4]黄升.花庵词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何旺生)
Acceptance of Anthologies of Tang-Song Ci by Cipu of the Ming Dynasty
GAN Song
(schoolofHumanities,HefeiNormal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Anthologies of Tang-Song Ci provide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pu in the Ming dynasty. Ci Xue Quan Ti derived directly from Cao Tang Shi Yu. The majority of cases in Shi Yu Tu Pu of ZHANG Yan are from Cao Tang Shi Yu, which XU Shi-zeng had selected from Hua Jian Ji.
Key words:Cipu of the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of Tang-Song Ci; acceptance; Ci tune
[收稿日期]2016-0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唐宋词选的接受与明代词学演进”(12YJC751016),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词集序跋整理与研究”(SK2012B381),安徽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宋代词集序跋研究”(2011SQRW102)
[作者简介]甘松(1979-),男,湖北公安人,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诗词学。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6)02-006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