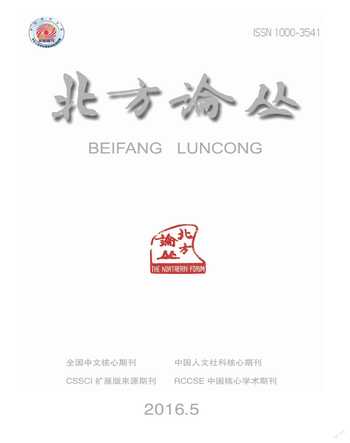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2016-06-09田瑞文
田瑞文
[摘 要]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关键词]阮元;四书文;文統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76-05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1](p.609)这一观点多为学者所批评,章太炎以为阮元假孔子《文言》耦丽,并牵引文笔说,借以证成,适足自陷[2](p.51)。今人在骈文学术研究中,也多视此为“偏激的思想”[3](p.131)或“错误结论”[4](p.441)。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骈文研究视野中,多数学者将这一问题置换成骈文为文之正统说,这种置换看上去比较合理,能够把阮元的这一观点放到骈文史叙事范畴中讨论,但显然阮元想要表达是四书文(即八股文)而非骈文为文之正统,在八股文为人所激烈批评的学术背景下,阮元的这个观点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但阮元确是此意。实际上,阮元提出四书为文之正统的观点,既与他的政治经历和学术认识有关,也与阮元独特的文学观念有关。
一、阮元的四书文观
阮元如何看待四书文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关于四书文的批评中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
四书文又称八股文、八比文、时文、制艺等,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八股文的写作有着严格的程序限制,在修辞上要求对偶、排比,这八股是文章的主体部分[5](p.14)。始于明初的八股取士,其目的一如朱元璋的诏书所言:“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6](p.1695)在正统到嘉靖之间,八股作者确实也多能做到“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7]。但明后期至清以来,八股文却多为人们所批评。清康乾之际,朝野之间也不乏废弃八股取士的声音,比如康熙曾下令:“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8](p.145)乾隆三年(1737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9](p.3150)从康熙和舒赫德的言论来看,八股文之弊端在于不切实用,是无涉政事的空言。清末康有为在西学背景下的废除科举之议对这一弊端有更为全面的总结,他的基本思路是“立法之始,意美法良”。然而,“凡法虽美,经久必弊。”他认为,科举之业,“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且“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对于这一取士之法,康有为的认识颇为清醒,“昔在闭关之世,或以粉饰夫承平;今当多难之秋,不必弊精于无用”[10](pp.78-80)。康有为所说的“粉饰承平”,与鄂尔泰反对舒赫德的观点具有内里相通之旨:“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11](p.67)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要求,康熙在下令废八股取士后很快重又恢复,而舒赫德的谏议也被礼部的“议复”所驳回。
这个虽颇遭反对,但终明清两朝一直未曾废除的取士制度,其存在的深层原因是它符合封建官僚统治的人才选拔要求。主要有两点表现:其一是这种以《四书》为考试范围,以朱子之义为解释原则的主题要求,保证了封建思想认同的统一性;既保证了所选之士中绝大多数者能与朝廷同心,同时又使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们在日常的温习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王朝的统治思想,从而有助于加强士民对王朝统治的认同;其二,八股文程序化的写作训练,也有助于朝廷公文的处理,尤其是“台阁之制,例用骈体”[12](p.19),这是因为要“用文字的排比来象征威权的气象”[13](p.330)。因此,骈偶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形式的问题,这种形式本身对官府文诰来说,也代表着一种威严。骈文写作非经严格的训练,是不能轻易而成的,八股文的摹写恰好能提供这种文字写作训练。其实,八股文不仅仅训练了士人的骈对写作能力,同时八股文写作的逻辑训练也有助于其他文体的写作。王士祯曾问汪琬某名诗人诗多格格不达,汪琬认为:“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王士祯接着讲:“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14](p.300)《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虽是个小说人物,但他那番话却颇合实际:“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15](p.122)鲁编修的这番话在文章写作技巧层面是成立的。
生活于清代乾嘉道盛世之际的阮元,对用于科举取士的四书文是极其熟悉的。在先后就学于贾载清、江振鹭、胡西棽、栗溥、乔书酉、李道南等名师后,阮元于16岁开始参加童子试,23岁中式乾隆五十一年(1781年)丙午科江南乡试第八名举人,26岁己酉恩科会试第二十八名,殿试二甲第三名,27岁散馆钦取一等第一名,28岁大考钦取一等第一名,擢詹事府少詹事,南书房行走,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在这十来年的考试中,阮元的表现非常突出,而这优异成绩的背后,不难想象阮元对四书文的谙熟程度。走向仕途的阮元,也多次主持各级考试,评阅考生的试卷。乾隆五十八年(1786年),30岁的阮元简放山东学政,两年后,调任浙江学政。在学政之任上,辗转各地,按试诸府,衡文校士,多拔英杰。乾隆五十九年(1787年)秋,阮元的恩科会试座师铁保典试山东,诗赠阮元云:“六千髦士汇群英,半是宗师作养成。我向齐州悬玉尺,门生门下中门生。”(铁保《劝赠阮学使伯元》)虽曰戏作,却也较合实情。嘉庆四年(1799年),36岁的阮元充经筵讲官,寻奉旨充会试副总裁,是场“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在“闱中阅卷之暇”,阮元还作了《衡文琐言》一卷,对自己衡文的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总结[16](p.21)。嘉庆十七年(1812年),阮元奉旨派阅大考翰詹卷。在此后出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时,多次监临场屋。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阮元直经筵讲师,奉旨派讲《四书》论[16](p.193)。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83岁的阮元虽已致仕归乡有年,但朝廷似乎并没有忘记这位为大清科场做出重大贡献的宿儒,在道光帝的批准下,阮元重赴鹿鸣宴,晋加太傅衔,诚如梁章钜所说:“如斯旷典,前此所未闻。”[17](p.17)这既是对阮元一生为大清镇守地方的肯定,也是对阮元为大清科举事业所做努力的认可。可以说,阮元一生都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而他所写、所阅、所讲的四书文也几与之相伴终生。
但出人意料的是,阮元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不喜作时文”的观点。道光四年(1824年),61岁的阮元在和儿子阮福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幼时,即不喜作时文,塾师曰:‘此功令也,欲求科第不得不尔。俗谕谓之敲门砖,门开则弃之,自获解后即不恒作。尔既不能为此,亦不能闲居食粟,当改学经史诗文。”[18]在现有文献材料中,虽然直到60岁左右,阮元才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喜时文的观点,但他这种不喜时文的表现却早已有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19岁的阮元在家持服时,既已“屏去旧作诗词时艺,始究心于经学”[16](p.6)。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丙午科乡试阮元以第八名中式,而这次乡试的典试者正是“每握文衡,必合观经策,以精博求士”[19](p.292)的朱珪。可以说,对经学的趋向和对时文的有意无意的偏离,是阮元得以中式的一个重要原因。饶有意味的是,嘉庆四年(1799年),36岁的阮元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而会试的主考官正是他的座师朱珪。在这场考试中,师徒二人将“取士重经策”的选士原则发挥到极致,“是科二三场文策,大兴朱公属先生一人批阅,乃选出长策一千三百余卷,穷三日夜之力,再选出二百卷,分为三等,以观头场,名士经生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也”[16](p.21)。清代内帘阅卷虽然允许“首场平通而二三场辞理博雅,断据详明者,并与收录”[20],但显然朱、阮二人的做法与以头场四书文为重的常例相左。这自然引来一些人的不满,是场同考官汪镛在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道奏章中,即攻讦朱、阮“阅三场策卷后面先有墨笔记注,圆尖点实,实属违例。”嘉庆上谕认为,汪“所奏甚是,嗣后着考试官恪遵定例,先阅头场,后阅二、三场”,自此之后,“天下士子咸以通经博士为讳”[21]。道光十三年(1833年),70岁的阮元再次奉谕充会试副总裁,而正考官则是“深嫉迂诞之学”[22](p.229)的曹振镛。在俞正燮的选录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阮元欣赏俞正燮折中群言的经义策问,“及榜发不见名,徧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曹振镛)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23](p.220)。两度会试副总裁,相差近三十年,但阮元不重时文重经义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同样,在阮元所创设的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他也力倡“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用八比文、八韵诗”[16](p.41)。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已经79岁的阮元在给梁章钜的一封书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八股文的看法:“弟生平最怕八股,闻人苦读声谓之为唱文,心甚薄之。故不能以此教子弟,子弟竟以不能攻此,未有科名。”[24]这似乎与18年前对阮福所说的那番话构成一种响应,在时文和经史之间何以立身的问题上,阮元似乎也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
在这种世俗经济和学术理想、置身于内和意欲超越的冲突中,阮元态度的表达虽然比较明确,但他的行事却每有与之相左之处。如果说阮元读书求仕与政治参与,让他无法与时文截然两分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那么他在某些时候的一些言论和做法,则似乎又表明了他对时文的认可。他不仅发表了四书文为文之正统的观点,而且大约从60岁左右开始着手编订《四书文话》,虽然大约此时,他刚对阮福说过“我幼时,即不喜作时文”的话。经过“廿年”的编订,在他79岁时,他将仍未完成的书稿寄给梁章钜,请其为之订正。
阮元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和他对四书文功用的不同理解有关。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阮元认为,时文选才的导向限制了人们知识视野的扩展,自然也就陋于体用。早在阮元11岁时,父亲就告诉他:“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1](p.365)阮元的乡贤如汪中、王念孙等,交友如凌廷堪、孙星衍等,多博通经史,生于其间的阮元自然也形成了不拘时文的观念。这种观念对阮元知识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观阮元一生阅读与著述,经、史、子、集无一不涉。而他无论是在诂经精舍,还是“仿照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的学海堂的教授中,也都极力主张“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25](p.2)。在经史致用的观念下,阮元超越了时文的限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世界,在博学通儒明体达用的人生成就感中,完成了努力与收获的平衡。在这种人生设计中,时文达宦并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虽然阮元本人是时文达宦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阮元对时文的超越是建立在经史经世人生价值实现的基础上的。但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作为封疆大吏、朝之重臣的阮元又充分地肯定了四书文的功用。他在《四书文话序》中,对此有着清楚表述:“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1](p.1069)因此,阮元虽心薄八股,“然又以为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24]。
二、阮元文统观的形成
阮元肯定四书文,既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关,也与他的文统观有关。在阮元看来,文章之义应主要由经疏、子、史来承担,而文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完成。单独来看,阮元的文统观自成体系,但同时也应该明白,这只不过是阮元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阮元这种文统观的形成导源他对经、子、史与文的不同功用的区分。
阮元的学问之境,使他对一般的问题,往往有更为超越俗常的认识,因此,他的某些结论不能作为一般的泛泛之论,而应当放到他的学问结构中去评说,才能曲尽阮元本意。阮元的知识涵盖经、史、子、集,举凡经、史、小学、金石、天部、地理、算法、词章、书画等皆有涉猎,且每有的论,如论书,既从史论的角度,指出南北书派的消长,以及“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的原因,同时又在“旧碑新出甚多”[1](p.591)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提出了南北书派的新观点,将王派由书之正统推到一个流派的位置上,同时大大提高了魏碑的地位,改变了当时书学史的叙事格局。“阮元以经学大师问鼎书法,提出‘南北书派之说,并非信口开河,故意樹立异端,”而是“以史家的睿智,朴学的功力,考据的精细”[26](p.540)提出这一观点的。这就形成了阮元较为独特的思维特征,即对待学问知识,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这显然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正因为阮元的知识渊博,所以能够对某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也正因为阮元的知识所涉领域之多,所以,阮元对每一个领域的向学者都多加肯定,并给以导引。如“(周)治平拙于时艺,久屈于童子试,余至台州,治平握算就试,特拔入学。治平精于西人算术,通授时宪诸法,明于仪器”[27]。并使周治平入诂经精舍学习。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阮元任满奉调回京,友人在为之送行时,对其在浙三年的成绩予以评价:“自公在浙,浙人士沐浴教泽,若弟子之于其师,各得随所,分际成学以去。公学无所不通,而尤深于经……其取士也,不循一格,经生常业外,如天文、律历、步算之术,以及词章书画之伦,茍有一长,无不录也。”[28]其后,阮福不善四书文,阮元即属其“当改学经史诗文”[29]。但在众多知识领域中,阮元尤属意于经、史、诗文。他不仅自己勤力于编纂《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等文献,并且在教育中也特别强调经史的重要性。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试浙江优行生员的《策问》中即提出:“士之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这一问题。次年,阮元在《浙士解经录序》再次谈到类似话题,“朱石君师谓元曰:‘经解、诗赋最易得人。故元之以经覆试也极勤”[30]。嘉庆十二年,阮元与王引之“捐廉购《十三经注疏》百余部,分置各学,教士子以根柢为务”[31]。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阮元“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16](p.132)仍是这一导向。嘉庆十三年(1808年),阮元命其子常生受业于凌廷堪,“每日课经之外,必以司马氏《通鉴》授读,谓熟读此书,则千古以来成败得失之故洞若观火,而他日侍帷幄、备顾问、述往事,以匡时就陈编而悟主,无有过于此者”[32]。由此可见,阮元对经史所承载的“匡时悟主”功能的冀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阮元才将之看作是以表义为主的非文之体,从而相应地建立了自己的文统观。
阮元区分文与非文的标准很简单,即协音成韵与单行直言,“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1](p.605)。进一步说,“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1](p.608)。显然按照阮元的理解,经、子、史都在单行直言之列,不能称之为文。因为单行之言,专意于义,而韵偶之语,长于辞饰。阮元所面对的文统却非如他所解,他当然要予以排摈,“自唐、宋韩、欧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1](p.608)。在阮元看来,唐宋八家古文,非经即子,非子即史,而“号唐、宋八家为古文”以“别于四书文”“骈偶文”的明人,却忘了他们谙熟的“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这才是真正的文。阮元讥之曰:“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为了现身说法,阮元对《书梁太子昭明文选序后》的性质判定是“言之无文,子派杂家而已”[1](p.609)。在谈到另一篇《塔性说》时,阮元也说了类似的话:“此笔也,非文也,更非古文也。”[16](p.156)在与经、子、史的对举中,阮元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文统观,即以声韵、偶对、平仄等修辞手段所写之文方可称之为文。
三、四书文在阮元文统中的地位
阮元所理解的文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四书文正处在这一演进的终端,是文之极胜的代表,自然也被看作是文之正统。
阮元论文立足文之文饰、修辞之初义,强调文的纯粹性。阮元文章观念的逻辑起点为孔子《易·文言》。阮元认为,由于早期书写材料获取的不便,要想达意、行远,必须“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阮元这里所说的“文”,就是修饰文词“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1](p.605)。《周易正义》孔疏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也正是此意。而孔疏认为:“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义理,非是文饰华彩,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33](p.14)实际上,文饰华彩为其外在形态,而释卦为其义理所在,两者并不矛盾,是形、义的统一。阮元执其外在形态而言,其目的仍在文章义理能“使人易诵易记”。也就是说,义理准确、有效的传达需要着力于“象其形”的文,而文之法在阮元看来,就是“用韵比偶”“错综其言”。因此,阮元所谓文就偏指义理表达的技巧性问题,侧重于论说对象的法的讨论,而非义。这就是阮元所理解的文。
沿着这个逻辑,阮元找到的另一个支撑材料是《昭明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是阮元特别精熟的一本书,8岁即在胡西棽的指导下学习《文选》。嘉庆八年(1803年),40岁的阮元在为胡西棽所撰墓志中说:“元幼时,以韵语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选》之学。”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阮元自述“以韵语受知于先生”,这完全可以看作是阮元对《文选》理解的角度,因为他对《文选》的认识是“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1](p.608)。但阮福《文选》不押韵脚者甚多的疑问,也进一步迫使阮元来思考翰藻与音韵之间的关系,阮元的回答是“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韵脚,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1](p.1064)。这番回答实际上本沈约《谢灵运传论》“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34](p.1779)而来。这就将可见之韵扩展到行文的节奏感,进一步扩大了文言翰藻的范围。但同时追求声韵和章句平仄的效果,也将文的极致归逼到四六体上,即阮元所说的“四六乃有韵之文极致”。不过阮元很快就意识到,四六虽为文之极致,但却溺于声律,弱于达义,因此其体渐卑,不过从文统而言,却又是文进一步精致化发展的必然。而四六的比偶对待与声韵相协在明清的四书文中被进一步规范化,以至“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故此“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統也。”[1](p.609)这种变与不变正是阮元“体格有殊,文章无异”[1](p.739)基本思想的体现。从《易·文言》到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阮元所谓的文统指的就是文言翰藻的修辞——声韵、比偶、平仄——之统。
阮元的这种认识既有其不合理之处,也有其合理之处。这种不合理之处在于他的论说逻辑偏执一隅。他认为,出于易传诵需要而文其言是因为书写材料的困乏,“古人无笔砚纸墨,往往铸刻金石,始传久远。其着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1](p.605)。“古人简策,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非如印本经书,家家可备也”[1](p.607)。因此,文言就显得十分必要,且不论阮氏文言之因的论述是否切当,单就文言与书写材料之间的关系演变来说,阮氏之论不能成立,如果说早期因简策书写不易而需要文言的话,那么后来书写材料渐趋丰富、易得,尤其是纸张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广泛为人所用时,阮氏协音、文言以易记诵的强调就忽略了言之传播的另一种主要方式——书于纸张。而书于纸张正是“动辄千言万字”的前提,正是散文可以驰骋的物质基础。所以,从阮元要求于书写物质材料的局限以说文言之必须的论断来看,他的文言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人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阮元意不在此,他的主要目的不过是假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来尊体文言。阮元这种认识的合理性在于,他从文其言的逻辑出发,并一以贯之,逐代推衍,在对文之修辞统绪强调的前提下,从唐宋四六一直推衍到四书文,这样看来,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文之发展的极致,自然也就成了文之正统的代表。也就是说,在文的系统中,四书文是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这个逻辑本身是完整的,因此,在阮元对文之概念的理解中,这一结论也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台阁之制,例用骈体”的需要也是阮元这种文统观存在的现实基础。台阁之文的骈化不仅显示出朝廷的威严,而且骈语丽句的华彩也是王朝雍容华贵的一种外在体现。这样看来,取士之八股不过是官方四六文书的一场预演,敲门成功,等待着这些忙碌于翰林院的士子们的是,大量充斥着四六体的台阁之文,若之前准备不充分,补课也就是必然的了。《骈体文钞》是清代著名的骈文选本,然而,其真正目的却多為人们所忽略,是书序中,李兆洛说:“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12](p.19)所以,无论阮元,还是李兆洛,一旦成为官府人员,自然要向这种体现着官方威仪的文章风格靠拢,这才是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这一观点成立的坚实的现实基础。阮元所谓四书文为文之正统,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体现出其存在价值,具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在阮元的知识世界里,经、子、史皆为壮子,当堪体国经野之大任,而文则是一宠女,主要任务就是自顾自地专心于自己的华丽。阮元对经、史、子、文的区别对待,是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这一观点得以成立的前提。后人在批评阮元骈文观或四书观时,并没有真正理解阮元内心的这种曲结。
[参 考 文 献]
[1]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杨旭辉.清代骈文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王凯符.八股文概说[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M].四库全书本
[8]清实录·圣祖实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C]//康有为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陆保璇辑.满清稗史[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原上海新中国图书局排印本).
[12]李兆洛.骈体文钞·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8.
[13]王瑶.徐庾与骈体[C]//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4]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6]张鉴,等;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梁章钜.太傅衔[C]//浪迹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阮福.揅经室训子文笔·跋[M].清光绪乙亥淮南书局刊本.
[19]陈康祺.朱石君衡文之精[A].郎潜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清光绪十二年本
[21]文廷式.纯常子枝语[M].1943年刻本
[22]张穆.癸巳存稿序[C]//俞正燮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
[23]姚永朴.旧闻随笔[C]//俞正燮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
[24]阮元.答梁章钜书[C]//梁章钜.师友集.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25]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C]//阮元订.诂经精舍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6]王章涛.阮元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03.
[27]阮元.定香亭笔谈[M].清嘉庆五年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刻本
[28]袁钧.送举主浙江学使少宗伯阮公还朝叙[C]//瞻衮堂文集.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29]阮福.揅经室训子文笔·跋[M].清光绪乙亥淮南书局刊本
[30]阮元.浙士解经录·序[M].清嘉庆再到亭刻本
[31]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M].1937年北平来熏阁书店排印本.
[32]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M].程演生《安徽丛书》本.
[33]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系平顶山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